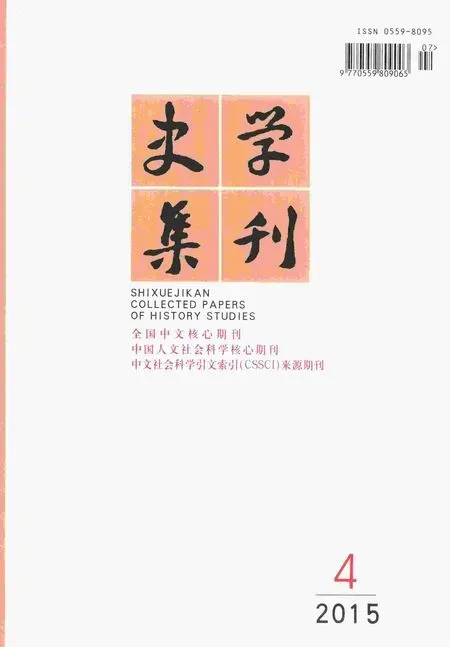《史记》老庄同传发覆
徐 莹
(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河南开封475001)
《老子韩非列传》是《史记》中引起后世争议较多的篇章之一,对于这篇合传,古今学者争论的焦点在于将老子与韩非,也就是将道家和法家的两位代表人物放在一起立传是否得当,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但却少有质疑老庄同传的声音。①李泽厚曾对老庄同传提出过疑问:“《史记》老庄申韩同传。把老子韩非放在一起还好说,因为它们都是社会政治哲学,并在讲阴谋权术上有承接处。把庄子搁在中间,则似乎总有点别扭。庄与老有接近连续关系,但基本特征并不相同。”参见李泽厚:《庄玄禅宗漫述》,《新版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页。个中的原因在于,自汉代以来,老庄并称、同属道家门下,早已成为一种固定的认知模式。
笔者此前曾撰文,从“老庄‘道’论之分殊”、“老庄学说属性之差异”、“以孔学为参照的老庄比较”三个方面,阐述了庄子学说的独立性。②虽然老、庄之学在理论体系的发端处都使用了一个“法自然”的最高本体之道,但它们拿着这一原始的“道”概念,去做了两类性质迥异的事情。老学从自然的规律推导出人世的法则,作为统治者施政的纲领,其学说性质为社会政治学说;庄学由大道的状态提炼出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作为个体生命的寓所,其学说性质是个体生命学说。老、庄从共同的起点出发,最终到达的是两个相距甚远、各不相关的目的地。这一状况犹如站在共同起点上的分道扬镳,当形而上的最高本体之道渐渐向下运行,从天而降地到达人间,老子之道最终成为一种规律和法则,统御人世;而庄子之道则体现为一种个体性的精神境界,安顿心灵。所以,将庄学归入以“君人南面之术”为思想特征的道家学派门下的理论基础是十分值得商榷的。详见徐莹:《庄子学说之独立性研究——以内七篇为中心》,《文史哲》,2009年第6期。从学术史方面考察,先秦时代,庄子和老子也本无关联,庄子归属于老子的道家学派是汉代人所做的学术分野。③徐莹:《庄子学说之独立性研究——以内七篇为中心》对老庄合流的学术史略有论及,指出老庄并称为汉人的学术分野,但未及对此进行详细的梳理,故作此文予以补充。汉人整合老庄的过程中,《史记》对老庄申韩的同传而书,无疑具有开拓性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因此,厘清司马迁归庄入老的原因和依据,对于探讨老庄合流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一、司马迁眼中的庄子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对庄子的记载如下: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讠此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①《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43-2145页。
上引两百多字的庄子传,是一篇极具司马迁个人风格的评传,叙事兼具评述的性质,从中不难看出庄子在太史公心中的形象和地位。对于庄子其人其学,司马迁认为:
其一,庄学虽涉猎广泛,“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庄子·大宗师》论道:“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②郭庆藩:《庄子集释》,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46-247页。这与《老子》所说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③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3页。观点基本相同,即庄子与老子在各自学说的开端处,都使用了“自然”这一形而上的“道”概念。因为老学早于庄学,虽然《庄子》书中从未祖述老子,但司马迁还是认为,庄学根源于老子之学。
其二,庄子“指事类情”,写得一手好文章,但其洋洋洒洒十余万言的著述,在司马迁看来,大多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无稽之谈,其思想学说的特点是“洸洋自恣以适己”,对于现实政治、对于治理人世来说,无所可用。所谓“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④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098页。庄学道论的核心是一种天人合一的个体精神境界,这种出离人世的精神境界是无法用语言进行客观描述的,因此庄子只能用各种意象性的文字,借助种种迷幻的形象和故事进行曲折的表达。《庄子》书中借以传道的多是漫延恣肆、别有寄托的文字,司马迁认为它们不过是寓言而已。而这种出世的学术思想追求的是逍遥自在的精神生活,是不愿、也根本不能与现实政治结合的。司马迁其后举出庄周拒绝“楚威王聘相”之事,突出了庄学适己自得的个体性特征。
其三,司马迁认为,寓言本《庄子》的现实目的和作用在于攻击儒、墨等当世的宿学,特别是诽谤孔子之徒,以此来彰明老子学说。对此,他列举了《庄子》外杂篇中激烈攻击孔学的文章《渔父》、《盗跖》、《胠箧》作为证明。
在《老子韩非列传》末尾的“太史公曰”中,司马迁总结说:“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张大可等学者将“散道德”的“散”字解释为“推演”,⑤张大可、梁建邦:《史记论赞与世情研究》,张大可、安平秋、余樟华主编:《史记研究集成》第四卷,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214页。这种释义显然是受到老庄同门观念的影响,还有待商榷。“散”,其本意为与“聚”相对的“分”,《说文》曰:“散,杂肉也。”《广韵》:“散,诞也。”《韵会》:“不自检束为散。”“散道德,放论”一句,“散”与“放”相对,相互阐发,意思是说,庄子能言善辩、放言高论,将“无为而治”的治世之道离散得漫无边际、放诞不羁。一个“散”字,既点明了庄学对“道德”的任意散发,又描述出庄子游离人世、游心于无穷的散诞,何其传神。其逍遥适己的自得之态,被《索引述赞》形容为“庄蒙栩栩”。⑥《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第2156页。先秦时期,荀子曾一语中的地指斥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①王先谦:《荀子集解》,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93页。太史公所谓的“散道德,放论”,正如刘洪生先生所言,也正是直接针对庄子本人的一种态度鲜明的批评。②刘洪生:《司马迁的庄学研究及其意义》,《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这种批评是基于庄子对人间世事、特别是对政事的逃避与诀别,对此,在《史记》的其他篇章里也可得到验证,如《孟子荀卿列传》中,司马迁就说“庄周等又猾稽乱俗”。
就庄子其人其学在太史公心中的大致面貌而言,可以说,司马迁读了庄子之书,明白其中的言论所指,但作为一个现实的史家,他并不相信庄子所说的那些关于大道的茫昧无形的话,也不认可庄子学说。而为司马迁所不相信的那些“寓言”,却正是庄学的思想核心。这也为老庄的同传而书埋下了伏笔。
二、《史记》老庄同传而书的理论依据
《老子韩非列传》是老子与韩非的合传,传主是老、韩二人,庄子是作为附传,附在老子之后。虽然附传中的人物在历史上并不是不重要,但和传主比较起来,总是等而下之的,司马迁的这种处理手法也与本文第一部分的分析相合。《史记》合传的原则是以类相从,老子与韩非合传的原因在于“自源徂流”,③黄震:《黄氏日抄》卷四六《史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0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1页。申明其前后相因之意,这也是老庄同传而书的一个主要依据:庄子学说的要旨本源于老子之学。
《庄子》在《大宗师》中曾经借孔子之口说过这样的话:“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丘则陋矣!”司马迁的上述观点,即庄学“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就是一个典型的“游方之内者”对“游方之外者”的判断,其合理性是基于现实世界,即“方之内”的观察视角。所谓“外内不相及”,如果站在庄子这样游心于方域之外者的立场上,事情便不是这样了。
纵观《庄子》内七篇,老子虽然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他的肯定,但却并无丝毫以老学为思想源头之意。在《庄子·天下》篇,作者综述了包括老、庄在内的先秦诸家学说,老子与庄子也是作为两个相互独立的学派出现的,且各有所宗:一者“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另一者“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④郭庆藩:《庄子集解》第1093、1098页。概括起来,老子道论的中心是由对立转化、柔弱处上的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引出人类的法则,教导统治者实行无为之治,其思想的本质属性是一种社会政治学说。而庄子早已从老子“相反相成,对立转化”这一自然规律的循环往复中抽身而出,超越了物我的两两对立,站在“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的无穷流变的圆环的中央,将是非、成败、生死,将天地万物“道通为一”了。从形而上的最高本体到无毁无成的复通为一,庄子之道最终成为一种与天地精神同来往的精神境界,成为个体生命的寓所,用以安顿心灵。对于治理天下,庄子以“趣取无用”的姿态唯恐避之不及,治者与政事对于其全生的思想主题都是有害而无益的,这样的是庄子怎么会认老子的政治学说为本源。至于老庄学说的共同点,那个最高本体的原始“道”概念,只不过是作为各自学说的前提条件高悬在空中罢了。⑤关于老庄道论之分殊,详见徐莹:《庄子学说之独立性研究——以内七篇为中心》的相关论述。
《史记》老庄同传的另一个理论依据是庄学致力于攻击儒学,以非议、诽谤孔子之徒为己任。对于这一点,我们还是要到庄子的书中寻找答案。
孔子是《庄子》书中出现频次最高的人物形象,吊诡的是庄子赋予其三种不同的脸谱:其一,儒者孔子;其二,道家孔子;其三,沟通前两张反向脸谱的一种中间面貌,即幡然开悟后弃儒入道的学习者。后世面对《庄子》书中复杂多变的孔子形象,纷纷然莫衷一是:一则以为庄子诋訿孔子,这种说法始自司马迁;一则以为庄子赞许孔子,这种说法源于苏轼。①苏轼在《庄子祠堂记》中说:“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其正言盖无几。至于诋訾孔子,未尝不微见其意。其论天下道术,自墨翟……以至于其身,皆以为一家,而孔子不与,其尊之也至矣。”参见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7-348页。两种非此即彼的论断各有支持者,自古以来聚讼不已。其实,庄子并非尊孔者,这是可以肯定的,但他对于孔子的态度也仅仅是不赞同而已,认为仁义之道较之于无所不在的大道仅仅是得之一隅,在当时的混乱现实中根本行不通,其“不赞同”远不具有“诋訿”那样强烈的攻击性质。
《庄子》多寓言,《天下》篇说那是因为“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天下如此污浊,根本不能说什么严正的话。不过,说着“不可与庄语”的《天下》篇,倒恰恰是一篇庄重、严肃的纵论百家的学术史著作,从中正可窥见庄学对孔学的真正态度。《天下》篇谓:
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道术将为天下裂。
在道术为天下裂的时代,包括儒家学说在内的各家各派只是谋得一星半点大道的余绪,各自得到一孔之见,却因此片面之得而自负、自满,将原本完备的、无所不在的大道割裂得支离破碎,这是庄学对诸子学说的概括性评价。其中,“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云云显然指的是孔子之学,虽然它比不上“不离于宗”的天人、“不离于精”的神人、“不离于真”的至人以及“以天为宗”的圣人,但是,“君子”的评价至少还是肯定性的。只是,庄子并不赞成儒家“临人以德”的行事作风。
《庄子》内七篇中的《人间世》,开篇讲颜回向孔子辞行,要到卫国去劝诫独断专行的卫君,救黎民于水火之中。孔子说:“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术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恶有其美也,命之曰灾人。灾人者,人必反灾之,若殆为人灾夫!”②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36页。《人间世》篇塑造了“卫君”等诸多“其德天杀”的当权者形象,表达的是庄子对政治生活和统治阶层的极度绝望。颜回此行的“临卫君以德”是典型的儒家君子之风,而孔子在这里对颜回所说的话,则正是庄子要对孔子讲的:名和智都是凶器,“临人以德”就像是螳螂当车,既于事无补,又会白白牺牲掉自己的生命。对于好名尚智的儒家,在该篇的末尾,庄子安排楚狂接舆对孔子吟唱道:“天下无道,圣人生焉……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天下无道,圣人也仅仅是保全性命,你那些仁义道德之说,还是算了吧。
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场景中,庄子对于“论辩”持鲜明的反对态度,这一点在其著名的《齐物论》篇有着十分清晰的表达,说他以诋毁儒家为己任,显然不符合庄学的性情。站在个体生命的立场上,庄子学说以全生为主题,其思想脉络为:自然而然的大道生生不息,其间,个体生命的长度也是无限的,生命随大道的运转而流变,这一世为人,下一世或为虫臂、鼠肝,如此这般与造物者同游,其快乐是无穷无尽的。③《庄子·大宗师》:“若人之形者,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其为乐可胜计邪?”“伟哉造化!又将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参见郭庆藩:《庄子集释》,第244、261页。庄子的自然无为是一任个体生命在大道中流转,生不喜、死不悲,安时处顺,不进行任何人为的干预,绝不肯“弊弊焉以天下为事”。④郭庆藩:《庄子集释》,第30页。这与老子教导统治者的“无为而无不为”的为政之道有着天上人间的本质区别。司马迁抓住两者的一个次要联系,即学说的前提——原始“道”概念,只看到庄学有不赞成儒学的一面,便将庄子归本于老子,也可谓是只谋得一星半点庄学的余绪,以此片面之得,将老庄整合在一起了。
三、《史记》老庄同传的原因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称“申子之学本于黄老”、“韩非者……而其归本于黄老”但对于庄子却说:“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黄老”是比“老子之言”更加具象的统治术,此处“黄老”与“老子”的区别使用以及“适己”、“王公大人不能器之”等语句表明,司马迁对庄学关注个体生命、与政治绝缘的基本特征是有所体察的。因此,《史记》归庄入老并不是因为司马迁根本没有读懂《庄子》,而是他看到却又舍去了庄学的核心思想,这其中的原因,在于时代影响和个人素质两个方面。
时代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两点:其一,是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其二,是儒道斗争的社会现实。
毋庸置疑,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期是一个昂扬向上、踌躇满志的时代,而世人的精神面貌也是积极进取的。这恰如《庄子·人间世》篇所说的:“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有道时,世人都汲汲于入世之学,致力于成就一番事业。只有到了动荡战乱的魏晋时期,庄子出世的思想学说才被世人捡起来,用以安慰在混乱现实中无法安身立命的痛苦心灵。汉初的司马迁以《庄子》为寓言,其对庄学的不认可,也是情有可原的。
关于儒道斗争的社会现实,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中所说的“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反映的正是汉代的社会状况。
黄老思想因切合汉初的政治需要而风行于世,“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①《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第3117页。“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②《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第1975页。到了汉武帝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③《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第3118页。这一时期,儒学与黄老之学的斗争并非单纯的学术之争,而是已上升为最高统治者的政治路线斗争。司马迁身处政治漩涡的中心,深深浸染在西汉的社会现实之中,在《史记》的《儒林列传》等不同篇章里,都对那一时期的儒道斗争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描述。但是,司马迁将当世的政治斗争套在先秦不同思想流派之间正常的学术分歧上,并以此为据,作学术史的分类,显然有失妥当。
此外,在司马迁的个人因素方面,是其“务为治”的指导思想导致了老庄的同传而书。司马谈总括先秦学术时曾说百家之言殊途同归,都是为了治理天下,“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④《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3288-3289页。而司马氏父子著史何尝不是如此。虽然,班固在《汉书》中称道司马迁具有良史的实录精神,⑤《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8页)但太史公父子相继编纂史书并非为了客观地记录历史事实,其网罗古今的目的,是继承《春秋》明善恶、定是非的微言大义,考察往事的兴衰,探究兴衰背后的原因和规律,以便为当代的政治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帮助。其间,始终矢志不渝地贯穿着“务为治”的指导思想。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政治是天下、也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就体现在其政治生命当中。参与政治、为政治服务,“务为治”既是绝大多数世人的学术宗旨,也是其安身立命之所。司马迁以“务为治”的立场审视庄子,庄子学说出离人世的思想主题对于治理天下来说不仅空洞无实,而且有害无益,所以,他在《史记》中对庄子整体持批评态度,说其“滑稽乱俗”。在当时儒道家斗争的社会背景下,抛开那些空洞无实的寓言,庄学也就只有反对儒学这一点对于现实政治是有用的,因此,司马迁只列举了外杂篇的《渔父》、《盗跖》、《胠箧》三篇抨击孔学的文章作为庄子学说的代表作,而对庄学真正核心的内七篇却置之不论。
四、余 论
综上所述,归庄入老是司马迁在西汉的时代背景下整齐百家,服务于政治而提出的学术思路,汉人的这一学术分野,是对先秦学术的反动。两汉文化,或者说秦汉文化,和先秦文化相比有着质的差异,胡适、徐复观、熊铁基等近代以来的诸多学人都曾对此给予了一定的关注,而李振宏先生则明确提出“先秦学术体系的汉代生成说”,认为我们所能见到的先秦诸子,大都是由汉人整理或由他们重新写定而流传下来的,后世把汉人改造过的先秦诸子当成了先秦诸子本身,忽略了它们被改造的事实。①李振宏:《汉代文化研究需要引起新的重视》,《光明日报》,2007年1月7日,第9版。也可参照李振宏:《论“先秦学术体系”的汉代生成》,《河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因此,廓清司马迁老庄合流的原因和依据,剥离老庄,对于重新认识庄学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无疑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