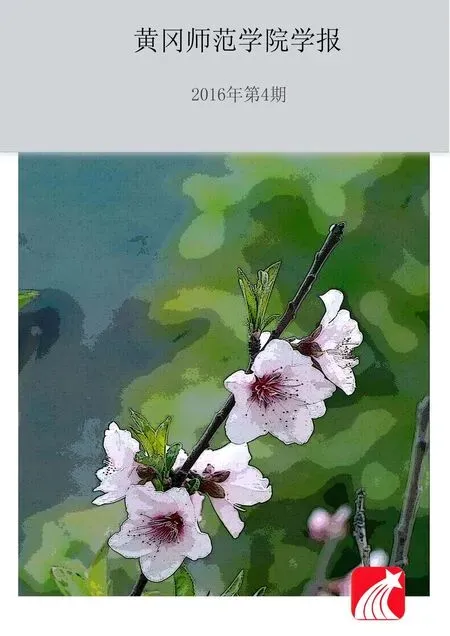论《人面桃花》的神秘叙事
周 静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论《人面桃花》的神秘叙事
周 静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人面桃花》不仅是格非对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双重把握,更是他积极向“传统”内转,使文本染浸着传统底色的一部作品。其中的种种“神秘”叙事和传统神秘文化存在着内在的勾连,这种勾连使文本始终萦绕着一种神秘氛围,对叙事内容产生重要影响,更深化了文本的意义层,使其展现丰富的叙事魅力。具体表现为:其一、神秘莫测的命运变数激发对历史和生活本相的玄思;其二、诡异蹊跷的梦境体验促进文本叙事的开阔化;其三、人物的神秘化加深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格非;《人面桃花》;神秘叙事
神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近代以来,传统神秘文化被看做封建迷信,因此很是沉默了一段时间。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文化逐渐呈现多元化格局,人们对神秘文化采取包容的态度。文学创作方面,在西方后现代主义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下,中国作家们的创作转向“非理性”,而民间和“神秘文化”更成为一部分作家创作的源泉,如贾平凹《太白山记》志怪系列,莫言的《生死疲劳》等等,神秘文化思潮可谓涌动不止。格非也曾谈到:“中国文学作品有一种可亲的入世情怀,有人伦,也有神秘的天数。”[1]作为一个“不可知论者”和“宿命论者”,格非深受传统神秘文化的浸润。本文从《人面桃花》所涉及的“命运”、“梦境”、“神秘人物”等内容来具体阐释该文本“神秘”叙事的深层意义以及对作品思想和艺术特色的积极作用。
一、命运的意味
中国有悠久的神秘文化渊源,如命运之说,影响久远,不只是一种思想,乃成为一种文化心态。这种心态既可以说是一种“反叛”和“觉醒”,也可以说是一种“豁达”和“无奈的劝慰”。构成一种交杂却并不两极分化互为否定的思维方式。在《人面桃花》一书中,作者以“命运的意味”进行历史和生活本相的探索,揭示了个人命运的偶然无常以及个人与历史、现实之间的非理性关联。
格非相信奇遇对人生走向的作用,相信命运的注定,人生既有天命、时势,亦有偶然、变化。这股命运的绳索交织捆绑,在尽头处是注定,在过程中是千变万化。《人面桃花》中并没有明确交待陆秀米为何走上革命者的道路,可始终缠绕在她身上的有一种宿命的意味。“她用手指轻轻地叩击着釜壁,那声音让她觉得伤心。那声音令她仿佛置身于一片寂寞的禅寺之中。禅寺人迹罕至,寺外流水潺潺,陌上纤纤柳丝……有什么东西正在一寸一寸地消逝,像水退沙岸,又像是香尽成灰,再想想人世喧嚣嘈杂,竟全然无趣。”[2]从作者描写陆秀米叩击瓦釜产生的幻觉开始,她就在冥冥之中即将踏上属于自己的命运之途。“寂寞、禅寺、流水”,这里已经预言了她来到花家舍的那座孤岛,遇见韩六,登上围困的心之岸,也预示着她最终“香尽成灰”的“消逝”。然而她并不是消极地等待命运给自己的安排,命中注定之中,其实有着更多非逻辑的存在。秀米被劫完全是一个偶然性事件,打破常识和经验,突如其来。这时的非逻辑却进一步促进她走向宿命,偶然性成为必然性的前提,作者对宿命的特别关注通过偶然渗透出来。偶然具有普遍性,生命充满了意外,这种种意外促使他人及其自身做出种种看似“必然”的决定。作者此时用不可知性代替了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观,秀米的行为及命运变幻莫测,玄奥离奇。《人面桃花》以一定的时代历史作背景,故事显得有据可考。但是历史和个人常常是不可知的,我们习惯于按照我们的需要解读他人的行为和思想。秀米为什么要奔上革命道路,是什么促使了她,作者并不从社会历史的宏观角度来刻画,而从个人的角度去展现。可以说,秀米受着命运的莫名牵动,她的身上时常表现为有一种“莫名的欲望”。她的成长及具体行为作者时常有意“远视”,这些都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个人以及生活本相之间的差距。
《人面桃花》中神秘莫测的命运在诡谲变幻间为作品带来深刻的玄思性。神秘的背后是思索,人们会孜孜不倦地追求由“不可知”到“知”。福斯特认为:“神秘感对情节是十分重要的,没有智慧是无法欣赏的。对好奇心强的读者只要‘然后……然后……’就行了,而要欣赏到神秘的奥妙,除用一半心思阅读下去外,还要留下另一半心思进行思考。”[3]这种形而上的玄思也就是上文我们谈到的对生活和历史本相的思考,是作品对命运和偶然的追问,是对存在的思索和探寻。
二、梦境的打开
“梦”除了受到西方心理学的关注,自古以来在中国也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所在,除了《周公释梦》,更有“庄周梦蝶”、“黄粱美梦”、“南柯一梦”等著名典故,而《红楼梦》的太虚幻境描写也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梦不仅是一种神经活动,也是一种心理实况,还代表了某些神秘预示和感觉体验。很多新生代作家的作品中展现梦境体验,打开新的文化视窗,一方面是现代意义上的“神秘梦境”,另一方面离不开我国传统神秘文化中对“梦”的思考。“人唯有在梦境中才能获得真实感,这就是格非的哲学。”[4]由此可见,在作品中进行梦境描写对格非的重要意义。梦境叙事可以说是一种开放性叙事,非理性的描写丰富了作品的表现力。在《人面桃花》中,梦境成为一种跨时空的生命体验,承续传统梦境描写的预示作用,弥补日常经验的缺失。秀米未曾见过王观澄,却在他被杀的那个夜晚梦见王来找秀米,而秀米所见真人和所梦并无二样,这种诡异梦境给整部作品以神秘气氛,推动情节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彰显了独特的生命体验,表现了现实世界中难以直露表现的事物。王观澄借梦境抒发自己的理想和苦闷,秀米通过梦境了解不易看清的本相,正印证了格非在创作中对梦境的“信任”。人在一生中会产生大量梦境,现实的经验因为连续性会构成完整的记忆,然而梦境却成为断裂的人生碎片,于潜意识深处丰富我们的人生体验,让幻觉和直觉等等不易言明的抽象事物找到一个有力载体,人有了第六感甚至第七第八感。因此作者实则让梦境成为一个载体,联想和意义在此得到延伸,现实得到延展。“现实”和“梦境”之间也存在着一股张力,使得《人面桃花》挣脱理性的束缚,同时展现丰富的生命体验,在“虚”与“实”之间走向咀嚼不尽的想象空间。
《人面桃花》中的“梦”常常也作为一种契机带来虚假和真实的思索,在传统文化中,“南柯一梦”、“庄周梦蝶”从哲理层面思索现实和梦境的关系,到底是人生如梦,还是梦里人生。《人面桃花》中多次出现梦和现实的恍惚感受:“她不由得这样想,尽管她现在很清醒,但却未尝不是一个更大、更遥远的梦的一部分。”[2]49以及“会不会是这样:那天她根本没有遇到土匪,没有来到花家舍……所有这些事,只不过是她在轿内打了一个盹,做的一个梦。”[2]137可以说在这里,作者将传统的“人不能完全区分真实和虚幻”的感受真真切切地诉诸笔端。个人的感受是狭隘的、主观的,如果人生仅仅是一场虚幻的自我欺骗的梦境,那么现实到底多大程度上驻扎在浮云幻世之中。人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又多大程度上接近了自身的真实,个人的生命感受经受作者的质问。“大同思想”“桃花源梦”是集体心理的产物,但是这一梦想必须“个体”联接“个体”有意识继而有组织地去实现。作者以复杂的心态通过对“梦”的体验,将历史、现实、个人纳入考量之中,作品因而展现了开阔深邃的叙事局面。但是如果放任“虚幻”的缰绳驰骋就会陷入唯心主义的圈套之中,作者尽力把控着现实背景,将现代意识和传统文化积淀搅拌均匀,各有侧现。
梦境叙事使《人面桃花》的叙事局面更为开放,作品也因而更具象征意味。“梦”是理想,是欲望,是非理性存在。作者以梦境为“心灵窗口”,使得很多理性无法囊括的东西得以展现,作者也可以在自由天地里表现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感觉、感受、直觉、幻觉、潜意识、神秘力量等等非理性、非逻辑性内容使作品更加充盈饱满,同时也拓展了思想的维度,延伸了体验的深度。这些对“梦”和现实的恍惚感受唤起读者的思考,个人体验和集体体验的共通性也为作品带来迷离朦胧、若有所思、若有所感的审美效果。
三、人物的神秘化
在中国古代的“志怪”“传奇”等作品中都离不开神秘人物,他们行踪不定,身世不明,行为举止也不易被人察觉,因此他们身上也带有浓厚的神秘意味。神秘人物总有其独特的标志,常常出现在文本中的如肮脏邋遢的乞丐,疯疯癫癫的和尚,来路不明的陌生人等等。在《人面桃花》一书中,神秘人物是推动情节发展必不可少的人物,他们隐晦不定,若隐若现,使小说叙事有所空白和悬置,进一步加重了叙事的神秘氛围并促进情节的内在变化。神秘人物时常成为一个符号,她们背后所代表的常常是一种高于人物本身的情节或思想设定。秀米在整修阁楼的工匠都要离去时竟然遇见了庆生,庆生的表面身份是木匠,真实身份却是土匪,他既是土匪又是木匠,双重身份的分离体现了庆生身份的神秘特点。工匠们不仅仅为了整修阁楼,还为了日后的打劫做下准备,身份不定的庆生和工匠们预设了秀米人生转折的开启。在这里,作者设置的“陌生人”的“行动逻辑”是“陌生化”的,人物形象只是侧面刻画,人物行为难以测定,无论是这群土匪还是秀米,在机缘巧合之下某个行为就会成为生命中的一个节点,用无形之手推动情节和故事的发展。而“庆生”不仅代表“普通人”,也代表了膨胀的“个人欲望”。花家舍本是王观澄努力构建的“大同世界”,但是住在那里的一群“领袖”人物却成了“欲望的容器”,他们就像一串珠链,从第一颗珠子膨胀断裂开始,后面也相继分散迸落,团体从个人的分离开始分崩离析,故事在毁灭中前进,个人欲望的膨胀和无节制导致花家舍最后的覆灭。但是王观澄的理想却在秀米身上得以现代性的延续,陌生人和陌生人之间亦有难以厘清的莫名联系,正是这种蕴藉其中的潜在关系和意义等待读者的发现和探寻。
“陌生人”们成为偶然性要素和神秘力量来源,在情节进展过程中他们可以悬置,可以缺失,也可以多面展开,因此神秘的“陌生人”具有多重意义,他们时常能被信手拈来,形象的模糊性正促使其具有更多的可塑性,还为故事增添跌宕起伏之姿态,伏笔之外再添伏笔,无形之中驱使读者畅想和领悟。秀米的“谜”离不开来到她身边的那些“陌生人”,除了庆生,她来到花家舍的岛上又遇见“韩六”。韩六与其说是一个尼姑,毋宁说“尼姑”只是她的一重身份。韩六一出场她的遭遇就让人心生怜悯,但是在之后的发展中她却越来越给人深藏不露之感,她有着不同常人的睿智和淡然,也有世俗的需要和处事方法,到最后她给秀米一枚“金蝉”,她的身份更成了一个谜。韩六究竟是“蜩蛄会”的一位头领还是无意之间在某人的指示下将金蝉交给秀米……韩六在这里实际上就代表了多种可能性,也代表了不确定性,她让读者觉得故事情节还有一条“隐线”,作者只让我们看到表面的那一层,但是内在的那一层却云里雾里、扑朔迷离、耐人寻味。
神秘叙事将《人面桃花》投向“形而上”的高度,将文本带入更为开阔的叙事境地,丰富了作品的表现力,将读者引入“深度思考”的阅读体验之中,这些不仅增添了作品的思想性和内涵性以及艺术魅力,也完成了文本和读者的巧妙“沟通”和“问答”。
神秘叙事还使作品笼罩上一层神秘氛围,因此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作者用充满灵气的笔触勾勒出诡奇的艺术面貌,而不是因为科学和理性导致的想象力丧失而一味用“神秘”去代替艺术创造。将“传统”和“现代”结合,联接两者的是影响久远的文化心态,是思想解放的必然,是艺术多元化的生发。
与此同时,“神秘作为一个审美范畴,它能给人一种朦胧、含蓄、深邃的美学感受。”[5]缺失和悬置以及对象的不可知与模糊性会带来迷离朦胧的神秘美感。神秘叙事打破我们的习惯思维,输入非理性,感受非经验逻辑性的存在,产生陌生化效果。因此可以说“它体现出创作主体对审美对象的一种特定感知方式。”[6]
[1]刘伟.格非的神秘主义诗学[J].文艺评论,2009(01)65.
[2]格非.人面桃花[M].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68.
[3]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27.
[4]余中华. 雨季·梦境·女性——格非小说的三个关键词[J]. 小说评论,2008(06)52.
[5]张学军.中国当代小说流派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266-267.
[6]洪治纲.追踪神秘——近期小说审美动向[J].当代作家评论,1993(06)69.
责任编辑 张吉兵
2016-03-17
10.3969/j.issn.1003-8078.2016.04.10
周静(1992-),女,安徽铜陵人,安徽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I206.7
A
1003-8078(2016)04-004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