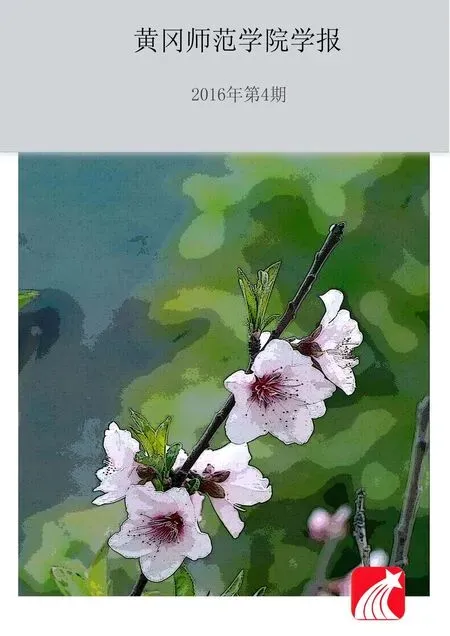清代词坛尊体运动中的《诗经》
龚 敏
(湖北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清代词坛尊体运动中的《诗经》
龚 敏
(湖北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在清代词坛的尊体运动中,各种手段层出不穷,或攀附诗骚,或溯源乐府,或并驾唐诗,或以词存史……本文主要从词的形式比附《诗经》、溯源《诗经》的风雅论、溯源《诗经》的寄托说、《诗经》到词的文体演变等四个方面论述了《诗经》在清代词坛尊体运动中发挥的作用。将词溯源比附《诗经》,虽然有牵强附会的味道,但它作为一种尊体手段确实使词的地位在清代得到了提高。而另一方面,源自《诗经》的比兴、风雅等理论也在这场尊体运动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诗经;词;尊体运动;风雅;寄托
词学的尊体概念虽然到周济才最先提出,“中仙最多故国之感,故着力不多,天分高绝,所谓意能尊体也。”[1]到况周颐才开词学尊体研究的先河,“张皋文、周止庵辈尊体之说出,词体乃大。”[2]但是,从陈维崧、朱彝尊等人的词学理论中不难看出,没有“尊体”之名的清初词坛,早已具备了尊体之实。在清代词坛的尊体运动中,各种手段层出不穷,或攀附诗骚,或溯源乐府,或并驾唐诗,或以词存史……本文将具体探讨《诗经》在清代词学尊体运动中是怎样发挥作用的。
一、从词的形式出发比附《诗经》
《诗经》句式以四言为主,间或杂有二到九言的各种句式。词,又名长短句,因为大多数词的句式参差不齐。基于《诗经》和词的这一共同特点,清代一些学者便将词攀附上《诗经》,以提高词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徐釚《词苑丛谈》卷一所引《药园闲话》,讨论得最为详尽:
屈子《离骚》亦名辞,汉武《秋风》亦名辞。词者,诗之余也。然则词果有合于诗乎?曰:按其调而知之也。《殷雷》之诗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阳。”此三、五言调也。《鱼丽》之诗曰:“鱼丽于罶,鱨鲨。”此三、四言调也。《还》之诗曰:“遭我乎峱之间兮,并驱从两肩兮。”此六、七言调也。《江汜》之诗曰:“不我以,不我以。”此叠句调也。《东山》之诗曰:“我来自东,零雨其蒙。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此换韵调也。《行露》之诗曰:“厌浥行露。”其二章曰:“谁谓雀无角。”此换头调也。凡此烦促相宣,短长互用,以启后人协律之原,岂非三百篇实祖祢哉?[3]
《药园闲话》从句式长短不齐、叠句、换韵、换头(即《诗经》的分章和词的分片)等方面来论证了《诗经》为词之祖。其中,叠句、换韵、换头很少被后人论及,句式长短不齐这一论证证据最为清代其他学者所接受。汪森的《词综序》说:“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居其五;至《短箫铙歌》十八篇,篇篇长短句,谓非词之源乎?”[4]康有为在为王鹏运《味梨集》题的序中也说:“为文辞者,尊诗而卑词,是谬论也。四五七言,长短句,其体同肇始于《三百篇》。”[4]217
长短句的出现是词体成立的重要标志之一,但以长短句来溯源《诗经》,只是看到二者之间的一种相似点,并非它们的本质特征。汪森纯粹从句式的长短出发,推溯词的源头,忽略了词的音乐特征,引来其他词论家的批评。江顺诒《词学集成》卷一引王述庵《词综序》说:
汪氏晋贤,序竹垞太史《词综》,谓长短句本于三百篇,并汉之乐府。其见卓矣,而犹未尽也。盖词实继古诗而作,而本于乐。乐本乎音,有清浊、高下、轻重、抑扬之别,乃为五音十二律以著之。非句有长短,无以宣其气而达其音。故孔颖达《诗正义》谓风、雅、颂有一二字为句,及至八九字为句者,所以和人声而无不均也。三百篇后,楚辞亦以长短为声。至汉郊祀歌、铙吹曲、房中歌,莫不皆然。苏、李画以五言,而唐时优伶所歌,则七言绝句,其余皆不入乐府。李太白、张志和以词续乐府,不知者谓诗之变,而其实诗之正也。由唐而宋,多取词入于乐府,不知者谓乐之变,而其实所以合乐也。[5]
词体成立有两个重要标志,一个是长短句的出现 ,另一个是以歌词之法代替歌诗(近体诗)之法。燕乐传入中原后,句式整齐的诗作为歌辞适应不了燕乐的繁复变化,长短句的出现成为当时的需要。以五、七言律绝为本,增减字句,化齐言为杂言,以趁歌拍,是当时制作歌辞的一种方法。叠句就是在这一方法中诞生的。燕乐对词的规定体现在词的格律和音律,长短句、叠句、换韵、换头都只是词的格律和音律的具体表现。“上古至汉,以乐从诗;汉至六朝,采诗入乐;隋唐以来,倚声填词。”[6]《诗经》是以乐从诗,词产生之初是以词就乐,它们与音乐的关系及其所属的音乐系统是它们之间最本质的区别。
二、溯源《诗经》的风雅论
除却从外在形式上来将词溯源《诗经》,清代词论者也从风格特征上来要求词向《诗经》看齐。邹袛谟在为吴伟业《梅村诗余》作的序中说:“词在季孟之间,虽所作无多,要皆合乎国风好色、小雅怨悱之致。”[4]27邹袛谟虽然并非常不看好词的地位,但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的诗教传统来评价吴伟业的词。这评价是非常高的,后来的沈祥龙即以这一评价来规范词风,其《论词随笔》说:“词者诗之余,当发乎情,止乎礼义。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离骚》之旨,即词旨也。”[5]50俞樾更是把它简化成诗教中的“温柔敦厚”四个字,他在《玉可庵词存序》中说:“温柔敦厚,诗教也,词为诗之余,则亦宜以此四字为主。”[4]451阳羡派陈维崧认为词人要有美人香草之志意和宽和温厚之心,反对词的“淫亵之音”和“佻巧之习”。他在《蝶庵词序》中说:“夫作者,非有国风美人、《离骚》香草之志意,以优柔而涵濡之,则其入也不微,而其出也不厚。人或以淫亵之音乱之,以佻巧之习沿之,非俚则诬。”[4]478
上述诸人虽然没有提到“雅”这个概念,但他们的“不淫”、“不乱”、“温柔敦厚”等观点都可以纳入“雅”的范畴。雅在诗学传统中,源自“风雅颂”,最初是《诗经》中一类诗的总称,后被用来评价文学风格。 “雅者,指内容雅正或高雅,语言典丽含蓄,长于比兴等等。”(赵晓蘭《宋人雅词原论》)
浙西派词人论词主姜夔、张炎,推崇雅。朱彝尊提出“醇雅”。所谓“醇雅”,就是鄙弃淫词、俗词,以及粗率叫嚣、应酬、类曲等种种不纯正之词。朱彝尊在《词综发凡》中说:“言情之作,易流于秽,此宋人选词,多以雅为目。”[4]318他评马阑浩等人的词,认为“陈言秽语,俗气熏入骨髓,殆不可医。”到厉鹗时, 这一雅正词论被发挥到极致。厉鹗《群雅词集序》载:“词源于乐府,乐府源于诗,四诗大小雅之材,合三百有五。材之雅者,风之所由美,颂之所由成。由诗而乐府而词,必企夫雅之一言而可以卓然自命为作者,故曾端伯选词,名《乐府雅词》,周公谨善为词,题其堂曰‘志雅’。词之为体,委曲啴缓,非纬之以雅,鲜有不与波俱靡,而失其正者矣。”[4]211
清代词论者或举“雅正”之大旗,或推崇“醇雅”,或标榜“骚雅”,名目及具体意涵虽有异同,但其中心思想都根植于《诗经》以来的风雅传统。
三、溯源《诗经》的寄托说
与浙西派提倡风雅以推尊词体不同,常州派所采取的的基本手法是倡言比兴寄托。常州派的开山之祖张惠言引进《风》、《骚》的内涵评词,提出了以比兴寄托为中心的“尚意”的要求。张惠言在《词选序》中说:“《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
张惠言所特意强调的词体之 “意” 是“风谣里巷男女哀乐”、“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而且这个“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意”,它同 “《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是相近的。
张惠言对词体内涵的论述,具有相当浓厚的比兴寄托意味,后来的论者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周济在其《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说:“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若乃离别怀思,感士不遇,陈陈相因,唾沈互拾,便思高揖温、韦,不亦耻乎?”周济更加注重词与时代社会和人生的关系,把词的社会功能提到了空前的高度。谭献在《重刊微波词序》中评钱牧之词,说:
“先生(钱牧)高言令德,旷代逸才,遐举人海之中,托兴国风之体,玄微其思,锵洋其音,如谢眺、柳恽五诗,所谓芳兰竟体者已。”清末的况周颐对张惠言的词论也有极其明确的认识,他在《词学讲义》中说:“意内者何?言中有寄托也。”
常州派在倡言比兴寄托的同时,也提出了一套与之相对应的治词手法。饶宗颐《张惠言 <词选>述评》中说张惠言治词“简直是用诗序说诗的方法”。《诗经》原为文化典籍,后为五经之一,其在后世的接受过程中也是以经学与文学的双重身份进行,诗序说诗的方法是典型经学与诗学两者合一的方法。张惠言《词选》中评苏轼《朴算子》(缺月挂疏桐)说:“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时代稍后的黄苏也采用了这一治词手法,如他在《蓼园词选》中评辛弃疾《鹧鸪天·秋意》说:“其有《匪风》、《下泉》之乎?可以悲其志矣。”评刘过《贺新郎·游湖》说“前阙尤奇崛郁勃,得《骚》、《雅》之遗。”
四、从《诗经》到词的文体演变
把某种文学样式作为某一时代的代表性体裁,这一做法在金元时期就已发端,罗宗信在为《中原音韵》写的序中所说:“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罗宗信为了提高元曲的地位,搬出地位在文学史上已经稳固的唐诗宋词,使三者相提并论,这是一种尊体策略。这一尊体策略在清代词的尊体运动中同样被使用,《诗经》在其中为词的张本提供了一种“坐标”。成肇麐《唐五代词叙》说:“十五国风息而乐府兴,乐府微而歌词作。”成肇麐的论述颇为简略,以国风、乐府诗、词相提并论,中间忽视了别的文体。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则讲得较为详细:
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即久,染指遂多,自成俗套。豪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7]
这段话被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概括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王国维这一理论影响巨大,后世谈论文学体裁时,每以唐诗宋词并称,词终于真正获得了与诗同等的地位。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清代其他词人的着眼点主要是提高清词或者说词在清代的地位,而王国维的理论,无论其有意或无意,提高的是宋词的地位。宋词地位的一味抬高,必然招致清词的被忽视,这在在词学上追随王国维的胡适和胡云翼那里,表现得十分明显。胡适在为词的历史作分期时,认为晚唐到元初是词的“本身”的历史时期,而把清初到今日(1900)当作模仿填词的时期,是词的“鬼”的历史。胡云翼更是反对填词,认为宋以后无词。
将词溯源《诗经》,除了上述几种角度外,还有从写作动机出发的,如谢章铤《张鸣珂寒松阁词序》:“古不云乎,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夫人苟非不得已,殆无文学,即填词亦何莫不然。”[4]471认为词同《诗经》一样,是人发愤之所作。然而,谢章铤在词坛的地位并不高,其这一理论也少有人接受,因此本文不作详细讨论。
将词溯源《诗经》,虽然有某些不合理的地方,但它作为清代词坛尊体运动的众多策略中的一种,确实发挥出了一定的作用。莫友芝在《香草词序》中说:“词自皋闻选论出其品第,乃跻诗而上,逌然国风乐府之遗,海内学人始不以歌筵小伎相疵褒。”[4]39而源自《诗经》的比兴、风雅等理论也在清代词坛的尊体运动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1][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9.
[2][清]况周颐.蕙风词话[M].北京: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61.
[3][清]徐釚.词苑丛谈[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1.
[4]施蛰存.词籍序跋萃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87.
[5]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 中华书局,1986:1834.
[6][宋]王灼,沈义父,张炎,陆辅之.碧鸡漫志,乐府指迷,词源,词旨[M]. 北京:中华书局,1991:3.
[7]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9:7.
责任编辑 张吉兵
2016-01-05
10.3969/j.issn.1003-8078.2016.04.13
龚敏(1991-),男,湖北咸宁人,湖北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2014级硕士研究生。
I207.23
A
1003-8078(2016)04-005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