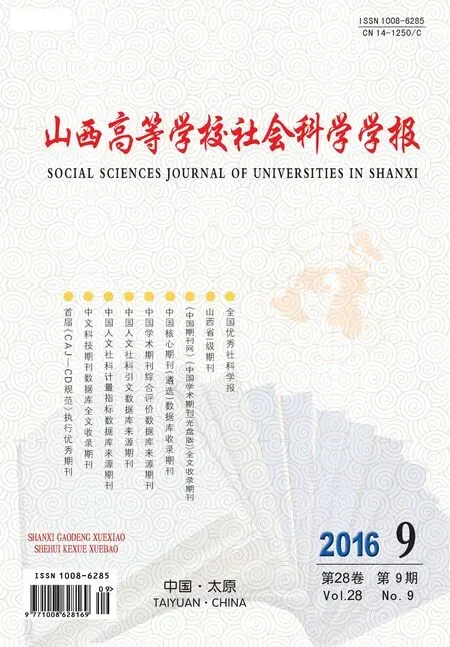论医疗侵权诉讼证明责任分配
郭相宏,高 寒
(太原科技大学 法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论医疗侵权诉讼证明责任分配
郭相宏,高寒
(太原科技大学 法学院,山西太原030024)
医疗侵权证明责任分配,面临着立法分配上的左右摇摆、理论上分歧突出、实践中分配两难等诸多困境。从诉讼主体结构、程序与实体价值等理论角度以及社会因素等方面考量,应当由患者一方承担证明责任。这样既符合证明责任一般的分配原则,在遵循现行立法的基础上,又能够恰当衡量诉讼主体利益,实现诉讼程序与实体的双重价值,达到良好的社会与司法效果。
医疗侵权;证明责任分配;利益衡量;程序正义;社会因素
我国《刑法》已将备受关注的医闹行为纳入其规制范围,医疗侵权又一次成为社会的热点。医疗侵权证明责任分配则是诉讼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在该诉讼中,证明责任究竟应该由医患双方当事人哪一方承担更为合理,一直以来都是学界与实务界关注的课题。
一、医疗侵权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困境
在我国通说认为,证明责任是当作为裁判基础的法律要件事实在诉讼中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一方当事人因此而承担的诉讼上的不利后果[1]。证明责任在医疗侵权诉讼中的分配,则是研究这种不利后果如何承担的问题。很显然,诉讼上的这种风险,诉讼双方都不乐意承担。但法律真实毕竟不同于客观真实,需要证据予以支持,当待处理的案件事实上真伪不明时,法律上关于证明责任承担的规定则会成为司法裁判的最终依据。正是由于证明责任的这种利益相关性,造成在医疗侵权诉讼中证明责任的承担与分配,面临多重困境,一直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
(一)立法分配上的左右摇摆
在现代众多诉讼类型中,医疗侵权诉讼作为现代新型诉讼,该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在立法上也经历了一定的发展变化。
起初,针对现实中医疗侵权诉讼中证明责任如何承担在立法上并没有明文规定,法官仅仅依据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理论,完全由患者一方承担证明责任。但是,鉴于医疗案件中相关知识的专业性、医患双方知识结构的差异性等因素,导致在医疗侵权诉讼中,证明责任之所在则为败诉之所在,使患者一方的正当权利得不到有效地维护,医患矛盾在诉讼中无法真正妥善地解决。
针对这一现状,为了改变患者一方在医疗侵权诉讼中的不利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将此两项侵权要件的证明责任倒置给医疗机构,以期实现医患双方武器平等,在诉讼中能够平等对抗。然而,现实状况却是医疗机构为了避免承担证明责任,在医疗过程中往往采用大量非必要措施。不仅造成了当事人就医负担的增加,而且也严重影响了医疗技术的进步。
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随后,自2010年7月1日起实施的《侵权责任法》实现了证明责任承担主体的回归,确定了医疗侵权诉讼中实行以过错责任为原则、附条件推定过错责任为例外的归责。也就是说改变了《证据规定》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基本由患者一方承担证明责任。对于医疗侵权诉讼中关于证明责任如何分配的规定,经历的这种由“谁主张,谁举证”到证明责任的双重倒置再到最新的证明责任分配上的回归,这种立法的左右摇摆,足以显现出该问题解决的两难。
(二)理论上的分歧
关于医疗侵权证明责任分配,在学界同样也有不同的分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侵权责任法》仅仅将此问题视为一般的侵权类型,并未对其证明责任分配有特殊的规定,应当按照一般的侵权理论对其证明责任进行分配,理应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理论由患者一方承担医疗侵权诉讼中证明责任,当事人应当需要根据实体法律效果的逻辑组合,对其提出的权利主张所对应的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2]。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医疗侵权诉讼中医患双方存在先天的不平等,医疗机构不仅有专业的医护人员掌握着专业的医疗知识,而且还握有大部分甚至是影响案件判决的决定性证据。如果在这种不平等的先决条件下仍由患者承担证明责任,只能扩大这种不平等,显然不符合诉讼的基本理念。因此,应当坚持证明责任倒置,方是良策[3]。此外,还有些人认为医疗侵权案件多种多样,对于证明责任的分配不能一刀切的进行规定,应当结合具体的案件由法官自由裁量证明责任的分配[4]。
(三)实践分配上的两难
从根本上说,医疗侵权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分配是医患双方当事人利益的角逐和对抗的结果,是立法者进行价值选择的结果。如果证明责任由患者承担,由于患者一方的取得证据困难与专业知识的匮乏,往往会使案件无法得到一次性解决,极大地浪费诉讼资源。同时,案件常常也会陷入“案了事不了”的困境,影响与扰乱了社会的稳定与正常秩序。另外,如果证明责任由医疗机构承担,会使其为了避免承担责任而进行防御性医疗,为患者做没有必要做的检查、化验、护理,不单单会过度地增添患者的经济压力,而且还会阻碍整个医疗事业的良性发展。可见,在理论与现实中妥善地将证明责任在医疗侵权诉讼的分配困境重重。
二、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
在法律体系中,目前《民事诉讼法》中并未明确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仅仅只是在《证据规定》和一些实体法中对某些具体案件有明确的规定。
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证明责任分配普遍采用的是“法律要件分类说”,即“规范说”理论。该理论由德国法学家罗森贝克所创,他以法律规范为基本元素,通过分析它们彼此的相互关系来发现分配的原则,按照规范的措辞、构造、适用顺序将法律规定分为不同的规范类型,并以此分类为基础,以法律规定的原则性与例外性关系及基本规定和相反规定的关系为标准分配证明责任。主张诉讼中当事人理应根据其适用的法律规范对该规范所要求的构成要件承担证明责任。
罗氏的“规范说”将实体法与程序法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巧妙地解决了证明责任的承担与分配问题,通过纯粹的对实体法的分析,探寻出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我国,在学界和立法上实际上也采用上述学说。《证据规定》中有关证明责任的规定就是以其“规范说”理论而设的。同时,在一般原则的基础上,考虑到某些案件的特殊性也有所变通。通过有效地变通规定追求个别案件的公正,防止一刀切带来的不利后果。
三、医疗侵权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医疗侵权诉讼中如何恰当地分配证明责任,的确有一定的困难,但为了实现司法的统一,实现程序正义,切实保护利益相关人的正当权利,提高司法公信力,实现社会稳定,必须对此问题予以明确。
对于医疗侵权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的问题应当坚持证明责任的一般分配原则,即坚持由患者承担案件真伪不明时的不利后果。
(一)立法上的依据
尽管我国立法在医疗侵权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问题上出现了左右摇摆的局面,经历了证明责任正置—证明责任双重倒置—证明责任的回归的历程。但是就现行立法而言,为了保证司法中正确适用法律,实现司法的统一,必须坚持现行最新规定也就是《侵权责任法》关于医疗侵权的有关规定。该法并未将医疗侵权视为特殊的侵权类型, 因此只能按照“规范说”的一般理论由患者对其主张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
至于《证据规定》中有关证明责任双重倒置的有关规定,完全可以视为与新法之间的冲突,按照法律适用原则,应以新法为准。一方面,以法的位阶视角而言,《侵权责任法》作为《证据规定》的上位法,当二者立法发生抵触时,理应以上位法为准;另一方面,《侵权责任法》相对于《证据规定》是新法,从理论上讲《侵权责任法》的法规具有适用上的优先性。故而,在医疗侵权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分配应当坚持由患者一方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
(二)医疗侵权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分析
法的运行本身就是利益负担的问题,是价值选择的结果。医疗侵权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也不例外,是法的价值在当事人双方与法院三者之间利益选择与价值衡量综合考虑的结果。
1.诉讼主体之间的利益衡量。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衡量是我们在证明责任的分配过程中,首先应当加以考虑的。其二者的关系从诉讼主体结构的角度而言,实则是诉权的冲突。在诉讼中追求诉权的平等与对等是现代诉讼理念的基本要求。在现代诉讼构造中,双方当事人应当设计为平等的诉讼地位,亦即一方诉讼主体能否与另一诉讼主体形成“对峙”[5]。根据这一基本要求,在医疗侵权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中,医患双方的利益分配也应以这一要求进行设定。一方面,我国法律特别是《侵权责任法》中以实体法规范的形式,对医疗侵权责任基本上以过错责任原则进行归责,根据证明责任规则原则,实则将证明责任隐含地分配给患者一方,同时考虑到医疗侵权中的专业性等问题,也做了相关的实体规定减轻患方的举证负担。另一方面,程序法中也有申请法院取证、申请专家辅助人的相关规定,以此来追求诉讼中医患双方的诉权平等与对等。
那些认为医疗机构具备专业的知识,医患双方存在天然的信息不对称就应由医疗机构承担医疗侵权诉讼中的证明责任的观点也值得思考。这是事实,不可否认。但是这种不平等是专业分工不同而造成的天然差距,这种所谓的“不平等”并非是诉讼中的不平等,而是现实状况使然。如果医疗侵权诉讼中的这种信息不对称也能称之为不平等,那么大概这种“不平等”会广泛存在。医疗侵权诉讼也更不具有特殊性了。而且,这种天然的差距完全可以在诉讼中得到相应的弥补与缓解。专家辅助人制度本身也是针对因存在专门知识的差距而设置的。在医疗侵权告诉中,作为原告的患者完全能够聘请专家辅助人摆脱这种天然的困境。
有观点以“证据距离”“证据偏在”为理由,认为医疗侵权诉讼中由处于劣势的患者一方承担证明责任这种风险显然是不平等的。其实,此观点已然将证明责任此种事实真伪不明时需要承担的诉讼上的不利风险,与提供证据具有行为意义上的责任混为一谈。证明责任作为一种诉讼上的客观结果不同于诉讼过程中提供证据的责任。前者是客观结果由且仅能够由一方当事人承担,是静止的、固化的。而后者则是一种行为意义上的责任,在当事人之间是不断转换的,随着诉讼的进行逐渐深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如果将二者等同,那么当医疗机构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而案件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这种以“证据偏在”的理由主张由医疗机构承当证明责任的主张就不攻自破了。况且,在患者一方承担证明责任的前提下,“证据偏在”而导致所谓上述医患双方的不平等完全可以用诉讼的方式解决。当患者取证困难时,可以根据法律规定申请相关法院提取相关的专业证据与关键证据。所以说,这种观点也无法使人信服。
民诉中当事人双方与法院的关系,也是价值考量与选择的重要考虑因素。他们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诉权与审判权、私权与公权的关系。权利与权力自法治思想萌芽以来就始终保持着相对紧张的关系,权力主体始终有滥用权力的内在冲动。孟德斯鸠就曾经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到一直遇到有边界的地方才休止。”[6]审判权也是如此,在诉讼过程中都有侵犯诉权的可能。因此,在现代法治理念中,限制权力、保护权利始终是法治思想中的一条不可动摇的红线。在医疗侵权诉讼中,如果许可法官对证明责任的负担进行自由裁量,就极大地增加了法官利用审判权侵权的可能性。
我国作为单一制的法制国家,如果许可法官对证明责任的负担进行自由裁量,很可能由于法官对案件、对法律理解的不同,致使法律适用的不统一,影响法律的权威与公信力,牺牲法本身的相对确定性与可预测性。在我国证明责任的分配建立在“规范说”理论的基础之上,将证明责任交由立法者通过明确的或隐含的规定进行分配,显然比法官的自由裁量更可靠。因为大家始终相信制度比人更可靠。这种将证明责任分配交由法官的自由裁量的做法显然不符合我国的现行理论与制度。
在我国法官作为事实的裁判者,法律法规的适用者,而非制定者。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的问题完全是一种适用法律的问题,法官只能根据相关的法律进行适用。因此,作为裁判者的法官对于哪一方负担证明责任根本不具有自由裁量权。主张由法官根据医疗侵权诉讼的相关案情自由裁量证明责任的分配,不符合我国的司法体制,在我国这种统一的法律框架下显然无立足之地。况且,如果法官对诉讼中证明责任承担根据心证裁量,无疑增大了法官滥用权力的隐患。加之我国司法队伍目前的业务素质仍有待提高,更不能由法官自由分配证明责任。
2.追求诉讼正义实现诉讼价值。证明责任作为案件真伪不明的一种不利后果的负担,以案件事实真伪不明为前提。进行医疗侵权诉讼的目的,无非就是保障患者权利、维护患者正当利益。患者一方作为证明责任的负担者,为了避免证明责任在诉讼裁判中得到运用,会充分发挥程序的作用,积极参与诉讼,充分借助诉讼程序的力量实现权利的司法救济。正如法谚所云“自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维护者”。在医疗侵权诉讼中作为原告的患者,不仅仅是权利的受害者而且同时又是证明责任的负担者,相对于医院等医疗机构而言,其对维护权益的要求更为迫切。尽管患者一方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但是在程序所创造的内在动力与外在压力的双重作用下,患者积极参与诉讼,主动搜集相关证据,为维权而努力。相对地,作为医疗机构则为了避免败诉承担责任也会认真应诉,参与诉讼,双方当事人都能直接参与、自愿参与诉讼。由此形成了双方在程序框架内的良性互动,在诉讼程序中平等对抗,探求案件事实,不断压缩证明责任适用的空间,实现程序正当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追求实体权利的保护,实现司法诉讼的双重价值,达到了维护当事人合法利益定纷止争的目的。
(三)社会因素的考量
社会因素也是医疗诉讼中证明责任这种不利益负担不得不考虑的因素。患者承担证明责任,通过诉讼程序的充分运用,使诉讼双方对诉讼结果都比较信服,避免医疗侵权案件陷入“案了事不了”的尴尬局面。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减少当事人缠讼、滥诉的现象,提高诉讼效率、节省司法资源,极大地提高司法的公信力与社会实效。患者承担证明责任同时辅之以相关的程序措施,可以在诉讼中解决诉讼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弊端,既处理了程序平等的问题,也可以防止医疗机构过度进行防御性医疗。这既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又可以促进医疗事业健康有序发展,发挥司法救济的应有功能,最终实现社会的稳定。
总而言之,证明责任这种不利风险的负担本身就是法的价值衡量选择的结果。医疗侵权诉讼中,由患者一方承担证明责任既符合分配的一般的原则,同时也是立法的价值取向。考虑到医疗本身的专业性特点,以诉讼内的手段加以弥补,体现了诉讼程序的独特价值,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诉讼程序的角度而言,患者承担诉讼中的证明责任也是充分发挥程序价值,实现诉讼中平等对抗的有利选择。总之,医疗侵权诉讼中,患者一方承担证明责任对实现程序正义与实体公正更为有利,在实践中也利于维护司法权威,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1] 张卫平.民事诉讼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208.
[2] 曾培芳,段文波.德国表见证明理论在医疗诉讼证明责任分配中的运用[J].政治与法律,2007(4):170-175.
[3] 田平安,李战.我国医疗损害证明责任转换配置研究[J].河北法学,2014(6):39-43.
[4] 沈冠伶.民事证据法与武器平等原则[M].台北:元照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93.
[5] 樊崇义.诉讼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140.
[6]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54.
On the Burden of Proof in Medical Tort Action
GUO Xianghong,GAO Han
(School of Law,Taiy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aiyuan 030024,China)
Allocating the burden of proof of medical tort is facing with unsteady legislative allocation, outstanding theoretical differences, practical distribution dilemma, and many other difficulties.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cluding lawsuit subject structures, procedures and physical value of litigation and other social factors, it should be borne by the patient party to prove responsibility.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not only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distribution of burden of proof, in compliance with current legislation, but also the proper measurement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subject of litigation. Only by this means can the value of the procedures and physical value be achieved,good social and judicial effect be achieved.
medical tort;burdening of proof;evaluation of interests;proceeding justice;social factors
2016-06-29
郭相宏(1971-),男,山西曲沃人,太原科技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法学理论。
高寒(1991-),男,河北保定人,太原科技大学硕士生。研究方向:民事诉讼。
10.16396/j.cnki.sxgxskxb.2016.09.013
D925
A
1008-6285(2016)09-005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