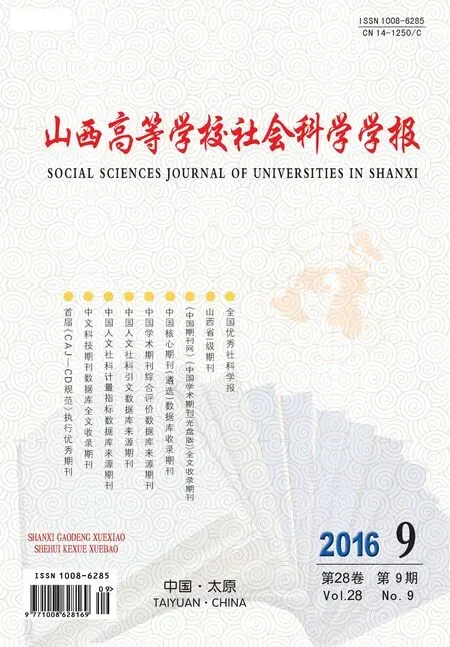试析马克思的真正的人*——从毛泽东诗词中的四次眼泪谈起
张檀琴,李 敏
(太原科技大学 思政部,山西 太原 030024)
试析马克思的真正的人*
——从毛泽东诗词中的四次眼泪谈起
张檀琴,李敏
(太原科技大学 思政部,山西太原030024)
毛泽东因杨开慧写的四首诗都写到眼泪,马克思致燕妮的一封信中说,因为爱情,“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使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伟人之为“伟人”,是因为对人的肯定;伟人又异于常人,因为他是真正的人。真正的人与现实的人相对,具有价值引领和批判功能;相反,现实的人标志人的发展水平,但同时又是应当被超越的对象。真正的人就是有真爱的人,爱有两个层次,情爱和博爱,博爱是真爱的基础和内涵。博爱植根于人的自然本性,又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分界,但是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一起构成人的辩证论。
马克思;毛泽东;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人的发展
毛泽东说,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我的兴趣是不废婉约,偏于豪放[1]230。既然不废婉约,婉约在其创作实践中有何表现?毛泽东认为婉约派一味儿女情长,儿女情长又有何表现?眼泪是儿女情长的标志。研究毛泽东诗词中的眼泪可以很好地了解毛泽东对婉约的实践。
一、毛泽东的四次眼泪
男儿有泪不轻弹。有种说法认为毛泽东一生两次掉泪,第一次是在长征路上,敌机轰炸,贺子珍掩护战士而身受重伤,毛泽东以为要生死离别。再一次是到了延安之后,因为贺子珍老生孩子生怕了,单方面决定到苏联学习。有的文章说,看到老百姓受苦、警卫员牺牲,毛泽东就要掉泪[2]。这些说法不管真假,辗转流传,实难考证。有一种方法绝对可靠,是以其诗词(以下简称“诗”)为证。依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毛泽东总共有五首诗写了眼泪,除了《挽易昌陶》的“涔泪侵双题”,其余四首都为杨开慧而写。
第一首是1921年的《虞美人·枕上》。诗中有“不抛眼泪”,让人怀疑是否掉泪?但是在全句中“不抛眼泪也无有”是双重否定,双重否定等于肯定,因此掉泪是肯定的!有些细节必须交代,毛泽东将此诗赠给杨开慧,杨开慧与闺友李淑一分享,1957年李淑一致信毛泽东,请求毛泽东重书该诗,毛泽东回复说:“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吧。”但另作《蝶恋花·答李淑一》,交给了李淑一[1]226。在文革“如火如荼”的岁月,80岁高龄的毛泽东凭记忆把《枕上》和《别友》写下来,前者手迹1994年发表在《人民日报》[1]166。
第二首是1923年的《贺新郎·别友》。毛泽东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1]266诗中有“热泪欲零还住”,诗人说话果然“拐弯抹角”。零者,落也;住者,停也;到底是停还是落?但是可以肯定,泪已经出来,否则何以有“热”和“欲零”的感觉?了解其他写法,诗的意思会更清楚。目前发现该诗共有三件手迹[3],题为“别友”的手迹把“人有病,天知否”写为“重感慨,泪如雨”,另一件把“重比翼,和云翥”写为“重感慨,泪如雨”。看来诗人不仅掉泪,而且不是一般的掉泪。最后一韵又为“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更不为昵昵儿女语”显然是化用“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沾巾者,泪沾巾也。
第三首为1957年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诗中的“泪飞顿作倾盆雨”是在写谁泪飞?从字面看,是骄杨泪飞。但昔人已去,泪飞是诗人想象,映现了诗人自己的感受。毛泽东不废婉约,偏于豪放,是婉约与豪放的结合,在该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该诗豪放之处体现为奔放不羁的想象和纯正高远的格调,不同于婉约派的一味温柔细腻,甚至庸俗颓废。对泪的描写也是婉约与豪放的结合。首先,眼泪不是哀婉悲悼,而是幸福喜悦,因为革命成功了。其次,“倾盆雨”本身就是一种豪放。
第四首是1961年的《七律·答友人》。从字面看,该诗写舜妃娥皇、女英。1975年毛泽东说:“‘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就是怀念杨开慧的,杨开慧就是霞姑嘛!可是现在有的解释却不是这样,不符合我的思想。”[4]霞姑是杨开慧的小名。
四次眼泪,第一次是抛眼泪,第二次是热泪如雨,第三次是泪飞,第四次是千滴泪。由泪之描写,表现毛泽东的强烈感情。毛泽东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毛泽东对杨开慧的激烈情感得到杨开慧的热烈回应。1982年湖南省修缮杨开慧故居,在墙缝中发现杨开慧遗稿,其中有五言长诗《偶感》,有“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抒发了杨开慧对毛泽东浓烈的情意。
二、马克思何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革命者是真正的浪漫主义者,但浪漫不是浪荡,而是杨开慧“死不足惜”的态度,而是陈铁军和周文雍刑场上的婚礼。革命者有浪漫,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有浪漫。马克思对爱情的伟大实践,包括求爱技巧,与燕妮在漫长岁月里同甘共苦,都是留给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马克思宣称:“燕妮,你笑吧!你会惊奇,为什么在我所有的诗章里,只有一个标题:给燕妮!”马克思激烈澎湃:“我是闪电,在天空写下最耀眼的文字,向世界宣布:我爱你,燕妮!我是惊雷,在天空发出最响亮的声音,向世界宣布:我爱你,燕妮!”(对原诗有改编)[5]120岁月无情,容颜在变,青年时代的讴歌逐渐成为深情的书信,马克思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又一次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因为我感到了一种强烈的热情。……然而爱情,不是对费尔巴哈的‘人’的爱,不是对摩莱肖特的‘物质的交换’的爱,不是对无产阶级的爱,而是对亲爱的,即对你的爱,使一个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5]197
这封信袒露了马克思作为西方人的浪漫气质,既是对爱情的崇拜,又清楚表达了马克思怎么理解爱情和人性的关系。马克思说,因为爱情,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后面重复道,对你的爱,使一个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对家庭以至男女关系的重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色。《礼记·昏义》认为:“昏礼者,礼之本也。”鲁哀公问:“冕而亲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君何谓已重乎?”接着解释道:“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6]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齐家,并非家庭内的统治和压迫,而是积极的交流和建设。
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五四”前夕新文化运动的洗礼,骨子里秉承了祖先“关关雎鸠”的本性,又受了西方“爱情至上”的浸染。周恩来和邓颖超是此种典范。邓颖超在一封信中反复吟咏:我可想你得太……我真想你得太[7]!邓颖超不愧是“五四”女性,周恩来亦是真丈夫,很少写古体诗的周恩来写过一首五言:“结婚十八载,至友兼爱妻;若云夫妇范,愧我未能齐!”[7]17这首诗可以表明他们何以成为伟大革命家,因为有真情的人才能对国家和人民怀有真情。
三、伟人之为伟人
讨论伟人的爱情,目的是讨论什么是人。人大致分为伟人和普通人。伟人何以是伟人?不是因为一个“伟”字,而是因为一个“人”字,是对人的肯定,而不是对人的背离,因而具有普遍性。或者说,因为他真正地是人,是“真正的人”或“真正意义上的人”。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聚焦于现实的人和社会的人,这一聚焦自有其理论和实践价值,有助于实际地改变人的现实,但是科学不排斥抽象和普遍性。现实是矛盾和冲突,是永恒之现实与非永恒之现实的紧张。现实的人与社会的人自有其局限性,其存在有充足理由,却不见得有全部合理性,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缺乏价值引领功能或社会批判功能。与之相反,“真正的人”固然与现实保持距离,甚至远离现实,但是必定是人和社会的发展方向、批判现实的尺度,是人们改变现实的最终理由和必须实现的客观目的,因而不仅有批判功能,更具实践价值。“现实的人”作为问题其实渗透了“真正的人”这一概念,一旦分析现实的人,必定是用“真正的人”这个尺度对它做价值评估。马克思明确了“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才会提出劳动异化这个问题。因为有“类特性”这把尺子,劳动异化才成为不现实的现实。异化无疑是一种现实,但是与某种现实(人的类特性也是一种现实,只是没有充分成为现实)格格不入。因此,人的科学必须涵摄对现实的人和真正的人的两种研究,构成关于人的辩证论,体现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
从某种超越性(不是超自然)的人出发,是马克思一贯的思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提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8]9。两个命题都在揭示出人的矛盾,同时也包含了两个关于人的概念,即真正的人和现实的人。“人本身”、作为“人的最高本质”的“人”,即是真正的人,亦即高于现实的人。与之相反,“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中的第一个“人”字,“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中的第二个“人”字都指现实的人。因而,现实的人的根本是真正的人,真正的人是现实的人的最高本质。
真正的人、真正意义上的人就是合乎人的本性,这种本性应该存在于所有人,并且或多或少地以心理形式显现于所有人。真正的人必然与常人有共同之处。《中庸》认为:“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马克思在《自白书》说:“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5]348这句话出自希腊神话,用以概括诸神特性,即“人的一切弱点,神都有”。马克思不再把“人的一切”称作“弱点”,是他的科学之处。姑且不谈人所具有的,只看马克思具有的是什么?我们发现无非是亲情、友情与爱情。马克思和父亲的通信说明他不仅有伟大的爱情,还有深厚的亲情。至于友情,列宁这样评价:“古老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这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9]
四、人之为人
伟人同于常人,在于对人的肯定;伟人异于常人,还在于对人的肯定。此时,人的内涵仍未解决。真正的人只能被理解为人本身、人的本质(“1844年手稿”讨论的人的本质)、人的本性。人性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避讳,“1844年手稿”认为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10]《资本论》认为共产主义是:“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11]如果谈人而不谈人性,是非常奇怪的。
伟人的特点是具有浓厚的亲情、友情与爱情,总起来说就是爱。如果从中看到利己主义,那是一种误解,真正的爱是自私自利的反义词。人之完善,是回到人自身,回归人性,真正占有自己的本质。问题在于什么是人?忽视人的真理,结果就是反人性和反主体性。动物的心理在自然进化中被严格规定,出生之时具有良知良能,所作所为完全符合自然法则和主客体尺度。人类与此不同,出生之时心理近乎白板,只有不断地探索、学习和修养,并且接受社会及其规范的约束,才能发现真我,实现复归。人的毁灭往往源于自我毁灭,庄子说“天下尽殉也”[12],就是讲人如何成为假我的牺牲品。真正的人,是认识人的真理并合乎客观本性的人。
中国文化把人性和兽性相对,强调人性积极面,人在德性上高于动物,把人性理解为爱,认为人的发展方向是人本身;西方文化把人性和神性相对,强调人性消极面,人在德性上同于动物,把神性理解为爱,认为人的努力方向是神性。宗教观念受到现代科学巨大冲击,上帝已远去!仁爱为内涵的那部分神性何处安顿?费尔巴哈认为是人创造了上帝,就不是人性分有神性,而是“人性包含神性”,神性是人性的折射。自然界是真实的造化者,是神性所映现的本体,物性也就包含人构想的神性,仁爱并非人类专利,动物或多或少也有。蜂蚁是职业道德楷模,燕雀是家庭美德楷模,犬马是友谊的象征。动物有伦理缺陷,但是人类的缺陷更大。恩格斯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13]如果兽性全无价值,人性就绝无希望。自然属性即是人的本性,本身有神圣的一面。文化属性则是个体差异亦即个性的根源,造成人的现实本质而与人性相对。基于文化先进性与腐朽性的内部矛盾,个性千差万别。动物的“文化”基本与生俱来,人类靠社会提供并且历史地形成的文化才能活动。因此个性不完善是特定文化对人的扭曲,是特定文化的特性,而不是人的本性,这一实质是无限人世苦难的根源。
动物自然属性在进化过程中形成,同时符合主客体尺度。人的自然属性也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也同时符合主客体尺度。对于社会性动物,个体不能独立生存和发展,亲情、友情、爱情就是保证其生存发展的自然属性。当然,战争也是人类从动物那里继承来的,但是有的动物通过奥林匹克式的和平竞争,完成同类之间的优胜劣汰。人尤其是社会动物,《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8]61社会化是多方面的,爱是其重要纽带,如果爱不是人的本性,马克思因爱而“成为真正的人”又何以可能?爱能否作为人的本性,涉及价值和理想的定义。黑格尔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可见理想不脱离现实,不过是对现实的抽象,对美好部分的抽象肯定,对不美好部分的抽象否定。爱,有庸俗的一面,又有崇高的一面。如果庸俗,不是爱本身庸俗,而是爱不真实。如果爱不是人的本性,全部道德岂不是扭曲人性?真正的人就是真爱的人。燕妮去逝的那天,恩格斯为马克思“判了死刑”,绝望地说道:摩尔也死了[14]。伟人异于常人,是他们的爱异于常人的爱,这种爱,接近爱的理念,或爱本身。所有人终将成为真正的人,而真爱是必由之路。
黑格尔在《自然哲学》讨论生命的特点,指出个体通过类属过程(交配)而达到普遍性。动物的类属过程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实现传宗接代而有客观价值,另一方面感受苦乐而有心理价值,从而既是客观要求又是心理需要,而客观要求是更深层的意义,并且在进化中作为主体尺度而对其心理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但是高等动物类属过程的心理形式进一步分化为情欲和爱欲,情欲是自我满足,爱欲是自我牺牲。两种倾向在动物那里都表现为本能,并且在进化中达到和谐;在人类那里则由于本能弱化而呈现各种可能的个性化发展;但是不论何种可能,都不能改变爱欲作为人类本性的事实。
情欲与爱欲的分歧在理论上的意义是表明人本主义(humanism)与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的区别。人本主义基于人类中心主义和对人类的崇拜,表现为对情欲的尊重。人道主义更进一步,强调的是爱欲,但是二者植根于人的本性。
爱欲本身分为两个层次,较低层次是个体对个体的爱,较高层次是个体对群体的爱。在生物那里两个层次已经充分发展出来。生物个体都代表类,因而需要表明谁是正确的代表,并且通过同类竞争解决,因此生物个体之间首先是对抗关系。同时客观上个体为类的发展而投入竞争,必然表现出对群体的爱而与整个群体发生关系。这一规律表现为社会性动物的雄心。所谓雄心,是雄性动物之心,是强者对族群的服务意识。雄心必然同时表现为爱欲和情欲及其和谐,在人类社会则可能堕落为单纯情欲。因此爱欲固然比情欲更进一步,但是如果止步于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爱欲,其实仍然在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之间游移不定,甚至更多地接近人本主义。相反对群体、对人类,直至对全体生命、全部自然界的爱才是人道主义。人本主义是狭隘之爱,可以概括为爱自己,即使把爱扩大到他人,例如爱亲人、爱朋友,仍然不能超越自爱,人道主义则是博爱。人本主义固然是人类社会的本质,但是人类要真正超卓于动物界,除了知识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还要认识到人道主义是其特质而成为其真正的基础。
人和其他生物的发展有截然不同的规律,生物个体即是类,个体同时包含个性与共性,包含特殊性与普遍性。生物通过繁殖就可不朽,人类个体则仅仅在生物性上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在心理方面仅仅是总体的一个部分,甚至随着人类意识的发展,个体在总体中的比重日益下降,导致个体与总体的对立。准确地说,在生物性上人类个体是理念的复制,在心理方面则是理念的分有,为此人的发展必须通过“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及其发展,以及个体与个体日益从对抗走向合作。对于动物,遗传和继承(继承指心理方面的继承,即后辈向前辈的学习)是其发展的途径。对于人类,遗传和继承仍然重要,但是作用日益降低。基因优越的人未必在生物学上也能有良好发展,人的生物学发展极大程度地受心理发展水平(即德性)的制约,而德性的发展有极其复杂的规律,但首要规律是遗传和继承的作用日益下降,故此《论语》提出“君子之远其子也”。至为吊诡的是德性发展往往以缺陷为前提并作为缺陷的补偿。精神财富的“继承”较为困难,物质财富的继承非常容易,但是后果却是“财富对人的伤害”。这一逻辑在资本逻辑的历史环境中也迫使人们做出适当反应,例如在“捐赠宣言”(Giving Pledge)的带动下,美国有不少富豪承诺捐献大部分财产。人的发展实质上是其社会性发展,孤立的个人发展终将成空,如果一个人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他终将发现,命运在捉弄他。
博爱是自然本性和客观要求的统一,为人的发展提供现实基础和价值目标,至于发展实际水平,主要由历史文化和社会关系决定,但是作为一种主体尺度,必然具有最高的实践价值,持久地发挥批判功能,从而最终实现自身。再回到伟人之爱,这种爱绝非贾二爷与多姑娘的爱,博爱正是其前提和本质,也就是恋爱中人对此种人格相互而深刻理解,使爱恋实际作为一种自我意识。毛泽东和周恩来以“改造中国与世界”“振兴中华”为职志和人格,马克思则“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15]这种博爱精神并不孤独,而是与所爱之人共有之人格,作为爱情基础,进而成为婚姻内涵。正如燕妮所说:“坐在马克思那狭小的办公室里,誊抄他写得字迹不清的文稿的那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5]342杨开慧则说:“我同情下层生活的同胞,我忌恨那些穿华服只顾自己快活的人。我热天和下层生活的人一样,穿大布衣。”这是在讲博爱,接着讲到对毛泽东的爱:“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16]可见伟人的爱固然是真正地爱,但是前提是对方也有博爱情怀而理解自己,值得自己以真爱待之,实质是博爱与博爱之间的爱,理念对理念的爱。
马克思成为“真正的人”,是博爱与情爱的统一,也就是人本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人本主义极大推动了历史进步,也是人类新灾难的开始,而且越往后,灾难越花样翻新,变本加厉。如何拯救人类,马克思的方案是“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这里的人道主义是humanismus,即通常讲的人本主义。但是马克思也在人道主义的意义上使用“人道”一词,马克思晚年在讨论土地国有化及共产主义时提出:“这就是19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追求的人道目标。”[17]原文为英文,“人道”使用的是humanitarian。片面人本主义在当代愈益显现出反人性的负效应而要求实现一种自我超越,也就是与人道主义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人和社会发展的辩证论。
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又是相互渗透的。第一,人道主义被理解为人的自然本性(尽管这种本性只为人类心理发展提供基础)和客观要求,可以放在人本主义范畴中。第二,人道主义要以人本主义为旨归,即致力于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人道主义即爱人,但是如何爱人?就需要以人本主义为指导。第三,人道主义是人本主义的前沿。发展人道主义说到底是重视人的精神需要,主要是爱的需要。需要具有整体性,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不可分割。物质需要的意义往往由精神需要决定,例如面对老幼饥寒交迫,人们往往不会先满足自己的温饱需求,生死考验当中存在着同样的问题。第四,人道主义因而又是人本主义的前提。促进人的共同发展是实现个人发展的途径,个人的价值或发展水平终究是由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来衡量,正如生物个体的意义终究在于充当物种延续和进化的环节,在于内在普遍性的实现和增进。随着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从发达国家扩展到发展中国家,人道主义和爱的内涵也必须随之扩展到整个的生态和自然界,从而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实现古人“民胞物与”的理想境界。“民胞物与”的途径不是人的退缩,而是人的进取,但不是物质需要无限度地进取,而是精神方面的无止境追求,把对自然界的物欲之爱上升到理念之爱,把过度物化的现代生活转化为适度精神化的经济形态,因而实现“民胞物与”理想境界就是人类真正开始承担这样一种使命——“最后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脊椎动物,在它身上自然界获得了自我意识,这就是人”。
[1] 毛泽东.毛泽东诗词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2] 李敏,王桂苡.我的父亲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4.
[3] 郭发明.哪篇才是《贺新郞·别友》词的定稿?——对毛泽东三件手迹的研究[J].百年潮,2001(5):75-78.
[4] 杨建业.在毛泽东身边读书:访北大中文系讲师芦获[M]∥毛泽东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51.
[5] 马克思.最美丽的爱情:马克思爱情诗文选[M].龚维才,编.广州:花城出版社,1987.
[6] 四书五经:上[M].长沙:岳麓书社,1991:619.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5.
[10]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1.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28.
[12]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01:239.
[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42.
[14] 保尔·拉法格.回忆马克思恩格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39.
[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7.
[16] 欧金林.留取丹心照汗青:馆藏新发现的杨开慧手稿试读[EB/OL].[2016-03-29].http:z.book118.com/xue shu/xue shu 08/.htm.
[1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0.
The True Man in Marx′ Eyes——SheddingtearsinfourpoemsbyMAOZedong
ZHANG Tanqin,LI Min
(Educational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Taiyuan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Taiyuan030024,China)
In four poems that MAO Zedong had written for YANG Kaihui,he used the word "tears", while in the letter to Jenny, Marx said that love had made him a true man. Their experiences demonstrate that why a great man turns to be great is not being great but being a man in its real sense. Being a true man is in essence a return to self by nature. They also demonstrate that a true man is a man with true love which is necessarily a man′s nature or his natural attribute.Nevertheless,cultural attribute is blended in a real man who will finally become true man through truth and love. Love has two levels, viz. amour and fraternity,which are based on human nature and objective development need. It is fraternity that differentiates humanitarianism from humanism. Together they constitute a sort of dialectics on human.
Marx;MAO Zedong;humanism;humanitarianism;development of man
2016-06-13
张檀琴(1971-),男,山西临县人,太原科技大学讲师,哲学博士。
李敏(1973-),女,山西陵川人,太原科技大学副教授,法学硕士,硕士生导师。
10.16396/j.cnki.sxgxskxb.2016.09.022
I206
A
1008-6285(2016)09-0088-05
*太原科技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从人本主义到人道主义”之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