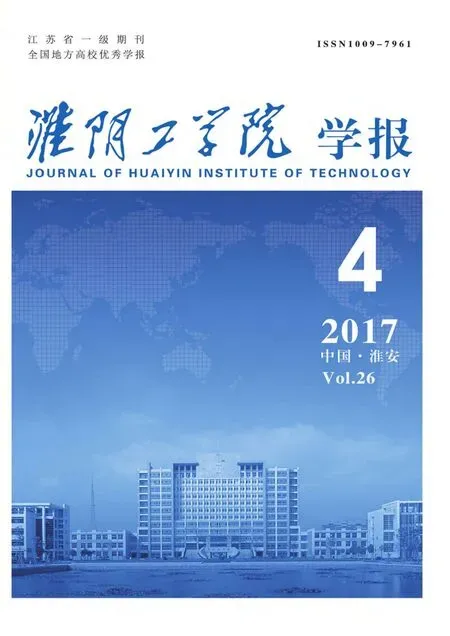明清时期苏南运河区域的金龙四大王信仰
胡梦飞
(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山东 聊城 252059)
明清时期苏南运河区域的金龙四大王信仰
胡梦飞
(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山东 聊城 252059)
明清时期苏南运河区域不仅是商品经济极为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是金龙四大王信仰较为盛行的地区。漕粮运输和水上航运的现实需要是金龙四大王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漕军、商人成为信仰传播的重要媒介,文人、谢氏宗族对金龙四大王谢绪事迹的颂扬亦推动了信仰扩展。运河沿岸的金龙四大王庙宇在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祭祀需求的同时,在扩大社会交往、增进社会互动方面亦发挥了显著作用。
苏南运河区域;漕运;金龙四大王信仰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沿线区域不仅是一条繁荣的商品经济带,同时也是一条密集的水神祭祀带。苏南运河沿线的苏州、常州、镇江等地是当时中国较为富庶的地区,同时也是各种水神信仰较为盛行的地区,其中就包括官方和民间对金龙四大王的崇祀。
1 金龙四大王庙宇的地域分布
金龙四大王,名谢绪,南宋诸生,杭州钱塘县北孝女里(今浙江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安溪村)人,因其排行第四,读书于金龙山,故称金龙四大王。作为黄河河神和漕运保护神,金龙四大王除具有防洪护堤、护佑漕运的功能以外,民间也赋予了保障航行安全、掌管水上生死等职能。既为河漕官员、漕军、运丁所崇祀,也为船工、水手、商人所供奉。明清时期苏南运河区域既是漕粮的重要输出地,也是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运河沿岸的镇江、常州、苏州等地几乎都有金龙四大王庙宇的分布。表1是笔者对金龙四大王庙宇的地域分布情况所做的简要统计。

表1 明清苏南运河区域金龙四大王庙宇分布情况
由表1可以看出,明清时期苏南运河区域金龙四大王庙宇分布较为广泛。创建庙宇的既有地方官员、漕军、运丁,也有商人和普通民众,从中也可以看出金龙四大王信仰群体的普遍性。相比明代,清代金龙四大王信仰更为盛行,庙宇数量更多,分布地域也更为广泛。据笔者统计,明清时期徐州(含宿迁、萧县)境内共有金龙四大王庙宇18座,淮安(含桃源、盐城、阜宁)境内共有金龙四大王庙宇40座,合计58座。相较徐州、淮安等黄运交汇地区,苏南运河区域的金龙四大王庙宇并不是太多。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苏南地区并无严重的水患,当地官民信仰河神的欲望并不强烈,金龙四大王只是作为水上航运的保护神,职能较为单一;另一方面,苏南地区神灵种类众多,其中亦不乏金总管、晏公等水神,它们同样被人们赋予了保障水上航运安全的职能。职能相同的神灵彼此之间存在着竞争,故相较徐州、淮安等地区,苏南运河区域的金龙四大王信仰并不是极为盛行。
2 金龙四大王信仰传播的原因
明清时期漕运和河工关系国计民生,倍受统治者的重视,金龙四大王作为黄河河神和漕运保护神,因具有护佑漕运、防洪护堤、御灾捍患等功能,不断得到明清官方的加封。景泰七年(1456年),明朝政府采纳左都御史徐有贞的建议,建金龙四大王祠于沙湾。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派兵部侍郎万恭前往鱼台致祭,正式敕封河神谢绪为“金龙四大王”。天启六年(1626年),加封其为“护国济运龙王通济元帅”。清朝建立后,继承明朝的传统,将官方和民间对金龙四大王的崇祀推至顶峰。从清顺治二年(1645年)开始,清朝历代皇帝不断给金龙四大王敕加封号。至光绪五年(1879年),金龙四大王最后的封号为“显佑通济昭灵效顺广利安民惠孚普运护国孚泽绥疆敷仁保康赞翊宣诚灵感辅化襄猷溥靖德庇锡佑国济金龙四大王”,达44字之多。官方的重视推动了民间金龙四大王信仰的盛行,往来于运河之上的漕军、客商、船工、水手,甚至普通民众无不虔诚祈祷,以求神佑。
中国古代社会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儒家的忠孝节义观念受到了历朝统治者的推崇,士绅阶层和普通民众对儒家思想也给予了高度认可。经过文人改造之后的谢绪,成为忠义的化身,这无疑也是导致其传播和盛行的重要原因。“明朝奉行儒教原理主义的祭祀政策,重视人格神生前的义行,明初被列入王朝祀典的人格神几乎都是先帝、明王、忠臣、烈士之类。明中期,儒教原理主义祭祀观念更为盛行,原本属于忠臣、烈士的人格神迅速走强”。[1]金龙四大王的人物原型谢绪忠于宋室,于南宋灭亡之际投水而死,属于忠义之士,谢绪在吕梁洪之战中显圣大败元军的传说更突出了其忠义形象,迎合了儒教原理主义祭祀政策。在儒教原理主义的影响下,金龙四大王谢绪的忠义形象得以推广。
明代文人徐渭在其《金龙四大王庙碑记》中云:“自洪武迄今,江淮河汉四渎之间,屡著灵异。商舶粮艘,舳舻千里,风高浪恶,往来无恙,佥曰王赐,敬奉弗懈。各于河滨,建庙以祀,报赛无虚日。九月十七日,为其诞辰,祭赛尤盛,非王忠义之气,昭昭耿耿,光融显赫,而能然乎?”[2]苏州浒墅关有金龙四大王庙在火神庙南,乾隆四十年(1775年),榷使舒文《重建金龙四大王庙碑记》云:“古之享天下后世祀者,必有盛德大烈被乎寰宇,其或功盖一时,名震一国,其祀事亦止于其乡而不能及乎远,惟神一诸生毅然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卒之未竟其施,挟报雠泄愤之意,而抑郁以没。其精灵足以塞宇宙,声烈足以昭简册,端人正士义其忠,武夫劲卒钦其勇,田唆村妪慑其神,江河湖海、帆樯贾客之流被其覆帱而至于无穷,以故庙祀几遍天下。自大都剧邑迄于偏州僻壤,甚而枵然十家之聚,往往裒金券地,畚土伐木,以隆祀事。”[3]
金龙四大王为漕运保护神,往来于运河之上的漕军、运丁成为传播金龙四大王信仰的重要媒介。漕军、运丁负责漕粮的运输,往返于运河之上,涉江过河,艰险无比,故建庙祀神,祈求保佑。《金龙四大王碑记》云:“至我国家长运特仰给于河,而役夫皆兵,沙梗风湍,岁以为患,四百万军储舳舻衔尾而进,历数千里始达京师。缘是漕储为命脉,河渠为咽喉,兵夫、役卒呼河神为父母,蔑不虔戴而尸祝之。”[4]丹徒、石门金龙四大王庙均为漕军、运丁创建。光绪《丹徒县志》记载丹徒县金龙四大王庙:“在城西西津坊关帝庙左,……万历末,运军及商贾建庙江口。”[5]
商人商帮亦是金龙四大王信仰的重要群体。康熙六十年(1721年),济宁商人于苏州府吴江县盛泽镇建金龙四大王庙。乾隆《吴江县志》记载:“邑故无庙,自山东济宁众商往来盛泽,遂建庙祀之。”[6]《敕封黄河福主金龙四大王庙碑记》云:“金龙四大王,河神也。立庙祭献,淮扬济泗间称极盛。吾江邑向无大王庙,其有于盛湖滨者,则自济宁州诸大商始。盖盛湖距县治五六十里,为吾邑巨镇。四方商贾,云集辐辏,所建神祠不一,而惟大王一庙,尤为巨丽。”[7]丹徒越闸有金龙四大王庙,为安徽商人所建,两江总督陶澍《丹徒越闸金龙四大王庙碑记》云:“丹徒越闸之有神庙,乃皖人之客于此者所建,其基购于镇海菴僧并店民纪氏。自嘉庆丙子始建神殿,道光丙戌,又增新楼及左右廊庑,既焕既崇,有严有翼,皖之人经此,必奉瓣香致散焉。”[8]
苏南运河沿岸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众多文人聚集于此,文人笔记、文集中大量有关金龙四大王事迹的记载,成为传播金龙四大王信仰的重要载体。明人刘荣嗣《简斋先生集》云:“前从夏镇见金龙四大王碑记,是姚现老笔序,其义不仕元及国初显应事甚悉,顾未知其为晋太傅裔也,得大作为之爽然。”[9]清人陆陇其《三鱼堂日记》亦云:“(夏镇)又有金龙四大王庙极壮丽,有姚公希孟碑文,大略言:‘金龙四大王,余初以为必龙神,及观朱平涵相国所著《涌幢小品》载神事甚详。”[10]清人彭孙贻《客舍偶闻》载:“长江大河之上,金龙四大王之神最为显赫,予意以为称金龙必神物之长水族者也,及读庙碑乃知神为宋诸生,浙东人,姓谢氏,兄弟四人。”[11]运河沿岸留下大量碑刻,往来于大运河上的文人深受影响,而文人又将谢绪事迹付诸诗文,推动了信仰的扩展。
3 金龙四大王信仰的功能及影响
运河沿岸的金龙四大王庙宇为往来的漕军、运丁及客商提供了重要的祭祀场所。常州府无锡县西门外坝后建金龙四大王庙一座,“每岁粮船将发,祭于此而后行。”[12]丹徒运河入长江水口处建有金龙四大王庙,清人郑光祖在其《一斑录》中云:“道光戊子正月,余往金陵,舟至丹阳,河流枯涩,……丹徒口水小不得入闸,多船停泊待潮,时值西北风,潮来甚小,闸不启者三日,众心共望东南风甚切,余不胜焦闷徘徊闸上,小坐金龙四大王庙,见壁上悬挂签诀一本,意欲藉以叩问神明。”[13]
金龙四大王信仰在扩大社会交往、增进社会互动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官员出于扩大与地方社会交流等目的,在修建庙宇过程中,往往发动士绅及民众广泛参与。此外,金龙四大王信仰的盛行,对运河沿岸民众社会生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特有的风俗习惯和祭祀活动,上文已有所涉及,在此不再赘述。相较运河沿岸的其他地区,苏南运河区域的金龙四大王信仰无疑更为民间化和本土化。金龙四大王信仰在运河沿岸民众中间也颇为盛行,形成了特有的风俗习惯和祭祀活动,这在地方志等史料中多有记载。清人魏标《湖墅杂诗》云:“江淮贩米泊粮帮,争赛金龙四大王。台下人观蜂拥至,乱弹新调唱滩簧。”[14]《苏州旧闻·龙王返驾》记载了当地民众祭祀淮安漕帮所携“龙王”之事:“淮阴清江浦船帮时都停泊在阊门外吊桥湾南童梓门,某日有船携来龙王,仅长尺许,盘于盆中,实一小蛇耳。金龙四大王庙僧人接入供奉,演剧娱神,热闹一时。”[15]无锡杨市镇北湖村有金龙四大王庙,建于清末,农历九月十七日为节场,演社戏两本,演戏时,半只戏台须搭在水中。[16]常州新北区大王庙坐落在罗墅湾镇南,建于清光绪年间,坐西朝东,为硬山式砖木结构,共三进,大王庙落成后,每年农历九月十七日这一天,由船商筹款,开坛纪念,称为“行会”,庙会风俗一直延续至今。[17]
大运河沿岸的金龙四大王庙宇不仅是行人的问卜之地,而且亦是运河文化景观的组成部分。清人龚士荐《谒金龙四大王庙》:“激荡中原气,灵光万古留。位非同相国,志已在春秋。封怒含沙尾,云横落远洲。丹青英爽近,极目大河流”。苏州吴江盛泽镇金龙四大王庙:“前辟三门,又旁开甲门,筑石径以达焉,取便也。若夫崇乎其中者有台,峙乎其左右者有楼,敞乎其前者有轩。其西偏为堂五楹,为轩三楹,疏池叠石,有亭翼然,岩洞幽邃。其东偏则起高楼,楼极宏敞壮丽。庭中列植嘉木,每春秋佳日,花卉映发,升高楼,望远山,白云缭绕,湖波淡沲,飞鸿灭没,渔歌欵乃,皆庙中胜概也”。[18]
4 结语
明清时期苏南运河区域河网密布,水路运输发达,商人和商帮数量众多,文人较为集中,再加上距离金龙四大王谢绪的桑梓之地较近,故其信仰较为盛行。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相较徐州、淮安等黄运交汇地区,苏南运河区域的金龙四大王庙宇数量并不是太多,这与当地并无严重的水患、神灵种类众多有着密切关系。相比水患严重、治河活动频繁的苏北地区,苏南运河区域的金龙四大王信仰更多体现出民间化、世俗化和本土化的特征,神灵更多扮演的是乡土神和地方保护神的角色。现今苏南运河沿岸地区已几乎找不到金龙四大王信仰存在的痕迹,对其进行相关梳理和研究,在深化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同时,亦为了解苏南区域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视角。
[1] 朱海滨.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2] (明)徐渭.徐渭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 江苏省苏州市浒墅关经济开发区.阳山文萃[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7.
[4] (清)仲学辂.金龙四大王祠墓录[M]//丛书集成续编·史部(第59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5] (清)何绍章,冯寿镜.光绪丹徒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29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6] (清)丁元正,倪师孟.乾隆吴江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19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7][18] 王国平,唐力行.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
[8] (清)陶澍.陶澍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2010.
[9] (明)刘荣嗣.简斋先生集[M]//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4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10] (清)陆陇其.三鱼堂日记[M]//续修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第55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1] (清)彭孙贻.客舍偶闻[M]//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杂谈类(第117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2] (清)陈梦雷,蒋廷锡.古今图书集成·常州府祠庙考[M].北京:中华书局;成都:巴蜀书社,1985.
[13] (清)郑光祖.一斑录·杂述四[M]//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92辑第915册).台北:文海出版社,2003.
[14] 孙忠焕.杭州运河文献集成(第1册)[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
[15] 王稼句.苏州旧闻[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3.
[16] 高燮初,朱小田.吴地庙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17] 常州市新北区政协文史委员会,常州市新北区社会事业局·新城文迹[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郑孝芬)
TheBeliefinGoldenDragonKingAlongtheGreatCanalofSouthernJiangsuinMingandQingDynasties
HU Meng-fei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Canal,Liaocheng University,Liaocheng Shangdong 252059,China)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the Canal region of Southern Jiangsu is not only an economically developed place,but also the one where people believe in Golden Dragon King. Its popularity resulted mainly in the realistic need of grain's transport and water shipping. The army of water transport,businessmen were the important medium of the belief spreading; the Literati and the Xie clan also promoted the extension of the belief by praising the heroic deeds of Xie Xv (who's named Golden Dragon King after his death). Golden Dragon King Temple along the canal met the ritual need of different social groups,played a prominent role in expanding social exchanges and enhancing social interactions as well.
the Canal region of Southern Jiangsu; water transport of grain; the belief in Golden Dragon King.
K248
:A
:1009-7961(2017)04-0001-04
2017-04-10
聊城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321051519)
胡梦飞(1985-),男,山东临沂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明清史和运河文化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