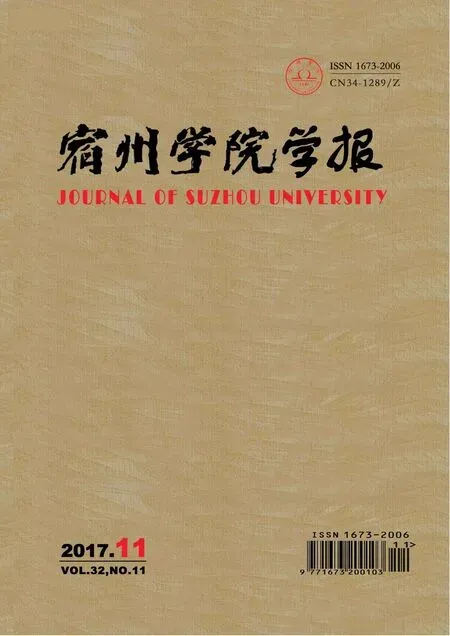转喻在语篇中的动态推理机制探究
——基于关联理论与认知语言学视阈
王 芬
龙岩学院外国语学院,龙岩,364012
转喻在语篇中的动态推理机制探究
——基于关联理论与认知语言学视阈
王 芬
龙岩学院外国语学院,龙岩,364012
为了厘清转喻影响交际话语的推理过程,在关联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内,选取生活中的一些即时会话为分析语料来考察转喻在交际话语中的工作机制。结果显示:关联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的融合研究对转喻工作机制分析有很强的阐释力,转喻工作机制贯穿于交际话语的生成、识解和语用效果三个方面,话语生成时转喻源域和目标域中概念的选择是受话语要达到的效果制约,听话者对话语的识解也需要从转喻的源域和目标域的映射对应出发,才能很好地理解话语,从而达到顺利交际的目的。
转喻; 关联理论;认知语言学;语用推理
1 问题的提出
转喻在认知语言学框架内被认为是一种比隐喻更为基础的认知方式,认知语言学认为转喻是ICM(理想化认知模式)内一种概念激活映射在另一概念的心理过程[1-2]。转喻的工作机制是基于邻近性的概念映射和认知凸显,这在认知语言学领域达成共识。近年来,在语篇层面上有关转喻的研究出现了理论交叉的趋势,国内在认知语言学框架内进行理论交叉研究日益增多。经过梳理发现,与转喻交叉的理论主要有关联理论[3-4]和批评话语分析[5]。理论的交叉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单一理论研究带来的局限性,拓展了转喻研究的新角度和新思路,这些研究目前方兴未艾,值得继续探索。Ruiz de Mendozaamp; Hernandez开始尝试将关联理论(Reference Theory,以下简称RT)和会话中的隐喻、转喻现象结合起来,他们认为隐喻和转喻能够建立会话含义的关联性[6]。Barcelona指出,根据语用原则可以分析隐喻和转喻二者目标域和源域之间的映射选择[7]。以上研究让学界看到了解决会话中转喻现象的新角度。国内学者将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结合起来研究语篇,也让学界看到语用学对转喻语用现象的阐释力。但这些研究的分析手段都有偏向性,注重一种理论对转喻语言的描述,语用学和认知学在转喻研究上结合得并不紧密。因为转喻在进行映射时为何是此概念被激活进行映射、凸显,而非彼概念;转喻生成后对交际双方是如何围绕转喻的语言推理将交际行为顺利开展下去等问题似乎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为此,本文将在关联理论和在认知语言学框架内研究语篇中转喻动态推理过程,并试图回答以上两个问题。
2 理论基础
2.1 关联理论
关联理论(RT)被认为是认知语用学的基础,因为他从认知的角度发展了格莱斯的会话理论,提出语言交际是一个认知推理的过程[8]。关联理论的核心是最大关联和最佳关联。最大关联是指人们在交际理解过程中付出尽可能小的努力而达到最大的语境效果。最佳关联是指人们在话语理解中做出合理的努力之后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 简单地说,前者倾向于话语理解的认知过程,后者注重话语交际后产生的实际效果。
2.2 RT对转喻的解释力及不足
RT认为人类在理解话语时倾向于用最小的认知努力来寻求话语中的最大关联,转喻的认知过程正好符合这一点。转喻被认为是认知突显[9],即人类通过抓事物的某一特征来认知事物,这一观点与Lackoff的理想认知模式不谋而合。当听话人在寻找转喻词语的关联中,会构建包括转喻的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邻近关系,并根据语境的制约,选择最大的关联,以达到交际的最佳关联。转喻是有规约性的,是一次性的,也是在线生成的。交际话语的生成和推测不仅涉及心智模式也涉及到社会、文化,是一种动态的心理意义构建和推理过程。因此,RT对转喻特别是对实时转喻有很强的解释力。
RT关注的是语言进行时的当下推理过程,不能解释深层次的认知机制运作即域的突显选择。虽然RT重视语境特别是动态语境对话语推理的作用,但弄明白映现关系的建立和交际效果,则取决于发话者的语音与语境相互关联的认知操作,这一点是关联理论所忽视的[10]。
(1) Peter:Will you go to the concert tonight?
Mary:The saxophone has caught a bad cold.
Peter对Mary 发出邀请,提出活动建议,这是一个明示交际行为,Mary利用saxophone中的转喻现象指吹奏saxophone的人生病了获得明示解释意,因此今晚不适合听演奏会。RT的解释到此为止,并没有指出为什么选择saxophone作为人的转喻指称的突显代表,而不是直指名字。也就是说,对RT而言,这一转喻的生成和理解并不是它关注的重点,它只在乎人们能否注意到这一转喻。
3 认知语言学
3.1 认知语言学对转喻的解释
转喻被认为是人类的一种认知方式。转喻主要发生在同一概念领域里,但是对转喻的工作机制分析却不尽相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转喻是在同一领域内的指称、替代、凸显,并没有体现出转喻的工作机制[11-12];另一种则认为转喻是在一认知域内一概念激活映射在另一概念域的心理过程[1]17。大量的研究证明转喻也是一种思维认知方式,因此必定有具体工作机制。邻近性是转喻发生的基础,也是转喻的重要特征。这里的邻近性可以理解为在同一认知域内的相邻关系,如“the head of the queue”(走在队列前面的人),这里的头和人在同一认知域内,将头作为身体部位中居首的特征来激活走在前面的人这一概念域。
3.2 认知语言学对转喻解释的不足
转喻现象在会话中普遍被采用,这也是一种间接言语行为。转喻在动态语境中受作用于知识﹑概念﹑社会文化因素以及当下的情景和情感因素的影响。发话者选择转喻﹑隐喻﹑反讽﹑夸张等手段达到交际意图。在实际会话中的转喻现象涉及命题概念的认知模型(心理框架和心智空间)与认知场景的运作。关联理论注重推理过程。实际会话过程注重交际双方的心智活动。发话者根据理性和预设整合作出语言选择,表达交际意图。受话者通过整合发话者的话语概念,包括概念转喻和隐喻,在一定语境场里激活双方共享概念域而作出话语推断,实现话语交际目的。因此,交际会话里的转喻机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推理演算过程。对来源域的选择涉及到心理认知模式、语言习惯、情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单纯的映射观、突显观、参照点都只是单一的关注其中一种心理认知模式,无法解释会话中来源域的选择制约因素以及如何进行概念整合来进行会话推理。
A:你是怎么来的?
B:我是坐“11”路车来的。
在这个会话中,认知语言学注重解释“11”的转喻生成过程。该理论认为“11”这个数字的型是源域,目标域是人的双腿,源域和目标域之间在形态方面发生转喻,用“11”来转指双腿。认知语言学的关注度到此为止,它并没有解释这个转喻的推理。
3.3 RT和认知语言学的互补性
语用学中的关联理论认为语用推理是一个动态的整合过程。动态整合体现在概念、双方身份、交际场合以及个人知识之间的整合[13]。语用框架下的概念整合只涉及具体哪些方面的整合,并没有关注整合的动态机制。特别是隐含会话中的转喻现象,转喻是典型的人脑左半球基本认知机制的概念和语言表征[14]1-19。因此,会话中的转喻现象一方面是具体因数之间的整合,更是认知机制的动态概念整合。转喻是跨域之间的映射,在启动具体因数的整合时,具体因数的概念内部也在进合。因为具体因数内部的概念整合会影响源域和目标域的限制选择,进而影响实际的交际意图,所以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对转喻的分析,可以让人们了解转喻内部机制的运作。但是有多少概念内容被激活映射,才能使人们的话语顺利进行,则需要语用原则的制约。
由于语言意义并非孤立存在,在人类互动中产生和传递,因此认知语言学所理解的语言概念及其基本结构也关系到社会和文化情境下的认知[14]3。对话语的生成推理和理解,主要是关注受话者的语用推理过程。话语的生成至少是二者的话语意义建构、推理和理解过程。一个交际话语的成功需要发话者生成话语,受话者构建心里表征、根据与受话者共享的社会、文化、知识进行话语回应,最后生成交际话语。交际会话都是在一定的语境下发生的,认知语言学和RT虽然都讲究语境,但是侧重不同。认知语言学的语境是指人们在与世界的互动中构成的对某一特定概念的心理经验网络构造。RT的语境观是话语发生在动态语境下,包括背景知识和知识。因此,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在解释转喻话语时是有互补性的。
Bierwiaczonek在综合现有的转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转喻表达式大致分为四种类型:形式转喻、指称转喻、命题转喻和以言行事转喻[15]。形式转喻属于词语的形态和句法现象;指称转喻是语义扩展的方式,虽在语篇中人称、事物也可发生指称转喻,但在此文中不是讨论的重点。命题转喻和以言行事转喻是语篇中概念整合以达到实际会话交际意图的主要现象,也是此文讨论的重点转喻类型。在关联理论和认知语言学框架内,分析在交际话语的隐含义(implicature)中转喻思维是如何体现在转喻语言和语言的转喻理解上的,转喻工作机制在参照点的选择、映射、突显上如何影响交际话语的生成、识解和交际效果。
4 实例分析
以生活中的会话场景为分析语料,运用关联理论分析转喻的动态机制。关联理论认为会话含义包括明示义(explicature)和隐含义。隐含义很大程度上涉及转喻思维、概念图式、话语理解和言语交际意图。
⑴ A:Why don’t you buy the dress like this one?
B:I don’t like this one.
⑵ A:Why don’t you buy the dress like this one?
B:My husband don’t like this color.
A:… (对B的识解)
例(1)是明示会话,“I don’t like”表明听话者的直接意图,不喜欢也就不会买。例(2)是隐含会话,这里的隐含义可以包括两个:女为悦己者容。“My husband don’t like this color”。例(1) 作为听话者回绝说话者建议的主要理由。例(2)表示惋惜之感,听话者喜欢,想买,但是碍于丈夫,只好作罢。所以这里的会话含义还蕴含了说话者的情感语气(在这不予讨论)。例(2)中无论是哪种含义都涉及了语言的转喻理解,说话人用他人喜欢来表明实际意图,可以把它看作是命题转喻和以言行事转喻。其背后的动机并没有涉及概念的映射,而是用其他命题来指代实际交际意图,即丈夫的喜好决定了说话者的实际行动。在转喻思维中源域没有选择儿子的建议,而是丈夫的喜好,是因为丈夫和妻子在服饰选择方面的密切关系。发话者从听话者的回答中得到的推理,有可能是丈夫的喜好就是听话者的喜好,或是丈夫的喜好阻碍听话者的选择。但是实际的会话交际意图则是听话者不会买这件连衣裙。听话者回答中的转喻现象除了是夫妻是一体外,丈夫这个源域是最佳的选择,女为悦己者容,所以在选择服饰方面,丈夫的喜好有很大的影响力。其转喻机制如图1所示。

图1 例(2)会话中的转喻推理机制
⑶“别动!……叫你别动就别动!”
“动一个‘裤脚管’有什么? ”
“什么‘裤脚管’?! ”
我不知道是哪根神经的传导,使这位双目失明的演员知道我在偷偷撩动翼幕。我习惯叫翼幕为“裤脚管”,这使他很生气,…… 他那无光却仍有魅力的眼睛,突然涌出两颗泪珠,挂在眼角上,不落下来。
……
他说:“ 一个完整的艺术品, 应当包括这个框架。翼幕就是舞台框子。假使把翼幕当成‘裤脚管’, 随便破坏它,那我们怎么能称得上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呢!”
这个对话是表现盲演员不能容忍某些演员对神圣的艺术不敬, 将舞台的翼幕戏称为“裤脚管”。盲演员和年轻演员之间刚开始的对话因“裤脚管”的变化而产生隐含意义。裤脚管和翼幕都是一个整体的最末位部分。其中,裤脚管是裤子最接近地面的部分,是最容易被弄脏,不被人看到的一部分;翼幕是整个幕布最靠近地面,最容易被弄脏的区域。二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翼幕被称为“裤脚管”兼有转喻和隐喻。转喻是基于二者有相似性,这里盲演员在推理话语中“裤脚管”时进行了转喻机制的启动,寻找二者的相似性。但是,为什么盲演员寻找到的形似之处是二者都是最接近地面的部分,是最容易被弄脏,不被人看到的一部分呢?因为青年演员的“动一个‘裤脚管’有什么? ”动作“动”、“有什么”预先设定了盲演员搜寻到是这一相似之处。话语推断限定了源域的选择,不是选择裤子的其他部分,如裤腰或裤袋等,而是裤脚。翼幕和裤脚管之间基于这一相似处的转喻映射为后续话语推理埋下伏笔。后面的“生气”、“泪珠”让人们知道盲演员对这一转喻不但不喜欢,还觉得是对艺术的贬低。最后盲演员觉得翼幕也是艺术的一部分,不能随意破坏,这体现了他对艺术的热爱,其会话中的转喻工作机制可以归纳为图2。

图2 例(3)会话中的转喻推理机制
5 结束语
从以上的会话分析可以看出,关联理论的两大原则制约着交际双发的认知推理和语用含义,从而制约转喻中源域的选择。而源域的选取跟会话所涉及的事件需要有紧密的联系。交际话语中如果涉及隐含意,发话者和听话者携带交际意图,决定隐含义中转喻源域和目的域的选择,交际双方对交际意图的识解取决于双方对转喻映射的认知框架,转喻映射的完整性和突显性影响交际效果,转喻在话语的生成、识解和效果的三个环节中贯穿始终。同时, 这一研究也为转喻的工作机制提供了更清晰的思路。
[1]Radden G,Kövecses Z.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y[C]// Panther K U.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Amerstam philadelphis: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9:1-27
[2]Barcelona A.On the Plausibility of Claming a Metonymic Motivation for Conceptual Metaphor [C] //A Barcelona 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Berlin/New York:Moulton de Gruyter,2000:1-28
[3]覃胜勇.关联理论角度中的转喻认知机制[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8):39-44
[4]江晓红.转喻词语理解的认知语用机理探究:关联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的整合分析模式[J].现代外语.2011(1):34-4l
[5]李克,王湘芸.修辞批评视域下的批评转喻分析模式新探[J].现代外语,2015(2):185-193
[6]L P Hemdndez.Cognitive operations and pragmatic implication[C]//L Thornburg.Metonymy and Pragmatic Inferencing.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3:23-49
[7]Barcelona A.Metonymy is not just a lexical phenomenon:On the operation of metonymyin grammar and discourse[EB/OL].[2017-04-15].http://www2.english SU se/nlj/metfest_08/Barcelona_08.pdf
[8]Sperber D,D Wilson.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Blackwell:Oxford,1995:1-335
[9]Papafagou A.On metonymy[J].Lingua,1996 (4):169-195
[10]张辉,蔡辉.认知语言学与关联理论的互补性[J].外国语,2005(3):14-21
[11]Lakoff G,Johnson M.Metaphors We Live By.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1-225
[12]Croft W..The Role of Domains in the Interaction of Metaphors and Metonymy [J] .Cognitive Linguistics,1993(4):335-370
[13]樊玲,周流溪.认知语用推理框架中的转喻 [J].外语学,2015(2):18-22
[14]Geeraerts D,G Kristiansen,Y Peirsman. Advances in Cognitive Sociolingusitics[M].Berlin:Mouton de Gruyter,2010
[15]Bierwiaczonek. Metonymy in Langue, Thought and Brain[M].Sheffield:Equinox Publishing Ltd,2013:1-300
(责任编辑:刘小阳)
10.3969/j.issn.1673-2006.2017.11.015
H030
A
1673-2006(2017)11-0066-04
2017-09-13
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概念隐喻与转喻语篇的动态识别机制探究——关联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的融合视角”(JAS160523)。
王芬(1982-),女,福建龙岩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