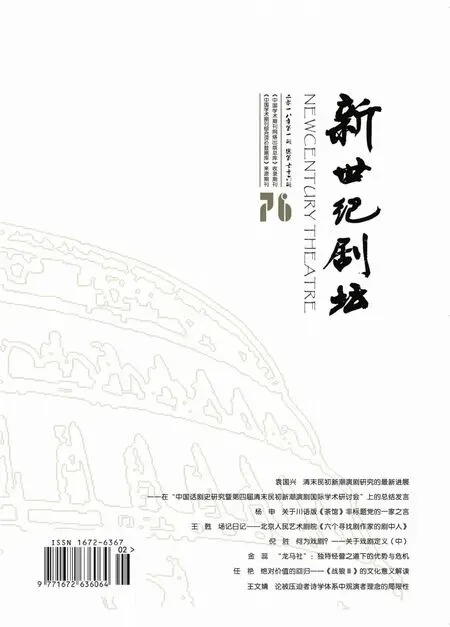不可回避的艺术现代性
——以芭蕾舞剧《化蝶》为例
时至今日,在探讨艺术的现代性问题时,我们应当意识到,现代性这一语汇在艺术领域内所属的范畴,已经不再单纯聚集在“集体”这个共性语词上,反之,越来越多的“个体”,以其具象性的生命存在感,招摇而又强烈地涌进我们的审美视野。这正是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强力表现。即便后现代意识终究不会成为主流意识,但是它对自由表达的推崇,却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渗透进艺术的各个领域,甚至跨过西方,滑落东方。也正因此,所谓艺术的现代性,已然成为当代诸多创作者自由伦理观念的畅然申述。
一、艺术现代性中的个体表达
我们都知道,自由伦理的申述方式就是“叙事”,而艺术天然地具备“叙事”的因子,无论是雕塑、绘画、音乐、舞蹈,还是戏剧,只要有思想、情感、意义的表达,就是“叙事”的轮廓,这个“事”,不仅仅是事件,更可以是一段情绪,一声叹息。如果说“叙事”是人类生命的古老机能,那么艺术就是我们需求表达和被表达的本质。不同的是,今天的叙事,很多已经从过去对集体、人民、传统英雄、大众的关注,转移到诸多微小的个体。普通个体生命对自我生活表层隐喻下的追问,或许更能打动观赏者的心。尤其在戏剧或电影的幽暗大厅里,我们常常在似曾相识的叙事轮廓里,完成了感同身受的心理实践。
足可见,在审美体验过程里,艺术具有一种天然的道德实践力量。它深知审美观赏者内心有着强烈的“内模仿”式的冲动,也有着强烈的对自我意识思考的渴望。所以,当下我们看到的艺术的现代性,正逐步抛弃对“集体”的模糊描画,而试图把握每一个“个体”的抽象脉搏和真实欲求。刘小枫先生在《沉重的肉身》里对个体生命从艺术化走向自由化的期许正在大众的审美浪潮里演变为现实。
二、芭蕾舞剧《化蝶》中的现代性呈现
辽宁芭蕾舞团近期与葡萄牙著名编导瑞洛·佩斯合作的《化蝶》,艺术地展现了艺术的现代性特质。该剧可以说是西方文化对东方悲剧的一次大胆解构和全新解读。从人物定位、动作语言、服装、音乐(除尾章处)等舞剧各个元素来看,我们都没有看到那个曾经盘亘在中国人心中数十年的爱情传说的依稀旧影。显然,在讲述方式上,编导瑞洛·佩斯抛弃了这一传统爱情故事原有的悲剧理念,甚至在人物情感设定上都重新进行了较为平等的刻画分配,最为重要的是,他拆解了故事的戏剧性。这种强力地运用西方抽象思维的对象性来描绘东方审美意象的艺术解构实验之所以能够成功,绝大程度上是因为观众对这个故事耳熟能详。
全剧不过45分钟,不分场次,用音乐的间歇性营造出八个段落,在家中、学校、路上、墓地四个场景的变换中,娓娓道来这个众所周知的故事。只是,在受众的舞剧观摩体验里,与以往动觉记忆截然不同的是,所有演员统一着练功服出场,这似乎意味着他们代表的不再是传说中的那些人物,而是褪去人物身份皮囊之下的灵魂。在演员一系列展示其人物性格的舞蹈动作中,我们才渐渐看到他们所诠释的灵魂角色与自身练功服上颜色的分类匹配。原来导演此举,如此别有用心。被刻意淡化的人设,凸显了内在的灵魂线条,而这种淡化溶解在空旷的舞台上,仿佛东方艺术里的留白,给每一位观赏者的审美情感留以巨大的写意空间。
这种大胆尝试不啻为对舞蹈本体理念的回归,让人不再沉溺于这个忧伤故事的内容如何被讲述,而是透过舞台,更多地去关注、感受所有人物的情绪生命。而舞蹈的原初意义不就是去表达灵魂的温度吗。可见,《化蝶》里的艺术现代性,在削弱传统戏剧的故事性的同时,却更为深刻地展示出剧中人物的灵魂世界。每一个蕴含着剧中人物情感脉搏的舞蹈动作紧密贴合着音乐,所营造出的连动画面在舞台上缓缓流淌而出。不同于观看传统芭蕾舞中为演员技巧性展示而喝彩,这一次剧场中的凝神屏息,是为那些忧伤无解的灵魂泣诉。
艺术的现代性意义莫过如此,不再沉溺于对宏大叙事的建构,而是透过纷繁复杂的世界表象,探究每一个个体内在不能言说的秘密。将个体的生命意义放置在空洞的群体性概念之上,是人类对自我精神的一次正视和解放,也是艺术趋向纯粹之必由之路。没有过多的道德功利性肩负,只有自由和美,是艺术永恒的追求。在《化蝶》简单而富于质感的舞台上,我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空旷的舞台,没有任何实景装置,没有道具,只有一层貌似现代二维码却更像古意竹纹的薄纱帘,置于舞台后方,仿佛现实与梦境、残酷与美好的隔离,巧妙地衔接着肉体和灵魂的各自独白,以及舞台时空的自由转换。这也恰恰是现代性艺术在表现形式上不拘泥传统的灵活性体现。
不同于西方经典爱情故事《罗密欧与朱丽叶》,祝英台对梁山伯的誓死追随,最终挚感天地,得以化蝶重生,这是东方爱情理念最完美的诗化观照。所谓因爱而生,死而美,大抵如此。导演瑞洛·佩斯也正是感受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舞蹈整体架构和动作编排上,剥开繁复的叙事外衣,从头至尾,重在诠释灵魂,使得整部舞剧充满了诗意性。正是这诗意性的情怀,让我们有机会抛弃旧有的观念和世俗成见,顺着每一个人物的灵魂线条,看到其情感轨迹。这种透视,让我们对马文才、祝英台的父母都有了全新的解读。不再是面具型的单一人格,我们看到每一个人物内心有着同我们一样的矛盾冲突。比如马文才对祝英台发自内心的喜爱,对其另有所爱而发自内心的妒忌、挣扎和痛苦,又比如在全剧快进入化蝶的尾声之时,马文才空荡的手臂里,永远触碰不到的爱人的灵魂,那种酸涩的苦楚,曾几何时,都轻易地埋葬在世人对其不假思索的谩骂声中。而对于祝父、祝母,谁又曾真切地体味过他们在那种时代背景下取舍的由衷?以及他们最终丧女的哀痛?所以,艺术的现代性中对个体的重视和关注,终于让我们能够放下成见,用诗化的情感,与他者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与自我的灵魂做真切的沟通,让我们能够超越传统演绎中的礼教束缚,去关注真实的生命本身。所以,舞台上最终显现的,是一个个具象鲜活的个体生命,一个个生动脆弱的个体灵魂,而非片面绝对的善与恶,好与坏。
最终化蝶的时刻,那层曾经分离现实和梦境二元世界的薄纱终于缓缓升起,伴随着传统《梁祝》的主题音乐旋律,舞台彻底成为纯粹的理想梦境,在这梦境里,祝英台唤醒了梁山伯的灵魂,彼此终于可以为自由而踏实地活下去。这何尝不是全人类至情至性的纯真理想。舞台上这一时刻的美,纵然忧伤,却超越了时空,化为永恒。
一部舞剧,音乐自然不能不提。这部舞剧的音乐也充满现代性。传统芭蕾舞剧运用并造就了诸多画面感极强的主题性音乐。而这部《化蝶》除了结尾出现传统《梁祝》音乐的主体旋律外,其余段落,皆是现代感极强的弦乐展示。弦乐一方面拉伸了生命对永恒的渴求,体现了其充满伤感的坚韧性;一方面又在被打击乐的不间断敲击隔断中展现了理想与现实撞击后的破碎,以及人物内心不能解决的矛盾境况。在这里,音乐不再刻意描绘画面,而是重在渲染情绪,一个音符的轻跃,连一声叹息都不放过。
可以说,芭蕾舞剧《化蝶》的舞台整体呈现对艺术现代性是一次全面而成功的展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艺术的现代性可以肆意充斥任何领域。“现代性”终归只是一种“意识”,它并非无所不能,更不是左右审美的评判权威,它不代表真理。《化蝶》拆解的是我们熟悉的故事,所以我们能凭借旧有的记忆痕迹找到舞台诠释的突破口,而它能与西方现代意识相融合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部舞剧的动作元素是芭蕾,而且是极具象征意味的现代芭蕾。
三、现代性理念的自由维度
艺术的现代性意识的确从某种程度上扩大了我们创作理念的自由度,但是这个自由是有限度的,即便是个体伦理的表达也应该在一定的道德规范之下。如果我们把以中国古典舞为主要动作元素的舞剧进行现代性意识的舞台处理;或者将一部充满地域民族特质的歌舞剧配以现代性意识极强的音乐配器手段;又或者在处理某些历史性重大题材上,偏偏要回避集体行踪而凸显个人狭窄视角;再或者将个体申述发展至无病呻吟、变态扭曲、魔性宣泄的境地……我相信,那都将是自毁艺术。虽然在现代审美境遇下我们几乎无法回避艺术的现代性问题,但是,不要试图简单、盲目地拼贴和迫不及待地装载“现代性”,这种尝试只能是流于形式,让人心生隔阂。比如孟京辉的《女仆》,又比如诸多现代戏曲作品里那些时刻让人出戏的惊人语汇。
如前所述,现代性是一种思想意识,一种人文理念,不是能够生硬照搬的技术手段,不是被凭空割裂出来的口号标语、装置形式。它必然有其历史性的文化基因存在,同时它也是变动不居的,因为在当下,自由伦理申述是每一个个体最渴望的生命诉求,所以当下的现代性才有了自由申述的内涵,随着时代的行进,艺术的现代性指向必然会有所变迁。甚至于东西方的艺术现代性理念幻化在舞台上的审美形式都理应有所差异。所以,我们不能抱守唯一,也不能全盘西化。正因此,某些舞台艺术作品如王晓鹰导演的《红色》,在整体审美现代性的把握上,不够深入人心。单纯西式化的处理始终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翻拍的经典的外国戏剧,我们看不到中国美学视角下的舞台艺术呈现和艺术处理,没能让这个戏剧褪去国别的外衣,呈现更好的思想精髓,与大众产生更具有融合性的灵魂击撞。如果说《化蝶》是用西方思维解构东方意象,最终呈现出西方伦理价值观,那么《红色》,也应该尝试运用东方思维来架构、挖掘人类共通的审美情感。
戏剧虽然是舶来品,但是它应该衔接上民族的气息,在中华民族优秀而古老的传统文化理念下,焕发出崭新的东方意蕴。
前段时期,编剧万方的《新原野》在盛京大剧院上演,除去剧本对女性内在情感生命体验挖掘不够的硬伤之外,该剧在舞台的整体呈现上竟出乎意料的精彩,一个东方故事与一位外国导演的美学风格竟然能够如此贴切融合,一方面在于观众的审美新奇感使其乐于接受新鲜的观感体验,另一方面在于东方美学意识里有诸多能够与这位导演舞台理念阐释相通的视角。而后者对于剧作的流传显然更为重要。因为东方式审美元素永远是中国大众审美心理的首要接受范式。
所以,无所谓创作素材的国别,也无所谓创作人员的国别,如何真正地沉淀、摸索到中国审美视域下的艺术现代性理念,及其符合中国大众审美心理的贴切表达方式,似乎真的需要好好探索一番。
曹禺先生对创造真正属于中国人审美特点的中国式话剧的理想,直到今天,也未有几多成功的尝试。那种“抬腿就走、撂地儿能演”的带有中国味道的戏剧作品,却是最考验艺术家真材实料的。创新和创造,都需要寻路者的勇气,然而艺术的感人之处不就在此吗?我们都知道,有时候世俗的审美意识从来不会去等待艺术创作者的自我觉醒。但是,这些审美意识流大多只是大众的盲目判断和无意识追崇。所以,抛开现当代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真正的艺术创造,应该慎终如始,清醒自觉,不被左右,不改初心。
刚刚落幕的《老舍五则》就是最好的例子。始终空灵利落的舞台,体现了导演林兆华鲜明的个人风格,这风格未必有多高明,但是却给了表演足够的留白。这个充满中国式审美张力的舞台,却将舞美艺术的现代性展现到极致。许多人说这台戏就像演员在闲话老舍的课本剧,人物之间没有太多鲜明的舞台戏剧性。可是,演员真实自如的表演所建立起来的与观众之间的情感纠葛算不算一种戏剧性呢?我惊讶于这台戏剧给予我如此强烈的“在场性”感受。这难道不是戏剧最原初的审美动力吗?虽然这五个故事都是对过往的呢喃,可是我的生命情感却如此关心它们暗含的叙事结局,这又算不算一种戏剧艺术的现代性体验?
或许,该是时候转变观念了,究竟什么是舞台戏剧性?什么又是对其评判的标尺?要知道艺术总是在不断尝试建立规则又不断去尝试打破它们,艺术自身尚有如此的勇气,我们又何必固执到底呢?毕竟真理用于追寻艺术理想,而非评判艺术本身。可贵的是,艺术的现代性意识对个体迥异价值观的“宽容”也在于此。
抛却了一切世俗规范和社会形式的我们,在幽暗的剧场大厅里,透过舞台,与艺术相连。无所谓东方西方,也无所谓新旧,艺术的现代性就是让我们用真实的自我去感受舞台上一切发生着的灵魂困境。如果生活注定是一种欠缺诸多生命体验的过程,那么艺术就是对这种欠缺最好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