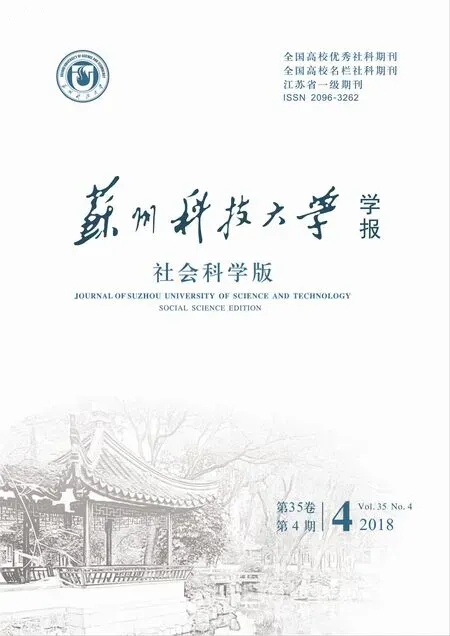试论柳亚子人格的文化生成*
陈友乔,秦晓慧
(1.惠州学院 国学与传播研究中心,广东 惠州 516007;2.潍坊护理职业学院 公共基础部,山东 潍坊 261041)
柳亚子(1887—1958),江苏吴江人,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领袖,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就人格而言,柳亚子身上带有浓郁的名士气质:一方面,具有狂狷、率真、风雅等传统文人之性;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以道自任、崇尚名节等士大夫气质。人格与文化有着不可割裂的内在关联:一方面,文化是人格生成的土壤;另一方面,人格是文化的投射。一般说来,对个体人格的生成、发展发生作用和影响的因素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客观的文化情境,二是主观的自我选择。而文化情境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又可以细分为社会家庭、文化心理等单元。就柳亚子而言,由于地域文化传统、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社会实践等文化单元的机缘凑泊,加上强烈的主体选择,形成了他特有的人格特质。
一、地域文化传统:柳亚子人格生成的摹本
地理是历史展开的舞台,是知人论世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地理是历史的舞台,历史即地理的骨相,读历史如忽略地理,便失去其许多精彩的真实意义。”*参见王恢:《中国历史地理·编著大意》,转引自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考察地域文化传统对柳亚子人格生成的影响,其胞衣之地的吴江,乃至苏州、江南都应纳入研究视野。
自三国孙吴以降,经过长期的开发,南方经济后来居上,到唐末、北宋末分别完成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的南移,中经南宋、元朝而至于明清,江南经济、文化的优势得到进一步加强。李伯重指出:
江南是明清中国科举应试教育最发达的地区,科举功名之盛,甲于天下;但同时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和出科技人才最多的地区。[1]
明清江南是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而苏州则是江南的中心。在苏州府各邑中,吴江经济遥遥领先。以吴江盛泽镇为例,其以丝绸业闻名:
凡邑中所产,皆聚于盛泽镇,天下衣被皆赖之,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来买者,摩肩连袂,如一都会焉。[2]
吴江发达的经济、文化催生了繁荣的声伎业,晚明名士、名妓联袂演绎了一幕幕江左风流的活剧。陈寅恪亦论及于此:
吴江盛泽诸名姬,所以可比美于金陵秦淮者,殆由地方丝织品之经济性,亦更因当日党社名流之政治性,两者有以相互助成之欤?[3]
吴江向为出产名士的风雅之地,有“见秋风起而思莼鲈”的魏晋名士张翰、挟伎泛舟分湖(今称汾湖)的元代名士陆行直、满门风雅的吴江叶氏文学家族的领军人物叶绍袁等。值得一提的是,吴江是几社、复社活动的中心区域,复社的第一次大会就在吴江尹山举行,孙孟朴、吴扶九等吴江名士均为复社眉目。江南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无疑是可以沾溉后世的。陈平原谈及晚明陈继儒一类名士时认为,由于清廷的文化专制,加之顾炎武等人基于亡国之痛而进行严厉抨击,以致风雅中辍,在晚清再度“复活”,“中间一隔就是两百多年,到了晚清以后,又是这一块地方,又是这一批文人起来了”[4]。
地域文化传统使柳亚子的名士特质浃髓沦肌,尤其是几复名士的流风余韵,更是他心摹手追的对象。柳亚子曾与陈去病、高旭等人在清季党禁松动和社团活动空前活跃的背景下,以民族革命为旗帜,追踪几复风流,发起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在成立南社之前,陈去病进行了预演,发起了“隐然是南社的楔子”[5]6的神交社。在《神交社例言》中,陈去病毫不掩饰地指出,神交社发起的时会地域乃至组织规程,均是以几复为型模,“考复社虎阜往例,来宾咸挟一小册,书是日与会者姓名而去。慎交社例同,今即仿之”[6]。柳亚子虽未预神交社雅集,但他对于几复风流的向慕之情溢于言表:
降及胜国末年,复社胜流,风靡全国,其意气不可一世。迨乎两京沦丧,闽粤继覆,其执干戈以卫社稷者,皆坛坫之雄也。[7]193
1908年1月,柳亚子、高旭、陈去病等在上海酒楼聚会,通过了陈去病提出的继续晚明云间几社结社事业,并定名为“南社”。此后南社正式进入酝酿阶段。在南社的筹备阶段,柳亚子反复强调南社与几复风流的历史传承。“复社逃盟更慎交,百年坛坫属吾曹。”[8]1011908年3月,柳亚子赴沪,有见于结社诸人星散,不能有所作为。面对上海酒楼聚会合影,柳亚子感慨赋诗:“鸡鸣风雨故人稀,几复风流事已非。”[8]61南社尚未成立,柳亚子就得到上海酒楼结社中的刘师培夫妇降清的消息,刺之以诗,发抒荃蕙化茅之痛:“千秋谁信舒章李,几社中间着此贤。”[8]99这期间,柳亚子积极推进南社成立的进程,并担负着很多实际的工作。如其所谓:
我是以梁山泊上小旋风柴进自命的,在复社是自比于吴扶九、孙孟朴,自然是要尽奔走先后的职务了。[5]10-11
1909年11月13日,仿复社旧例,南社在虎丘正式成立。柳亚子诗以纪之,诗题中有云:“盖社事零替以来,三百年无此乐矣!”[8]115南社之后,柳亚子还先后发起新南社和南社纪念会。
联盟结社、诗酒风流的名士风雅,已经淀入柳亚子的骨髓。南社成立后,仿晚明名士结社旧例,定期举行雅集,狂歌痛饮,事后印行诗文。1915年5月9日的第12次南社雅集之后,柳亚子偕高燮、姚石子同游杭州,在西泠印社举行南社临时雅集,在冯小青墓畔为冯春航题名勒碑纪念,一共流连了二十多天,三人所作诗结成《三子游草》印行。其中,柳亚子有诗二十余首。柳亚子自谓:“胜概豪情,自命不可一世。”[5]731915年中秋,柳亚子还与里中友人顾悼秋、沈剑双、凌莘子等人发起酒社;此后直到1920年,每年中秋前后都在金镜湖上狂歌痛饮,抒发牢愁。“以中秋水嬉之夕,大会于秋禊湖上,画舫清尊,穷日夜忘返。”[7]567其中以1919年为最盛,与会十三人,撰诗五十余首。柳亚子仿乾嘉《诗坛点将录》作《酒社点将录》,并撰叙;他还裒集酒社历年唱和之作——《酒社中秋唱和集》并撰叙。最见其名士意态之狂的是,柳亚子效仿名士杨维桢(号铁崖)携妓游分湖的故事。*至正元年(1341)春,杨维桢应隐居武陵溪的诗人顾逊之邀,结客七子(会稽杨维桢、甫里陆宣、大梁程翼、金陵孙焕、云间王佐、吴郡陆恒、汝南殷奎),乘坐钓雪舫大游分湖。在“雨甚急”的情况下,乘坐“晓风残月之舫”,“决游分湖”;同游八人,“盖较武陵溪主人(指顾逊——引者注)增一客、减二妓焉”[7]604。
计斯游自启程至返棹,为日浃旬,得诗百数十首,而朋俦唱和之作尚不与,信乎山川寥落后之豪举矣。以视铁崖当日,草草撙罍,寥寥篇什,徒以伎人行酒,夸耀俗流者,又遑敢谓方今之不如古昔也。[7]607
这种自觉的模仿还在于,杨维桢作《游分湖记》《游分湖诗》,柳亚子亦作《游分湖记》,他还将狂游期间友朋赓酬唱和之作裒辑成册,名曰《吴根越角集》。柳亚子的狂游分湖,除了没有携妓之外,出游规模、诗词数量等方面远迈前人,可谓狂态豪兴毕现!柳诗云:“越角吴根一棹秋,铁崖去后我来游。”[8]323几复名士之性,是柳亚子挥之不去的“意结”。20世纪30年代,柳亚子在落寞之余致信次女无垢,感叹昔日文酒风流不再:
你们吃酒赏月倒写意。我们是没有什么酒吃,照常地老早就睡觉了。……想起从前在黎里闹酒社,闹得真高兴,却不胜其今昔之感了![9]
作为南社领袖,柳亚子念念不忘再作冯妇,重操南社旧业。抵达北平后,他把南社雅集的大本营从上海搬到北平,把昔日狂歌痛饮的乐土从分湖移到昆明湖。在这里,柳亚子与旧雨新知宴饮赋诗,斗酒斗诗,谈诗论政,优游竟日。柳亚子发起规模大、规格高的南社、新南社联合临时雅集, 他甚至希望继承南社遗风,建立北社,“应开北社承南社,更废南都建北都”[8]1565。
二、家庭环境:柳亚子人格生成的深层反应堆
家庭环境是文化对个体人格模塑的一个中间驿站,个体通过家庭与社会的接触,最主要的是通过家庭成员施加的影响来完成社会化的。坎托指出:
某个家庭里的成员同时也是更大范围群体的成员,他们在家中所保持的常规与更大团体的常规相同,他们所作出的各种反应刺激了家里的年幼的成员,使之具有更大范围群体的文化素质的特征。[10]255
弗洛姆强调:
儿童的性格模式是在其父母的影响下形成并发展的。父母和他们培养孩子的方式又是由他们所处的文化的社会结构决定的。一般的家庭是社会的“精神培养处”,通过使自己适应家庭,儿童养成了性格,在日后的社会生活中,这种性格能使他适应他所必须完成的工作。[11]
柳亚子的家庭环境对其人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柳氏原籍浙东慈溪,南明时迁至吴江东村,北厍大胜柳氏是其中的一支。柳树芳是柳亚子的高祖,他是大胜柳氏在文坛的开山祖,完成了柳氏从自耕农向文学世家的过渡。柳兆薰是柳亚子的曾祖,中过举人,担任过教官,希望子孙沿着祖先规划的方向走科举仕进的道路。此后,每一代都有获秀才及以上功名者。对此,柳亚子不无自豪地声称:
我的家庭,真是一个美满的家庭。所谓书香门第,耕读世家,在我是当之无愧的。[12]44
柳亚子的名士基因得益于这个大家族的濡染。在这个大家族里,亲友中多名士。父亲柳念曾是本地的乡绅兼名士,通经书、文辞、书法、围棋,喜品茶、听评弹。母亲费氏师从吴江名士徐山民的女儿徐丸如,而徐山民、吴珊珊夫妇则是袁枚的弟子。因此,就师承渊源而言,柳亚子可以算得上袁枚的“四传弟子”。此外,柳亚子还深受舅祖父凌退修的影响。凌退修是一个“爱国病”患者,因为甲午中日之役的败局而忧愤不起。柳亚子对他歆慕不已:
砺二爷是名士,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家,目光如电,心光如轮,是情愿牺牲小己,完成国家大业底第一流、了不起的人物。[12]64
柳亚子还煮酒论英雄:
要是退修先生不死,一旦蛟龙得云雨,还怕不是老康一流人物?……但他的抱负,他的主张,今天还得由我记录下来,传之于天下后世。那末,据我的估计,吴江的政治家,在过去只有退修先生,在现代只有我柳亚子。[12]66-67
柳亚子的士大夫气质是从童年时被灌注的。正是基于慎终追远的文化心理,祖先的荣耀成了他无形的道德资源和奋斗动力。柳亚子回忆儿时情形:
就是曾祖父在时,他自己觉得年纪太大了,精神渐渐不济,而对我又是抱着非常期望的。他常常说道:“我老了!也不指望看见小和尚发科发甲,我只要能够看见他上学的一天,也就心满意足了!”[12]56
曾祖去世时,柳亚子只有四岁。五十多年后,在抗战时期的桂林,柳亚子对曾祖的恩德仍念念不忘:
照我个人那时候小小心坎上的想头,对于我曾祖父真是希望他长生不死哩!因为他对于我的恩德,实在太大,而对于我的印象,也实在太好了。[12]53
他向以士大夫自许:
我虽然没有发科发甲,但现在活到五十七岁,还未曾脱掉读书人的本色。我常常自命为典型的中国士大夫,始终抱持着天地正气,不为威屈,不为利诱,虽然太太骂我为神经病而不悔。[12]56
柳亚子应邀参加政协会议,抵达北平后径直向毛泽东提出任职江南的要求,“欲借头衔荣父老”[13]1616;并以“吴江一品大臣”[14]229自居;在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之后,他马上衣锦还乡,拟看望苏沪一带的亲朋故旧:
我这次南巡,共来还三个礼拜。到了上海、无锡和南京。苏州和黎里都没有去,因为陈毅将军不许我去也。[15]399
迁居北长街八十九号后,柳亚子在志得意满之余坦露心曲,“王侯第宅皆新主,居然朱门华桷矣”[12]380。对此,所谓“贪心不足”“要这要那”“私心发作”一类评价*关于柳亚子的“牢骚”诗,在“文化大革命”的语境下遭到批判,相关的研究论及此点。参见应靖国:《这也属不实之词——对柳亚子〈感事呈毛主席〉一诗解释的质疑》,《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第61-63页;黄波:《寂寞一诗翁——重说柳亚子》,《书屋》2007年第3期,第42页。,均未能着其痛痒处;唯有用士人光耀门楣的心理来照察,他的这种行为方式才能获得更为圆通的解释,才更加顺理成章。
三、学校教育:柳亚子人格基色的奠定
学校较之家庭,是一个目的更为直接、计划更为系统的文化场所。弗洛姆认为,教育方式是形成人格的一种机制,对于个体人格的塑造,虽非决定性的,但起着重要作用。
教育的社会功能是促使个人具有将来在社会中起作用的功能,即是使个人的性格向社会性格方向靠拢,使个人的欲求符合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需要。……虽然教育方式并不是某种特定的社会性格的致因,但是,它们都是促使性格形成的一种机制。[16]
坎托也强调,学校教育对个体人格的影响在于,它使儿童人格趋同。
在这种文化化背景之下,儿童主要获得了各种知识反应,也就是说,他具备了在某一特定的学校上学的所有人共同的种种理性见解。[10]256
柳亚子也接受了各种教育元素,并对其人格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柳亚子接受的教育新旧杂陈。他前段接受的是系统而规范的旧式科举教育,并且赶上了科举制度的末班车,取得了最低等级的秀才功名。柳亚子从两三岁开始,就在母亲的指导下接受启蒙教育,五岁正式上私塾。私塾是他学校教育的起点,在这里,逐步形成其名士气质。这些塾师基本上是一些声名等级有差的名士,其名士做派对柳亚子起了很大的熏染作用,他们甚至还手把手地教他做名士。*柳亚子谈及塾师马逸凡老师教他效名士与人订交,交换“兰谱”, 王云孙王老师教他下棋、喝酒。参见柳无忌、柳无非:《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83页。因此,在十岁左右,柳亚子就有着与两位塾师“把酒看花,赏玩秋光”经历,并暗生才子佳人的情愫:
大概我的名士脾气,就是在这十岁的时候开始养成的吧。黄老师又喜欢看小说,他肚子里的东西很多,口才也不差,能够绘声绘色的演讲出来。……在情窦初开的我,听起来自然津津有味,想做起佳人才子的勾当来了。[12]82
十三四岁时,柳亚子开始在报上发表香奁诗,玩起了美人香草的一套,并一发不可收拾。
但从此以后,我做开了头。便常常做起无题诗和香奁诗来,从李玉溪、韩致光一直做到王次回、黄仲则。[12]119
十五岁时,柳亚子与同赁黎里镇寿恩堂的另外两家所聘的塾师往还,指天画地,声震屋瓦。[12]124-125
柳亚子后段主要在上海爱国学社和同里自治学社接受新式学堂教育,既不系统,为时也很短,总共不到三年的时间。爱国学社、自治学社的自由学风,正与其率性任情、遇事辄发的名士之性相契。在爱国学社时,柳亚子经常与章太炎、邹容、金一(天放)等人一起下馆子、题诗。在同里自治学社时,柳亚子天马行空,我行我素。为了参加朋友冯沼清的“苏苏女校”庆典,在社长委托人不批准的情况下,柳亚子斩关夺将,公然违反社规,甚至连社长金一都不放在眼里。[12]192-193
这一时期,章太炎对柳亚子人格生成的影响不容忽视。在清末民初,发生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回潮现象,士人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认同,出现了一批“隔代”名士。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体现魏晋回响。“魏晋时期的思潮,正是由务实转向崇虚,由客体转向主体,由群体转向个体,与民元之初的思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也有一些可资借鉴的有益之论。”[17]“倘以文人心态论,晚清与魏晋确有不少相似之处。”[18]这类名士以章太炎及章门弟子如黄侃、鲁迅等为典型。二是几复名士的地域复活。在党禁松弛以及社团活动空前活跃的背景下,催生了追踪几复的名士团体——南社。有人指出:
清末民初文人结社之风的复兴,上法晚明、回首前尘,可谓已经成为其中挥之不去的“情结”和无法绕开的“心病”。[19]
就柳亚子而言,由于地域文化传统,其人格得几复名士为多;但同时受章太炎的影响而带有魏晋名士的气质。柳亚子自中年后就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常常闹着神经兴奋和神经衰弱的把戏。兴奋时其热如火,衰弱时其冷如冰,终于没有和平中正的一天”,柳夫人呼之为“柳痴子”, 称其受“章痴子的道统心传”。[12]79柳亚子也有一股“疯态”,从中可以见到章太炎的影子:亡命日本期间,他杖逐好为人师的不良老人[20];三十年代,他还因“细故”棒逐诗友林庚白[21-22];抵达北平后,他在颐和园乐善堂“一怒冲锋”[12]360,在景福阁骂哨兵[12]367,在华北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以墨水瓶掷卫兵[23]。此外,受章太炎影响,柳亚子也以善骂闻名。南北议和时,柳亚子“天天骂南京政府,骂临时参议院”,“把袁世凯骂得狗血喷头”[5]39-40。在南社诗论启衅中,柳亚子以街巷谩骂之语施之于南社内的反对派朱鸳雏,甚至袭用了章氏的“名骂”*民元前,章太炎与吴稚晖因《苏报》案发生龃龉而互詈。章氏骂吴氏,至有“善箝而口,勿令舐痈,善补而裤,勿令后穿,斯已矣”等粗鄙之语。后柳亚子骂朱鸳雏,“嗟嗟,杨锡章门下之弄儿,周维新幕中之契弟,下流所归,君子不齿,善箝而口,勿令舐痈,善补而裤,勿令后穿,斯已矣,何狺狺狂吠为”。参见柳亚子:《磨剑室文录》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6页。。旅桂期间,因不许举办鲁迅先生六周年祭,柳亚子像“长桥上骂知县”一样,把“省当局大骂一顿”[24]1463。友人评价他的使酒骂座:
柳先生喜做诗,也爱喝酒。……他喝了酒,有时也会骂,我曾亲见过几次,因此我想当年复社诸君子痛骂那《燕子笺》作者阮大钺(铖)的情景,大概也是这样。[14]48
柳亚子对章太炎的敬慕之情老而弥笃。他在颐和园接待俞平伯夫妇时赋诗感怀:
余杭门下负传薪,敢与周吴竞德邻。贱子髫年惭受莂,本师晚节定完人。[13]1621
因之,这段新式学堂的教育经历,固然为柳亚子的知识结构增添了新质,使其传统价值观念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但就根本而言,非但不能对其名士气质进行脱胎换骨地改造,反而起了助长作用。
四、社会实践:柳亚子人格的存养
社会实践也是影响个体人格形成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说来,个体的人格状况总是通过人的道德实践深刻而完整地表现出来。王晓明强调人文精神的实践品格:
如果把终极关怀理解为对终极价值的内心需要,以及由此去把握终极价值的不懈的努力,那么我们讲的人文精神,就正是同这关怀所体现,和实践不可分割,甚至可以说,它就是这种实践的自觉性。[25]
对柳亚子而言,早年的教育经历奠定了他人格的基色;在此后的社会实践中,他的名士特质基本未受干扰地以近乎原生态的形式被保存。
柳亚子有着丰富的社会经历。他先后就职于新式文化机构,充当过学堂教师、报纸主笔、南社领袖等社会角色;他还积极投身政治,先后加入同盟会、光复会、国民党,担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委、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务。深有意味的是,这些社会角色竟然与其名士之性兼容无间。
民元之前,作为“双料的革命党人”*1906年,柳亚子由于高旭、朱少屏“两人介绍,加入了‘同盟会’。一方面又由蔡孑民先生主盟,参加了‘光复会’,算是双料的革命党人”。参见《自传·年谱·日记》第199页。,柳亚子总是以一副名士面目示人。在上海“健行公学”时,革命者、教师、报人、名士等诸多身份竟然能在他身上和谐共处。
这样,丙午的上半年,算在“健行”住下,一面教书,一面编《复报》,还要喝酒赋诗,常常和天梅相酬唱,诗兴也越来越浓了。[12]200
民国初年,柳亚子先后供职于《天铎》《民声》《太平洋》等报馆,因灰心国事,一度热衷于捧角,“大喝花酒”,俨然一副“妇人醇酒”的做派,动辄“浩然有归志”[24]1176-1177。并且,他在革命活动中追求那种“千里搭帐篷”的热闹场面:
《太平洋》的局面是热闹的。大家都是熟人,并且差不多都是南社的社友。不是的,也都拉进来了。那时候,可称为南社的全盛时代。[5]42
这种请客吃饭式的革命,带有浓厚的名士雅集意味。
南社时期是柳亚子名士性格最为张扬的时期。对柳亚子而言,南社是一个重要的亚环境。在这里,他身上的名士基因被激活,且大放异彩。南社是柳亚子终身以之的事业,南社之后有新南社、南社纪念会,甚至抵达北平后,他还组织了南社、新南社临时雅集。柳亚子孜孜于南社事业,固然是由于他与南社近乎二位一体的关系:一方面,南社成就了柳亚子在近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另一方面,柳亚子对南社倾注了满腔心血,贡献颇巨。但是,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作为名士团体的南社,“与柳亚子的革命倾向、名士习气、诗人激情极为契合”[26]。柳亚子与社友流连山水,诗酒酬唱,其名士之性得到淋漓尽致的挥洒。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南社,柳亚子就不成其为柳亚子,其名士之性至少要大打折扣,更不用说“最后的名士”了。南社是柳亚子开展文化生产、社会交往、公共影响的重要平台。南社的实际创始人陈去病、高旭把他引上革命之路,并先后加入同盟会、光复会、国民党。南社中很多人是同盟会、国民党的重要成员,如汪精卫、廖仲恺、叶楚伧、戴季陶、于右任、马君武等。柳亚子借此广泛地获取政治资源,并进一步拓展,结识了大批国共要人,使得他无论在国民党内还是在共产党内都有一层保护网。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由于他律与自律的双重作用,被改造者的风雅基因被人为地删除了,柳亚子则获得了一定的豁免, 在名士谢幕之际,他还奏了一曲《广陵散》。因此,柳亚子拥有的在中共高层的保护网,是其荣膺“最后的名士”的至关重要的一点。
纵观柳亚子的一生,他基本上没有受到体制的规约,这是其未被扁平化而保持名士之性的重要因素。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柳亚子当过三天大总统府秘书后就“胜利大逃亡”了:
天天游山玩水,喝酒做诗。这样搅了三天,我的身子吃不消,忽然发起寒热来,只好对不住铁崖,卷铺盖而出总统府,还到上海来当流氓了。[5]39
“献身党国”[12]21之后,柳亚子“睹党中诸领袖态度,知天下事未可为,始浩然有退志。既返里,蛰居弗出者数月”[24]1068。20世纪30年代,柳亚子担任上海通志馆馆长期间,极力经营自己的独立王国:对作为上级机关的上海市政府,我行我素,决不肯轻易迁就;对内而言,垂拱而治,坚卧不起。柳亚子绝不接受组织或党魁的约束。对于民盟,他的态度是合则留,不合则去。在民革内,一遇人事方面的纠葛,柳亚子往往“顿足拍案”,甚至索性撒手不管;他对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始终不服,并一直与其斗法。对于中共,柳亚子极力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在中共尚未取得政权之前,他反对“尾巴主义”:
对于中共呢?做他的朋友,我举双手赞成,但要我做他的尾巴,我是不来的。[24]1542
中共取得政权之后也是如此。抵达北平后,对于中共的“怠慢”之举,柳亚子随即向毛泽东写呈了那首著名的“牢骚诗”,摆出一副“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的姿态。
五、主体选择:柳亚子人格生成的自我角色意识
人格的形成受诸多因素的制约,除了客观的文化情境之外,还有主观的主体选择。弗洛姆指出,由于社会性格的不同以及每个个体体质气质的不同,不仅不同文化模式中的个体人格特征各不相同,即便是同一文化模式中的个体其人格特征也是不同的。[11]这种个体人格的差异性,包含着主体的自由选择,即社会品格通过个人自身的体质、气质、理想、信念,并通过个人的选择而转化为个体的品格和人格,这就使得个体人格呈现纷繁复杂的面貌。柳亚子有明确而自觉的角色意识,以维护名士之性,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排异性。一旦置身于异质的文化情境,他或选择退缩,或同压迫人格的异己力量相抗争。
柳亚子担任过三天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府秘书。关于他辞职的诸多说辞,如对临时政府和议空气失望一类的皮相之见*参见李海珉:《柳亚子》,《江苏文史资料》第122辑,1999年,第36页;《论柳亚子诗歌的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是难得其实的。合理的解释应该是他的名士之性使然:总统府秘书作为公职人员,要循着规制按部就班,从事琐屑的案牍工作,这与名士的风雅之性相左。为此,柳亚子在“过不惯这种紊乱的生活”的情况下,“逃回上海”[12]3,恢复被破坏的文化生态系统。
在革命活动中,柳亚子表现出志行薄弱。*柳亚子多次谈及此点:“余根器浅薄,一摧挫即颓然自废。”(《磨剑室文录》上册第204页)“终以志行薄弱,拂衣归隐。”(《磨剑室文录》下册第1186页)其实,从另一角度而言,他缺乏革命者的勇猛精进,正是由于名士之性过于强烈。长期从事艰苦、琐屑的革命工作,是其名士之性所不堪忍受的。在大革命时期,柳亚子虽然“一身兼领中央暨省部诸要职”,但不过“坐啸画诺”,“拱手受成而已”[24]1068。作为名士型的革命者,柳亚子深感角色的错位:
我是不懂理论的人,叫我做左派理论,真真笑话!
我在省部的好处,不过你和应春、冰鉴可以热闹一点,或是请你们看看影戏而已。至于工作方面,实在是等于零,这也并不是我的不肯做,实在做不来,也是无可如何的。[15]80-81
至于“每天做文章和对外接洽”的琐屑理论或实际工作,令柳亚子“看了就头痛”,且是“绝对不能胜任的”[15]96。为此,他选择回归名士本位。
柳亚子自觉地以“道统”人物自居,并要求“政统”人物以宾师之礼待之。因此,他对于大小“地主”们的礼遇居之不疑。“宾师款我礼无妨”[13]1251,极其鲜明体现了他出于主体选择的角色意识。
旅桂期间,柳亚子结识了一批大小“地主”,为其生活提供了很多的方便,其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是最大的“地主”。尽管李济深给了他很多的帮助,但他还不满意,甚至抱怨,“他(李济深——引者注)半年中只送了我两千元”[15]259。1944年6月底,长沙沦陷,衡阳被围,受震动的桂林下达了强制疏散令。柳亚子拟经平乐到八步,投奔及门弟子廖尚果、王青君夫妇。经李济深同意,柳亚子搭乘其眷属的船到平乐。临行之际,柳亚子未经李的同意,捎带上了老朋友林庚白的眷属。李的部下不同意,要照单清仓。结果,双方起了冲突。为此,柳亚子大光其火:“你们不配对我讲话,叫你们的李主任自己来好了。”为了打破僵局,李济深派人请柳亚子去商谈。柳断然拒绝:“我不去,叫他自己来吧。”不得已,李济深只好亲自“蹬在船头上和我开谈判”。李不迭地陪小心,柳根本不买账,“他先叫了我几声‘亚子先生’,我兀自不睬他”。继而,柳指责李,“你要做西市盟主,能够这样不客气的对天下贤士大夫吗?”并抗言,“你是李主任李院长,我是手无寸铁的书生,得罪了你,你把我枪毙好了”。这场冲突最终以李的卑辞让步得以止息。[12]258-259柳亚子给人的这种“麻烦制造者”的形象,正是出于强烈的主体意识。
面临相同情境的不同反应,柳亚子与其他个体的差异更凸显了人格形成过程中主体选择的重要性。
1949年2月底,柳亚子乘船离港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3月初,抵烟台登岸,途经解放区。与柳亚子一同应邀北上的这群民主人士,大多数是抱着作客的心理,在被解放的欣喜之余,多少有些谨慎与不安:江山是共产党打下来的,他们理所当然地是主人;而在中共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自己要么做了旁观者,要么做了同情者。其中叶圣陶就比较典型。进入解放区之后,一向以艰苦自奉的中共对民主人士招待殷勤。对此,叶圣陶多次表示“不安”*抵烟台时,“菜肴丰盛,佐以烟台美酒,宾主尽欢”(参见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80页)。叶表示,“明日行矣,以此为别,我人身感受之不安”。抵沧州时,天津方面派来专车,叶又表示了不安:“解放军以刻苦为一大特点。而招待我人如此隆重,款以彼所从不享用之物品与设备,有心人反感其不安。”入住六国饭店之后,再次表示不安:“服用至舒服,为夙所未享。虽主人过分厚意,实觉居之不安。”甚至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被褥太暖,进食太饱,未得美睡。”(参见叶圣陶:《旅途日记五种·北行日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59-173页)。而柳亚子则根本不作如是观。在他看来,自己是大名士,共产党理应礼贤下士。所以,每到一地,他都要在欢迎会上发表讲话,俨然以主人自居。*在莱阳城附近,适逢三八妇女节,“柳亚老自请讲话,颇慷慨得体。”(参见宋云彬:《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柳亚子主动请战,同行者也乐得顺水推舟,抵达莱阳后,柳亚子拟参加三月八日的妇女大会,结果因为风大被劝阻,柳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今日为三八节,欲赴妇女大会,因风烈为郭老(子化)所阻,不果去,甚怏怏也。”(参见《自传·年谱·日记》第334页)所以,柳亚子总说“余被推讲话”。(参见《自传·年谱·日记》第334页)抵达华东局及华东军区所在地青州,柳亚子“闻战犯杜聿明解来大礼堂,即赴会鞫之,余与迥老发言最凌厉,该犯唯唯而已”。(参见《自传·年谱·日记》第336页)他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反而觉得中共方面有所怠慢。在沧州,他就因接待不周发脾气。*叶圣陶在日记中云:“昨夕在车站等候较久,亚老向招待人员发脾气。”(参见叶圣陶:《旅途日记五种·北行日记》第100页)柳亚子在《三月十六日夜,沧州火车站中有作呈叶圣翁。圣翁者,余对圣陶先生之尊称也》之一云:“驱车夤夜入沧州,风露中宵动旅愁。蛇影杯弓疑过敏,如虹剑气浩难收。”之二云:“谩骂灌夫原失态,数奇李广不成名。水心两字能箴我,‘克己’终怜负友生。”(参见柳亚子:《磨剑室诗词集》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7-1528页)在北平,柳亚子与来自解放区及国统区的知识分子有明显的差异。1949年7月,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在这里汇合。一次月夜泛舟北海,郑振铎对月感怀:“今夜的月色真美啊!”那位解放区的作家竟然表现木然,毫无反映。郑似乎有些担心:“我是不是谈风花雪月,暴露了着急的小资尾巴?”[27]来自解放区的知识分子由于他律与自律,表现出一种体制人格,诗性基因被人为地删除了;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则犹抱琵琶半遮面,尾巴不自觉翘起来之后又赶紧夹住了。而柳亚子则不然。在颐和园里,他与旧雨新知斗酒斗诗,泛舟赏月,优游竟日。这里虽僻处西郊,但柳亚子所居之益寿堂,完全是大名士孔融所追求的“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的境界。
六、结 语
个体人格的生成,不仅是特定文化对个体塑造的过程,而且是个体主动选择的过程。一方面,社会文化作为一个超强的文化场规定了生活于其中的个体人格的基本方向;另一方面,个体接受社会文化的规范,形成自己价值原则、文化精神,并据此对具体的人格模式、途径进行选择。就柳亚子而言,由于特定的客观环境,加上强烈的主体选择,形成其特有的名士特质。首先,地域文化传统、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社会实践等文化单元的机缘凑泊,赋予他浓郁的名士气质,这是柳亚子人格形成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其次,主体选择是柳亚子人格形成的最重要因素。地域、家庭、学校、社会等环境,不过都是一些外缘性的客观因素,个体人格的形成最终还须从主体选择上得到说明。柳亚子有着强烈的角色意识,名士之性淀入了他的文化心理的深层,思虑营为,接事应物,就会不自觉地表现出来。由于置身于剧烈变迁的近现代社会,柳亚子成了“两截人”:一方面,他追随时代潮流,趋新求变,唯恐被时代所抛弃;另一方面,由于在传统文化情境中濡染既深且久,他对社会的变迁持一种排拒心理*如其在《〈吴根越角〉后序》中云:“尝自憾不早生六十年,欧西文化未大入吾土,天下事犹简单而易治,或足与洪天王辈上下议论功业。”(参见《磨剑室文录》上册第686页)。如果不是剧烈的时代变迁,他与他的前辈毫无二致,做一个有钱的江南文人,美人香草,诗酒流连。因此,他的转化很不彻底,不过是在传统文化的底色上涂了一层现代新质。如其所谓:
小地主出身的我,封建意识当然浓重,还不能脱掉才人名士的习气,事实如此,无可讳言。而思想方面,却又像孙猴子一个斤斗云翻过十万八千里,已到了太平大同的世界了。[24]1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