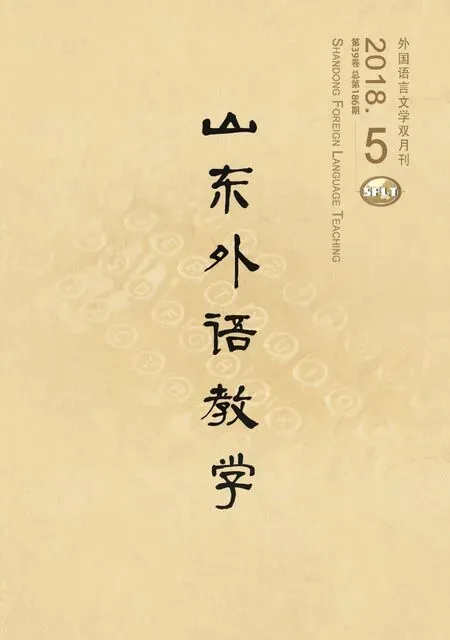中国英语学习者的音段细化
——基于元音/ɑ/和//的特征对比研究
钟彩顺
(江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1.0 引言
音段细化理论是基于特征几何理论和不充分赋值理论提出的一个音系发展假说(Rice & Avery,1995)。该假说认为,语音习得始于元音和辅音的分化;然后通过区分腔部、舌位、口腔张合度、口形、音长等形成元音特征几何。通过区分声带振动、气流阻塞的部位和方式等形成辅音特征几何,在此过程中,充分的语音输入及关键期内语言习得机制的支持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学习者需接触不同音段,内化其区别性特征,促使相关音段特征几何的表征从初始的简单状态,逐步细化、成熟。然而,外语学习普遍缺乏上述条件,且受母语音系干涉。因此,它的音段细化过程和程度有别于母语语音习得。但目前尚不完全清楚母语音系知识、学习者认知等因素如何相互作用于外语音段的特征细化。鉴于此,本研究拟对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元音音段细化进行研究,探讨其特点和规律。
2.0 文献回顾
2.1 母语语音习得研究
母语语音习得研究的焦点是学习者音系发展的有序性和差异性。Jakobson(1941)最早通过跨语言对比和对不同水平学习者的音段区别性特征结构进行比较,提出音段清单发展理论,确立音段发展的一般顺序。Chomsky & Halle(1968)的生成语音学对语音发展的有序性和差异性都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释。他们把语音知识表征分为深层和表层两个层次。其中,深层结构属于人类共同的语言机制,决定语音发展过程的共性。表层结构由深层结构转化而来,该转化过程有普遍性规则可循,但表层参数的具体赋值因语言而异。该理论为现代语音习得研究奠定基本框架,后来的学者主要从认知、学习经验、语音产出或感知等角度对其进行验证或补充。其中,Rice & Avery(1995)的音段细化理论就是一例。他们认为,学习者的语音习得是以非标记性的普遍音段特征结构为基础,以语言体验为条件,通过不断添加和内化符合特定语言的标记性特征结构,丰富音段对立的表征,完善音段特征结构知识。音段细化理论把音系学中的标记理论、传统的特征几何理论及语音习得理论进行了整合,对音段发展的语言认知机制作出了系统的解释。但目前该理论仅限于解释母语音系发展。
2.2 外语语音习得研究
外语语音习得多在母语音系知识成熟后发生。因此,母语的迁移或干涉作用最受关注。早在1950年代,Lado(1957)就提出对比分析假设,认为外语语音习得的困难主要源于母语和外语的音系差异。基于此,有人后来又提出母语迁移假设(Odlin,1989), 这在一些研究中已得到证实(裴光钢,2010)。但基于对比分析和迁移假设的研究存在明显局限性。比如,它们无法解释外语语音习得中存在的跨语言个体间差异。Hancin-Bhatt(1994a)在研究日语和俄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时发现,虽然日语和俄语都没有/θ/这一辅音,但日本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该辅音时,倾向于用/s/来替代,而俄国英语学习者则用/t/。显然,我们无法把这种习得差异性简单归因于学习者的母语与外语在音段类别上的不同。现有研究显示,影响外语音段习得的主要有如下三个因素:
1)特征标记
Eckman(1977)的标记性差异假说认为,当外语音段特征的标记性高于母语对应特征时,学习者会有习得困难;相反,若前者标记性更低,则其习得就容易。据此,我们可以说,外语音系发展的顺序并不取决于音段特征几何的复杂度,而是取决于外语和母语在相关音段区别性特征上的属性差异(Brown,2000)。然而,学界目前并没有就标记性的评估形成系统一致的理论或方法,更没有可行的跨语言标记性比较方法。现行分析维度包括结构复杂度、频率分布、认知突显性等(Givon,1995)。
2)语音感知
Hancin-Bhatt(1994b)的特征竞争模型认为,母语音段特征的突显性是决定外语音段特征习得的关键要素。母语音段特征越突显,越容易被感知和迁移。Best(1994)的感知归化假设认为,外语学习者会基于母语的音系知识来感知外语语音。他们只获取与自己母语音段相似的特征,过滤掉母语中非显性的特征。从而经常会把目标外语音段误归为母语中相似的音段类别。Flege(1995)的言语学习理论认为,学习者会受制于“等同范畴化机制”(mechanism of equivalence classification),当某个目标外语音段与母语中的音段相似时,可能会被归作同一类。
此外,外语学习者的语音感知策略也会影响其语音习得。比如,在对相似音段进行区分时,外语学习者会因对某些区别性特征信息感知不足而转向非区分性信息(Bohn,1995;Bohn & Flege,1990),把注意力聚焦于一些不正确的声学参数上(Iverson,Hazan & Bannister,2005;Mackain,Best & Strange,1981),影响特征几何的正确表征。
3)生理机制
除母语外,外语语音习得也受发展性因素制约。电流生理学的研究表明,幼儿在习得母语时,经过一定的语音对比体验后,其听觉脑皮层的神经表征会产生某些变化,使其能有效自动处理语音(Hisagi et al.,2010),但这一机制在青春期后发生的外语语音习得中已不复存在,因为学习者已过语言学习的关键期(Birdsong,1999),很难获得和处理母语语音一样的自动化能力。
上述研究从多个方面揭示了影响外语语音习得的可能因素,为探讨外语音段特征细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但这些理论仍不能充分解释外语音系发展的规律。
2.3 英汉元音特征差异

图1 汉语单元音分布图(Lee & Zee,2003) 图2 英语单元音分布图(Hillenbrand,2003)
习得研究显示,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困难主要在于区分前半开元音/I, e,ɛ,/(吴诗玉、杨枫,2016),而后元音的区分对他们来说相对容易。这可能是因为英语的后元音除了口腔张合度外,还有口形差别,如//和//。而口形特征在汉语音系中存在,标记性相对一致,容易习得。在前元音当中,可能也受标记性差异的影响,中国英语学习者对/i/-/I/的区分也要好于半开元音//-/ɛ/的区分(Flege, Bohn & Jang 1997)。然而,研究也显示,中国外语学习者,在区分/i/和/I/时,更倾向于依赖音长信号(Bohn,1995;Flege, Bohn & Jang,1997;Liu, Jin & Chen,2014)。这也就是说,即使在习得标记性很低的目标外语元音时,中国外语学者的语音区分策略与母语使用者也会有所不同。
3.0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共邀请56位中国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参加语音实验。所有受试均为女性,年龄在22-26岁之间,平均24.7岁。她们都有15年以上英语学习经验,属于高级英语学习者,但均无海外学习或生活经历。她们的语言态度均偏好美音。另外,本研究还邀请了4位美国语言学专业的研究生,作为参照组。她们年龄均为22岁,女性,以英语为母语,且都来自美国东北部费城。所有参与者言语能力正常,无发音障碍。
3.2 语料收集
本研究语音材料录制在普通语言实验室完成。录制所用设备包括因卓G2000型号耳机、praat软件和PC电脑。录音采样速率为44.1赫兹,分辨率为16位。测试过程如下:受试先填写一份个人英语学习背景的问卷;然后,进行适应性训练,朗诵10个单词;最后朗读正式测试材料。该材料包含buck/bark, bud/bard, but/bart, cup/carp, cud/card, cut/cart六对单词,这些单词随机排列。受试共朗读7遍。
3.3 语料分析
4.0 结果
4.1 /ɑ/和//的特征区分维度
4.1.1 音长
4.1.2 共振峰
4.2 /ɑ/和//特征区分的准确度
4.2.1 音长
4.2.2 共振峰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英汉音系对比研究的结果(Wang,1997),汉语/ɑ/与英语//在元音特征上最相近。然而,本研究数据显示,中国英语学习者产出的英语/ɑ/和英语母语者的//在元音空间上已分开距离。这可能是因为中国高级英语学习者在产出/ɑ/时,已有意识地克服母语的直接迁移,采取了一些音段细化的策略,以区别于//。比如,她们通过舌位后移,形成与英语母语者一致的特征对立。

图3 基于共振峰均值的元音分布图

表1 中国英语学习者和英语母语者共振峰等同性的t检验
然而,从个体元音分布图看(见图 4),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区分口腔张合度和舌位这两个元音特征方面都存在着不稳定性。她们所产出的/ɑ/和//在共振峰上存在过大的个体间差异。比如,中国英语学习者的f分布区间为326-1102,而美国英语母语使用者则是733-796,前者变化范畴是后者的12.3倍。其它几个共振峰情况类似(见表 2)。这种音段特征赋值不稳定现象说明,她们音段特征结构并不成熟,音段细化还不充分。

图4 元音分布图

个案数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标准误差中国英语学习者F1-ʌ563261102810.482122.68942F2-ʌ5690918341345.732133.75680F1-ɑː563141019766.464323.90234F2-ɑː5683618121240.785733.73280美国英语母语使用者F1-ʌ4733796761.000026.57066F2-ʌ4153116621598.250063.56296F1-ɑː4771810789.000017.14643F2-ɑː4125314611353.500087.24105
5.0 讨论
根据Jakobson (1941)的理论,母语音系发展始于音段分化。其中,/ɑ/是多数儿童在母语习得中最早掌握的元音音位。然而,本研究通过对比分析中国英语学习者所产出的/ɑ/和//发现,前者的音段特征准确度并不高于后者。这表明,外语的音段发展顺序与母语并不相同。通过对外语和母语两组受试所产出的元音三个特征赋值进行组间和组内对比分析,本研究在如下两个方面揭示了英语元音音段细化的一些特点:
5.1 元音音段细化的顺序
综上所述,我们可看出,中国高级英语学习者已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母语迁移,不再直接用母语音段替代目标外语音段,并有意识通过对音长、舌位和口腔张合度三个特征进行重新赋值,以区分/ɑ/和//两个音段。但她们在赋值的准确度方面与英语母语者相比仍有一定的距离。三个特征中,音长赋值表现最好,舌位次之,口腔张合度表现最差。
5.2 元音音段细化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虽然未直接针对音段细化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但通过比较元音三个特征在赋值上的差异,我们仍可窥见一斑。首先,音段特征存在标记性或突显性的差异,它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习者的音段细化进度。如果以区分复杂度来界定特征标记性,那么音长应该最简单,因为它只分长短两类。舌位相对来说更复杂,它有前中后之别,但与口腔张合度相比,它又更为简单,因为后者从元音空间图看(见图2),至少有4个以上层级的区分。因此,三者当中,音长标记性最低,舌位的标记性应该中等,口腔张合度最高。从学习者习得的结果看,他们的赋值准确度与标记性刚好呈正相关。这说明,标记性假说也适合外语音系发展(Eckman,1977),特征标记性越高,它的赋值范畴越小,它对学习者的赋值准确度要求就越高,音段细化的难度也就越大。
其次,音段特征区别的意识是外语音段细化的重要方面。外语学习者一般先获得元语音知识,然而才逐渐有真实的语音输入和产出机会。在中国,音标教学在初级阶段就有。对于元音//和/ɑ/,很多老师一开始就会告诉学生它们是英语中的两个音段,并说明它们在音长方面的区别(张明杰,1989)。这种元语音知识使得学生较早形成音段相对区分能力。但它也会使学习者错误地把注意力转向非关键性特征。这也就是为什么学习者在语音习得过程中会作出一些不当的“区分重释”(reinterpretation of distinction)(Weinreich,1953),依赖于一些不合适的“隐性对立”(covert contrast)(Rice & Avery,1995),造成特征赋值失误。
再次,音段细化需要基于充分的语音实践。中国英语学习者虽然较早就有音段区分意识,但她们对特征的绝对区分能力仍不足。这可能是因为特征区分的准确度主要取决于语音产出器官的自动化程度。但由于中国英语学习者语音输入和产出机会少,所以即使他们的语言学习达到高级水平,也难以在特征赋值上达到理想的准确度。
最后,外语学习者会受多种英语语音变体的影响。不同变体的音段特征会有不同的赋值要求。比如,就/ɑ/的舌位而言,在英格兰南部它比较靠后,而在英格兰北部它则靠前。如果外语学习者同时接触这两种变体,那么她们就难以形成稳定的绝对区分能力。中国英语学习者一般都会接触英音、美音等多种变体,这对听力训练有好处,但不利于他们对音段特征的准确赋值。
外语音段细化受特征属性、学习者认知、学习语境、教学策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个体间和特征类别间的细化进度差异明显,这些都在特征赋值的准确度上有所体现。虽然本研究只对两个元音进行分析,没有充分数据来解释不同音段中的相同特征为什么在细化进度上有差异,但我们发现,特征赋值应是探索和建构外语音段细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6.0 结语
当代外语音系发展研究大多以母语干涉假设前提,从音系对比角度,探寻外语语音习得的规律。然而,这些研究只能解释外语初学者存在的语音替代现象,对于外语音系发展中更普遍存在的音段不充分区分、音段过度区分、区分重释(Weinreich,1953)等现象,我们仍缺乏合理充分的理论解释。本研究提出基于特征赋值的音段细化理论,以元音/ɑ/和//为例,通过和英语母语者进行对比,着重分析了中国英语学习者在音长、舌位和口腔张合度三个特征上的赋值特点。结果显示,外语音段细化是一个特征赋值从相对区分转向绝对区分的过程,其进度会受音段特征的标记性、学习者认知、教学策略等因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