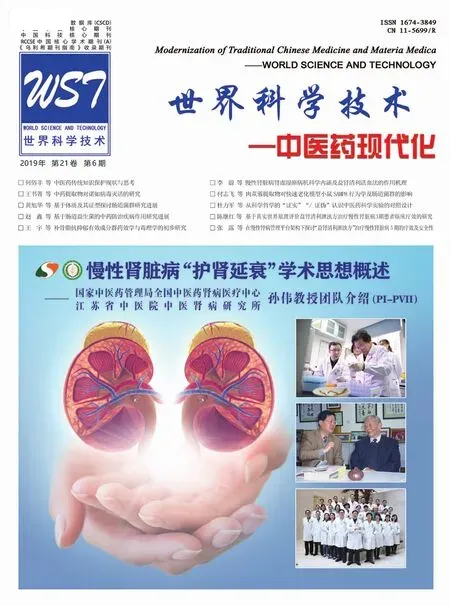基于体质及其证型探讨肠道菌群研究进展*
黄旭华,何 俊,高秀梅**
(1.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医药研究院 天津 301617;2.天津中医药大学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方剂学实验室 天津 301617)
近年来,医学领域已建立人类肠道菌群与胃肠道疾病、免疫性疾病、骨质疏松症、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恶性肿瘤及精神类疾病的相互关系[1-8],而中药对肠道菌群的调节作用及其机制等菌群研究进展,需贯穿现代科学研究与中医传统思维[9],即从辨病、辩证、辨人体质等诊断思维了解肠道菌群相关特征及变化。
肠道菌群在人体形成的微生物生态系统对营养的吸收、有机化合物的合成、获得性免疫系统的形成、及人体对病原体的防护能力发挥高度专属性作用,对宿主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10-13]。中医体质是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所形成的形态结构、机体功能活动个体特征,与心理性格相关,也是证得以产生的背景和重要物质基础;而中医证候是疾病发生和演变过程中某一阶段所具有的病理特点及规律[14,15]。本文通过查阅国内外文献,探讨人类肠道菌群是否与中医体质、证型存在相互关系,以及其相关研究的发展现状。
1 体质与肠道菌群关系
《中医体质分类及判定》[15]将人体质分为9 种,即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瘀血质、气郁质、及特禀质。人的体质随着生命过程、环境因素、禀赋遗传因素、形神构成因素而变化,为体质四个基本原理[16]。人的肠道菌群也随着生命不同阶段、地理环境[17]、基因表达而有所不同。故肠道菌群与体质或许存在一定的共同点。目前与体质相关的肠道菌群研究仅见气虚体质、阳虚体质和阴虚体质三种。
1.1 生命过程论
以生命过程论而言,婴幼儿童具纯阳之体、身体处于稚阴稚阳阶段,故而体质多变而不易掌握[18]。相比之下,婴幼儿肠道菌群亦处于迅速变化状态,研究显示更换乳奶至固体食物可增加肠道菌群多样性,其中以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a和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变为主要优势菌门,而Actinobacteria的主要优势菌种双歧杆菌Bifidobacteria因少了乳奶中丰富的低聚糖而随之减少[19]。故婴幼儿肠道菌群因其饮食结构改变而迅速变化,与其稚阴稚阳、体质多变阶段的直接关系尚未建立。
成人阶段人体气血充沛,脏腑功能强盛,而其肠道菌群也变为更复杂、且更稳定状态[19]。研究显示成人肠道菌群中主要优势菌门变为厚壁菌门Firmicutes及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其丰度值占肠道微生物90%,而Actinobacteria和Proteobacteria丰度值现仅占肠道微生物10%[20]。成人体质偏颇多见气虚质、阳虚质、痰湿质、湿热质;一般认为女性气郁质、血瘀质较多,男性痰湿质、湿热质较多[18]。故而在以上成人肠菌特征的基础上,或许存在与体质相关的特征性菌群。Ma等显示气虚质成人肠道菌群中具水解纤维素功能的丛毛单胞菌属Comamonas和与炎症相关的鞘脂菌属Sphingobium及梭菌属Clostridium较平和体质明显增多,而有助于脂肪、蛋白、多糖代谢及生产的巨球型菌属Megasphaera、韦荣球菌科Veillonellaceae、假单胞菌科Pseudomonadaceae、链球菌科Streptococcaceae、双歧杆菌属Bifidobacterium较平和体质明显下降,可与气虚质疾病易感性及能量代谢下降相关[21]。Arumugam等[22]于2011年首提肠型概念(enterotype),依据来自四个国家的22个新粪便元基因组序列及已发表数据集,发现人体肠道菌群变化为分层性而非连续性(据2 篇样本量大的数据集分析),并将人体肠菌分为3 型,即拟杆菌属Bacteroides(肠型1)、普氏菌属Prevotella(肠型2)及瘤胃球菌属Ruminococcus(肠型3)。目前学者认为肠道菌群分型可能为连续体,且具随着生活、环境、饮食因素等而改变的不稳定性,故认为不能按肠型将人归类[23]。用以上3种肠型无法对应9种中医体质,但研究显示三分之一的成人具有相似的肠道菌群结构[24],与成人中占平和质的比例相符[25],有待日后研究探讨前者肠道菌群结构是否具平和质人群的生理特点。
进入年老阶段,人体逐渐由盛转衰,天癸竭尽,阴阳气血失调,脏腑功能减退,体质偏颇多见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18]。研究显示老年人群的肠道菌群多样性下降、糖降解菌(saccharolytic bacteria)减少、蛋白质分解菌(proteolytic bacteria)增多、核心优势菌种丰度降低、亚优势菌种丰度增多[26],符合年老阶段的生理特点。俞若熙等[27]基于前期研究发现阴虚体质存在肠道菌群的失衡、且与细胞衰老经典NF-κB活化途径相关因子mRNA表达异常,提出“阴虚质女性渐衰期存在与衰老相关特征功能菌群,且与宿主NF-κB通路存在共变化调控特征”的假说。然而,Lu 等认为与年龄相关的肠菌变化未必因衰老引起,而可能源于老年性身体衰弱引起的营养不良及药物摄入有关,如慢性炎症、神经退行性疾病、认知下降、1 型及2 型糖尿病等[28]。可见,生命过程论中的肠道菌群结构变化虽与体质发展变化具有相似之处,但未能建立直接关系,排除其他影响因素。
1.2 环境制约论
环境制约论认为生活条件、饮食结构、地理环境、季节变化、社会因素都可产生体质偏颇的制约性,甚或决定性影响[29,30]。Dong 等以近十年文献论述环境因素对肠道菌群的影响,总结出分娩方式、乳奶、少时逆境、压力、饮食结构、药物摄入均可影响肠道菌群生态改变[31]。
1.2.1 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如气候、地理环境对体质有一定的影响。研究显示东部和北部多见气虚质及阳虚质,西部多见气虚质、阴虚质及痰湿质,南部多见湿热质[32]。广州地区属南部湿气较重之地,故而其湿热质、痰湿质及阳虚质较北京(气候偏干燥)地区多见[33]。Bruno Senghor等对地理区域与肠道菌群规律关系进行综述,总结出非洲地区人体肠道菌群多样性较高,主要优势菌群为Actinobacteria(Bifidobacterium)、Bacteroidetes(Bacteroides-Prevotella)、Firmicutes(溶组织梭菌C.histolyticum、真细菌Eubacterium、颤杆菌克属Oscillibacter、丁酸梭菌屬Butyricicoccus、Sporobacter)、Proteobacteria(琥珀酸弧菌属Succinivibrio、志贺氏菌属Shigella、埃希氏菌属Escherichia)及螺旋体门Spirochaetes(密螺旋体属Treponema);欧美等西方国家人体肠道菌群主要优势菌群为Firmicutes(布劳特氏菌属Blautia、杜尔氏菌属Dorea、罗斯氏菌属Roseburia、普拉梭菌属Faecalibacterium、Ruminococcus、颤螺旋菌属Oscillospira、产气荚膜杆菌C.perfringens、艰难梭菌C.difficile、金黄色葡萄球菌S.aureus)、Actinobacteria(青春双歧杆菌B.adolescentis、链状双歧杆菌B.catenulatum)、疣微菌门Verrucomicrobia(嗜粘蛋白-艾克曼菌A.muciniphila)及Bacteroidetes(Bacteroides);而亚洲人群趋于两者之间,一部分似非洲人群,主要优势菌群为Bacteroidetes(Bacteroides)和Firmicutes(Prevotella),另一部分似西方人群,主要优势菌群为Actinobacteria(B.adolescentis)和Firmicutes(丁酸弧菌属Butyrivibrio,C.perfringens,S.aureus)。该作者认为地理环境对肠道菌群的影响主要来源于饮食习惯,未提自然界地理环境影响因素[34]。E.Angelakis等对不同地理来源的肥胖人群进行肠道菌群分析,发现不同地理来源的肥胖人群各有其不同的肠道菌群结构,但以西方饮食为主的肥胖型人,无论来自何方,皆具相似肠道菌群结构,并认为其肠道菌群结构差异源于不同区域的饮食习惯及生活条件[35]。可见,自然环境与肠道菌群的关系尚未被确立。
1.2.2 社会环境
社会因素如饮食起居及生活习惯皆对体质产生一定影响。各种饮食有其四气五味属性,四气为寒、热、温、凉,五味为酸收、苦降、甘补、辛散、咸软,偏嗜一方则可引起人体脏气偏盛偏衰,出现偏颇体质[36]。犹如,《素问∙奇病论》曰“膏粱厚味,油腻腥膻,易积湿生痰,而成痰湿”,研究也显示喜食油腻及平素运动水平低是导致痰湿体质的重要因素[29]。高糖脂-低纤维(西式)饮食人群中肠道菌群丰富值低于低糖脂-高纤维(非西式)饮食者[35,37]。高脂肪摄入引起的肠道菌群变化主要为肠道菌群丰富值下降及F/B 比例增大[38,39]。故而肠道菌群丰富值下降、F/B 比例增大可能与痰湿体质有关,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除了依照四气五味推测饮食对体质、肠群的影响外,摄入含微生物发酵类食品(酸奶、泡菜、奶酪、啤酒等)也可直接作用于人类肠道菌群[40]。进食发酵类食品后会有一部分摄入的微生物存活于人体消化道[41,42],构成人体肠道菌群新且短暂性的菌类[43],故未能说明发酵类饮食及体质肠菌的关联。
中医认为动则生阳,静则生阴;阳虚体质[15]为机体阳气不足,其形体特征为肌肉松软不实,性格多见沉静、内向。研究显示,运动量适多可改善人的体质偏颇[44],促进肠道菌群多样化增多,提高有益微生物群落,增加肠道菌群代谢能力及降低F/B比例;其对肠菌作用机制可能源于胆汁酸机制、代谢免疫机制,体重下降及肠道转运时间等[45]。李英帅等[46]于2015 年提出“阳虚质肠道菌群结构的变化会影响主宿代谢功能,并存在与代谢相关的特征功能菌群”假说。王均衡[47]为验证前者假说,对比分析阳虚质与平和质者粪便典型代谢产物谱特征,发现阳虚质者的代谢通路切实存在与平和质不同的代谢通路改变,并在找出阳虚质特异标志性代谢产物的基础上,寻找到与阳虚质典型代谢标志物相关且影响宿主共代谢的特征功能菌群,即明串珠菌属Leuconostoc、罗氏菌属Rothia、Defluviitaleaceae_incertae_sedis和丁酸弧菌属Butyricimonas。
1.3 禀赋遗传论
禀赋遗传论指人始生的体质状况受父母生殖之精的质量、母亲孕育情况、及婴儿营养状况直接影响[30]。J K.Goodrich 等从英国双胞胎人口(TwinsUK)分析对比1000 多个粪便样品(包括416 对双胞胎),发现单卵双胞胎之间的肠道菌群相似度高于双卵双胞胎,并鉴定许多微生物类群丰度值是受宿主基因学影响,其中以最具遗传性的分类群(taxon)为关克里斯滕森菌科Christensenellaceae[48]。J.Walter以综述表示基因组学对肠道菌群的影响仅次于饮食影响[49],而D Rothschild[50]却提出肠道菌群结构与遗传基因组学并无显著性关系,主要以饮食摄入、服用药物等环境因素相关。可见,禀赋遗传(遗传基因组学)对肠道菌群结构的影响仍存在争议。
丁维俊等[51]纳入家族性肾阳虚患者(n=16)和正常人(n=10)的粪便标本进行对比研究,发现肾阳虚患者的葡萄球菌属Staphylococcus、肠球菌属Enterococcus、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等肠道需氧菌异常增加,Bifidobacterium、乳杆菌属Lactobacillus等益生菌显著性下降。然而,该研究因未能排出后天环境因素影响而无法准确体现出遗传因素对肠道菌群的影响。黄腾杰[52]研究阳虚质肠道菌群结构特征,发现阳虚质与平和质肠道菌群总体上没有太大差异,但有部分肠道菌群结构上出现改变,即阳虚质短波单胞菌属Brevundimonas、Leuconostoc、Rothia较平和质含量显著性偏高,而平和质中Megasphaera、Ruminococcus、毛螺旋菌Lachnospira较阳虚质含量显著性偏高。相比之下,无论因先天或后天形成的阳虚质,都存在着一定肠道菌群结构性差异,而此差异理应与阳虚机体功能活动(代谢)相关。例如:家族性阳虚质Staphylococcus、Enterococcus、Escherichia coli等肠道需氧菌的增加,通常是机体对食物腐熟运化功能低下所见,而益生菌下降为机体正气虚弱,拮抗外邪能力下降[51]。
1.4 形神构成论
中医认为人体由形和神构成。形为神之宅,即在一定(躯体)形态结构和生理机能的基础上,才可产生心理特征;而神乃行之用,即心理特征也会影响形态结构和生理机能[30]。现代医学认为心理压力及抑郁因素可引起饮食偏好、调变应激激素、炎症反应及自主神经反应,从而重塑人体肠道菌群结构;而肠菌通过其代谢产物、毒素、及神经激素,反过来调节宿主的饮食偏好及心情[53]。可见,心理因素与体质及肠道菌群具有相互影响作用。气郁质及血瘀质者易患抑郁症[54,55]。研究显示,抑郁症肠道菌群中Actinobacteria和Firmicutes菌门表达过多,菌属Bifidobacterium(7%)及Blautia(8%)丰度较高于正常人,而正常人以Prevotella(16%)丰度较高[56]。J R.Kelly等显示抑郁症与肠道菌群丰富性及多样性下降有关,并将抑郁患者肠道菌群移植到缺乏肠道菌群的大鼠,发现大鼠接受移植后出现焦虑、快感缺乏等抑郁特征及色氨酸代谢变化[57],提示肠道菌群可作用于大鼠机能,诱发抑郁症。Chung等[56]认为肠道菌群通过戊糖磷酸酯和淀粉及蔗糖代谢过程,影响宿主抑郁情况。虽然目前尚未见有气郁质及血瘀质相关的肠道菌群特征性报道,但可参考抑郁症肠道菌群特征,结合气郁质及血瘀质向抑郁症发展趋向,对其肠菌特征进行探讨。
2 证型与肠道菌群关系
肠道菌群失衡与胃肠道疾病、代谢疾病、免疫类疾病、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精神类疾病等密切相关[1],而中医学对许多疾病的诊断均以证为名[58],即在辨病基础上以不同证型特有的病理表现为辨证依据进行诊治,故而不少学者探讨不同中医病证是否具有其独特的肠道菌群特征及中药辨证治疗是否影响其肠道菌群结构。
2.1 气虚证
气虚证指元气不足,气的推动、固摄、防御及气化功能减退,或脏器组织机能减退,出现气短、乏力、神疲等临床表现。梅一岚[59]发现脾胃气虚型消化性溃疡患者的Actinobacteria较少于健康人、脾胃虚寒兼胃络瘀阻证型患者,并提出门水平上的中医分型或可从Actinobacteria区分脾气虚弱证。Actinobacteria为厌氧细菌,主要包含3个厌氧菌科(Bifidobacteria,丙酸杆菌属Propionibacteria及棒杆菌属Corynebacteria)和1个需氧菌科(链霉菌属Streptomyces)。Actinobacteria参与抗性淀粉的生物降解,Bifidobacteria参与亚油酸对共轭亚油酸的转换,而共轭亚油酸具有增强免疫功能、抗糖尿病、抗肥胖症的作用[60],故Actinobacteria下降可见脾气虚弱,脾失健运、正气不固的表现。
2.2 阳虚证
阳虚证指机体阳气亏损,温养、推动等作用减退,具畏寒肢冷为主要表现的虚寒症候。雷春红等[61]研究显示,脾肾阳虚型结肠腺瘤性息肉患者肠道菌群中种群多样性显著低于健康人群,其Firmicutes与Bacteroides(F/B)比值低于健康人群、γ-Proteobacteria丰度值高于健康人群,梭菌纲Clostridia、Blautia、及Ruminococcus丰度值低于健康人群;经温肾健脾方治疗后,脾肾阳虚型结肠息肉患者粪便标本中Firmicutes相对丰度明显上升,Bacteroides及其纲、目、科、属相对丰度明显下降,Clostridia及其目、Blautia及瘤胃球菌科Ruminococcaceae的相对丰度明显升高,其肠菌结构更接近健康人群[62]。
然而,Zhang 等综合研究脾阳虚患者代谢性特征及其肠道菌群特征分析,发现脾阳虚患者Firmicutes丰度高于健康人群、Bacteroides丰度低于健康人群、F/B比值高于健康人群,并提出Firmicutes增高主要影响脾阳虚患者能量代谢障碍[63]。F/B 比值现被考虑为代谢综合征及肥胖症的相关指标;J.A.Santos-Marcos 等提出代谢综合征患者的肠道菌群结构变化以F/B比值增高,伴见肠菌降解碳水化合物为短链脂肪酸(SCFAs)能力下降[64]。研究显示Firmicutes具348 种代谢途径,相对Bacteroides的76种代谢途径较多,故Firmicutes增多意味着宿主具备更多可利用能量(从饮食提取),符合与肥胖症相关的F/B 比值增大[65]。综上,F/B 比值增大尚未能作为阳虚证的肠菌特征,但Zhang 等提出的“Firmicutes增高主要影响脾阳虚患者能量代谢障碍”,可能与“湿邪损伤阳气”的致病特征相关。
2.3 阴虚证
阴虚证指体内阴液亏少,无以制阳,机体失于滋润、濡养,出现咽干、五心烦热、盗汗等虚热症候。韩苗苗[66]以ERIC-PCR及16S rDNA-RFLP分析番泻叶加甲状腺素脾阴虚模型大鼠肠道菌群,结果显示ERICPCR 特征条带340 bp 及16S rDNA-RFLP HaeIII 酶切特征条带470 bp见于正常大鼠,经脾阴虚造模后消失,但经中药治疗后又出现,克隆结果为Lactobacillus等有益菌;16S rDNA-RFLP Hinf I 酶切特征条带360 bp 未见于正常大鼠,经造模后出现,且治疗后又消失,克隆结果为铁氧化细菌等有害菌,反应了阴虚证模型大鼠肠道菌群变化。
2.4 痰湿证
痰湿证多因脾气不运,湿浊内停,聚而生痰,为中医证候的一种,临床多见咳嗽痰多,色白质稀,或吐涎沫,或痰鸣喘促,或呕恶纳呆等症状表现[67]。痰湿证型中重度痤疮患者肠杆菌科Enterobacteriaceae低于健康人群,产碱菌科Alcaligenaceae和萨特氏菌属Sutterella丰度高于健康人群,且未检测出Prevotella[68]。脾虚痰湿型代谢综合征患者的肠道总菌群、Bifidobacterium、Lactobacillus数量显著低于健康人群,Enterococcus,Escherichia coli,球形梭菌Clostridium coccoides、柔嫩梭菌Clostridium leptum、数量显著高于健康人群[69]。目前痰湿证型的相关肠道菌群研究不多,尚未能概括痰湿证型特属的肠道菌群。
2.5 湿热证
湿邪和热邪相合致病为湿热证,具有身热不扬、口渴不欲多饮、泄泻、尿黄等临床表现。溃疡性结肠炎湿热证候人群肠道菌群多样性高于健康人群,其肠菌以乳杆菌属Lactobacilli、乳杆菌科Lactobacillaceae、Erysipelotrichaceae、Erysipelotrichales等为主,而健康人群以拟杆菌科Bacteroidaceae、Bacteroides、Firmicutes、Clostridium等为主[70]。
人体肠道内环境几乎为完全无氧状态,仅有微量氧气从肠道上皮细胞渗入肠腔内,故人体肠道菌群中主要有厌氧细菌,其次为兼性菌群[71]。付肖岩[72]提出湿热证与脾虚证肠道菌群的区别为脾胃湿热证以需氧菌、Enterococcus增加为主,而脾虚证以Bifidobacterium、Lactobacillus等厌氧菌减少为主。研究显示,脾胃湿热证的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肠菌中Enterobacteriaceae、Enterococcus等条件致病菌明显多于健康人,Bifidobacterium、Lactobacillus等益生菌明显少于健康人;与脾虚证相比,脾胃湿热证患者Enterobacteriaceae、Enterococcus、Bifidobacterium、Lactobacillus均明显增多[73],提示两者皆有Bifidobacterium、Lactobacillus等益生菌减少,但脾虚证者尤甚。动物实验显示,湿热证模型肠道菌群中Escherichia coli、Enterococcus、Clostridium等条件致病菌过度增长,而不同病机引起的两种湿热证模型出现Bifidobacterium、Lactobacillus等益生菌含量表达差异;因脾阳虚而生内湿的湿热证见有Bifidobacterium、Lactobacillus含量减少,而因湿邪困扰的湿热证见有Bifidobacterium、Lactobacillus含量增多[74]。故或许益生菌代表人的正气,正气虚则益生菌减少,邪实而正不虚则益生菌增多以对抗外邪,其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湿热蕴结型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患者中条件致病菌,即Enterobacteriaceae及Staphylococcus含量均明显多于健康人群,而其Bacteroides、Bifidobacterium、Lactobacillus等益生菌含量均明显少于健康人群(P<0.01);经“多烯磷脂酰胆碱胶囊、枯草杆菌二联活菌肠溶胶囊、及加味茵陈五苓散”连续治疗12周后,患者Enterobacteriaceae及Staphylococcus数量明显降低,Bacteroides、Bifidobacterium及Lactobacillus数量明显提高,其疗效优于单纯西医“多烯磷脂酰胆碱胶囊、枯草杆菌二联活菌肠溶胶囊”治疗(P<0.01)[75]。口服中药联合青赤散灌肠治疗能改变大肠湿热型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肠道菌群丰度值;经治疗后,Firmicutes、Actinobacteria及Bifidobacterium丰度较治前增多,而Proteobacteria、Escherichia coli、Enterococcus等条件致病菌丰度较治前下降,差异均具统计学意义[76]。葛根芩连汤联合二甲双胍治疗II型糖尿病湿热证患者除改善临床症状和血糖水平外,还可降低Enterobacteriaceae数量、升高Clostridium及Bifidobacterium数量,其临床疗效及对肠道菌群的影响显著性高于单纯二甲双胍治疗[77]。综上所述,湿热证型的肠道菌群结构以条件致病菌明显增多,而其正气虚实或可反应于益生菌的多少。
2.6 血瘀证
血瘀证指瘀血内阻,血行不畅,出现固定刺痛、肿块、出血、肌肤甲错等临床表现。基于中医理论“心与小肠相表里”,郭宗耀[78]探讨冠心病血瘀证与肠道菌群的关系,发现冠心病血瘀证大鼠的Lactobacillus及Bifidobacterium数量明显减少,Escherichia coli及真菌数量明显增多;经养心通脉方治疗,不仅见其血脂及血液流变指数改善,还有其肠道菌群失衡的改善,如Lactobacillus及Bifidobacterium数量的恢复,提出冠心病血瘀证型可能与肠道菌群失衡存在相互关系。Lactobacillus及Bifidobacterium均具有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两者通过调节免疫细胞、降低促炎性细胞因子而缓解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后者还参与共轭亚油酸的形成,而促进抗动脉粥样硬化、抗糖尿病、抗肥胖等作用[60,79]。然而,Lactobacillus及Bifidobacterium与血瘀证的关系尚未建立,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3 展望
该综述旨为探讨体质、证型与肠道菌群结构的规律,以指导中药针对体质及证型来影响肠道菌群结构,进而调节其相关免疫、代谢、消化吸收等作用。已有研究显示中药可以通过其益生元特性、细菌抑制性、细菌消除性、胃肠道pH 值调节作用、胃肠道转运时间调节作用、免疫调节作用等,影响肠道菌群结构;并通过中药引起的肠道菌群结构变化及机体酶活性变化,影响肠道菌群代谢作用[80]。然而,除上述已知生物医学途径外,中医临床诊治处方仍需结合中医传统思维以指导用药。
中医证候与肠道菌群关系的临床和实验研究方面,于2003年前主要涉及脾虚证腹泻的微生态研究[72]。近年来,随着人们重视肠道菌群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有学者开始关注肠道菌群与中医体质及证候的关系。这方面研究进展之益有三:①建立肠道菌群与体质偏颇的生理病理关系有助于体质调节对肠道菌群结构改善的认知;②鉴定病证相关的肠道菌群结构变化,可为中医诊治提供新靶点;③观察方证对应在疾病诊治中的肠道菌群变化可揭示其疗效机制,为临床诊治添加依据。
综上所述,体质及证型的相关肠道菌群研究处于发芽阶段,虽有已知体质、证型相关的肠道菌群差异及优势菌群,但其涉及影响因素较多,如病种、病机、病位等差异,故有待结合肠道菌群微生物代谢性特征与中医理论进一步探讨,并确立其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