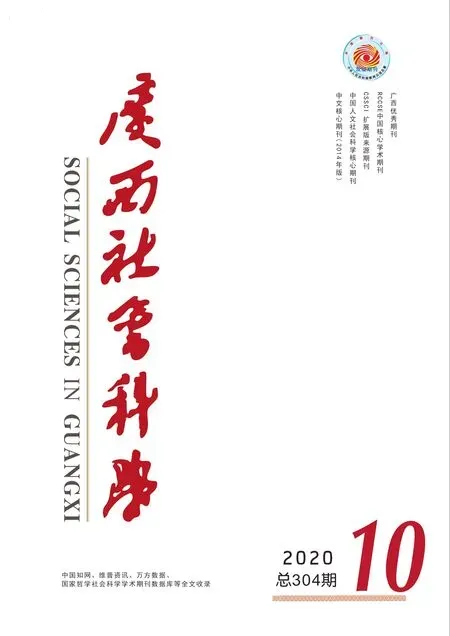作为民族的经典与传统
——重读韦其麟的《百鸟衣》
(宿迁学院 中文系,江苏 宿迁 223800)
民族叙事长诗《百鸟衣》是韦其麟的代表作和成名作,其所形成的民族叙事诗模式在文坛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与地位。作为展示少数民族诗歌和现代诗歌写作经验与审美意识的经典作品,《百鸟衣》深刻地影响广西现代诗歌的审美思考与时代探索。因而,回溯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百鸟衣》的本体定位与时代观照,总结《百鸟衣》在民族书写和文化叙事方面的经验,呈现《百鸟衣》作为壮族诗歌、广西现代诗歌及中国少数民族诗歌的经典与传统的地位,对启示当下的诗歌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百鸟衣》的创作定位与时代背景
首先,《百鸟衣》是现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它是以壮族民间传说故事《百鸟衣》为原型加工、创作而来的作品,对这一民间传说基础及其创作的本体定位,虽然有论者认为它是一种整理而不是创作[1],但学术界不少人认为它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诗歌创作。比如,20世纪50年代,陶阳认为《百鸟衣》“是根据民间传说所创作的一部成功优美的诗篇”[2];李冰认为《百鸟衣》是“在壮族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而加工创作的一首长诗”[3];贾芝亦是肯定《百鸟衣》“在原故事的基础上进行了创作加工”[4]。20世纪70年代以后,学术界以越来越清晰明确的“叙事诗”定位肯定《百鸟衣》是创作而不是整理。如莫奇指出《百鸟衣》是“根据壮族民间传说创作的长篇叙事诗”[5];郭辉认为《百鸟衣》是韦其麟“按照自己的理解,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对题材进行了较大的加工”[6];马维廷指出《百鸟衣》“是一种融汇了自我情愫的再创作”[7];杨长勋认为《百鸟衣》是“在超越原始传说的同时却真实的逼近社会生活的原型和历史生活的原型”[8];宋尤兴则指出“《百鸟衣》完完全全不是根据民间原有的长诗整理出来的产物,而是韦其麟以民间故事为题材所创作的一部长诗”[9]。显然,20世纪70年代以后,学术界普遍认为韦其麟的《百鸟衣》不是整理民间传说故事的产物,而是在原故事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现代民族叙事诗。
其次,《百鸟衣》运用民族性的修辞与审美特征。《百鸟衣》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类型,它在现代汉语诗歌中一直以鲜明的民族性修辞与审美特征彰显其独有的语言与文化魅力。对于《百鸟衣》文本中运用的修辞与审美特征,黄懿陆认为其“很好地吸收了民间山歌的传统特点,用形象化的语言,浓郁的抒情色彩,突出的民族风格,表现了一幅幅动人心弦的图画”[10]。梁庭望也认为韦其麟“善于吸收壮族民歌的营养,大量采用民族的比兴、夸张、重叠等表现手法,通过朴素而生动、简洁而活泼的语言,形成明丽的诗的意境和浓郁的抒情气氛,有着较高的艺术价值”[11]。就修辞方面而言,除赋、比、兴外,《百鸟衣》还运用较物、摹状、反复、反语、设问等[12]。对学术界论及《百鸟衣》中运用的民族性修辞与审美特征,韦其麟也予以正面回应,他指出:“在民歌里,那大胆的带有浪漫色彩的夸张,和那丰富的比喻、起兴、重复,是那样形象、精确、具体、生动和恰到好处,给人的印象是那样强烈、新鲜、明朗。”[13]因而,他个人在写作《百鸟衣》时十分注重选用具有壮族特征的修辞手法与审美技巧,以创造出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的文化书写与艺术审美。由此可见,正是凭借壮族山歌赋、比、兴传统修辞与民族性、地域性审美的综合运用,《百鸟衣》得以在汉语诗歌中表现出独特的文化书写与语言魅力。
最后,《百鸟衣》建构广西现代诗歌的抒情传统。作为现代诗歌中的叙事诗类型,《百鸟衣》虽是根据壮族民间传说故事的原型和融合壮族山歌赋、比、兴抒情传统修辞及现代诗的种种修辞手法创作而成,但其所要表现的审美本质依然是叙事诗具有的情感、心灵世界。M.H.艾布拉姆斯指出:“在一首诗的各种要素中,措辞要素,特别是修辞手法,成了基本要素;因此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判断这些东西到底是情感和想象的自然表露,还是对诗歌惯例的刻意仿效。”[14]显然,由上文学术界肯定《百鸟衣》是创作而不是整理的可知,《百鸟衣》作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诗歌创作,表现的是韦其麟个人对壮族文化的情感认知,而不是单纯地将壮族传说故事还原或仿效,是壮族文化的心灵表现而不是再现,是一种民族形式的抒情。韦其麟也认为:“我想,人们根据民间故事传统而写作叙事诗,并不是在民间故事传说中发现诗,仍然是在生活中发现诗,通过叙事而抒情明志。”[15]可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也即广西现代诗歌的转型期之初,《百鸟衣》及韦其麟的叙事诗创作为广西诗人如何进行有关自身民族、自身地域的民族书写、文化书写以及其情感性、表现性叙事和抒情提供诗歌路径与借鉴经验,这在很大程度上建构了广西现代诗歌的抒情传统。
综上而述,无论是从韦其麟个人的诗歌创作经历,还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西现代诗歌发展的整体历程来看,“韦其麟《百鸟衣》模式的民族叙事诗创作,不仅证明了其本人诗歌写作的价值与意义,更作为一种主流的创作模式引领广西诗人群体的创作”[16]。
二、《百鸟衣》的民族书写与文化叙事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1961年学术界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举办的“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讨论会”上(195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也有涉及),基本规定了“民族成分”“语言”“题材”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和少数民族创作属性的三项基本要素[17]。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和少数民族作家、诗人的创作,最能反映他们创作和作品的民族特征和文学影响的是“语言”和“题材”。我们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以张承志(回族)、阿来(藏族)、晓雪(白族)、吉狄马加(彝族)等为代表的一批对当代中国文坛产生重要影响的少数民族作家、诗人,他们立足文坛的具有民族特征的创作和作品亦是由“语言”和“题材”所建构,而不是“民族成分”这个宽泛的规定。《百鸟衣》作为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具有建构性意义的作品,它能够在当代文坛中产生影响与得到认可,亦是因为在语言修辞、题材选择及文化叙事层面上表现出了独特性。
在语言修辞层面,《百鸟衣》以广西传统的“排歌体”山歌与现代诗歌语言相结合的民族书写,呈现个人诗歌创作的现代性。一般而言,广西的“排歌体”山歌是:“每首的句数不定,但一般是双数;每句字数也不定,但大多数是单数。除每两句须押腰韵外,比较自由,句子往往采用辅排的方式。”[18]“排歌体”山歌这种句数、字数、韵律及叙事都相对自由的形式,决定了其很容易与现代诗语言相结合,而且,其辅排的叙事特征也利于诗人表达情感与诗意创造。韦其麟由于从小“浸泡”在广西山歌的海洋之中耳濡目染及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韦其麟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在民族记忆、山歌传统与现代诗歌熏陶的综合影响下,促使他的诗歌创作表现出“在向壮族民歌学习的过程中,既注意继承和发扬壮族民歌的优良传统,又立足于改革与创新”[19]的时代特征。韦其麟在《百鸟衣》中写道:“山坡好地方,/树木密麻麻,/鹧鸪在这儿住下,/斑鸠在这儿安家。”[20]“水向低处流,/物归原主有,/娘对着公鸡问:/‘红冠的公鸡呀,/你的主人是那一家?’”[21]纵观《百鸟衣》全篇,虽然在部分诗节中,韦其麟运用了两句、五句、六句及八句的句数,但主体是四句数式的行文。这种主体为双句数、部分章节为了叙事需要又打破双句数限制的现代诗语言运用,既表现了他在诗歌创作中遗留的“排歌体”山歌传统影响,又表现了他作为少数民族诗人却能熟练运用汉语进行现代诗写作。在这两节诗歌当中,我们也发现,在诗句的字数方面,韦其麟以“5/5/7/7”和“5/5/6/6/8”的字数运用打破了广西山歌或是民间诗歌中字数通篇整齐划一的特征,呈现出区别广西传统山歌和民间诗歌的现代诗歌创作形式。此外,这两节诗表现出的辅排叙事特征,也表明《百鸟衣》和韦其麟的诗歌创作具有由彼物至此物、由自然及人的理性与诗性特征。
在题材选择方面,《百鸟衣》的题材选择既“具有深厚的神话色彩”[22],同时又在超越传统壮族神话传说的基础上,“给远古的神话染上了既有真实感又充满了神幻的迷人色彩”[23]。作为一个出生和成长于广西南宁横县文村的壮族人,韦其麟深受文村中“讲古”(也叫摆古)传统的影响,可以说他的成长过程中几乎每天都在“听着老人伴讲着那古远的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24]。因而,壮族的各种神话、传说故事也潜移默化地成为韦其麟个人记忆、情感及认知方面的组成部分,并影响着他的诗歌创作。对韦其麟而言,《百鸟衣》即是受神话、传说的影响与现代诗创作愿望相结合的产物,这种具有壮族传统特征与时代特征的诗歌创作形式,也表现了壮族诗歌和广西现代诗歌的奇幻、迷人及异质性的特征。如韦其麟在《百鸟衣》中写道:“第三个月第三朝呀,/不听见公鸡啼了,/笼子里没有了公鸡,/院子里站着个姑娘。”[25]“娘气死了,/依娌被抢走了,/树林里的小鸟吓跑了……清清的小溪旁,/没有依娌淘米了,/淙淙的流水呀,/也流得不响了。”[26]从中看到,作为在壮族民间神话传说基础上创作而来的诗歌作品,其全篇表现的原型主题即是民间神话《百鸟衣》中古卡和依娌的爱情故事,这是韦其麟民族叙事长诗《百鸟衣》中神话特征的最大反映。同时在内文诗节的写作过程中,公鸡变依娌、树林里的小鸟(吓跑)和流水(不响)通人性的神性特征也强化了《百鸟衣》的神话和奇幻色彩。
在文化叙事方面,《百鸟衣》展现出熔铸壮族文化的诗性特征。肖远新和李玩彬指出:“把壮族民间传说诗化,这是韦其麟诗歌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27]显然,作为一部民族叙事长诗,《百鸟衣》全篇无论是主题、体例还是情感表达都表现出韦其麟十分注重对壮族文化的运用,以创造其中民族书写的诗性特征。在《百鸟衣》中,他写道:“那么佬来了,/烧香又点烛,/喃喃又跳跳,/依娌没有笑……卖膏药的来人,/好笑的故事,/讲了一百个,/依娌仍不笑。”[28]诗中的“那么佬”即壮族民间的道士、师公,“卖膏药的来人”即壮族民间以走江湖为生的人,他们一般既能驱邪看病又能说会道,从当下非遗保护的视角看,他们是壮族民间文化的传承者。作为深受壮族民间文化影响的诗人,韦其麟在创作《百鸟衣》的过程中,亦是在诗歌的叙事与审美之间熔铸壮族民间文化,以增加其文化趣味与诗性。此外,《百鸟衣》本身的文本、修辞及审美特征都吻合主流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少数民族作品的特征。郭辉指出:“正是有了对本民族文化生活的熟悉和理解,有了对这些文化深深的热爱和敬重之情,使得韦其麟的作品总蕴藏着一股浓郁的民族本色。”[29]我们也可以说,正是在壮族文化传统的熏陶之下,《百鸟衣》的民族书写和文化叙事才具有如此鲜明的民族特征、地域特征及时代特征,在广西现代诗歌和中国少数民族诗歌(文学)中具有持续性的影响力和价值,被不同时代的写作者和批评家所认同与肯定。
三、《百鸟衣》的当代价值与“重读”意义
综合而论,60余年来《百鸟衣》正是凭借自身开启的民族叙事诗创作模式、引领广西现代诗歌创作与探索的潮流,以及其所积淀起来的民族和文化意义,使得其既以起始性的民族书写模式建构和影响着广西现代诗歌整体的创作与审美,又以显著的诗歌价值、民族价值表现着广西现代诗歌和少数民族诗歌在当代文坛中的影响与书写贡献。
第一,建构广西诗歌的现代转型。作为一种新文学类型,少数民族诗歌虽然与现代汉族诗歌(即新诗)一样萌生于晚清,成型于“五四”时期,但其发展的速度与产生的影响明显滞后于汉语诗歌。梁庭望在《中国诗歌通史:少数民族卷》考察了晚清到“五四”期间中国诗坛中纳兰性德(满族)、蒲松龄(蒙古族)、仓央嘉措(藏族)、郑献甫(壮族)等具有少数民族身份诗人的“作家诗”创作;但就少数民族地域内部而言,不管是主流的诗歌形式还是创作者身份而言,与汉族诗人创作的现代诗歌相比,少数民族地域的诗歌创作实则还是以民间艺人、歌师、毕摩等人的口头创作或演唱的民间诗歌为主,真正意义上的“作家诗”(现代诗)相对较少。就此,梁庭望指出:“少数民族诗坛在很长的时间里,是由民间诗歌(包括民歌、民间长诗、民间说唱)领衔的,作家诗产生比较晚。”[30]就广西地域而言,由于“勒脚歌”与“排歌体”形式的山歌、歌谣、民间长诗及说唱等是广西民间诗歌创作与演唱的传统与主要形式,因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西地域内“以全新的现代新诗的艺术形式与壮族最古老的民间文化相应地有机地结合,并在中国现当代新诗的格局中取得应有的艺术地位的,则是韦其麟”[31]。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少数民族诗人,韦其麟于20世纪50年代创作完成的民族叙事诗《百鸟衣》及所形成的广西现代诗歌创作经验与模式,经由与韦其麟同代的广西诗人侬易天(壮族)、苗延秀(侗族)、萧甘牛(壮族)、包玉堂(仫佬族)等共同强化与后续的系列创作,最终促进广西诗歌由民间诗歌向现代诗转型。
第二,影响广西现代诗歌的创作进程与审美维度。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由于韦其麟与其同代的诗人(包括生活于广西地域内的汉族诗人)大都致力于广西地域内的民族叙事诗创作,他们这种创作“合力”,一方面促进广西诗歌由民间诗歌向现代诗歌的时代转型;另一方面不断扩大与加强韦其麟《百鸟衣》模式的民族叙事诗的影响与意义并使其经典化。因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受到当代文坛的民族“寻根思潮”及广西地域内“百越境界”理念的影响,冯艺、黄神彪、黄堃、杨克等新一代广西诗人也是紧跟韦其麟《百鸟衣》模式的民族书写传统,开展围绕少数民族神话传说、传统及“花山壁画”等形式的多维度的民族书写探索。壮族诗人冯艺的散文诗集《朱红色的沉思》、壮族诗人黄神彪的长诗集《花山壁画》及汉族诗人杨克的经典组诗《走向花山》都显示新一代广西诗人具有的民族书写特征。广西文艺界在20世纪末开展的“广西青年文艺家花山文艺座谈会”(1996年)“广西百名青年作者创作会”(1997年)及新世纪的全区范围内的广西“花山诗会”(2017-2018年),也在很大程度上昭示着韦其麟《百鸟衣》模式的民族书写传统的当代影响与传承轨迹。显然,韦其麟《百鸟衣》模式的民族叙事诗,作为广西现代诗歌的创作传统与审美谱系,一直影响着广西现代诗歌的创作进程与审美维度。
第三,呈现广西(壮族)诗歌的价值与意义。从文学地理学注重探讨“人地关系”和“文地关系”的意义上看,广西作为壮、瑶、苗、侗、仫佬等多个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域,这种民族与地理(地域)的关系特征也反映于广西地域内的文学(诗歌)创作中。李建平指出:“广西的少数民族文学在各民族作家的开创下,也发展成为广西文学最重要的文学形态,其体现出来的民族性,就由原来的地域性特征上升为独立的文学特征了。”[32]在诗歌方面,由于广西是以壮族为主的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壮族诗人是广西地域内少数民族诗人群体的主体构成,所以从诗人及其作品的数量与质量上看,壮族诗人的诗歌创作及其作品不仅一直影响与领衔广西其他少数民族的诗歌创作与审美倾向,还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建构与推动广西诗歌整体创作与探索的作用。韦其麟《百鸟衣》模式的民族叙事诗创作作为壮族诗歌和广西现代诗歌的创作传统与审美谱系,无论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还是自广西诗坛的20世纪80年代及21世纪以来,具有民族特征、地域特征、文化特征的书写模式一直被强化与多维度探索,进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新的民族书写形式与审美特征呈现广西(壮族)诗歌在当代诗坛中的价值与意义。
第四,表征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发展与价值。现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诞生的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学类型,其大致形成于1958年“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和1961年“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讨论会”召开之后。可以说,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从原来的民间文学走向现代文学即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过程中,韦其麟1955年发表的民族叙事诗《百鸟衣》属于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写作者以自身民族题材进行写作的典型作品。而且从时间和影响上看,韦其麟将民族神话传说“诗化”的叙事范式和文本范式,不仅被认为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典范,还佐证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并且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初创期及现代发展与探索过程中,“韦其麟创作中所体现的民族文学现代转型的历史逻辑被深深地嵌入民族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之中”[33]。当下,《百鸟衣》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诗歌)的代表作品,很大程度上表征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发展与价值。
从当下广西诗歌创作的多元共生态势来看,《百鸟衣》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作品,其根据壮族民间传说创作的路径和视角虽已不被追捧,但60余年来,它所形成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如何进行民族书写和文化叙事的模式和经验,却深刻影响着广西现代诗歌甚至中国少数民族诗歌的创作和发展。广西现代诗歌的“花山”探索和“百越境界”讨论即是《百鸟衣》的民族书写传统深化与新探索的有力体现。同时,《百鸟衣》所建构的民族诗歌、现代诗歌的叙事和抒情传统,亦是在不同时期影响着新一代广西诗人对广西这片热土的感知与书写。由此,《百鸟衣》作为壮族诗歌、广西现代诗歌及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经典文本与创作象征,在时间之流中一直发挥着参照与启示作用。
——评王泽龙《现代汉语与现代诗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