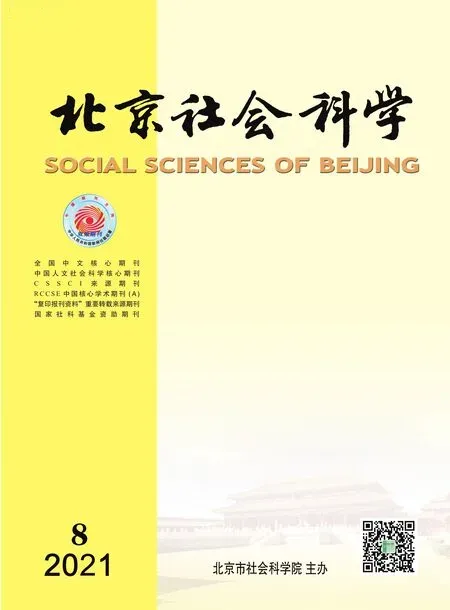论《昔昔春秋》的戏编、奇构与“中体日用”
倪晋波
一、引言
日本江户中期名儒中井履轩(1732-1817),名积德,字处叔,通称德二,履轩是其号;中井甃庵(1693-1758)次子,中井竹山之弟,父子三人俱为当世大儒、大阪怀德堂学派的代表人物。据载,履轩器宇旷迈,不妄交游,谈论奇辟,不循常径,有“畸人”之称。[1]履轩一生服膺儒学,沉迷中国经典,学识浩博,著述宏富。据王三庆先生等主编的《日本汉文小说丛刊》(以下简称“《丛刊》”)所载《〈昔昔春秋〉中文出版说明》,目前可知的履轩著作共有150种左右,所论几乎遍及早期中国的经、史、子、集。其中,与《左传》相涉的有《通语》十卷、《左氏雕题》十五卷、《左氏雕题略》三卷、《左氏逢原》六卷、《属辞连珠〈左传〉年表合本》一卷、《昔昔春秋》一卷等。[2]这些著作中,《昔昔春秋》在日本流布甚广,其体制、内容亦自迥出,深具“中国特色”,目前国内学界专论较罕,故本文拟对该书稍作解析,以就教于方家。
二、《昔昔春秋》的内容、版本与作者之辨
昔者,过往也。《周易·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孔颖达疏:“据今而称上世,谓之昔者也。”[3]昔昔者,夜夜也。《列子·周穆王篇》云:“精神荒散,昔昔梦为国君。”[4]不过,据内容考之,履轩所取当即“过往”之意,“昔昔春秋”即谓“往日的故事”,以重言名之,意在强调。近代学者刘声木《苌楚斋续笔》卷三指出:“书名以重文见义者,《非非国语》《反反离骚》知之者多矣,然类似者甚多。……亚伶散人撰《梦梦录》二卷,撰《昔昔春秋》□卷。”[5]虽然卷数有阙,亚伶散人及其书的详情也暂不可考,但可知中国亦有名曰《昔昔春秋》之书。履轩的《昔昔春秋》用汉文写就,包括《爷公》《桃公》两部分,分别有4300、2300多字,计6600余字,篇幅不算长。该文以日本民间广为传颂的“浦岛太郎”“桃太郎”故事为主轴,以“嫦娥奔月”“猿蟹合战”“播花公公”“活猴肝”“截舍雀”“狸土舟”等中日传说为辅,整合重构而成一篇首尾贯通的小说。这篇新帙模仿《左传》等中国典籍的体制,以爷公、桃公父子为中心人物,以爷公之祖浦岛负约变成白发老翁为引子,以爷公借口其妻婆氏无子而欲弃之为发端,以桃公伐鬼岛功成后羽化升仙为收束,叙写了爷公、桃公两代国君的生平行事,特别是与猿侯、蟹侯、犬伯、狸子、龟子、鬼子等的争斗杀伐,曲折离奇,极具想象。
《昔昔春秋》的具体创作时间,目前不可确知。孙虎堂先生认为在18世纪末,与熊阪台州《含饧纪事》属同代之作。[6]笔者推测可能要更早一些。履轩著有《通语》十卷,叙论日本平安时代保元年间(1156-1159)至南北朝时代元中年间(1384-1392)治乱兴废之事。履轩友人清水中洲说该书“系吾天乐翁早季之作,实在于明和初季矣”;[7]又称“其为书,就当时史乘,以立篇目,因系以语,名曰《通语》,盖效《左氏外传》云。……考核精覈,修辞简明,而褒贬予夺,深得《麟经》之旨矣”。[8]可见,《通语》体效《国语》,旨近《春秋》,作于江户时代明和(1764-1772)初年。《昔昔春秋》是效仿《左传》之作,一经一传,以年系事,叙议相承,褒贬间出,与《通语》也许是同期之作。另一方面,从社会文化背景看,日本明和年间以太田南亩的《寝惚先生文集》等作品为标志,狂诗、狂文开始流行。[9]在这种氛围下,履轩“戏编”中日民间故事而成新制,亦不无可能。
《昔昔春秋》目前流传较广的是青藜阁名山阁版,《丛刊》所收即该版的松村九兵卫发兑本,其内封、版权页均未标明出版时间,但《丛刊》编者在《〈昔昔春秋〉中文出版说明》中称该本出版于“明治十三年(1876)”,[10]未知何据。而且,明治十三年乃公元1880年,1876年对应明治九年,二者有4年之差,故其所称“明治十三年”与“1876”二者必有一误,或均有讹。孙虎堂先生的《日本汉文小说研究》亦承袭致误。[11]据笔者查考,青藜阁名山阁版《昔昔春秋》另有同志书屋翻刻的巾箱本,内封页标“青藜阁名山阁梓”字样即是其证;其版权页又署:“原板年月未详、明治十三年四月六日翻刻。”可见,青藜阁名山阁版必然早于“明治十三年四月六日”,或许就是明治九年。明治十八年(1885)的颜玉堂翻刻本《昔昔春秋》,其版权页亦谓“原版年月未详”。《昔昔春秋》还有文海堂宝玉堂版,其版式、字体、行款与青藜阁名山阁版完全一致,唯发兑者有异,且不标出版时间,应该是明治时期的另一种翻印本。本文以下所引文字即出该本。这四种版本的刻印时间均在明治早期,表明《昔昔春秋》在此时已广为传播。另,昭和八年(1933)大阪青叶俱乐部刊刻铅印本《昔昔春秋》,附于诗文杂集《松风亭》之后;与前四本相比,该版删去了正文中的6处《易经》卦画,或是出于排版便利之虑。
上述前四本的内封页中心位置均依例题写书名《昔昔春秋》,其右署有“中井履轩先生戏编”字样,“戏编”二字暗示该书体制独特。其中,第一、第四两个版本的内封页左侧有一段内容完全相同的日文《提要》,同志书屋本亦录,唯因版式限制,析为两页,列内封页后。《提要》中译为:“履轩先生文章,一时杰出,而传世者稀。此书以桃太郎伐鬼岛童话及猿蟹与狸水陆合战故事,仿《春秋》体制游戏文字,然其文法高大,实作文规则。”[12]显然,明治时期的书贾是将这篇先贤之作视为奇货可居的作文轨范加以推介,有强烈的商业动机。《昔昔春秋》是否“游戏文字”,或有异辞,但它在内容上熔铸中国和日本的诸多民间传说,又在体制上承袭中国的《左传》等经典,文殊体异,确然“高大”。
关于《昔昔春秋》的作者,本无争议,但近代日本学者馆森鸿认定《昔昔春秋》的原作者是清水中洲。其《〈昔昔春秋〉辨》云:
中井履轩著《昔昔春秋》,诚奇构矣。亡友关口士璠尝谓余曰:“吾闻此《春秋》非履轩之作,作者仙台人也,今忘其姓名。其原稿之成也,示之履轩。履轩一见,叹曰:‘非熟左氏文法,决不能为,而修辞未至者,具施点窜,行文更佳。’闻者传写大行,书肆请而梓之。”余求其作者久矣。顷者中目白岭访余庐,白岭仙台人,主铎大阪外国语学校。白岭曰:“昔时仙台人居大阪者不少。清水中洲名原,笃学士也,与吾祖考及履轩亲善,其诗文散逸,吾搜而获廿余篇。中洲为《通语序》,而其墓在大阪。”然则士璠所谓作《昔昔春秋》原稿者,为中洲无疑,而其不署名,盖让美于履轩也。白岭于世界列国,无不涉历,平生尊崇先哲,诱掖后进,而著述甚力,余每敬之。白岭赠《昔昔春秋》,求为之辨,因书以俟博雅。[13]
馆森鸿的依据是友人关口士璠曾告诉他,《昔昔春秋》的作者本是仙台某人,稿成后示之履轩,后者大赞;书商不察内情,又因履轩声名显赫,遂误植其名下。后来,馆森鸿又根据中目白岭之言进一步推论:清水中洲既然是仙台人氏,又与履轩亲善,并为其《通语》作序,那么《昔昔春秋》的原作者必为中洲无疑。馆森鸿此辨,不无疏漏。
细察其说,关口士璠和中目白岭二人皆未直言清水中洲是《昔昔春秋》的原作者,也未提供任何直接的证据,馆森鸿却牵合二者之言,仅凭中洲的籍贯是仙台及其与履轩相善两点,就遽然断言,恐难服众。据山本矶《松风亭记》,清水中洲名原,字士进,通称弥三郎,“庆应丁卯二月九日病卒,享年七十有八”。[14]庆应丁卯即孝明天皇庆应三年(1867),上推可知中洲生于光格天皇宽政二年(1790),少履轩58岁,二人友善,当属忘年之交。中洲以后辈之姿呈送书稿就教于前辈,自合情理。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中洲就会“让美”,履轩亦会“掠美”。事实上,履轩为人洒落不羁,著述等身,生前却多不署名。早野正己《通语序》云:“野史氏以幽人自居,与荣辱毁誉相遗。凡有所述作,皆不表著其名字,又不肯苟出以示人,是以近者或未能悉其意,远者或异而未信。”[15]清水中洲对履轩不以著述邀名射利的心性更是洞若观火,其《刻通语序》亦谓:“翁之著书,不题其名,盖不欲显于世者。”[16]一个连自己的著作都不愿署名的人,又怎会夺人之稿呢?即使中洲主动相让,履轩也断不会接受。因此,所谓“让美”云云,完全是馆森鸿的臆测。大约正是履轩书成不苟出的个性,《昔昔春秋》在其卒后数十年的明治年间才广为世人所知,并被视为“文法高大”的奇构。另一方面,履轩身处江户中叶,对中国经典的认知有与时代氛围相契的古典主义倾向。他认为《论语》为天地间第一文章,其次为《孟子》《庄子》,再次为《左传》《史记》,韩柳以下不足学,东坡以后无文章。[17]察之《昔昔春秋》,确乎如是。该文所镜鉴的华夏典册,集中于早期中国的《周易》《诗经》《左传》《史记》等,唐以下未见(详后)。总之,履轩作为当世硕儒,清高尚古,谓其挟前辈之名而掠后辈之书,揆诸情实,实难置信!《昔昔春秋》的原作者乃中井履轩无疑。
三、《昔昔春秋》的体制及其中国渊薮
对于《昔昔春秋》的体制,前述明治时期的多个版本的内封页《提要》均称之为“春秋体”。孙虎堂先生说这一体例“即经、传搭配组合的形式。就规范的编年体史书而言,‘经’是用最精炼的语言来概括的史实,‘传’则详细叙述对应史实的事件内容,而且其中的历史内容严格按照时间先后排列”。[18]此言大体可从,但若严格检视,则不无可议。中国历史散文的体例,较早出现的是春秋体,以编年式的叙事框架和提要式的事件记录为文体特色,并未涉及“传”的成分。《魏书》卷六二《李彪传》云:“自成帝以来至于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国书》,编年序录,为《春秋》之体,遗落时事,三无一存。彪与秘书令高祐始奏从迁固之体,创为纪传表志之目焉。”[19]李彪对春秋体与纪传体的分际了然于心,并指出前者述事过简,有经无传,不能存录史迹全貌。从正文来看,《昔昔春秋》以时系事,经传相成,其体制与《左传》类同,称之为“经传体”更合适。
为论述之便,先行撮录《昔昔春秋·爷公元年》经、传的部分段落如下,括号中的文字为原文自注。
【经】
元年春王正月,公如山。(樵山。)二月,公会猿侯、犬伯、狸子、兔子伐薪。(翁话曰:“爷入山刈草。”今曰薪者,从谈也。)夏五月,夫人婆氏濯于河,(濯,洗衣也。)有桃流来。(桃,桃实。)秋七月,公至,自伐薪。(无传。传例曰:“告庙则书。”)冬十有一月,桃公生。(所谓“桃太郎”也。)
【传】
元年春正月,公如山,为樵也。初,公娶婆氏,有宠,衰老至,无子,叹曰:“寡人娶室,非色是溺,唯继之求。夫人不体吾志,至今无孕。古人有言:‘非其所憾而憾焉,谓之不知其所憾。’寡人将何处乎其憾?且我闻之,老而无子则去,夫人其谓之何?”婆氏跪泣曰:“天之与人嗣子,非人之所得而能,故尧之子实为丹朱,舜之子实为商均,则有犹无。苟以不孕弃之,天下尽为孀妇,而孰育之者?虽然,妾有罪焉,妾听命矣。”入房将缢,公惊,使急止之……公如山,婆氏请曰:“君将有事于山,妾当内守者固也。《诗》曰:‘薄澣我衣,薄漱我私。’”……婆氏乃赋《采薪》曰:“采薪采薪,于彼山巅。”公亦赋《洗衣》曰:“洗衣洗衣,彼河之边。”
五月,婆氏濯于河。……河上有物,绛绛而圆,使取之,桃也。啖之,美,乃筐一斤而归……公喜啖之,忽然化为美丈夫。入视妇人,亦既为美少妇,相与惊且喜,而又有羞色,遂寝。夫人如有震,公使筮之,遇《睽》之《归妹》,其贞曰:“女承筐,无实。”其悔曰:“载鬼一车。”史曰:“是为睽孤,(睽,乖离也;孤,独也。)夫人承筐,喰是实,所以无实也。离,丽也。夫妇虽丽附以说,或相睽也,(离为丽,兑为说,言爷婆相配以悦,后或相乖离,是因睽卦以推其离合。)后而其子孤也。(即指桃公。)上变为震,震为长男,必太子也。此子也,生六年,将有事于鬼国,乃大有获。”(上六变,故曰“六年”;“载鬼一车”,故知有事于鬼而有大获也,为桃公二年伐鬼城传。)
冬十一月,婆氏生桃。桃生而神爽,越五六日,力克扛鼎,屹如大人。公爱之,咳名之曰桃……君子曰:“爷公其衰乎!《诗》曰:‘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谓华速盛也。华,身之文也;实,心之质也。质以树德,文以饰礼,虽有文华,宁遗心实。华盛则实衰,盛之速乃衰之速也。今太子生而盛矣,爷公无奈衰乎!且文木兆为桃,爷氏之盛衰将木是兆,谚所谓‘桃栗三年’,亦速之谓也。”(为下婆氏蒐于株木舟报仇、公老于薪山传。)[20]
先经后传,经略传详,正是《昔昔春秋》的体制特点之一。全篇经传相间,对举6处,外加开头作为引子的单传1处,7处经、传共叙述了爷公、桃公两代君主6年之事,其中《爷公》4年,《桃公》2年,是典型的经传体。赵生群先生说:“左氏解经,不外乎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发凡起例,一是综述其事。《左传》凡例部分无法离开经文而独立存在,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而《左传》叙事部分同样必须附丽于经。”[21]《左传·庄公二十七年》:“凡诸侯之女,归宁曰来,出曰来归,夫人归宁曰如某,出曰归于某。”[22]说的是与嫁、娶、归宁相关的凡例。上引《爷公元年》所谓“无传。传例曰:‘告庙则书’”,正是发凡起例。《桃公元年》“鬼师败绩不书者,龙王讳之也”,[23]亦是如此。但与《左传》不同的是,《昔昔春秋》的发凡起例皆以注文形式呈现。

履轩模仿《左氏春秋》,经传间举,以传解经,又自注其文,诠解传意,借用的正是中国经学的传注体。传、注、笺、疏、章句等解经方法是历代经学最基本的言说体式,经学家以此诠解经文,揭橥大义。学者指出,这种“经、注一体”的话语方式也是后世文学评点“注文与正文一体”的体例之源,运用经学传注从事文学批评,是经学语境下文学批评家必然的文体选择。[28]但对于博通中国经籍的履轩来说,以传注体进行文学重构,则是深谙其道的主动选择,此一选择不仅使《昔昔春秋》串联起山川异域的中日民间故事,而且贯通了本自悬隔的经学与文学,谓之“奇构”,名副其实。
四、《昔昔春秋》的“中体日用”特征及其表现
日本的汉文学史源远流长。神田喜一郎先生谓:“日本汉文学是我国第二国文学……是以汉本土的文学为基础而派生出来的。因为它的作品是用汉本土的文字,根据汉本土的语言规则而作,而且在历史上是一边不断追随汉本土文学的发展,一边实现自己发展的。”[29]就是说,不同于以和歌、和文为代表的“第一国文学”,日本汉文学是使用汉语并遵循其语法规则、思维模式,通过模仿、改造和融合而衍生出来的中国文学的一条支流,从一开始就具有“中体日用”的特征。《昔昔春秋》的主体故事虽然来自日本传说,但它是汉文写作的新小说,属汉文学无疑。不同寻常的是,在“追随汉本土文学”的过程中,触处可见的中国典籍及体例模式、内容情节等令《昔昔春秋》中的“日本故事”的主体性发生了转换,几乎变成了一个意到神随的“中国故事”,此即“中体日用”。上文论及的以中国经注之体制重构民族故事,正是其表现之一。不惟如此,它还以中国文史之内容敷衍遗逸意蕴,此其表现之二。
作为先秦礼乐文化的标志性图景,赋诗言志也是《左传》最突出的文本符识和时代表征之一。《汉书·艺文志》:“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30]微言相感、称诗谕志,既可以别贤不肖、评骘人物,也可以宣达使命、见盛观衰,还可以袒露心意、互陈款曲。履轩深解其中三昧,包括赋诗言志在内,《昔昔春秋》直引《诗经》原文或暗用《诗》意者共有13处。上引《爷公元年》,爷公因婆氏年高无子,言欲弃之,婆氏听后,悲愤欲缢,爷公急止之,二人遂互陈心曲,和好如初;随后二人分别有事于山、河,婆氏赋《采薪》曰:“采薪采薪,于彼山巅。”公亦赋《洗衣》曰:“洗衣洗衣,彼河之边。”考诸《诗经》,《周南·汉广》有“翘翘错薪,言刈其楚”,“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之言,[31]未有《采薪》之目;《葛覃》有“薄污我私,薄浣我衣”之句,[32]不见《洗衣》之篇。爷公、婆氏所赋两诗显然是履轩借用、改造《诗经》而作,意在互表关怀,弥补嫌隙,此即其“志”。又如,《爷公四年》:“公醉,令狸子鼓腹奏乐,自赋《七月》之四章。”履轩以注文的形式揭示了其中之“志”:“《诗》曰:‘取彼狐狸,为公子裘。’公歌之,以辱狸子为戏。”[33]此写爷公赋《诗经·七月》第四章相关诗句戏辱狸子,也为下文狸子的报复埋下了伏笔。
《昔昔春秋》用《诗》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合“君子曰”而用之。如,《爷公元年》“《诗》曰:‘桃之夭夭,灼灼其华’”、[34]《桃公元年》“《诗》曰:‘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35]均以“君子曰”形式称引,意在生发议论。这一模式亦源自《左传》。《隐公元年》:“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36]“君子曰”作为《左传》的一种义例,共出现了40多次。虽然“君子”一词之所指,尚存异说,但其具有评断是非、劝善惩恶、兴观群怨、阐扬大义等功能则是学界共识。同时,这一义例多称引经典之文或先哲之言,此处引用《诗经》来表彰颖考叔之孝,也有劝诫世人之意。《昔昔春秋》全文有7处“君子曰”,其中5次是合《诗》而用,可见其多。不过,履轩对“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诠解已然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注疏。《毛传》:“兴也。桃有华之盛者。夭夭,其少壮也。灼灼,华之盛也。”[37]履轩则赋予其“华盛则实衰,盛之速乃衰之速”的微言大义,用来隐喻爷公为子取名为“桃”的不祥后果,并为后文张本,凸显了履轩对中国经典的创造性理解和灵活应用。
《左传》的另一个重要特色是多叙巫卜之事。晋人范宁因此批评“《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38]对其多叙鬼神、卜筮、预言、梦境、灾详之事颇为不满。然而,正如凌稚隆《春秋左传注评测义》所云:“说者往往病其诬,盖据其所纪妖祥梦卜鬼怪神奇一一响应,似属浮夸。然变幻非可理推,古今自不相及,安知事果尽诬,非沿旧史之失耶? 惟是专以利害成败论人,故先为异说于前以著其验。”[39]就是说,以历史主义的角度视之,《左传》的巫卜未尝不是所来有自的“实录”,真实地折射了当时的主体认知和文化心理;而作为历史的忠实记载者,左丘明或许并无神学目的论之企图。《昔昔春秋》作为中日多个民间传说的杂糅之作,镜鉴《左传》巫卜手法之处俯拾可见,但主要出于文学考量。该书以《易经》卦画、爻辞为文者有6处。如前引《爷公元年》,爷公和婆氏吃了河中漂流之桃后,分别幻化为美丈夫和美少妇,此后婆氏有孕,爷公命史官卜之,得《易》之《睽》《归妹》二卦。前者的上九爻辞谓:“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40]后者的上六爻辞曰:“女承筐,无实。”[41]史官据此卜断是吉兆,认为婆氏必生太子,并在其后六年大败鬼国。后来,婆氏果然生下太子桃公,其他卜兆亦获应验。在日本《桃太郎》的原故事里,老妪捡获河中漂来的桃子后,正准备与老翁剖食,此时从中蹦出一个小孩,即桃太郎。[42]两相比照,可知履轩是以中国史著的叙事手法和哲学思维改造民族故事的传统情节,不仅取得了卮言悦人的陌生化效果,更增进了叙事张力和文学趣味。这自然亦是履轩娴习《左传》《周易》的结果。
《昔昔春秋》对《左传》的袭用还体现于经典情节、人物名号等方面。《爷公四年》:“龙王之妃有疾。医鱼曰:‘病在膏肓,非牛溲马勃之所能治。’”[43]显然是取意于《左传·成公十年》医缓断晋景公膏盲之疾这一情节,妙用无痕。《昔昔春秋》的人物差序类似《左传》,以王、公、侯、伯、子为次第,龙王、爷公、猿侯、犬伯、狸子等形象,等而下之,秩序森严。其中,犬伯有子名杵臼,这是《左传》的常见人名,齐景公、陈宣公、宋昭公都叫杵臼。《昔昔春秋》还多次以讴谚俗语入文。《爷公四年》载,妪氏被狸子杀害后,爷公遍寻不见,这时,“有讴于窗前者,曰:‘喰妪之爷公,孰知庖下之骨。’”[44]藉此歌谣的暗示,爷公才明白妪氏的所在。《左传》谚语歌谣的功能较为复杂,《昔昔春秋》虽比之不及,但作为一种叙事话语,无疑增进了其文本的多样性和戏剧性。
可见,《昔昔春秋》不仅承用《左传》体制,而且利用其赋诗言志、巫卜预言等标志性叙事模式,更有对其诸多细节的直接借用,的确是“非熟左氏文法,决不能为”,但这并非是其“中体日用”的全部。履轩对《尚书》《诗经》《周易》《庄子》《孟子》《礼记》《公羊春秋》《史记》等中国经典及其注疏也驾轻就熟。他的《记钓游》一文被认为深得庄周门径。[45]《昔昔春秋》文末,桃公昼寝,梦见自己“腋生两翅,蹁跹欲飞,愕然而觉”,[46]遣词用语极类《庄子·齐物论》文末的寓言“庄周梦蝶”。又,《爷公二年》“躇阶而避”下注:“《公羊传》。何休云:‘躇阶,越阶也。’”[47]文、注皆用《公羊传》,唯语词稍异。《公羊传·宣公六年》:“躇阶而走。”何休注:“躇,犹超遽不暇以次。”[48]又,《爷公四年》传,兔子对桃公说:“臣之祖先大夫毚兔尝与嫦娥婚,死而奔月,月中之婆娑乃臣之先人也。”[49]兔子竟然以古老的中国嫦娥奔月神话为“吾家事”,可见履轩的陌生化重铸不仅施之于己,亦施之于人。信手拈来的径行袭用与时空易置的迁想移植,是《昔昔春秋》以中国经典之内容,改造、丰富本土传说故实的两种基本文学技法,实乃“非熟中国文史,决不能为”。
前文述及,《昔昔春秋》之作可能与明和年间流行的狂诗狂文风潮有关。也有学者指出,《昔昔春秋》是江户中后期儒学“多歧化”“余技化”“游戏化”的产物。[50]明治年间多个版本的《昔昔春秋》均标注“中井履轩先生戏编”,或亦缘此。履轩固然狂放不羁,但并非矜夸惑众的浅薄之徒,其著述不苟示于人者,乃欲“俟后之子”也。[51]早野正己《通语序》谓:
唐虞三代之道,宇宙之间无不有也。修己治人者,苟能有取焉,以广其鉴省,则野史氏必欣欣含笑于地下矣。若或徒喜奇文至论,忘求诸己,昂然搦管,欲效颦以求名耶,则其于读斯篇也违,而非得野史氏之心者也。[52]
《通语》以“野史氏”之名褒贬予夺,《昔昔春秋》藉“君子曰”之例衡论短长,两著时或声情相通,互见“野史氏之心”。《昔昔春秋》中,爷公为人轻率,常常以言辱人。《爷公元年》记录了他对婆氏“老而无子则去”的愤言,直接导致婆氏自杀未遂。《爷公四年》又载,爷公常以言羞辱侍臣狸子,后者因此怀恨在心。一日,爷公将狸子缚悬梁上,并戏言:“不出诘朝羹汝。”狸子遂决心报复,竟将爷公续娶的妪氏“捣而弑之”,并做成羹汤给爷公吃,爷公知悉真相后,大为悲恸,但悔之晚矣。叙事方毕,履轩即以“君子曰”的方式批评说:
爷氏一言之戏以征祸,言可弗慎诸乎?《诗》曰:‘“白圭之玷,犹可磨也。”又曰:“善戏谑兮,不为虐兮。”爷氏于是乎?阙之矣。[53]
爷公负恃国君之威,一再苟言凌人,不懂慎言戒惧之古训,终致戏言贾祸。然而,纵观历史,言行轻率而不知鉴往之人何其多也!《通语》卷八《元弘语》:“野史氏曰:天下难为之事,为之信难。为之而一踣,后人将惩而弗继;为之而再踣,后人将相戒勿继。惩而弗继,尚或有弗惩焉;相戒勿继,然后竟无有继焉者。是故君子临事而惧、深虑而后动。夫王政之替,亦已久已哉,兴之不亦难乎?承久踣之于前,元弘、延元踣之于后,然后有复之者?已焉哉!已焉哉!余深为当世慨之。”[54]慎言敏行、临事戒惧,方能谋而能远、兴而不坠,履轩的这一历史认知互见于《通语》和《昔昔春秋》。这也提醒读者,若纯然以“戏编”来审视《昔昔春秋》,就会忽略其间的奥蕴。
值得注意的是,履轩这里再一次合《诗经》而申“君子曰”。“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是《卫风·淇奥》的末句;“白圭之玷,犹可磨也”出自《大雅·抑》,后续之句谓:“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无易由言,无曰苟矣,莫扪朕舌,言不可逝矣。”[55]慎言戒惧是古老的中国智慧和训诫之一。《诗经》《论语》等经典的相关表述,不仅指向了道德修养和个体荣辱,更将其提升至国家兴亡的高度。[56]履轩以爷公之祸申发议论,引《诗经》之句而不尽举,当是留白以待读者自味其意,深得中国古典文学含蓄蕴藉、意在言外之旨。又,《桃公元年》:“君子曰:以德报德,人犹为慊。猿侯报以诡谲,蟹侯报以暴戾,二侯不免乎?《诗》曰:‘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二侯之不得永好,亦其宜矣哉!”[57]同样是引《诗》立说,申明“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华夏古义,反对阴谋暴戾之行。这一点在《通语》中也有呼应。护良亲王(1308-1335)是后醍醐天皇(1288-1339)之子,在协助其父讨灭镰仓幕府的过程中功莫大焉,但在功成之后与足利尊氏(1305-1358)争权,并意欲篡位,终致事败身死。日本不少人认为护良是无罪冤死,履轩批驳道:“乃以私怨寻干戈,欲擅勠天子宠臣,护良其罪也。”[58]直言护良是以私怨寻衅的罪人。作为大阪朱子学派的后期代表,履轩有着鲜明的人本主义立场,而言与德则是儒学衡人量行的基本范畴,《昔昔春秋》的“君子曰”反映了他对世道人心的价值期待。
总之,从著述旨归看,《昔昔春秋》具有以中国儒学之价值规讽当世教化之诉求,这是其“中体日用”的第三个表现。河野荃汀《题履轩〈昔昔春秋〉自画赞》云:“中井兄弟最用力左氏,竹山之于《逸史》、履轩之于《通语》,可谓克肖盲史,而《昔昔春秋》最得其神髓,未可以游戏文学轻之也。”[59]诚哉斯言!
五、结论
纵观履轩的思想意识,其置身于以朱子学为核心的江户儒学共同体中,服膺中国经典,以中国为“文化的原乡”,并没有因为他者身份或外部力量而引发过多的文化紧张感,但他的确感受到了“儒学本身跼蹐在其硬壳中丧失了理论上向前发展的可能性,显示出转化为经学、文章学乃至经济类的倾向”。[60]因此,履轩通过批判性地诠释朱子学,呼应伊藤仁斋的“人伦日用”之“道”,突出了儒学的人间品格和现实价值。履轩在当世以“幽人”自居,又曾将自己居住的陋室命名为“天乐楼”,自称“华胥国王”。对于此举,子安宣邦解读说这是履轩“居于世界之内,却以外部视角观察世界的一个虚构之场……确保了一个外部视角,从而完成了对既有知识构图的转换”,并将“自己的存在形态转变为独自的知性表达”。[61]所以,就学理言,履轩不是一个迂执不化的陋儒,其自我疏离不是自绝于世,反而是迈向知性独立和澄明之境的津梁。他以中国文史经典的体制内容和价值旨归改撰日本传统故事而成《昔昔春秋》,并与《通语》等著作呈现出一体化的学思逻辑,与其说是“戏编”和奇构,不如说是其独特的知性转换的文学呈现。进而,就文学言,江户汉文学被认为是日本汉文学史的第三个高峰,甚至是最高峰,但无论是依附儒学而存的早期,还是古典主义风行的中期,抑或折衷学派主宰的后期,汉诗都是其创作的主流。履轩却对当时的诗风深恶痛绝,不屑作诗。因为在他看来,“古人以诗言志,今则以诗贴花傅叶,务出新奇以斗才华,风雅扫地,即使作诗能侪古人,也只是雕虫小技,非丈夫所为”。[62]《尚书》云“诗言志”,《左传》谓“诗以言志”。履轩尚友古人,信而有志,但不愿言之以诗,自然只能寓之于文。因此,履轩依傍《左传》等中国经典而作《昔昔春秋》,也有反动江户时代浮华诗风的意味,并最终造就了这篇日本汉文学史上别出机杼而极具 “中国特色”的妙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