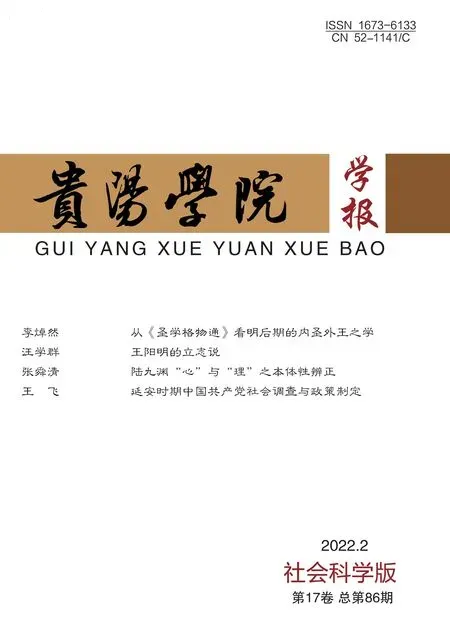王阳明的立志说
汪学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古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王阳明十分重视立志,强调立志的必要性,立志是做人的根本,也是为学为道的前提,更是用功不可或缺的部分,或者说立志就是一种工夫。
一、立志是根本
关于志与气的关系,《孟子·公孙丑上》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朱熹注:“故志固为至极,而气即次之。”[1]281主张志与气前后有次序。有人就此问王阳明,王阳明认为志与气无先后顺序:“‘志之所至,气亦至焉’之谓,非极至次贰之谓。‘持其志’则养气在其中,‘无暴其气’则亦持其志矣。孟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夹持说。”[2]24志至气也至,志至并非至于极之谓,气次也不是气居第二位之谓。他反对朱熹的说法。“持其志”养气在其中,“无暴其气”也是持其志,说明持志与养气没有先后,共时即同时存在,相互统一。告子主张性无善恶,生之谓性,仁内义外,立论片面,孟子批判告子,因此在志与气问题上左右扶持,使其不偏。立志是根本,“立志者,其本也”[2]183。有有志而无成者,没有无志而能有成者,说明立志是成功的先决条件。
人并不都是圣人,其心不能无所系着,不系于正就系于邪,不系于道德功业就系于声色货利,因此必须先端正方向。这是王阳明经常强调首先要立志的原因[2]1807。郭善甫从学一年多准备回去,临行前向王阳明请教道:听闻你的立志之说,也知道如何去实践,现在我将远去,敢请赐一言以为时刻遵循。王阳明回答道:君子对于学如同农夫种田,先挑择好种子,深耕易耨,去其蝥莠,时刻灌溉,早作而夜思,如此秋天才有好的收成。志不端正如同杂草,志端正而不用功似五谷不熟,还不如杂草。我看你曾求获佳种尤其恐惧杂草,见你勤于耕耨尤其恐惧不如杂草,农事讲究农时,所谓春种而秋成,立志也如此。先学习立志,立志而不惑,持之以恒,加倍努力。我讲学时从游者众多,虽然也不乏阐释自己学说者,但真正立志的却不多。因此,王阳明常告诫从游者贵在立志,立志是从事一切的前提。
王阳明在致人书信中认为,当今朋友具有优美品质的不在少数,但有志者却不多,说做圣贤达不到,所为也不过是建立功名炫耀一时,以骇愚夫俗子之观听。本来人都可以为尧舜参天地,而却以功名自期,不也感到很悲哀吗?朋友中每每倡导立志,却有感到厌烦的,可以看出立志的艰难。为学如果不立志如同植木无根,生意将无从发端,从古到今有志而无成者有之,却没有无志而能有成者。与张世文远别无以为赠,则反复申明立志之说,这并不是迂阔而是表现出立志的执着[2]1050。在给滁州诸弟子信中指出,离开滁州后一天也没有忘记你们,虽然没有文字往来,这并不是简约,而是不想以世俗无益之谈相往复。有志的人虽然我没有一个字写给他也如朝夕见面,无志的人虽然面对面也如千里,即便是千里之外的通信也无用[2]1030。此番议论是勉力有志者,鞭策无志者或使他们树立自己的志向。
王阳明致黄宗贤书中讲起与诸弟子学习《孟子》“乡愿狂狷”一章,颇觉得有所警发,相见时必须要再作深入讨论。四方朋友来去无定,中间有切磋砥砺之益,但真有力量能担荷得者却十分少见。大体说近世学者缺少一定要做圣人的志向,只是胸中有物而未得清脱。听说引接同志孜孜不怠为圣人之志,这非常好,但议论须谦虚简明为佳。如果自处过任而词意重复,恐怕无益而有损[2]1297。又致薛侃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仁指爱物的真诚,又有不能控制的,关键要遵循《周易·系辞上》所说“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困心衡虑以坚定其志节,动心忍性以增益其不能,自古圣贤只有这样做才能屹立于天下[2]1822。
弟子问立志,王阳明把存天理、良知与立志联系起来,说:“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则自然心中凝聚,犹道家所谓结圣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驯至于美大圣神,亦只从此一念存养扩充去耳。”[2]12把存天理称为立志,天理之念常存在于心中并加以凝聚,这如同道家讲的结胎,也可以说是结圣胎,其无形却是精神凝聚。精神凝聚处如胎中下圣种,常常存养扩充天理之念,就会如《孟子·尽心下》所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美大圣神是赞美常存天理之念,而这一念离不开存养扩充,说明存天理离不开立志工夫。一次,何廷仁、黄宏纲、李侯璧、王畿、钱德洪座陪,王阳明对他们说:“汝辈学问不得长进,只是未立志。”李侯璧起来回应道:“珙亦愿立志。”王阳明说:“难说不立,未是必为圣人之志耳。”又问:“愿立必为圣人之志。”王阳明回答说:“你真有圣人之志,良知上更无不尽。良知上留得些子别念挂带,便非必为圣人之志矣。”[2]115这段对答表明学问长进在于立志,立志要立圣人之志而非其他志向,必须从良知入手,良知纯静无所挂带便有圣人之志。
二、立志与学道
立志是起点而非终点,立志的目的在于学道,学即为学或学问,道即学问或为学之道,也包括道德等精神方面的追求,这是王阳明强调立志的另一个方面。他主张:学者立得定,便是尧、舜、文王、孔子的根基,如说:“由志学而至于立,自春而徂夏也。由立而至于不惑,去夏而秋矣。”[2]1676志学与立志互为因果,立志则不惑,立志是主心骨,贯穿整个生命过程。
朱守谐与王阳明有一段问答讨论为学与立志的关系。朱问为学之道,王答:立志而已。朱又问立志,王答:为学而已。朱不解,王答:人学做圣人如果没有一定要做圣人的志向,虽然想做圣人也做不得,如果有做圣人的志向而平时不努力去做,空谈立志于事无补,“故立志者,为学之心也;为学者,立志之事也”。立志是确立为学的心志,为学不过是立志的实现。如《孟子·告子上》载:两人下棋,下棋是事,专心致志说明心专一,而以为鸿鹄将来是心为二,弈秋专心致志于事,而心想着用弓箭射鸿鹄是分心,做事如何做得好[2]293。
王阳明提出“夫学,莫先于立志”[2]276的命题,志不立如同不播种而只从事于培壅灌溉一样,劳苦无成。世间之所以因循苟且、随俗习非,最终沦为污下之人都是未立志。“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而曰学,皆苟焉以自欺者也。”立志在先然后才是学。如同种树,志是树根,不培植好根树就不能生长。现在的学者谁肯自称无志?他们能够像农夫对于田地、商贾对于货物,用心思计量,早晚勤劳,时刻挂念吗?不如此就是无志。如果有志于货物,虽然有亏耗但终究有利息,有志于田地,虽然有旱荒但终究有丰年。笃志一定会获得成功,不立志将一事无成。因此,孔子说志学志仁志道,匹夫不可夺志。周敦颐说志伊尹之所志,程子说有求为圣人之志,然后可与共学。王阳明说志是人之命,命不续则人会死,病源学脉不外乎此。
有人问:“为学以亲故,不免业举之累。”王阳明说:“以亲之故而业举,为累于学,则治田以养其亲者亦有累于学乎?先正云:‘唯患夺志’。但恐为学之志不真切耳。”[2]33为学最要紧的是确立自己的志向,先正即程子有所谓科举之事,不怕妨功而唯患夺志,说明志向高于一切。为学的志向要真切,讲的是学在于求心,遵循天理、孝顺父母自然应包括其中。志可战胜私欲,学问不明在于有志的人太少,人不能战胜私欲,竟沦陷于习俗。朋友之间有志者是件很可喜的事,而立志艰难且易坠,因此也要深深畏惧才是。
在王阳明看来,天下之人志轮便能成轮,志裘便能成裘,志巫医便能成巫医,有志于其事而没有不成的,所谓有志者事竟成。轮裘巫医遍及天下,“求圣人之学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欤!”求圣人之学者却少得可怜,是为圣人之事难抑或为圣人之志难?当然是志难,没有立志便不可能成其事。林以吉就此问王阳明,他回答道:“志定矣,而后学可得而论。”[2]242—243如你志在闽将求去闽之路,我对你说去越之道路,你肯定不听;我志在越将求去越之路,你对我说去闽之路,我也不听;士大夫久溺于流俗而突然向他们讲求圣人之事,或茫然无所对,或以各种托词推委,由此可见确立自己志向的艰难。志向一旦确立,学问便成功了一半,立志是为学的前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学问杂乱无章之际,我辈要有清醒的认识以团结同志务求其实,以身明道学为己任。虽然具体为学的过程中有所差异,但不妨碍其志趣相同,这才是最主要的[2]197。
立志是立善念,王阳明说:“学者一念为善之志……故立志贵专一。”[2]36立一念为善之志,所谓立志要专一,专一又非刻意有为而是顺其自然,如《孟子·公孙丑上》所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以种树喻指养心,种树在于培植其根,种德在于培养其心,养非外求,尤其不要把精神耗费在诗文上,而要反向内求,不要人为或主观助其长,只管培植而使其自然成长。这说明立志之后下工夫也是顺其自然而非主观人为。唐诩问:“立志是常存个善念,要为善去恶否 ?”他回答说:“善念存时,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恶,更去何恶?此念如树之根芽,立志者长立此善念而已。”[2]21刘宗周评说:“念本无念,故是天理;有念可存,即非天理。”[3]善念存即是天理,说明此善念超越善恶对立属于本体,因此无所谓为善去恶。立志就应从立此善念开始,又引《论语·为政》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正是立志善念后的行为纯熟与灵活运用。
王阳明在致其族叔祖王克彰信中也论述善恶之念:所谓“善念才生,恶念又在”,也足以见尝用力,但于此处须加猛省。为何如此?这正是习气所缠。自从俗儒之说盛行,学者只从事于口耳讲习,而不再知晓有反身克己之道,现在想要反身克己,必须要摆脱口耳讲诵之事的束缚。他说:“夫恶念者,习气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为习气所汩者,由于志之不立也。故凡学者为习所移,气所胜,则惟务痛惩其志。久则志亦渐立。志立而习气渐消。学本于立志,志立而学问之功已过半矣。”[2]1031—1032把恶念视为人后天的习气,善念视为人先天的本性,如果本性为习所胜气所汩,其原因在于志不立,因此立志尤为重要,可以说是人的主心骨。要坚定其志,消除后天的习气而回归于先天人的本性,这又离不开学问,也可以说学问是为培养心志服务的。他通过致书信方式阐述立志有自我反省之义,钱德洪在书信后作跋也有与王阳明之子王正亿共勉之意。
《论语·述而》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一句,王阳明解释说:“只‘志道’一句,便含下面数句功夫,自住不得。”[1]109如同盖房屋,志于道是想着要去择地鸠材,经营成个区宅,据德是经营谋划已成有据可依,依仁是常常住在区宅内更不离去,游艺是加些画采美此区宅,艺是义即理之所宜,如诵诗读书弹琴习射等皆所以调习此心,使之熟于道。如果不志道而游艺,则如无状小子不先去置造区宅却只管要去买画挂做门面,不知将挂在何处?这是以盖房屋为喻说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等工夫,如此说道德仁艺四者方打成一片,志于道无疑是根本。
王阳明认为,志于道主要讲的是精神志向。人问:“孔门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任礼乐,多少实用?及曾晳说来,却似耍的事,圣人却许他,是意何如?”王阳明答道: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人是“有意必”即太着意,违背《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只能行此事而不能行彼事,格局不大而且趋于片面,子路、冉有、公西华是《论语·公治长》所说的“汝器”。曾点则“无意必”即不着意,这便是《中庸》所讲的:“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素位即现在所处的位子,这里指在什么地位就能做什么事,位子不同做事也不同。同时也不拘泥于一事,即如《论语·为政》所说的“君子不器”,不为一技之长所限。前三人各有一技之长,属于实用性人才,曾子则不属于此类,三人就务实这一点而言,孔子也十分赞赏,但更欣赏曾点不局限一技之长而领悟大道。王阳明也以此为上,以道为旨归,此道为精神志向。《论语·公冶长》载:孔子“使漆雕开仕”,漆雕开说:“吾斯之未能信。”对于漆雕开不急于当官而专心学礼,孔子很高兴。《论语·先进》载: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孔子认为这是误人子弟。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陪孔子,孔子请他们谈自己的志向。子路说:“千乘之国……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孔子讥笑他。冉有说:“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公西华说:“宗庙之事……愿为小相焉。”曾点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赞同曾点的说法,王阳明以为,“圣人之意可见矣”[2]15。孔子不喜欢自己的弟子立志向于当官或者说追求某种利益,而更注重精神上的洒脱。如称赞曾点的志向,此志向超凡脱俗,甚至趋向审美,王阳明也是追求此志向的人。
王畿、黄勉之陪同王阳明,他握着扇对他们说:“你们用扇。”黄勉之起身答说:“不敢。”王阳明说:“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装做道学的模样。”王畿说:“观‘仲尼与曾点言志’一章略见。”王阳明予以肯定,认为:“以此章观之,圣人何等宽洪包含气象!且为师者问志于群弟子,三子皆整顿以对。至于曾点,飘飘然不看那三子在眼,自去鼓起瑟来,何等狂态。及至言志,又不对师之问目,都是狂言。设在伊川,或斥骂起来了。圣人乃复称许他,何等气象!圣人教人,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2]114见弟子们拘谨,则批评为道学模样。又引《论语·先进》“仲尼与曾点言志”一章说明圣人宽宏气象。孔子让弟子们各言己志,曾子狂言而孔子却肯定,如果换作程颐可能斥骂起来。二程与韩持国同游西湖,持国命诸子侍行。行次,有言貌不庄敬者,程颐回头看后厉声叱道:“汝辈从长者行,敢笑语如此,韩氏孝谨之风衰矣。”持国遂皆逐去之[4]。王阳明是在批评程朱道学拘谨,圣人教人不束缚,狂狷并蓄,因材施教而且有宽大志向。
志士就是有崇高志向的人。弟子问《论语·卫灵公》“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一章含义,王阳明答道:“只为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来太重,不问当死不当死,定要宛转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却丢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为?若违了天理,便与禽兽无异,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过做了千百年的禽兽。学者要于此等处看得明白。比干、龙逢只为他看得分明,所以能成就得他的仁。”[2]113不要把肉体生命看得太重,应该超越生死,因为生身命与天理比是次要的,天理是第一位的,如果违背天理,人与禽兽就没有什么区别,把天理看成最重要的,不惜生命去捍卫天理,这才是志士仁人。如殷纣王的叔父比干谏纣不听被杀,夏桀贤臣龙逢谏桀不听被杀,这些大臣为维护天理而谏,最后被杀,可谓杀身成仁,即志士仁人。
《论语·述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朱熹注曰:“未得,则发愤以忘食;已得,则乐之而忘忧。”[1]125王阳明不赞同朱熹以未得与已得解释“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一句,而以圣人之志与道诠释说:“‘发愤忘食’,是圣人之志,如此真无有已时;‘乐以忘忧’,是圣人之道,如此真无有戚时。恐不必云得不得也。”[2]105-106以“发愤忘食”释圣人之志,“乐以忘忧”释圣人之道,志与道的统一为圣人内在所固有,因此孙奇逢评道:“圣人元无不得之时。”[5]立圣人之志、达圣人之道才是最重要的。
王阳明屡申立志之说,以此劝勉同仁:“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2]174而当时人所谓的道德即是功名,所谓的功名也即是富贵,把道德与功名、富贵等同是错误的。仁人应“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有谋计之心,虽然标榜正谊明道,也不过是功利罢了。他说:“但能立志坚定,随事尽道,不以得失动念,则虽勉习举业,亦自无妨圣贤之学。若是原无求为圣贤之志,虽不举业,日谈道德,亦只成就得务外好高之病而已。”[2]181-182立志比科举重要,是道德实施的前提。古人所以有所谓“不患妨功,惟患夺志”之说,说到夺志应该已有志才可夺,如果没有可夺之志,那还不如先立志。夺志是以立志为前提的,因此立志是第一位的。
三、志与工夫
立志与工夫关系密切,是用功的前提,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立志就是一种工夫。王阳明说:“我此论学是无中生有的工夫,诸公须要信得及,只是立志。”[2]35-36正是此意。
立志是下工夫的前提,黄绾刚拜谢铎为师不久,任后军都督府都事,听王阳明讲学,两人见面。王问:做什么工夫?回答说:刚立志,还没有做工夫。王说:人怕的是无志,不怕无工夫可用[2]1685。古代圣贤因时立教好像有所不同,其用功大旨没有太大的区别。如《尚书·大禹谟》“惟精惟一”,《周易》“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孔子“格致诚正,博文约礼”,曾子“忠恕”,子思“尊德性而道问学”,孟子“集义养气,求其放心”等,虽然立论的角度各有不同,但宗旨是一致的。这是为什么?因为“夫道一而已。道同则心同,心同则学同”[2]278。如果有不同,恐怕是邪说。后世学术大患在于无志,因此当今反复强调立志之说,是想表明终身的问学之功在于立志而已。
王阳明形象比喻立志与工夫的关系,立志如同播种,种荑稗得荑稗,种佳谷得佳谷,种什么获得什么,学问的工夫在于立志,犹如栽培耘耨为的是培植其根。这个工夫在《大学》表现为格致,在《论语》表现为博约,在《中庸》表现为慎独,在《孟子》表现为集义,表现虽然有所不同,但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要保存而不忘记。有耕而不获者,但绝没有不耕而获者,下工夫是立志的前提,不下工夫如何谈立志?[2]1599又把立志用功比作种树,种树伊始只有根芽而没有树干,有树干而没有树枝,有树枝而后有树叶,有树叶而后花实。开始栽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不要想到枝、叶、花、果实,空想这些没有任何益处,只要坚持栽培,总会结出枝叶花实[2]16。这说明立志用功要脚踏实地,属于自然而然或者说水到渠成,所注重的是当下的工夫,每一步培植坚实可靠,循序渐近,才能顺理成章地获得结果。
王阳明注意到立志不是件容易的事,作为圣人的孔子自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这里的立即立志,“不逾矩”指志的不逾矩,志岂可小觑?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通则流息,根不植则木枯,命不续则人死,志不立则气昏,因此,君子之学无时无处不以立志为自己的事业。立志要专心致志,所谓目不歪视,耳不他闻,精神心思,凝聚融结,然后此志常立,神气精明,义理昭著,到此时一有私欲立即发觉,自然容不下。接着他进一步提出“责志”:凡有一毫私欲萌发,只要责己志不立,私欲立刻就退出;听到一毫客气(外邪侵入体内)萌动,只要责己志不立,客气立即消除。怠心生而责志即不怠,忽心生而责志即不忽,懆心生而责志即不懆,妒心生而责志即不妒,忿心生而责志即不忿,贪心生而责志即不贪,傲心生而责志即不傲,吝心生而责志即不吝。一言以蔽之,凡事皆在立志责志,无时无刻不在立志责志,责志工夫对于去人欲来说如烈火燎毛,太阳一出而魍魉潜消[2]277。
在与人书信中谈及责志,王阳明认为遭人议论时必须反身痛自切责,自己的志向如果不能坚定则应该激昂奋发。只要知明己之善立己之诚以求尽快足于己,哪有时间顾及别人的讥笑与指责?学者只需责自己的志向是否坚定,如果志向坚定,别人的嘲笑与诋毁不足动摇,反而成为自己砥砺切磋之地[2]292。要责志立诚,凡是语言意思不能完全表达的则多借助于譬喻,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如此才能真正把握。如果一定要拘文泥象,那么虽然是圣人之言也不能没有错,更何况于吾辈学问浮浅,在词意之间肯定存在着各种弊端。当今学者的大患在于不能立恳切之志,因此依我的意思当务之急在于责志立诚,希望以此共勉[2]1044。
立志还需要为己谨独之功,程颐说:“有求为圣人之志,然后可与共学。”(见《近思录·为学》第二)王阳明发挥道:“夫苟有必为圣人之志,然后能加为己谨独之功。能加为己谨独之功,然后于天理人欲之辨日精日密,而于古人论学之得失,孰为支离,孰为空寂,孰为似是而非,孰为似诚而伪,不待辩说而自明。”[2]1074为己谨独之功是实现圣人之志的手段,对于论学也应如此,因为人心中必须要实有诸己,实有诸己而伪者自然不得强入,实有诸己则殊途而同归。不然,终究要忘己逐物,把精力白白浪费在文句之间,并且还自诩已经知晓大道。这不仅有捕风捉影之弊,而且还有执指为月之病,对文句辨析愈多反而离道愈远。因此,他与朋友论学时只举立志以相切砺,至于议论同异姑且置之不辨,不是不想辨而是根本未立,虽然想辨也无从下手。
周道通十分重视日用工夫尤其是立志,认为立志主要体现在与朋友交谈。而独自时如何培养志?以此请教王阳明。王阳明肯定以立志为日用工夫,并说:“此段足验道通日用工夫所得,工夫大略亦只是如此用,只要无间断,到得纯熟后,意思又自不同矣。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所谓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今好色之人未尝病于困忘,只是一真切耳。自家痛痒,自家须会知得,自家须会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须不能不搔摩得。佛家谓之‘方便法门’,须是自家调停斟酌,他人总难与力,亦更无别法可设也。”[2]63日用工夫在于不间断无时不下,纯熟以后自然体会有所不同。这里的关键在于立志,立志有头脑指有方向性,立志也要真切,出现困惑与遗忘的毛病在于立志还不够真诚切实。立志要真诚切实,凡所寓目措身等皆在培养其志,不间断立志必有所得而无困忘之病。“自家”“自知”强调立志在于自己而非靠别人,立志是自己的事,靠的是自己的主动性,没有朋友也可以立志,工夫属自修,自己调停斟酌,自己帮助自己。佛家所讲的“方便法门”指随机度人,其前提应该首先是度己。
王阳明与薛侃对话谈及持志,说:“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岂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2]14薛侃问:“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说闲语,管闲事?”王阳明说:“初学工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着落。若只死死守着,恐于工夫上又发病。”[2]29“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出自《孟子·告子上》。朱熹注此章曰:“孔子言心,操之则在此,舍之则失去,其出入无定时,亦无定处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测,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难。”[1]402王阳明注此提出持志,守持自己的心志就如同心痛一样,念念之间一心都专注在痛楚之上,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说闲话、管闲事呢?也要知晓孟子讲的把持住心,否则将导致不确定无方向。心之神明原本如此,即心不受任何外在影响,无时无向指无执无滞,达到至诚无息的境界,持志与心应该是统一的。工夫也应从此下才有着落,如果一味死守,这是工夫上的弊病。当初有人嫌《传习录》持志如心痛一段太执着,他则认为,不要这么说,放此药在,有用得时,所谓未雨绸缪[2]1681。
立志才能分辨义利,王阳明认为,数年切磋立志只是辨义与利,如果在这方面没有尽力,那么平日所讲的都是些空话,平日所见的也都不是实得,不可不猛省[2]183。立志也要警戒,王阳明反复以“警戒”二字叮咛朋友弟子,以为朋友大患在于不能立志,由此因循懈弛,散漫度日。如立志必须警戒,警戒为立志的辅助,能警戒,学问思辨之功、切磋琢磨之益将日新又新,沛然莫之能御[2]291。王艮听到弟子歌“道在险夷随地乐”一句,便说这是王阳明处境艰险时说过的话,学者不知用自己的想法去揣度别人的心志,有的可能安于险而失其身[2]1681。前人说:“做官夺人志。”如果致知之功不间断就没有夺志之患[2]1823。
应元忠的弟子周莹不远千里向王阳明请益,两人有如下一段对话。王问:你是从应元忠那里来吗?周答:是。王问:应元忠如何教你?周:没有别的,只是每天教我希圣希贤之学,毋溺于流俗。又转述应元忠的话:这也是我曾经就正于王阳明先生的,你若不信我的话何不亲自去见他?所以我不远千里来拜谒。王问:你来了还有所不信吗?周回答:信了。王问:信了为什么还要来?周回答:尚未找到方法。王说:你已经得到方法,不必再跟着我。周悚然片刻说:希望您看在应元忠的份上指点我。王说:你已经得到方法,不必再跟着我。周悚然而起,茫然片刻说:我愚钝,不得其方法。您不要戏弄我,望赐教!王说:你从永康来路程有多远?周说:有千里之遥。王说:这么远是乘船来的吗?周说:乘舟之后又陆行。王说:辛苦,正当六月天气很热吗?周说:途中天气非常热。王说:艰难,有资粮和童仆吗?周说:中途仆人生病,不得已弃货而行。王说:更为艰难,你来此既远且艰难如此,为何不返回,何必要来呢?恐怕没有比你强的。周说:我来拜见您,尽管路途劳苦艰难,但内心真诚且非常高兴,难道因为困难而折返,又等待人强于我?王说:这是我所说的你已经得到的方法,你的志向是想要进入我的门下,于是至于我门而不借助于他人。你有志于圣贤之学,有不至于圣贤者吗?借助于他人吗?你舍舟从陆,捐仆货粮,冒着毒暑而来,还需要从我受之方法吗?周跃然起拜说:这是命中的方法,我由于其方而迷于其说,必定要听您的话而后高兴。王说:你没有看过烧石以求灰的人吗?火力具足后,石得水遂化。你回去,你的老师应元忠加足其火力,我将储担石之水以等待你再见[2]249-250。周莹远道而来且经历路途上的种种艰难,这一过程本身就说明其志向坚定,或者说只有志向坚定才能排除各种困难永往直前。王阳明对此予以积极的肯定,同时也反映了他教人在于随事指点或者说有针对性而非空洞说教的特点。
王阳明强调立志,以为立志是做人为学的根本与前提,是本原之学,同时便是一种工夫。他在与人书信、教导弟子中屡次申明立志的重要性,并把它与去人欲存天理、良知等联系在一起,把立志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立志可被视为良知的自觉,是人们精神力量的源泉,也是理想人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