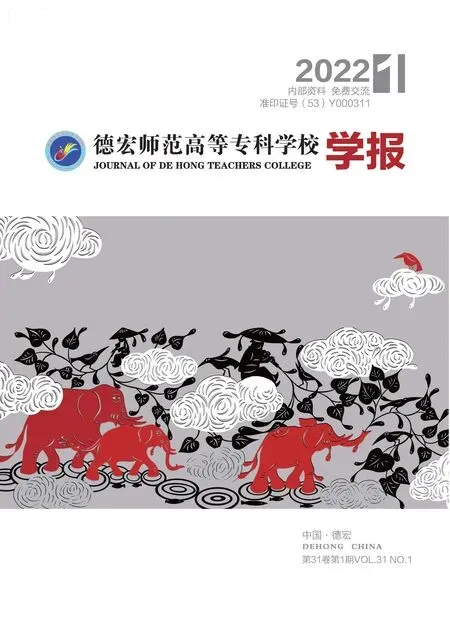论金沙江两岸“纳”与“纳西”族群的文化交织
——以宜底为例
何林富
(云南省民语委办公室,云南 昆明,650500)
自称为“纳”与“纳西”的这两个族群,都具有“纳人”之意,在历史上具有“摩沙”“麽梭”“摩梭”等他称,新中国成立后,民族识别时居住在云南省的“纳”“纳西”,族名都统一称为纳西族。在丽江市境内以金沙江为界,“纳西”族群主要居住在金沙江以西的玉龙县、古城区等地;“纳”族群主要聚居在金沙江以东的宁蒗县。新中国成立后,“纳”族群一直坚持呼吁要求摩梭人作为本民族族称,为此国家虽未将摩梭人单独列为一个单一民族,但云南省人大常委会于1990年4月召开的七届十一次会议上同意在云南省宁蒗县境内的“纳”族群称为“摩梭人”,允许宁蒗县境内摩梭人身份证上用“摩梭人”作为本人的民族身份。而且,在历史上“纳西”族群聚居地基本都是在木氏土司的势力范围内,“纳”族群则是在永宁阿氏土司和蒗蕖阿氏土司的管辖地。因此,金沙江是两个土司之间的天然屏障,也是两个族群间的文化交界点,“纳”和“纳西”之间的历史和文化在金沙江一线交织在一起,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特点,其中宁蒗县翠玉乡的宜底是个典型例子。
一、宜底的基本概况
宜底,位于云南省宁蒗县翠玉乡金沙江边,北接宁蒗县拉伯乡,西、南与丽江玉龙县宝山乡隔江相望,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峡谷小坝子,外来人员亲切的称之为“神仙居住的地方”。历史上的宜底是个人口稀少、土地肥沃的地方。直到解放前还有“ȵi³³di³¹so³³tshɿ⁵⁵ʐʅ³¹”(宜底三十家)的说法,是当时永宁土司的一个“小粮仓”。这一点从“宜底”这个名称的由来便知,宜底即摩梭语“ȵi³³di³¹”,“ȵi³³”是“二”的意思,“di³¹”为“地方”,连起来意思就是“两个地方”。村里普遍流传着这么一个传说:有一次永宁土司派人来到其管辖的领地内收粮食,收完后进行数量对比后发现,“宜底”这个地方收上来的粮食相当于其他地方的两倍,于是土司说“宜底”这个地方,一个相当于其他地方的两个,从此就称为“宜底”,一直沿用至今。
宜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宜底指行政意义上的宜底村委会,包括宜底大村、路跨、东山坝、牛克席、阿次落、余落、格忠、肯定石、曲依普米村、曲依大村、下岩科等11个自然村,其中宜底大村、路跨2个为摩梭村,东山坝、牛克席2个为傈僳村,阿次落、余落、曲依普米村3个为普米村,格忠、肯定石、曲依大村、下岩科4个为纳西村,人口少的一个村只有10余户,人口多的一个村达近100户。狭义的宜底只包括大村、路跨两个自然村。本文中宜底指狭义的概念,仅包括大村、路跨两个摩梭村寨。两个村寨现有151户,总人数684人。其中大村总共有95户,433人,具体为摩梭77户,356人,其他民族18户,分别为纳西5户,普米2户,傈僳4户,汉族7户,共77人。路跨总共是56户,251人,具体为摩梭48户, 210人,其他民族有8户,分别为纳西2户,藏族2户,普米2户,汉族2户,共41人。因此,宜底两个村有摩梭125户,566人,其他民族共有26户,118人。摩梭户数及人口比例分别占82.8%,82.7%[1](p2)。
二、历史的溯源:宜底地区摩梭人的地缘政治历史
宜底地区,除了居住有摩梭人外,历史上还有几户刘姓、宋姓、康姓、洛姓、宗姓等汉族,但通过调查了解,基本都是从外地流浪或逃难到此。因此,从现有的资料和可考证的相关遗址而言,最早来到宜底地区的是摩梭人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最早来宜底的摩梭人是从现今云南省宁蒗县永宁地区、四川省盐源县一带迁徙而来。这一点从宜底 “嘎萨”(ɡɑ³¹sɑ⁵⁵)①家族、“恩雅”(ɛ³³jɤ³³)家族至今还保留着的送骨灰习俗中可以得到证实。当时宜底摩梭先民们来到宜底后,因时刻怀念故乡,于是“嘎萨”家族的老人去世时,把骨灰送到一座叫“瓦次瓦多”(ŋuɑ⁵⁵ʦhɿ¹³ŋuɑ³¹to⁵⁵)的主峰上,那里正好能看到永宁格姆神山的顶峰,以此表达对故乡的思念之情。据阿彦直②介绍:最初葬骨灰的主峰并不是“瓦次瓦多”,而是比它更高的“宜底怎尔普”(ȵi³³di³¹dzɛ³³ər³¹phə³¹),现为翠玉白岩子,海拔4000多米,可以看到永宁整个格姆山。随着时间的推移,宜底阿姓家族的势力逐渐削弱,家族成员也逐渐平民化,送骨灰也越来越艰难,据传说有一次送骨灰上山时,拴在山下的马被老虎吃了,人们不得不迁移放骨灰的地点,即迁到距下洋监槽1500米左右的“瓦次瓦多”主峰上,那里还能看到格姆山的顶峰。从此以后,阿姓家族的后代,一直以来将正常死亡人的骨灰送到那里,代代不间断,一直传承到今天,称为“嘎萨窝基克”(ɡɑ³¹sɑ⁵⁵o³³ʨi³³khər⁵⁵),意为“嘎萨家族寄放骨灰的地方”。而关于“恩雅”家族送骨灰的习俗,据笔者奶奶恩雅·青玛③讲述:“恩雅”家族最初是把骨灰送到“火地”(xo³¹di³¹)的,即现四川省盐源县左所一带,后来途中经常遭遇土匪抢劫,每一次送骨灰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因此,简化为在永宁开基桥边举行一个“披开”(phi³¹khɛ¹³)仪式,即给祖先敬饭,再后来,家族势力衰落,再加途中土匪猖獗,仅仅是在村口通往永宁和盐源的路边念诵“热布”经,意为已给祖先敬过饭,不再去永宁、盐源。此仪式至今还保留着。
宜底地区摩梭人的历史,结合宜底“畏吾”家族的家谱和相关史书,可以追溯到永宁土司牙玛阿时代,至少已有三百多年。根据“畏吾”(uɛ³¹u³³)家族的长辈格若尼玛④讲述:牙玛阿世袭土司职位后便派亲弟弟牙玛萨到现在的宜底地区驻防,镇守江外码头,以防丽江木氏土司势力跨过金沙江来到永宁土司辖区,后来牙玛阿一直没有招弟弟回永宁,所以牙玛萨及其后代留在了宜底,即现今“畏吾”家族的祖先,他们也就是最早来宜底的摩梭人。直到今天,“畏吾”家族以及宜底其他“来地”“啊昂”“衣瓜”“啊克”等大部分阿姓家族敬锅庄时都会念到牙玛萨和牙玛阿。而关于牙玛阿在相关历史书籍中有明确记载,在郭大烈、和志武编撰的《纳西族史》写到“阿镇麒即牙玛阿,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仍任土知府”[2](p435),《中国地方志集成康熙云南通志(二)永宁府》也载:“本朝平滇,镇麒投诚,授世职”,因此,以阿镇麒继位的时间1659年为准,则可推断出宜底的摩梭人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畏吾”家族的祖先迁徙到宜底地区,当时是一次带有地方土司政治目的的迁移。因为江外码头是当时永宁阿氏土司与丽江木氏土司交往的一条重要交通要道。金沙江是永宁土司和丽江木氏土司之间的一道天然界限。虽然都是归于中央王朝的版图之内,但地方土司势力的争夺,木氏和永宁阿氏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由于木氏土司的势力强盛,经常越过金沙江涉足到永宁阿氏土司的势力范围内。因此,宜底对永宁阿氏土司来说极为重要,所以牙玛阿才派亲弟弟牙玛萨镇守宜底一带。然而,木氏土司的势力还是时常到达永宁土司的辖区,主要是在今天宁蒗县翠玉、拉伯一带,至今翠玉乡宜底村委会有以曲依自然村为中心的四个纳西族村寨,大部分为姓木与姓和,当时都从木氏土司管辖下的丽江纳西族地区迁徙而来。因此宜底地区曾有一种说法叫“宜底嘎萨,曲依木瓜”,而嘎萨、木瓜分别是永宁阿氏土司和丽江木氏土司对辖区内的基层组织,可见宜底和曲依成为永宁阿氏土司与丽江木氏土司的势力分水岭。“宜底嘎萨,曲依木瓜”的历史格局深刻影响了宜底摩梭文化的多元性特点。
三、文化的交融:宜底地区摩梭人的文化多元性
(一)喇嘛、达巴、东巴缺一不可的丧葬习俗
宜底地区以前除了信奉达巴教、喇嘛教之外,还信奉东巴教,这一现象在其他摩梭聚居区是很少见的。主要体现在丧葬仪式中,宜底传统的丧葬仪式,喇嘛、达巴、东巴是缺一不可的。仪式中他们各自的诵经、仪式并不冲突。达巴主要是主持“热布”“日吾”“摆披”“日处”等仪式,活动地点主要是在家屋里,在死者的灵柩前,以及村口家族送魂的固定地点,达巴是人与神、人与鬼的中介,其主要职责为第一时间把死者的灵魂送往祖先居住的地方,丧事期间负责给死者敬饭,并托死者将各家族带来的祭品带给“斯布阿纳瓦”⑤的祖先们,丧事期间深夜给死者诵安魂经,并出殡早晨宣布生与死的区别。东巴负责葬礼期间吹奏唢呐,以及在院子中间主持“软昌”仪式,负责安慰死者的灵魂骑上马,便于回到祖先居住的地方,但东巴不送魂。喇嘛则主持念诵“鲁古”“达久”“玛尼古”以及火化等法事,活动地点主要是在经堂、家屋里及火葬地,负责把死者的灵魂送到极乐世界,同时为死者赎罪,为生者祈福,在火葬场负责火化死者遗体。在丧葬仪式中,达巴、喇嘛、东巴三种宗教各取所长、互不冲突。
(二)父系为主、母系为辅的双系家庭婚姻形态
宜底地区的摩梭到宜底定居后,与具有浓厚母系文化的永宁在地域上形成隔离。同时宜底地区土地肥沃,有了一定的财富积累,并且“财富的积累开始向社会的男性成员手里集中后私有财富增多,诱使一个男性不仅供养本氏族的成员,即外甥们,而且也开始娶妻供养外氏族的成员,即他自己的儿女们。”[3](p95)父系地位的逐渐突出,“有的甚至娶两个老婆,以大老婆、小老婆区分,以有能力者掌管着家庭内务。”[3](p95),再加上受土司体制和周边其他民族的影响,社会家庭逐渐形成以父系大家庭为主的婚姻形态。同时,也有部分的母系文化余存,家庭中的女性可以选择“走婚”的婚姻方式,终生不出嫁,但有固定的伴侣,同样,家里男性多的家庭,个别男性也可以选择终生不娶妻,选择“走婚”的婚姻生活。谢苗诺夫曾说“氏族相继关系的更替往往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在母系氏族继续存在的同时又出现了父系氏族,而父系氏族则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意义,并把原始的母系氏族排挤到次要地位上。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发现社会上同时存在着两种相继关系——母系的和父系的,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存在着双重的相继关系”[4](p250-251)。因此,以前宜底地区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社会家庭以父系大家庭为主,同时存在少部分母系血缘家庭,即以父系为主、母系为辅的双系并存家庭形态在宜底地区延续了漫长的历程,直到民主改革(1956年)后才分成若干父系小家庭和少量的母系单亲小家庭。当然,宜底地区至今也保留着一些母系大家庭的风俗,比如存在这样一个普遍现象:若男女出现离婚的情况,女方可以回到自己的母亲家,如果已有孩子,孩子往往归为女方,一般由舅舅家帮忙抚养长大,即便女子改嫁,孩子一般也留在舅舅家,成为舅舅家的一员;当然,女子也可以不改嫁而选择另立门户,其子女沿用母亲家族的姓氏,参加母亲家族所有的社会、宗教礼仪活动,完全得到本家族其他成员的认可。
(三)相对开放的通婚习俗
因多民族聚居的生存环境,以及宜底地区摩梭人不分家的社会习俗,历史上与周边纳西、普米、傈僳等少数民族的通婚是很频繁的。尤其是与曲依、下岩科等一带金沙江边⑥纳西族通婚比例很高,至今很多流传在宜底的民间传说以及真人故事都与江边纳西族有关,比如“恩雅”家族的达巴为什么衰落了⑦?“啊昂”家族是从哪一代开始兴旺起来的⑧等等故事。2019年笔者调查发现,宜底大村、路跨两个村有37个家庭娶了江边纳西族姑娘⑨。可见,从历史上到现在,宜底地区摩梭人与江边纳西族的通婚频率是极高的。
(四)贯穿纳西语东西方言的语言特点
金沙江不仅是“纳”和“纳西”的文化习俗交界,也是语言的交界线,一直以来,学界以金沙江为界,将纳西语分为东部方言和西部方言,以丽江市玉龙县和古城区为主的纳西族使用的语言为西部方言,以宁蒗县摩梭人使用的语言为东部方言,两种方言差异较大,彼此沟通困难。宜底地区摩梭语属于东部方言,但宜底地区摩梭人历史上长期居住在永宁和丽江的交界地带,受江边纳西族的影响较大,形成独特的江边方言,构成了宜底地区摩梭语的多元化。具体表现为宜底地区摩梭人能听懂也能使用永宁地区摩梭话,而永宁地区摩梭人听宜底地区的摩梭语存在一定的障碍;宜底地区摩梭人能听懂能使用江边的纳西话,当然江边纳西人也能听懂,甚至也能使用宜底地区的摩梭话,只是在交流过程中都不太习惯使用对方的语言,各说各的方言却不存在交流的障碍。来自宜底的摩梭人在丽江生活多年后,能完全听懂西部方言,甚至能够顺畅交流。
可见,宜底位于“纳”和“纳西”两个族群的边界,也是历史上丽江木氏土司和永宁阿氏土司的势力交界点,从丧葬、婚俗、家庭形态、语言特点等各方面都充分体现了双方文化的交织和融合,形成具有区域性、多元性的金沙江边摩梭文化特点。
注释:
①嘎萨(ɡɑ³¹sɑ⁵⁵)应类似于以前西藏的“噶厦”,是一种土司制度下的基层组织。可能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当时阿姓家族来到宜底后,宜底最早的“确吉的来寺”(文革中被毁,2002年开始重建,2007年正是开光)也随后建立,体现一种政教合一的基层管理形态。后来,在宜底掌权的阿姓家族习惯上都称作“ɡɑ³¹sɑ⁵⁵”家族。今天宜底“畏吾”(uɛ³¹u⁵⁵)、“来地”(lɛ³³di³¹)等家族都习惯称“嘎萨”家族。
②阿彦直:家名:维米·鲁斤,宜底完小退休教师,对宜底历史文化有较深了解。
③恩雅·青玛:女,属羊,2019年已逝。
④格若尼玛:汉名阿久山,男,现年68岁,能颂“锅庄经”,对宜底摩梭传统文化、习俗掌握较深。调查时间:2020年1月23日。
⑤斯布阿纳瓦:祖先居住的地方。摩梭人认为人死后灵魂会回到祖先居住的“斯布阿纳瓦”。
⑥曲依一带金沙江边:以下简称“江边”。
⑦据说“恩雅”家族还住在“雅格罗”(位于宜底坝子北面)的时候,一个达巴(现已记不清楚具体是哪个达巴)娶了一个下岩科的纳西族媳妇。有一天,全家人外出干活,没人在家里带孩子,于是达巴就变出一条黑色的蟒蛇来照顾孩子,妻子临时回家,看到自己的孩子被蛇缠着,惊慌之下,用裙子把蛇给拍死了。从此,“恩雅”家族达巴的神威失去大半,逐渐衰落。(讲述者:恩雅·恩奇基,2011年8月)
⑧据说“啊昂”家族之前很穷,直到“戈登勒”一代,娶了勤奋的一个下岩科纳西族姑娘,从此“啊昂”家族才富起来,一度成为宜底的大富人家。(讲述者为笔者外婆啊昂·青玛,现已逝。)
⑨此数据笔者于2019年调查所得。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37个家庭,指的是常住宜底大村和路跨,户口在宜底并且还在世的人员情况,已过世或者嫁到宜底但在外工作或户口已在外地的不计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