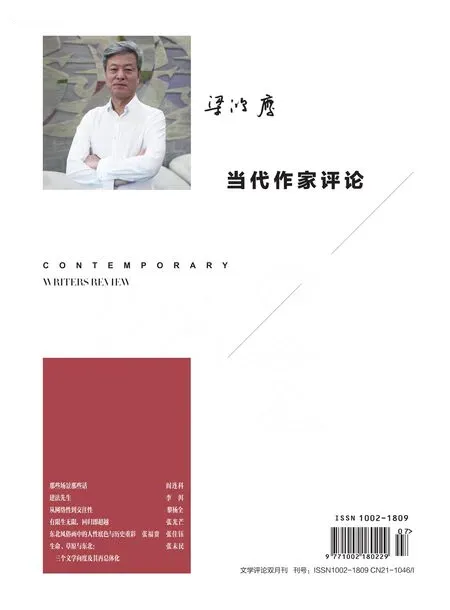又见菖蒲,再忆建法
王 尧
我多次想象,如果建法身体恢复正常,我们之间会深入谈些什么?
我知道这是不可能了。但我和连科兄觉得还是要说出我们的建议,我们分别几次电话嫂子和建法,那时建法还能简单交流。我们建议他去做手术,并且认为奇迹可能出现。我们俩固执地轮流劝说,固执的建法并不接我们的话。建法可能有点嫌烦了,有一阵子不搭理我们。建法固执地对别人,也固执地对自己。这样的性格可能是缺点,但建法不伪饰自己。
戊戌年的春或秋,我和连科、季进、杨慧仪几位约好去沈阳看建法。饭后在建法的书房里,记不清是高晖还是刘庆建议,我们合作写一幅字留作纪念。诸位客气,我先在纸上落墨:文学建法者。建法坐在轮椅上,微笑着看我们舞文弄墨。好像是刘庆还是高晖,扶着建法用毛笔写了“建法”。
记得那天我们在议论文学界的种种现象,建法一直静静听着,他应该想说什么,但说不出来。建法在手机上先是写了“王尧不仅”四个字,我们都不知道他接下来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建法又在手机上写了“莫言”两个字。已经无法言语的建法仍然心在文学界,直到完全不能动弹之后,建法才放弃了文学年选的编选工作。这让我时常感慨,建法用病躯诠释了何谓文学信仰之坚定。
我后来一直想着“王尧不仅”后面可能出现的文字。建法一直对我怀有期待,总觉得如果我不旁骛,应该能够写出更好的文章。我和建法开始熟悉时,自己的人生道路也正面临着选择。他看我整天疲惫不堪,便说:你太想要周到,其实是做不到的。他再进一步说,即使做到了,许多事也没有价值。我去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半年,建法邀约了几个朋友在杭州为我送行。他后来在写我的文章中,特地说了我旁骛过多不能专心学术的问题。就像我们平时交流一样,建法在文章中毫不掩饰对我的批评和期待。我曾经遭遇到一些困顿和挫折,虽然问题并不是由自己引起的,心境难免受影响。在这种情形下,建法只是劝我专心写作,有时候还给我命题作文。我和建法几乎是两种不同的性格,我们相同的是在原则问题上从不动摇。
建法就是这样,如果他认为你是一个可以造就的批评家,或者是一位值得评论的作家,他就不遗余力关注你,为你创造条件。这个方式也引起一些非议,但建法坚定不移。他觉得一个杂志的学术积累,应当是具有代表性的批评家在杂志不断发表重要作品的过程。我以前很少写即时性的作家作品论,和建法联合主持“小说家讲坛”之后,越来越多地介入文学批评一线。建法知道我对作家作品论比较谨慎,很少约我写即时性的评论,他觉得我的长处是文学史专题研究。一次他问我最近在写什么,我说在写“文革”关于“五四”和“现代文艺”的叙述与阐释。他说这个研究很重要,写好给他。我有点犹豫,这篇文章涉及思想史的许多问题,我感觉自己短时间很难处理好。此后建法不时催促,生怕这篇稿子给了别的杂志。他几乎隔天电话询问进展。这篇长达6万字的文章发表后,建法又约学者朋友写了对话式的文章呼应。我的关于“文革”时期文学与思想文化的论文基本集中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
我与建法的合作,深刻影响了我的学术路径和后来所谓的跨界写作。在主持“小说家讲坛”之后,我坚定了文学口述史的尝试。在口述史的访谈过程中,建法介绍了许多他熟悉的作家、编辑和文学活动家,我才有了走万里路的可能。我做口述史的那张“文学地图”是在建法不断填充后形成的。《当代作家评论》率先发表了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系列,尽管这部口述史的出版颇经周折,但我一直庆幸在建法的帮助下,我得以完成自己想做的事。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小说家讲坛”和“新人文对话录”丛书,我和一些作家朋友有比较多的交往,我的作家作品论并没有因此增加,反而减少了。曾经有记者问我,和作家朋友交往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说,这有助于知人论世。现在仍然活跃着的那些当代优秀作家,他们阅读广泛,几乎都是饱学之士,可以说在阅读经验、审美判断等方面比批评家更具优势。他们是在创作中融合文本内外的,批评家则在解释文本中连接文本与世界。在谈论其他作家作品时,小说家会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理解,在这个方面,批评家相对缺少自己的语言。在主持“小说家讲坛”时,我已经开始写作《民谣》,然后断断续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作家朋友激发了我写作散文和小说的激情。《民谣》在《收获》发表后,我给嫂子寄了一本杂志。嫂子微信说,她读了几段给建法听,建法知道王尧完成了小说。如果建法还能打电话,他读到小说时一定会在第一时间电话我。我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我的很多同辈批评家都得到建法兄的指点和帮助,其中的多数批评家朋友可能在青年时期就和建法相遇了。我第一次参加建法主持的会议是在大连,那次见到了很多只熟悉名字但缘悭一面的青年批评家朋友。这次会议之后,我融入批评界。现在这些朋友中的大多数都从青年到中年,从中年迈向老年。《当代作家评论》不是同人刊物,即便是,集结在四周的朋友也会因各种原因聚散。在建法主持《当代作家评论》的后期,建法对自己此后可能的落寞已经有些思想准备。
差不多在这个阶段,在常熟理工学院担任领导的朋友告诉我他们接了一份刊物,准备办成人文社科综合性刊物,让我推荐执行主编人选,我便推荐了建法。这位朋友觉得建法很合适,我说你们只要充分授权,不加太多干预,建法一定能办好杂志。果然,在主编《当代作家评论》之余,建法迅速让《东吴学术》风生水起。退休以后,建法又主持了一段时间《东吴学术》,因病情加重,主动辞去了执行主编职务。此后,他四处求医和静养,去过徐州,去过昆明,去过南宁。我和季进飞往南宁,建法在嫂子搀扶下还能走路,见到我们特别开心,但语言表达已经没有那么连贯。第二天和他告别时,建法站着和我们挥手。又过了一年,我再见到建法时,他已经坐在轮椅上。建法站不起来了。接下来的几年是疫情,我们几个相约几次往沈阳,都被神出鬼没的疫情打断。学昕在大连,时常去探视建法,是建法最温暖的朋友之一,他不时告知我建法的最新状况。《扬子江文学评论》研究建法的那组文章发出来以后,不少朋友私信问我建法的情况。我电话嫂子,我们圈子都称呼建法爱人为嫂子,我问嫂子建法状况如何,嫂子说,昨天给他读了你们几位的文章,建法流泪了。这几年建法不能说话,但思维清楚。好像只有嫂子能读懂他的神态,知道他是不是开心。
大连春天的那次会议让我耳目一新。会议开始时没有领导致辞,也没有协办单位发言,开始便是与会批评家发言。这就是我们后来经常说到的纯学术会议。当时我还在行政岗位上,知晓这样办会议是不容易的。会议间隙,建法告诉我,他一直这样办会,不请领导讲话。企业家朋友赞助的会议,建法也不请这些朋友讲话。建法如此不落俗套,确实令人钦佩。但我有时换一个角度想,单位领导能如此正确对待,也显示了单位对建法的宽容。建法一直在相对自由的氛围中办刊,这是成功办刊的原因之一。建法任上最后一次在沈阳办会,是我主持的。开场白中,我特意说了我的这些想法。我说:作为《当代作家评论》的作者,我体会到了杂志和单位的新型关系,别人认为建法比较任性,其实建法简单,他认为只有办好刊物,才能不辜负单位,建法做到了;我要代表批评家朋友感谢辽宁省作协对建法的理解和支持。散会后,建法憨憨地笑着:你代表了我的心意。
作为文学编辑家,建法的重要贡献是创造了杂志介入文学批评生产的一种方式。建法不是单一地约稿、审稿和编稿,他始终处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前沿,这是他背着行囊到处游走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建法办研讨会,编辑年选,出版批评文选系列,包括作家作品研究专书,自己也以批评家的身份撰写文章。可以这样说,建法改变了编辑家的单一身份,他让一份杂志以多样化的学术方式与创作和研究保持了密切联系。《当代作家评论》现在仍然延续着建法创造的这一风格。
建法一直活在他那个文学世界里,这几年世界变化之大与他已经没有关系。他痛苦,但他活得越来越简单了。建法走了,也带走了他的文学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