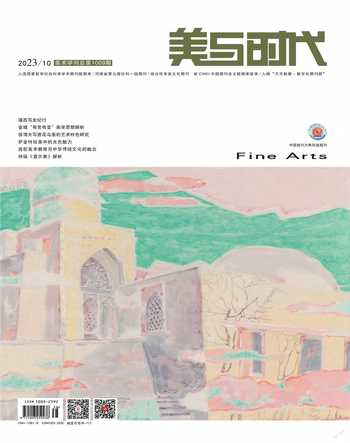中西绘画构图中的空间与叙事

摘 要:中西方绘画由于对客观世界的观看、感知与理解方式不同,所以在创作思维和表达方式上存在不同,构图中的空间关系和叙事关系处理也不尽相同。从西方绘画构图中的空间与叙事模式入手,通过西方构图模式的转向,以中国古人注重内在精神修养的“中和”思想的形成以及中国绘画构图中的空间与叙事这两方面为中心展开论述。
关键词:中西绘画;空间;叙事;“中和”思想
一、西方绘画构图中的空间与叙事
西方艺术随着文艺复兴时期透视学、解剖学等自然学科的发展,逐渐在绘画中形成了对于客观事物的一种真实的再现与模仿。其再现理念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的“模仿说”及“理念说”。柏拉图的“三张床理论”认为,艺术作品的床是对工匠所做的床的模仿,工匠做的床又是对理念的“床”的模仿,所以绘画的床是理念“床”的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囿于這种模仿或再现思维,西方绘画自文艺复兴始一直在试图再现视觉上的一种现实,或者说,对于人们正常视觉所看到和显现的视觉空间进行再现。如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实际上是模仿。达·芬奇也在《论绘画》中提出了“镜子说”和“第二自然”的观点,同样认为绘画是对客观世界最真实最本质的模仿或再现。这种再现思维在西方绘画中逐渐奠定了中心透视或焦点透视的科学透视原理。
根据焦点透视理论,人们的视平线随着空间的移动和推进最终消失在一个点上。拉斐尔的作品《雅典学院》就是透视学应用的典范之一,可以看到艺术家试图在一个有限的二维画面空间来营造一个符合视觉规律的三维空间,并在画面中心的两位古希腊先贤的位置设置了画面视线的消失点,通过地面、拱门的精准透视再现了古希腊先贤们进行哲学讨论的场景空间。马萨乔的作品《三位一体》也堪称透视学应用的典范,马萨乔在画面中也试图在有限的画幅中为观者营造一种三层视觉空间的错觉,当观者在观看这幅壁画作品时,首先看到的是位于拱门前的两位正在祈祷的人,随着视线的推进,在拱门内可以看到两位修女和钉在十字架上的圣子,圣子背后的空间还站立着圣父。作者通过阶梯、台面、柱头以及拱门的透视,在视觉上形成逐渐深入的三层空间,试图还原或再现“三位一体”的经典图式。
西方绘画焦点透视所带来的视觉效果决定了画家在描绘一幅作品时,只能描绘一个特定的瞬间或者整个叙事情节的一个节点。这被称为“富于孕育性的顷刻”或单一场景叙事模式。此概念由莱辛在其著作《拉奥孔》中提出。莱辛认为“顷刻”往往会避开叙事情节的“顶点”,以暗示事件发生的前因与后果,留给观众遐想空间,让观者在意识中完成一个叙述过程。这在叙事题材或历史题材绘画作品中屡见不鲜。例如,布留洛夫的作品《庞贝城的末日》描绘了灾难来临前人们仓皇失措的场景,留给观众对于灾难发生的一个想象空间;马特伊科的作品《格伦瓦尔德之战》也描绘了联军即将击败条顿骑士团获取胜利的瞬间;陈逸飞、魏景山的《攻占总统府》通过在总统府上插上五星红旗代表着解放南京,同时具有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隐喻。
二、西方绘画空间与叙事模式的转向
西方绘画发展到了19世纪,随着东西方贸易和文化的不断交融,西方艺术开始注意到了东方艺术中独特的风格与绘画图式。例如,莫奈的作品《穿和服的卡米尔》、惠斯勒的《来自瓷器国的公主》和马奈的《左拉肖像》等作品都试图借鉴和融入一些东方的浮世绘风格,但这一时期对于日本浮世绘风格的借鉴仍停留在表现形式上。
到了20世纪,在西方艺术中涌现了较多关于东方风格与图式的借鉴与应用。马克·夏加尔的作品《我与村庄》出现了区别于以往西方绘画作品中单一场景叙事和焦点透视的一些视觉要素,画面中不仅直观地表现了两副对视状态的面部轮廓,还以多线叙事的手法刻画了正在挤牛奶、扛着镰刀去干农活的农夫等,这些叙事情节或叙事要素展现了作者与村庄之间深厚的情感羁绊。
三、中国绘画构图中的空间与叙事
在莫伊谢延科的作品内容中,我们看到近代西方绘画在画面的空间表达和叙事模式上开始寻求一种多样的表现方式,而对于中国绘画来讲,这种绘画的叙事模式与空间处理方式其实很早就出现了。
首先,中国传统绘画对空间的认知方式区别于西方的焦点透视,从大量古代的历史遗存以及中国传统绘画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人在描绘客观对象时往往不会直观地描绘视觉所呈现的空间,而是采用一个倾向于“上帝视角”或者是统筹全局的观看方式,仿佛置身于思维或者意识上的高地。这种独特的绘画观察与感知方式与古人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宇宙心灵”有关。“宇宙心灵”的内涵源于汉代王充和阮籍的“元气自然论”学说。“元气自然论”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气”,“气”是艺术家的创造力与生命力,亦是宇宙元气与艺术家元气相结合的产物。同理,中国古人讲的“天人合一”与“以大观小”的美学思想亦是如此,“以大观小”中的“观”也是一种仰观俯察、远近游目的认知和感知方法。古人认为,通过“宇宙心灵”或“以大观小”的方式可以达到对于宇宙本原或本体“道”和“气”的观照。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宇宙元气与艺术家元气相结合呢?在艺术创作中需要一个“思”的阶段。荆浩在《笔法记》提及“思者,删拨大要,凝想形物”,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也提到“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物我两忘”指的就是主客体融合无间,也就是郭熙的“身即山川而取之”和石涛的“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的状态。“离形去智”说的是排除主观欲念,例如,老子“致虚极,守静笃”、庄子“心斋”与“坐忘”、宗炳“澄怀观道”说的都是一种思维上虚静空明的境界。只有达到上述阶段,才能在绘画过程中达到“得于心,应于手”“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神者,亡有所为,任运成象”“万象必尽,神人假手,穷极造化也”的境界,达到绘画创作的高度自由。
“宇宙心灵”的概念其实在古代诗文中也多有体现,如陆九渊的“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王维的“山河天眼里,世界身法中”,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也提及“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仰观”和“俯察”则表明了中国古人独有的一种宏观的观察视角,这种视角在绘画中逐渐表现为散点透视的空间模式。散点透视也叫多点透视,表现为视线不局限于一个固定的位置,处在不断的移动和转换中。例如,在和林格尔东汉墓室壁画的《宁城图》中,通过散点透视的方式共时空地记述了墓主生前诸多来宾以不同方式前来拜谒的场景。敦煌莫高窟第61窟的《五台山图》也堪称散点透视的典范,画面中不仅以地标的形式精确地再现了五台山全貌,也记录了关于五台山的诸多佛教故事,完整地交代了五台山的叙事与场景空间。
同时,散点透视的空间处理方式决定了中国绘画在叙事上不会描述一个固定的情节或故事。在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文物宴乐铜壶的局部纹样图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艺术工作者将“弋射”的情节完整地描绘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通过拉弓引箭—射中—拖拽三个叙事过程完整地交代了“弋射”的动作过程。这种叙事模式被称为线性的、共时空的叙事,也叫“综合性叙事”,其含义是把不同时间点上的场景与要素并置在同一画面中,使画面的叙事更为完整。敦煌莫高窟第254窟的《舍身饲虎图》同样也是艺术典型,在同一面墙壁(空间组织)中,同时出现了入山见饿虎、投身跳崖、以身饲虎、利木刺身、再次投身跳崖、再次饲虎、虎啖萨埵、找见残骸、抱尸痛哭、起塔供养共十个情节与叙事,详尽地记述了萨埵太子舍身饲虎的全部過程。
四、中国绘画中的“中和”思想
通过上述对中西方绘画构图中叙事和空间问题的简要分析之后,有必要对中国绘画图式形成的原因进行讨论和阐释。
与西方注重“视”“听”和事物外在的感知方式不同,中国以“味”“触”为基础的感知方式和审美意识决定了感知主体、感知方式、感知对象之间存在内在的融为一体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古人面对客观事物不会像西方那样注重再现和事物外在表象的部分,而是对客观事物的认知有一个过程,是由表及里、由事物表象到事物本质的一个进化过程,通过反复观照才能做到主客体融合(“物我两忘”),甚至“天人合一”的境界。在主客体内在精神融合的过程中,反映出中国古人特有的一种“中和”精神。“中和”首先出现在儒家的美学观点中,它在建筑上则反映为以中轴线为中心两边对称的艺术形式,意为“中正平和”。而“中和”在美学中更多地反映为两个互相对立事物的统一。艺术批评家高名潞有言:“‘中和是指不同的异类如何互取的意思。”前文提及的将艺术家元气和宇宙元气结合就是一种“中和”的体现,我们熟知的符号“太极图”也是一种“中和”的表现。
“中和”理论在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应用十分广泛,比如美学概念“意”,“意”是“图理”“图识”“图形”相互重叠、相互渗透的部分。“图理”意为卦象,也就是符号;“图识”意为文字,表达观念;“图形”意为绘画,表达形象。在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理论中经常可以看到关于“意”的概念,其有三个含义:一是事物的本质意义或规律,如《易传·系辞传》中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二是意境或者境界的意思,“意境”一词可以追溯到南朝谢赫在《画品》中提及的“取之象外”,也就是对意象中有限的象的突破,是“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清晰地表达了意境的美学本质,意境所表达的是虚实相生、情景交融的“境”,是造化自然、气韵生动的图景,同时体现出宇宙本体和生命的“道”或“气”;三是移情或者会意的意思,也就是从客体中体会到主体的思想或意志,如《历代名画记》中张彦远论吴道子画“意在笔先,画尽意在,虽笔不周而意周也”,再比如北宋苏轼跋赵云子画“笔略到而意已俱”。除此之外,中国传统文人画的核心——“写意”精神的含义也与之不同,“写意”是文人抒发胸中逸气,表达主观情感的体现。例如,倪瓒《答张仲藻书》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
除“意”的美学概念外,“中和”理论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应用也十分广泛,如传统绘画中的题跋。古人通过题跋将诗与画融合,也就是将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相融合、相渗透。依据前文所说,绘画一般描绘的是特定的叙事、情节和相对静态的空间,通过题跋的方式,将诗这种时间艺术所表现出的动态的嗅觉、触觉以及听觉要素融入静态的绘画艺术中,做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宋代画家郑思肖的作品《墨兰图》(图1)直观描绘了“无根之兰”的艺术形象,画面右侧所题的“向来俯首问羲皇,汝是何人到此乡,未有画前开鼻孔,漫天浮动古馨香”,道出了画家不趋炎附势的气节和志向。综合“无根之兰”的意象和题诗的内容,画家表现出了山河破碎后的悲愤及不愿随波逐流的爱国情怀。
再如老子讲的“有无相生”的美学观点,其意为“有之以为利,皆赖无以为用也”。老子认为,万物是“有”和“无”、“虚”和“实”的统一。有了这样的统一,万物才能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在艺术作品中才能产生意境。中国画中的留白就是有无相生、虚实相生且有意义的空间组织。一幅画面中“有”的部分的精彩与夺目,是靠画面“无”或留白的部分衬托而来的,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无”的部分并不是空白和有待填充的背景,而是气息流动、氤氲浑化的空间,如“马一角”“米氏云山”“一江两岸”等绘画图式都能充分地利用留白来达到作者想表达的一种思想或精神境界。说到底,“中和”思想彰显出中国传统文化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特质,这是中国文化包容力的体现。
五、结语
本文所阐述的中西绘画构图中的空间与叙事实质上都不可回避其背后形而上层面的理论依据。我们知道,西方现代美学和艺术理论所经历的哲学转向、符号学转向(语言学转向)和图像转向三个阶段仍在探讨艺术如何再现现实或真实的问题,其诸多理论仍需追溯到柏拉图。同理,中国传统美学观点与艺术理论也不曾脱离老庄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关于“道”或“气”的学说仍贯穿于中国美学理论体系的发展中。
参考文献:
[1]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2]邹跃进,诸迪.美术概论[M].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3]高名潞.西方艺术史观念:再现与艺术史转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4]崔雪冬.时空的“设计”: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研究[D].北京:中央美术学院,2014.
[5]龙迪勇.空间叙事学[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8.
作者简介:
关懿恒,硕士,北海艺术设计学院美术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当代油画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