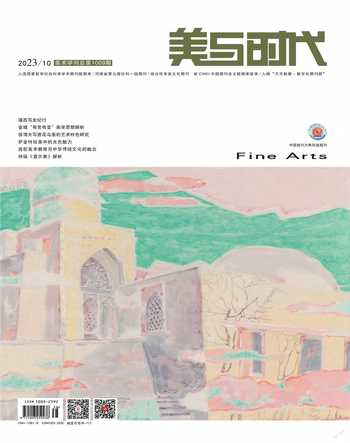马远《晓雪山行图》赏析
摘 要:历代画家对行旅题材山水画的创作都青睐有加,通过行旅活动与自然山水的现实联系,揭示当时的社会面貌和文化背景,同时也承载着画家自身的精神境界以及对人生的思考。从构图形式、笔墨技法、意境表达等方面探析马远《晓雪山行图》,并借此来窥探行旅人的生活与思想,以及马远身为宫廷画家却能心系百姓、情系民生的崇高品格。
关键词:马远;《晓雪山行图》;行旅题材;构图形式;笔墨技法;意境表达
一、马远与《晓雪山行圖》概述
(一)马远生平
马远,字遥父,号钦山,祖籍河中(今山西永济),后移居钱塘(今浙江杭州)。不少学者通过综合古文献资料、对比史料等方式对其具体生卒年进行考辨,但仍无法考据出确凿无疑的时间,只能粗略推断出其活动于南宋光宗、宁宗、理宗三朝期间[1]。马远为南宋画院待诏,并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在画史上与李唐、刘松年、夏圭并称为“南宋四家”。他精通山水、人物、花鸟与台阁杂画等各类绘画,尤其在山水画方面,他在继承李唐的大斧劈皴绘画技法和构成形式的基础上,结合各家山水画特点、所处的地域环境和自身的审美体悟,将大斧劈皴发挥到极致,且更加刚劲有力和简约大气[2]。此外,他独创的“马一角”构图形式,引领着整个南宋时期山水画构图风格的改变,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画家们的审美取向,对南宋时期院体山水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3]。明代曹昭在《格古要论》将其边角之景形容为:“全境不多,其小幅,或峭峰直上而不见其顶,或绝壁直下而不见其脚,或近山参天而远山则低,或泛舟孤月而一人独坐,此边角之景也。”[4]因其画艺精绝,故有“独步画院”“院中人独步也”之美誉。马远在山水笔墨与局部取景的图式上的独创性,使其作画风格具有无可取代的作用,典型的山水画作品有《踏歌图》《梅石溪凫图》《寒江独钓图》《水图》《山径春行图》等。
(二)《晓雪山行图》概述
《晓雪山行图》,绢本水墨,纵27.6厘米,横42.9厘米,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晓雪山行图》是一幅典型的行旅题材的山水画,古代的“行旅”通常有着明确的目的,是指长时间、远距离的外出活动,所以行旅题材作品中一般涵盖着旅人、路径、行装、车马等元素。图中描绘了两头毛驴驮着木炭和干柴在深山白雪覆盖的小径上俯身低头前行,赶驴人肩上用木棍挑着一只仿若山鸡的动物紧随其后的生动场景。深夜下过雪的山麓冒着寒气,枯树的杈桠被雪压得低垂下来,只见赶驴人衣着单薄,寒风侵肌,他将双手藏于袖内,缩头弯腰、步履蹒跚地行走在积雪皑皑的山间。正如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中云:“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此图虽是一幅小品画,画幅偏小,但画中别具一格的一角式构图方式、炉火纯青的笔墨技法和萧瑟凄凉的意境给人以无尽的遐思空间,同时也被后世众多画家仰慕和效法,是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杰作。
二、《晓雪山行图》作品赏析
(一)构图形式
与北宋时期强调纷繁复杂、气势雄浑的客观山水的全景面貌不同,大面积留白成了南宋院体山水画常用的构图手法,它不仅指向具体的题材内容,还引导着画面,蕴含着深刻含义,体现着画面的气势与神韵,也能引发出观画者的回味和无限联想[5]。留白成为画家表现意境和虚实变化的一种形式,也成为其构图时的一种创作技巧。因靖康之变,宋室南迁,家学底蕴深厚的马远迁家至烟雨迷蒙的江南水乡。身为院体画家,马远作画时多以江南山水边角为参照,将李唐之局部取景、留白构图等风格特征发展到了一个顶峰。在《晓雪山行图》的左上方部分,马远用大笔劈皴法利落地勾勒出远处险峻陡峭的侧峰,表现出山石的坚硬质感,半坡则采取大量留白的方式,生动展现出山脉被层层积雪笼盖的情境,从而烘托出天气的严寒。画面上方他只露出了一些树根、不完整的树干和枯萎下垂的枝条,仿佛远处是重峦叠嶂的群山,抑或是密密匝匝的茂林,令人不禁遐想联翩,“一角”之美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画面的右边是马远用“拖枝”来塑造的枯枝,他习惯将笔触拉长来刻画山石树枝之苍劲有力,被后人称为“拖枝马远”。右上角的枯枝带着零星的叶子向下垂挂,想必是被深夜的积雪压弯了。画面的主体部分描绘的则是瑟瑟发抖、举步维艰的农民和驮着木炭的两头毛驴在山间的河边施施而行,从而反映出当时社会底层人民艰苦的生活。河也是采用了小中见大的留白方式,以有限的笔墨描绘出了绵延不绝的河流。《晓雪山行图》画风简约,对角线的构图方式简单明了,追求诗意,以大面积留白的构图样式营造出“天寒色青苍,北风叫枯桑”的凄凉场景。
马远在其简洁的构图中以简练精到的笔墨刻画了点景人物,如《踏歌图》中的老汉、《寒江独钓图》中的渔父、《西园雅集图》中的文人雅士和《高士观瀑图》中的高士等等。尽管这些山水画中的点景人物在神态面貌上的描绘并不精致细腻,但其不但超越了客观物象,而且使得画面中有了虚实、主次等笔墨形态上的特征[6]。宋代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变革发展也影响着画院画家的灵感来源和作画风格,他们常以普通百姓的生活场景为内容,以山水为背景,以风俗为题材进行创作,具有极为深厚的人民性和普遍性。宋代商品贸易的兴盛,推动了商品在市场间的贩运与流转。《晓雪山行图》中的点景人物是放置于画面右下端近景处的一位赶驴人,他颤颤巍巍地行走在荒寒的山水间,从两头驴背上驮着沉重的木炭和干柴可以推断出赶驴人是一位卖炭翁,他将去集市上贩卖这些炭和柴以维持生计。虽然当时农产品开始商品化,但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阶级要承担繁重的苛捐杂税,且各方面都受到朝廷的压迫和剥削,生活过得十分艰苦,使得当时农民起义频发。这位卖炭翁就是农民阶层的典型代表,在这个寒风冷冽的清晨,他衣着单薄、弓腰驼背地行走在山间小河边,周围的枯树和寒石都映衬着天气的严寒,也烘托着农民生活的艰辛和不易。马远虽身为院体画家,却能心系百姓,通过塑造褐衣不完的樵夫形象来以小见大,并以此劝诫朝廷体恤平民、关爱人民。
(二)笔墨技法
曹昭在《格古要论》中记载:“马远师李唐,下笔严整。用焦墨作树石,枝叶夹笔;石皆方硬,以大斧劈带水墨皴,甚古。”[7]李唐创立了大斧劈皴,马远继承并将其发挥到极致。在《晓雪山行图》的远处,马远侧笔横扫,用大斧劈皴加上大面积留白的方式塑造出雪山之形,去掉了繁细的山石结构,显现出强烈的空间感。近处他用重墨作斧劈皴,用轮廓线勾勒出树枝和山石,山石方硬有棱角,石块采用了石分三面法,底部着墨较多,而顶部墨水较少,体现出石头的厚重感,让人感觉更加立体而不呆板。以竭墨勾勒出的树枝则采用了他独特的“拖枝”,虽是萧条的枯枝,却横斜曲折,苍劲有力,同时他细腻刻画了寒风中摇摆的稀稀落落的枝叶,后面的枯枝上还散落着零星的雪花,这体现出他对细节的忠实。远处他用淡墨和线条勾画出扎根地面的树根、曲硬如铁的树干和向下微微弯垂的枝叶,因只画了一角,从而给人以崇山峻岭的感觉。地上零散的小石块仿佛随时都要从山坡上翻滚下来,使得山间的行走难乎其难。
明代邹德中《绘事指蒙》从人物画线条的角度概括称:“减笔:马远、梁楷之类。”同为减笔,但不同于梁楷潇洒飘逸的率笔写意,马远的线条工整而不失谨细,强调笔法的健朴凝练,衣纹劲健,多顿挫转折与粗细变化,人称“鼠尾”“柳梢”[8]。《晓雪山行图》中卖炭翁的衣纹是用干笔勾勒的强劲直线,描绘出衣服的褶皱,显现出衣衫薄如蝉翼,并用水墨渲染了帽顶。刻画人物脸部时,他以细致重叠的线条来描绘眼、鼻,以墨来渲染脸颊的阴影和眉毛,只见卖炭翁将双手藏于袖口内,嘴往袖口内哈着气,并不停交换着双手以握住竹竿,生动塑造了一个冽冽寒风中为生计奔劳的行旅人形象。前后相随的两头毛驴及其背上的竹筐、木炭也是用干笔勾勒、水墨渲染的,墨色浓淡的对比增强了立体感,栩栩如生,细枝末节处分明逼真。用焦墨画出的驴眼向地面望着,驮着重物的驴背微微弯曲,在驴腿的膝关节处用笔有力,加以停顿强调,驴蹄则用笔尖勾出,呈三角形状。而放置篓中的木柴顶端微微泛白,象征着积聚的小雪。
(三)意境表达
“意境”一词最初源于古代的诗词领域,而后成为中国山水画的重要灵魂,也成为评判艺术作品的重要标尺。中国山水画意境之美不仅表现在诗意之美方面,还表现在情感之美方面。马远的《寒江独钓图》仅用渔翁、孤舟、江水元素和大面积留白的表现手法,寥寥数笔描绘出唐代柳宗元《江雪》中“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寒意萧索、幽静凄冷的空灵意境,其二者之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以境界之统一将诗画巧妙融合。《寒江独钓图》也以平远的构图方式营造出恬淡无为之境,使观画者感受到“安心恬荡,栖志浮云”的平和心境,对后世绘画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晓雪山行图》用行旅人卖炭翁的一段山行之径为局部取景构图来以一斑而窥全貌,并以大面积留白的方式展现出雪山的层峦叠嶂和连绵不绝,将衣衫单薄的卖炭翁和驮着木炭慢慢腾腾往前走的两头驴放置于画面的中心,无一不显现着在大雪封山的清晨,寒气刺骨的萧条荒凉之境以及卖炭翁为了生计戴霜履冰而不辞辛劳的孤独凄凉之境。正如白居易《卖炭翁》中所写的“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诗画中均体现着天气之严寒、卖炭翁生活之不易和处境之矛盾。马远将卖炭翁作为底层穷苦人民的代表来以小见大,表达其对百姓的关爱与同情。画中场景可能并非身为南宋院体画家的马远亲眼所见,但其寓情于景,将忧国忧民的情感融于空荡冰冷的雪景之中,营造出了情景有机融合的完善意境。
这幅画虽然给人以寒气袭人的直观感受,使观者心中不禁泛起对卖炭翁的种种同情,但从驴背上的木炭、老翁的步伐這一角度,却给观画者一些逆境中的鼓舞。尽管寒风凛冽,随时面临着雪崩的危险,但卖炭翁为了生计坚持在雪中运木炭,其坚韧给这个寒冬带来了一丝温暖与光明,以及对春暖花开之期盼。这也寄托着马远对百姓坚毅品格的欣赏以及对重振国家繁荣的信心。
(四)蕴含的理学思想
作为宋代精神文化的主流思想,理学不仅是儒学的发展,而且深刻影响着宋代山水画的美学思想的形成。美学家李泽厚在《华夏美学》中说,宋明理学高潮时期也大体是中国山水画的高潮时期[9]。理学中“格物致知”“穷理尽性”“天人合一”等观点或多或少影响着马远的创作风格。所谓“格物致知”,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马远在《晓雪山行图》中以简洁的一角式构图、大面积的留白描绘出意境深远的荒山雪景和行旅人孤独赶路的凄凉画面。留白不仅衬托出了画面的主体部分,也深化了画面的意境,给观画者以更大的想象空间,这无疑是受到了理学“天人合一”的体系影响。作为一幅小品画,此画取雪山之半坡、树枝之半截、小河之半边,虚实相生,赋予整幅画以和谐理性之美。马远在笔墨技法上师法李唐,运用大斧劈皴突出雪山的陡峭与危险,笔墨运用上法度严谨,以浓墨与淡墨相结合的方式赋予画面空灵高旷之境。正是马远对于客观事物细枝末节的忠实把握和对于忧国恤民的个人情感之体悟,从而真正做到了托物言志和理性之显现。马远的其他作品,如《雪滩双鹭图》《梅石溪凫图》《水图》等也贯彻着“格物致知”的理学思想,体现着画家高超的理学素养。
三、结语
作为南宋院体画坛的重要人物,马远在“边角之景”的空间表现、大面积留白的构图方式以及独特的水墨技法等方面形成了自身独到的风格,不断为后世所效法与学习,并传播到日本、朝鲜等国家。《晓雪山行图》是一幅典型的以行旅为题材的小品画,题名中的“晓雪”就给人荒寒冷寂之意,此画在构图方式上采取了局部取景和大面积的留白,并刻画了一位为生活奔波劳碌的点景人物,在笔墨技法上将李唐的大斧劈皴和水墨苍劲风格发展到极致,在意境表达上将对社会底层人民的同情和忧国忧民的情感寓于画面中,借此希望朝廷能体恤民情,且图中蕴含着丰富的理学思想,使其在创作中有所自省和创新,这值得结合马远的其他作品进行深入挖掘和研究。
参考文献:
[1][6]刘心.马远山水画点景人物与画意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21.
[2]孙晓露.南宋四大家山水皴法成因探析[D].武汉:湖北美术学院,2021.
[3]秦雅.“马一角”构图在南宋绘画中的价值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20.
[4][7]曹昭.新增格古要论:下[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34,33.
[5]邢雅琦.南宋院体山水画构图中的“留白”研究:以马远、夏圭“边角山水”为例[D].长春:长春师范大学,2022.
[8]于洋.悉其精能 造于简略:南宋马远的生平与画风研究[J].荣宝斋,2009(1):5-21.
[9]李泽厚.华夏美学[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237.
作者简介:
胡馨予,中国计量大学人文与外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哲学、宋明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