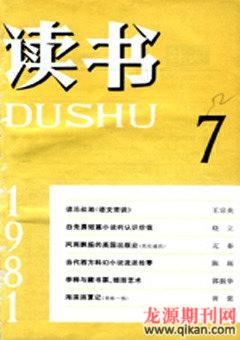1981年第7期,总第28期-品书录
《印度哲学》,〔印〕德·恰托巴底亚耶著,黄宝生、郭良
印度哲学是个宝库,跟中国哲学一样,历史悠久,资料丰富,并且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可惜,目前我们国内探索这个宝库的人还不多。
我觉得本书有三大特点:
首先,它是一部介绍印度哲学的通俗读物。作者的写作意图是普及印度哲学遗产,因而他设想这部著作可能是读者接触的第一部印度哲学著作,在写作时力求简明扼要,并在书后备有《印度哲学派别、人名和书名表》和《印度哲学专名索引》两个附录(每个条目都加了简短的注释),供读者查考。作者还认为,“通俗”的含义不仅仅是一种简明易懂的客观介绍,还必须考虑到“人民的哲学需要”,区分出古代哲学中的精华和糟粕,以利于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
由此而形成第二个特点,即全书贯穿了鲜明的唯物主义观点。向来,印度被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家认为是唯灵论和神秘主义的故乡,传统的印度哲学家也将诸如“解脱”、“业”和“瑜珈”这样一些唯心主义哲学概念视为印度哲学的光荣和骄傲。恰托巴底亚耶不怕“得罪流行的感情”,甘冒“触犯众怒的危险”,大力发掘古代唯物主义思想材料,恢复它们在印度哲学史上应有的崇高地位,并借以批判印度的唯心主义思想传统。本书不仅在思想观点上,而且在结构上也是别开生面的。传统的印度哲学家(如摩陀瓦的《摄一切见论》)在概述印度哲学时,将印度古代唯物主义派别顺世论作为最低派别放在开头论述,而将极端唯心主义派别不二论吠檀多作为最高派别放在最后论述。他们认为这是按照精神认识逐步达到的高度安排的。恰托巴底亚耶反其道而行之,有意将唯心主义派别放在前面论述,而将唯物主义派别放在最后论述,作为本书的压卷之作。
第三个特点是本书的作者虽然是位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他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并不简单粗暴,而是有分析,有说服力的。例如,印度最早的哲学著作《奥义书》是被印度国内外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奉若“圣典”的。德国的叔本华曾经宣称《奥义书》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可能是世界上最有益和最崇高的读物;它是我活着时的安慰,也将是我死去时的安慰。”《奥义书》唯心主义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认为世界是“梵”(即纯意识),所谓的最高知识就是认识“梵”。恰托巴底亚耶利用《奥义书》本身的材料,步步深入地说明:《奥义书》哲学家为了摒弃正常的人类知识,不得不“从梦中意识,从无梦的睡眠,甚至最后从死亡中寻求庇护地”。这样,印度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观点从它诞生之时起就自我宣判了死刑。但恰托巴底亚耶并没有因此而全盘抹煞《奥义书》的历史作用。他认为《奥义书》的产生是一种“思想的解放”,“我们从中看到理论意识首次从对于巫术仪式的唯一兴趣中解放出来”,“至此,才能提出一些真正的哲学性质的问题。”又如,他对佛教唯心主义也持这种态度,对佛教哲学中的辩证思想和佛教哲学家对逻辑学的贡献作了充分肯定。
总之,这部印度哲学的入门书是值得一读的,希望它能引起国内更多同志的兴趣,去探索印度哲学的宝库。(梁云)
《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集》,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十二月第一版,1.58元。
朱先生是我国美学界的代表人物之一,就其整个的著作来说,这本三十万字的书,虽不免略嫌单薄,但所收文章的确是他一生学术研究的精华。通过它可以大致了解作者美学、文学的基本观点及学术思想发展的脉络。且不说收入本书的作者解放后写的许多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建立很有价值,就是他解放前写的《文艺心理学》等,也很值得重视,绝不能因为它的基本观点是唯心主义就一棍子打倒。须知唯心主义对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也是有巨大贡献的。朱先生解放前的美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这是他自己也不讳言的,但我们只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去分析,还是可以从中发现很多富于启发性的东西的。
比如作为作者美学基础的“形相直觉”说,就很可以细细研究一番。作者强调的是两个东西:一是形相,认为美感的对象是具体鲜明的形象,而不是它的抽象意义。认为这种形相是“孤立绝缘”、“独立自足”的。二是直觉,认为美感经验中,心所以接物者只是直觉而不是理性思维。这在过去都被说成是唯心主义,全错了。我看还不能全盘否定,披沙拣金,还有可取之处。应该说,“物我两忘”、“物我同一”确是审美欣赏的极境,但这种境界的造成,不能如朱先生所说,只是直觉的结果。这直觉的背后,其实还是理性在起作用。这种理性是以往多次审美经验积累的结果。由于审美的直感性,往往用不着思索一番,这就造成错觉,以为审美只要直觉而不要知觉了。再说形相,诚如很多批评者所说的,它只是美的事物的外在形式,事物之所以美,究其根源还是它的内容在起作用,所以形相不可能是“孤立绝缘”,“独立自足”的。但朱先生强调“形相”在审美中的特殊地位,无形相就谈不上美,这个看法是对的。
此外,作者在《文艺心理学》中论述的审美经验中的“心理距离”说和移情作用等,也都有许多可资借鉴、汲取的东西。李泽厚同志讲得好,唯心主义美学“有个好处,就是它们揭示了描述了许多美的经验现象”。美的问题是很复杂的,与人的心理、生理很有关系。唯心主义着重从人的生理、心理角度去探讨美。在这方面,它研究得很深,很细。问题是它把这部分绝对化了,忽视乃至排斥了对美的社会学研究,特别是人的生产实践的研究。朱先生解放前的美学是不是也可以作如是观。
朱先生的美学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结合文艺谈美。他主张美学应该是艺术的哲学。美是艺术的一种特性。《诗论》就是他运用美学理论研究中国诗的专著。他的研究方法是:用中国古典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开创了比较文学的先河。《诗论》解放后未再版过,本书收入了其中大部分章节,更弥足珍贵。
本书收入了朱先生各个时期的著作,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待学术研究的态度是极为严肃的。比如收入本书的《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一文,就表明了六十年代作者在美学思想上的新发展。在这篇文章里,他明确主张要用实践的观点取代静观的观点去研究美学。也许他阐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观点还不那么完善,甚至有错误,但作者的这种精神还值得敬佩。(陈望衡)
《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编,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年五月出版,25元。
河北省古代文化遗存非常丰富。最近河北省博物馆及文物管理处的考古工作者将近三十年来本省考古发掘工作的重要成果选编成《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一书出版,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本书书前有由河北省博物馆及文物管理处编写的《河北省考古工作概述》,写于一九七七年,而从文意观测,当时全书似已编辑完竣,但本书的出版时间却迟至一九八○年五月,出版周期未免过长。而正因如此,这三年内河北省的一些考古新发现都无法收入书中,使本书失却了反映最新考古成果的作用,间接亦降低了本书的学术价值。
由于上面所说的原因,《河北省考古工作概述》一文难以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遗漏与疏误之处。
首先是文中对河北省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磁山文化并未提及。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武安磁山遗址是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至七七年四月发掘,撰写此文时无法赶及叙述。但是磁山文化材料相当重要,对研究黄河流域早期新石器文化提供宝贵的资料,所以即使在发掘未结束前,在文中适当的提一下是很有必要的。本文对于平山中山国墓葬的处理方法就恰好可以作为一个借镜,该遗址是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至七八年六月进行调查发掘,本文撰写时发掘尚未结束,在本文中却已有述及。
其次是本文叙及一九七二年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铜钺铁刃鉴定结果的部分是有问题的。文中根据该遗址发掘简报(刊《考古》一九七三年五期)附载冶金工业部钢铁研究院对铜钺铁刃进行鉴定的结果,认为铜钺的刃部“基体为铁,刃口部分经过金属热变形和锤打,系古代熟铁,”并且推断:“早在商代,我们的祖先已经有了较为进步的冶铁技术,并把它应用于制造武器,从而把我国冶铁的历史,由战国初年上溯到商代晚期,提前了千年左右的时间。”(28页)其实早在该遗址发掘简报发表时,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先生已在读后记中对此表示怀疑,认为“根据已做过的化学分析和金相学考察,似乎并不排斥这铁刃是陨铁的可能,还不能确定其‘系古代冶炼的熟铁。”其后,北京钢铁学院再经详细鉴定,终于证明“藁城铜钺铁刃不是人工冶炼的铁,而是用陨铁锻成的。”(见李众:《关于藁城商代铜钺铁刃的分析》,《考古学报》一九七六年二期,31页)在本文撰写时,该文章已经发表,本文理应依据新的鉴定结果来加以叙述。
此外,本书对出土文物的文字说明似可更为详尽一些,除了器物出土时地,大小尺寸等基本资料外,最好能增加一些有关该器物的形制、纹饰、用途等的介绍,以方便读者利用,在这一方面,《江苏省出土文物选集》一书可以作为范例。
最后一提的是,本书的黑白图版印刷效果一般,但是彩版却相当精美,比起国外的印刷技术也未遑多让。这值得高兴。(晓村)
《黑猩猩在召唤》,〔英〕珍妮·古多尔著,刘原一、张锋译,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年三月第一版,1.05元。
这是一本专门记述野生黑猩猩群体生活的科普读物,也是一项来之不易的科学研究成果。
作者是一位年轻的英国姑娘,从小就培养起对大自然的热爱,中学毕业后怀着浓厚的求知欲望,远离故土,抛弃繁华的大都市生活,长时深入到人迹罕至的非洲莽林当中,对一群黑猩猩持续地跟踪考察达十余年之久。她战胜了无数艰难困苦,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这项极有意义的工作,终于获得了大量的、十分珍贵的实际观察资料和研究成果,在动物研究史上,首次揭开了野生黑猩猩的行为习性、群体关系和个性特征等种种奥秘,提供了丰富的科学知识,使我们对这种和人类最近似的动物有了更为全面和生动的了解。特别是其中的许多有意义的新发现,足以动摇或否定长时期来在黑猩猩研究领域中的一些传统的观念,填补了不少空白。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野生状态下的黑猩猩使用自然物体作为“工具”的能力,要比以往了解或估计的为强。它们不仅会用石块砸开油棕果的硬壳,取食果仁,用棍棒捅进土蜂窝里,舐食棒上的蜂蜜,而且择取细长的藤枝,捋去叶子,修整成适合于应用的草棍,来“垂钓”食取白蚁丘内的白蚁。它们在威慑和攻击时,也会想到凭借石块和棍棒的作用而加以使用。叫人惊异的是黑猩猩还具有集体捕食动物的能力。过去,人们一向以为黑猩猩是素食者,这种看法在事实面前应该被推翻了。
引人入胜的是黑猩猩群体中比较复杂的结构。它们中间除了亲缘关系外,还存在着自然的等级关系,这些关系象一条无形的纽带,贯穿在黑猩猩的许多活动中。
在我们的星球上,没有比黑猩猩在外形、生理结构和行为习性各方面更近似于人类的了。人类和猿猴有着共同的起源和祖先,古生物学发现的证据,迄今已经有两千万年漫长的历史了。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探索早已消失了的人类童年时代的社会生活情景,了解最早人类集团的构成,考察劳动、思维、语言的萌芽,心理现象的发端,以及人和某些动物在行为机制方面的共同起源等等,黑猩猩社会群体提供的线索或证据,能给予我们很有益的启示,具有重大意义。
诚然,黑猩猩和人类是非常近似的,但是不管两者如何酷似,人和黑猩猩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人类不仅有完善的高度发达的思维器官和语言的能力,而且会劳动,制造工具,创造社会财富,具有自觉的能动性,这是一切动物界包括最聪明的黑猩猩都是望尘莫及的,它们无法获得也不可能具备我们人类的本质。因此,作者认为黑猩猩也能制造工具,甚至需要给人类重新下一个定义的说法,恐怕难于成立。此外,书中在分析或解释黑猩猩某些行为习性时,有些地方难免有混入人为的主观想象之嫌,譬如雨季来临,黑猩猩在雨中欢快地跳起所谓的“雨舞”,给人造成黑猩猩似乎有了一定的宗教意识的错觉,这都需要读者细心留意的。
(蔡家骐)
《教海拾贝》,丁家桐著,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年十月第一版,0.24元。
这是一本启发教师探索教育规律、进入最佳教学状态的好书。
作者对教育理论进行了新的探索。他没有令人乏味的说教,而是娓娓动听地谈心;没有满足于干巴巴的原则阐发,而是象一个好的教师那样,不但“使学生从有疑到无疑”,而且更“善于引导学生从无疑到有疑”,因而这对读者的学习和探索,无疑“是大有帮助的”。作者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具体作用,谈到教学艺术的探索,谈到德、智、体育诸方面的追求,谈到教师的自我修养。举个例子说吧。作者在介绍“新旧联系,新课慢讲,螺旋上升,反复巩固”这一教学经验时,没有抽象地宣扬这条经验的好处,而首先对学生学习的过程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再结合教师帮助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的比较,令人心折地得出这一结论。这不是作者强加给你的现成口诀,而是你与作者一起进行思考以后得到的科学结论。多年来,这样的文章我们见得太少了,而今读来,耳目一新。我想,任何一个细心的读者,从这里都决不仅仅只学到一条教学经验,单从文风来说,不就够我们从中去寻求启迪么?
当然,这本书也有它的缺陷。依我管见,《教海拾贝》这个书名就不新颖,落了套子。自秦牧《艺海拾贝》以来,世人踊跃而拾贝者多矣。于是乎《诗海拾贝》、《文海拾贝》、《戏海拾贝》纷纷涌出。这个“教海拾贝”,为什么不可以换一个新鲜的题目呢?跟在名人后面赶“时髦”么?
在目前出版界出现的一股滥印剑侠小说、复习指南之类的“热流”中,本书毕竟是一股小小的清泉,一股令人头脑清醒地去探索、去追求、去为革命事业添砖加瓦的清泉。
(王向东)
《宋词》,周笃文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年四月第一版,0.37元。
这是一部持论允当,文彩雅瞻的普及性词学著作。全书八万来字,内容凡五章:首论“词的起源和特点”;次论“两宋词概论”;三、四两章分述北宋、南宋词坛;末论“宋词的地位与影响”。著者既是选隽解律的选家,评论也具有真知灼见,笔调又非常流畅。这就赋予该书以一种清新朴茂的气息。
首先是选材得宜。该书在重视思想比较积极的苏辛词派的同时,对在词学发展上有过重大影响的婉约派词家如周清真、姜白石、吴梦窗等的艺术成就,也给了客观的、比较充分的评价。只要片长足录,确有特色,哪怕是无名氏或女性的作品也不使脱漏。甚至域外词家的活动,也酌与介绍。比如书中所举日本嵯峨天皇次韵张志和的《渔歌子》一事,发生在九世纪初,上距张作不过二、三十年,等。这种纵横系联的方法,不仅开阔了视野,而且具有立体感,使作品显得更加深刻有力了。
其次,敏锐的观察力。比如,它说:“词,这种新兴的文艺形式,它与高踞文坛正统地位的诗或文不同:它毋须矜气作色来显示自己的‘尊严,不受‘文以载道的说教所束缚,因此,它比较活泼自由,敢于冲破‘禁区去表现普通群众的生活、爱情和愿望……它是真正的抒情文学。我们读到它,就仿佛听到了肺腑的倾诉和触到了脉搏的跳动,不能不深受其感染。”这样观察问题的方法,显然不是已往词话作者所能具备的。只有新时代的作者,才会有这样的感受。
还有,是善于推陈出新。这是一本浓缩化了的著作。征引书目已过百种。而且含英咀华,时出新解。这种融裁消化,如狮搏兔,是花了大气力的。对于学术上的争论,作者也表现了积极的态度。比如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问题,过去余嘉锡、夏承焘先生已经提出疑问。本书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如指出《藏一话腴》所引“又作满江红,其忠愤可见”一语,乃清初馆臣的误书。又考订出《古今词选》上署名文天祥的同调、同韵之作,并非文氏作品。而且从两词的风格、韵式、流传年代极为相似等特点,论定两词不得早于明代,很可能出于一人之手,等等。该书最后说:“当然,这样说,并不等于否定其艺术价值。这里所涉及的仅仅是历史的真实性问题而已。”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作者治学态度的严谨和富有启发性了。(周采泉)
《<雷雨>人物谈》,钱谷融著,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年十月第一版,0.49元。
对文艺批评文字的不满由来已久。尝够林彪、“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酷评”之后,人们早就渴望快出几部新鲜、扎实的著作,一扫公式化的风气,造出一派生机。在已见到的不多几种这类书籍中,本书堪称一部独辟蹊径、别开生面的作品。
文艺作品的价值首先应从作品自身中去发现,或可说是本书的宗旨。与着重从历史背景、思想意义方面对作品进行社会学分析的方法不同,本书直取《雷雨》这部杰作本身为对象,以探究话剧艺术创作规律为己任,一般常被单独抽出加以阐释的思想内容在这里作为与艺术形象整体不可割裂的部分加以说明。它对《雷雨》中从周朴园到鲁贵的八个人物作了各自成篇的剖析,同时又结合戏剧冲突、结构、语言等从横的方面详加研讨。尤其难得的是,作者时时处处顾及创作与欣赏两个方面,又能将作家—作品—观众视为一体,从而使人对作品的成就及不足能获得一整体概念。
某些文章的一大弊端是批评与理论捆绑而成夫妻,读起来如嚼夹生饭。本书则令二者相融无间。究其原因,乃在理论阐发能深植于艺术分析之中。细细品读,但见理论文字不知不觉姗姗而来,复又不知不觉悄然而逝。哲学的思流与美感的体验熔于一炉。结论则如水到渠成、顺藤取瓜,自然得出。凡看风定向、穿靴戴帽之作见此当无地自容。
话剧最讲究语言、对白,而“言为心声”。书中最善于结合环境、气氛、冲突,从人物的口吻、声气、态度溯寻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奥秘,发现常人难以发现的动机、情欲、意向,显示出作者体察入微的审美感受和心理分析才能。
钱先生文字细腻流丽、酣畅清醇,常旁征博引,又长于比较研究之法,所以既能深入浅出,又能引人入胜。去年我曾在庐山听钱先生一次讲演,他挥洒自如、左右逢源的谈锋给我印象极深。读《<雷雨>人物谈》,那情景又时时现于眼前。
书不长,仅十二万余字。一气读下,只觉清芬阵阵,扑面而来,文思、情思为之一振,虽月至中天,竟难释手。(郭瑞)
《我的童年》,天津新蕾出版社编辑出版,一九八○年六月第一版,0.75元。
童年,这是一个象金子一样闪光的字眼。一个人的思想品格、知识水平以及他后来所走的道路,总是和他的童年生活联系着的。然而,真正懂得童年的价值,珍惜这段宝贵时光的,往往是在成年以后,甚至是在鬓发斑白的时候。成年人对童年的回忆,对儿童往往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从这个意义来看这本《我的童年》(《作家的童年》第一集),觉得编印这样一本书是个好主意。这里共收我国当代著名作家郭沫若、老舍、丁玲、冰心、张天翼、臧克家、秦牧、杨沫、柯蓝九位同志撰写的童年生活片段。他们从不同的侧面回答了少年儿童关心的一些问题:什么是幸福的童年,应该怎么利用童年的美好时光,作家们是怎样度过了他们的童年的,等等。
《作家的童年》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仅丰富了少年儿童的精神生活,使他们从作家的童年生活中增长历史知识、社会知识和文化知识,而且通过了解作家们的成长道路,认识人生的意义,明确自己对祖国对人民所承担的历史重任。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的童年》这套丛书,不仅教育着这一代少年儿童,并且还影响着下一代。
(季军、一尘)
《魂兮归来》,王新纪、陶正、田增翔著,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八○年十二月第一版,上册0.93元,下册1.00元。
出于某种人所共知的原因,对工农兵大学生,一般作家的作品是尽力回避的。但是,《魂兮归来》则不然。小说正面描写一群工农兵大学生,并对其中大多数加以讴歌,这种敢于探求的精神是良能可贵的。
《魂兮归来》反映了一九七二——七六年间,新华大学中文专业七二班的一群工农兵大学生,以他们的生活、命运,尤其是他们的追求,反映出时代和青年的一个侧面。作为工农兵大学生,他们的一切都与“文化大革命”关联着。因此,他们之中除了有蠹虫、苍蝇、鹰犬外,即使是纯正者,也都带有“文化大革命”的烙印,那种偏激、粗鲁、狭隘、冷漠,甚至狂妄、颓唐,尽可发见。但是,他们不是醉生梦死之辈,他们也在真诚地追求、探索着。尽管目标不一,但毕竟都在现实面前思索。他们有过迷惘、失望、悲观,但占多数的是终于醒悟,正义之魂还归,勇敢地投入了全民族的共同战斗。当然,即使在他们投身四·五运动时,他们的思想、认识也并不一致,今天看来,更有幼稚、甚至荒唐处;但他们那种深沉的爱国之情、执着的探索毅力、无私的献身精神,无疑是熠熠发光的。正是从这里,我们感受到了民族之魂、正义之魂深深地蕴涵在新一代青年的心底。小说之成功处、可贵处,就在于真实地写出了这一切。也正因为如此,“魂兮归来”的呼喊才不是空洞的,而是有着实际意义和现实基础的。
小说作者没有停留于此,而是通过青年学生探索、“招魂”的过程,形象地告诉我们:在人民大众之中,在真正的共产党人之中,民族之魂、正义之魂从不曾消逝,也永远不会消逝。真正的共产党人如梁牧、王磊、钟仁远等中流砥柱,他们创造了历史,创造着现在和未来,撑持着中国的脊梁,使学生们在探索中发见了闪光的东西,逐渐认识到了生活的真谛,从中汲取了力量,坚定了信念。从这一切中,我们会进一步体会到:党、人民、是欲招之魂的根本所在;民族之魂不死,正义之魂可招。
“魂兮归来”语出《楚辞·招魂》,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指出的:即使在今天的生活中,“招魂”也仍有很大的意义,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作者的心意是深长的。事实上,“魂兮归来”也是人民的呼声、时代的呼声。同时,又是对民族之魂、正义之魂的热情讴歌,是对新的未来的热切呼唤。(何宝康)
《金瓯缺》,徐兴业著,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十二月第一版,上册1.10元、下册1.35元。
中国历史上,十二世纪是个大动荡的时期,也是一个英雄辈出、众星灿烂的时期。长篇历史小说《金瓯缺》就是以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为背景,形象地再现了在我国辽阔的疆域上曾经并存过的辽、宋、金三个政权和它们的兴衰变化,塑造了一批“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民族英雄。这里面,不但有为救亡图存而九死不悔的北宋爱国将领刘
历史上的马扩原是个低级军官,偶然的机遇把他卷入了一场涉及三个朝廷兴灭存亡的历史大风暴中。作者把马扩当成那个时代各方面联系的纽带,通过他写出那个时代。这个艺术构思是可贵的。他在马扩身上倾注了满腔热情,认为马扩是“诗人屈原笔底下‘国殇的散文化”。这样,马扩这个艺术典型,成了《金瓯缺》的灵魂。
在马扩的塑造上,作者以史料中提供的马扩作依据,“七分真三分假”地驰骋丰富的想象力,选择了一系列富有典型意义的情节和细节,展示马扩的性格。固然,作品中某些情节未见于史料,但传奇色彩的基调和英雄的爱国业绩,都是史料提供的,作者正是根据这个基调发挥了创作的自由。
在本书中,作者调动各种艺术手法,确实成功地塑造了马扩和他同时代的各种代表人物的形象,把他们的气质、性格和内心世界,都刻画得力透纸背,具有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难怪八十八岁高龄的古典文学家郭绍愚读后,欣然作序,指出这部小说写的是“历史的大事,也是民族的大事”,“一般忠臣义士所耿耿于怀的满腔心事都在徐氏的笔底流露出来。”的确,我们今天读着它,很容易引发民族的自尊和正气,激奋新的爱国主义热忱。
(卓钟霖、游斌)
《恶之花》,〔法〕波德莱尔著,王了一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年十二月第一版,0.89元。
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的中文译本终于在北京出版了。这卷现代诗歌的先驱在我国遇到的厄运比在它的故乡更有过之。许多年来诗人被戴上一顶颓废派的帽子,隔离在一边,没有人敢去接近他。其实颓废派这顶帽子本是法国资产阶级卫道士用来惩治叛逆者的。后来苏联人把它接了过去。接着,我国也有人不分青红皂白把别人的立场误认为是自己的立场,犯了一次意识形态的错误。
然而,这么说并不是意味着把《恶之花》看成是天工无瑕,没有问题的问题。文艺作品和人类一切产品一样,自然有个好坏优劣的区分。但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一个文艺作品呢?这就成了很有争议的问题。诗人瓦莱里说过,衡量作品成功与否的标准是作家的意图和作品间的差距。这是个公允的看法。因为,欣赏文艺作品并不是上帝或法官在进行审判,怎能用道德标准或是作品以外的标准作为唯一标准来看待它呢?文艺评论的领域,应该就是这个作品的本身。
作家萨特曾对波德莱尔作过一次不公允的评论。他认为这位诗人的悲剧是咎由自取:波德莱尔清醒地认识到生活的荒诞,但是他却不用他的自由作出抉择。相反,波德莱尔承认了资产阶级的既定秩序。这个评论从哲学的范畴来看也许有一定道理。但是波德莱尔是一位诗人,应该从诗歌的角度来评论他。
诗人韩波在他的《慧眼人的信》中,把这位探索“未知”和寻求“新事物”的波德莱尔称为“诗圣”(roidespoètes,赞扬他是一位“真正的上帝”。可是,他也提到了这位诗人的一个关键性弱点,那就是《恶之花》的语言形式对于诗人所要求的创新来说是过于局限了。今天,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诗歌语言的转变,我们读《恶之花》时,虽然十分欣赏它语言艺术的精湛和典雅,却不禁感到这些优美的诗篇已经是属于过去的时代。王了一先生用我国的旧诗体来翻译这卷诗集,形式和内容与原诗均比较协调。然而我国的格律诗也是属于过去士大夫阶级的语言了,和当前的读者存在着差距。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和福楼拜一样具有敏锐的语言感的波德莱尔在他去世前的两年间那么热衷于尝试写作散文诗。
(健君)
《一个世纪儿的忏悔》,〔法〕缪塞著,梁均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年七月第一版,0.89元。
我翻开《一个世纪儿的忏悔》,看到一个忧虑多愁、伤感多情、悲观失望的青年,他生活在一个阴沉可怕的黑茫茫深渊里。一个充满丑恶、庸俗、自私卑俗的社会使他感到无限的悲哀和痛苦。虽然憎恨这个世界,然而他无力抵抗,自己也陷入泥潭。这便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法兰西青年面临的现实。拿破仑帝国崩溃,反动的封建势力卷土重来。昨天已成了永远被摧毁的过去,充满光荣幻想的信心丧失殆尽;未来在当时青年的心目中虽然美丽可爱,但她却不能唤起人们的激情。留给青年的于是只有现在了。这是怎样一个现实?它坐在一只装满骸骨的石灰囊上,把自己紧紧地裹在利己主义的大衣里,在可怕的严寒中颤抖着。流行在社会上的“世纪病”感染了人们,黑暗、绝望笼罩在青年人的心灵上。
小说的第一部分是一篇导言,作者在这里简炼地概括了当时的时代特点,仔细分析了当时的历史事件并做了冷静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社会认真严肃的思索、研究及对人生的探索。他解释了青年人苦闷、空虚、“世纪病”产生的原因,指出了社会的实质问题。本书并不是一般的爱情故事,可以称得上是一本记载着拿破仑失败后法兰西民众、特别是青年人的思想史,对于了解、研究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法国有相当的意义和价值。
小说在表现手法上有不少独到之处,其中突出的是许多精妙比喻,在形象里包含了深刻的寓意,辞尽而意不尽,颇有回味之妙。作者别出心裁构思的“灵魂和肉体的对话”和“智慧与良心的对话”更添了不少新意妙趣。小说的心理分析也有着无可低估的成就。
缪塞的创作时期正值欧洲大陆上浪漫主义席卷大地之时。有人常将浪漫主义截然分割成“积极的”和“消极的”,消极的便是反动的,因为是反动的文学便成了我们的敌人,几乎没有任何一点值得肯定可取之处了。文学作品毕竟不是政治教科书,评论一部作品,一个作家,一种流派,一种思潮应该更多地从文学本身去研究,机械地为某一作家“定性”“划成分”是不足取的。只提现实主义不提浪漫主义,把前者抬到过高的地位,这种做法是不是完全正确?所谓“消极”的浪漫派中有没有积极的进步的意义?英国的华兹华斯、法国的夏多布里昂等人都值得重新研究、评价。
(姚远)
品书录
梁云/陈望衡/晓村/蔡家骐/王向东/周采泉/郭瑞/季军/一尘/何宝康/卓钟霖/游斌/健君/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