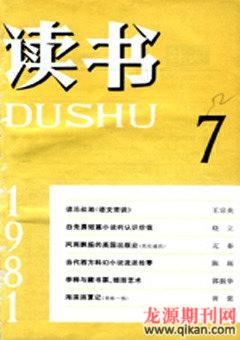石心的金子
郭良夫
邓以蛰和他的《艺术家的难关》
老一辈的美学家,早在二十年代就蜚声文坛的,首推号称“南宗北邓”的两大家。南宗,指南方的宗白华;北邓,指北方的邓以蛰。宗先生健在,知道的人也多;邓先生前几年已经去世,知道的人恐怕很少了。要谈论现代中国的美学和美学家,邓先生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有清一代的书法篆刻大家完白山人邓石如是邓先生的高祖。邓先生家学渊源,书画等美术珍品收藏丰富。邓先生的著作不多,但也给我们留下了一本,这就是《艺术家的难关》。本书包括论文八篇:一、艺术家的难关,二、诗与历史,三、戏剧与道德的进化,四、戏剧与雕刻,五、中国绘画之派别及其变迁,六、观林风眠的绘画展览因论及中西画的区别,七、对于北京音乐界的请求,八、民众的艺术。这些文章都是先在当时北京的报刊上发表,后来结集成书的。
闻一多先生对邓先生的论文作过公平、准确的评价。他在《邓以蛰<诗与历史>题记》①一文中说:“作者一向在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并不多(恐怕总在五数以下),但是没有一篇不诘屈聱牙,使读者头痛眼花,茫无所得,所以也没有一篇不刊心刻骨,博大精深,只要你肯埋着头,咬着牙,在岩石里边寻求金子,在海洋绝底讨索珍珠。……在病中拚着三通夜的心血,制造出这样一篇让人看了头痛眼花的东西出来,可真傻了!聪明人谁犯得上挨这种骂!但是我以为在这文艺批评界正患着血虚症的时候,我们正多要几个傻人出来赐给我们一点调补剂才好。调补剂不一定象山珍海味那样适味可口,但是他于我们有益。”
“作者这篇文章有两层主要的意思:(一)怀疑学术界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二)诊断文艺界的卖弄风骚专尚情操,言之无物的险症。他的结论是历史与诗应该携手;历史身上要注射些感情的血液进去,否则历史家便是发墓的偷儿,历史便是出土的僵尸;至于诗这东西,不当专门以油头粉面,娇声媚态去逢迎人,他应该有点骨格,这骨格便是人类生活的经验,便是作者所谓‘境遇,这第二个意思也便和阿诺德的定义:‘诗是生活的批评正相配合。”
“……假如你因为那诘屈聱牙的文字,望难生畏,以致失掉了石心的金子,海底的珍珠,那我可只好告诉你一句话:‘你活该!”
诘屈聱牙,博大精深,石心的金子,海底的珍珠,邓先生《艺术家的难关》全部文章都当得起这评语。
从和柏拉图辩难开始,邓先生阐述了自然能吐露宇宙的真消息,艺术也能吐露宇宙的真底蕴的美学理论。自然中的现象,最是变动不居的东西。艺术若只得到现象的真实就不再向前进时,柏拉图是要驱逐它出境的。艺术家被人事的情理层层束缚,纵然象元朝大画家倪云林也概莫能免。倪云林虽觉人类脚迹足污大地灵秀,但他也舍不了篁里茅亭,为栖息意志之所,似乎美的感得,处处总要人事上的意趣来凑合。人事的情理,抽象并且具有普遍性的知识,实用化的本能,都构成一切艺术的共同的敌阵,艺术家必须冲过这难关。
《诗与历史》,除了闻一多先生所指出的主旨以外,其中论到不同种类艺术的特点,也特别精彩。诗若流入音乐和绘画的境界,也就与历史脱离关系,只剩下一个空格式了。诗若只是讲究声调,终超不过音乐;若只是讲究用宇,也绝对比不上绘画。诗的言词用来和声音颜色相抗衡,总是吃力不讨好。所以用文字描写的情景,结果必然堆砌得厉害;汉赋便是一个明证。诗既以言词为工具,它所及的远处,应不止于情景的描写,古迹的歌咏,它应使自然的玄秘,人生的究竟,都借此可以贯输到人的情智里面去,使吾人能领会到知识之外还有知识,有限之内包含无限。
雕刻家的材料,全在人的身体上。
《中国绘画之派别及其变迁》,是一篇中国绘画史的纲要。在欧洲,直到十八世纪才看见风景画在英法两国出世,而中国山水画在唐代已大兴(七世纪至十世纪)。验之历史风景画之起,是在人物画之后;这确实使人惊叹中国绘画发达之早。自汉代到晋代,表现人物情态的人物画,全仗着线条的钩勒。晋代顾恺之的人物画,可以见出线条表现的力量之大。人物画在唐代为极盛时期。后来线条附丽于颜色以生存,以致变成线条钩画的实习,忘去所表现的是人物动作的情态,人物画就绝迹了。古人说得好:“佛道人物,士女牛马,近不及古;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古不及近。”证之中国绘画发展的历史,大略如此。
山水画六朝已见端倪,至唐大兴,宋代极盛。中国画特别是山水画,描写的是诗人的胸襟,不是自然的直接模仿。画家必须先对自然景物的变化,涵味要深,使胸中包罗万有;同时也必须对绘画诸法练习经久,知所以运用笔墨骨法,使所绘的物态生动而有气韵。所谓挥洒自如,笔起云烟,非胸中涵泳娴熟,用笔如意,何克臻此!所以山水画家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胸襟和笔法。具备这两个条件,才可以语创造。犹之乎人物画变成线条的钩画,忘记所表现的是动作的情态,于是人物画绝;山水画变成皴擦的堆砌,而失去气韵生动,于是山水画无足观。此外还论及中国山水画和西洋风景画(LandscapePainting)在画家和艺术两方面的根本不同之点。西洋风景画画家,一切全凭自然,颜色、远近,都当作绘画的要素,除此以外胸中一无所有。可以说画家本人没有什么内在的东西要表现。中国画家则不然,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纵目旷观。所谓纵目旷观,只是动目不动手。中国画家,中国画论无不以探求阴晦晴明之理为主。至于自然景物的颜色、远近并不是山水画的要素。颜色在景物中没有多大意义,因为颜色的变化,在自然中全赖光之明晦以为断。所以山水画只讲究用墨。墨色浓淡,尽够表现光的变化了。中国画家要纵目旷观,成竹在胸,动手作画时,全在骨法用笔的本领了。如果用颜色、透视等法来批评中国山水画,却是张冠李戴。
从艺术上说,西洋风景画是颜色涂抹,而且可以反复涂改,一画之成,往往经年累月。中国山水画,必须一气呵成,否则谈不上气韵生动。画幅之上可以皴染,不能涂抹,必得笔笔是笔,才可以下笔。这正是所谓“意在笔先”,“下笔如有神”。
《对于北京音乐界的请求》一文对音乐的性质和功用说得那样透辟,实在是非有对音乐的深刻理解不能办到。音乐成于流动的声音,也可以说这声音形成流动的音乐宇宙。生命本身就是流动的,同音乐一样的流动。人们一听到音乐,血液情绪俱为之颤动,艺术之能和生命打成一片的无过于音乐了。音乐是生命本体的副本,生命对于音乐如对镜看自家的颜色。大音乐家的音乐,无不从生命中来。音乐给人的安慰有如久别后初投入母怀的安慰,反本归原的感人人的根和底。人们性情上的赘瘤得以化除;音乐有洗刷排泄与激扬砥砺的能力。因此作者得出结论说:我们社会需要你们艺术家,你们艺术家也需要我们社会。
为北京艺术大会而作的《民众的艺术》,说明作者二十年代的见解就有不少合理的成分。从艺术的源头看,艺术自始就是和生命分不开的,艺术和民众不能说成两回事。初民带着由剧烈性的音乐所激起的同样的热情来参加群众的跳舞;这中间若除去群众,即无所谓舞蹈和音乐了。欧洲北部和英国有些初民的遗迹是用极大的石头堆起来的,这种建筑,根本非群众莫办。再如故宫博物院以及院中收藏的商周鼎彝等等,那一件艺术品不是民众创造的?历史尽管为功臣名将的名字填满了,宫殿华屋尽管只是帝王阔人居住的,那一点又不是民众的心血铸成的?艺术根本就是民众;民众若离了艺术,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可以使人觉得出来的呢?难道一个人只是吃饭睡觉,就可以算是存在吗?作者坚持这样的观点:民众的艺术,必得是民众自己创造的,给民众自己受用才成。这本书虽然出版在二十年代,可是书中有的论点今天仍然是新鲜的。我希望今天研究美学的同志注意到这一已经遗忘的旧著。
(《艺术家的难关》,邓以蛰著,北京古城书社一九二八年二月第一版)
①原载一九二六年四月八日晨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