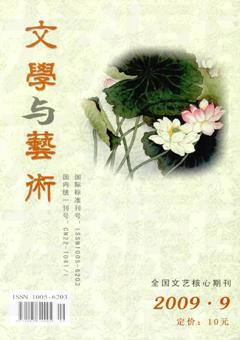“宗教情怀”之于林语堂
王 丹
【摘要】中国现代作家林语堂深受中国传统道教和西方基督教的影响,不同的宗教文化在林语堂的内心吸收和融合。这种复杂的宗教情怀对他的文学创作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体现了宗教与文学的互渗形态。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切入,把林语堂的文学创作置于和宗教的交叉中,探究中西杂糅的宗教情怀对其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林语堂;道教;基督教;宗教情怀;文学创作
在20世纪的众多作家中,林语堂是与众不同的,他是一位“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作家,对中西文化均有广泛地研究,著作颇丰。综观大量的文献资料,学界对林语堂的研究经历了上个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期的滥觞期,40年代到1979年的沉寂期,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复苏发展期,和21世纪之初的快速发展期。相比较而言,大陆积累了他前半生的资料较多,研究论著多出于中青年文学研究者之手,理性色彩较重;而台湾的优势是林语堂后半生的史料较丰富,回忆、评论文章的作者大多与林语堂有过交往,感性色彩较浓。但“毋庸讳言,对林语堂的研究与其他文化名人的研究相比较,无论在深度或广度上,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对林语堂及其文本较多的是从人生哲学、文化观、文化交流、文艺思想、幽默、小品文等主题去关注,对其复杂宗教观的研究虽然也有一些,但对林语堂的文学创作与宗教关系的交叉则涉及很少。林语堂的作品在神气与道风杂糅中闪烁着独特的风采,其宗教情怀也融会贯通其中。本文试着梳理其作品中基督、道的因子,并进而探究宗教情怀对其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影响。
一 自觉地追寻道教文化
林语堂出生于闽南乡间,由于时代、地域、家庭的影响,他早年一直接受基督的教诲。直至林语堂任教清华园时,身处浓烈的传统文化氛围中,他开始认识到自己与传统文化的背离,故其转向对传统文化的追索。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的认识一是中国儒家的伦理观念,一是道家的处世态度。他在《吾国吾民》中曾说:“道家精神和孔子精神是中国思想的阴阳两极,中国的民族生命所赖以活动。”林语堂也把道家看成自己的宗教信仰来崇信,他说:“倘若强迫我在移民区指出我的宗教信仰,我可能会不假思索地对当地从未听过这种字眼的人,说出‘道家二字。”在儒家和道家的文化思想中,道教文化思想对林语堂的影响最为巨大。
他总结出老子的全部哲学是以柔弱的教义为基础,大自然的水虽是柔弱的、趋下的,但它无孔不入,无坚不摧,因此也就最有力量,也最长久,几近于道家的“道”。所以林语堂对老子的不斗、不争、不抵抗思想颇感兴趣。老子强调柔弱的力量,居下的优势和对强力的不信任也促使林语堂反对竞争,反对武力征服观念的形成。而且老子的告诫“不可为天下先”也使林语堂明白了争论之无益,坚信老子的做人观念:“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他对道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庄子也给予了颇高的评价。他认为庄子是中国所曾产生的最伟大及最有深度的哲学家,认为庄子深具宗教性的崇敬生命,他与灵魂及永生、存在的性质等问题缠斗,他洞察本体的问题,他是严格的一元论者,他觉察到且能表现出人生难以忍受的内在不安,他关注灵性的宇宙的问题,这些和耶稣及基督教是那样的相似。
总之,在道教的影响下,林语堂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道家生命观和人生观:宇宙周而复始的学说———所谓生命,乃是一种不断地变迁,交互兴盛的现象。因此人不应为生死观念所困扰,不应为生死所带来的哀乐情绪所束缚,应超脱生死,以博大的心境与开放的心灵去迎接人生的境遇。
二 “一波三折”的基督教情结
在“亲情似海的基督教家庭”的熏陶下,林语堂自然地成了一名基督徒。幼年的林语堂自然快乐而单纯地信仰着基督教。这时对其影响较深的是基督教义中的人道主义、平等思想,尤其是男女平等思想。
如果说林语堂早年是因为家庭尤其是父亲的影响被动的选择了信仰基督,那么在他历经“异教徒——基督徒”这两个阶段完全是自己的主动选择。进入圣约翰大学期间,林语堂涉猎极广,大量吸取社会学,伦理学,自然科学等学科知识,广泛地接触了西方的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这使他对西方文化产生浓厚兴趣,从而影响其人生道路的择定。知识的丰富,也为林语堂思考宗教间题提供了理论基础,为他对上帝基督质问提供了武器。他开始以全新的视角来阐释其基督教观。进人清华教学以后,在与学者文人交往后,林语堂日益感到自己国学的医乏,认为几年的教会教育使他被骗去了民族遗产。于是重捡其搁下许久的国学,进行中国传统文化“补课”。此后学术生活中,由于日渐接触了许多佛教、道家和儒家学说,林的思想又掺人许多杂色分子。自然地开始了他异教的信仰之旅,如他自己所描述的那样:“我曾在甜美、幽静的思想草原上漫游,看见过某些美丽的山谷;我曾住在孔子人道主义的堂室;曾爬登道山的高峰且看见它的崇伟;我曾瞥见过佛教的迷雾悬挂在可怕的空虚之上;而也只有在经过这些之后,我才降在基督教信仰的瑞士少女峰,到达云上有阳光的世界。”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林语堂曾走过一条探讨儒、道、释三家宗教哲学核心内涵的道路,在这期间有过种种惊诧、困惑、犹豫、仿徨、失望和灰心。最后,终于在基督发出的“威严的大光”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五十年代再度皈依基督教,宣称他的搜寻已告终结。虽然林语堂一再声明:“在儒家、道家及佛教中,我首要关切的是人的灵性问题,及这些可敬思想系统关于宇宙及人生哲学的见解;我最关心生命的理想及人类的品性。”虽然他一再解释他并不想把儒、道、佛三教与基督教作一简单的对比,可是先人为主的基督教观念决定了林语堂必将不遗余力地去发掘中国传统的儒、道、释思想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思想相融合之处。虽然曾在中国传统的儒、道、释三教中游历过,并自称“异教徒”,但他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异教徒,恰如他的挚友徐舒在《追思林语堂先生》一文中所说:“在语堂渊博的中西文学修养中,他最读得精熟的还是圣经。这似乎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他这一点,他的心是贯穿着基督教的精神,因此尽管有许多种不同的思想与趣味,无论是老庄或孔孟,苏东坡对他的吸引,他只是赞美与欣赏而已,他一直没有违离基督教教育所给他的道德世界。”这可谓是对林语堂的宗教信仰最为恰如其分的概括。
三 宗教情怀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文学作为人的心灵和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关注灵魂,守望灵魂,构筑人生信仰,这无疑是它的终极使命。从文学与人生的审美联系上说,文学对信仰的表现,也就是文学对人生的一种永恒把握的表现;文学对于人生信仰的建构,必然要涉及到文学与宗教的关系。周作人于1921年在《圣书和中国文学》中强调,“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才是最高尚的艺术”。虽然他的观点不一定完全正确,但却指出了文学、艺术与宗教的密切关联。文学一个关键的作用就在于它能激活人的情感、抚慰人的心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与宗教意识相通了。宗教情怀不仅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更重要的是使文学创作具有一种充满博爱精神的情思。从思想内容上说,其间总是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气质,一种充满着对不幸的人生、不幸的人们的关爱之情。
宗教情怀而不是宗教形式,对人世生活不可或缺。这一判断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现代作家林语堂,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有些作品不能让人首肯,原因并不是因为宗教,而是因为他与主流创作倾向并不完全一致。现在人们能够正视作家与宗教的关系,是在摒除了某些思想意图之后才能实现的。宗教宗教情怀包含了许多社会一般伦理意识,而这与时代主流意识、政治伦理有差别,因此在某些时期具有宗教意识、蕴含宗教情结的作品不被人们重视。如今,重新解读林语堂,在我看来形式尽管不同,但价值指向还是那个人生终极关怀的问题。而这其中又与创作者的宗教情怀是密不可分的。
1.对宗教经典书籍文本资源的借用
林语堂复杂的宗教情怀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多方面的资源,包括创作素材、创作理念乃至包括人格气质的熏陶和培育。道教经典著作及老庄哲学和基督教《圣经》中的语汇、思想丰富了林语堂作品的想象空间,增添了几许飘逸、空灵和述说的亲和力。宗教语汇在林语堂的作品中频频出现;基督教中的神、祈祷、耶稣、上帝、天国、圣乐、圣父、圣子、阿门、十字架、受难的基督等宗教文化意象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其笔端冒出。林语堂对《老子》、《庄子》和《圣经》烂熟于心,因此,这些语汇与意象能够信手拈来,与文章水乳交融。
其次,林语堂还创造性地借鉴了《庄子》、《圣经》独特的叙事手法。宗教面对的是广大的普通民众,出于扩大影响的目的,一般都非常重视利用栩栩如生的故事来传播教义。林语堂的散文具有尺水兴波的结构美,趣味性强,行文平易,开拓了一个闻所未闻的新空间,适合各个年龄的读者。他的作品叙家常、论国事、谈风景、说美食等,虽不见上帝,不论道,但其中灌注着作者对生活的宗教性体验,显示着作者观察生活的宗教式思维特征,使作品具有一种意境深远、典雅精致的韵味,其中的滋味也更耐人咀嚼。
2.自由的个人主义
六十年代,台湾即有人指出:“论思想,语堂先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论文章,语堂先生是一个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在求无滞无疑,个人主义在求独立独行。”实则自由主义乃其文化姿态,个人主义乃其文化理想。先中后西的文化教育的特殊性和生活在闽南地域文化圈的特殊性是造就林语堂独特文化个性的重要原因。林语堂明确以自由个人主义来表达自己的文化观念,以核心的“儒道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与西方既定文化伦理相对照,通过个人文化趣味与文化感悟,阐发中国传统文化伦理的人文价值及其对应于社会文化选择的个人文化特质,倾注自己的文化寄托。《生活的艺术》一书,作为林语堂自我人生哲学的诠释,是一个面向传统,回归心灵的现代人生活的写照,即他所谓“一种私人的供状,供认我自己的思想和生活的经验”。站在一个现代人的立场而与白居易、苏东坡、李蛰、袁枚等古代人物谈笑论道,实则是一种自由个人主义人生观念的充分展示。
林语堂将自由的个人主义文化观诉诸文学的表现全在于展现自我的个性,探究人类心灵世界的奥秘,创作属意于自己性灵特征的文学典型。在《京华烟云》中,林语堂赋予主人公姚木兰“艺术”化的生活体验:作为“道家的女儿”,她面对现实,处变不惊。十岁随家人外出避乱,只身落人企图拐卖她的义和团散兵游勇之手,为避祸知道乖乖听话。由道家门楣嫁人官宦曾家,她相夫教子,做事周全,把对孔立夫的爱的浪漫情怀寄托于对家庭生活的珍重。作者通过姚木兰与小说中的孙曼娘形成对比,以体现其道家世俗理想。一方面,在曼娘身上传统伦理道德中各种禁锢人性的东西相互作用使她隔离于现代生活氛围;另一方面,在木兰身上,伦理与人性的矛盾和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冲突,都偏离了它们本来的对立地位,而以顺应自然的个性相调和,造就其独具特色的性灵之美。这正是林语堂站在自由个人主义立场上贬儒崇道的结果
经历了生命的坎坷历程,林语堂对待生命的态度达到了一种更高的境界,他已非常自然地把一己情感融入多元的文化背景中,又从宗教文化的多个层面超脱出来,形成一种丰富而又融合的思想体系。
文学或多或少,或大或小,都是要阐述着人生的一种境界。这个境界是我们要借鉴的。无论是古人和今人,是中国的儒、佛、道、禅,还是国外的宗教、哲学。宗教情怀对于当代文学的发展有许多挖掘的地方。对西方文学中国作家不必盲从或仿制,因为思维方式不同,形成的技巧也不同,而通往人类贯通的思考的境界最终都是殊途同归。作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林语堂,他能将西方基督教文化和中国传统儒道文化糅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独特的境界,这对于中国作家也是一个启发。
【参考文献】
[1]林语堂著《信仰之旅》,新华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2]林语堂著《林语堂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
[3]林语堂著《人文主义回到基督信仰》,《林语堂文选》(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8月第l版
[4]林语堂著《从异教徒到基督徒》,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90.
[5]林语堂著《生活的艺术》,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
[6]施健伟著《林语堂在海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1992年
[7]王兆胜著《闲话林语堂》,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