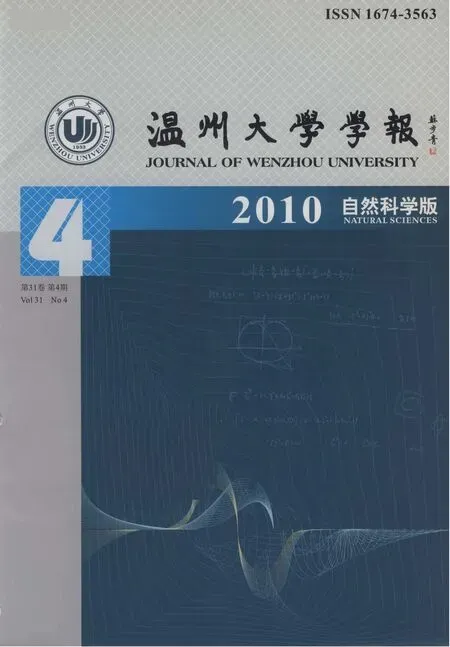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理解与适用
刘 倩
(苏州大学法学院,江苏苏州 215006)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理解与适用
刘 倩
(苏州大学法学院,江苏苏州 215006)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具有人权保障、国家责任、控辩对等和国家刑事政策方面的依据,它是解决刑法中事实不明时的裁判规则,它有别于罪刑法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和择一认定原则,具有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的性质.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在有根据的合理怀疑和控诉方履行举证责任后案件事实仍真伪不明的前提下,在判断犯罪是否成立、处断犯罪的罪数、断定犯罪的效果、追诉时效以及法律解释存疑时有其适用空间.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理论依据;性质定位;适用空间
作为一条刑事司法原则,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是指在适用法律和认定案件事实存在模糊之处时,应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结论.即在一个具体的刑事诉讼中,当出现对法律理解的不一致,或者案件事实的证明过程中出现不确定的因素时,应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或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认定[1].目前,学术界对此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该原则在实体法层面上不仅涉及实体犯罪事实的认定,而且涉及刑法条文的解释,并将之与无罪推定和选择确定等原则相混同[1-2],也有学者认为,“‘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不是一项普遍适用的刑事司法原则,将该原则不加区分地扩大适用到刑法领域是错误的.”[3]本文拟对此原则进行初步梳理以作澄清.
1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理论依据
当实体犯罪事实的认定出现难以解决的疑问时,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只允许司法者做出有利于被告的选择,其理论根据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1.1 人权保障根据
刑法兼具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两大机能.刑法的法益保护是指通过禁止与惩罚侵犯法益的犯罪行为,从而使法益免受侵犯;刑法的人权保障则是指通过限制国家的刑罚权从而保障行为人个人的权益.刑法的人权保障的机能,主要是通过罪行法定得以实现的,因为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对被告人的任何不利选择都于法有据,从而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与自由不受法外剥夺.由此,刑法不仅成为善良人的大宪章,而且是犯罪人的大宪章;刑法在给犯罪人带来不利选择的同时,也保障了犯罪人的权益.显然,立足于社会需要的法益保护与着眼于个人需要的人权保障之间存在冲突,需要进行平衡与协调.协调的结果,就是在保障人权的基本前提下追求法益保护.以此为出发点,在刑事司法中,法官只能以充分证据证明的事实作为定案的根据,不容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没有完全被证明的事实对被告人产生不利的后果.因此,在案件事实存在疑问时,只能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
1.2 国家责任根据
在刑法适用上发生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存在实体意义上的有利于被告的问题.刑法适用产生疑问,无论是因为刑法没有明文规定还是因为刑法规定矛盾抑或是刑法规定模棱两可,都是立法不完善的结果.立法的不完善,是由于立法者的疏漏或过失.因此,刑法适用上所遇到的任何疑问,理应由立法者来承担责任,而不应由公民来担当立法不完善的后果.民法上关于格式合同的解释原则富有启发意义,按照民法上解释格式合同的规则,当格式合同的接受方与提供方因为格式合同条款的疏漏或模糊等发生争议时,应该采纳不利于格式合同的提供者的解释.刑法虽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格式合同,但其与格式合同颇有相似之处.如果在刑法适用发生疑问时,其责任只能由制定方来承担,以体现国家责任意识.
1.3 控辩对等根据
被告人在强大的国家追诉机关面前,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国家追诉机关的侦查能力、强制措施与执行能力远远胜于被告人的辩护能力、防御措施与保护力量,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强化、提升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使其能运用以辩护权为核心的各项诉讼权利与国家追诉机关的控诉行为相抗衡,是公平正义原则的必然要求.因此,任何一项对罪责事实的合理怀疑,均成为阻碍该有罪判决的理由.被告人无需为自己无罪加以证明;相反,控诉方必须证明被告人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以特定的方式实施了特定的犯罪行为方可证明其有罪.如果国家追诉机关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不能达到排除人们合理怀疑的程度,案件事实仍然真伪不明时,只能作出对被告人有利的认定.
1.4 刑事政策根据
在我国,刑事政策不但构成刑法的立法指导思想,而且在刑事司法领域也时有体现.存疑有利被告原则,与现行“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判可不判的不判,可杀可不杀的不杀”的刑事政策不谋而合.无论是“可捕可不捕”、“可判可不判”,抑或是“可杀可不杀”,都是从案件事实与刑法规定得出的结论,而“不捕”、“不判”与“不杀”是对被告有利的选择,这与“存疑有利于被告”不但貌似,而且神合.既然如此,“有利被告”虽然是一个外来语,但因其与我国的刑事政策相吻合,不存在“排异反应”或者“水土不服”问题,易于为我国司法者所接受[4]180.
2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定位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可以从实体法与程序法两方面向来理解.从实体法方面而言,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补充了实体法的罪责原则.根据罪责原则,有罪始有责,唯有有罪责的被告才应该被处罚.司法实践中,法官只有先确认被告的犯罪事实,才能据此适用法律为有罪判决,进而科处刑罚;反之,如果作为适用实体法的事实基础有疑问,而法官仍据以为有罪之判决,该项判决为违背实体法则.从程序法方面而言,本项原则补充了诉讼法的证据评价原则.被告之罪责本来应在合乎诉讼规则的程序中被证明,但是,法院若于调查证据程序之后,法官依照自由心证仍然无法形成对于被告罪责的确信时,应做出对被告有利的认定.因此,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虽然不是自由心证原则的一环,但却补充了自由心证原则之运用.一言弊之,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是指法官在未能形成确信时应如何判决的裁判法则.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该原则的性质定位是:“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并不是用来指导法官如何评价证据并形成其确信,而是规范法官当最后仍然不能形成完全的确信之时,应该如何裁判的规则.这里所称的‘最后’,是指法官依法践行审判程序并调查证据之后,依照自由心证原则综合评价所有‘出于审判庭的证据’后,对于被告犯罪事实仍然无法形成法官个人的确信时.此时,依照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法官应为对被告有利结果之认定”[5]147-148.
2.1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有别于罪刑法定原则
“从当今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早期的绝对罪刑法定原则已受到了各种挑战,代之而起的相对罪刑法定原则已成为各国刑法改革的重要成果和发展方向.相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之一就是一定条件下适用有利于被告原则”[6].1997年我国《刑法》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原则之一加以确认,明确性原则是罪刑法定原则所派生出来的原则之一.所谓明确性,是指规定犯罪的法律条文必须清楚明确,使人能够清楚了解违法行为的内容,准确地确定犯罪行为与非犯罪行为的界限,以保障该规范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会成为该规范适用的对象.“罪责之所以能够确定并予以适当承担的原因就在于确定的不法行为的存在.违法性的行为能够确定,就承担罪责,反之不能确定就不能承担罪责.重的违法性行为不能确定而只能确定轻的违法性行为,就只能承担轻的罪责.”[7]在这里,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正好补充了明确性原则,因此,可以认为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虽有别于罪刑法定原则,但它是相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应有之意.
2.2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不同于无罪推定原则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与无罪推定是刑事法上两个重要的原则,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①学术界有将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与无罪推定原则等同看待者, 也有将前者视为后者的效果或是核心内涵者,也有持两者间虽然有一定的关联性, 但是仍然不能等同看待的立场者..笔者认为,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与无罪推定原则是密切联系的.一方面,两者都是在反对封建专制诉讼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都体现了对人权的保障.无罪推定原则是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思想源泉.另一方面,按照无罪推定原则,任何人在被证明有罪之前,应当被推定为无罪.当控诉方没有将其指控证明到法定的程度,仍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则法院不能否定无罪的推定而只能对被告人作出无罪判决,即罪疑从无.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是无罪推定的必然要求.
但是,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与无罪推定原则并不是完全等同的.无罪推定原则是指每个人在受到有罪判决之前均应被推定为无罪,也就是在确定的有罪判决之前不能将被告作为罪犯对待.由此可知,无罪推定只是个假设性的审判前提,与如何设计审判规则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无罪推定并不指导法官如何作出有罪判决,而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如前所述是一项裁判规则.因此,在这一点上很难说无罪推定可以“推出”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综上,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与无罪推定原则并非处于同一层次,针对的问题也有所不同,虽然有密切联系,但不能互相取代.
2.3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与择一认定原则有区别
所谓择一认定,也称选择确定,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若司法人员极尽一切事实上以及程序上所允许的证明方式,仍无法将案情事实完全厘清,只知道被告所为的事实经过,仅存有两个“非此即彼”的可能性,而分别可能符合两个刑罚构成要件,若构成其中一个,即排斥另一个,但总是构成一个,绝对没有无辜的可能.此时,若该列入考虑的上述二个以上犯罪构成要件彼此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时,司法人员可以基于多选择的事实基础,对被告处以较轻的有罪判决.择一认定,在诉讼法上极易与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混淆.先看一案例[4]179:
在被告人处发现一被从物主处盗窃的首饰.该受盗窃罪指控的被告人辩解说,首饰是从一陌生人处买来的;购买赃物符合窝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不可能对犯罪事实作其他解释.被告人要么实施了盗窃行为,要么实施了窝赃行为.
上述案例中,盗窃罪与窝赃罪处于择一认定关系.如果适用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被告人既不得因盗窃,也不得因窝赃而受到裁判,而应当宣告无罪,因为就盗窃和窝赃这两个行为本身而言,没有哪一个行为得到证实.这种分离的观察方法对于事实情况而言是不公正的.“为了避免违反公平正义的无罪判决,选择确定理论允许法官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就处于选择事实间关系的案例,判处被告择一且较轻的罪名(如案例所示之收受赃物罪).所称‘一定条件’,是指不同的可能事实之间,并不处于高低轻重的关系,而是处于‘择一性’(非此即彼)的关系”[5]173.
“选择确定理论,在于刑事政策的考量,以免因为‘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而导致过于泛滥的无罪判决.因此,德国通说认为选择确定可以说是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例外.”[5]173-174正如有学者理解的那样,“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是为了避免让行为人负担不应该的有罪判决,“择一认定”是为了防止不当的无罪判决,因此在同一个案中不可能发生同时适用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以及择一认定的结果[7].
3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适用
我国现行立法中,对存疑有利于被告这一原则未进行明确规定,直接影响到对被告人的权利保护和程序正义的实现.构建适合我国的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规则,不仅可在程序操作中切实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充分行使,加强其诉讼主体的地位,还可以增强刑罚权行使的正当性.
3.1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之适用前提
实体法适用前提——有事实根据的合理怀疑.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适用于存在事实疑问的案件,但并非在任何事实存在疑问的情况下都可以适用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因为任何与人为的事务有关并且依赖于人为的证据的东西都容易存在可能的或想象中的怀疑,所以只有存在有事实根据的合理怀疑时才适用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所谓有事实根据的合理怀疑,应当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合理怀疑的构成依据是客观事实,而非随意猜测;换言之,提出怀疑是基于证据,而不是基于纯粹心理上的怀疑.第二,合理怀疑的判断标准是理智正常且不带任何偏见的一般人的认识.第三,合理怀疑的成立标准是证明有罪证据尚不确实、充分;换言之,如果有罪证据已经确实、充分,那么合理怀疑是不可能成立的.”[8]
程序法适用前提——控诉方履行举证责任后案件事实仍真伪不明.“在刑事诉讼中,绝大多数罪名的举证责任由控方承担,控诉方必须向法院举出证明犯罪事实存在之证据.如果举证义务人未能履行法定的举证义务,裁判者有权依据客观的证明责任作出对其不利的判决”[9];如果公诉方的证明未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裁判者有权驳回公诉或作出无罪判决,而不得“疑罪从挂”将案件久拖不决,更不得在无证据或证据不足情形下而判决刑事被告有罪[10].
另外,法官面对的仅仅是纯粹的法律争议问题时,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可有条件地适用.
3.2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之适用空间
第一,判断犯罪是否成立时,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有一定的适用空间,即犯罪成立要件之相关事实,适用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所称“犯罪成立要件”除了刑法分则上各该罪名之特别构成要件要素之外,尚且包括刑法总则所称的犯罪成立要件,亦即,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以及刑罚排除事由、刑罚解除事由等等.再者,许多罪名之成立,是以特定的身份为前提.如贪污罪,有关主体的要求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这些特定的实体事实直接关系到应成立何种罪名及如何处罚的问题,如不存在实体事实就不构成该犯罪,因此犯罪成立要件之相关事实存在时,有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适用的空间.
第二,处断犯罪的罪数时,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也可适用.如果关于犯罪单数或犯罪复数的事实认定有疑义者,也有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之适用.如甲因怀疑乙偷了自己的财物强行搜查了乙的住宅,并窃取了乙家的东西,法官穷尽调查仍不能判定甲究竟是为盗窃而强行搜查乙处还是在搜查过程中才临时起意.如是为盗窃而强行搜查则二者构成牵连关系从一重处断,如果是临时起意则应数罪并罚.依照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应认为行为具有牵连性定为一罪.一般情形下认定一罪轻于数罪是有利于被告人的,但是如果数罪并罚的结果更轻反而应该适用数罪.
第三,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在判断犯罪的效果方面也有运用的空间.关于犯罪的法律效果,包括狭义的刑罚以及保安处分在内,只要是科处该法律效果的前提事实有所疑问,都应适用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就狭义的刑罚部分,包括各种刑罚之量刑与处罚,诸如缓刑、累犯、易科罚金等等.受特别预防理论的影响,有许多刑罚与保安处分是以“某种”预测为前提的,例如,我国刑法中的假释制度,“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是假释的实质性要件,这也是一种预测.预测是对未来可能性的推测,未来是高度不确定的,存有疑问应是常态,但是预测必须要有依据,也就是过去或现在的某种事实基础,如果对此种事实基础无法确认,即应适用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作出对被告有利的认定.
第四,对于追诉时效问题,通常也认为应适用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做出对被告人有利的判断.一般说来,程序事实在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下无适用余地,不过追诉时效是一个介于实体刑法和诉讼法之间的法律制度,追诉时效直接关系国家刑罚权的存在与否,时效完成,国家刑罚权归于消灭,也就是实体法上的刑罚权已不存在.因此,当时效经过与否的事实到最后仍无法确定时,就应适用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不再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第五,对于法律存疑且结论为复数时,应适用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在法律解释存疑时,在适用目的论解释的前提下应受文义解释的限制.对于法律存疑,是否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解释,理论上大多持否定态度.台湾学者林山田教授认为:“对于法律问题因见解不一而有所怀疑时,则无罪疑惟轻原则之适用,法院并不能就有利于被告之方向,从事认定,而应选择正确之解释,以适用相当之刑法条款,定罪科刑.”[11]张明楷教授也认为:“当各种解释方法得出不同的解释结论时,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目的论解释,而不是有利于被告.如果说解释目标是有利于被告,则意味着只有缩小解释是可能的,其他解释方法都得舍弃,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当出于法益保护的目的,需要对刑法条文作出必要的扩大解释时,即使不利于被告人,也适用这种解释结论.”[8]
尽管我们总是希望通过解释来解决刑法规定及其适用中的疑问,但围绕刑法规定及其适用的分歧或争议往往客观地存在.只要存在“解释不清”的刑法条款,只要有凭解释消除不了的法条疑问,在刑法适用上便总会有“难以解决的疑问”,因而可能并存着不利被告与有利于被告的两种选择的竞争,从而给有利于被告原则留下了贯彻的空间.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法律存疑,并非是适用法律出现疑问时立即以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为根据作出有利于被告的结论,在确定法条的客观的可能含义范围后,首先要进行论理解释,以分析法条与事实之间的对应关系.当结论为复数的时候,可以根据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作出有利于被告的结论.
[1] 时延安. 试论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J]. 云南大学学报: 法学版, 2003, (1): 39-44.
[2] 邱兴隆. 有利被告论探究: 以实体刑法为视角[J]. 中国法学, 2004, (6): 146-154.
[3] 张兆松. “刑法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质疑[J]. 人民检察, 2005, (6上): 51-54.
[4] [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 托马斯·魏根特. 德国刑法教科书[M]. 徐久生, 译.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
[5] 林钰雄. 论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C] // 林钰雄. 严格证明与刑事证据. 台北: 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02.
[6] 李苗苗. 实体刑法视野下的“有利于被告”原则[J].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06, (9): 100-102.
[7] 陈珊珊. 论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J]. 法律实务, 2007, (2): 104-109.
[8] 张明楷. “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的适用界限[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2 (1): 54-63.
[9] [德]莱奥·罗森贝克. 证明责任论[M]. 庄敬华, 译.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 45.
[10] 陈珊珊. 论“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原则下刑事被告之举证负担[J]. 法学论坛, 2007, (6): 82-87.
[11] 林山田. 刑法通论[M]. 台北: 台湾大学法律系, 1998: 44.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Principle of Favoring the Accused when in Doubt
LIU Qian
(School of Law,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China 215006)
The principle of favoring the accused when in doubt, whose theoretical basis ar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equality between prosecution and defense and national criminal policies, is a judgment rule in settling non liquet case in Criminal Law. The Principle, which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principle of legality, the principle of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and the principle of “Wahlfeststellung”, has features of substantive law and procedural law.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he facts are still unknown after some solid and reasonable doubts and that the prosecution has conducted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of, the principle is applicable to judge whether there is a crime, award the number of crime, affirm the effects and the limitation of prosecution and explain the law when it is inexplicit.
Principle of Favoring the Accused when in Doubt; Theoretical Basis; Identification of Feature; Range of Application
D925.2
:A
:1674-3563(2010)04-0033-06
10.3875/j.issn.1674-3563.2010.04.007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朱选华)
2009-11-12
刘倩(1986- ),女,江西吉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诉讼法学
——以“被告人会见权”为切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