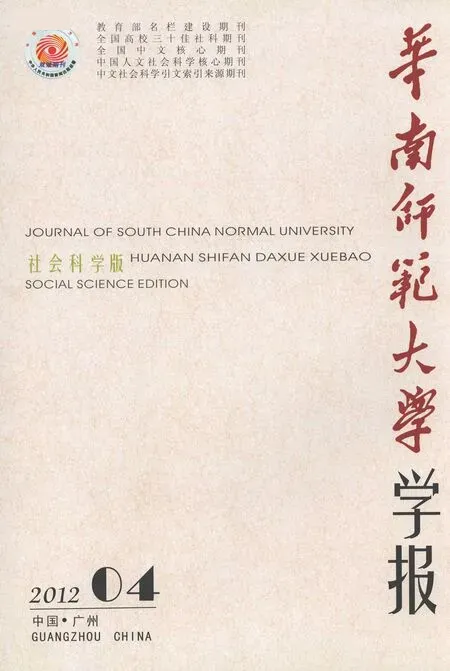从社会角色看唐代文馆文士与文学之关系
吴 夏 平
(1.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100871;2.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01)
从社会角色看唐代文馆文士与文学之关系
吴 夏 平1,2
(1.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100871;2.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01)
唐代文馆系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等文化馆所的统称。各馆文士因所从事职务的不同,社会角色内涵和规定性也彼此相异。文馆文士或在朝或在野,朝野之间的迁转促使文人地域空间流动。因此,从社会角色这个特定角度来考察文馆文士与文学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展开:一是文士群体共相,二是文士角色流动。通过对文士社会角色的研究,以期引起对唐代文士群体性和流动性的进一步关注。
唐代文馆文士 社会角色 群体共相 角色流动 唐代文学
近年来,学界多运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来从事文学研究。多学科交叉往往能激发观察事物的新视角,从而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唐代文学研究同样如此。学者多关注文人空间分布、社会阶层、作家性别、文化生态等与文学的关系,对唐代文学有了更多新的认识。对于任职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等文化馆所文士的研究,则多从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层面展开。本文拟借鉴社会角色理论,从文士角色规定性和流动性等方面来考察,揭示文馆文士与唐代文学演进的内在联系。
一、问题的提出
“文馆”到底指什么,关涉到研究对象的确立,研究者的表述不尽相同。正史所记,无一统摄性确定概念,而仅出现于专有名词之中,如弘文馆、崇文馆之类。两《唐书》有“三馆”一词,如《旧唐书》卷八十八韦嗣立上武则天书云“三馆生徒,即令追集”①刘昫等:《旧唐书》,卷八八,第2867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新唐书》卷十四“三馆学官座武官后”②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一四,第355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但此“三馆”当指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三个学馆,与文馆概念相去甚远。
较早关注文馆的是日本学者池田温。他认为唐代学馆之盛,中古所未见,而学士荣誉,尤著于青史。唐朝官制,政府图书之署有秘书省,国史编纂之府则有史馆,而教授学生之学校亦有国子监及州、县学。其外更有馆院之设,可谓备矣。唐朝馆院,名称屡改,兴废不常,其名目大致有文学馆、弘文馆、崇文馆、崇玄馆、广文馆、集贤院、翰林院。③[日]池田温:《唐研究论文集》,第190-19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照池田温氏的说法,文馆的范围是很大的,举凡掌管学艺、庋藏图籍、教授生徒、政治辅弼之机构,概应纳入文馆范围。
李德辉认为文馆似不应包括秘书省、史馆、国子监:“两汉以降各王朝政权都以‘尊儒重学’为名,在掌理图书的秘书省之外设置了各种名目的‘馆’,主掌图籍的校理编撰与生徒教授等事,以其多从事著撰文史等务,且馆中所聚都是文人,故统称文馆。它虽然属非常设性文化机构,但其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发挥作用之大,却是一般秘书省、史馆、国子监等文化机构所无法比拟的。”④李德辉:《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之关》,第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这样就将文馆与常设性机构区分开来。
笔者认为,文馆概念所指,是与论题的选择密切相关的。研究者所关注的对象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对文馆的界定大可不必相同。本文认为,从宏观通照的角度,可将文馆界定为与文化建设和文学发展联系较为密切的馆所,包括国子监、史馆、秘书省、崇文馆、弘文馆、集贤院、崇玄馆、广文馆等文化机构。正是缘于所解决的不同问题,其所关注的对象也不一样。如罗时进《唐诗演进论》、李福长《唐代学士与文人政治》、聂永华《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等,均从研究实际需要出发,对文馆有不同的择取。
从文馆研究的历史来看,研究者比较重视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历史学视野,关注文馆制度本身的渊源和流变,着重于制度的梳理和考辨。二是政治学视野,着力剖析文馆文士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三是文馆与文学,侧重于文馆制度与文学嬗变、文士唱和与诗体发育等方面。面对已有成果,笔者认为文馆研究空间的拓展,主要还有赖于思维方式的转变和研究视野的开拓。选取文士社会角色作为切入点,其价值和意义主要有三方面:其一,吸收前人成果,推进并深化文馆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改变过去的研究格局和研究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学术史价值。其二,以现有研究成果为基础,借鉴社会学理论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力图还原文馆文人与唐代文学演进的历史原貌,系统化现有成果,同时也是对学术方法运用的检测,具有方法论意义。其三,学者热衷于从空间分布、科第出身、文化背景等层面来研究文士,对于文士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则关注不够。因此,从文士社会角色变迁来考察文士精神风尚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
二、文士社会角色
根据社会学角色理论,社会角色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规定性表现角色和开放性表现角色。前者的权利和义务均有较明确的规定,承担者不得随心所欲地自由发挥;后者的行为规范没有明确严格的限制,承担者有较多自由发挥的余地。①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第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基于此种理论,文馆文士的规定性角色是指文士所任官职及其承担的职责。比如学官职司教育、秘书省官员负责图籍的庋藏和整理、史官纂修史书等。开放性角色则指社会所赋予的某种荣誉角色,比如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经学家、思想家等。需要注意的是,规定性角色和开放性角色并非截然分开,往往同时集为一体。比如韩愈既担任过国子博士、史馆修撰等职,同时又是教育家、思想家、诗人。这种现象,学界称之为角色叠加或“角色集”,在唐代是较为普遍的。此外,以下两点与文士社会角色内涵密切相关,应予以特别注意。
其一,区分兼职与专职,有必要弄清楚官与职的区别。对于官与职的区分,傅璇琮有较为明确的论断:
官与职的区别,我们还可以举白居易自己所写的一篇文章来作佐证。白居易友人李建,于贞元末、元和初曾为翰林学士,他于穆宗长庆元年(821)卒,白居易特为其作一碑文:《有唐善人碑》(《白居易集笺校》卷四一)。碑中概述李建的仕历,把官、职、阶、勋、爵分得很清楚:公官历校书郎、左拾遗、詹府司直、殿中侍御史、比部兵部吏部员外郎、兵部吏部郎中、京兆少尹、澧州刺史、太常少卿、礼部刑部侍郎、工部尚书;职历容州招讨判官、翰林学士、鄜州防御副使、转运判官、知制诰、吏部选事;阶中大夫;勋上柱国;爵陇西县开国男。这是当时人叙当时事,应当说是可信的。由此可见,如校书郎、左拾遗等是官,翰林学士、知制诰等是职。而凡翰林学士,都须带有官衔。……这是因为,翰林学士本身是一种职务,他必须带有其他正式的官职名称,这样才有一定的品位,一定的薪俸。而同时,不管所带的是什么官衔,他仍在内廷供职,承担翰林学士的职能,并不去做所带官衔的职务。②傅璇琮:《从白居易研究中的一个误点谈起》,载《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此段论述,将官与职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讲得很清楚,有助于加深对唐代文馆文士角色的认识。国子监和秘书省两个机构的官员,均为职事官。史官和弘文馆、崇文馆、集贤院学士均属临时差遣。史官的差遣性质,有学者指出:“无论担任史馆史官的情况如何转变,他们都有其本职事官,平时必须处理日常公务,另拨时间来兼负撰述史书的工作。也就是在其工作之上,增加额外的工作分量,因此,每当修撰国史或实录完成献上时,天子为了体恤、酬佣他们的辛劳与成就,往往颁赐爵赏等以为旌勉。”③张荣芳:《唐代的史馆与史官》,第152页,台湾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4年版。“三馆”学士也都有其本职事官,学士属于临时差遣性质,有时作为荣誉授予有功之臣,多数时间则是为了完成某种特殊工作;当工作完成之后,官员所充任的学士头衔也随之罢去。
其二,文士社会角色是动态的开放系统,主要表现为角色的社会变迁。规定性角色在一段时期内是较为稳定的,但从整个发展过程来看,则又是变动不居的。比如弘文馆学士,在唐初担任着多重职责:“掌详正图籍,教授生徒。凡朝廷有制度沿革,礼仪轻重,得参议焉。”①刘昫等:《旧唐书》,卷四三,第1848、1852、1855页。但在中宗神龙以后,其职责固化为详正图籍和教授生徒,而作为皇廷智囊参政议政的角色逐渐萎缩废弃。主要原因是盛唐集贤院和翰林院的兴起剥脱了其部分职能。再比如著作郎官,其工作性质也发生了从修史到职司碑志的转移。《旧唐书》卷四十三“史馆”:“历代史官,隶秘书省著作局,皆著作郎掌修国史。武德因隋旧制。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始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②刘昫等:《旧唐书》,卷四三,第1848、1852、1855页。被罢去史职后的著作郎主要工作是“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与佐郎分判局事也”③刘昫等:《旧唐书》,卷四三,第1848、1852、1855页。。文士的开放性角色也同样发生着变迁。比如国子监学官,在唐初还主要是以经学家和经师的身份从事教育。中唐以后之学官,像韩愈、吴武陵、欧阳詹、温庭筠等人,已经从经学家转变为文学家。他们与唐初孔颖达、贾公彦等人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三、群体共相与文学
所谓群体共相,是指学士群体共通的基本特征,具有相对稳定性。偏于静态的文士群体共相与文学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三方面:一是文士诗文作品表现出强烈浓厚的角色意识,二是诸馆文士的文学活动各具特色,三是职务的重要性影响文学心态。
其一,文馆文士社会角色意识强烈,主要表现在自我体认和对他者的认同上。唐代诗人都有较为强烈的角色体认和认同意识。以卢纶诗歌为例。卢氏曾以诗评友,诗题详细地罗列出他们的官职:《纶与吉侍郎中孚、司空郎中曙、苗员外发、崔补阙峒、耿拾遗湋、李校书端、风尘追游,向三十载。数公皆负当时盛称,荣耀未几,俱沉下泉。畅博士当感怀前踪,有五十韵见寄。辄有所酬,以申悲旧,兼寄夏侯侍御审、侯仓曹钊》④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二七七,第3145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于此可见唐人角色意识程度之深。文馆文士的诗文作品,同样也体现出这种角色意识。刘禹锡任职集贤学士时,作有《裴相公大学士见示答张秘书谢马诗并群公属和因命追作》⑤刘禹锡:《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陶敏、陶红雨校注,第447页,岳麓书社2003年版。,裴相公指裴度,曾任集贤殿大学士;张秘书指张籍,曾任秘书郎。吉中孚任校书郎职满归乡,李嘉祐、卢纶、李端、司空曙等相聚送行,诗题均作“吉校书”⑥参看《全唐诗》卷二百六李嘉祐《晚秋送吉校书归楚州》、卷二六七卢纶《送吉中孚校书归楚州旧山》、卷二八四李端《冬夜与故友聚送吉校书》、卷二九二司空曙《送吉校书东归》,分见第2151、3124、3235、3322页。。诗歌中特别强调其所任职务,如司空曙诗云:“少年芸阁吏,罢直暂归休。”卢纶诗云:“青袍芸阁郎,谈笑挹侯王。”芸阁即秘书省,“芸阁吏”和“芸阁郎”是说吉中孚曾任职秘书省校书郎,“罢直”指任职期满。从题目到内容,诗作无不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角色体认意识。
其二,诸馆文士群体的文学活动各有特色。不同社会角色不仅在文学创作上存在差别,而且对文化和文学传承革新的使命感以及由此造就的文学思潮和思想氛围也是有区别的。比如国子监的主要职责是教授生徒,但教育总是与科举考试相联系的,在“诗赋取士”风气影响下,学官不仅要传授经术,而且还要教导诗歌创作。史官的主要职责是修撰前代史和当朝实录,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对社会易持批判态度。如唐传奇作者模仿史传的叙事传统,往往在小说的结尾处有一段模拟史传论赞的议论,即其明证。秘书省相对闲散,为文士提供了许多活动空间。秘书省图书采集,促进文人地域空间流动。元稹和白居易任职秘书省校书郎期间,创作多与秘书省的特性有关。学士群体的诗歌活动,促进新诗体的发育,推动近体诗律体律调的定型。
其三,职务的重要性影响创作心态。比如唐初秘书省,因无实权而饱受诟病。《太平广记》卷一八七“秘书省”条引《两京记》:“唐初,秘书省唯主写书贮掌勘校而已。自是门可张罗,迥无统摄官署。望虽清雅,而实非要剧。权贵子弟及好利夸侈者率不好此职。流俗以监为宰相病坊,少监为给事中中书舍人病坊,丞及著作郎为尚书郎病坊,秘书郎及著作佐郎为监察御史病坊。言从职不任繁剧者,当改入此省。”⑦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一八七,第1405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所谓病坊者,实为鄙薄之辞。因其非实权部门,故为世俗所不喜。这种情形也直接反映在诗歌创作中。如卢象开元中曾任秘书省校书郎,有诗《赠程秘书》:“客自岐阳来,吐音若鸣凤。孤飞畏不偶,独立谁见用?……顾余久寂寞,一岁麒麟阁。且共歌太平,勿嗟名宦薄。”⑧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二二,第1217页。天宝时期綦毋潜曾官校书郎,但不久即弃官东归。王维《送綦毋潜校书弃官还江东》云:“明时久不达,弃置与君同。天命无怨色,人生有素风。念君拂衣去,四海将安穷。”①王维:《王维集校注》,第222页,陈铁民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这些都反映了校书郎的失意落寞。但这种情况到中唐发生改变,秘书省校书和正字成为士子竞进的目标。杜佑说:“(秘书省校书郎)掌雠校典籍,为文士起家之良选。其弘文、崇文馆,著作、司经局,并有校书之官,皆为美职,而秘书省为最。”②杜佑:《通典》,卷二六,第155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文士的心态与此变化密切相关。白居易在离任十年后再次经过秘书省时,不禁感叹道:“阁前下马思裴回,第二房门手自开,昔为白面书郎去,今作苍须赞善来。吏人不识多新补,松竹相亲是旧栽。应有题墙名姓在,试将衫袖拂尘埃。”③白居易:《白居易集》,卷一五,第301页,顾学颉校点,中华书局1979年版。元稹所作和诗也一同回忆当年情形:“经排蠹简怜初校,芸长陈根识旧栽。”④元稹:《元稹集》,卷二○,第231页,冀勤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在慨叹世事变迁的同时,对曾所任职颇有自豪之感。与秘书省为世鄙薄相对,唐代学士地位相对尊崇,群体心态也较为高涨,在诗文中亦有所表露。如宋之问《景龙四年春祠海》无不得意地说:“三入文史林,两拜神仙署。”⑤宋之问:《宋之问集校注》,卷三,第517页,陶敏、易淑琼校注,中华书局2001年版。对其曾经入直习艺馆、预修《三教珠英》及兼任弘文馆学士之事,津津乐道。开元初集贤学士徐安贞作《书殿赐宴应制》:“校文常近日,赐宴忽升天。酒正传杯至,饔人捧案前。玉阶鸣溜水,清阁引归烟。共惜芸香阁,春风几万年。”⑥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二四,第1227页。亦不无飘飘欲仙之感。总体来看,唐代文馆文士中,学官和秘省官员为闲职,史官和学士群体则相对尊宠,文士的创作心态受所任职务影响甚大。
四、角色流动与文学
文士社会角色流动,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社会阶层流动,主要指职务迁转;二是地域空间流动,主要指地理位置变换。角色流动与文学的关系颇为密切。
第一,文馆文士社会阶层流动。唐代文人的职务迁转,是其社会阶层流动的体现。一般来说,由底层向上移动,五品是一个转折点。因为五品以上官员的职务迁转由朝廷敕授,不再受吏部铨选。孙处约任考功郎中(从五品上)一职,是其社会阶层转变的一个明显标志。文士社会阶层流动,引起创作变化。下面以元稹和白居易为例略加申述。如前所述,元白任职秘省校书期间创作的总体特点是闲适。但在除左拾遗、历监察御史之后,元稹的诗歌风格发生了显著变化。元和四年,元稹任监察御史,曾作《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取其病时之急者,列而和之”⑦元稹:《元稹集》,卷二四,第277页。,是元稹新的创作倾向。白居易在元和二年至元和六年迁任翰林学士,期间的创作亦改变此前风格,尤为关注社会和民生。元和四年所作《新乐府序》径云:“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⑧白居易:《白居易集》,卷三,第52页。元白新乐府诗,一诗议一事。这些关注现实、针砭时弊的诗歌,显然是与元稹所任左拾遗承担讽谏、监察御史负责纠弹以及白居易所任翰林学士的近侍进谏特点有关。由此可见,文士社会角色流动对文学风格变迁产生重要影响。
第二,文馆文士地域空间流动。地域空间流动,主要指文士地理位置的变换。文士空间移动,多发生于京城与地方之间。唐代文士由京城到地方,动因来自于多方面:常态职务迁移,临时差遣,出镇地方使府,文人入幕,贬谪,等。此外,还有其他的流动途径。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模式包括三个要素:移出场、移入场和移动路径。移出场是指人或物移出的场所,移入场是指人或物移入的场所,移动路径是指连接移出场和移入场之间的连线。⑨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第18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文士区域流动对文化交流和文学传播产生重要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诸方面。
其一,从强势文化区移出,势必将先进文化理念输入弱势文化区。所谓强势文化区,主要指长安、洛阳及其周边地区,弱势文化区则是相对于京洛而言的其他区域。如韩愈贬潮州,在兴办教育、改易风俗、传播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始潮之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人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⑩苏轼:《苏轼文集》,卷一七,第509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精确地概括了韩愈的功劳。宋璟由国子祭酒贬为广州刺史,传授当地百姓烧制泥瓦和建筑技术,改善居住条件。①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六,第3032页。阳城由国子司业贬为道州刺史,史书记载的第一件功绩是“禁良为贱”②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二,第5133页。。韩愈、宋璟、阳城的事例,很好地说明了文士空间移动与文化传播的关系。
其二,移动路线和移入场的异地风物,往往记录在诗文中。文士进入异地,多为新奇风物吸引。如耿于大历八年(773)至十一年(776)秋,奉使江淮搜访图书③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第498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途径江西鄱阳时曾作《奉和第五相公登鄱阳郡城西楼》,诗云:“湓浦潮声尽,钟陵暮色繁。夕阳移梦土,芳草接湘源。封内群甿复,兵间百赋存。童牛耕废亩,壕木绕新村。野步渔声溢,荒祠鼓舞喧。”④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二六九,第2998页。展现安史之乱后江南乡村风景,令人耳目一新。沈佺期神龙年间贬逐州,曾作《题椰子树》:“日南椰子树,香袅出风尘。丛生调木首,圆实槟榔身。玉房九霄露,碧叶四时春。不及涂林果,移根随汉臣。”⑤陶敏、易淑琼校注:《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第121页,中华书局2001年版。写他从北方来到南方后的惊奇感受。元稹在通州(今重庆通县)曾作诗赠白居易,云:“平地才应一顷余,阁栏都大似巢居。入衙官吏声疑鸟,下峡舟船腹似鱼。市井无钱论尺丈,田畴付火罢耘锄。此中愁杀须甘分,惟惜平生旧著书。”于“阁栏”句下自注:“巴人多在山坡架木为居,自号阁栏头也。”⑥元稹:《元稹集》,卷二一,第236页。真实地记录了古代巴人的巢居习俗。游记散文方面,最典型的当然是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这些记载异地民物风情的诗文,在流传过程中就自然地发挥“诗可以群”的功能,自觉地传播地域文化。
其三,移入场的文士雅集,形成较有影响的区域文化和文学中心。天宝初,秘书正字萧颖士“奉使括遗书赵、卫间,淹久不报,为有司劾免,留客濮阳。于是尹征、王恒、卢异、卢士式、贾邕、赵匡、阎士和、柳并等皆执弟子礼,以次授业,号萧夫子”⑦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二○,第5768页。。萧颖士到濮阳以后,就形成以他为中心的文学群体。再比如韩愈量移袁州,使得区域文学创作中心的位置更为突出。韩愈与当地文人多有交往,特别是江西使府文人,渐次形成以韩愈为核心,包括府主王仲舒、幕僚王绩、陆畅、卢简求以及吉州司户孟简等人在内的文学中心。
其四,文馆文士不同场域的送别活动促成大量别诗的创作。送别活动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文馆文士作为送行主体,是饯行活动的主动施行者;二是文士作为被送的对象,是饯行活动的受动者。前者可称为文士送别诗,后者则称送文士别诗。每一次祖饯活动,都为送别诗增添新的内容。不仅如此,别诗的创作还有助于诗艺的进一步提升。正如刘禹锡《送王司马之陕州》所言:“两京大道多游客,每逢词人战一场。”⑧刘禹锡:《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第463页。文士的每一次送别,其实都是诗歌写作的集体竞赛。从这个角度来说,送别诗发挥的不仅是“诗可以群”的人际交流沟通功能,在文化传播和诗艺提高方面亦有所推进。
综上所述,从社会角色研究唐代文馆,拓展出新的研究空间,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文士社会角色有规定性和开放性之分,前者主要就职务特征而言,后者则重在社会评价。文士社会角色与文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群体共相和角色流动两方面。文士群体共相偏于静态,通过角色体认、群体特征、创作心态等对文学产生影响。角色流动具有动态开放特征,包括文士社会阶层流动和地域空间转换。文士角色流动在促进区域文化交流和文学传播等方面产生了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赵小华】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ltural Museum Literatus and Literature in Tang Dynasty from Social Role Perspective
(By WU Xia-ping)
The Cultural Museum is the joint name of Imperial Academy,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Literature,Institute for the Vene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other cultural institutions in Tang Dynasty.The Literatus in each Cultural Museum did different jobs,and thus the social role connotation and the rules ar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No matter in court or in commonalty,the move between the court and the commonalty impel scholars'spatial flow.Therefore,from the social role to se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ltural Museum Literatus and Literature,we can examine the content in tow aspects.One is the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and the other is Literatus flow.Through the study on the social role of the Literatus,it can attract further attention to Literatus'group and flow in Tang Dynasty.
the Cultural Museum literatus in Tang Dynasty;social role;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Literatus flow;the literature in Tang Dynasty
吴夏平(1976—),男,江西都昌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研究人员,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2012-03-14
I206.2
A
1000-5455(2012)04-007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