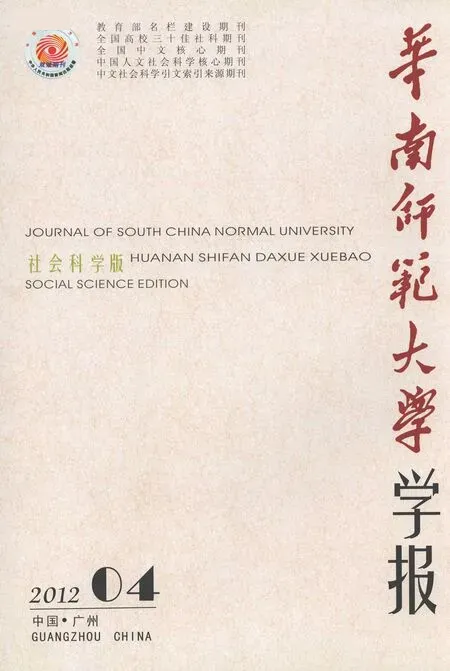关于“财产性收入”的思考
——基于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
张俊山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071)
关于“财产性收入”的思考
——基于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
张俊山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071)
作为财产性收入依据的财产必须具备所有权、数量基础、价值等内涵。财产性收入的主要形式有金融资产、房屋的利息或租金收入和资产本身的溢价收入。财产并不创造收入,只是在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把一定的社会财富吸引到自身来的手段,这些收入的源泉最终还是来自于生产领域的剩余劳动产品。因此,财产性收入只能是社会上一小部分依附于生产经营的人员的收入,不可能作为广大群众获取收入的形式。职工持股这一形式给职工带来财产性收入,这一形式有助于把工人的利益与企业的发展结合起来,调动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但就收入的源泉来说不过是使工人以参股的形式取回自己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产品。财产性收入的源泉、形成条件等决定了,它只能是当前调整收入分配的一个辅助手段。
财产 财产性收入 职工参股 收入分配
在当前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的讨论中,财产性收入常被人们当成改变收入分配格局的一个途径。为了改变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状况,有人提出要通过使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来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的问题,还有人认为收入分配不公是财产占有不公造成,甚至藉此把矛头指向国有资产,主张把国有资产、国有土地变为私人财产,以使人民群众都能获得“财产性收入”。为准确地认识这一问题,必须对于所谓“财产性收入”的本质、来源、依据等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财产与财产性收入
在统计中,财产性收入是指“金融资产或有形非生产性资产的所有者向其他机构单位提供资金或将有形非生产性资产供其支配,作为回报而从中获得的收入”①参阅《中国统计年鉴》中指标解释。。在本文,我们从理论上来研究财产性收入,因此,我们并不处处拘泥于统计机构的规定,而是按照通常理论界和人们一般理解的内容来对待这一概念。
目前,在统计上按照个人收入的直接来源及其依据,将各种形式的收入归纳为四种类型: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按照这样的划分,除转移性收入来源比较明显以外,其他几种不同类型的收入本身看上去好像是来自于各不相同甚至是互不相干的源泉。这种收入分类在收入分配理论研究中的反映就是,不少人致力于论证如何鼓励财产性收入,并主张通过扩大财产性收入来增加普通群众的收入进而缩小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着的巨大差距。同时,在当前社会中,财产性收入已确实成为某些机构组织、社会成员收入的重要来源,在收入分配领域出现的矛盾也常常表现为争夺财产性收入的矛盾。因此,需要深入分析财产性收入,对它有一个清晰、科学的认识,才能准确地了解财产性收入在收入分配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才能确定对于它们的政策态度。
“财产”只是人们日常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概念,并不构成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范畴,它泛指属于作为一定经济主体的个人或组织所拥有的社会财富,它一般表现为被占有的物质产品、土地以及其他一些自然资源及其价值形态。但是并非物质产品、土地等天生就属于财产,它们只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转化为财产。这些条件主要包括:第一,只有在物质产品、土地以及其他自然资源被一定的所有者占有,并使它们的所有者、占有者从中获取特定的经济利益时才属于财产。这特定的经济利益主要是,凭借对它们的占有,它们的占有者有条件现实地或潜在可能地,获得财产本身以外的经济利益。第二,作为财产的物质产品具有相应的量的规定性。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他们所持有的物质资料只有在数量上超出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部分才能属于财产的范围。第三,作为财产都具有存在的持久性。这种持久性可以是物质上的持久性,但更主要的是价值上的持久性。没有这种持久性,它们就不可以持久地存在,更不可以使它们的占有者凭借占有关系获得经济利益。按照以上条件来看,在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符合财产条件的事物最典型的就是资本。在生产领域资本关系的影响下,社会经济中一切具有价值形态的事物,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都要求向资本转化,构成人们通常所说的“财产”。一些本身没价值,但在商品及资本关系普遍存在条件下也具有价格的事物,也构成人们通常所说的财产,如土地、证券等。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财产关系不过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所谓“财产性收入”有两方面来源:类利息收入和资本利得收入。其中,获取资本利得的“资本”又可以通过收入的资本化被创造出来,成为虚拟资本。这样,“创造+升值”促使金融形式的资本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因此,“财产性收入”成为部分人财富迅速扩张的方式。
如果说在人们日常经济生活中所说的财产除包括那些用于价值增殖的物质产品、自然资源、货币等以外,还包括着一些作为使用价值使用和作为贮藏财富形式的物质产品,例如房屋、车辆、家具、首饰等等,那么,当我们研究“财产性收入”时,其中所说的“财产”只能是用于价值增殖手段的物质产品、土地以及自然资源、货币资本等等。因为,作为使用价值和贮藏手段的财富是不能给它们的所有者带来收入的。凡是能够带来收入的财产,必然主要是作为资本使用的财产,土地本身虽然不是作为严格意义上的资本取得收入,但它是以社会上存在着的资本关系为条件,使它们的所有者或占有者可以凭借所有权和占有权获取收入的。因此,所谓“财产性收入”就是以资本关系为基础的收入形式。
但是,财产性收入与政治经济学中所说的资本收入还不完全相同。政治经济学中的资本收入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下的产物,就其整体来说它包括着生产领域工人创造的所有剩余价值。而通常人们所说的财产性收入则是以个人收入的直接获得方式为依据形成的。财产性收入在它普通的含义中,是指到达个人手中的收入,因此,第一,它是剩余价值经过再分配所形成的最终收入形式;第二,它是其获得者通过生产经营以外的出租、出借行为获得的收入形式,因此只包括那些单纯凭借资本关系而不需要财产所有者付出任何努力而获得的收入,如利息、股息、分红、租金等形式的收入。政治经济学中产业利润、商业利润等剩余价值形式被归入了“经营性收入”甚至“工资性收入”之中。
根据以上分析,所谓“财产性收入”本质上是资本价值增殖收入的一类形式,它们以资本关系的普遍化为基础,来源于社会剩余劳动,是作为资本的财产的所有者单纯凭借所有权或占有权所取得的收入。这种以财产性收入为表现形式的收入,只是生产领域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产品的一部分,只是在社会存在着资本关系的基础上,财产的所有者才有可能凭借对作为资本的财产的垄断占有,分取社会剩余产品的一部分。可见,财产并不是创造收入的源泉,而是像马克思所说,作为“一台汲取剩余劳动的永久抽水机”、作为“一块永久的磁石”把社会剩余劳动的一部分汲取或吸引过来的手段。财产性收入不是社会经济中的原始收入,而是通过再分配形成的一类收入形式。
二、财产性收入的运动特征
财产性收入是资本价值增殖关系的普遍化和表面化产物,因此,它带有资本运动的一切表面特征,但是各种具体的财产性收入形式又各自有着自己特有的运动特征。
财产性收入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是通过凭借从物质上或价值上对作为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财产的垄断占有来获取的收入,财产性收入只能源于社会的剩余劳动。取得财产性收入仅仅依据对“财产”的占有,而不需要财产的所有者投入其他的努力,因此,财产性收入是资本关系主导下的财产所有权的实现形式。上面已经提到,对于形成财产性收入的“财产”而言,它们本质上是作为价值增殖手段的资本而发挥作用的,因此,它们都以价值的形式存在,受价值增殖规律的制约。这是所有财产及财产性收入的共同特征。
在当前社会中,形成财产性收入的“财产”具体形态不同,财产性收入的运动又有各自的特有表现。形成财产性收入的“财产”大体有以下几种形式: (1)各类金融资产,如银行存款、各类金融债券、基金、股票等;(2)居民用于出租的房屋;(3)农民暂时不耕种的承包土地等。相应地,“财产性收入”主要包括:(1)各类金融资产带来的增殖额和金融资本本身的溢价;(2)居民出租房屋获得的租金收入; (3)农民转包土地的收入。在上述三种财产性收入中,农民对外转包土地虽然可以获得一部分收入,但是,目前在农村地区出现的农民转包土地现象,主要是由于部分农民需要外出务工或因其他原因自己无法耕种,为不使土地撂荒才将土地转包出去。转包的主要动机并不在于取得收入,而是为了保持自己对土地的承包权。从数量上看,目前农民转包土地的收入很低,每亩每年只有几百元,还不能达到可以支持转包农民生活支出的数量。因此,这部分收入并不构成当前财产性收入中的主要内容。当前,在收入分配中起到重要影响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是上述的前两项。
各类金融资产是个人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来源,它们通过两种方式给它们的所有者带来收入:第一,价值增殖收入,包括银行利息、股息、分红、租金等形式。这些收入虽然直接从形式上看是由“财产”带来的,但是究其本质,它们最终都是来自于生产、流通领域的经营收入,是其中的一部分,归根到底是生产领域劳动者剩余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的一部分。这部分社会财富之所以采取了“财产性收入”的外观,是由于在生产领域存在着可以使价值增殖的社会生产关系,赋予了社会上一切生产条件以资本的属性,因而成为个人收入的直接源泉。各类金融资产的存在是资本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互分离的结果,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在市场经济中货币是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因而它们也就成为从事生产活动所必需的条件的一般代表。货币本身不能创造任何产品,也不能创造收入,但是,在高度发展了市场经济中,它们可以借助虚拟资本这一中介进入生产经营领域。通过控制劳动过程,使它们的所有者能够以价值形式占有一部分社会剩余产品。因此,以各种金融资产形式存在的虚拟资本看上去就成为“财产性收入”的源泉。这类财产性收入在数量上,首先受到生产领域资本的价值增殖能力即利润率的影响,此外,利息率水平对于金融资产的增殖额有着直接的影响,其中,银行利息率直接决定银行存款的利息收入。利息率,就其基础来说,是由市场上货币资本的供求决定的,利息率对生产经营企业的收入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利息率又是国家经济管理部门用来调节经济、引导投资的重要政策工具。利息率以企业利润率为基础,利息率过高会使生产经营企业形成过高的负担,从而抑制生产经营活动。因此,从社会再生产的需要来说,不能通过高利率将企业的利润转化为金融资产的“财产性收入”。
第二,金融资产的溢价收入。各种形式的金融资产(在一定意义上也包括房屋)属于虚拟资本,它们的价格直接由金融市场上的供求决定,但是这种供求并不是普通的商品供求,而是资本的供求。决定供求的因素是资本价值增殖的程度,资本的价值增殖程度高,对资本的需求大,代表资本的虚拟资本价格就会提高。虚拟资本的价格提高就会给其所有者带来溢价收入,这种溢价收入是以持有金融资产为前提的,因此也属于财产性收入的范围。但是,金融资产的溢价并不能立即构成现实的收入,它们产生之初仍是处于观念形态上的收入,只有在金融市场上变现才能成为现实的收入。然而,当金融资产变现后,它们处于货币形态上是不能继续增殖的。虚拟资本同样是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增殖,虚拟资本溢价作为财产性收入的手段就必须不断地处在金融市场上的买卖过程之中。把虚拟资本溢价作为财产性收入的来源,存在着一个障碍,这就是,金融市场并不能创造财富,虚拟资本溢价收入的实现只能来自于其他货币资本的进入,只有不断地有货币资本注入才能保证虚拟资本溢价并实现。事实上,金融市场所起到的只是再分配的作用,通过市场价格的涨落使货币资本从一个人手里向另一个人手里转移。可见,这样的所谓财产收入只是对少数人而言,不可能成为群众普遍的收入来源。进一步说,能够经常进入金融市场推动金融资产价格上涨的,只能是代表着社会剩余产品的那部分货币资本,如果人们能够持续地获取这部分货币资本作为的收入源泉的话,那么也就不必通过金融资产的市场溢价取得收入了。
就金融资产本身的价值增殖额而言,它们也只能是依附于生产经营成为一小部分人的“财产性收入”,而绝不可能成为广大群众获取收入的新源泉。马克思曾经指出:“假如大部分的资本家愿意把他们的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那么,结果就会是货币资本大大贬值和利息率惊人下降;许多人马上就会不可能靠利息来生活,因而会被迫再变为产业资本家。”①《资本论》,第3卷,第424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这段话说明了,利息类的“财产性收入”只能由社会上少部分人在依附于产业资本的条件下获得,不可能扩大为广大群众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收入形式。
房租收入是财产性收入中重要的一类,它是由租用住房者向住房的所有者所支付的费用。这部分费用主要包括如下内容:住房的折旧费用、日常的修缮费用、房屋所有者对住房者的服务费用、真正的房租。在整个房屋租金中只有真正的房租构成所谓“财产性收入”。房屋是人们必需的基本生活资料,表面上看,它来自租房者的工资收入(假定租房者是工薪劳动者),是用劳动力价值支付的。但是,当房租高启超过了住房的折旧费用、日常的修缮费用和房屋所有者对住房者的服务费用时,事实上是通过降低工人的劳动力价值,把工资中的一部分作为剩余劳动,以房租的形式转移给房屋所有者。住房虽然也是一种生活资料,但是由于它在地域上的位置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因此,作为商品它们的价格形成不同于其他作为生活资料的商品,它的价格中包含一定的垄断收入。这部分垄断收入的存在,使房屋价格远远高于由住房自身价值所决定的价格。住房价格影响着房租水平,因此,伴随住房价格的上涨,房租也会相应上涨形成来自住房的“财产性收入”。就其本来意义而言,住房出租可以使暂时闲置的房屋得到使用,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但是,由于房屋价格和房租水平的决定方式,使得住房出租成为无偿占有他人剩余劳动的一种有力手段和便捷方式,因此,住房在社会经济中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生活消费品变成了投资品。当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以后,住房的价格决定就有了新的规律,住房转化成为一种虚拟资本,价格的决定受虚拟资本的定价规律支配,包含了大量金融因素的影响。住房价格和房租水平超出由商品价值规律决定的水平以后,住房就成为一种汲取社会剩余劳动的手段。而且,这种汲取不是发生在商品生产与流通领域,而是发生在生活消费领域,因此过高的房租直接降低着租房者用于生活其他方面的收入。可见,对于广大劳动者而言,住房不可能成为普遍持有的财产性收入手段,房租高启事实上起着压低劳动力价值和攫取产业利润的作用,因此,社会不可能通过住房的方式增加群众的财产性收入。
三、关于以职工持股带来的“财产性收入”
在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讨论中,有人提出通过推行职工持股计划让工人获得财产性收入。黄范章在《推行“财产性收入”大众化 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一文中主张:“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推行这项计划对职工来讲,增加了一笔工资外的福利性收入;对企业来讲可以通过该‘计划’,用企业股份将企业职工的利益紧密地与企业利害融为一体,把职工从劳资关系的对立方变成企业的‘利益攸关者’(stake holder),有助于使企业成为营造‘和谐社会’的‘和谐细胞’。”②黄范章:《推行“财产性收入”大众化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2期。实行职工持股计划,使职工对企业的一部分资产享有所有权,凭借这一权利分享企业相应的利润,增加职工收入的渠道,这确实是收入分配改革的一项有意义的思路。与前述分析的各种“财产性收入”相比,职工持股计划的设想把目光从生产领域以外转向了生产领域以内,使职工有权利分享企业的利润,是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中更现实的思路。
把对利润的分享直接纳入企业内部分配制度,从而形成对传统的工资-利润分配制度一定程度的改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利润分享制度的具体实施形式虽然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其中最基本的内容都是,允许员工按照一定比例分享企业的利润。这一分享有的是直接规定员工在利润中分享的比例,有的则是采取职工持股的方式,获取来自利润的股息和分红。譬如,美国沃尔玛公司于1971年全面实施了利润分享计划。这一计划不仅是对高层人员,而且包括了大部分员工。具体规定为:(1)凡加入公司1年以上,每年工作时数不低于1 000小时的所有员工都有权分享公司的一部分利润。(2)公司根据利润情况和员工工资数量的一定百分比提留。当员工离开公司或退休时,可以提取这些提留,提取方式可选择现金,也可选择公司股票。而公司每年提留的金额大约是工薪总额的6%。该计划发展很快,在1972年,用于该计划的金额是17.2万美元,共128人获益。沃尔玛公司还实行有一个“雇员购股计划”。这个计划通过工资扣除的方式,让员工以低于市值15%的价格购买股票。这项计划从1972年开始实施,属于职工福利,然而又是自愿的。由于公司股票的升值,这一计划使许多员工积累了大量财富。公司约80%的员工有资格参与这项计划。由于还有大约20%的员工要么还不够资格,要么是进公司的时间尚短,不能参与利润分享,所以,沃尔玛还推行了许多奖励和奖金计划,以使每个员工都能像合伙人那样参与公司业务。其中最成功的奖金项目之一就是所谓的“损耗奖励计划”,即公司与员工一同分享店铺因减少损耗而获得的盈利,它较好地体现了沃尔玛的合伙原则。
总的来看,利润分享计划是以工资制度的存在为前提的,工资制度的存在使公司获得的新价值分成了两个部分——工资和利润。但是,在分享制度中,工资和利润只是公司收入分配的最初形式,还不是最终形式。在这个最初形式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原则把利润形式下的部分收入分配给员工,就使传统的工资制变成了分享制。利润分享制度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本质,但是,形式的变化也带来了内容上的部分变化。经典意义上的工资范畴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由于劳动力价值的规定性,使它在一定时期是一个相对确定的量。利润则是随着经营的改善可以增长的一个可变的量。当工人收入的一部分采取了利润分享的形式,就使工人的收入从传统的作为固定量的工资范畴,转变为一个与利润挂钩的可变范畴。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是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里为雇主创造的收入,因此利润的多少与工人在生产中的努力程度、专心程度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利润分享制度使工人的收入与利润的增长相联系,打破了传统工资制度的僵化界限,使工人的收入从一个不变量转化为一个可变量,从而淡化了企业内部劳资收入之间的对立关系,使工人收入增长的对立面从企业内部资方利润转化为企业外部的市场。这样就在劳动与资本之间构造了一种形式上的“合伙关系”,在面对市场扩张和生产经营成本降低方面取得了统一性。这样就可以从整体上调动职工的生产与节约的积极性。可见,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利润分享制度虽然是资产阶级力求从管理角度调动工人积极性的一种改革,但是客观上,它把工人的收入与企业的经营效果联系起来,使工人能够享受到自己劳动成果增长的一部分,这样,就使工人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不再单纯具有“劳动力价值”这一质的规定性,使工人的收入能够随着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而提高。这种变化体现了在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部分质的变化。虽然这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雇佣劳动的基本关系,但是,劳动者的收入与经营效果相联系,我们可以认为,从理论上看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形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因素。但是,它究竟是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的因素,还是“文明和精巧的剥削手段”,还需要根据它在实施过程中的具体做法和结果来考察,要看工人阶级收入增长是否因此超过了资本收入的增长。事实上,从实行利润分享的实施效果来看,它仍是以能否给资本带来更多的利润为决定是否实施的标准。
在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过程中,推行职工持股计划以增加普通职工的收入来源,是对现有生产关系不做根本性改革的条件下,即维持劳动与资本的基本关系条件下,对收入分配的局部调整,因此不失为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一种比较现实的手段措施。如果职工能够通过持股方式,在正常的工资范围以外分享一部分利润收入,也会使普通劳动者收入有所提高。但是应当看到,如果我们以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为目的而推行“职工持股计划”,将是一项涉及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它不同于一般性地以调动职工劳动积极性为目的的“职工持股计划”,要使职工持股能够改变当前的收入分配格局,就必须有大的改革,不仅职工持股份额要大大增加,而且职工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地位也要有大的改观。这样,通过“职工持股”来增加普通职工的收入,本质上不只是通过“职工持股”的股息、分红等形式使普通职工把他们剩余劳动创造的收入取回一部分,而是要提升工人在企业经营决策中的地位。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市场经济的外壳下,改变企业内部生产关系,实现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由此看来,“职工持股”只是一个形式,在这种形式下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以增加普通职工的收入,在事实上已经涉及普通职工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转变问题。这样的改革对于多数私营企业来说,已经是改变性质的改革了。因此,它的推行直接涉及资本的利益,需要有强有力的措施。在目前情况下是否可行、能在怎样的程度上可行还需要专门研究。
四、财产性收入在收入分配改革中的作用
在以上各部分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尽管对于个人而言,“财产”可以成为他的收入“源泉”,他可以尽力地创造条件扩大自己的“财产性收入”,但是,对于社会而言,所谓“财产性收入”本质上不过是通过对社会生产、生活条件的垄断占有,从这些条件的使用者手中分取一部分社会产品而已。“财产”虽然可以扩大个人的收入,但不能真正扩大社会收入的总源泉。财产性收入的存在以生产领域中存在着的资本价值增殖关系为前提,资本关系普遍化和表现化的充分发展,使得一切可以被垄断占有的物质财富都转化为“财产”并要求从社会剩余产品中得到相应的一份“财产性收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原理告诉我们,财产性收入本身就是私有制在收入分配上的最表面化体现,对生产或生活条件的私人垄断造就了“财产性收入”,它的存在是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折射。因此,如何对待“财产性收入”本质上就是如何对待社会上存在着的对生产和生活条件的私人垄断权的问题。“财产”之所以能给它的所有者或占有者带来收入,并不是由于财产在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给予的“贡献”,而是私有制带来的对人们社会生产与生活条件的垄断控制,这种垄断控制使得使用“财产”的社会成员必须向这种垄断控制交纳贡赋。
根据对财产性收入的源泉、性质等的分析,可以看到在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中,我们不能寄希望于通过扩大个人财产性收入来解决当前社会严重存在着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财产性收入占有状况是以财产的占有状况为前提的,没有对财产占有的增加,就没有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没有财产占有结构的改变也就不会有财产性收入分配的改变。低收入人群,从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来看,总的来说是不可能占有很多财产的,这样的话又何以扩大他们的财产性收入呢?不改变财产的分配状况是不可能改变财产性收入的占有状况的,进一步说,所谓财产(资本)是收入转化而来的(资本积累),要增加低收入人群的财产,首先要增加他们的收入,如果我们能够有其他方式增加他们的收入,那么也就没有必要靠财产性收入来增加他们的收入了。可见,寄希望于通过扩大财产性收入缓解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低下状况本身就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
在对财产性收入总体上否定的同时,也需要看到,财产占有权对于部分收入的转移作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用来对收入进行再分配,使部分收入向低收入人群的更合理需要转移。但是,要实现这种再分配,仍必须有财产占有状况的根本性变革。这样一种变革不能在普遍的财产私有制占有的情况下实现,即不是靠扩大个人的私有财产的方式直接实现收入向私人的再分配,而是要靠建立由社会或集体共同占有的、产权明晰、责任清楚的财产占有制度和占有形式来实现财产性收入的获取,并在这种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采取一定的具体形式按照需要进行再分配。这种借助财产性收入实现收入再分配的方式,是财产占有制度的一项局部性改革,它借助共同占有的财产,同社会上其他资本一样通过流通活动占有相应的财产性收入,在此基础上,按照有利于促进民生、满足需要、缩小收入差距等原则对已获得的收入实行再分配,从而让“财产性收入”这一资本价值增殖的产物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
通过这种形式利用“财产性收入”实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在市场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早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成长起来的社会化生产方式突破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桎梏的要求,在资本主义经济内部形成了股份公司这一经济组织。对此,马克思指出:“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①《资本论》,第3卷,第494-495、495页。马克思还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再生产过程中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②《资本论》,第3卷,第494-495、495页。马克思的论述启示我们,利用财产性收入调节收入再分配,不能也不必要只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框架内寻找出路,完全可以通过资本所创造出的社会化财产占有方式实现财产性收入的共同占有,合理分配。在资本主义信用制度长期发展过程中,创造出了在许多共同占有财产的基础上实现财产性收入再分配的社会经济形式。其中,20世纪蓬勃发展起来的各种养老基金就包含着以财产性收入形式,按照养老需要的原则实现收入再分配的内容。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中存在的各种养老金计划中,资金的管理和资金的运营构成养老金计划内部的两个基本构成部分,其中资金的运营就是通过以基金的名义持有各种金融资产以获取利息、红利等收入,或获取资产的溢价收入,这些收入和本金构成向受益人发放养老金的资金来源。资金的管理则是按照人们未来养老的需要筹集和发放养老金。在养老金制度中,养老金向个人发放的具体规则是多种多样的,譬如,有“固定受益”的养老金,即受益人在工作期间履行了缴费义务后,在退休后就可以按照一定的数额定期领取养老金;还有“固定缴纳”的养老金,即在受益人退休把受益人在工作期间缴纳的基金和增殖收入作为投资以获取增殖收入支付养老金。不管资金的筹集和发放具体规则如何,这些工作都是围绕着如何保证人们失去工作能力以后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生活的需要这一原则设计的。因此,在各种养老金计划中资金的管理和运营之间互相分离,就使得既利用了资金(资本)在市场经济中具有的价值增殖属性,通过金融市场活动占有“财产性收入”,又按照特定的需要将“财产性收入”进行再分配,以适应收入合理分配的要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须对于“财产性收入”形式给予合理的运用,使之成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工具,而不能简单地把“财产”视为收入源泉,片面鼓励个人以各种手段占有财产、获取财产性收入。在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中,对于个人形式的财产性收入,如房屋租金、资本利息、红利等要加以限制,以减少凭借财产占有收入的情况,引导社会成员努力通过劳动增加自己的收入。
[1][美]威茨曼.分享经济 用分享制代替工资制.林青松,何家成,华生,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
[2]周新城.关于财产性收入的若干思考.学习论坛,2011 (2).
[3]杨娅捷.对提高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问题的思考.经济问题探索,2011(1).
[4]何玉长.财产权利与财产性收入.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1).
【责任编辑:于尚艳】
Thoughts on the Incomes from Property——On the View of Distribution Theories:Marxian
(By ZHANG Jun-shan)
This paper discussed a social idea,which argues that we should enlarge people's“incomes from property”to narrow the gap in income distribution.The paper explains the concept of“property”which brings incomes to its owner,and shows that necessary components include the ownership of the property,necessary quantity,and value.The main forms of property income include the interests of financial assets,rent of houses,and the capital gains.Property is not the source of income.It is just a means that absorbs the social wealth under the special social productive relations.The final source of these incomes is the surplus value created in productive fields.Therefore,“income from property”could not act as a kind of income for the majority; it is just the income form for a few people who attach themselves to production.The paper discussed the issue of share held by staff.In this form,staff could get some incomes from the profit of the firm,and it could make staff's economic interests closer to firm,so that could encourage staff work hard.But the source of their income from share hold is still the value produced by themselves.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that“income from property”is only an auxiliary means to adjust income distribution,and we should not use it as a main means.
property;incomes from property;share holding by staff.
张俊山(1954—),男,天津市人,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与完善我国现阶段分配制度研究”(09BJL003)
2012-06-20
F014.4
A
1000-5455(2012)04-008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