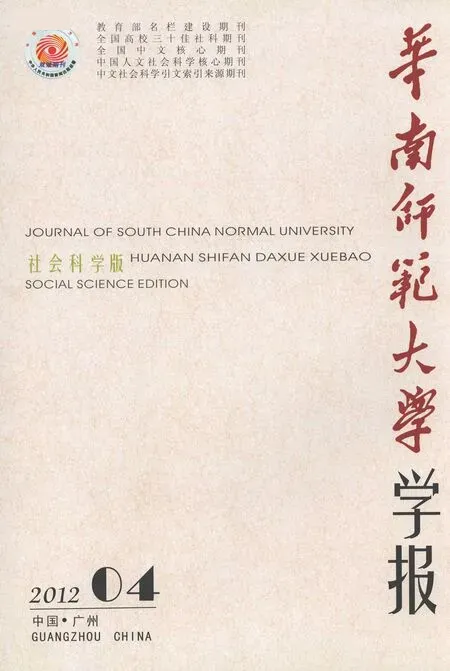数字化音乐的人文精神与价值重构
李志刚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艺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在数字化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将其称为媒介时代是合情合理的,从20世纪中期世纪以来,数字化技术在音乐各领域上的应用,已是一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以互联网为主要形态的“新媒介”迅速发展,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媒介生态格局,也在某种程度上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音乐“场域”,同时由数字化进程带来的音乐创作,传播等诸方面的变化也是根本性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在研究的主要任务中提出:“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深入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外延和实践要求,研究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整合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和办法,推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因此,在当前数字化媒介背景下,我们有充分理由去寻找那些对音乐的人文精神产生深刻影响的文化特征,去研究寻求数字化媒介影响下音乐中具有指导意义的价值观,为音乐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有益的途径。
一、数字化音乐中人文精神的特征
马克思指出,人不是某种驯服的自然能力,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主体出现的。中国科学院网站在《科学精神与科学的人文精神》中讲到:“近代科学技术上的发现及其广泛运用,一方面极大地发展了人的主体性,增强了人的认识和实践能力,创造出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改变了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思维和情感方式等,拓展了人的生活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等之间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冲突’。”①《科学精神与科学的人文精神》,中国科学院网站:http://www.cas.cn/jzd/jrcjy/jysp/200601/t20060118_1699956.shtml,2006-01-18。我们可以说数字化媒体推动了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伴随着数字化媒介的历史进程,数字化音乐已逐渐成为现代文明的一种形式。而且在这一进程中,它也经常在追求和体现一种完整的美,有时也力求体现一定的科学态度和道德,体现了其作为现代文明的特征,因此当我们把数字化作为文明的一部分时,也昭示着我们打开了音乐发展的另一个前景。
回顾一下人类与其工具的关系的最初状态。我们记起一切出自人们意愿的人类活动都出自心灵,同时也是为了满足心灵的要求而进行的,这类活动的第一个工具是人的身体。②[美]鲁·阿恩海姆:《艺术心理学》,第171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音乐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精神现象,人文精神的载体,是人类所特有的,是为人而存在的,是人类有史以来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说,一部浩瀚而无有穷尽的艺术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地“认识你自己”的心灵历程的形象化的历史。正如英国著名美学家科林伍德指出:“没有艺术的历史,只有人的历史。”③陈旭光:《21世纪素质教育系列教材——艺术的意蕴》,第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一旦我们将数字化媒介放到音乐的一切活动与其作为工具的关系这样一个境遇中来考察,我们就有必要知道数字化媒介是如何对待音乐创作和表现中的那些永恒和不变的内容,数字化媒介作为人造和人享的东西,并不是所有的东西是全新的,毕竟人是其主体,它们也必须像旧东西一样仰仗着同样的基本原理、同样地资源和同样的需求。因此有其历史传承的一面。
我们普遍认为,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在成功的数字化音乐作品中,一切的音乐构成不论来自何处,它还是按照一定的音乐规律来表现,虽然有时带有些创意,但还是没有离开音乐本身。对于音乐艺术来说,不管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都应该是建立在某些基础的人文尺度之上,其人文精神的内涵和外延的一切形态都是共通的,由此引申的审美体验的一切形态也是有共性的。
二、数字化音乐中的人文精神的多元解读
古斯塔夫·西奥多·费希纳(Gustav Theodor Fechner)作为心理物理学家,在1871年所写的《论实验美学》一文中认为:“美学永远不会有象物理学那样的精准性,他和生物学一样具有不完满性”。他说,人尽其所能而为而己。在费希纳看来,人们的冀望唯有通过追求艺术作品的完美才能得到最高的实现。①[美]鲁·阿恩海姆:《艺术心理学》,第184、439页。我们注意到,在数字化媒介的发展史中,一切和音乐有关的技术进步,最终目的是为了服务音乐本身,以数码音乐制作软件的开发为例:从cakewalk到sonar和Cubase/Nuendo等的不断升级,以及Logic从PC机到苹果电脑开发推进,到PRO TOOLS的录音行业的业界标准化发展,大量的音乐效果器以及音色库插件等的开发,网络技术以及多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所有这些的一切技术的发展都是为了更好地表现和表达音乐艺术。我们也注意到,在数字化媒介下音乐的创作有时倾向于简单的数字特点音乐题材以及风格,有时倾向于有深刻感性认知的难以应付的复杂性音乐题材,这也可解释为人类心灵对科技的不同反应,也可理解为不同个体对生活方式的不同态度及追求。
经济学家哈耶克在(F.A.Hayek)在《科学的反革命》(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中提出:“科学打破并取代我们的感觉性质所呈现的分类体系,这虽然不太为人熟悉,却恰恰是科学所作的事情。”②哈耶克(Friedrich A.Hayek):《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第10-11页,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哈耶克表现了对科学过度权威的忧心忡忡。而斯诺(C.P.Snow)1959年在剑桥做了一次著名的演讲,取名《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他当时认为科学的权威还不够,科学还处于被人文轻视的状况中,科学技术被认为只是类似于工匠们摆弄的玩意儿。对于以上两种不同观点的疑惑,无疑给我们提供了某种思想资源,是有积极意义的。③江晓原:《当代“两种文化”冲突的意义——在科学与人文之间》,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而苹果电脑公司创始人斯蒂夫·乔布斯的语录更具有代表性:“我们说着别人发明的语言,使用别人发明的数学……我们一直在使用别人的成果。使用人类的已有经验和知识来进行发明创造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我愿意用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④《史蒂夫·乔布斯经典语录:10 Golden Lessons From Steve Jobs》,中国日报网:http://www.chinadaily.com.cn/language_tips/book/2011-08/25/content_13192204.htm。面对日新月异的数字化技术,很多人提出乔布斯是将“技术与艺术完美结合的天才”。当今可以说数字化无处不在,同时数字化媒介也获得的越来越大的权威和话语权,因此警示我们要探寻数字文明和音乐间理解的可能性。从人文价值论的视角看,“无论技术如何发展,都不应该丧失其人文性的目标指向和意义定位,而应该让高技术里面隐含高人文,在工具理性中渗透价值理性,因为高技术与高人文的统一才是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的大智慧”⑤欧阳友权:《数字化文艺学的人文承载》,载《长江学术》2009年第3期。。
学者顾毓秀提出“人文精神就是求善与求美”。“人文精神同科学精神,正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相辅相成的。”⑥顾毓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http://chinaxhpsy.sunbo.net/show_hdr.php?xname=P7Q3D11&dname=49C1361&xpos=17。针对数字化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来自不同学界的声音,陈平原在《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中提到:“我们的责任,不是表达对于‘网络’这个独领风骚的‘当代英雄’的赞赏或鄙夷,而是努力去理解、适应、转化,尽可能在趋利避害中重建新时代的精神、文化和学术。”⑦陈平原:《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见陈卫星主编《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第198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可以说,数字化媒介下音乐的人文意义至少应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普世性的人性关怀;二是感性思维和理性上的思考;三是对生活意义的追求。
音乐借助数字化媒介进行音乐创作以及传播,数字化媒介其实一直参与到音乐的艺术表达当中,我们在网络上听到的每一首音乐作品可以说是它自身的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世界。阿恩海姆提出:“建设性的思维依靠语言所意指的东西而进行,但这些语词所指的对象本身并不是词语的,而是知觉的。”①[美]鲁·阿恩海姆:《艺术心理学》,第50页。那么人文精神的重构和技术发展是否会有互相矛盾之说呢?我们可以从电子音乐中寻找答案。有人提出作为现代音乐的分支的电子音乐,“已形成了创作中较为成熟的空间思维。在这种观念的影响和技术的作用下,将空间思维在作品中加以‘强化’和‘突出’,形成了电子音乐中的两种空间思维:静态多维空间思维和动态运动空间思维。”②李鹏云:《电子音乐中的空间思维》,载《黄钟》2006年第4期。因此,当我们把思维最为数字化音乐的一部分,也就是技术的一部分时,也就是解读技术与人文的悖论的一种方式。
三、重构基于人文精神的数字化音乐
人文精神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人们的价值观、人性观、时代精神的集中反映。从目前音乐所依存的社会现实来看,数字化媒介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人们物质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同时也带来了人们整个思想价值观念的裂变,社会的市场化数字化的转型,音乐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可避免地更多走向了“商业化”,由此带来了传统音乐价值观念的进一步解体,数字化音乐创作的方便性,传播的快速性,特别是网络音乐的直接性,必然会导致音乐艺术在现实面前失去了精神支撑与价值观念而变得随波逐流。因此我们不仅要问:音乐还有担当社会道德的责任?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有必要的。因此有人提出建构数字化人文精神要做到:(1)对数字技术的人文关怀;(2)协调数字技术与人的自由发展;(3)以网络文明为数字技术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支撑。③张桂芳:《中国数字文化发展的人文生态维度》,载《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1期。
“人类一切活动,其本性都可概略为以最小值,去追求最大能;以最少形式,去概括最多内容。”④王英琦:《价值重构五论》,载《文学自由谈》2005年第5期。这点在数字化音乐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数字化媒介下,数字化创作者可以集作曲、配器、演奏、传播于一身,面对功能强大的数字化技术以及浩瀚的网络媒介,你可以既是作曲家,也可是录音师和发行传播人,在此,音乐艺术实践的独立性得到了最大化的展示。另外数字化音乐在多媒体的发展过程中,把大量的原始自然声音、生活声音以及特效音色应用到音乐本身,使音乐越来越接近生活世界本身,也体现其寻求自由的本质。当然我们也知道,即使是成功的数字化媒介音乐作品的表现也都有着范围以及特征上的局限性,在一种通过音乐情感与认知的表达的创作性的限制中与数字化媒介领域里的限制之间,我们“必须在内在矛盾的对立中,找到反差性的美,协调互补的美——平衡和谐的临界奇异之美”⑤王英琦:《价值重构五论》,载《文学自由谈》2005年第5期。。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及媒体实验室的创办人尼葛洛庞帝(Negroponte)把当今称为数字化生存时代,并提出数字化生存的四大特征是:“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和赋予权力。数字化生存所以能让我们的未来不同于现在,完全是因为它容易进入、具备流动性以及引发变迁的能力。”⑥[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第267页,胡泳等译,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如果上述判断是正确的,我们就有必要在数字化媒介下对音乐的价值构建的过程中进行价值多元化的思考。在数字化生存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价值多样性和差异性的追求,在音乐上也反映了现代社会人们对自我情绪表达的关切。以此关怀不同音乐形式的价值选择。对于数字化音乐而言,每一首音乐作品其实也是立足于知觉来创作的,有其客观的价值,对于大多数创作者来说,“价值完全是建立在个人的特殊审美趣味和喜好基础上的,这些趣味和喜好是依凭文化和个人的背景而培养起来的”⑦[美]鲁·阿恩海姆:《艺术心理学》,第50页。。同时也和个体的数字化技术的能力有关,在数字化媒介背景下,抛却人类中心主义,突破价值认识的相对主义,摆脱经验主义的束缚,从多层次、多维度去认识音乐本身,结合艺术创作实践和科技掌握经验,回到人自身存在的认识域,是人类正确认识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唯一方法,也是人类价值重构的有效途径。⑧邓立、任兰兰:《论现代化背景下的价值重构》,载《理论界》2008年第10期。
四、数字化音乐价值重构的理性抉择
探讨数字化媒介下音乐的价值重构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怎样对待传统音乐和现代音乐这两个问题。它的实质在于如何基于人文精神的理念来看待和处理音乐的继承与发扬以及民族与世界的关系。它的价值取向也必须是找出有中国特色数字化媒介的音乐艺术,构建有高度“真”“善”“美”的中国音乐艺术。“因此数字化媒介下音乐艺术作为中国新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其核心就是要建立一种以独立人格为基础的具有独立文化精神为价值指向的,以平等、自由、科学、民主为主要内涵的新文化。①潘福晶:《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与价值重构》,载《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5期。同时价值重构和文化选择是多元共生的,它的演进发展完全可以视作是一种“精神家园”的共建。”②黄曼君:《精神家园共建:世纪之交的价值重构与文化选择》,载《中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
在艺术实践中,我们经常认定一个伟大的音乐作品不仅要能满足受众感情的客观需要,还要有卓越的启迪作用,以至于为这些作品保留高尚的地位,这种现象在传统音乐和经典音乐上表现得更为普遍。对于数字音乐而言,我们不可避免地对其达到艺术的最高旨趣和境界而向往,基于这样的标准,可以这样认为:真比假更有价值,深刻比平庸更有价值。只有这样,未来的数字化音乐艺术和科技的关系才会表现为科技的艺术也是艺术的科技。同时,“数字化艺术的创造仍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艺术赋予的最重要的使命”。③许静涛:《数字化艺术创造 仍需深厚的文化底蕴》,载《美术观察》2005年第6期。因此今后数字化媒介下音乐的发展和进步完全取决于我们眼中所见的品质。
从音乐史的演进规律看,数字化音乐应该具有广阔的前景,特别是随着数字化音视频等多媒体的开发,数字化音乐将会从多元走向更多元。另外,从技术层面看,数字科技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仿真”,也积极需求体现模拟传统音乐模式的最大化,体现创作价值的最大化,在“虚拟”中体现“真实”,使人类实现最便捷的音乐创作和欣赏过程,把音乐的创作空间、音色变化、和声体验、演绎手段、传播方式等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宽度,让音乐艺术与科学技术的完美统一由可能变为现实,实现音乐的审美功能、娱乐功能、交流表达功能以及社会和文化功能,也体现了音乐要在艺术的时空中确证自由的创造本性。就像宋瑾在《音乐的功能、价值与本质》中提到的:“在音乐样式上,最大可能是保持多元性的生态进化,较不可能归到一种模式。因为人与人之间有审美能力和审美趣味的区别,审美需要各有不同,何况人对音乐在非审美的功用领域还有多种需求。”④宋瑾:《音乐的功能、价值与本质(三)》,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网站,http://www.ilf.cn/Theo/29571.html,2011-07-10。
数字化媒介背景下音乐中的人文精神与价值重构,不应把它作为音乐的异己来对待。就像当时印象派刚出现一样,它不是洪水猛兽,而可以认为它是一种音乐流派和风格,音乐作品的价值体现更多地是由文化、社会以及心理等所决定的,音乐作品从创作到传播,更多地是取决音乐的内在价值而绝不是科技本身。在数字化新媒介下,音乐应该以多层次、多维度去认识科技与人文本身,同时将音乐回归到更有价值的人文态度上去,为现实的人类需要服务。在开放多元的音乐艺术语境下以及与科技交往对话的过程中,努力坚守当代科技人文的现代性价值立场,体现当代音乐的精神价值。就像人民网《2011年,一个被网络改变的中国》中的评论一样:“改变世界,从改变自己开始。”⑤金苍:《2011年,一个被网络改变的中国》,http://opinion.people.com.cn/GB/16775937.htm,2011-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