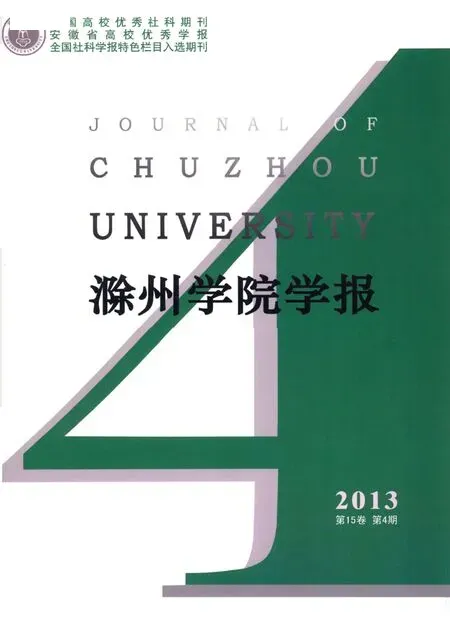王禹偁与滁州
景 刚
一
王禹偁字元之,祖籍澶渊(今河南濮阳),梁季乱离,流落到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县南),遂为济州人。巨野春秋时属鲁地,故王禹偁又自称鲁人。王禹偁后周世宗显德元年(954)生于巨野,家境贫寒,以磨麦制面为生,有时甚至要向亲友借贷。王禹偁儿童时就学于乡先生,即览白居易、元稹《长庆集》,十余岁能属文。宋太平兴国五年(980)省试登甲科,但殿试落选。八年省试第一,殿试中乙科进士,是年30岁,从此踏入仕途,先后任成武县主簿、长洲县知县。987年太宗闻王禹偁文名,诏赴阙,任右拾遗,上《御戎十策》,受到宰相赵普器重。太宗亲试贡士,王禹偁援笔立就,拜左司谏、知制诰。990年摄中书侍郎,不久加封柱国,太宗面赐金紫。正当一路顺风之时,王禹偁却因为直言敢谏而遭受到仕途上的第一次挫折。事因庐州僧尼道安诬陷左散骑常侍徐铉,依法当追究道安的诬陷罪。也许因为徐铉是南唐旧臣,以才学、名臣自负,曾当面指责宋太祖不应灭南唐,所以太祖、太宗都对徐铉心存芥蒂;也或者是因为当时僧尼的势力较大,太宗想息事宁人,所以下诏对此事不予追究。而王禹偁却违背太宗旨意,上书据实为徐铉辩诬,论道安告奸不实罪,这就触怒了太宗,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直到993年8月才被太宗召回朝廷,授左正言。太宗谓宰相曰:“禹偁文章,独步当时,然赋性刚直,不能容物。卿等宜召而戒之。”[1]11月兼昭文馆。看来,太宗赏识王禹偁的文才,但对他的“赋性刚直,不能容物”却有所顾忌。995年正月王禹偁拜翰林学士、礼部员外郎、知制诰,兼知审官院及通进、银台、封驳司,制敕有不便,多所论奏。这再次激发了王禹偁极大的从政热情。几个月后,当他被贬滁州,在《滁州谢上表》中描述了这段时间的生活:“一百日间,五十夜次当宿直,白日又在银台通进司、审官院、封驳司勾当公事,与送湜、吕祐之阅视天下奏章,审省国家诏令,凡于利害,知无不为。三日一到私家,归来已是薄暮。先臣灵筵在寝(994年秋王禹偁遭父丧),骨肉衰绖满身,纵有交朋,无暇接见”然而,令太宗所难以容忍的王禹偁“赋性刚直,不能容物”的性格却未因被贬商州而有所改变,这直接导致了王禹偁仕途上的第二次挫折。995年4月28日开宝皇后(太祖宋皇后)薨,群臣不成服,王禹偁觉得不合礼仪,对同僚说:“后尝母仪天下,当遵用旧礼。”有人向太宗告密,太宗不悦,对宰相说:“人之性分固不可移。朕尝戒勖禹偁令自修飭。近观举措,终焉不改。禁署之地,岂可复处乎?”[2]太宗为何未按礼仪办理宋皇后的丧事,史书没有记载,但《宋史》在评价太宗时也明确说:“宋后之不成丧,则后世不能无议焉。”[3]可见王禹偁所说肯定是有道理的。但他又一次让太宗不悦,就不能不受到惩罚。5月9日,王禹偁“坐轻肆”(《宋史》本传作“坐谤讪”)罢为工部郎中、知滁州军州事。其黜官制词云:“王禹偁顷以文词,荐升科级,而徊徉台阁,颇历岁时。朕祗荷丕图,思皇多士,擢自纶阁,置于禁林。所宜体大雅以修身,蹈中庸而率性;而操履无取,行实有违,颇彰轻肆之名,殊异甄升之意。宜迁郎署,俾领方州。勉务省躬,聿图改节。”[4]
二
王禹偁至道元年(995)6月到任滁州,至道二年11月移知扬州,实际在滁时间一年半。关于王禹偁在滁州施政的具体情况,《宋史》本传和其它史料没有记载,《小畜集》中作于滁州的80多篇诗文也基本没有反映施政情况,而主要是反映作者的生活和思想状况。
《滁州谢上表》(以下所引王禹偁诗文均引自上海古籍书店1987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不另注)是王禹偁到达滁州后写的第一篇文章。在表中,除了上文引用的对内庭一百日尽心尽力工作情况的回顾以外,王禹偁还义正词严地写到:“况臣头有重戴(注:宋太宗诏两省及尚书省五品以上官员皆重戴。重戴是一种帽式。),身被朝章,所守者国之礼容,即不是臣之气势。因兹谢表,敢达危诚。况臣粗有操修,素非轻易,心常知于止足,性每疾于回琊。位非其人,诱之以利而不往。事非合道,逼之以死而不随。”对制词中强加给他的“操履无取,行实有违,颇彰轻肆之名”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反驳,认为自己关于宋太后丧仪的主张“所守者国之礼容”,而绝非意气用事。这篇表充分表现了王禹偁刚直不屈的精神。
王禹偁在由滁州移知扬州后所写的《扬州谢上表》中,对自己在滁州履职的情况作了如下的概括:“去年自禁中出职,滁上临民。黾勉在公,忧虞度岁。鬓发渐白,眼目已昏。”关于“黾勉在公”,恪尽职守,目前所能看到的史料约有以下一些:
当王禹偁任职滁州时,朝廷调民输碳往饶州(今江西上饶),以供铸钱之需。自滁抵饶,水路遥远,民夫十分辛苦。王禹偁考查历史,草拟奏章,建议在池州分设铸钱之所,滁民可就近输碳往池州,以减民劳。因康州知州杨允恭在王禹偁上奏前先行上奏并获得朝廷同意,所以王禹偁的奏章未及上报,问题已经解决,但此事已足以说明王禹偁对民瘼的关心[5]。
至道二年夏,滁州旱热,稻秧无法种植。王禹偁按当时习俗,到处求雨,随后天降甘霖,旱情解除。当时有民谣赞颂王禹偁(歌词内容未见记载),清流县主簿杨遂为此赠诗给王禹偁,王禹偁作《和杨遂贺雨》一诗。诗中描写当时的旱情是“可堪今夏旱,如燎复如焚。劂田本涂泥,坐见生埃氛。”诗人不忘地方官的责任,“食禄忧人忧,早夜眉不伸。促决狱中囚,遍祷境内神。”终于“偶与天雨会,滂沱四郊匀。插秧复修堰,野叟何欣欣”。对于民谣的颂扬,诗人坦言:“为霖非我事,职业唯词臣。若有民谣起,当歌帝泽春。”由此也可见王禹偁为人行事的作风。
滁民自古盛行山歌。至道二年三月王禹偁作古诗《唱山歌》,诗云:“滁民带楚俗,下里同巴音。岁稔又时安,春来恣歌吟。接臂转若环,聚首丛如林。男女互相调,其词非奔淫。修教不易俗,吾亦弗之禁。”对滁州古代民歌的歌唱演出情形及风俗作了生动具体的描述,同时表现了王禹偁重视、热爱民歌,顺应民心民意的施政理念和作风。
此外,王禹偁在滁时写有《答黄宗旦第二书》。其中写道:“孟子称仁政必自经界始,而汉废古井田,用秦阡陌,是本已去矣。”[6]对井田制和郡县制的优劣此处不论,但从中可以看出王禹偁对农民土地问题的关注。在滁时又作《官酿》诗,其中写道:“自从孝武来,用度常不足。榷酤夺人利,取钱入官屋。”认为汉武帝以来实行的酒类专卖是与民争利,也表现出王禹偁对民生的关心。
王禹偁在滁州的大部分诗歌如《诏知滁州军州事因题二首》、《滁州官舍二首》、《制除工部郎中出内署》、《戏题二章述滁州官况寄翰林旧同院》、《雪中看梅花因书诗酒之兴》,以及《朝簪》、《身世》等,都表达了作者当时复杂的心情,主要是忠而被贬、官场受挫的迷茫和失落。
例如《诏知滁州军州事因题二首》其一云:“晓直银台作侍臣,暮为郎吏入埃尘。一生大抵如春梦,三黜何妨似古人。不称禁中批紫诏,犹教淮上拥朱轮。时清郡小应多暇,感激君恩养病身。”诗的前两句颇似韩愈“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忧愤和失落。诗的后半则以人生如梦、古人三黜和郡小多暇、适宜养病而自我排解安慰。
又如作于至道二年的《诗酒》:“白头郎吏合归耕,犹恋君恩典郡城。已觉功名乖素志,只凭诗酒送浮生。刚肠减后微微讽,病眼昏来细细倾。樽勺不空编集满,未能将此换公卿。”将遭受打击后刚肠不减又心灰意冷、既想归耕又难舍素志的矛盾心情表达得细致入微。
《偶题》三首其一以西汉贾谊、东汉桓谭自比,抒发内心的愤懑并引以自慰。诗云:“贾谊因才逐,桓谭以谶疏。古今当似此,吾道竟何如。”
《夜长》则将内心愁苦、夜不能寐的情形表达得淋漓尽致。诗云:“后楼前阁五严更,颜髩侵人睡渐轻。病眼已甘书册废,愁肠犹取酒杯倾。风摇纸帐灯花碎,日照冰壶漏水清。吟尽旧诗犹展转,百回移枕未天明。”
三
王禹偁在滁州期间排解内心苦闷的主要方法是将内心的情感诉诸诗文。他在《滁州官舍二首》其二中说:“公余不敢妨吟咏,异日声名继至之。”一心学习唐代滁州刺史独孤及(字至之),希望能借诗文留名后世。《雪中看梅花因书诗酒之兴》云:“年来滁上兴何长,唯把吟情入醉乡。”《诗酒》云:“已觉功名乖素志,只凭诗酒送浮生。”因此,在滁州一年多的时间,成为王禹偁诗歌的又一个丰收期。不仅让我们从中了解了王禹偁在滁时的生活和精神状况,更成为人文滁州的重要史料。
《小畜集》卷十有《琅琊山》诗一首,其小序云:“东晋元帝以琅琊王渡江常居此山,故溪山皆有琅琊之号,不知晋已前何名也。”这段小序明确告诉我们,琅琊山之名确实源于西晋末年琅琊王司马睿南渡时曾居此山,而此山原来的名字已不可考。诗云:
连袤复岧峣,峰峦架泬寥。
流名自东晋,積翠满南谯。
洞碧通仙界,溪明润药苗。
古台临海日,绝顶见江潮。
杉影挐云暗,泉声出竹遥。
庙碑传汉祖,寺额认唐朝。
旱岁时霑稼,灵踪合禁樵。
诗章因我盛,屏障遣谁描。
近住人多秀,频登酒易消。
图经标八绝,灊霍合相饶。
王禹偁在“诗章因我盛”句后自注:“唐贤游者多矣,无琅琊山诗。”此说并不确切,因为韦应物任滁州刺史时就写有《游西山》、《同元锡题琅琊寺》、《游琅琊山寺》、《秋景诣琅琊精舍》等多首游琅琊山诗(受当时图书条件的限制,王禹偁可能没看到韦应物的这些诗),但这些诗大多没有对琅琊风光作具体细致的描绘,而王禹偁的这首诗却具体细致地描绘了琅琊山奇峰绵延、苍翠满目、溪水潺潺、禽鸟嬉闹的美丽景色,宛如仙境。尤其是具体写到了琅琊寺、南天门、高祖庙碑等著名景点。从这一角度说,王禹偁此诗可称为描写琅琊风光的第一首。
王禹偁留给滁州人民最宝贵的诗篇当数《八绝诗》。此诗第一次集中描写了琅琊山的八大景观(据唐独孤及《琅琊溪述并序》,唐滁州刺史李幼卿在疏浚琅琊溪的同时,曾“自赋八题于岸石”,独孤及也曾“状而述之”,但这些诗都没有流传下来),开此后以组诗描写琅琊风光之先河。诗前有序云:“唐大历中,陇西李幼卿以宫相领滁州刺史,游琅琊山,立宝应寺,故泉有庶子之号。李阳冰篆其铭,存诸石壁。白龙泉又次焉。由是亭、台、溪、洞,合垂藤盖,谓之八绝云。皇宋至道元年,予自翰林学士出官滁上,因作古诗八章,刻石于寺。寺名开化者,我朝改之也。”此序记载了八绝之名的来历,并告诉我们,琅琊寺唐名宝应寺,宋改名开化寺。王禹偁的这八首诗,当时就已刻石立于寺中,可惜今已不存。八绝为庶子泉、白龙泉、明月溪、清风亭、望日台、归云洞、阳冰篆和垂藤盖,每绝一首,对每一景点作了详细的描述并融入了作者的心情。例如《清风亭》:
兹亭废已久,厥址犹在哉。
清风为我起,疑有精灵来。
神交念宫相,临砌倾一杯。
回头问黄菊,寂寞为谁开。
古诗《北楼感事》开篇即描写了北楼的方位和壮观的景色:“北楼出林眇,登览开病姿。旁带滁州城,雉堞何唯一。下入刺史宅,却临统军池。”诗前小序云:“唐朱崖李太尉衞公为滁州刺史,作怀嵩楼,取怀归嵩洛之义也。……(作者)到郡之日,访衛公旧迹,楼之与记皆莫知也。而郡有北楼,通刺史公署……”由诗及序可知,唐李德裕任滁州刺史时为寄托嵩洛之思,曾建有怀嵩楼。但经过五代兵乱,到宋初已无人知晓其位置,是否即为北楼,也难定论。所能明确的是,宋初滁州官衙应仍为唐代旧所。王禹偁是北宋初期的著名文学家,创作诗文甚多,自编《小畜集》三十卷,其曾孙王汾辑录遗文、遗诗340篇,编成《小畜外集》。王禹偁反对唐末五代以来的纤丽文风,主张文应“传道而明心” ,“句易道,义易晓”。他的诗学习白居易,古雅简淡。他的诗文在当时文坛产生了重大影响,师从者甚多,是宋代诗文革新的先驱。王禹偁《御戎十策》、《应诏言事疏》等奏章提出了一系列的变法主张和具体措施,也是北宋政治改革派的先驱。王禹偁在朝为官,直言敢谏,刚直不阿;被贬偏郡,体恤民情,顺乎民风,是封建时代士大夫的偶像,所以深得时贤及后人敬重。林逋《读王黄州诗集》赞扬“纵横吾宋是黄州”。苏轼在《王元之画像赞并序》称赞王禹偁“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见公之画像,想见其遗风余烈,愿为执鞭而不可得”。在《书韩魏公黄州诗后》又说:“元之为郡守,有德于民,
民怀之不忘也,固宜。”宋仁宗庆历五年,欧阳修知滁州,作《书王元之画像侧》,诗云:“偶然来继前贤迹,信矣皆如昔日言。诸县丰登少公事,一家饱暖荷君恩。想公风采常如在,顾吾文章不足论。名姓已光青史上,壁间容貌任尘昏。”表达了对王禹偁的敬仰之情。北宋后期,滁州琅琊寺建有“四贤堂”,王禹偁名列其中。明代以来,琅琊山醉翁亭内有“二贤堂”,人们也多以王禹偁、欧阳修并称。王禹偁是滁州人文史上一个闪光的名字。
[参 考 文 献]
[1] 续资治通鉴:卷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57.
[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 宋史:卷五 [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 宋大诏令集:卷二0三[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 小畜集:卷十七·江州广宁监记[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5.
[6] 小畜集:卷十八[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