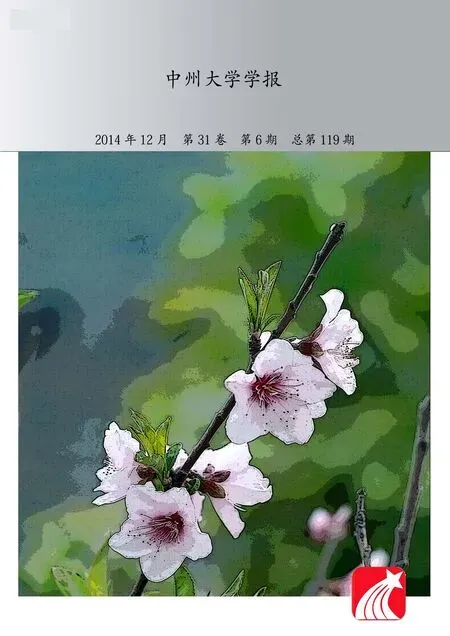论柳宗元诗文中的孔子
周岩壁
(郑州师范学院 中原文化研究所,郑州 450044)
一
柳宗元(773—819),是和韩愈齐名的唐代古文运动的领军人物。但两人的思想见解和学术观念,并不一致,甚至存在着微妙的差异,虽然二人并没有激烈的直接的冲突。
韩愈所作的《顺宗实录》,对由王伾、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持完全否定态度,并说:“有当时名,欲侥幸而速进者: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刘禹锡、柳宗元等十数人,定为死交。”[1]556所以直斥子厚,是因为传统史官的直书不隐精神、历史客观性的要求使然。在《柳州罗池庙碑》中云:“子厚,贤而有文章,尝位于朝,光显矣;已而摈不用。”[1]217
柳宗元的《天说》,以韩愈与柳子对话的形式,驳斥韩愈所持的“天人感应”[2]卷十六的传统观念。二人对于佛道的态度,则是明显不同。柳宗元在《送僧浩初序》中说:“儒者韩退之与余善,尝病余嗜浮图言,訾余与浮图游。近陇西李生础自东都来,退之又寓书罪余,且曰:‘见《送元生序》,不斥浮图。’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2]卷二十五
就整个政治思想史来看,柳宗元是个极具异端色彩的人物[3]271-275,在传统社会儒家意识形态背景下,长期被人误解。李慈铭说:“子厚终身摧抑”,“二王八司马之事,千载负冤,成败论人,可为痛哭……而世无特识,多为昌黎《顺宗实录》所压,虽欧阳文忠、宋景文、司马文正尚皆不免,可叹也夫!”[4]627意思是说,永贞改新的历史描述,《顺宗实录》为《旧唐书》提供了蓝本,而在此基础上修成的《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则也因而未改。在《送薛存义序》中,柳宗元对官吏与人民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2]卷二十三
这和韩愈《原道》中说的“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1]19大异其趣。比较起来,韩愈一副统治者帮凶的面孔,显得虚张声势,穷凶极恶。柳宗元的说法,则和后来的公仆意识已经非常接近。
柳宗元诗文中的孔子形象,也显得与传统形象大异。自认为得孔子真传的荀子说:“仲尼之状,面如蒙倛。”[5]卷三荀子著《非相篇》,主旨在于反对当时兴起的骨相学:他以外貌断人吉凶才能贵贱。举孔子为例,“论其志意,比类文学”。《皮子文薮》卷七有《相工》一文,其中云:“今之相工,言人相者必曰某相类龙,某相类凤,某相类牛马,某至公侯某至卿相是其相类禽兽,則富贵也。”可见中晚唐时,这种缺少实际依据的具有神秘化倾向的相人之术非常流行。韩愈在《杂说》四则之三中说:“昔之圣者……其貌有若蒙倛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谓之非人邪?”[1]49韩愈在这里主张的也是论心不论外貌,和荀子类似。但他们都承认孔子的面貌与一般人不一样,以为事实如此。这在客观上助长了把孔子神秘化、非人格化的不良倾向,此一倾向,在中国文化史上,绵延不绝。柳宗元则在《观八骏图说》中明确地反对这一偏见:
传伏羲曰牛首,女娲曰其形类蛇,孔子如倛头,若是者甚众。孟子曰:“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今夫人,有不足为负贩者,有不足为吏者,有不足为士大夫者,有足为者,视之圆首横目,食谷而饱肉,絺而清,裘而燠,一也。推是而至于圣,亦类也。然则伏羲氏、女娲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慕圣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倛头之间。故终不能有得于圣人也。[2]卷十六
柳宗元不相信孔子倛头,认为孔子在相貌上和一般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性情嗜欲,和众人也没有什么不同。《与杨诲之第二书》:“乐放弛而愁检局,虽圣人与子同。圣人能求诸中,以厉乎己,久则安乐之矣,子则肆之。其所以异乎圣者,在是决也。若果以圣与我异类,则自尧、舜以下,皆宜纵目卬骞鼻,四手八足,鳞毛羽鬛,飞走变化,然后乃可。苟不为是,则亦人耳。”[2]卷三十三
圣人与一般人的差异既不在相貌,也不在七情六欲;圣人能够长期地自觉地检束自己。在《天爵论》中,这一点有更清晰的阐述:“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夺,则庸夫矣。授之於庸夫,则仲尼矣。若乃明之远迩,志之恒久,庸非天爵之有级哉?故圣人曰:敏以求之——明之谓也;为之不厌——志之谓也。”[2]卷三孔子对自己的描述是:“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6]133“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6]139“述而不作,信而好古。”[6]133“好古,敏以求之。”[6]140就是说,柳宗元的孔子形象,是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以严格的现实为尺度的。
二
柳宗元在一首言志诗的开头说:“知命儒为贵,时中圣所臧。”[2]卷四十二这是柳宗元在诗文中屡次提到的“大中”之道,《时令论(下)》云:“立大中,去大惑,舍是而曰圣人之道,吾未信也。”[2]卷三《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云:“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2]卷三十一“大中”被认为是孔子所具有的一项重要品质。《与杨诲之第二书》云:“夫刚柔无恒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则出应之。应之咸宜,谓之时中。”[2]卷三十三在《说车赠杨诲之》中云:“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遇阳虎必曰诺,而其在夹谷也,视叱齐侯类蓄狗。不震乎其内。后之学孔子者,不志于是,则吾无望焉耳矣。”[2]卷十六就是说,柳宗元认为孔子在待人接物时,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势,采取适宜的措施、策略。
柳宗元提倡“大中”之道,他认为这实际上是学习孔子的“时中”而已,是对孔子的自觉继承。《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云:“仲尼可学不可为也。学之至,斯则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败国,卒中矢而死。”[2]卷三十四他不光用宋襄公在战场上大讲仁义的不恰当行为,来反衬孔子凡事中的雍容优裕;而且认为被太史公以来的舆论一致赞扬的荆轲,也不过是个虽勇却愚的人物!《咏荆轲》:“秦皇本诈力,事与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实谓勇且愚。”[2]卷四十三慨叹荆轲不知道秦始皇和曹沫所劫持的齐桓公不是同一类人,不知道五伯时代与七雄时代不同了。这令人想到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一书中嘲笑的路易·波拿巴:革命形势已发生变化,他还一味模仿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拿破仑,以致自己成为闹剧中的人物!
柳宗元的这些论述,给人一种印象,即通过努力践行,达到孔子那样的圣贤地步,似乎也不难。然而,这只是理论上如此,柳宗元并不认为孔子之后的1300余年中,历史孕育出了第二个可企及孔子的人物。《师友箴》云:“吾欲从师,可从者谁?……吾欲取友,谁可取者?……仲尼不生,牙也久死,二人可作,惧吾不似。”[2]卷十九《故御史周君碣》云:“第令生于定、哀之间,则孔子不曰‘未见刚者’。”[2]卷九言下之意也是慨叹时无孔子,故周子谅不得被剪拂、受赏识。《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云:“虽孔子在,为秀才计,未必过此。”[2]卷三十四亦言时无孔子。在柳宗元心目中,孔子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与杨诲之第二书》云:“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2]卷三十三在《道州文宣王庙碑》中,柳宗元毫不含糊地说:“夫子之道闳肆尊显,二帝三王其无以侔大也。”[2]卷五就是说,孔子的尊显,使尧舜二帝与禹、汤和周文(武)三王都相形见绌。等于说,孔子在历史上是空前伟大、无人可与之比肩的。
唐代的古文运动,是宋代道学兴起的序曲。张君劢《新儒家思想史》第四章标题就是“理学的先驱:韩愈”[7]。韩愈《处州孔子庙碑》云:“生人以来,未有如孔子者。”[1]卷七也认为孔子,贤过于尧舜远矣。后来,道学家更是把孔子说成是“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8]卷九十三,这成为普遍的共识。但在柳宗元的时代,这只是少数精英才有的明确认识。
在柳宗元眼里,孔子和二帝三王的区别,是“无大位”。《 论语辩(二篇)》(下篇):“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者也。上之尧、舜之不遭,而禅不及己;下之无汤之势,而己不得为天吏。生人无以泽其德,日视闻其劳死怨呼,而己之德涸然无所依而施。”[2]卷四感叹孔子没有赶上凭才能可以通过禅让得到帝位的尧舜时代,也没有像商汤那样,有祖上的基业可以作为发达的凭借,甚至连可以在朝廷推行自己政策举措的大臣也当不上!《与韩愈史官书》云:
孔子之困于鲁、卫、陈、宋、蔡、齐、楚者,其时暗,诸侯不能行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当其时,虽不作《春秋》,孔子犹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虽纪言书事,犹遇且显也。又不得以《春秋》为孔子累。[2]卷三十一
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言:“孔子圣人,作《春秋》,辱于鲁、卫、陈、宋、齐、楚,卒不遇而死。”[1]473完全颠倒了作《春秋》和政治上的不遇二者间的因果关系。柳宗元此文正是针对退之这一可笑的、幼稚的迷信观念而作。
孔子所处的时代,用沈约的话说,就是:“昔周之衰,下陵上替,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纲纪乱矣。”[9]卷十四不光是现实的不可能性与孔子淑世理想的冲突问题,在柳宗元看来,还有“善人少,恶人多”[2]卷三十三。《与杨诲之书》是有精英意识的悲观主义的看法,《意林》卷二曾引《庄子》,即有类似说法。归根到底,它是一个启蒙的问题,是先觉如何觉后觉的问题。圣贤不被普通人所理解和认可,甚至被讥谤,这尤其令人痛心和感慨。在《谤誉》中,柳宗元慨叹:“善人者之难见也”,“其谤孔子者亦为不少矣:传之记者,叔孙武叔,时之贵显者也。其不可记者又不少矣。”[2]卷二十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吊屈原文》云:“但仲尼之去鲁兮,曰吾行之迟迟。”[2]卷十九此是采用孟子的说法,孟子云:“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6]450
其实,孔子自己对他所处的时代非常清楚,说自己栖栖惶惶,是“行其义也”;“道之不行,亦知之矣”。朱子认为这是子路说的;即使是子路说的,当也是孔子同意者。[6]270行其义的目的,是要致其道,义无反顾,不计毁誉,“孔子不避名誉以致其道”[2]卷二十三。就此,柳宗元曾拿后来被提升为道统人物的孟子来与孔子作比:
孟子好道而无情,其功缓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2]卷二十
孔子把民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安利元元为务”[2]卷三十。《书明谤责躬》这一急民的孔子形象,并不是唐代大多数人的共识。唐人心目中,孔子固然整日栖栖惶惶,为何栖栖惶惶?未曾着眼,或多不知其所以然!唐玄宗的《经邹鲁祭孔子而叹之》诗,对孔子的认识就是表面的、现象式的,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的话语——这里借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在《列宁与哲学》中提出的重要观念。它颇具规范性,也很有代表性:
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地犹鄹氏邑,宅即鲁王宫。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今看两楹奠,当与梦时同。[10]卷三
三
柳宗元在一篇具有戏说性质的文章中,对孔子所说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欤!”[6]109进行重新诠释:
海与桴与材,皆喻也。海者,圣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游息者也。桴者,所以游息之具也。材者,所以为桴者也。《易》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则天地之心者,圣人之海也。复者,圣人之桴也。所以复者,桴之材也。孔子自以极生人之道,不得行乎其时,将复于至道而游息焉。[2]卷十六
孔子最终还是退了下来,和子路等门生“复于至道而游息焉”;以“余言持世”[2]卷六。柳宗元认为,孔子最重要的一项事业是作《春秋》,“圣人褒贬予夺,唯当所在”,“见圣人之道与尧舜合,不唯文王周公之志,独取其法耳”[2]卷三十一。然而,《春秋》却很难懂。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为传者五家……秉觚牍,焦思虑,以为论注疏说者百千人矣。攻讦很怒,以辞气相击排冒没者,其为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或合而隐,或乖而显。后之学者,穷老尽气,左视右顾,莫得而本。则专其所学,以訾其所异,党枯竹,护朽骨,以至于父子伤夷。君臣诋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圣人之难知也![2]卷九
其实,圣人并不难知,只是那些“论注疏说者”把圣人之道弄得繁难晦涩了。柳宗元对圣人之道有简明的概括:
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2]卷三》
“仲尼岂易言耶?马融、郑玄者,二子独章句师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师,仆幸非其人。”[2]卷三十四在柳宗元眼里,马融、郑玄,也不过是点窜经句的老儒。“学不能探奥义、穷章句,为腐烂之儒。”[2]卷三十六明确表示自己不为皓首穷经的那一类学者!在《读书》诗中,柳宗元又说:
得意适其适,非愿为世儒。道尽即闭口,萧散捐囚拘。[2]卷四十三
柳宗元相信,孔子之道,人人都可了解并得到,只要通过适当的渠道去学习和揣摩。对当时的经学家陆质,柳宗元给予很高的评价,因为他廓清了繁缛解经的瘴雾,使孔子大道显露出来。“有吴郡人陆先生质,与其师友天水啖助,洎赵匡,能知圣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积学以入圣人之道,传圣人之教,是其德岂不侈大矣哉!”[2]卷九
当时,有一种把孔子神圣化的倾向,韩愈也说“圣人无过”,“夫圣人抱诚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苟发诸中形诸外者,不由思虑,莫匪规矩;不善之心,无自入焉;可择之行,无自加焉。故惟圣人无过。”[1]卷十四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三,有驳“世俗之说者则谓圣人无过”。朱子犹云:“圣人无过,何待于不贰?”[8]卷三十直到清代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三之《惜寸阴录序》中尚訚訚置辨于此。柳宗元则不以为然。在《与杨京兆凭书》中说,“孔子亦曰‘失之子羽’”[2]卷三十,意思是孔子自己尚且说,以貌取人,结果在子羽身上出了差错。《孔子家语》卷五:“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胜其貌……孔子曰:里语云,相马以舆,相士以居。弗可废矣。以容取人则失之子羽。”可见圣人无过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
《国语·鲁语》记载:“有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焉。使人问仲尼曰:穿井获狗,何也?仲尼曰:‘以丘所闻者,羊也。’”下云“专车之骨、隼集陈庭”二事,亦见此卷。柳宗元认为:“君子于所不知,盖阙如也。孔氏恶能穷物怪之形也?是必诬圣人矣。”[2]卷四十四相信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左丘明(柳宗元认为《国语》是左丘明所作)是诬圣,把那些神怪之事往孔子身上安。又有孔子对专车之骨、隼集陈庭贯楛矢而死之问,柳宗元指责:
左氏,鲁人也,或言事孔子,宜乎闻圣人之嘉言,为《鲁语》也,盍亦征其大者,书以为世法?今乃取辩大骨、石砮以为异。其知圣人也亦外矣。言固圣人之耻也。”[2]卷四十四
《左传》昭公二十年载:
齐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进。公使执之,辞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故不敢进。”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韪之。[11]卷四十九
孔颖达在《左传》正义中对此也没有异议。贞观十三年,任太宗“起居注”的褚遂良和太宗有段著名的对话,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12]卷七《新唐书》卷一百五和《旧唐书》卷八十的《褚遂良传》,皆载此事,大同,唯“何不书之”作“君举必书(记)”。《贞观政要》在唐代是作为士人考试的一项科目,《通典》卷十七,《选举五》载有儒者赵匡的《举人条例》云:“国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实录,并贞观政要,共为一史。”普遍地被阅读。所以,“守道不如守官”,是普遍认同的。然而,柳宗元认为“是非圣人之言”,专门著《守道论》予以驳斥,但为维护孔子,只好把此话归罪于“传者之误”[2]卷三。
柳宗元并不掩饰自己对孔子也采取一种实证的检验态度,不像大多数儒者一样,对于圣贤的言论一味盲目地信奉唯谨。这在《捕蛇者说》一文末尾不由自主地透露出来,他听了蒋氏三代人为逃避沉重的徭役而宁愿捕蛇被咬死的故事后,想起孔子说的“苛政猛于虎也”。(《礼记·檀弓下》)柳宗元说:“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2]卷十六因为在现实中目睹了蒋氏这样的悲惨遭遇,他才相信孔子会说“苛征猛于虎也”的话,也才感到这句话的分量。柳宗元出生于书香门弟家庭,青年时代大部分时间在长安及近郊度过,生命的最后14年才被贬谪到西南边地为官,所以他对下层民众的辛酸生活缺乏感性认知是必然的,就他文中所描述的感受来看也是真实的。
四
在柳宗元看来,孔子其人至为平易,以一种蔼然长者的形象出现;孔子之道,则是康庄大道。所以,《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告诫:
求孔子之道,不于异书。秀才志于道,慎勿怪、勿杂、勿务速显。道苟成,则悫然尔,久则蔚然尔。源而流者岁旱不涸,蓄谷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2]卷三十四
可见,柳宗元对孔子之道,是自信确有所得的。“学孔氏,扬芬郁。”[2]卷十在《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2]卷九中回忆与吕温,在长安,志同道合,切磋砥砺。
君昔与余,讲德讨儒。时中之奥,希圣为徒。志存致君,笑咏唐、虞。
揭兹日月,以耀群愚。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齿舌嗷嗷,雷动风驱。良辰不偶,卒与祸俱。直道莫试,嘉言罔敷。佐王之器,穷以郡符。
这些要致君尧舜、造福斯民的努力,最终换来了长期的贬谪!他不由地慨叹:“凡余之学孔氏为忠孝礼信,而事固大谬,卒不能有立乎世者,命也。”[2]卷十这是凌准的话——凌氏与柳宗元同是永贞革新成员,革新失败后分别被贬连州和永州。所以,这话应该是柳宗元高度认同的。虽然这样不为世人所理解,柳宗元还是抱定他所信奉的孔子之道,以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利民行道。
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处,以独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诏,娄君智可以任职用事,文可以宣风歌德,行于世,必有合其道而进荐之者。遽而为处士,吾以为非时。将曰老而就休耶?则甚少且锐;羸而自养耶?则甚硕且武。问其所以处,咸无名焉。若苟焉以图寿为道,又非吾之所谓道也。夫形躯之寓于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尧、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尧、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若是而寿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慊,虽夭其谁悲?今将以呼嘘为食,咀嚼为神,无事为闲,不死为生,则深山之木石,大泽之龟蛇,皆老而久,其于道何如也?仆尝学于儒,持之不得,以陷于是。以出则穷,以处则乖,其不宜言道也审矣。以吾子见私于仆,而又重其去,故窃言而书之而密授焉。[2]卷二十五
这里把孔子的淑世之道,与道教求长生的利己之道,严格区别开来。在《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中说:
今丈人乃盛誉山泽之臞者,以为寿且神,其道若与尧、舜、孔子似不相类焉,何哉?……尝以君子之道,处焉则外愚而内益智,外讷而内益辩,外柔而内益刚;出焉则外内若一,而时动以取其宜当,而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获是而中,虽不至耇老,其道寿矣。今夫山泽之臞,于我无有焉。视世之乱若理,视人之害若利,视道之悖若义;我寿而生,彼夭而死,固无能动其肺肝焉。昧昧而趋,屯屯而居,浩然若有余,掘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己独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谓夭也![2]卷三十二
对杨朱式的自求长生、对民之疾苦无动于衷的隐士,充满了鄙夷;同时表示,自己要“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
柳宗元生命的最后四年,在柳州刺史任上理民所取得的成就,表明他确实把自己所信奉的孔子之道,用他的说法是“大中之道”,见诸实践了。他在《觉衰》诗中说:
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沉。古称寿圣人,曾不留至今。[2]卷四十三
这里充满了清醒者的悲哀:老子、彭祖这样长寿的人也死了;周公、孔子这样的圣人也杳不可期。所留下的还有什么?想要“但愿得美酒,朋友常共斟”,又能为期多久呢?就这样,在持续的忧虑中,柳宗元抱着难以实现的崇高理想,46岁的时候,在当时的蛮荒之地柳州,去世了。他心目中平凡而又神圣的孔子形象,并没有被太多的人所接受。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只承认柳宗元是个文章家,但他的人品是非常有问题的!所以,他关于孔子的见解几乎成了一种邪说。
参考文献:
[1]阎琦.韩昌黎文集注释[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2]柳宗元.柳河东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4]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
[5]王先谦.荀子集解[C].上海:上海书店,1994.
[6]朱熹.四书集注[C].长沙:岳麓书社,1995.
[7]张君劢.新儒家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8]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9]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全唐诗(增订本)[C].北京:中华书局,1996.
[11]十三经(据四部丛刊初编本影印)[C].上海:上海书店,1997.
[12]吴兢.贞观政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