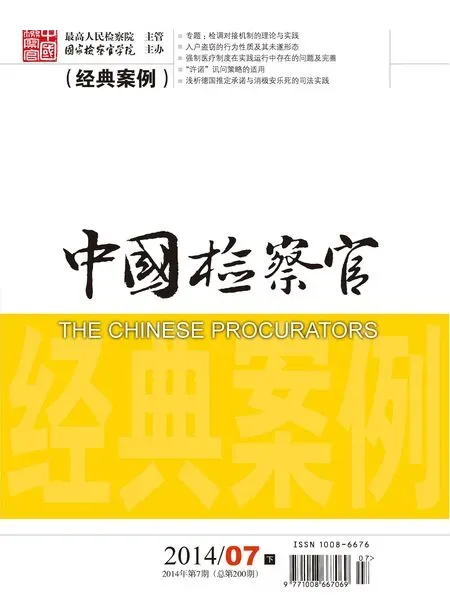抢劫罪、敲诈勒索罪与勒索型绑架罪的认定
文◎吴杰赵荣
抢劫罪、敲诈勒索罪与勒索型绑架罪的认定
文◎吴杰*赵荣*
一、基本案情
2014年2月10日23时许,犯罪嫌疑人唐某山、唐某梁等六人与被害人朱某、张某文、饶某勇、张某曙(四人合伙出资,由朱某负责具体赌博)在江苏省泗洪县青阳镇凤凰国际酒店14楼1406房间赌博时发现朱某出老千玩假被激怒。唐某梁当即用烟灰缸将朱某头部砸破致流血,朱某拿出手机欲求救,唐某梁当场将其手机抢去摔坏。后唐某山、唐某梁二人当场以拳打脚踢、皮带抽等方式对朱某进行殴打,逼迫朱某下跪,并把房间窗户打开,扬言要把朱某从窗户扔下楼、烧开水烫朱莫的手和头部,对朱某等人进行恐吓。朱某害怕,提出退还所赢赌资(6000余元),唐某山、唐某梁即向朱某、张某文、饶某勇等四人索要现金10万元。出于害怕,朱某答应出5万元,张某文等三人出5万元。随后,张某文打电话给家人要钱并说自己在凤凰国际酒店。唐某山、唐某梁等人害怕张某文家人报警,于当夜零时前后将朱某等四人强行带至该县孙园镇一河边的小树林内,又以拿刀剁手再扔河里洗澡的言语对朱某进行恐吓,朱某当即下跪磕头求饶。此时,唐某梁递给朱某一部手机要求其赶快凑钱,朱某立即打电话给其姐姐朱某兰,称自己跟别人打牌时被人绑了,让其姐姐给其筹5万块钱;唐某山也拿过电话告诉朱某兰说朱某赌钱玩假,要求朱某凑5万块钱给他们。朱某兰赶紧起床筹钱,于凌晨2时前后将5万元钱凑齐后打电话给朱某联系如何交钱,并问其能否报警?朱某说自己头部被人打破正在流血,不要报警。后朱某兰按照要求到孙园街乘坐由对方联系的一辆出租车到孙园镇双桥附近的水泥路上,朱某也被唐某山等人带到,朱某兰把钱交给唐某山等人后朱某被释放。后张某文、饶某勇、张某曙等三人通过朋友说情也被释放,但被要求退还实际所赢赌资。事后张某文等人将所赢赌资退还给唐某山等人,又通过送烟、请客的方式才了结此事。
二、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唐某山、唐某梁等人采取暴力和以暴力相威胁的方式,向被害人非法索取明显超出实际所输赌资数额的资金,其行为构成抢劫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唐某山、唐某梁等人行为不具有抢劫罪的两个当场性;嫌疑人实施殴打、胁迫行为是为泄愤,而非劫财,索取财物的故意是在被害人提出退还赌资时产生的,其后行为人只是对被害人进行言语威胁,未再进行殴打。因此,本案应构成敲诈勒索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唐某山、唐某梁等人采取暴力和以暴力相威胁的方式,非法控制被害人人身自由,逼迫被害人向其亲属借钱偿还明显超出实际所输赌资数额的资金,并利用被害人亲属对被害人人身安危的担忧最终从被害人亲属手中取得钱财。因此,本案符合以钱赎人的绑架行为特征,应当构成绑架罪。
三、评析意见
(一)抢劫罪、敲诈勒索罪与勒索型绑架罪的界限
抢劫罪、敲诈勒索罪与勒索型绑架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或者勒索他人财物为目的,在犯罪的主观故意、侵犯的客体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在实现目的的方式上存在差异:
1.作案手段及强度。敲诈勒索罪的手段仅仅限于威胁、要挟,通说认为也可以存在轻微的暴力,但其暴力行为对被害人产生的心理强制较小。抢劫罪的手段是暴力、胁迫或者其他致使被害人处于不敢、不能甚至是不知反抗境地的方法。勒索型绑架罪的手段则是控制被绑架人的人身自由,利用第三人对被绑架人人身安危的担忧勒索钱财。
2.威胁的方式及对象。敲诈勒索罪多以毁人名誉、揭发隐私向被害人发出威胁,即使以暴力相威胁,也不具有实施的即时性,而是在将来的某个时间付诸实施。抢劫罪一般以暴力伤害、杀害向被害人发出威胁,其威胁具有当场性,即对被害人以立即实施暴力相威胁,进行精神上的强制,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不敢反抗。勒索型绑架罪则是在控制被绑架人人身自由后,以杀害、伤害被绑架人或者以给付钱财方恢复被绑架人人身自由向第三人发出威胁。相比之下,抢劫罪、勒索型绑架罪的威胁具有立即付诸实施的紧迫性和现实性。
3.获取财物的来源。敲诈勒索、抢劫都是对被害人本人实施犯罪行为,直接从被害人手中取得财物;而勒索型绑架则是向被绑架人以外的第三人提出勒索要求,也是从该第三人处取得财物。
(二)具体案情剖析
1.如何理解本案行为人的暴力和威胁程度。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量。一是从言行上看,唐某山、唐某梁等人先是在县城酒店14楼的封闭房间内用烟灰缸砸、皮带抽、拳打脚踢等方式对朱海进行殴打并将其手机摔坏,用扔下楼、烧开水烫等言语进行威胁;被害人被转移到孙园镇一河边的小树林后,又受到拿刀剁手后扔河里洗澡的言语威胁。二是从人数对比上看,行为人一方始终是6个人,被害人一方是4个人,行为人明显占据人数优势。三是从作案时间和环境上看,事情发生在午夜至凌晨2时许,现场转移到远离民居的乡村小树林,特定的时间和环境无疑会加剧被害人的心理恐惧。综上可以看出,行为人的言行已经着实对朱某及其他一直未敢言语的三被害人产生了极大的心理强制力。
2.如何理解本案的犯意提起。有意见认为,本案行为人在县城酒店房间内实施的暴力、威胁行为是出于对朱某等人赌钱玩假表示不满的泄愤行为,当时并未产生劫取钱财的故意,因此不符合先起意后劫财的抢劫罪特征。此观点值得商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条的规定,行为人实施伤害、强奸等犯罪行为,在被害人未失去知觉,利用被害人不能反抗、不敢反抗的处境,临时起意劫取他人财物的,应以此前所实施的具体犯罪与抢劫罪实行数罪并罚。司法解释的这一规定,可以理解为行为人在实施伤害、强奸等犯罪行为后,利用这一犯罪行为的余势而实施了强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因此,根据司法解释的精神实质,行为人利用其基于其他目的实施暴力、威胁行为所造成的被害人不能反抗、不敢反抗的处境,临时起意取走尚未失去知觉的被害人财物,应当构成抢劫罪。
3.如何理解本案暴力、威胁的当场性。有意见认为,本案的作案地点、时间和环境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实施的暴力、威胁行为中断,“当场”发生变化,此观点也值得商榷。对抢劫罪中当场取得财物中的“当场”的理解不能过于狭隘。纵观本案情节的发展,可以看出,犯罪嫌疑人前后行动用时只有一个小时左右,期间并未放松对被害人的控制,暴力、威胁行为具有连续性。因此,实施暴力、威胁的当场是被“延伸”而不是被“变换”。
4.如何理解取得财物的当场性。有意见认为,唐某山等人在孙园镇双桥取得财物,而实施暴力、威胁行为在县城酒店或者孙园镇一河边的小树林,取得财物的当场与其实施暴力、威胁的当场不具有同一性。此观点同样是人为地割裂了情节的整体发展过程,割裂了前后行为的联系。理论通说认为,暴力、胁迫行为与取得财物之间虽然持续一定时间,也不属于同一场所,但从整体上看行为并无间断的,也应认定为当场劫取财物。本案中,实施暴力、威胁行为的当场延伸到孙园镇一小河边的小树林后,假设朱某没有给其姐姐打电话,而是被逼说出自己身上有一张银行卡,并在唐某山等人的看押下取出5万块钱后得到释放。此种情况下,仍然应当认定是当场取得财物。因为取钱过程中朱某一直被唐某山等人控制,行为并没有间断,“当场”得到了进一步延伸。
综合上述四点分析,如果本案案情只发展到第四点的假设情况,那么本案应当认定唐某山、唐某梁等人构成抢劫罪。
5.如何理解第三人交付财物。行为人控制被害人并通过被害人向第三人索要财物的,有的是通过被害人转达勒赎请求,以使第三人确信被害人被控制的事实并增加威慑力量;有的是明确要求被害人不能暴露其被控制的事实,使第三人误以为其因正当事由需要财物而提供;有的是笼统要求被害人向第三人索要财物,至于被害人以何种名义向第三人索要财物在所不问。对此,必须区别情况,区别对待。前两种情形的结论比较明确,以是否胁迫第三人为标准,如是胁迫第三人,则认定绑架罪;如不是,则认定抢劫罪。对于第三种情形,由于第三人对行为人是否胁迫被害人处于不确定状态,需要视被害人与第三人的沟通情况而具体认定:如果被害人告知第三人其人身被控制而要钱,则被告人构成绑架罪;如果被害人并未告知第三人其人身被控制,即使第三人感知,但在无证据证实行为人有明确的胁迫第三人的主观犯意和客观行为的情形下,以抢劫罪定罪处罚。这样定罪,不会轻纵犯罪分子,而且较之以绑架罪定性更有利于做到罪刑相适应。
本案中,先是张某文打电话给其家人要钱,并告知家人其在泗洪县凤凰国际酒店。这是上述第三种情形的第二种情况,张某文打电话要钱时并未告知其家人自己人身被控制,就算是张某文家人有所怀疑,但没有相应证据证实唐某山等人有明确的胁迫张某文家人的犯意和行为。因此,只能认定此情况构成抢劫罪。后朱某打电话给其姐姐朱某兰称自己跟别人打牌时被人绑了,让其姐姐给其筹5万块钱,唐某山也拿过电话告诉朱某兰说朱某赌钱玩假,要求朱某凑5万块钱给他们。这是上述第三种情形的第一种情况,朱某要钱时明确告知朱某兰自己被人绑了,而唐某山与朱某兰的对话看似是在辩解,实则起到了使朱某兰确信朱某被控制的事实并增加威慑力量的作用。因此,应当认定此种情况构成绑架罪。
(三)本案的罪数问题探讨
1.触犯的罪名。本案不是有预谋的绑架行为,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随着具体情况的发展,行为人不断变更犯罪方法,最后实际采取了绑架的方法。最初,唐某山、唐某梁等人在凤凰国际酒店房间对朱某等人实施暴力、威胁行为,并将朱某手机摔坏,断绝其对外联系,直到朱某等人被转移到孙园镇一乡村小树林,这个过程中朱某等人一直被控制。这期间,朱某等被害人既是劫持对象又是取财对象。后朱某打电话给朱某兰,要其筹钱。此时,劫持对象和索要财物的对象发生了分离。朱某成为人质,朱某兰筹集资金成为交付财物的人,已经符合绑架罪劫持对象和取得财物的对象相分离的要求。因此,可以看出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既构成抢劫罪,又构成绑架罪。
2.如何定罪。本案究竟应当以抢劫罪、绑架罪数罪并罚还是以绑架罪一罪认定呢?笔者认为不应当数罪并罚。(1)行为人的抢劫行为、绑架行为都是基于同一概括犯罪故意实施的,都是以要求退还赌资为由勒索财物;(2)行为针对的是同一对象,即被害人朱某等4人;(3)行为中间没有间断,具有延续性、交叉性。应当认定为一次犯罪。在一次犯罪中,行为人实施了抢劫、绑架等数个行为,笔者倾向以“吸收犯”重行为吸收轻行为的原则,以绑架罪一罪认定。
吸收犯是指事实上存在数个不同的行为,其一行为吸收其他行为,仅成立吸收行为一个罪名的犯罪。具有以下特征:(1)具有数个独立符合犯罪构成的犯罪行为;(2)数个行为是同一犯罪目的支配下实施的;(3)数个行为必须触犯不同的罪名;(4)数行为之间具有吸收关系,即前行为是后行为发展的所经阶段,后行为是前行为发展的当然结果。结合本案具体分析,在前三个构成要件上是没有异议的。在是否符合“前行为是后行为发展的所经阶段,后行为是前行为发展的当然结果”这一要件上,存在较大的分歧意见。
第一种观点强调“吸收关系的必然性”,认为吸收犯要求的“吸收关系”必须必然的存在于每一起同类型的犯罪过程中,例如“入室抢劫”的行为,其必然存在“非法侵入住宅”这个预备行为;“盗窃枪支”的行为,其必然存在“非法持有枪支”的后续行为。第二种观点承认“吸收关系的事实性”,认为应从具体案件的发展过程来看行为的延续性。例如,行为人在诈骗不成的情况下实施了勒索行为,在勒索不成的情况下实施了抢劫行为,在抢劫不成的情况下实施了绑架行为,虽然行为人行为“经历阶段、发展结果”不必然存在于每一起犯罪过程中,但就具体事实而言仍然是“经历阶段、发展结果”的关系。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因为第一种观点是抛开了客观事实的关联性、多样性、复杂性,而只是机械探究刑法条款“罪状”间的吸收关系,必然导致这种吸收关系固定的存在于特定的罪名、特定的犯罪行为之间。第二种观点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唯物辩证观点,结合行为的逻辑性、事实性、行为人的主观心理、事件客观发展情况综合评价“吸收关系”,更具科学性。当然,笔者的观点还是存在较大争议的。用何种理论来认定绑架过程中又抢劫行为的罪数问题,在法学界也是众说纷纭。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该类案件只认定绑架罪一罪已经成为普遍的做法。
*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检察院[273200]
——美创科技“诺亚”防勒索系统向勒索病毒“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