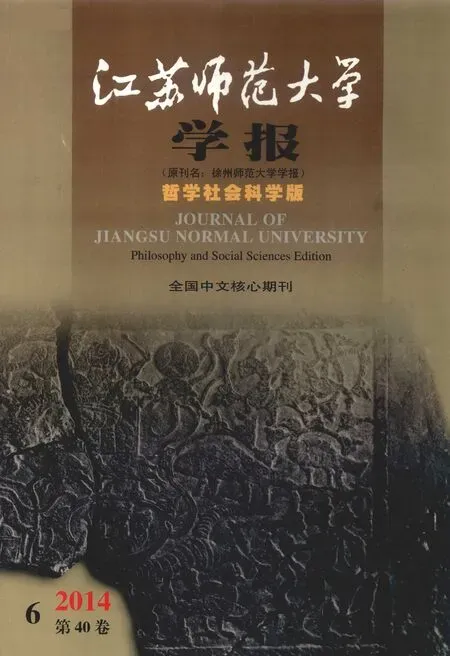《乐府诗集》“鼓吹”“横吹”曲辞的乐类特征及其乐府学意义
王淑梅 于盛庭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乐府诗集》“鼓吹”“横吹”曲辞的乐类特征及其乐府学意义
王淑梅 于盛庭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乐府诗集;鼓吹曲辞;横吹曲辞;铙
郭茂倩将“鼓吹”与“横吹”从汉鼓吹乐的杂合状态中析出,分别设类,但如何把握鼓吹与横吹乐的区别与联系,郭氏解题未能给出明确答案。如果我们根据出土文献保存的音乐表演信息,借助音乐图像与书面文献资料互证,便不难发现,在乐器的使用上,鼓吹无角,却有鼓、铙和短箫,歌者击铙、鼓为节而歌,构成鼓吹乐的基本特征。横吹则以角、笛为标志性乐器,又有小型节鼓,鼓手或即歌者。值得强调的是,横吹曲虽然源于北狄诸国的马上之乐,但马上奏乐只能算作骑吹的标志,与军乐并无必然联系,亦非鼓吹与横吹的区分标志。尤其是鼓吹与横吹乐自汉以后仍不断发展演化。通过音乐图像还可以看出,乐器使用上的差异所形成的音乐特征才是鼓吹与横吹乐的本质区别,这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目前书面文献记述零散不系统的缺憾,对乐府音乐学的研究至关重要。由汉至唐,鼓吹与横吹曲辞在音乐与文学的交织中继续发展,蔚为大观,郭茂倩将其从“鼓吹乐”中分列出来,不仅彰显了两类曲辞的音乐学与文学成就,还昭示出汉唐乐府诗的发展趋势与脉络,具有重要的乐府学意义。
乐府诗作为宫廷乐舞表演中使用的乐辞,乐舞表演生态的还原是理解、把握其艺术魅力的重要基础。因此,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在分类辑集汉唐乐府诗文本的同时,并以题解说明各类乐府诗所属的音乐特点,包括各类曲辞所属音乐的产生来源、隶属乐署、演奏乐人、乐器使用、表演方式、用途功能及其演变等。其中,鼓吹、横吹乐曾广泛使用于朝会、道路、军中,在实际演奏中往往密不可分,加上时代久远,历代嬗变,其间区别较难辨析清楚。出于《乐府诗集》的编纂体例及分类需要,郭氏虽以“有箫笳者为鼓吹,用之朝会、道路,亦以给赐……有鼓角者为横吹,用之军中,马上所奏者是也”[1]相区分,但仍留下诸多疑问。之后,王运熙、刘怀荣等学者皆试图进一步厘清二者的关系,但从刘怀荣《汉魏以来北方鼓吹乐横吹乐及其南传考论》一文所列大量资料看,鼓吹与横吹乐在用乐场合、演奏方式及乐器使用等方面都存在交叉,界限并不分明[2]。既然如此,究竟应如何理解郭氏的分类,能够轻易否定其分类的意义吗?
笔者以为,无论郭氏题解还是当今学者的研究,所依据的书面资料主要限于各时代乐舞表演的零散记述,仅能形成各时期古代乐舞的零碎印象,如同斑斑碎片,碎片间留下了许多空白。乐舞因时而变,记述前后不一,亟待新材料的出现填补这些碎片的空白。现今出土的音乐图像资料,特别是汉画像石中保留了不少乐舞表演的画面,恰可作为参照,故将其与文字资料相印证,以资对鼓吹与横吹乐悬疑之谜作进一步考察。
一、鼓吹乐的标志性乐器——铙
《乐府诗集》“鼓吹曲辞”解题云:“鼓吹曲,一曰短箫铙歌。”“然则黄门鼓吹、短箫铙歌与横吹曲得通名鼓吹,但所用异尔。汉有《朱鹭》等二十二曲,列于鼓吹,谓之铙歌。”[3]可见,郭茂倩“鼓吹曲辞”的分类不仅尊重蔡邕“短箫铙歌”的称名,同时也强调这部分曲目与其他鼓吹乐的区别。据《汉书·礼乐志》载,无论古兵法武乐抑或宴乐、祭祀乐,都置鼓员。另据郭茂倩题解,隋以后横吹四部乐当中,除第四小横吹部无鼓,其余三部皆有鼓,说明“鼓吹乐”的确与鼓有关,但就郭茂倩对“鼓吹”与“横吹”曲辞的分类看,“鼓吹”区别于“横吹”的音乐学特征实在于“铙”。那么“铙”究竟是怎样的乐器,又是如何演奏的呢?却未曾深究。
铙是商周考古中发现的一种铜制钟体鸣乐器,主要发现于河南,少量出土于鲁中南和陕西关中一带。“关于铙的名称,因所出带铭文的铙未见有自名的,故向来说法不一。李纯一先生通过对甲骨文用、庸、庚诸字并结合文献、实物进行研究,指出中原地区所出商代一般所谓的‘铙’就称之为‘庸’”[4],如图1所示:铙体呈合瓦形,甬中空呈管状,下粗上细,舞平,于内凹成弧形,铣间径大于舞修。正鼓部置有方形台面,钲部饰凸起饕餮纹,鼓内壁铸有铭文“古”字。

图1 商代殷墟二期 古铙《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第69页
此小铙柄短,且柄末粗而根细,是“为了便于在柄内插木,并置于座、架上来演奏”[5]。由于商代铙柄部插木的做法在无意中对高次谐波所起的阻碍作用,到了西周早期时,可能已被意识到。因此西周早期制作的甬钟“甬加长,末粗而根细,演奏方式与一般商铙不同,即为悬挂演奏”[6]。
不过,“铙”还有许多其他名称。如《说文解字》曰:“铙,小钲也。军法卒长执铙。”下图便是1980年11月发现于襄城县范湖乡盛庄西的新莽天凤四年(公元17年)的“钲”。

图2 天凤四年钲《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第50页
钲体作合瓦形,较扁长,舞上有甬,甬呈圆柱状,顶部细,根部粗,中部突起两道圆箍,两箍之间有一环,作悬挂之用。钲口部弧曲,钲身无纹饰。器身正中有铭文曰:“颍川县司盾发弩令正,重四十四斤,始建国天凤四年缮。”[7]天凤为新莽政权年号,适绿林赤眉农民起义之时。其后6年刘秀与莽军大战于昆阳,莽军40万全军覆没。此器出土地点盛庄,正是当年莽军阵地之属,故此钲当是莽军在昆阳战败后所弃之物。
此外,《说文》亦云:“铙也。似铃,柄中上下通。”[8]《周礼》“以金铙止鼓”注:“铙如铃,无舌有柄。执而鸣之,以止击鼓。”[9]而《广雅》则径谓“和、銮、鐲、铎、钲,铙、钟、鑮,铃也”[10]。考古发现“铃”的确从“铙”演化而来。“天门石家河发现了可能是体鸣乐器的铜铃。一般认为,这种陶铃与后起的铜铃乃制铜制钟类乐器中出现较早的铜铙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湖北地区的铜铙,在阳新曾出土过2件,其器形大小介于湖南所出大铙和中原地区出土的小铙之间。从形制上看,似更接近于中原地区的小铙”[11]。
从音乐考古发掘的实物来看,铙与钲、铎、句鑃、甬钟和钮钟都属钟类击奏乐器,其体制都是平顶、凹口、侈铣的合瓦形钟体。正因其形制相同,故名称被互相混用。

图3 方建军《地下音乐文本的图解——方建军音乐考古文集》第195页
总之,以钲、铙、鐲、铃等乐器伴奏演唱的曲辞均可称“铙歌”。

图4 东汉成都站青杠坡鼓吹画像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四川卷》第174页
“铙”的演奏方式有两种,一是乐人单手持铙敲击的演奏方式。以1952年成都站东乡青杠坡3号东汉墓出土的鼓吹画像砖为例,此为军旅出行时所用仪仗,详看下图:图上6骑,分两横队并辔而行。右上一骑执幢麾,并执笳于口中演奏。居中一骑,马上树鼓,骑吏正挥槌击鼓,下一骑吏执排箫吹奏。左上一骑,一手执铙,一手举桴欲击。居中骑吏吹笳,下一骑吏吹排箫。与之相似的尚有1954年成都羊子山出土的东汉鼓吹画像砖,见下图:

图5 东汉成都羊子山鼓吹画像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四川卷》第175页
图上也是6骑,骑吏头戴圆顶帽,身着广袖长服,分两横队并辔而行。右上一骑,上树一幢,幢上羽饰飘舞。居中一骑,手执桴作击铙状(铙被马足所掩),下一骑吹奏排箫。左上一骑,上树建鼓,鼓上木柱顶端饰有羽葆,其两侧下垂。居中一骑,似弹琵琶。下一骑执排箫而吹。除了马上从行鼓吹,还能看到持铙于殿庭演奏鼓吹的情景,以南阳县卧龙岗崔庄出土的汉画像石为例:

图6 东汉南阳崔庄乐舞画像石《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第167页
图中除了杂技舞者,另有一人鼓瑟、两人吹排箫播鼗鼓、一人吹埙,右首尚有持钲以锤敲击者。这位持钲者也就是执节而歌者。这三例持钲铙敲击图极为罕见,弥足珍贵。原因在于我们看到的汉画像石多见击鼓者,却少见击钲铙者。
除了以上所列单手持钲敲击图之外,还有一种演奏方式是敲击附着在鼓上的丁宁。这种方式在汉画像石中更为多见。《诗·小雅·采芑》云:“方叔率止,钲人伐鼓。”[12]因为伐鼓的钲人需要在伐鼓的间隙击金钲以止鼓,最方便的设置是在鼓上附设铙,即小钲,鼓者方可以不移位而便捷击铙。如果是大钲旁置,演奏则颇不顺手,所以铙即钲人在伐鼓时所击之钲。以下面这幅1978年在河南省唐河县出图的汉画像石为例:

图7 西汉天凤五年汉郁平大尹冯君墓乐舞画像石《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第160页
左边的鼓者左手正注视并敲击建鼓下方的球状体,即丁宁,也称令丁。《左传》宣公四年:“伯棼射王,汰辀,及鼓跗,著于丁宁。”杜注:“丁宁,钲也。”[13]可见丁宁与鼓跗相邻。《文献通考》将金镯、金钲和丁宁等同,并引郑玄:“镯如小钟,军行鸣之,以为鼓节。盖自其声浊言之谓之镯,自其儆人言之谓之丁宁,自其正人言之谓之钲,其实一也。”[14]《国语·吴语》曰:“昧明,王乃秉枹,亲就鸣钟鼓、丁宁、錞于振铎,勇怯尽应”。韦昭注:“丁宁,谓钲也,……军行鸣之,与鼓相应。”《札记》引段玉裁说,当作“丁宁,令丁,谓钲也。”[15]一般的画像石风格粗犷,难作精细刻画,只能取其大概轮廓,刻成球状,所以让人难以领悟这就是钲。而南阳新店出土的画像石拓片,参见下图:

图8 东汉早期南阳新店鼓舞吹箫画像石《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第171页
可以清楚看到丁宁是如何固定在鼓身上的,而且左边的丁宁刻画精细,显示出左侧丁宁朝向左下方的椭圆口,显然是钲铙的造型。
下方这幅1978年出土的西汉建鼓画像石则具有更丰富的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到,中间一层鼓下悬垂的两个三角状物体,似钟而较小,其实就是钲。不过华盖羽葆下面的横木下及鼓架下各有两个圆盘状物,看来也应该是击打乐器。鉴于后世往往将“铙”“钹”并称,这种击打乐器会不会就是钹呢?《辞源》载:“【铙钹】乐器。古称铜钹、铜盘、铜钵。其围数寸,隐起如浮沤,贯之以韦,相击以和乐。”[16]此说似据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马氏释“铜钹”云:“铜钹谓之铜盘,本西戎南蛮之器也”;释“铜钲”则说:“钲如大铜曡(似铜盘),悬于簴而击之,南蛮之器也。”[17]根据以上材料,笔者认为:图9中的四个悬于簴的盘状物是后世钹的初始形态,而鼓下悬垂的两个三角形物体形状似钟而较小者才是钲铙。因为铙和钹的悬挂位置及功用近似,才导致后世铙钹并称混合为一体。至于秦汉时代及其以前的铙和钲,则因形状、功用相近而被用来互释。

图9 西汉方城东关击建鼓画像石《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第165页
如是,则图10这幅在新野县张家楼1962年出土的画像砖拓片中,除了吹排箫者等人,鼓下的两个球状物显然是“丁宁”,而鼓左右上方的两个圆形物也应是盘状物,我们姑且称之为“钹”。在汉画像石中,此类图像颇多。1973年出土的东汉早期的南阳王寨乐舞画像石,参见图11:

图10 西汉晚期新野张家楼鼓舞吹箫画像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第193页

图11 东汉早期南阳王寨乐舞画像石《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第179页
左边鼓上饰羽葆,鼓下两侧有圆形球状物,鼓侧两男子高髻、窄衣、细腰,双手各执鼓槌,跨步蹲身张臂,且鼓且舞。中间一女子,高髻、长袖、细腰,翩翩起舞。舞者之右,又有3人伴奏,一人吹箫播鼗,一人吹埙,另一人左手拊耳,似在歌唱。再以1983年南阳县辛店乡英庄村的汉画像砖为例,如下图:

图12 东汉南阳英庄乐舞画像石《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第181页
帷幔下共刻6人,画面正中置建鼓,鼓下有虎形座,鼓上饰羽葆,鼓旁两男子双手各执鼓桴,跨步张臂,且鼓且舞。鼓左2人站立,吹箫拨鼗。鼓右亦2人,一人跽坐掷3丸,一人身体前倾,仰面作戏。
在汉代画像资料中,也有许多无“钲”无“铙”的鼓乐图像。比如下面这幅于郑州二里岗出土的空心画像砖拓片,只有建鼓,而无“钲”“铙”,这就不是鼓吹乐。已出土的此类古代音乐文献资料很丰富,能够真实反映当时鼓乐的演奏风貌及特征。

图13 西汉晚期郑州二里岗乐舞空心砖建鼓舞图《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第187页
综上所述,郭茂倩的“鼓吹曲辞”实即蔡邕所谓“短箫铙歌”。顾名思义,以短箫与铙为标志性乐器,执节而歌,正是其音乐的本质特征。汉画像石的资料揭示出,铙既可单独持而击奏,又可附着于鼓上,即有铙便有鼓,乐人伐鼓击铙以为节,这才构成鼓吹乐的基本内涵。不过,铙与鼓、埙的编器方式早在商代就已出现。方建军《河南出土殷商编铙初论》认为:“从目前发现的商晚期鼓、特磬、编磬、编铙和埙来看,它们当可组成一个比较可观的乐队。其编制和配器方式似应为:三件埙中的两件同调埙担任高声部主旋律演奏,编磬、编铙则各有一组,每组一般是三件或多至五件,用于演奏中声部主旋律或调式框架音,特磬则突出调式主音,与鼓一起加强节奏重音,以增强乐曲的表现力。”[18]
二、“鼓吹”与“横吹”的区别
如何区分“鼓吹”与“横吹”?郭氏“横吹”解题云:“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其后分为二部,有箫、笳者为鼓吹,用之朝会、道路,亦以给赐。汉武帝时,南越七郡,皆给鼓吹是也。有鼓角者为横吹,用之军中,马上所奏者是也。”[19]他首先强调“横吹”是“马上奏之”,题解还引《宋书·乐志》“此则列于殿庭者名鼓吹,今之从行鼓吹为骑吹,二曲异也。又孙权观魏武军,作鼓吹而还,此应是今之鼓吹”。此处又多出了“骑吹”一词,受沈约的影响,南宋姜夔《圣宋铙歌鼓吹曲十四首诗序》云:“臣闻:铙歌者,汉乐也。殿前谓之鼓吹,军中谓之骑吹。”[20]演奏方式的不同是“鼓吹”与“横吹”的区别。除此之外,郭氏也强调乐器的不同,他又引《晋书·乐志》曰:“横吹有鼓角,又有胡角。……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21]为便于理清头绪,兹将以上材料及郭氏解题涉及的相关论述列表如下:

称名乐器使用情况附加说明鼓吹箫、笳。《宋书·乐志》:“鼓自一物,吹自竽籁之属,非箫鼓合奏。”列于殿廷(《宋书·乐志》)用之于朝会、道路(郭氏解题)。包括短箫铙歌、骑吹、横吹。骑吹应劭《汉卤簿图》:“唯有骑执箛,箛即笳,不云鼓吹。”从行鼓吹(《宋书·乐志》)铙歌者,军中谓之骑吹(姜夔)。骑执箛,不云鼓吹。或骑吹,亦或横吹。横吹有鼓角,又有胡角。横吹有双角,即胡乐(《晋书·乐志》)。用之军中,马上所奏(郭氏解题)。隋以后与鼓吹并列。但横吹包括骑吹。短箫铙歌鸣笳以和箫声,非八音也。骚人曰:“鸣篪吹竽”是也。(刘瓛)军乐。(蔡邕分类)初未名鼓吹。
通过上述材料分辨“鼓吹”与“横吹”的确很困难,下面借助出土文献来作考察。下图是1958年河南邓县学庄村出土的南朝画像砖,对于了解南朝横吹曲的演奏形式及乐器类别应有较实在的帮助。

图14 南朝邓县横吹画像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第184页
左图中四人,步调整齐,可以想见其演奏的节奏感很强。前两人竖吹长角,角口饰有彩幡流苏;后两人腰挂扁鼓,右手执桴,左手持手摇乐器,既是鼓者,也应是歌者。右图五人,由右至左,一人吹横笛、一人吹排箫、两人横吹长角、一人吹胡笳。长角口处饰有垂缨流苏。他们的步调与左图四人完全一致,可以想见其演奏节奏也完全一致。我们无法断定这两块墓砖在墓壁上是否相连,但从两组演奏者的衣饰、步调、乐器组成分析,他们应是同一个演奏团队。郭氏解题对南北朝时期横吹的演奏情况语焉不详,但云:“自隋已后,始以横吹用之卤簿,与鼓吹列为四部,总谓之鼓吹,并以供大驾及皇太子、王公等。一曰棡鼓部,其乐器有棡鼓、金钲、大鼓、小鼓、长鸣角、次鸣角、大角七种。……二曰铙鼓部,其乐器有歌、鼓、箫、笳四种……三曰大横吹部,其乐器有角、节鼓、笛、箫、筚篥、笳、桃皮筚篥七种……四曰小横吹部,其乐器有角、笛、箫、筚篥、笳、桃皮筚篥六种。”[22]这两块画像砖上的乐队与第三大横吹部相较,除了缺少两种筚篥,其他全都齐备。说明这两块画像砖的内容所显示的正是横吹曲演化到南朝时期的新变形态。可见所谓“列于殿庭”还是“从行”,不应是鼓吹与骑吹的区分标志。前代“马上奏之”的鼓吹曲,从汉画像资料中也可以看到。除了上文所举成都画像砖外,在1978年四川新都东汉墓出土的画像砖亦是“马上奏之”(见下图):

图15 东汉 新都汉墓鼓吹画像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四川卷》176页

图16 东汉 新都汉墓鼓吹画像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四川卷》176页
不仅有胡人骑马吹奏竽和排箫的形象,甚至有两人骑在骆驼上击建鼓的形象。可见郭氏所谓“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乐也。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云云确有所本,但是发展到南朝阶段,与其说“马上奏之”是横吹曲的标志,倒不如说这是骑吹乐的标志更准确些。因此他所谓“有鼓、角者为横吹,用之军中,马上所奏是也”,强调横吹乐都是“马上奏之”,便与事实有了较大出入。
事实上,军乐与“马上奏之”之间并无必然联系。1986年新野樊集乡西汉晚期墓出土的长1.22米大汉画像砖上,生动展现了汉、胡征战的场面,其右端汉主帅身后有一人挥桴击鼓助威,建鼓半隐没在画面之外,所隐没的也可能有箫、铙之类鼓吹乐,但至少那位击建鼓的鼓员,并非在马上击鼓。详见下图:

图17 西汉晚期新野樊集37号墓击鼓攻战画像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第192页
再看下面这块在河南南阳淅川县西岭林业高中出土的画像砖:

图18 南朝淅川吹角画像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第199页
右边一人牵马而行,短褐打扮,似为马夫;马后跟随3名仆从,一人持曲柄盖,两人侧头横吹长角,角口饰有垂缨流苏。从构图角度看,主人竟没有出现。故此砖前后还应有其他画像砖相连形成一组演奏团队。值得注意的是,图中虽有马,但这支“从行”乐队并非“马上奏之”,如称“骑吹”,显然名不副实,仍应视为横吹乐队。按《晋书·乐志》的说法,两处的画像砖刻画的都是胡乐。根据这些材料,我们不妨推断:横吹曲与鼓吹曲的区别应仍然由所使用的乐器来决定。横吹曲有横吹的角和笛,又有小型节鼓,鼓手或即歌者;鼓吹无角,却有鼓、铙和短箫,而伐鼓击铙者同时又或可是歌者。
总之,古代乐舞的表演关涉到乐署、乐工、乐器、演奏方式、场合及功用等多种层面,并随时代变迁而有所变化,繁复如此,需要我们综合借鉴各类文献,以音乐图像与书面记述相参照,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对古代乐舞的全息艺术生态加以领会与解读,以此为基础,方能进一步厘清乐府诗的乐类特征。
三、《乐府诗集》“鼓吹”与“横吹”分类的乐府学意义
“鼓吹”乐在汉代是个杂合的概念,王运熙先生《汉代鼓吹曲考》、《说黄门鼓吹乐》认为,汉代“鼓吹”包括黄门鼓吹乐人演奏的黄门鼓吹(相和歌、杂舞曲)、短箫铙歌、横吹曲,通称“鼓吹”。《乐府诗集》“鼓吹曲辞”解题云:“鼓吹曲,一曰短箫铙歌。”“然则黄门鼓吹、短箫铙歌与横吹曲得通名鼓吹,但所用异尔。汉有《朱鹭》等二十二曲,列于鼓吹,谓之铙歌。”[23]郭氏所谓“鼓吹曲辞”当特指“短箫铙歌”、“铙歌”。
“短箫铙歌”名称源于东汉蔡邕对汉乐的分类,《东观汉记·乐志》记曰:
汉乐四品:一曰《太予乐》,典郊庙、上陵殿诸食举之乐。……二曰《周颂》《雅乐》,典辟雍、飨射、六宗、社稷之乐。……三曰《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诗》所谓“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短箫铙歌》,军乐也。其传曰黄帝岐伯所作,以建德扬威,风劝士也。[24]
蔡邕将汉乐分为四品的依据应是东汉时期具体的礼乐施用情况。以太予乐为例,包括郊庙、上陵食举用乐。所谓郊庙,《南齐书》云:“汉东京《礼仪志》:‘南郊礼毕,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蔡邕所据亦然。”[25]可见汉郊庙乐为“五供”祭祀用乐。从周至汉,演奏郊庙乐的乐署、乐人并非一成不变,据《唐六典》载:
周人建国,左宗庙,右社稷,祭天于南郊之圜丘,就阳位也;祭地于北郊之方坛,就阴位也。故有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以时而祭则征役于司隶,帅其属而修除之。秦、汉奉常属官有太祝令、丞,景帝改为祠祀,武帝更曰庙祀。后汉庙祀属于少府。[26]
西汉哀帝罢乐府而又有所变化,曾将郊祭乐演奏人员别属于祭祀南北郊的郊社署。《汉书·礼乐志》云:
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条奏,别属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乐人员六十二人,给祀南北郊。”[27]
再看蔡邕所说的上陵食举之乐。范晔《后汉书》云:“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原陵,如元会仪。”唐李贤注曰:《汉官仪》曰:“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寝于墓侧,汉因而不改。诸陵寝皆以晦、望、二十四气、三伏、社、腊及四时上饭,其亲陵所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庄具。天子以正月上原陵,公卿百官及诸侯王、郡国计吏皆当轩下,占其郡国穀价,四方改易,欲先帝魂魄闻之也。”[28]据《读通鉴论》卷七云:“明帝即位元年,率百官朝于先帝之陵,上食奏乐,郡国计吏以次占其谷价及民疾苦,遂为定制。”[29]上陵食举之礼是在东汉明帝(58年)时才成为定制。汉代食举乐除了上陵食举之外,还有宗庙食举、殿中御饭食举及太乐食举4种,详见下表:

食举乐类型曲目附加说明宗庙食举鹿鸣、承元气、思齐皇姚、六骐麟、竭肃雍、陟叱根前二者为章和二年之前宗庙食举用乐,后四为章和三年新造。上陵食举鹿鸣、承元气、思齐皇姚、六骐麟、竭肃雍、陟叱根、重来、上陵前六者为章和三年宗庙食举乐,另加后二曲而成。殿中御饭食举鹿鸣、思齐皇姚、六骐麟、竭肃雍、陟叱根、惟天之命、天之历数前五者为章帝三年宗庙食乐,另加后二曲而成太乐食举鹿鸣、重来、初造、侠安、归来、远期、有所思、明星、清凉、涉大海、大置酒、承元气、海淡淡鹿鸣、承元气是章帝二年宗庙食举乐,后加十一曲而成。
由上表可知,汉代各类食举乐曲目是在章和二年(88年)以后逐渐完善并基本定型的。到了熹平元年(172年),“春,正月,车驾上原陵。司徒掾陈留蔡邕曰:‘吾闻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礼,始谓可损;今见威仪,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恻隐,不易夺也。礼有烦而不可省者,此之谓也’”[30]。蔡邕根据殷人重神不重鬼的观念,认为上陵食举之礼乐皆可减省,但观灵帝意在孝悌,观念遂有所转变。由此可见,蔡邕将食举乐与郊庙、上陵均隶属于郊庙神灵所用的《太予乐》,皆是依据当时的礼乐实况。
上表食举乐中的《上陵》、《远期》、《有所思》三曲,与铙歌十八曲中的三曲相似,郭氏云:“(《上陵》)古词大略言神仙事,不知与食举曲同否?”[31]“按《古今乐录》汉太乐食举第七曲亦用之,不知与此(《有所思》)同否?”[32]关于铙歌《远如期》,郭氏云:“《宋书·乐志》有《晚芝曲》,沈约言旧史云:‘诂不可解’,疑是汉《远期曲》也。《古今乐录》曰:‘汉太乐食举曲有《远期》,至魏省之。’”[33]
汉代的食举乐为食礼用乐。食礼不饮酒,以饭为主。食礼依轻重不同分飨、食、燕三种不同的食礼,盛者九举九饭,其次七举七饭,再次五举五饭。《大戴礼记·保傅》:“食以礼,徹以乐。”[34]《周礼·天官·膳夫》:“卒食,以乐徹于造。”造乃“竃”之借字。汉明帝即位元年的上陵食举应为飨礼。据《通典》云:
《周官》云:“王大食,三侑,皆令钟鼓。”汉蔡邕云:“王者食举以乐。今但有食举乐,食毕则无乐。按膳大职‘以乐侑食’,《礼记》云:‘客出以《雍》,彻以《振羽》。’《论语》云:‘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如此,则彻食应有乐,不容同用食举也。”[35]
君王食毕,客出时须奏《雍》,侍食者撤去席上食物时要以《振羽》乐章作为伴奏,撤食者之动作要与音乐节奏相合。《礼记·哀公问》:“和鸾中《采荠》,客出以《雍》,徹以《振羽》。”郑玄注:“《采荠》、《雍》、《振羽》皆乐章也。”[36]可以看出,汉代食举礼中就只有食举乐,而无撤食之乐,而蔡邕认为,撤食时也当用乐,既然没有专门的撤食之乐,那么这就会产生借用曲目的情况。《古今乐录》曰:“汉章帝元和中,有宗庙食举六曲,加《重来》《上陵》二曲,为《上陵》食举。”[37]上陵食举中又加的两曲,可能是食举乐,也可能是撤食用乐。《淮南子·主术》云:“鼛鼓而食,奏雍而徹。”[38]可见《上陵》等曲演奏时必有钟、鼓乐器的使用。《乐府诗集》题解还引《宋书·乐志》曰:“汉享宴食举乐十三曲,与魏世鼓吹长箫同。长箫短箫,《伎录》云:‘丝竹合作,执节者歌。’又《建初录》云:‘《务成》、《黄爵》、《玄云》、《远期》,皆骑吹曲,非鼓吹曲。’此则列于殿庭者名鼓吹,今之从行鼓吹为骑吹,二曲异也。……按《西京杂记》:‘汉大驾祠甘泉、汾阴,备千乘万骑,有黄门前后部鼓吹。’则不独列于殿庭者为鼓吹也。汉《远如期曲》辞,有‘雅乐陈’及‘增寿万年’等语,马上奏乐之意,则《远期》又非骑吹曲也。”[39]可见,“短箫铙歌”中的曲辞演奏时不限于短箫的使用,还有使用长箫,“丝竹合作,执节者歌”。在演奏场合及方式上,不仅有列于殿庭者,还有从行鼓吹,马上奏乐的情况,足见乐舞表演的灵活性,从汉画像资料中的确可以看到上文描述的演奏情景。1986年出土于新野县樊集乡第23号西汉晚期墓、用作墓门的画像砖正表现了这种场景,详见下图:

图19 西汉晚期新野樊集鼓舞画像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第199页
图中殿堂下的演奏者分两层:上二人以舞姿击鼓、铙;下五人,一鼓瑟,两相对者吹排箫,一击鞞,一舞刀。《乐府诗集》引《宋书·乐志》曰:“雍门周说孟尝君:‘鼓吹于不测之渊。’说者云:‘鼓自一物,吹自竽、籁之属,非箫鼓合奏,别为一乐之名也。’”[40]其中说者所云并不确切,上图表现的恰恰是“箫、鼓合奏”,正如《伎录》所云,是“丝竹合作,执节者歌。”所谓执节而歌者,即画面中击鼓铙者,二人击鼓铙为节,边击边舞边歌。《汉书·礼乐志》称:哀帝下诏罢乐府官,而将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别属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称:古兵法武乐“凡鼓十二,(各类鼓)员百二十八人,朝贺置酒陈殿下,应古兵法。”[41]显然,古兵法武乐属于朝会所用的鼓吹乐。
然而,郭氏明知部分“铙歌”曲目不限于军乐使用,但又以“所用异耳”作为其“鼓吹曲辞”分类的区别性特征,足以表明“铙歌”在其他场合或用途的使用并不影响“短箫铙歌”作为一种类别存在的意义。此种情形正如“短箫铙歌”部分曲目固然用于食举乐,但铙歌十八曲作为军乐是东汉用乐的事实。因此蔡邕根据东汉时期礼乐施用的实际情形,考虑音乐的用途与场合不同,把“短箫铙歌”独立成类。郭茂倩为“短箫铙歌”设立“鼓吹”一类,其解题云:“汉有《朱鹭》等二十二曲,列于鼓吹,谓之铙歌。及魏受命,使缪袭改其十二曲,而《君马黄》……十曲,并仍旧名。是时吴亦使韦昭制十二曲,其十曲亦因之。……晋武帝受禅,命傅玄制二十二曲,而《玄云》《钓竿》之名不改旧汉。宋齐并用汉曲。又充庭十六曲,梁高祖乃去其四,留其十二,更制新歌,合四时也。北齐二十曲,皆改古名。……后周宣帝革前代鼓吹,制为十五曲,……隋制列鼓吹为四部,唐则又增为五部,部各有曲。”[42]显然,郭茂倩之所以能够在蔡邕分类基础上实现更大的突破,正是因为他能站在汉唐乐府发展的高度,目光如炬,看到铙歌曲历经魏晋后世之改造,成为历代制礼作乐、称述功德的经典套曲的演变脉络,以“短箫铙歌”专为一类正是充分彰显了这一乐府学意义。同样,汉代“鼓吹”乐中的“横吹”、“相和”、“杂舞曲”也因同样的原因,被郭茂倩一一设类,足以见出,音乐学与文学意义的双重并举,不仅是郭茂倩强调的类别意义,还同时体现出以《乐府诗集》的结撰精心呈现汉唐乐府发展脉络的用意。
[1][3][19][21][22][23][31][32][33][37][39][42]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09、224、309、309、310、224、229、230、232、228、223、224页。
[2]刘怀荣:《汉魏以来北方鼓吹乐横吹乐及其南传考论》,《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4]李纯一:《庸名探讨》,《音乐研究》,1988年第1期。
[5][6][11][18]方建军:《地下音乐文本的读解——方建军音乐考古文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65、165、176、135页。
[7]《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
[9][12][13]《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721、426、721页。
[8]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97页。
[10]王念孙:《广雅疏证》,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7页。
[14][17]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95、1195页。
[15]《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610页。
[16][38]《辞源》,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212、1800页。
[20]《丛书集成》,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49册《白石道人歌典》卷一,第1页。《宋史·乐志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054页,所述略有出入。
[24]刘珍等:《东观汉记》,见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9页。
[25]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2-123页。
[26]张九龄著,袁文兴编:《唐六典全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3页。
[27][41]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73、1073页。
[28]范晔:《后汉书》,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34页。
[29]王夫之:《读通鉴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续修四库全书》第499册,第566页。
[30]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78页。
[34][36]钱玄、钱兴奇编著:《三礼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3、1053页。
[35]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69页。
[40]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58-559页。
On the Music Features and Yuefu Academic Significance of"guchui" and"hengchui"of"Yuefu Poetry"
WANG Shu-mei YU Sheng-ting
(Literature colleges of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Xuzhou,221116)
Yuefu Poetry;Guchui;Hengchui;nao
Although"guchui"and"hengchui"have been selected out of the heterozygous state of precipitation respectively by Guo Mao-qian from the Chinese drum music,he didn't clearly tell the difference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m.According to the music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preserved in unearthed documents and by means of music image,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there are drums,cymbals and short flute except horns in the music of guchui,the singer sings striking cymbals which constitut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However angle and flute as the sign of musical instruments,there is also a small drum in hengchui music,and the drummer is maybe the singer.It is worth emphasizing that although hengchui songs are due to the music of the Northern-Di countries,but performing on the horse only as a sign of qichui and it is not necessarily linked with army music and it is not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with guchui.The most important difference is the musical characteristics caused by the different instruments,what must have deeply influence on the performance and func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songs.Both guchui and hengchui are still evolving continually after Han Dynasty,changes can be seen in music images which help to make up the deletion of the documents.The classification of"Yuefu Poetry"on" guchui"and"hengchui"not only embodies two lyrics of music and literature,but also show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Yuefu music and context,which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n Yuefu academic.
I207.226
A
2095-5170(2014)06-0010-08
[责任编辑:邵迎武]
2014-09-12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魏晋乐府诗的诗乐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0CXW020)、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诗词曲源流史”(项目编号:118LZD105)、“《乐府诗集》整理与补编”(项目编号:138LZD110)及江苏省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阶段性成果。
王淑梅,女,江苏徐州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于盛庭,男,江苏徐州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西泠印社社藏名家大系·李叔同卷:印藏》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