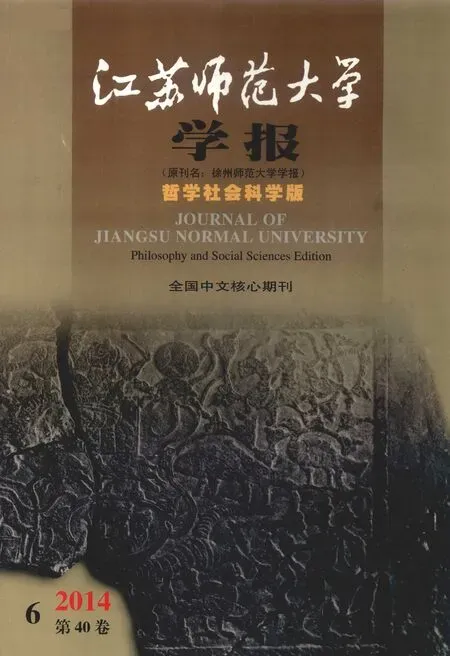西“工”东渐:近代西方工程学知识与技术在中国的传播
房 正
(教育部高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080)
西“工”东渐:近代西方工程学知识与技术在中国的传播
房 正
(教育部高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080)
近代工程学;工程知识与技术;西学东渐
16、17世纪,中西传统技术开始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中国传统技术朝着“技艺”的方向发展,而西方传统技术则与近代科学越走越近,并最终于18世纪中叶相结合,促成了近代工程学的诞生。与近代大多数学科门类一样,西方工程学知识与技术通过来华传教士逐渐传入中国,吸引了中国本土知识分子的注意。实际上,早在近代工程学诞生以前的晚明时期,中西传统“工程”技术之间就有过短暂接触,以王征为代表的少数文士已经开始关注西方“工程”知识与技术,并留下了《奇器图说》这样的重要译著。但由于各种原因,这时的中西“工程”交往,范围不大,效果也并不理想。晚清时期,在“西学东渐”大背景下,西方近代工程学知识与技术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国,吸引了大批中国本土知识分子投身其中,形成了大量与工程学相关的译著和著作。得益于此,近代工程学教育也逐步兴起,本土工程技术人才不断涌现,工程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近代西方工程学知识与技术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近代工程学的发端,成为对近代工业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积极影响的重要因素。
18世纪中叶,西方社会传统技术与近代科学相结合,近代工程学就此诞生。与近代其他学科门类一样,西方工程学知识与技术通过来华传教士逐渐传入中国,吸引了中国本土知识分子的注意。实际上,早在晚明时期,中西传统“工程”技术就有过短暂接触,但由于各种原因,效果并不理想。伴随着晚清西学东渐的浪潮,西方工程学知识与技术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国,涌现出一大批热衷于西方工程学的中国本土知识分子和大量工程学译著、著作。得益于此,中国近代工程学教育开始发端,工程技术人才不断涌现,工程技术快速进步,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了基础。
一、中西社会传统技术的不同走向及近代工程学在西方的诞生
元明以前,中国的传统技术长期走在世界前列。被称为“三大技术”的陶瓷技术、建筑技术和纺织技术,曾经创造出无数令世人惊叹的瑰宝;被奉为“四大发明”的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不仅推动了中国传统技术走向巅峰,西传之后更成为促使欧洲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因素。
中国传统技术一直保持着这种领先优势,直到16、17世纪。自晚明开始,中西传统技术开始出现截然不同的走向。
中国传统技术逐渐向“技艺”的方向前进。技术的延续依靠师徒之间代代相传,技术的进步依靠富有经验的工匠在实践中摸索。有科技史论者这样描述晚明中国传统科技的走向:一方面科学的发展逐渐被技术的发展所取代,科学成就明显减少;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量的缓慢增加,而很少有质的突破[1]。这一趋势同样被来华的传教士察觉,利玛窦曾如此描述:“因为这里的人民习惯于生活节俭,所以中国的手艺人并不为了获得更高的售价而在他创作的物品上精益求精。他们常常牺牲产品的质量,而只满足于表面好看以便吸引买主注目。”[2]
但就在同时,西方的传统技术却与近代科学越走越近。17世纪,经过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等人的努力,近代科学终于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找到了自己的观察与实验方法。18世纪中叶,欧洲爆发了工业革命,工场手工业开始向机器大工业转变。机器被广泛使用后,生产部门的专业化、复杂化程度及知识含量不断提高,技术革新仅靠工匠的直观经验和技艺已远远不够。为探究机器大工业时代工程问题的技术机理,工匠们开始关注自然科学的进展,以便寻求科学理论的指导。与此同时,自然科学理论日趋成熟,有些领域的理论成果已走在了技术的前面,具备了指导工程和生产实践的功能;适合于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的社会建制如大学实验室、工业试验室等已初步形成,作为学者的科学家也开始关注科学理论在实际中的应用。这样,工程技术的发明和发展进入了以自然科学理论为主导的新时期。于是,工程领域的科学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逐渐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工程学。土木工程学、机械工程学、矿冶工程学、电机工程学、化学工程学等学科于19世纪相继在英、法、德、美等国家诞生[3]。
然而,在西方发生的这一切,似乎与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毫无关系,直到一群陌生人的到来。
二、晚明时期中西传统“工程”技术的短暂接触
(一)王征与《奇器图说》:晚明中西传统技术交流的“昙花一现”
16世纪下半叶,即晚明时期,西方天主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为中西传统“工程”技术的交流与融合架起了桥梁。中西传统“工程”技术虽然只经历了短暂接触,却已经吸引了少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并孕育出了王征这样杰出的“机械工程师”和《奇器图说》这样重要的“机械工程”著作。
王征(1571—1644),陕西泾阳人,字良甫,号葵心。他自小受父(私塾先生,兼长算学,曾著《算学歌诀》)、舅(通晓兵法、善制器械)影响,对传统科学和技术很感兴趣。王征24岁中举,但直到52岁才中进士,其间虽然“连年公车不遇”,却恰逢“耶稣会士利玛窦讲学京师,……以屡上公车之故,亦时闻绪论。且性好格物穷理,尤与西士所言相契。遂受洗礼,圣名斐理伯”[4]。
1626年,王征在与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的交流中获知西方《诸器图说全帙》等机械书籍的概貌,遂挑选“其中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甚急者”,由邓玉函口授、王征执笔及绘图,编译成书三卷,名为《远西奇器图说录最》。连同王征自著《新制诸器图说》一卷,于1627年刻印成书,刊行于世。后世多将两书合版,简称为《奇器图说》[5]。
《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共分三卷:第一卷为“重解”,叙述地心引力、浮力、重心、比重、各种形体重心的求法等初等概念及其基本原理,其中包括流体静力学的“阿基米德”原理;第二卷为“器解”,叙述各种简单机械的构造原理、计算方法及其应用;第三卷为“力解”,谈各种机械的实际用途。全书“论各色器具之法,凡九十二条,次起重十一图,引重四图,转重二图,取水九图,转磨十五图,解木四图,解石转碓书架水日晷代耕各一图,水铳四图。图皆有说,而于农器水法尤为详备”[6]。《新制诸器图说》则收录了王征本人动手制作转磨、虹吸、鹤饮、刻漏、水铳、连弩、代耕等机械工具的方法和图录[7]。
虽然近代机械工程专家曾对《奇器图说》所记载的各种机械工具提出质疑,但却从不否认王征在中国机械工程史上的重要贡献。《奇器图说》所使用的一些名词和机械原理,除少数后来改译外,至今仍在沿用,例如“重学”、“重心”、“杠杆”、“流体”、“齿轮”、“螺丝”、“机器”、“起重”等。20世纪30年代,刘仙洲等一批机械工程专家编译和审定工程名词时,仍将《奇器图说》作为重要参考。
除王征外,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也都在此期的中西交流中对西方机械技术有所了解。徐光启曾与熊三拔合译《泰西水法》六卷,其中卷一、卷二和卷六实际上都涉及西方“机械工程”的相关内容。李之藻曾与传教士合译《同文算指》、《圜容较义》、《名理探》等著作,在西方数学、地理学、逻辑学输入方面贡献甚大[8]。
(二)晚明时期中西“工程”技术交流的影响范围与原因分析
晚明时期,尽管出现了王征、徐光启、李之藻等受西方“工程”知识与技术影响颇深的本土知识分子,但此时的中西方交流并未引起中国传统技术的根本性变革,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
一是受众仅为少数知识分子。晚明时期,与传教士关系密切、有机会接触和学习西学的基本以知识分子为主,而且仅局限于知识分子当中的极少一部分。熊月之根据《畴人传》和《徐光启集》等资料作过统计:自晚明至晚清西学东渐高潮兴起以前,明显受西学影响的科学家、学者仅有173人[9]。这与当时每年数以万计的科举应试者相比,可谓凤毛麟角。
二是传入知识以天文、历算为主,机械技术所占比重不大。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对天文、历算非常重视,早期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也正是依靠这两方面的知识获得当局认可。因此,传教士带来的西学中,天文和历算占了很大的比重,而有关西方传统机械技术的内容却很少。
三是技术应用范围狭窄,影响有限。除与天文、历算相关的机械技术在皇朝中心得以应用外,其余西方“工程”技术在中国并未得到大范围的应用。即使如王征这样学习西学并竭力实践的人,在当时的影响范围实际上也很有限。《奇器图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得到其应有的地位,而王征所制作的机械器具使用范围仅限其周边,并没有获得更大范围的推广。
造成以上状况的原因深埋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和认知观念当中:首先,传统知识分子自小习四书五经,奉孔孟为圣贤,又有“科举入仕、光宗耀祖”的理想,已经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惯性。其次,工程技术在传统文化中属于“艺”而非“道”,属于“形而下”而非“形而上”,是传统“读书人”所不应学或者说不屑学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何接触并投身西学的知识分子多为“科举落第的秀才”。
晚明西学东渐更像是中西传统“工程”技术之间的一次碰撞,擦出了像王征和《奇器图说》这样美丽的火花。但遗憾的是,这美丽的火花稍纵即逝,并没有点燃中西“工程”技术交流的熊熊烈火。18世纪初,因宗教礼仪问题,清政府与罗马教廷之间、中国耶稣会与罗马教廷之间、耶稣会与其他天主教会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最终以康熙禁止天主教在华活动、罗马教廷解散耶稣会收场。中国传统技术又步入了“冬眠期”。
三、晚清西学东渐浪潮中的近代工程学
(一)西方近代机械工程技术进入中国本土知识分子视野
中西工程技术的再次交流碰撞是近两百年以后的晚清。鸦片战争后,闭关锁国一百多年的清政府被迫打开了大门,西方近代科学与技术开始进入中国。
首先进入中国人视野的是西方的机械工程技术。魏源《海国图志》曾收录郭实腊《贸易通志》(1840年刊行)中对各种蒸汽机械的赞美:“遂造火轮舟,舟中置釜,以火沸水,蒸入长铁管,击轮速转,一点钟时,可行三十余里。翻涛喷雪,溯流破浪,其速如飞。不论风之顺逆,风之有无,潮之长落,溜之上下,借阴阳之鞲鞴,施造化之鹿卢,巧矣极矣”;“且火机所拖,不独舟也,又有火轮车,车旁插铁管煮水,压蒸动轮,其后竖缚数十车,皆被火车拉动,每一时走四十余里。无马无驴,如翼自飞”;“此外又有火轮车,凡布帛不假人力而自成织,巧夺天工矣”[10]。1853年,在香港出版的《遐迩贯珍》曾有“火船机制述略”一文,“将火船机制之理,简略论之”,并画简单“筒式”图以解释“水气机”(蒸汽机)的工作原理[11]。
此外,在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和梁廷枬的《海国四说》中都有对于轮船、火车及蒸汽机的工作原理和优点的详细介绍。王尔敏先生曾经粗略统计,鸦片战争后近20年时间(道咸两朝),中国官绅中对外洋兵船火器有深刻认识的就有66人[12]。如果根据今天掌握的资料,这个数字恐怕更大。由此可见,当时中国本土知识分子对西方近代工程知识和技术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认识。
(二)西方工程学著作的翻译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利,使得中国对西方工程技术从“冷眼旁观”到“满朝震惊”,再到“师夷长技”,从而畅通了中西工程知识与技术交流的渠道。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主动接触西方工程学知识,清政府也开始通过官方途径组织学习和借鉴,从而形成了一大批西方工程学译著,成为近代工程学知识与技术传入的重要载体。
在近代科技著作尤其是工程学著作翻译方面走在前列的代表人物有李善兰、王韬、张福僖等。其中李善兰翻译的《重学》成为近代介绍进中国的第一部比较系统的西方力学著作。
李善兰(1811—1882),字竟芳,浙江海宁人。自小迷恋数学的李善兰在15岁时便通习《几何原本》前六卷(晚明利玛窦、徐光启所译)。35岁时,他已是远近闻名的科学家,刻印了《方圆阐幽》、《弧矢启秘》和《对数探源》三种数学著作。1852年,李善兰进入上海墨海书馆,与伟烈亚力等传教士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后九卷、《植物学》、《代数学》、《谈天》等近代科学著作[13]。1859年,李善兰与传教士艾约瑟合作翻译的《重学》一书出版。研究表明,《重学》所据底本为英国科学家胡威力的《初等力学教程》(An Elementary Treatise on Mechanics),《初等力学教程》是当时英国大学的物理学教科书,从理论到计算基本包括了大学本科基础力学知识的全部内容[14]。《重学》共二十卷,除“胡氏所著凡十七卷”,又“益以《流质重学》三卷”。在书中,李善兰将“重学”分为静重学和动重学两类,并分别列举了静重学与动重学的器具,介绍了其工作原理。与明末清初相比,除了重心、简单机械、单摆和少数流体力学的知识外,《重学》所介绍的其他力学知识都是第一次传入中国,而且知识体系更为完整、丰富[15]。李善兰在《重学》序言中称:“自明万历迄今,畴人子弟皆能通几何矣,顾未知重学。……制器考天之理,皆寓于其中矣。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原其故,制器精也。”[16]
另一位重要人物王韬于1849年应英国传教士麦都思邀请入墨海书馆工作,开始接触西学,后翻译《中西通书》、《格致新学提纲》,编成《西学图说》、《重学浅说》、《泰西著述考》等,其中《重学浅说》也是近代中国译介西方力学的一部重要著作。张福僖1853年经李善兰介绍入墨海书馆,参与翻译《光论》等天文、格致书籍,《光论》是中国从西方翻译过来的第一部系统的光学著作。
由政府官方组织翻译西方工程学著作成绩最为显著的是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1865年,李鸿章与丁日昌依靠容闳购买的外国机器在上海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分设“机器厂”、“汽炉厂”、“铸铜铁厂”、“熟铁厂”等厂,并设独立“煤栈”,规模宏大[17]。1867年,徐寿向该局总办提议设立翻译馆“将西国要书译出,不独自增识见,并可刊印播传,以便国人今知”。1868年6月,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正式开馆。1871年开始正式出书,最早出版的是《运规约指》和《开煤要法》[18]。
资料显示,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40余年的译书活动中,共翻译西书约200种。如下表1所示,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兵学”和“兵政”,这与当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军事策略是相符的。除此之外,如果以近代工程学门类来看,则土木工程(“铁路”)和矿冶工程(“冶炼工艺化工”)类书籍都占了很大比重。其中,土木工程类译著有《铁路丛考》、《海塘辑要》、《铁路纪要》等;矿冶工程有《金石识别》、《宝藏与焉》、《相地探金石法》、《求矿指南》、《银矿指南》、《探矿取金》、《开煤要法》、《井矿工程》、《金石表》、《石印开矿器法图说》、《冶金录》、《铸金略论》、《金工教范》、《炼金新语》、《制羼金法》、《炼石编》、《铸钱工艺》、《炼钢要言》等;电机工程有《无线电报》、《电气度镍》、《通物电光》、《电气镀金略法》等;机械工程有《汽机必以》、《制机理法》、《汽机发轫》、《汽机新制》、《汽机中西名目表》、《兵船汽机》等;化学工程有《制火药法》、《煤油法》、《取滤火油法》、《造洋漆法》等[19]。从这些书名即可看出,此时翻译的西方工程学著作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种类繁多,门类齐全。无论是李善兰、王韬、张福僖等人翻译的《重学》、《重学浅说》、《光学》,还是江南制造总局组织翻译的大量与“工程”直接相关的译著,都成为西方近代工程学传入中国的第一批重要成果,为中国后来开展近代工程教育、发展工程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表1 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译书统计表
(三)洋务学堂与近代工程学教育的发端
西书翻译为西方近代工程学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但真正将工程学知识向更大范围内传播、形成更大影响的则是有组织的工程学教育。
“开风气之先”的是京师同文馆。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初期,只开设了英文、法文、俄文等外文课程。但随着中外形势的变化,洋务派人士很快发现,培养近代科学和技术人才同样重要。1866年12月,奕上奏称“开馆求才,古无定格。惟延揽之方能广,斯聪明之士争来。……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并强调“华人之智巧聪明不在西人以下,举凡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钩河摘洛之方,倘能专精实务,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20]。自1867年开始,天文、算学、化学等科陆续进入京师同文馆。如下表2所示,1876年的京师同文馆已经比较系统地教授数学、物理和化学知识,并开始教授机械工程学相关知识。

表2 京师同文馆课程古今学科对照表(1876年,八年制)

资料来源:《同文馆题名录》,收入高时良、黄仁贤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93页。
福州船政学堂成为近代第一所专门的工程教育机构。1867年,福州船政学堂正式开学。学堂分为“制造学堂”和“驾驶学堂”。“制造学堂”又称“前学堂”,使用法语授课,又分为造船学校、设计学校和学徒学校,培养目标分别是“使学生能依靠推理、计算来理解蒸汽机各部分的功能、尺寸,因而能够设计、制造各个零件,使他们能够计算、设计木船船体,并在放样棚里按实际尺寸划样”、“培养称职的人员,能绘制生产所需要的图纸”和“使青年工人能够识图、作图,计算蒸汽机各种形状、部件的体积、重量,并使他们达到在各自所在车间应具有的技术水平”;“驾驶学堂”又称“后学堂”,使用英语授课,分航海学校和轮机学校,航海学校的课程包括了算术、几何、代数、直线和球面三角、航海天文、航海技术和地理等,轮机学校的学习目标是指导学生掌握蒸汽机的理论和实践知识,并组织他们进行实际操作[21]。继福州船政学堂后,各类军事学堂纷纷建立。主要有天津水师学堂(1881年)、天津武备学堂(1885年)、广东水陆师学堂(1889年)、江南水师学堂(1891年)、直隶武备学堂(1896年)、湖北武备学堂(1896年)等。
19世纪70年代后,各种实业学堂的广泛出现将工程知识与技术从军用转向民用。1876年,丁日昌首倡在福州设立电报学堂,“专收生童学习电气并寄电信,如何寄法,又制造电线、电报各种机器”[22]。1880年,李鸿章奏请在天津设立电报学堂,雇用丹麦籍教习教授“电学与发报技术”。该学堂课程包括“电报实习、基础电信问题、仪器规章、国际电报规约、电磁学、电测试、各种电报制度与仪器、铁路电报设备、陆上电线与水下电线的建筑、电报线路测量、材料学、电报地理学、数学、制图、电力照明、英文和中文”[23]。之后,上海、南京和两广等地也纷纷建立了电报学堂。1890年后,各类铁路、矿务学堂也开始建立。1892年,湖北省矿务局开办矿务工程学堂。1898年,南京矿务铁路学堂开办,“招选年在三十以内,十五以外之生童,聘请泰西著名矿师为之教授,专课以矿学各书,以冀徐收实效”[24]。
从京师同文馆到福州船政学堂,再到各种实业学堂,中国近代的工程教育逐渐向前发展,中国本土工程技术人员逐渐增多,中国近代工程学发展呈现蓬勃向上的趋势。
四、结语
与晚明时期中西传统“工程”技术交流相比,晚清西学东渐浪潮下的近代工程学在华传播与交流更加充分,影响更加广泛,并最终促使了中国近代工程学的诞生与发展。细推敲其中原因,至少有三方面因素值得考量:
一是与16、17世纪相比,西方工程学到19世纪中叶时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工程学理论,具备了较为先进的工程技术,而中国自晚明至晚清在传统技术方面却并没有太大的突破,尤其没有出现类似西方近代科学诞生和工业革命那样巨大的质变,中西方在工程技术方面的悬殊差距激发了中国本土知识分子的危机感,从而推动了中西工程学交流的加速进行。
二是与晚明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学习研究西方工程技术多由“兴趣使然”相比,晚清时期知识分子学习研究西方近代工程技术则更多了一层“师夷长技以制夷”和“救亡图存”的使命感。整个晚清西学东渐都是在鸦片战争失利、民族濒临危亡的大背景下展开的,知识分子寻求自强之道以御外侮的使命感贯穿其中,为中西近代工程学交流注入了强劲动力。
三是与晚明时期王征、徐光启等人的个人行为相比,晚清时期中西工程学交流更多来自于清政府的官方动员和行为。在官方动员和组织下,晚清时期的中西工程学交流不仅完成了知识的引进,而且通过洋务学堂完成了知识的传授和传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工程学教育体系,真正掀起了西方工程学知识与技术在中国的传播高潮。
[1]刘洪涛:《中国古代科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2][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0页。
[3]史贵全:《中国近代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4]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23页;陈垣:《泾阳王征传》,《真理杂志》,复旦大学图书馆藏,1944年第2期,第213页。
[5]刘仙洲:《王征与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真理杂志》,复旦大学图书馆藏,1944年第2期,第215页。
[6]《奇器图说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本,第842册,第407页。
[7]张柏春等:《传播与会通——〈奇器图说〉研究与校注》,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66页。
[8][清]阮元等:《畴人传汇编》,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350页。
[9]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77页。
[10][清]魏源撰、陈华等点校注释:《海国图志》,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989页。
[11]《遐迩贯珍》,1853年第2号,收入[日]松浦章、内田庆市、沈国威编著:《遐迩贯珍——附解题索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703页。
[12]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13][16][清]诸可宝:《畴人传三编》,收入《畴人传汇编》,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767、772页。
[14]聂馥玲、郭世荣:《晚清西方力学知识体系的译介与传播——以“重学”一词的使用及其演变为例》,《自然辩证法通讯》,2010年第2期。
[15]聂馥玲:《晚清科学译著〈重学〉传入的经典力学知识及其特征》,《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汉文版),2009年第4期。
[17]《江南制造局记》,收入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18]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An Account of the Translation Department at the Kiangnan Arsenal),收入[美]戴吉礼(Ferdinand Dagenais)主编:《傅兰雅档案》(The John Fryer Papers),第二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34页。
[19][清]魏允恭:《江南制造局记》,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四十一辑,第175页。
[21][法]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福州船政局》(The Foochow Arsenal and Its Results 1874),收入林庆元:《福州船政局史稿》(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127页。
[22]《万国公报》,1876年6月24日,收入高时良、黄仁贤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58页。
[23]KBiggerstaff,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收入高时良、黄仁贤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66页。
[24]《集成报》,第三十册,收入高时良、黄仁贤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91页。
Research on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Engineering from the West to China
FANG Zheng
(Research Centre for Social Sciences of M.O.E,Beijing 100080,China)
the modern engineering;engineering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the entrance of the western cultur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y,the traditional technology in China and the West developed in the different direction:the traditional technology in China developed into an artistry,but the traditional technology in the West went closing to the modern science,and the engineering came into being accompani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techniques with modern science in the middl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As other modern sciences,the engineering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by the missionaries,attracting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During the late Ming Dynasty,the first contact occurred and few Chinese intellectuals like WangZheng who translated QiQiTuShuo appeared.But it didn’t obtain good results.With the entrance of the western culture,the engineering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a lot of engineering books wer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and a lot of modern schools where people could learn the engineering were built. Thanks to this,the engineering started its course in China,which greatly affected the industri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a.
K263
A
2095-5170(2014)06-0061-06
[责任编辑:刘一兵]
2014-05-24
房正,男,山东烟台人,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