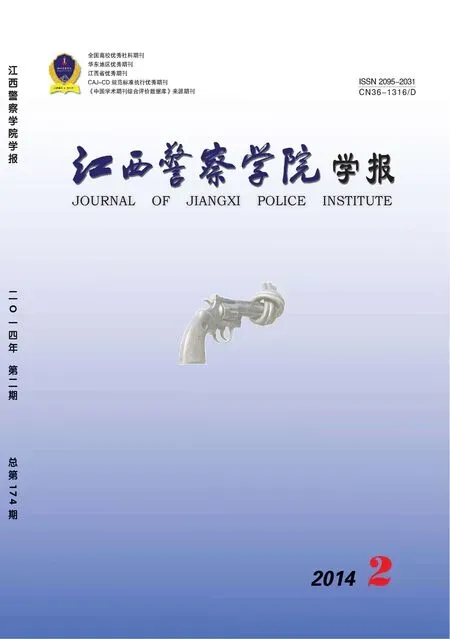“无害控制下交付”中的犯罪形态认定
——以毒品犯罪为视角
帅红兰
(苏州大学,江苏 苏州 215000)
“无害控制下交付”中的犯罪形态认定
——以毒品犯罪为视角
帅红兰
(苏州大学,江苏 苏州 215000)
2012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最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其中在“侦查”一章中增加了第八节“技术侦查措施”,正式确立了“控制下交付”在我国的合法地位。鉴于社会安全的考虑,实践中最常用的是“无害控制下交付”的手段,然而该手段却引发了不能犯未遂与能犯未遂的争议问题。准确界定“无害控制下交付”中的未遂形态以及解决该新型刑侦措施所带来的法律问题,需要对不能犯理论的正确解读和对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罪的停止形态的分析,如此,方可使该刑侦措施发挥出最大效益。
无害控制下交付;不能犯未遂;犯罪形态
“控制下交付”(Controlled Delivery)系一种打击国际有组织犯罪的侦查手段,主要被应用于毒品犯罪领域。台湾地区将其译为“监视下运送转移”,日本则将其翻译成“监控下移动”。早在1931年,美国禁毒机关就曾使用控制下交付的手段破获了从土耳其贩卖至美国的鸦片走私犯罪,[1]然而直至1988年,联合国才以公约形式确定其法定地位,即《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该公约第一条明确规定:“控制下交付,系指一种技术,即在一国或多国的主管当局知情或监视下,允许货物中非法或可疑的麻醉药品、精神药物、本公约表一和表二所列物质或它们的替代物质运出、通过或运入其领土,以期查明涉及本公约第三条第一款确定的犯罪的人”。其后2000年的《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2003年的《反腐败公约》又就该手段启动之条件、程序、原则等做了详细的规定,在此基础上,控制下交付逐渐被多国国内法吸纳,其应用范围也由最初的毒品犯罪扩大到其他一些隐蔽性较强的犯罪。
2012年全国人大十一届第五次会议通过了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下称《刑诉法》决定),自此,“控制下交付”作为一种有效的刑侦手段在我国取得合法地位。“控制下交付”一般分为有害和无害两种形式,它们的关键区别就在于侦查机关是否将违禁品秘密替换成非违禁品。“无害控制下交付”是实践中最受侦查机关青睐的一种手段,然而该手段也引发了很多法律问题,其中,争议最大的是行为人犯罪形态的认定问题,作为决定犯罪人量刑的因素,其是理论界和实务界无法回避的问题。笔者拟以毒品犯罪为例,具体分析“无害控制下交付”中行为人的犯罪形态的认定问题,以期能对该刑侦措施下存在的一些法律问题有所借鉴。
一、问题的产生——对“不能犯”的解读
“无害控制下交付”是指侦查机关在发现违禁品后,为防止布控不利而导致违禁品流入社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危害,而秘密地将违禁品全部替换成与之外形、重量类似的普通物品的布控方式。与之相对应,“有害的控制下交付”中侦查机关对违禁品不做任何改变,只是执行监控的任务。为确保万无一失,实践中侦查机关更多地选用 “无害控制下交付”,然而该措施使得“犯罪对象”这一要素发生本质变化,导致不知情的行为人产生错误认识,即误把非违禁品当做违禁品,基于这样的错误认识,行为人继续着原有的犯罪活动直至被抓获,最终犯罪未遂,客观上也未能产生任何现实的法益侵害。因此,多数人将这种因为认识错误使得犯罪不能既遂的行为定性为对象不能犯,并基于此引证据点阐述其关于不能犯是否可罚的观点。对此,笔者提出质疑:对象不能犯的成立是否只需同时具备“行为人的认识错误”和“不能既遂”两要件即可?要回答上述问题,关键在于对“对象不能犯”概念的准确理解。
我国对对象不能犯的定义主要有 “行为人具有实现犯罪的意思,但其行为所指向的对象并不存在,因而不可能发生结果”、[2]“犯罪人行为所指向的犯罪对象当时并不存在于犯罪行为有效的范围内,或者因具有某种属性而不能既遂只能未遂”。[3]定义虽说有所不同,但不外乎以下几个要素:
首先,时间要素,即犯罪人在实行行为的整个过程(着手实施犯罪行为直至行为终了这一段时间)中对犯罪对象的认识持续处于错误状态,换言之,行为人是基于对犯罪对象的认识错误才着手实行犯罪的,这就决定了对象认识错误必然发生在实行行为着手前,这也符合了对象认识错误是“事前错误”[4]这一理论。若是行为人在着手时,对象认识正确,但之后存在认识错误,则不能认定为不能犯。
其次,行为结果,即不能犯的结果是未遂。根据我国理论界通说,不能犯属于未遂犯的一种,即“不能犯未遂虽然不可能达到既遂,但行为人主观上有犯罪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该种故意支配下的犯罪行为,只是由于认识错误,才使得犯罪没有完成,因此,它完全具备了构成未遂犯的诸特征”。[5]因此,不能犯在我国就是不能犯未遂,而我国刑法典中规定的未遂则是指能犯未遂,两者都未实现犯罪结果,只是不能犯不能得逞的原因是对象认识错误。
故而,对“对象不能犯”的准确认定,可以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为:对象认识错误——行为人基于认识错误着手实行行为——犯罪未遂,三者缺一不可,且须依次出现。基于上述分析,将“无害控制下交付”中的犯罪形态笼统地认定为对象不能犯是对该理论概念的误读,是片面的。因此,笔者将以毒品犯罪为例,具体分析“无害控制下交付”中该类犯罪行为人的犯罪形态。
二、“无害控制下交付”中毒品犯罪的形态认定
鉴于“无害控制下交付”主要监控的是处于流转过程中的毒品,故而笔者重点分析毒品犯罪中的走私、贩卖、运输毒品这三种行为。有关毒品犯罪的既未遂标准在理论界存在很多争议,司法实践也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因此,笔者拟以学界通行观点作为阐述“无害控制下交付”中具体犯罪形态的基础。鉴于本文讨论的重点是准确界定两种未遂形态,故而对实践中可能出现的犯罪人中止犯罪行为或者侦查力量布控失败的情形,笔者不予考虑。
(一)走私毒品罪的犯罪情形
所谓“走私”毒品主要是指输入或输出毒品的行为,违反的是主管当局对违禁品出入国(边)境的管理秩序。关于走私毒品罪的既遂标准,学界通说观点为“到达说”,具体要区分毒品进入国(边)境的方式:通过陆路、海路或空路走私的,应当分别以毒品逾越国境线、使毒品进入国内领域内的时刻,装载毒品的船舶到达本国港口或航空器到达本国领土内时为既遂。[2]830-831而输出毒品的行为就相应地以毒品离开国(边)境为既遂标准。
根据该标准,“无害控制下交付”中走私毒品犯罪要区分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侦查机关在犯罪人着手实行行为后就得到准确情报,并进而启动布控行为,当毒品进入或离开国(边)境时,“毒品”已经不是当初的毒品了,犯罪行为不能既遂,但因为行为人着手实行行为时并不存在犯罪对象认识错误,因此,侦查机关的秘密替换行为应当属于意志以外的因素,犯罪行为是能犯未遂状态;另一种情形是,当毒品进入或离开国(边)境之前或当时,侦查机关都未发现任何犯罪活动,之后才得知相关情报,并采取了“无害控制下交付”的手段,最终将犯罪人绳之以法。但由于犯罪行为在毒品进入或离开国(边)的那一刻起就实现了既遂,之后的侦查措施对该犯罪形态没有任何影响。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购国家禁止进口物品的或者在内海、领海运输、收购、贩卖国家禁止进出口物品的,应当按照走私物品的种类,分别适用刑法第151条、第152条、第347条的规定定罪量刑。联系毒品犯罪可知,在内海、领海运输、收购、贩卖毒品的或者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购毒品的,应当认定为走私毒品罪,理由就在于:前者行为由于发生在内海、领海这些特殊地域,已严重侵害了国(边)境的管理秩序,其危害程度不亚于走私罪,对这类行为的既遂标准的确定,下文将有具体讨论;而后者则是将收购行为视作对走私行为的一种帮助,一种推动,对其既未遂的认定应当区分两种情况,“一是交易发生在我国国 (边)境外,其犯罪既遂与未遂的适用标准应适用出入境说;二是交易发生在我国境内,其交易行为一旦实施则犯罪目的即告得逞,亦属于举动犯形式的犯罪既遂而不存在未遂形态”。[6]也就是说,当行为人直接向走私人收购毒品的,需区分其行为发生地以具体确定其犯罪形态。
(二)贩卖毒品罪的犯罪情形
对于贩卖毒品罪中“贩卖”一词的理解,学界众说纷纭,未有定论。最高院于1994年出台了《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对“贩卖”的含义作出了明确规定:“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买毒品的行为”。据此规定,贩卖毒品罪中的“贩卖”包括“销售”与“收买”两种行为,其与规定中提到的“以贩卖为目的”中的贩卖是不同的,后者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理解的销售行为,而前者则是有权机关基于打击毒品犯罪的需要作出的扩张解释。另外,从语义表述的前后不重复的角度考虑,与“收买”并列的“销售”应当是对非通过购买途径获得的毒品的出售。
据此,关于“贩卖毒品罪”的既未遂标准以及“无害控制下交付”中具体形态的认定,应当区分下面两种情形:
首先就“销售”行为而言,关于其何时既遂,目前主要有契约说、交易说、转移说等几种观点,笔者倾向于支持转移说,即以毒品实际上转移给买方为既遂,转移后行为人是否获得利益不影响贩卖毒品罪既遂的成立。[2]831这同民法中的权利变动规则是一致的,即动产所有权的转移以动产交付为标志。“无害控制下交付”中,行为人将自产、祖传、拣拾等方式获得的或者是不能查明来源的毒品予以销售,很显然犯罪人在着手实行犯罪行为时对毒品并不存在认识错误,否则其行为就是典型的诈骗行为了,当然,也有可能行为人把自己拣拾的假毒品当做真毒品销售,那就不存在“无害控制下交付”的必要了,因为该手段启动的前提是必须存在足够严重且足以确定的危险,否则是无法得到批准的。因此,犯罪人着手实行行为时对犯罪对象的认识是正确无误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由此看来,行为人在着手实行行为时,犯罪是有可能既遂的,之所以最终不能既遂是因为过程中出现了意志以外的因素——侦查机关的介入,故而对行为人应当作贩卖毒品罪的能犯未遂的认定。
其次是“收买”行为,司法解释将行为人基于贩卖目的收买毒品的行为认定为贩卖毒品罪,而对这种收买行为的定性又直接影响到对行为人犯罪形态的认定,即“收买”属于预备行为还是实行行为。有学者将之视为贩卖毒品罪的预备行为,[7]认为对该罪中的“贩卖”应当做通常理解,收买只是制造条件、准备工具的环节,其危害性远不及销售来得大。因此,行为人在犯罪预备阶段就因为障碍而未能进入实行行为阶段的,不管该障碍是意志以外的还是行为人自身的认识错误,都一律归属于犯罪预备,且不管行为人是否实际上购得毒品都视为贩卖毒品罪预备也不太合理。故而,笔者觉得还是应当立足于司法解释对该“收买”行为进行定性,一方面从立法意图来看,将以贩卖为目的的“收买”同“销售”并列规定,是国家严厉打击毒品犯罪的政策的体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购买毒品这一行为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是不可低估的,行为人的贩卖意图及其收买行为已经共同构成了对法益的迫切威胁,若不予以及时的阻止,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台湾地区将以贩卖为目的的购买行为单独设定为“意图贩卖而持有毒品罪”[8]或许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吧。因此,从有效防控的角度来说,将贩卖意图下的购买行为定性为实行行为是更为合理与必要的。基于此,具体到“无害控制下交付”中,行为人基于对毒品属性的认识错误而实行购买行为,最终购得的是假毒品,对此,应当对该行为人作贩卖毒品罪的不能犯未遂的认定。当然,如果行为人只是为自留或吸食而购买毒品,一般是无罪的,除非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数额,才能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
(三)运输毒品罪的犯罪情形
所谓“运输”,无非是货物发生位移变化的过程,要认定该行为,关键得明确毒品移动的区域。运输毒品罪要求运输的区域限于国内或境内,同时要求不得在领海或内海上运输毒品,否则都视为是走私毒品罪。关于该罪的既遂标准,学界普遍采用 “起运说”,即“行为人为了运输而开始搬运毒品时,是运输毒品罪的着手,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不能或没有进入正式的运输状态时为未遂;否则即为既遂”。[9]据此,毒品被装至某种交通工具起运的或者已包装好被邮局接收的,都视为运输毒品罪既遂。
根据公约对控制下交付的定义,侦查机关发现毒品都是在其运输途中,因此对其实行的秘密替换行动实际上属于运输毒品罪既遂后的行为,由此引起的行为人对象认识错误对运输毒品罪的既遂形态没有任何影响。因此,根据“起运说”的既遂标准,“无害控制下交付”中运输毒品罪一般都是既遂形态。
(四)一人实施多种行为时犯罪形态的认定
上述单一毒品犯罪形态的分析是基于理论视角的分析,现实社会中,毒品犯罪尤其是跨国、有组织毒品犯罪通常都是包含数个行为的,譬如说跨国买卖毒品活动则包含了走私、运输、贩卖毒品等多种行为,对该犯罪活动的犯罪人如何认定是更有实践价值的问题。
根据2008年法院座谈会纪要,①2008年《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一条规定:“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是选择性罪,对同一宗毒品实施了两种以上犯罪行为并有相应确凿证据的,应当按照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性质并列确定罪名,毒品数量不重复计算,不实行数罪并罚。”“对不同宗毒品分别实施了不同种犯罪行为的,应对不同行为并列确定罪名,累计毒品数量,不实行数罪并罚。对被告人一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两种以上毒品的,不实行数罪并罚,量刑时可综合考虑毒品的种类、数量及危害,依法处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是选择性罪名,犯罪人只要是实施了这四种行为中的任何一种或几种行为,都只构成一罪,区别在于罪名的不同,而毒品的种类、数量只是作为影响量刑的因素。就比方说行为人将毒品从国外带进我国,在贩卖毒品的交易过程中被警方抓获,该犯罪过程中存在走私、运输、贩卖三种行为,因此,对犯罪人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罪,而毒品的数量、种类等都是量刑时才需考虑的因素。至于该罪的形态,笔者的观点是一行为既遂、全罪既遂。理由在于:若行为人甲只实施了走私行为且既遂,认定其为走私毒品罪既遂是毫无疑问的;若行为人乙实施了走私、贩卖的行为,其中走私既遂而贩卖未遂,对乙应当认定为走私、贩卖毒品罪,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两行为人所处的法定刑幅度应当是一样的,此时,若因乙有一行为未遂而将全罪认定为未遂,则对其可以比照既遂标准从轻减轻处罚,换言之,乙最终被判的刑法也许比甲还轻,这显然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因此,对于一人多行为的情况,笔者的立场是:一行为既遂,全罪既遂,立足于既遂立场,看其他行为的停止形态作为量刑时考虑的因素。
在“无害控制下交付”的具体情境下,要决定一罪多行为的犯罪人的全罪犯罪形态,需要具体分析其每个行为的停止形态,对此笔者在上文已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为进一步阐明个人观点,且举一例说明:行为人运输毒品进入我国国境前被我国警方发现,警方启动“无害的控制下的交付”,行为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毒品运进我国,并联系买家准备销售,在交易过程中被警方一网打尽。对该虚拟案例的分析是:首先运输行为在起运时既遂;其次毒品在行为人走私行为既遂(跨越国境)前被替换,故而为能犯未遂;最后,就贩卖行为而言,行为人基于对象认识错误使得犯罪最终不能既遂,成立不能犯未遂。对于买方,其属于一行为一罪,上文已有论述。因此,对该虚拟案例中的行为人应当认定为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罪既遂,但因为走私和贩卖行为都是未遂(其中贩卖行为为不能犯未遂),所以在量刑时应当比同等条件下三个行为全部既遂的要轻,亦比同等条件下一行为既遂、其他两行为都是能犯未遂的要轻。
综上所述,对“无害控制下交付”中的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罪的犯罪形态的认定不能一刀切,要根据行为人足以被认定的行为来具体确定其罪名和形态,或为不能犯未遂、或为能犯未遂,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一特殊的刑侦措施对行为人的犯罪形态的认定并无任何影响,故而切不可主观臆断。
三、“无害控制下交付”中未遂形态界定的必要性
由于“无害控制下交付”的主要特点即在于侦查机关对违禁品的替换,因而其关注的法律焦点不外乎是能犯未遂与不能犯未遂之间的界定问题,而这也正是笔者本文的核心所在,那对于这样的问题有讨论的价值吗?且不说我国刑法未对不能犯作出明文规定,讨论不能犯问题的法律根据存在缺漏之外,就司法实践而言,将同属于犯罪未遂形态的两种情形区别对待的价值又在哪儿呢?
(一)隐藏于我国司法解释中 “不能犯”的规定——法律根据
199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贩卖假毒品案件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指出:“不知是假毒品而以毒品进行贩卖的,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对其所贩卖的是假毒品的事实,可以作为从轻或者减轻情节,在处理时予以考虑。”而199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对此作了更为明确的规定:“不知道是假毒品而当做毒品走私、贩卖、运输、窝藏的,应当以走私、贩卖、运输、窝藏毒品犯罪(未遂)定罪处罚。”
上述两个司法解释都着重强调了行为人主观的不知请,也即主观上存在认识错误,但没有限定认识错误产生的时点,因此,对该规定的理解要区分不同情形:一种情形是行为人基于认识错误而着手实行犯罪行为,则其行为在开始时就注定不能既遂,也就是说上述司法解释是对毒品犯罪中的“对象不能犯”的定罪处罚作出的规定;另一种情形是行为人着手实行行为时,对毒品的认识不存在任何偏差,只是在行为过程中毒品由于某种原因成为假毒品,行为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继续原有犯罪行为最终未遂,该行为显然属于因意志以外原因而未能得逞的能犯未遂。
从立法意图来看,笔者认为作第一种情形的理解更为合理。这是因为,司法解释一般用于填补法律空白、或者是对法律中原则性的规定予以细化、再或是做不同于法律的特别规定,而第二种情形本身就是刑法典中规定的犯罪未遂的应有之义,是总则应用于分则具体罪名的体现,司法解释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因此,可以说上述司法解释就是不能犯这一理论在我国法律中的最真实的反映,也从侧面说明了我国实务界对不能犯所持的态度和立场是:可罚的犯罪未遂。这与笔者上文提及的我国理论界的通说是不谋而合的。司法解释对基于错误认识下的犯罪未遂情形作特别规定,本身就表明这是不同于一般情形下的犯罪未遂,其应有之义便是:不能犯未遂与能犯未遂应当有所区分。
(二)两种未遂形态的本质区别——法理价值
上述司法解释只是从解释层面说明我国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对相关问题的态度,但归根结底,这样的态度也是由不能犯未遂与能犯未遂的本质区别所决定的,简言之就是危害性的差别。
不能犯未遂和能犯未遂虽说同属于犯罪未遂形态,但它们客观上对法益的威胁程度是不同的,这从“能”与“不能”的语义区别即可看出,即两者实现法益侵害的可能性或者说几率是不同的。换言之,两者所产生的社会危害性的程度是有差别的,这决定了它们在量刑时应当有所区别,这是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对被告人基本权利的保障,因为从根本上来说,犯罪人只对其造成的法益侵害承担刑罚,不管该侵害是否能够实际出现,司法的结果若是要求行为人承担超过其侵害范围的刑罚,则是对其基本人权的侵犯,也是司法不公正的体现,司法的权威也将因此受损。因此,准确区分具体案件中的不能犯未遂与能犯未遂是公正量刑的必要条件。
因此,对不能犯未遂与能犯未遂作出区分是我国司法解释的应有之义,也是保障犯罪人人权和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
四、结语
“控制下交付”是一把双刃剑,作为一种有效打击国际有组织犯罪的侦查手段,其侦查效率是不容置疑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该刑侦措施也带来了许多利益冲突的问题。最新的《刑诉法》决定虽说对“控制下交付”作出了明文规定,但也只是停留在原则性或者说概括性规定的层面,尚未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这使得侦查机关在执行任务时可能会侵害到犯罪人的基本权利,包括在监控过程中不当地侵犯行为人的隐私权;诱惑意图中止犯罪的行为人继续犯罪抑或是诱惑本无犯意的其他人员犯罪,导致控制下交付转化为非法的诱惑侦查;此外,“无害控制下交付”中,侦查人员可能会有意或无意的改变行为人实际犯罪的毒品数量,当这些毒品被不加证实地作为犯罪证据使用时,对行为人作出的裁量将是不公正的。综上,“无害控制下交付”作为一种合法、有效的刑侦手段,其在侦破国际或国内大型有组织犯罪中将会被越来越频繁地使用,但若使用不当,则会严重侵害行为人基本权利、影响司法公正,故而需要就其启动条件、实施原则、证据保存等进行细致的规定,以确保司法机关能够准确认定相关犯罪的停止形态并作出公正判决。
[1]Ethan A.Nadelmann,Cops Across Borders.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U.S.Criminal Law Enforcement[M].Pennsylvania State Press,1993:36.转引自程雷.秘密侦查比较研究——以美、德、荷、英四国为样本的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538.
[2]张明楷.刑法学(第三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294.
[3]赵秉志.论不能犯与不能犯未遂问题[J].北方法学,2008,(1):77.
[4]刘明祥.刑法中错误论(第二版)[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56.
[5]马克昌.犯罪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432.
[6]曾粤兴,贾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形态研究[J].公安大学学报,2002,(2):65.
[7]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007.
[8]高巍.贩卖毒品罪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178.
[9]李希慧.刑法各论(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330;张明楷.刑法学(第三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011.
责任编辑:张 艳
D924.11
A
2095-2031(2014)02-0069-05
2013-10-19
帅红兰(1990-),女,江苏泰州人,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研究生,从事刑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