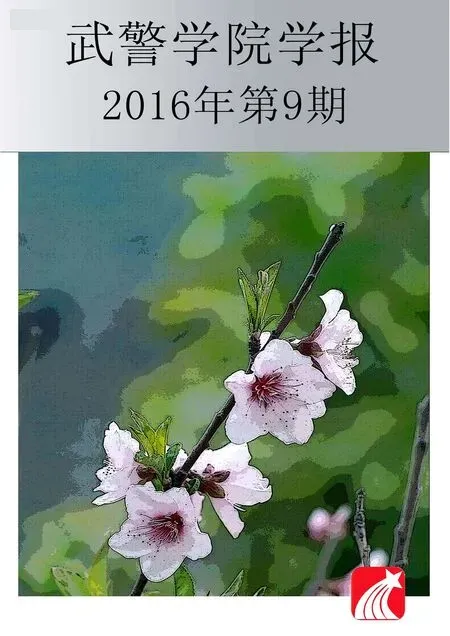运用中华传统武德教育方法培育军人血性的路径举要
杨 煦
(武警学院 研究生队,河北 廊坊 065000)
运用中华传统武德教育方法培育军人血性的路径举要
杨煦
(武警学院 研究生队,河北 廊坊065000)
中华传统武德对于培育军人血性具有现实启示意义。“正己化人”的武德教育方式揭示了干部以身作则的重要性,即干部需具备“忠、勇、信、爱、严”的武德人格;“众陷于害”的武德刺激方式揭示了极端环境对血性的激发作用,其动员话语范式是“情感渲染——直呈结论”;“教民以战”的武德孕育方式告诉我们要加强学生群体血性孕育、优化军训训练内容。
中华传统武德;军人血性;思想政治教育
中华传统武德是在中国几千年战争史中发展成熟起来的相对稳定的军事伦理文化。它既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又包含着民族文化的一般特征,在中华文明史上发挥了深刻的作用,并且延续至今。历史无法超脱时代而存在,中华传统武德虽留有封建思想之遗骸,但其中的合理部分,特别是其中激励士气的有效经验,对于培育军人血性具有现实意义。
一、正己化人:良将德行的示范作用
历代兵家著述多有辑录“正己化人”的思想,《黄石公三略》指出:“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逆者乱之招,顺者治之要。”[1]120可见将帅本身作为武德表率和行动示范,是对士兵进行武德教育的重要方式,是推行其军事伦理思想在军队中传播的重要载体。研究将帅达到何种武德标准才能实现“正己化人”以培育士兵的军人血性,先要明确军人血性的构成要素不是单一的勇气,而是由忠诚、勇气、信念、意志等综合因素组成的。因而,本文由“正己化人”这一逻辑出发,将将帅需具备的武德人格概括为“忠、勇、信、爱、严”。
(一)忠
在军人所有的武德人格之中,忠是其逻辑之始。军人血性之所以与常人血性有所不同,区别之一就在于军人明确知道自己在战场上随时可能牺牲,在这种情况下军人的血性必须能够长时间地提供给他超越死亡恐惧的精神力量和伦理支撑,时间跨度的不同决定了激发军人血性的不是一时感性,而是综合了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的一种武德人格,即“忠”。中国古代兵家高度重视忠的价值作用,阐发了许多经典论述。“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故良将守之,志立而名扬。”[2]41《草庐经略·忠义》认为:“第将非忠义,何以为立功建绩之本,而使三军感动兴起乎?”[3]10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在传统武德中忠的含义包括了爱国,但其根本指向是“忠君”,带有明显的封建性和排他性。作为当代革命军人的忠,并不能原封不动地继承传统武德语境下的忠,而要扬弃其中的糟粕,明确自身的性质和宗旨,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责任,忠于使命。
(二)勇
军人之勇是忠的必然逻辑展开。“教以忠义,使士卒皆有亲上死长之心,然后令之执干戈,擐甲胄以御敌,自然如手足之捍头目,子弟之卫父兄,有不战,战必胜矣。”[4]83勇是获取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古代兵家在审视战争时,很大程度上将胜利归因于将帅的勇敢——“以身先人,故其兵为天下雄”[1]38,认为作战中若“将无勇,则吏士恐”[1]45,要求将帅要“誓以居前”“将必先己”“临阵身先”。诚然“誓以居前”的武德要求囿于古代冷兵器作战的局限性,在当前大规模联合作战中不具备实际指导意义,但其中仍散发着超越时代、超越作战样式的武德光芒,这种先之以身、将不惜死的武德人格,在实际军事行动中比任何说教都更具说服力。另外,作为军队各项工作的引导者,将帅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因此必须辨清慈勇与武勇的区别。慈勇的概念由老子提出,可溯源至楚庄王的“夫文,止戈为武”[5]198,可见古人认为作为军事行动的武,其最终目的是否定武,而非武勇所弘扬的肯定武、发展武。
(三)信
广义上的信指的是言行一致,而本文仅从其中“赏信罚必”的角度进行讨论。“赏信罚必”不仅是一种武德人格,同时还是一种武德行为,具备行政操作意义,在“正己化人”的过程中发挥了价值导向的作用。将忠、将勇的武德人格在“正己化人”的逻辑公式中能够起作用是基于儒家“内圣外王”的性善论前提,但这种脱离物质利益的假设违背了人的天性。因此若仅凭将帅自身的忠和勇对士兵进行教化,其武德在传递过程中必然会因为官兵个体心理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程度的衰减。而“赏信罚必”作为一种兼顾物质与精神的武德行为,具有“存劝示惩”的作用,不但能够很好地弥补将帅武德在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衰减,而且其行为本身就能刺激士兵血性的生成,“禄予有功,则士轻死节”[6]211。历代兵家分别提出“赏罚不明不足以砺士气”,“所憎者,有功必赏;所爱者,有罪必罚”[7]43等观点,《六韬》还为奖惩工作树立了一条原则:“刑上极,赏下通”[7]98,虽然刑上赏下之道在理论上有所瑕疵,但从实践效果来看,司马穰苴斩庄贾而军威树,孙武吴宫斩贵妃则行伍齐,吴起北门徙辕而信义立等等史料都显示出刑上赏下能够有效聚拢人心,肃清军队纪律。可见实事求是的刑上赏下具有积极的道德意义,能够为培育军人血性树立价值导向和纯净部队环境。
(四)爱
爱即爱兵如子,其逻辑结果是和军一心,三军用命。爱兵如子在“正己化人”的过程中发挥了情感认同的作用。《孙子兵法》有云:“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8]119明将戚继光根据自身的军事实践创造了“爱卒——和军——克敌”[9]322的制胜范式,“爱行恩竭,力齐气奋,万人一心,何敌不克?”[10]187爱卒亲卒产生的情感认同和激励效果显而易见,古代兵家在爱卒的武德履践中通常采取两种方式:同甘共苦与推恩于下。同甘共苦在平时表现为将帅“后饮”“后食”“后舍”的“三后”精神;在战时表现为将帅与士卒同安危,共生死;在思想关怀方面表现为将帅要“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7]69。同甘共苦带来的情感认同能够在战场上强烈刺激军人血性,产生“故无甲兵而胜,无冲机而攻,无沟堑而守”[7]69的巨大精神作用。推恩于下则要求将帅能够有“克捷,推功于下”[11]377的广阔胸襟,充分肯定士兵在军事行动中的功绩,实现“良将之统军也,恕己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战如风发,攻如河决”[1]38。
(五)严
古语有云:“慈不掌兵”,自孙武在将帅武德中引入“严”的范畴后,经由后世兵家的不断丰富发展,“严”在将帅武德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兵家认为将严生将威,而将威又能够增强将帅武德在士兵中的接纳度,从这一逻辑来看,严在“正己化人”的过程中发挥了正向强化的作用。明代著名将领戚继光提出一条重要的道德教育原则——“严以自服”,他认为“非严不克。若认真到底,久亦自服。他日济事者,此也”[10]206。意指运用严格的方式教育训练部队,能够养成官兵自觉服从的习惯,这种自觉的服从不仅仅只局限于纪律规定等硬性条文,还涵盖了包括将帅的武德教育在内的教育训练本身。并且戚继光在研究将帅“爱”与“严”两条武德人格的时序性问题上,认为“爱”在“严”前,提出了“恩结在先,严求于后”[10]213的武德要求。因此,在“正己化人”的理想模型中,“严以治军”所能提供的正向强化要以“爱兵如子”产生的情感认同为基础,同时“爱兵如子”又要以“严以治军”为约束,二者逻辑顺序不可颠倒,辩证关系不可偏废。
二、众陷于害:极端环境的血性砥砺
“众陷于害”的提法最早见诸《孙子兵法·九地篇》:“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8]132孙子认为在战场上存亡、生死等矛盾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极端危险的环境中孕育着生的可能,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生和转化。虽然我国整体形势较为稳定,但边境安全形势依然相对严峻、复杂,这一系列问题与挑战都要求指战员在平时训练与军事行动中能够创造或借用“众陷于害”的武德环境激发军人血性,完成各项任务,实现军事目标。
(一)在日常教育中阐释“众陷于害”的武德理论内涵
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2]9“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官兵”[13]历来是军队政治工作的一大原则,“众陷于害”的理论是被无数战例证明了的科学的军事理论,在部队面临危局困境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干部应在日常教育中向士兵阐释“众陷于害”的理论内涵,厘清战场上胜负、安危、存亡、勇怯、强弱等的辩证关系,运用“因阳伐死,因阴建生”[14]420“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太阳,太阴”[15]2等兵家阴阳观点揭示在困局中我方的反败为胜正是建立在敌方的实力强大之上的战争规律。“阴”即危局,“阳”即转机,两者并非绝对对立,它们是一个系统内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体,当“阴”行至极致时必然刺激事物发生转变,向“阳”运行,这种转变或为士气血性的转变,如韩信的“背水一战”;又或为制度编制的改革,如毛泽东同志的“三湾改编”,这些转变的核心在于应局之人的主观能动性上,教育者应通过这种教育提升官兵对于“众陷于害”战场环境的认识,形成官兵“必死则生”的战场辩证生死观。
此外,在授课过程中必须注意力戒通篇引用古文,《司马法》认为“教极省,则民兴良矣”[16]5,它启示我们只有使用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的话语方式并辅以古代军队及革命战争时期的具体战例才便于士兵掌握“众陷于害”的理论内涵。
(二)在军事训练中运用“众陷于害”的武德心理培育
就部队日常训练而言,可在日常训练中设置一些带有危险性的心理训练科目,使官兵体验类似于“众陷于害”的心境,并借此锤炼官兵的胆气。例如车辆碾压训练、野外生存训练、徒手攀岩训练等。这些训练内容中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官兵可在训练过程中真实体验到恐惧、胆怯、惊慌、紧张等负面情绪,但随着训练任务的完成,官兵能够逐渐适应这些危险性训练所带来的心理刺激,进而控制和消除紧张、恐惧等消极情绪,实现情绪情感的正向转化,锤炼官兵勇敢过人的意志品质。
就部队军事演习而言,近似实战的军事演习对于激励官兵的勇武、协作等精神大有裨益,是培育军人血性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在制定演习方案时,导演机构应有意识地设计一些“危局”“死局”“败局”,例如在蓝军兵力十倍于红军并对红军实施围歼战的极端情况下,红军开展反围歼作战。让官兵在这种“危局”“死局”“败局”的演习中熟悉“众陷于害”的极端战场环境,增强心理承受能力,并完成对“必死则生”理念深层次的接纳与内化,从而锻造军人血性,培树军事乐观主义精神。
(三)在军事行动中发挥“众陷于害”的武德心理刺激
孙子认为,“众陷于害”的战场环境本身就能够强烈刺激将士的心理及情感,激发将士“勇”“固”“从”的武德人格。而考查战争史的结果表明,《孙子兵法》对于“众陷于害”环境下促使士兵士气转化中人的因素的研究存在缺失,指战员正确的话语动员同样是促使士兵在恶劣的战场环境中产生良性的武德心理体验的重要因素。
在“众陷于害”的情况下,官兵的心理受到极其惨烈的战场环境影响,会出现多种类、较复杂的情绪表现。这些情绪表现中消极因素与积极因素并存,并且同时存在于部队的不同个体乃至同一个体身上,此时需要指战员整合部队情绪,激发军人血性,扭转部队士气。指战员可采取一种极短的战时动员——“断言”来实现这一目标。群体心理学创始人古斯塔夫·勒庞认为断言法是一个群体的领袖十分重要的动员手段:“做出简短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17]107,“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威力。”[17]107总结历来极端战场环境下指战员运用断言法调动部队士气的经验,可提炼出一种话语范式:“情感渲染——直呈结论”,指战员通过简短的话语调动官兵同仇敌忾的情绪后,立刻不容置疑地给出作战结论。作战结论包括了作战方向和作战结果,即便二者之间不存在表面上的合理性,指战员也不需要论证作战方向与作战结果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极端环境下群体拒斥理性,非理性的号召反而可以激发出存在于不合理性中的合理性,带有隐喻色彩的断言法在极端战场环境下往往能极其强烈地刺激官兵的军人血性,甚至实现战局逆转。
三、教民以战:学生群体的血性孕育
儒圣孔子针对春秋时期兵争不断的格局需要,从仁本主义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18]152的军事伦理思想。后经李悝、吴起、商鞅等人演绎变成了“教民耕战”,但“教民以战”的军事伦理思想无论从其目的还是手段来看,都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有着军国主义的倾向,需要对其进行扬弃,使之符合习主席所提出的“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努力开创强军兴军新局面”[19]这一战略目标。军训作为军队对兵源主体即学生群体施加影响的最直接方式,在实践过程中却存在着一些形式主义的问题,因此需要优化军训训练内容,发挥其应有的“教民以战”的武德培育功能,以达到孕育学生群体血性潜质的目的。
(一)讲授军人血性故事
组织教员向学生讲授弘扬军人血性的故事,由于教官是现役军人,其述事风格带有更浓厚的兵味、更强的亲历性和情感性,且授课地点多为训练场而非较拘谨的课堂,授课时间多为训练间隙而非集中讲课,这使得讲授过程带有隐性教育的特点和优势,易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纳军人的理想人格,实现初步的内在认同。为方便教官讲课,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可联合教育部编写授课教材,或者军训单位的政治处联合学校编写教材,供教官讲课使用。在教材编写过程中需注意:第一,根据受训对象年龄区分授课的内容与目的。按照受训对象学龄阶段有针对性地编写教材,契合受训对象接受层次,形成不同年龄段由低至高阶梯式的德育目标。第二,优化教育的话语方式。需要通过优化教材的文字表达来优化教官的话语方式,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应当根据对象层次的不同由浅入深地进行表述,特别是针对大学生的教材,要打破话语呆板、形式单一、政治口号浓厚的旧的宣传话语范式,筛选一些被大学生普遍接受的新式话语内容,并提升其理论内涵,使之符合教学需求,形成兵味浓、大众化、时尚化的话语方式。第三,拓宽授课的事例范围。以我国革命战争时期、古代战争中发生的战例、军事实践为主,可适当增加外国意识形态较弱的战例或者军事家的事迹,并鼓励教官讲述本单位或友邻单位发生的具有教学意义的事例。使教育内容呈现层次多、纵深长、信度高的特点。
此外,军队可与地方院校形成定期授课的常态化机制,组织军队院校的专家或英模事迹报告团等军队人员定期进入地方院校为学生讲课,巩固军训期间的教育成果。
(二)开设心理训练科目
军训处于学生进入新环境学习的过渡期,这个阶段学生的心理活动往往出现较大的不稳定性和可塑性。部队可利用军训期间学生心理可塑性较强的特点,依托地方院校的设施与人员对学生展开心理训练,以锻炼学生的意志,强化他们的自觉性、果断性、自制力、坚持性等意志品质,培养军人的血性潜质。在训练过程中要注意:第一,遵循各阶段入学学生心理形成的渐进性规律,科学有序地设置训练进程。第二,设置的心理训练科目不宜太过复杂,方便教官组织施训。第三,将心理训练穿插于军训的各项内容之中,使学生在较艰苦的训练环境下增强心理承受能力、心理应激能力和心理防御能力。
(三)教唱弘扬军人血性的军旅歌曲
《乐记》认为:“乐者,德之华也”[20]27,可见音乐能够在道德品质形成过程中产生作用,军歌作为音乐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军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育人功能。军歌的德育功能是通过情感共鸣的形式实现的,然而当前军训中教唱的歌曲普遍以老一代军歌为主,老一代军歌受创作年代、话语风格等因素限制,难以使求新求异的当代青年学生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且当前军训中教唱的大部分歌曲主题并不是弘扬军人血性,譬如《团结就是力量》从根本上说突出的是集体主义精神,《学习雷锋好榜样》突出的是无产阶级立场,《文明礼貌歌》突出的是和谐的人际关系。因此,基于以上两点考虑可在军训中适当增加一些弘扬军人血性的新式军旅歌曲。以2014年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部向全军和武警部队推荐的20首战斗精神歌曲为例,其中《看我的》《血性军人钢铁汉》《强军战歌》等等一系列歌曲均主旨鲜明、节奏明快、词曲新颖,这种崭新的军歌艺术表现形式符合青年学生的审美需求,能够深深触动他们的情感,在传唱过程中以一种“春风化雨”式的隐性教育手段影响、塑造他们的道德情操和精神世界,催生他们坚强勇敢的意志品质,进而孕育学生群体的军人血性潜质。
四、结束语
中华传统武德文化与中国现代军事文化具有高度的理论契合性,其对武德履践与武德戒律的规定为培育当代革命军人血性提供了具备操作意义的路径指南。本文从烟波浩渺的古代兵书中择选一二思想,梳理出培育军人血性的三条路径:“正己化人”“众陷于害”“教民以战”。然而这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中华传统武德文化中还有更多的瑰宝等待我们去挖掘。大力探索其与现代军事思想的内在逻辑契合,借鉴其中不曾过时的实践方式,弘扬符合中国军人气质的武德规范,是响应习主席强军兴军思想的需要,也是军队政治工作继承与创新的应有之义。
[1] 黄石公.黄石公三略[M].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9.
[2] 诸葛亮.诸葛亮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0.
[3] 草庐经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 朱少华.中华武德名论[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8.
[5] 左丘明.左传[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6] 管仲.管子[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7] 六韬[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8] 孙武.孙子兵法[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9.
[9] 王联斌.中华武德通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8.
[10] 戚继光.练兵实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1]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Z].2010-08-09.
[14] 黄帝四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5] 三十六计[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9.
[16] 司马穰苴.司马法[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
[17] [法]古斯塔夫·勒庞.大众心理研究[M].戴光年,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
[18] 孔子.论语[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
[19] 习近平在出席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 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努力开创强军兴军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5-03-13(1).
[20] 乐记[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
(责任编辑李献惠)
Solution to Cultivating Military Courage and Uprightness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Takenori Educational Methods
YANG Xu
(TeamofGraduateStudent,TheArmedPoliceAcademy,Langfang,HebeiProvince065000,China)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takenori has a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for cultivating military courage and uprightness. Moralizing others by straightening out oneself reveals the importance of cadres to lead by example, in other words, cadres should possess “loyalty, courage, faith, love, strict”. The takenori stimulation method of being driven to desperation reveals the stimulating effect of an extreme environment on military courage and uprightness. The word pattern of mobilization is “emotional rendering——directly displaying conclusion”. The breeding ways of takenori which teaches people to war tell us to strengthen the students’ courage and uprightness, and to optimize the military training content.
Chinese traditional takenori; military courage and uprightnes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2015-12-24
杨煦(1992—),男,浙江乐清人,军队政治工作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E221
A
1008-2077(2016)09-006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