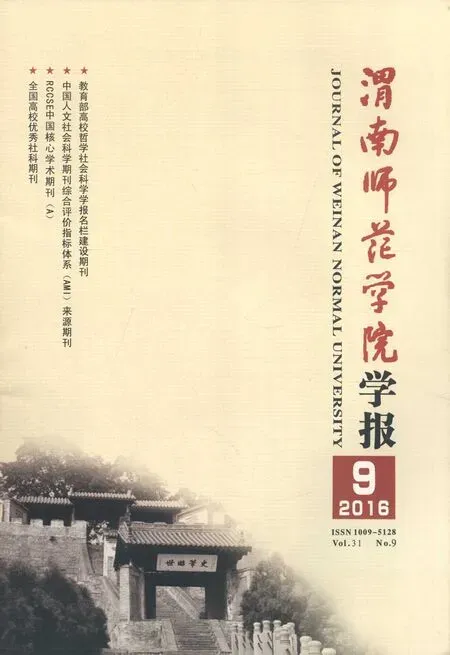司马迁的兵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刘 洪 生
(商丘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司马迁的兵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刘 洪 生
(商丘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摘要:战争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种存在形态。司马迁谙识兵道,将对战争的独特理解,巧妙地糅合在《史记》各篇中,如撮盐入水,无迹而味存,无形而魂在。比较而言,后之史家和史书刻意而拙笨地辟出“兵志”专栏,生硬罗列,与太史公的智慧相比,反倒是入于下流。即使今天,《史记》蕴涵的军事辩证法理论,仍是世界人民宝贵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军事思想;现实意义
李塨的《阅史郄视》卷二云:“李卫公言,史官鲜克知兵,故兵制不传。余览《史》、《汉》以至南北朝,良然。至《唐书》乃专志兵,则欧阳诸公之识可谓卓越前人矣。”文中的李卫公,是指唐代杰出的将领和军事理论家李靖,他认为唐以前的史学家是不晓军事的,因而他们的史书体例没有“兵志”。作为清初哲学家的李塨,赞同此观点,并申论中国正史最早专门记载军事问题是自《新唐书》始,并认为这是欧阳修、宋祁等人的远见卓识。而史学家顾炎武则说:“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势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及也。”[1]1883一反李塨之所论。近人程金造《司马迁的兵学》论:“我认为史官不知兵,若是指《汉书》以下诸著史之官则可,至于太史公司马迁,则殊不然。司马迁是通识兵书,深知兵略之人。”[2]314当代学者张大可先生的《司马迁的战争观》[3]101-125,以更为宽广的视域,认为“《史记》是一部古代最完备的战争史”,并分析“司马迁战争观形成的历史条件”,对“司马迁在史论中表述的战争观点”进行了大致归纳。笔者认为,当今这一话题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故就司马迁的军事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等问题,略陈鄙陋,以期使这方面的探讨得到深入和广泛关注。
一、严明的军纪是制胜的永恒法宝
首先,司马迁在《史记》中,详细记述了许多军事指挥家整肃军纪、严明军法的生动故事,如《司马穰苴列传》记载:
穰苴曰:“臣素卑贱,君擢之闾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权轻,愿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监军,乃可。”于是景公许之,使庄贾往。穰苴既辞,与庄贾约曰:“旦日日中会于军门。”穰苴先驰至军,立表下漏待贾。贾素骄贵,以为将己之军而己为监,不甚急;亲戚左右送之,留饮。日中而贾不至。穰苴则仆表决漏,入,行军勒兵,申明约束。约束既定,夕时,庄贾乃至。穰苴曰:“何后期为?”贾谢曰:“不佞大夫亲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于境,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于君,何谓相送乎!”召军正问曰:“军法期而后至者云何?”对曰:“当斩。”庄贾惧,使人驰报景公,请救。既往,未及反,于是遂斩庄贾以徇三军。三军之士皆振栗。久之,景公遣使者持节赦贾,驰入军中。穰苴曰:“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问军正曰:“驰三军法何?”正曰:“当斩。”使者大惧。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杀之。”乃斩其仆、车之左驸、马之左骖,以徇三军。遣使者还报,然后行。[4]1629-1630
这里,司马迁假穰苴对庄贾行刑前所言,表达了自己对用兵之道的深刻理解:第一,严明的军纪,不仅是一种组织原则和纪律约束,更是一种精神和信仰。军命如山,令行禁止,不容丝毫动摇和怀疑,是取胜的根本保证,所谓“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第二,在军纪面前人人平等。这不仅体现军纪的神圣性,更大的意义在于,能让普通士兵感受到尊严和价值,从而激发他们在战场上的自觉意识和坚强的斗志。因而,穰苴在处斩庄贾时,特别指出他的滞后,让“士卒暴露于境……百姓之命皆悬于君”。甚至对无视军纪、持节驰军的齐景公使者“斩其仆、车之左驸、马之左骖,以徇三军”。这样,士兵所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一种威严,也是一种极为可贵的平等价值和被尊重的荣耀。
在《孙子吴起列传》中,司马迁这样描写:
(孙子)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鈇钺,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4]1635
第一,这是一个颇滑稽的故事,一开始就写出了吴王阖庐对孙武、兵法看似尊重,实则等同儿戏的态度,当孙武回答他说“可以小试勒兵”时,他竟然出人意料地说“可试以妇人乎?”按通常的逻辑,战争让女人走开,于是出现了可想而知的荒诞局面。而孙武则毫不客气地贯彻了“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的军纪原则,在对战争认识的根本问题上,给荒唐的吴王上了一课,批评他“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第二,孙武坚决拿会让吴王“食不甘味”的二姬开刀,与上一个故事一样,体现了军纪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可见,司马迁是在通过这些事例,总结和强调这一古今铁定的军事定律。第三,在上述两故事中,穰苴曰:“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孙武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司马迁实录了二人几乎相同的话,深刻体现了他对将、帅独立性这一规律的认同和理解,也是极为经典和令人肃然起敬的。第四,严明的军纪是时效的保证,引文最后,司马迁交代:“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进一步肯定了军纪的作用。
《留侯世家》这样叙述:
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去,曰:“后五日早会。”五日鸡鸣,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曰:“后五日复早来。”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4]1519
这段文字告诉读者:第一,“老父”要求张良“当如是”的,正是正确的时间观念,它作为军纪的一种直接体现,在战场上是至关重要。第二,文中号称“兵仙”的老父黄石公,有几分虚无缥缈;《太公兵法》的具体内容,司马迁也完全省略了,而却用大量笔墨,叙述了“老父”对张良近乎苛刻的时间考察,是否有某种深意呢?第三,最后,张良“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因异之,常习诵读之”,联系前后文,似乎告诉读者,留侯从中所深刻领悟到的,正是一种用兵的精神,所以接着司马迁交代:“(张)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那么,这里刘邦“省”(他人“皆不省”),“省”的是什么呢?不正是一种“高级”的用兵之道吗?
其次,《史记》还通过不同民族的共同认识,揭示这一军事原则。《匈奴列传》记载:
单于(头曼)有太子名冒顿。后有所爱阏氏,生少子,而单于欲废冒顿而立少子,乃使冒顿质于月氏。冒顿既质于月氏,而头曼急击月氏。月氏欲杀冒顿,冒顿盗其善马,骑之亡归。头曼以为壮,令将万骑。冒顿乃作为鸣镝,习勒其骑射,令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行猎鸟兽,有不射鸣镝所射者,辄斩之。已而冒顿以鸣镝自射其善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顿立斩不射善马者。居顷之,复以鸣镝自射其爱妻,左右或颇恐,不敢射,冒顿又复斩之。居顷之,冒顿出猎,以鸣镝射单于善马,左右皆射之。于是冒顿知其左右皆可用。从其父单于头曼猎,以鸣镝射头曼,其左右亦皆随鸣镝而射杀单于头曼,遂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冒顿自立为单于。[4]2317
冒顿单于时期,是匈奴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这一辉煌时代的缔造者——冒顿,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上述记载分明可见,他作为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家,对严明军纪的执着追求,从“以鸣镝自射其善马”,到“以鸣镝自射其爱妻”,再到“从其父单于头曼猎,以鸣镝射头曼”,最终以鸣镝为号,通协百军,箭之所指,士兵所向,训练出一支所向披靡的铁血之旅。当时的冒顿,未必有对《司马穰苴兵法》和《孙子兵法》的学习和了解,但他作为一个天才军事家,对严明军纪的自觉领悟,恰能说明,这是古今中外一流军事家“英雄所见略同”的共识。
再次,司马迁还通过将帅不同治军风格的比较,进一步阐明军纪的重要意义。
程不识故与李广俱以边太守将军屯。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刀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不识曰:“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是时汉边郡李广、程不识皆为名将,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4]2301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于悲剧英雄,太史公常寄予过多的同情,而以情掩理,失之子羽。我们阅读《史记》时,也常常会迷失在那些浓郁的抒情性文字中。对李广的传记,正是如此。笔者认为,司马迁对李广这一形象的描写,是有所偏爱的。严格意义上说,李广只是一位优秀战士,而不是一个完全合格的将军或军事家;或者说,他仅仅部分地具备了军事家的一些素养,充其量只算是“半个将军”。而他的最终自刎,虽然催人泪下,但却是必然结果。在上述引文中,司马迁通过李广与程不识两种不同治军风格的比较,揭示了这种必然性:“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而最终结果却是:“程不识孝景时以数直谏为太中大夫。为人廉,谨于文法”;李广引刀自刭,却慨叹“岂非天哉”,实是对军事和兵法的茫昧不明。
此外,司马迁在《魏豹彭越列传》中,也写到了军风、军纪的问题:“居岁余,泽间少年相聚百余人,往从彭越,曰:‘请仲为长。’越谢曰:‘臣不愿与诸君。’少年强请,乃许。与期旦日日出会,后期者斩。旦日日出,十余人后,后者至日中。于是越谢曰:‘臣老,诸君强以为长。今期而多后,不可尽诛,诛最后者一人。’令校长斩之。皆笑曰:‘何至是?请后不敢。’于是越乃引一人斩之,设坛祭,乃令徒属。”笔者认为,《史记》这些看似类同的描写,绝非简单的重复,而是“借司马穰苴发表了自己对治军的看法”[5]191。总结和推导一种治军规律——严明的军纪,是制胜的永恒法宝,是战争胜利的第一步;同时,司马迁又对世俗庸儒的“闇于大较”“不当用兵”,进行了批判和嘲讽,并深表忧虑,他在《律书》中说:“晋用咎犯,而齐用王子,吴用孙武,申明军约,赏罚必信,卒伯诸侯,兼列邦土,虽不及三代之诰誓,然身宠君尊,当世显扬,可不谓荣焉?岂与世儒闇于大较,不权轻重,猥云德化,不当用兵,大至君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执不移等哉!”[4]898
二、士兵永远是战争的主体
兵将的关系,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之一。甚至某种意义上说,士兵才是战争的主体。没有士兵的战争,是不存在的;没有士兵的将军,也是没有价值的。因而,以士兵为主,一切依靠士兵,是取得战争彻底胜利的根本保证。“人们微不足道,统帅就是一切”的军事理论,正是拿破仑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正由于此,1849年3月,恩格斯在《皮蒙特军队的失败》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人民战争”的科学概念。毛泽东则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论著中,系统完善了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成为世界军事理论的经典,并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史记》中,司马迁通过客观叙述,记下了许多反映兵将关系的案例。
(一)将帅爱恤士卒,上下之间血肉相连、荣辱与共的关系
《司马穰苴列传》记述穰苴将兵,“士卒次舍,井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拊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卒,身与士卒平分粮食。最比其羸弱者”。正是穰苴这种爱兵如子之情,使得一旦有军情时,战争动员几乎是多余的,“病者皆求行,争奋出为之赴战”。
《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吴)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那么,吴起这样对待士兵,士兵又如何表现呢?“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虽然这位母亲的话,略带心酸,但吴起作为一个将军是称职的。所以司马迁补充说:“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
在战国四公子中,对于魏无忌的“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司马迁是最为称道的,“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4]1829。因而,一再描述魏公子爱恤士卒,士卒也乐为其用的事例,“公子遂将晋鄙军。勒兵下令军中曰:‘父子俱在军中,父归;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得选兵八万人,进兵击秦军。秦军解去,遂救邯郸,存赵”。“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走蒙骜。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当是时,公子威振天下,诸侯之客进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4]1828
《廉颇蔺相如列传》写道:“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幕)府,为士卒费。日击数牛飨士,习射骑,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显然,司马迁评价李牧“良将也”,不仅是因为他的战功,也因为他具备良将的基本素养——“厚遇战士”。
即使项羽,虽是一个失败的英雄,但《项羽本纪》中记载:“(宋义)乃遣其子宋襄相齐,身送之至无盐,饮酒高会。天寒大雨,士卒冻饥。项羽曰:‘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可见,“士卒冻饥”,而将军“饮酒高会”,是项羽斩杀上司宋义最合乎情理的借口。《陈相国世家》说项羽:“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洁好礼者多归之。”《淮阴侯列传》说:“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此所谓妇人之仁也。”此两处语境,虽有反讽味道,但也客观上肯定了项羽对下属的爱重,否则“垓下之围”时,与部将的诀别就不会那么悲壮。甚至连“半个将军”的李广,也懂得这种基本的统兵之道,“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4]2302。
(二)对士卒“若驱犬羊”,则必然导致战争的失败
首先,让我们看《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一段精彩叙述:
秦与赵兵相距长平,时赵奢已死,而蔺相如病笃。赵使廉颇将攻秦,秦数败赵军。赵军固壁不战。秦数挑战,廉颇不肯。赵王信秦之间。秦之间言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赵王因以括为将,代廉颇。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胶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赵王不听,遂将之。赵括自少时学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尝与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难,然不谓善。括母问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即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及括将行,其母上书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将。”王曰:“何以?”对曰:“始妾事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王以为何如其父?父子异心,愿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决矣。”括母因曰:“王终遣之,即有如不称,妾得无随坐乎?”王许诺。赵括既代廉颇,悉更约束,易置军吏。秦将白起闻之,纵奇兵,详败走,而绝其粮道,分断其军为二,士卒离心。四十余日,军饿,赵括出锐卒自博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数十万之众遂降秦,秦悉阬之。赵前后所亡凡四十五万。明年,秦兵遂围邯郸,岁余,几不得脱。赖楚、魏诸侯来救,乃得解邯郸之围。赵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诛也。[4]1887-1888
这是一个曲折生动的故事,更是一个绝佳的反面教材,或许,后者才是太史公的良苦用意。赵括为什么失败?第一,死读兵书,不知权变,“若胶柱而鼓瑟耳”。第二,草率出兵,缺乏对战略、战术和敌我双方的准确判断,“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更重要的是第三个原因,即将帅的人格精神和他在士兵心目中的地位,赵括的父亲、一代名将赵奢是“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而赵括却是“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回报他的必然是“士卒离心”。这是令人刻骨铭心的教训。
其次,《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司马迁还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记述,“楚闻廉颇在魏,阴使人迎之。廉颇一为楚将,无功,曰:‘我思用赵人。’”读到这里,笔者思考:为什么一代名将廉颇入楚则“无功”而“思用赵人”?是什么造就了英雄?战争中“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6]134?正如毛泽东所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资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能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6]131
司马迁之后约千年,赵宋王朝建立。在加强中央集权时,统治者最先考虑的,就是军队问题,对兵将之间的关系问题,可谓是煞费苦心:举天下之兵宿于京师,创禁兵制,设三衙,以三帅统领禁军;同时设枢密院,以枢密使主管禁军;三衙与枢密院、三帅与枢密使之间的关系是,“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7]17A再设以“更戍法”,名义上使士兵“习山川劳苦,远妻孥怀土之恋”,实则是靠这种“戍守边地,率一、二年而更”的频繁换防,造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斩断将兵之间的血肉纽带关系,“(宋)太祖、太宗平一海内,惩累朝藩镇跋扈,尽收天下劲兵列营京畿,以备藩卫……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内外相维,上下相制,等级相轧,虽有暴戾恣睢,无所厝其间。是以天下晏然,愈百年而无犬吠之惊。此制兵得其道也”[8]1327。姑且不论赵宋王朝是否真的“无犬吠之惊”,而靠士卒拥立和兵变起家的赵匡胤兄弟,对于兵将之间的这种关系,敏感程度是异乎寻常的,也许这正是他们深谙用兵之道的逆向之思!
三、对战争复杂性的认识
战争的本质是什么?战争给社会生活带来了什么?战争都是不可避免的吗?谁是战争的真正胜利者?战场上如何对待战俘?究竟如何评价历史上的战争……作为一部志在“原始察终,见盛观衰”[4]2790,“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9]581的巨著,《史记》作者思考并回答了这些问题,如张大可先生所论:“他的战争观不仅表述于史论中,而且也表述于述史方法和笔削内容之中。”[3]104
(一)战争的两面性
首先司马迁认识到,战争的本质是政治的延续,是社会矛盾斗争的最高形式,也是一种推进历史演变的动力,“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4]897,并批评“世儒闇于大较,不权轻重,猥云德化,不当用兵,大至君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这种不一味否定战争的态度,超越了儒、墨*《孟子·离娄上》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另见《墨子》之《兼爱》《非攻》等篇。等家,毕竟战争是人类社会活动不可避免的一种形态。正如列宁所指出:“历史上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和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有利于人类的发展,有助于破坏特别有害的和反动的制度。”[10]668
其次,司马迁认识到,解决争端,杀伐与征服并不是最佳选择,战争只能是短暂的存在,和平、道德、仁爱才是更高级的社会文明。《孙子吴起列传》记载:
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4]1638-1639
这里通过吴起对魏侯的教导,揭示和平治世的最高维系,并不是山河之险和坚船利炮,而是“修德”,“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作律书第三”[4]2761。这样,司马迁又超越了孙武对战争本质的片面认识——“掠乡分众,廓地分利”[11]122。清代祁骏佳在《遁翁随笔》卷下中叹服:“马迁常究心于兵法,不浅也。”
(二)战争的人性化
首先,司马迁明确表示,残杀俘虏是极其可耻的。《项羽本纪》记录了楚霸王项羽屠城和坑杀降卒的丑行,“项梁前使项羽别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项羽乃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于是楚军夜击阬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白起王翦列传》记录了嗜杀成性的白起,在临死前的反思:
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自裁。武安君(白起)引剑将自刭,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杀。[4]1778
在撰写秦将世家王翦、王贲、王离祖孙三人时,对王离的被虏,司马迁却说:“不亦宜乎!”并找出原因:“夫为将三世者必败。必败者何也?必其所杀伐多矣,其后受其不祥。”[4]1780特别是对李广的命运,司马迁在扑朔迷离的叙述中,也似有同情之外的复杂评价:“(王)朔曰:‘将军自念,岂尝有所恨乎?’(李)广曰:‘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大恨独此耳。’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4]2304
其次,《史记》还记载了每次战争的滥杀,这些血淋淋的数字,表露了太史公的人文精神。扬雄在《法言·君子篇》中说:“多爱不忍,子长也!”祁骏佳的《遁翁随笔》根据《白起王翦列传》,计算出秦将白起的杀人数字:“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攻魏,拔华阳,斩首十三万;又沉赵将贾偃之卒二万于河中。攻韩陉城,斩首五万。坑赵卒四十万。其他前后斩首虏且四十五万人。则其斩馘不啻百万矣。”[2]370实际上,司马迁还说他“攻南阳太行道,绝之”[4]1775,使一条道路为之断绝,又该是怎样的一种屠杀呢?因此,司马迁借用苏秦的话,说秦是“虎狼之国”[4]1708。事实上,春秋战国约500年间的58次重大战争中,诸侯国无不如此,因而,孟子说“春秋无义战”[12]455。
(三)战争的不可知性
首先,战争的法则,没有可遵守的教条。宋襄公在战场上大讲“仁义”,耐心等待强敌渡河列阵而后开战,终于招致败亡。司马迁嘲笑了这位战争愚人:“襄公伤于泓,君子孰称?”[4]2766《廉颇蔺相如列传》描写一代名将赵奢,精于用兵,而其子赵括却是一个徒有虚名的庸才,死读兵书,不知权变,妄自尊大,头脑简单,终于在长平之战中,葬送了赵国。正如《老子》所论:“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13]323
其次,鉴于战争的复杂性,司马迁肯定了合变奇胜的战术策略。《田单列传》中,田单以五千兵大破十万燕军,司马迁赞道:“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者,出奇无穷。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在井陉之战中,陈馀拒绝李左车的奇计,只知纸上谈兵,兵败身死为天下笑,司马迁语含讥讽地写道:
成安君(陈馀),儒者也,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曰:“吾闻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今韩信兵号数万,其实不过数千。能千里而袭我,亦已罢极。今如此避而不击,后有大者,何以加之!则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不听广武君(李左车)策。[4]2043
笔者认为,司马迁所谓“奇计”有两层含义:第一,是出人意表、不蹈故常的非常规之思,如田单的“火牛阵”;第二,李左车游说陈馀时说:“闻汉将韩信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新喋血阏与,今乃辅以张耳,议欲下赵,此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其后。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坚营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使野无所掠,不至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于戏下。愿君留意臣之计。否,必为二子所禽矣。”其实不过是延时、断后、包抄、劫粮道而已,而又的确是让对手韩信大吃一惊的“奇计”,原因是充分利用了特殊的地形和时机。也就是说在具体场景下,一切常规手段又都可能化为“奇”,“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耳”[4]898。第一种奇,是有形的奇,尚有迹可循,第二种是无形的奇,则是奇变无穷,充分体现出战争的不可预测性。因而,《孙子兵法》的第九、十、十一篇对地形、地物的讲论尤详。
第三,对战争结果的复杂情怀。《越王勾践世家》写越王欲伐吴,范蠡阻止说:“不可。臣闻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试身于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结果果然是越王“以余兵五千人保栖于会稽。吴王追而围之”。《平津侯主父列传》说:“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末节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圣王重行之。夫务战胜穷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在《乐书》中,司马迁更是论道:“夫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军旅鈇钺者,先王之所以饰怒也。”认为军队和兵器的最好使用,是张而不用,所谓“虽有甲兵,无所陈之”[13]357。《张仪列传》:“齐与鲁三战而鲁三胜,国亦危亡随其后,虽有战胜之名,而有亡国之实……秦赵战于河漳之上,再战而赵再胜秦;战于番吾之下,再战又胜秦。四战之后,赵之亡卒数十万,邯郸仅存,虽有战胜之名而国已破矣。”揭示了“失败的胜利者”这一特殊战争现象,所谓“为者败之,执者失之”[13]309,如《孙子兵法·谋攻》所谓“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匈奴列传》甚至批评了汉朝对匈奴连年用兵的失策:意气用事,“建功不深”,“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在司马迁看来,历史上那些无价值的角逐,蠢如庄周所说“以随侯之珠,弹千仞之雀”[14]972,这些战争悖论现象,即使今天,也值得深思,特别是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
四、结语
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近现代以来的历史饱经沧桑和患难;随着21世纪的到来,这只东方雄狮正昂首奔进在崛起的道路上。而在她的四周,无论是陆地还是海洋,又是那样的不平静,“文明冲突”,地域之争,使国际斗争,风云变幻,云波诡谲,甚至剑拔弩张,战事一触即发。在此历史的关口,我们一方面应积极学习和利用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富国强兵,积极备战;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利用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在我们先人的智慧和宝典中寻找资源、方略和借鉴。
与其他史书或专门性的军事著作相比较,《史记》中的兵学视域是宽广的,是以整体和宏观的高度去认识军事和战争。不仅是一部古代最完备的战争史,更蕴涵着系统科学的军事理论,深刻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太史公的这种兵道观深受老子道家思想*魏源的《老子本义序》说:“五千言动称经言及太上有言,又多引礼家之言、兵家之言。”《孙子集注序》说:“《老子》其言兵之乎……吾于斯见兵之精。”章太炎《 书·儒道第三》认为:“老聃为柱下史,多识掌故,约《金版》《六韬》之旨,著五千言,以为后世阴谋者法。”俞樾《诸子评议·补录》判定“兵家源于道德”。郭沫若《中国史稿》说“《老子》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又是一部兵书”。翟青《老子是一部兵书》(《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王明《论老子兵书》(《道家与道教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等文章,进一步探讨了该问题。葛荣晋先生甚至论定“老子对于中国兵学有开山之功”(《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版)。的影响,其“在德不在险”“非兵不强,非德不昌”“善战”“不以兵强天下”的战争观,备战、慎战、止战的军事精神,具有崇高的人文关怀,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传统和素养。因此,某种意义上说,《史记》中的军事思想是解决当今世界冲突的宝贵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 [明]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黄汝诚,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 程金造.史记管窥[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3] 刘乃和.司马迁和史记[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
[4] 王利器.史记注译[M].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
[5] 张大可,安平秋,俞樟华.史记研究集成:第三卷[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7] 左圭.左氏百川学海:第二十九册[M].北京:中国书店,1981.
[8]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兵考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6.
[9] [南朝梁]萧统.文选[M].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
[10] [苏]列宁.列宁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1] [春秋]孙武.孙子[M].曹操,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2] 杨伯峻.白话四书[M].长沙:岳麓书社,1989.
[13]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4] 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责任编辑朱正平】
The Military Thought of Sima Qian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LIU Hong-she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Shangqiu Normal University, Shangqiu 476000, China)
Abstract:War is a kind of existence form of human social activities. Sima Qian knew it well and skillfully wrote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wars into Historical Records. In comparison, the historian and the history books later deliberately and clumsily created “Bing Zhi” column, and roughly made the series of the list, which was not wise compared with Taishigong’s wisdom. Even today, Historical Records contains the rich military dialectics theory, and it is still a valuable resource of the world.
Key words:Sima Qian; Historical Records; military though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作者简介:刘洪生(1964—),男,河南柘城人,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6-03-30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16)09-0026-08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