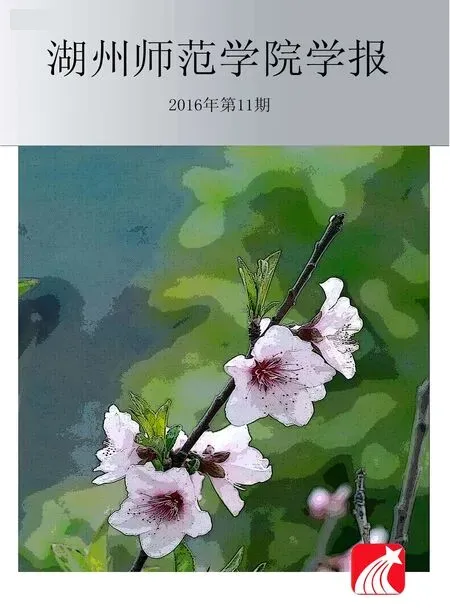正当命名:从场域运作看余华小说的译介*
龚艳萍
(浙江农林大学 暨阳学院,浙江 诸暨 311800)
正当命名:从场域运作看余华小说的译介*
龚艳萍
(浙江农林大学 暨阳学院,浙江 诸暨 311800)
场域理论认为场域是现代社会实体所包含的多个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的小社会;场域行动者拥有相应资本和对应的社会位置,凭借该位置可获得更好的社会位置与资本。以场域理论为基础,从影视场域、出版场域、翻译场域和其他场域分别梳理余华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传播与接受情况,指出其译介亦为正当命名余华之过程,由此角度希望能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参考性启示。
余华;正当命名;场域;翻译
翻译社会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要阐述译作在动态的异域文化中接受与传播的社会成因。若以译本接受度来看,理论上可分原本接受程度高于译本接受程度、原本接受程度等同译本接受程度、原本接受程度低于译本接受程度三种大概情况,而具有翻译社会学阐述意义的应为第一种和第三种。对当前遭遇诸多瓶颈问题的中国文学译介而言,原本接受高于译本接受的翻译情况或更具借鉴与参考意义。
由于余华小说在异域文化中突破了在原语文化中的旧有地位,常被指为“国内结果,国外飘香”,成为鲜有的成功译介案例;同时也由于任何一部文学译作都不是在纯粹的文学世界的框架中被析出,不是作为单纯的文本翻译出现在文学谱系上,而是以一种被动状态置放在复杂的社会建构中力求得到异域文化的传播和接受[1](P79)。透过不同于前有文献[2](P42-46)[3](P43-49)的布迪厄场域理论社会学视角,本文力图从小说译介的场域形态和动态的交错过程入手,解释从弱势文学体系进入强势文学体系中的文学译本关于社会筹码的增持过程,借此廓清文学接受与社会场域的内在关联,就中国文学译介之困与余华小说译介之立,提供译介启示与意义。
一、场域要义与文学译介
现代社会高度分化,统摄一切的社会实体并不存在,反之是由多个具有自身特定性的小社会构成。这些小社会就是场域,它也可以被理解为是社会位置与社会位置之间的一个客观关系网,每个社会位置都由它和其他位置的客观关系来决定,而这个位置则依靠自己在场域结构中所拥有的资本、种类、分布及潜在状况。资本、种类、分布与潜在可能越多,对于谋得场域的优越位置就越有帮助。[4](P69)各个场域彼此之间既有独立性,又有依赖性。
对于文学作品,场域理论认为它在文化生产场域也需要一定的活动前提。这些活动前提包括分析文学场在权力场内部的位置与时间进展,文学场的内部结构(关于各种位置客观关系的结构),为相应的合法性而竞争的位置占有,以及分析位置占据者的惯习生成和文学场内部的运作轨迹。[4](P38)可见,文学作品要在场域获得某一位置,不仅要拥有文学价值,同时还要兼有相关的场域运作、关系配置和资本累积。这些综合因素形成客观的关系网,最终影响到相关去向和结果。因此,可以断言之,一旦进入场域,文学作品就需要利用自身的位置和关系网络去营谋目标位置;居于场域之中,就意味着必须接受场域的基本规则。
文学译介也不例外,它需要数量不齐、形式多样的资本帮助完成译介过程。在翻译活动中,翻译行为者,比如译者、经纪人、出版机构、译文读者所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多,那么在翻译场域中所处的位置也就越优越,反之则是越被动和越尴尬。作为正式化和制约化策略的运行场所,任何场域所进行的争斗都是为了谋取某种合法性,其争夺焦点就是界限,就是边线,就是进入权和参与权。[1](P300-301)而来自于弱势文化的原语文学在强势的异域文化中要竞得生存,就必须经历原语文学场域、翻译场域、出版场域和目的语文学场域,所经历和遭遇的社会境况与文学过滤也将更复杂和更微妙。
对于游走在强势文学中的弱势翻译文学,能够被正名就是场域运作的第一站,这是场域理论中最核心的要素,文学的译介场域因此而各自产生和拥有自己的官方话语权,并进而发生以下几种场域运作功能:第一,为某文学作品或文学作家正名;第二,强调或淡化其文学意义或社会功能;第三,利用自身位置与资本为该文学争取文学合法性,帮助到达文学边缘或中心。
正当命名是象征权力斗争最为核心的方面,也是场域政治最为关键的地方……它制造了官方分类,由官方许可和保证象征资本。[1](P116)在正当命名的前提下,其余诸要素及行动力量将围绕它而展开。对文学译介而言,就是使译本能够成功到达翻译链条上的最后环节,且各个社会小场域中的不同行动者在所谓的、合乎本土文化情理的惯习驱动下,为了获得同一个社会合法性,同力作用在文学译介的行动方向上,通过资本累积直至被正当命名,确保译本接受和传播的可能性。
二、场域、正当命名与余华小说译介
从1983年开始,余华开始写作,著有多部小说、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并被多个国家翻译和传播。余华专论研究在文学界颇多,其中,洪治纲全面概述了余华文学作品特点,包括文学主题、语言特点及音乐的文学影响等等。[5]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国门且能幸获文学奖的并不多见,但余华却一人独占多部且获多项海外荣誉:凭借《活着》的意大利版本和英译本分别在1998年和2002年获得PremioGrinzaneCavour(theLiteraryMasterAward)与JamesJoyceFoundationAward,其中所获意大利文学奖的是该国的最高文学奖,而JamesJoyceFoundationAward则是第一次颁给了一位中国作家;2004年凭借Crisdanslabruine(《在细雨中呼喊》的法译本)获得法国ChevalierdeL’ordredesArtsetdesLettres;2004年凭借ChronicleofaBloodMerchant(《在细雨中呼喊》的英译本)获得美国TheBarnes&NobleReviewFromDiscoverGreatNewWriters;2007年凭借《兄弟》的英译本Brothers与法译本Lesfrères分别获得ShortlistedManAsianLiteraryPrize与CourrierInternational。从1998-2008年,余华共获得了6次海外文学奖。就此来看,余华小说的翻译和接受无论是从数量来看,抑或是从质量来看,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谱系中都是一个不容忽视和低估的案例,需要认真分析和总结其中译介经验。
(一)影视场域与余华小说译介之正当命名
并非所有的原语文学,尤其是弱势文化的文学原作,都能够在翻译之后在异域文化中得到同等的文学尊重。在《活着》面世之前,葛浩文在TheColumbiaAnthologyofModernChineseLiterature中已经纳入了余华的文学作品ThePastandthePunishments,但反响一般,至少它没有从很大程度上激发异域读者对余华的再阅读兴趣。而余华小说《活着》本身就是一部有生命力的好小说。1994年,张艺谋改编了余华小说《活着》,将其拍成电影《活着》,并在第47届戛纳电影节夺得评委会大奖和影帝双项桂冠。这是余华小说译介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形成的场域影响力和传播力作为无形的文化资本敦促了两个相关结果的迅速诞生:第一,《活着》的被英译;第二,把观众变成了读者。
影视场域实际上是一种极有力的传播渠道,受众面积大,传播速度快,能在短时间内向观众传递电影的主旨、内涵与相关外延。读者KevinM.Kuschel、H.Huggins和MatthewMiller*英文人名前缀有“读者”是指亚马逊英文版网站上真实读者,参考其真实阅读感受可帮助本文更好地审视翻译文本接受情况。就认为,对余华的阅读兴趣肇始于电影《活着》,可只看电影不看书,就是错过一半,因此,哪怕是随意拾及的《在细雨中呼喊》也并未令自己失望。
在余华译介案例中,必须承认的是,张艺谋、电影《活着》和多项戛纳电影荣誉所形成的影视场域力量可以辐射到更多场域中去,其中,受到影响最多的还是原著作者余华,这个事件激发了异域文化中其他社会场域的反应和兴趣,为进一步开启余华译介掀开了辉煌的一页:首先,它将原著《活着》从异域文化的视野盲区推到了可视区域,改变了位置关系;其次,它用影视话语权奠定了原著《活着》的文学合法性,强化它的翻译可能性和异域文化接受性,并且正当命名了《活着》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这些都会积极推动《活着》的译介以及余华系列小说的译介。尽管电影所带来的效果是偶然因素,但它也提醒了翻译工作必须重视任何一个来自于其他场域的潜在因素,这些因素可对其在异域文化的命运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出版场域与余华小说译介之正当命名
由于翻译文学受众面积小,市场份额不多,所以一旦涉及到翻译和出版,出版社的行动其实是非常谨慎的,若能得到出版社的文学青睐和喜爱,不怕赔钱的出版理念仍可为其译介护航。电影《活着》的巨大成功使诸多异域文学工作者开始对余华产生兴趣。在此驱动之下,AnchorBooks(蓝登书屋下属的出版社)的总编辑LuannWalther对小说《活着》有着强烈的阅读渴望。[6]由于LuannWalther的强烈兴趣,《活着》开始被翻译、被传播和被推广。这股出版场域的力量真正启动了余华译介史。换而言之,余华英译小说走得相对顺利,是得益于这种正面的出版场域的力量。于此,余华自己也表示,尽管海外出版领域的关注基于很多社会与政治的成分,但无论如何首先都是小说的文学特征吸引了出版社,然后才能延续后续的故事。[7](P59-63)
另外,余华小说的海外经纪人王久安(JoanneWang)常年生活在外,熟悉美国出版环境,在英译小说的推广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她成功的幕后运作是余华小说译介在出版场域所拥有的另一个资本。总编辑与翻译经纪人结合其他出版场域的资本,将《活着》的英译本的文学评论见诸于多家报纸媒体,在此书翻译之后,凡余华新作之译的报道在美、英、德、法等西方主流国家更是铺天盖地。这些讨论、争论和辩论围绕余华的英译小说形成了评论圈,本身就是一个新的阅读场域策动点,提升了余华知名度,带动了公众阅读兴趣,策动了更多的场域力量酝酿和发生。
如果说电影《活着》还只是从故事性的角度来间接折射其潜在的可能的文学价值,那么《活着》的英译就更是一种文学正名,其将文学文本带入阅读视野,这种合法性进入更加堂皇,在这场域所形成的资本、运作模式和位置关系同样可以重复利用到更多的余华小说翻译事件中去,最终为余华本人所正名。多种客观因素共同作用使《活着》英译版最终得以出版,并且极为成功。2002年,余华获得詹姆斯·乔伊斯基金奖,这种文学场域和出版场域联合的结果更加稳固了出版商的信心。而由ToLive吸引的大批忠实读者,也从此形成了对作者余华的高度信任。因此,可以说,由于余华作品的其他衍生形式在其他场域形成了预备资本,进而推动了文本自身的翻译活动。可见,对文学翻译而言,社会的独立场域看似形式独立,实际关系紧密,甚至可以说是犬牙交错、难以分界。
(三)翻译场域与余华小说译介之正当命名
余华小说的译者们不仅是翻译家,同时也是汉学家,他们了解西方出版业的运作机制,清楚媒介对译作传播的影响,更能与作者达成良好互动与协同,维护作家作品的真实形象,在翻译上把握合适的平衡点,如此可在海外学术研究领域以及西方大众传媒中最大限度地传播和拓展中国文学的影响及社会效应。[8](P11)因此,要把中国作品成功引介到异域文化中去,就必须重视译者资质。
余华小说集《往事与惩罚》和小说《许三观卖血记》由AndrewF.Jones翻译。AndrewF.Jones在美国高校亚裔文学系任教,对余华持有长久的研究兴趣,其早期的硕士毕业论文就是与此相关。《在细雨中呼喊》则是由AllanH.Barr翻译,其主攻领域是明清时期的中国文学。《活着》则是由MichaelBerry翻译,他与余华是多年好友,有着丰富的汉英翻译经历。《兄弟》由EileenCheng-YinChow(周成荫)和CarlosRojas夫妇联手翻译。
显而易见,余华小说的译者几乎都是L1译者。尽管《兄弟》的合译者周成荫是L2译者,但深谙中国文化、哈佛大学的文学副教授身份、丰富的语言经历,并在翻译过程中与L1译者CarlosRojas联袂合译,这种翻译协作方式反而更能使这部小说增加读者的阅读信心,使他们对译者资质有一种充分信任,进而能够推动译作在译语文化中的传播与接受。
余华小说英译者的翻译策略可谓是亦步亦趋,甚少改动。其中有两种异于L2译者的翻译策略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第一种是因文化差异而灵活采用的翻译策略。比如关于《在细雨中呼唤》的翻译就有两个问题。首先,它原是发表在《收获》(1991)上的《呼喊与细雨》,但翻译为何改名?其次,余华英译小说里的人物名称都用汉语标准拼音,为何单单是孙广才被译成了“Kwangtscai” 而不是“Guangcai”?对这些问题,译者AllanH.Barr解释,改名是避免读者将它与IngmarBergman的电影CriesandWhispers混淆;而孙广才有三个儿子孙光平、孙光林、孙光明,若都按拼音来,“广”和“光”发音一样,如此拼音直译的名字会让读者误会孙广才与他三个儿子之间的辈分关系。[9]以上改动均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文化误解,为避免译语读者在阅读译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阅读困惑而量身定做的特别翻译策略。这种灵活性很难为L2译者所具备,其主要原因在于L2译者自身相对产生的、对译语文化的陌生感和生疏感。
第二种情况就是余华作品由于时间重叠错乱使得阅读小说的读者必须保持头脑清醒,否则很容易会被弄得混乱,甚至在这时间的漩涡中迷失,而弄不清故事的来龙去脉。[10](P34)可是,叙述视角的频繁转换若是通过附注或增译来提醒读者,就难免厚译,打断小说的阅读连贯性。像这种情况,AnneWedell-Wedellsborg与AndrewJones都认为译者利用时态对照有效地保证了翻译效果。[11](P129-143)[12](P570-602)针对这两种语言情况的翻译策略或许不再新鲜,但是关于在怎样的情况下如何合理使用,L1译者多能以译语读者的文化感知和语言直觉来确定答案。
真的译作读起来是没有翻译腔的。[13](P105)L2译者对于原作的特殊语义、文化所指甚至历史背景都要胜于L1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语言解码较之L1译者有相当优势。L1译者的优势就在于他们对译语语言的熟悉程度及对译语读者阅读心理的揣度,使译作更能达到读者的心理界位,符合他们的传统化期待。由于语言文化的优势,相对于L2译者,L1译者能更好地考虑到读者哪里可能产生阅读麻烦。而最好的翻译途径应为“L1+L2”模式,从最大层面消除顾虑,保证译本质量。以上这些文本翻译细节极为琐碎,但正是这些琐碎的细节构架了翻译文本的合理性和可读性,完成译介工作在翻译场域需要的合法性程序,进而聚集译者场域的资本,形成来源于译者的软资本(文本翻译质量)和硬资本(各种社会位置关系),另加上前面所论及的影视场域、出版场域的资本,形成了对文学译介积极的推动力量。
(四)其他场域与余华小说译介之正当命名
余华小说在英语世界里的传播与加速传播,绝非是某个场域单独运作的结果,而是电影场域、出版场域、翻译场域、高校场域等多个场域之间独立形成的资本相互叠加、相互累积所形成的结果。从ToLive开始,余华英译小说的封底均会对其他作品进行告知推介,其中包括作者国籍、身份、成就与售价,以及对译作的故事梗概和文学性的正面评价。也是从这本小说开始,只要适逢译作出版,出版社均会安排余华在美国各大高校巡回演讲,并通过新闻发布会和签名售书等宣传策略有序地规划和策动阅读市场。整体来看,在场域有计划、有组织的运作下,余华小说已经进入了稳定的有计划的推介程序阶段。
另外一个重要场域就是网络。许钧、高方认为,普通读者即使不懂外文,也有权进行翻译批评,而文学翻译批评也应该重视网络资源,正视网络上普通读者的翻译批评,从而丰富翻译研究的内容和方法。[14](P216-220)我们以亚马逊网站读者的读后感,作为了解余华英译小说普通读者翻译批评的渠道。读者以网名发布读后感,网友们则通过点击“是”或“否”来表明读后感对了解译作有无帮助,实际上这是在排除信息泡沫。这些策略,有三个好处:第一,不再囿限于专业批评,普通读者的观点让翻译认识更加接近大众认知;第二,百花齐放的批评观点为全面的翻译考察提供了可信度;第三,译本读后感的被判断体现了读后感的信息强度。表1是亚马逊网站读者关于余华小说英译本阅读感受的一个简单统计。

表1 亚马逊网站读者关于余华小说英译本阅读感受
资料来源:本表根据2010-2014年亚马逊网站数据统计出来,且在2015年底重新更新。
在余华多部英译小说中,最受人欢迎的还是《活着》,其英译本在亚马逊网站拥有的读后感最多。多个译语读者均认为一流的翻译水准可让译本永垂青史。而关于《许三观卖血记》与《兄弟》英译本的看法则有分歧。多个译语读者认为《许三观卖血记》角色的语言重复,缺乏情感,句号过多,标点符号不够多样化,语言过于活跃和断裂,以至于阅读的时候难以和人物角色联系起来。《兄弟》的英译比较普遍的阅读感受是译作冗长反复。读者C.Finn认为假如1962年诺贝尔文学得主JohnSteinbeck是一位中国作家,那么他也会这么写。读者SethT.Halne认为,译本中的阅读麻烦都是因为原作风格制约了译作的活动范围。对此,Row亦有同感,认为 “余华语言十分直白和生动,要找到恰当的英语对应并不容易”。[15](P3-5)
可见,译者必须充分理解作者意图,深入考虑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体会,对翻译样章精益求精。一本翻译潦草的著作即使最终得以出版,它的生命也不会长久,甚至会累及其他文学作品的翻译命运。在从原语文学到目的语文学的文化传送链条上,最末端是译作读者,忽略他们的阅读感受和心理感受,是舍大求小。余华英译小说的读者反馈说明了L1译者的工作得到了大面积地肯定,而肯定的弦外之音则是,在未来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的问题上,场域运作既要关心异域文化的专业读者,也要关心业余读者。
事实上,《兄弟》英译本尚未面世,就被定格为或能成为第一本成功引进的中国文学小说;[16]读者KathrynShimmura虽对译作有诸多批评,但最终还是认为该书“值得一读”。这些异域读者一边抱怨,一边逼着自己读完译作。最耐人寻味的是读者ChristopherBarrett,怀着对余华新作的无限信任,将译作读完却很失望,迅即将批评之剑指向翻译。另一方面,从译介线路来看,余华译介首先是2003年8月发行出售ToLive;同年10月出版ChronicleofaBloodMerchant;2007年,才正式出版余华早期作品的译本CriesintheDrizzle。很明显,译作出版的时间顺序并不是按照原作出版的时间顺序而来。
这些零碎的社会文化和翻译现象实际上都是受诱于余华之正名。在异域文化视野中他已经被正当命名为一种符号,一种可以了解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必须选择,这也就意味着余华自身已被正名,而这个正当命名的形成与固定都滥觞于ToLive。《活着》的英译及其顺利传播为其在异域文化立下了一个标范和标高,而一切后续追读和追译都是为了继续追踪《活着》英译本所留下的正名印象。
可以说,余华在异域文化中,已经从文化盲区进入了文化可视区,从文学边缘进入了文学中心,并且获得自身的合法性,被正当命名的不再仅限于译作ToLive,而是余华本人。所以其本人的作品能被异域文化所正当命名,皆因来自余华之正当命名。所以,历史性地看,ToLive是余华英译小说场域运作的真正启动点和关键点,它标志着余华小说译介进入了程序化式的翻译阶段,正式开启了余华作品英译旅行的历时传播。
三、结 语
通过描摹余华小说英译情况,我们发现,就文本翻译工作来看,由于作家代表作品通常具有长久不衰的文学魅力,其成功译介意义因此更加深远。余华小说场域译介说明了中国文学的译介必须兼顾其文本性和社会性。在影视场域、出版场域、译者场域和其他场域的相互交叉影响的结果之下,《活着》译作获得良好反映,其小说译本多次获奖与其文学传播及接受形成网状的、双向的、连锁的场域运作反应,从而构成了翻译工作社会性与文学性唇齿相依的生动画面。以此来看,后来者应多多借鉴余华小说译介所反映的场域运作模式,其中甚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场域译介中的正当命名不能失误。
要承认的是,我们很难指望异域读者“广种薄收”地、一本一本地去了解翻译文学,这不单单是弱势文学进入强势文学的普遍情况,对于强势文学进入弱势文学也是一样。某个作家或者某类文学作品的第一部代表译本一旦在译本读者那里出现接受无效、传播失败的态势,就很容易形成对原语文学的偏见,其他力量也就很难再扭转乾坤地突破这些已形成的固有偏见和认识。所以,翻译文本的正当命名尤其重要,它关系的不再只是自身在异域文化中的旅行,更是后续译作的敲门砖、试金石。而一旦成功则可以启动对某一类型或者某一作家的其他作品的翻译兴趣,这对弱势文化而言,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1]刘拥华.布迪厄的终生问题[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2]李可.先锋派小说英译管窥——以余华作品为例[J].当代外语研究,2013(4).
[3]缪佳,邵斌.基于语料库的英语译文语言特征与翻译共性研究——以余华小说《兄弟》英译本为个案研究[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4(1).
[4]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5]洪治纲.余华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6]Standaert,Michael.InterviewwithYuHua[M].Columbus:TheOhioStateUniversityMCLCResourceCenter,2004.
[7]高方,余华.“尊重原著应该是翻译的底线”——作家余华访谈录[J].中国翻译,2014(3).
[8]胡安江. 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M].中国翻译,2010 (6).
[9]Barr,AllanH.CriesintheDrizzle[M].NewYork:AnchorBooks,2007.
[10]黄素莊. 余华短篇小说研究[M].香港:香港大学图书馆,2008.
[11]Wedell-Wedellsborg,Anne.OnekindofChineseReality:ReadingYuHua[M].Chinese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1996(6).
[12]Jones,AndrewF.TheViolenceoftheText:ReadingYuHuaandShiZhicun[M].DukeUniversityPress,1994
[13]Newmark,Peter.TranslationandMis-translation:TheReview,theRevision,andtheAppraisalofaTranslationAboutTranslation[M].Shanghai;Forei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Press,2006.
[14]许钧, 高方. 网络与文学翻译批评[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6 (3).
[15]Row,Jess.SundayBookReview:ChineseIdol[EB/OL].http:www.nytimescom/2009/01/25/magazine/25huathml.
[16]Mishra,Pankaj.TheBonfireofChina’sVanities[EB/OL].http:www.nytimescom/2009/03/08/books/review/Row-thtml.
[责任编辑 陈义报]
Name Officialization: A Study of Field Manipulation in Yu Hua Novels Translation
GONG Yanping
(Jiyang College, Zhejiang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Zhuji 311800, China)
Field Theory regards that various dependent but inter-influential societies are the prototypes of fields, in which the actors possess their respective capitals and responding positions, and moreover, the already-owned ones also are helpful to involve more and better positions and capitals for the original owners. This essay endeavors to analyze Yuhua’s fiction translation on the basis of Field Theory from film field, press field, translation field as well as other fields, and it points out the translation is the process of name offcialization for the author, and these findings might contribute to the transl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YU Hua; name offcialization; field; translation

2016-10-16
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场域赋形:浙江籍作家余华小说译介研究”(Y201432532)研究成果。作者简介:龚艳萍,讲师,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I
A
1009-1734(2016)11-006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