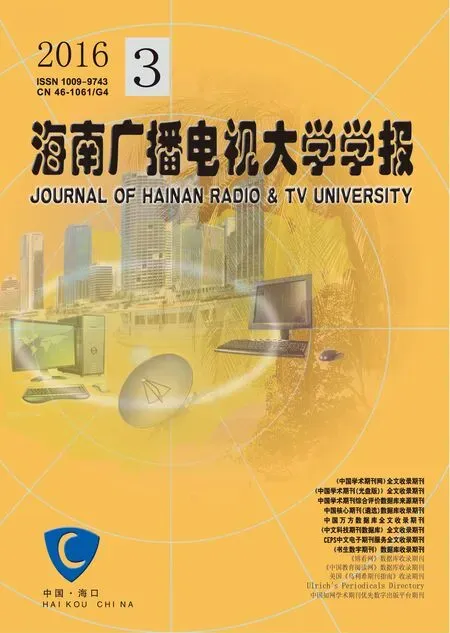传统的承继与再造:大姚彝族“插花节”仪式乐舞活动的当代建构
王敏玲
(云南艺术学院 舞蹈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传统的承继与再造:大姚彝族“插花节”仪式乐舞活动的当代建构
王敏玲
(云南艺术学院 舞蹈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插花节”是大姚县昙华乡彝族人民盛大传统节日, 其仪式乐舞活动的当代建构,是传统的继承与再造,保持了“插花节”仪式乐舞活动具有连续性与世俗性二元特点;赋予了传统乐舞节日宗教、政治、文化等多重意义,使传统乐舞活动保持生机与活力,也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地方性知识与民间智慧,笔者认为传统与当代并不存在根本的破裂而相互对立,应是在传统意义上重新建构的。
插花节;传统;再造;仪式乐舞;当代建构
“插花节”是大姚县昙华乡彝族人民的盛大传统节日,当地人又称彝年,每年农历二月初八在昙华山的千栢林中举行,已被列为世界一百个著名的民族传统节日之一,2009年被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有关“插花节”的研究多见于民俗文化类、地方风俗志、调查报告等著论,且只做了相关介绍性场景描述,对于其重要的仪式乐舞缺乏深入理论研究。在许多人类学家眼里,仪式有着特殊魅力,但是仪式中的舞蹈(或人体运动)却并未成为关注焦点[1]。关于“插花节”仪式乐舞的历史记忆不仅是强化族群自我认同力量,同时也是区分、标识族群之间和表达其族群认同的特殊“历史叙事”方式和媒介[2]。当代“插花节”仪式乐舞活动具有一定开放性公共文化空间,在传统意义基础上它又是如何进行重新建构呢?通过两次实地田野调查,以大姚县彝族“插花节”仪式乐舞活动为例,尝试对所提出问题作出回答。
一、基于集体记忆的“插花节”传统乐舞活动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对于印度尼西亚的研究使人们真切地认识到并相信“民族(nation)”事实上是“想象的共同体”。也恰恰是在这种想象中,“民族”得到了一种原生性解释,使人们获得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自己所认同的这个共同体是从来就存在的,甚至有着神圣的、不可质询的起源。族群对于共同的历史记忆在情感上得到认同,过去的历史在回忆中变成叙事,添加了想象,附加了意义,而最终成为了当代事件一部分[3]。对于昙华的彝族而言,插花节传统乐舞活动源于这个特定区域内的悲美传说。
富于幻想和智慧的彝族人民编织了许多解释和说明各种风尚习俗由来的传说,在昙华彝族地区,插花节就源于当地马缨花和咪依噜的传说故事。当早期的先民对大自然现象的认识能力较低,而又无法驾驭它时就只有求助于自身之外某种神秘力量作为驾驭的凭借与根据,于是人们将马缨花人格化、神化。英雄崇拜阶段是早期人类意识形态和思维能力发展颇显进步时期,能与当时阶级社会彝族人们生活现实结合,反应出社会历史发展。人们创造了具有民族地域特征的《咪依噜的传说》,将“咪依噜”拟化为正义化身,象征着幸福与吉祥。
“集体记忆”即是一个具有自己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自己过去的记忆。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2002)超越了生物学视角,把“集体记忆”理解为可以遗传的或“种族的”记忆,使关于记忆的研究从生物学框架转向文化框架[4]。从《马缨花的来历》到《咪依噜的传说》,族群在 “种族的”记忆中选择将花与人联系在一起,马缨花就是咪依噜的化身,咪依噜则是马缨花的彝语名字。因为它可以为彝家人带来幸福,族群便选择以节日方式,载歌载舞对它予以回报。基于“集体记忆”的传统仪式乐舞活动也通过“插花节”而得以塑造和延续。
二、当代“插花节”仪式乐舞活动行为实践
族群通过仪式、身体实践、地方与物体等记忆场所,作为表现形式或者传承载体。仪式的不断重复特征使得信息得以通过文化成员传达出来。彝族“插花节”乐舞的历史在记忆和回忆中变成了叙事,通过族群认同与选择,根据特定社会条件和需要进行诠释和重构。
(一)迎宾仪式

迎宾是插花节展现在社会舞台上的特定仪式。好客的彝家人通过自己方式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农历二月初八早上,在昙华松子园村新建的寨门前面,穿着鲜艳彝族服饰的彝家人热情地排成一排,两边各有两个吹着山号和唢呐的。彝族小伙和姑娘手里端着酒杯和酒,凡是客人通过,必须喝下这杯彝家栏门酒,彝家人都通过这样传统方式欢迎远方的客人。
(二)祭祀花神仪式表演

千柏林*千栢林是“插花节”的节日圣地,过去林中曾立有石佛像,也曾是建庙宇、开展祭祀活动的场所,为世人修身之境、快乐之地,也 称千佛林。作为节日盛典的固定圣地,标志了这一彝族传统文化符号在空间上的延伸。中午时分,四邻八寨的乡民聚集在千柏林,8名身披羊皮褂的彝家汉子再次吹响震山号,预示神秘的祭祀活动开始了。来自丫古埂村的老毕摩*毕摩在昙华民众的宗教信仰中是一个神圣的角色。在彝族社会中,他是人与神之间沟通的桥梁。毕摩是彝族社会中的巫祭,又是民间的知识分子;李学品*昙华彝族老毕魔,会用彝语唱诵《祭祀马缨花神调》、《驱鬼调》、《插花经》、《梅葛调》等。头戴神帽、身穿神衣、左手拿着神铃、右手拿着鹰爪,缓缓走出事先搭好的祭坛。紧随其后的是两名陪祭男子,其中一人也戴着神帽,用手抱着一只公鸡;另外一人端着碗,边走边把碗里的米撒向各方。用作祭祀仪式的祭台,由神树(用松枝做祭祀的神树,取其一年四季常绿的象征意义)和祭祀礼物(公鸡、香、五谷杂粮、酒、肉等)组成。神树前面还插满了树杈,据毕摩说这代表着不同的神。一切准备好以后,祭祀仪式正式开始,首先是祭祀马缨花神,彝族认为所要祭祀的马缨花神就存在于神树之上,毕摩手持松枝、神杖、鹰爪、神铃走到神树旁边进行卜卦,并把祭祀礼物献给马缨花神;祭祀完马缨花神后,毕摩便从陪祭手中拿过篮子,把篮子中用马缨花覆盖着的五谷杂粮洒在神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祈求马缨花神赐福于彝族群众,来年谷物有好收成;彝族认为祭献的鸡血具有神圣力量,因此,毕摩要杀鸡祭献花神和众神,并且唱诵彝族梅葛经文,通戒鬼怪不要伤害动植物和人类;最后便是选花仙子,彝族认为花仙子是美丽勇敢的咪依噜化身,她能给人们带来幸福和吉祥,是被毕摩通过特定的宗教仪式挑选而出,具有神圣性。
从某种意义上讲,仪式中的人体运动和舞蹈界限并不能明确划分。特纳将仪式定义为“适合于神秘物质或力量相关的信仰的特殊场合,不运用技术程序的规定性正式行为”。昙华乡彝族通过这种仪式中身体实践行为,维持族群认同为再生产社会秩序提供了媒介,通过仪式表演更好调节了相互之间关系,巩固和维系甚至促进了整体团结[5]。
(三) 当代“插花节”乐舞展演
当代“插花节”乐舞展演是一种对社会事实的呈现,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包含了传统仪式,它通过呈现来体现社会秩序,正是展演唤起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仪式与展演(Performance)也不同,前者以“转化”为主要特征,后者以“展现”为主要特征,从仪式到展演的演变中我们也看到了人类社会变迁。在当代多方力量(政府、市场、传统)博弈下,传统乐舞文化有着自己的走向和文化再生产行为逻辑及动力机制*图片由大姚县文化馆唐文老师提供。。

插花节祭花神仪式完成之后,便是乡政府组织的各种文艺表演与体育活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彝族集体舞蹈“跌脚”,*“跌脚”又称跳脚或称之为打跳,是插花节最具规模的乐舞表演形式。插花节中的打跳从二月初八晚一直持续到二月初十中午。成百上千的彝家人围成圆圈扣臂而舞蹈,月琴叮咚、笛声悠扬、舞步震耳,从中可以看出各个舞圈的乐曲、舞步、歌调特色。“打跳”有固定程式、套路、动作、曲调、节奏,现在昙华常跳的有四步翻、三跺脚等,在看似单调雷同、重复的舞蹈动律、节奏中,规范整合了彝族宗教信仰、神灵观念、伦理道德、审美情趣。“打跳”是早期插花节活动方式,仪式中的舞蹈具有神圣性与娱乐性相融、敬神与娱人并重特点。
当代“插花节”乐舞展演赋予了更多现实社会意义。由于社会变迁影响,村民生活有较大改变,传统乐舞文化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也有所变化,但事实上,传统乐舞文化仍然在不断转换形式过程中按照自身逻辑继承着传统。古老的宗教信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习俗,依旧在支撑着乡村社会秩序。
三、彝族"插花节"乐舞活动当代建构方式
“传统是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是人类过去所创造的种种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构成的表意象征;它使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6]当代“插花节”中依然延续着传统乐舞文化、原始宗教、文化习俗等,这些节日传统是彝族历经数百年历史传承至今的文化模式,对它的继承,使彝族“插花节”神圣与世俗交融的特点得以保持。而当代“插花节”乐舞展演的多重意义交织,又使得“插花节”乐舞活动得以重新建构,表现出空间开放与融合世俗性发展趋向。
(一)对“插花节”传统乐舞活动事项的继承
乐舞具有一定“文化依附性”,它们更多的是和宗教、民俗等文化事项具有内在关联的文化行为。彝族信仰原始宗教,相信“万物有灵论”,认为自然之间有着内在联系。直到现在原始宗教文化模式依然根植于族群内心,每年的农历二月初八都会在固定时间地点举行“插花节”祭祀仪式。

在祭祀花神仪式表演中有专门的服饰和法器。从功能上看这些法器主要有四点:第一,与神取得联系功能(如铃铛);第二,探知神意功能(如卦具);第三,震慑鬼妖功能(如鹰爪);第四,沟通天地功能(主要指鹰、麂子、野猪等动物法器)。毕魔李学品所使用的法器,是集中反映了当地彝族原始宗教信仰的重要物件。当代“插花节”仪式表演继承了这些宗教传统事项,保证了宗教仪式表演的节日属性与宗教文化教育。
“传统的各种功能的核心指向,就是保证整个社会生活转型过程的连续性”[7]因为族群有着共同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人们通过他们所共同具有的文化(观念和准则)而得以维系”。当代“插花节”仪式乐舞表演是凝聚、保存、展示和传承文化重要途径,继承和实现了地理空间内部整合的节日传统功能。
(二)对“插花节”传统乐舞活动的再造
新文化或者新传统建构与再造,是指与传统乐舞相关联的新文化可以被选择、吸纳、嵌入传统文化体系内。当代“插花节”乐舞活动不只是传统意义上欢歌打跳,而是已经延伸到了广阔社会生活领域,进行了新文化的重新建构。如为庆祝这一盛大传统节日,昙华乡政府每年都邀请省内有一定影响力的歌手、艺术表演团体进行歌舞表演;除了彝族左脚调子,还有流行歌曲、电影以及政府专门组织的或者自发组织的各种群众性体育活动;除各种内容丰富多彩的活动外,插花节还是一个大型商品交流会,现代商品逐渐挤进传统商品市场。跳脚场上也不再只是昙华彝家人,而更多的是四邻八寨和各地纷至沓来的游客。

昙华彝族“插花节”乐舞活动是昙华彝族传统文化活动源远流长的桥梁,展示了昙华彝族生活方方面面,集中反映彝族人民千百年来在宗教、哲学、社会及习俗等方面所形成的传统。当代“插花节”乐舞活动新文化的再造使昙华彝族“插花节”逐渐演化为以祭祀表演和娱乐商贸为主的节日,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实现了从单元到多元的转型*参见:《大姚彝族插花节调查报告》。
结 语
大姚彝族“插花节”仪式乐舞活动的当代建构,是对传统的继承与再造,保持了插花节仪式乐舞活动具有连续性与世俗性的二元特点;通过对传统乐舞活动新文化建构,强化了节日传统,丰富了乐舞活动内容,使插花节乐舞活动保持生机与活力,也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地方性知识和民间智慧。笔者认为在传统乐舞当代建构中,或许会出现一定程度断裂现象,但他们之间不存在更本的破裂而相互对立,是在传统意义基础上重新生产与再造的。
[1] 车延芬.书写、结构与仪式——舞蹈的人类学解读[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2(4).
[2] 王灿,李技文.近十年我国族群认同与历史记忆研究综述[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3).
[3] 马成俊.基于历史记忆的文化生产与族群建构[J].青海民族研究,2008(1).
[4] 李佳.乡土社会变局与乡村文化再生产[J].中国农村观察,2012(4).
[5] 王建明.艺术人类学新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6] 桂荣.传统的继承与重构:巍山回族圣纪节的当代变迁[J].民族研究,2012(2).
[7] 陈庆德.人类学的理论预设与建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赵峰)
Tradition Inheritance and Rebuilding: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Music and Dance of Yi People's Flower Arrangement Festival in Dayao County
WANG Min-ling
(Dancing college Yunnan Arts University,Kunming 650500,China)
The flower arrangement festival is a grand day to the Yi nationality distributed in Dayao County. Its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ceremony music and dance is inheritance and rebuilding of tradition, which remains the secularity and continuity and gives the traditional music-dance festival multiple meanings in religion, politics and culture. The contemporary structure not only makes the traditional music-dance maintain vitality but also shows us local knowledge and wisdom. As a conclusion, the tradition and contemporary is not contradiction but rebuilding of ceremony music and dance.
flower arrangement festival; tradition; Rebuilding; ceremony music and dance;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2016-05-25 作者简介:王敏玲,女,汉族,云南昆明人。云南艺术学院舞蹈学院2014级在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舞蹈文化研究。
J722.2;K892.1
A
1009-9743(2016)03-0030-05
10.13803/j.cnki.issn1009-9743.2016.03.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