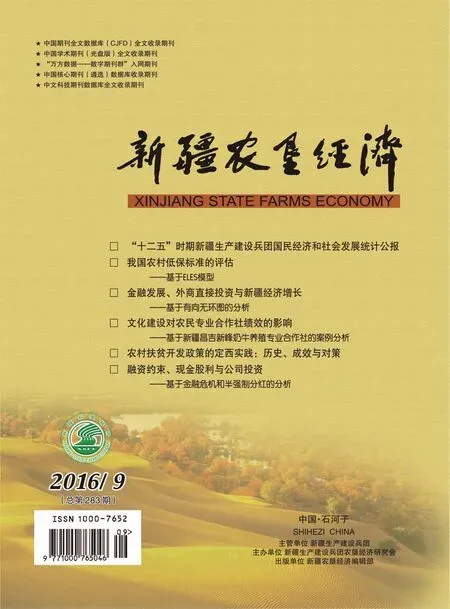我国农村低保标准的评估——基于ELES模型
王 倩 毕红霞
(山东省农业大学经管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
我国农村低保标准的评估——基于ELES模型
王倩毕红霞
(山东省农业大学经管学院,山东泰安271018)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最后一道安全网”,意在为贫困人口解决基本生活需要的问题。文章借助ELES模型测算出我国农村低保标准的三层次理论值,通过比较分析,得出我国现行的农村低保水平偏低,现行低保标准明显不能满足贫困人群的基本需求,而ELES模型测算的基本型保障标准却可以满足“保基本”的原则。基于这一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确保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合理制定,实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ELES模型;保障标准
一、引言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政府对农村贫困人口按当地最低生活标准进行差额救助的新型生活救助制度[1],是我国社会救助体系的基础。2007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国发[2007]19号)(以下简称《通知》),这标志着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我国全面实施(以下简称“农村低保”)。截至2014年底,我国农村共有2943.6万户、5207.2万人享受到低保。2014年,我国农村低保平均标准2777元/人/年,比2013年提高343元,增长14.1%;农村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129元,比2013年增长11.4%;各级财政共支出农村低保资金870.3亿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582.6亿元,占总支出的66.9%。该项制度在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保障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国的农村低保是以“保基本”为主要目标的,保障标准与保障功能仍然欠低,本文基于需求层次理论通过用ELES模型测算出三层次低保标准,对低保制度中最为重要的标准与水平进行评估,并分析其保障效果,对科学制定农村低保政策提供有针对性建议。
二、我国农村低保的发展现状
(一)农村低保标准及其覆盖率分析
农村低保标准及其覆盖率是衡量农村低保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近年来,我国农村低保制度得到了不断完善和发展(详见表1),具体来看:

表12007 -2014我国农村低保标准及其覆盖率
1.农村低保标准持续升高。2014年我国农村低保标准为每人2777元/年,相比于2007年的每人840元/年增长了230.60%。总体来看,农村低保标准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八年间,农村低保标准的绝对额平均每年增长276.71元,而农村低保的相对额即低保标准的年增长率均在12%-18%范围内波动,平均涨幅为15.65%。
2.农村低保人数呈递增趋势。自2007年国务院颁布了《通知》后,我国农村低保制度全面建立,农村低保人数为3566.3万人,约是2006年(1593.1万人)的2.3倍。在2014年,低保人数有所下降,这是由于我国低保制度逐渐完善的结果,一方面帮助贫困人群增加收入,逐步脱离低保群体;另一方面低保申请程序更加严谨,取消了一些“人情保”“关系保”等。
3.农村低保覆盖率逐年提高并趋于平稳。农村低保覆盖率是由农村低保人数与农村人口两个指标相比计算得出。该指标可以用来反映农村救助水平的保障程度,数值越大,说明应保尽保的程度越好。2007-2011年,该数值增长较快,自2011年以后,趋于平稳发展。2013年农村低保覆盖率达到最大,为8.56%,接近2007年4.99%的2倍。
(二)农村低保财政支持能力分析
弗雷德里克和亚历杭德罗[2]提到:“帮助穷人的办法取决于国内资源有多少可供使用,也取决于是否存在相应的政治意志把资源用来缓解贫困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对于低保标准的设定应当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以及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标准过低则不能满足低保对象生活的最低需求,使其陷入贫困或被社会排斥;标准过高则会产生“福利依赖”或“养懒汉”的现象[3],甚至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

图1 农村低保标准增长率和GDP增长率
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农村低保标准的增长率与GDP的增长率均呈动态变化,2011年以前,二者呈反向变动趋势;在2011年,二者的增长率相同,随后,二者的变动趋势趋于一致,但是农村低保标准的增长率始终高于GDP的增长率。
由表2中可以看出,一方面中央对农村低保补助数额占农村低保支出总额的比率较高,2011年最高为75.27%,其余年份均在60%~75%之间。2013年中央政府的补助额为612.3亿元,是2009年的2.4倍。这说明我国农村低保支出主要依靠中央政府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农村低保支出和财政总支出均处于逐步增长的趋势,从低保支出的年增长率可以看出,2008年的增长速度最快,高达109.62%;2009年、2010年、2011年和2013年的增长速度分别为58.72%、22.59%、50.04%和20.74%;而2012年和2014年这两年的低保支出变化幅度相对较小。低保支出从2007年到2014年增加了761.2亿元,增长率为697.71%。低保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值呈动态增长的趋势,2013年农村低保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值达到最高的0.62%,约是2007年0.22%的三倍。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政府一直在加大对农村低保的资金投入。

表2 农村低保财政支出情况单位:亿元,%
三、基于ELES模型我国农村低保标准的理论测算
本文将采用扩展线支出系统模型(ELES)法计算我国农村居民低保标准。一方面ELES模型是针对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来进行计算,符合我国把收入增加作为调控主关注点的方向。另一方面通过ELES模型对现有的数据进行精确地计算,减少了人为主观因素的干扰,这样得出的低保线更准确。
(一)模型的构建
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xten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ELES)是美国经济学家C.Liuch于1973年在线性支出模型的基础上建立的一个应用十分广泛的需求函数模型[4]。该模型有三个基本假设:一是在某一时期人们对各种商品或服务的需求数量取决于人们的收入以及各种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二是人们对各种商品或服务的需求分为基本需求和非基本需求两部分,并且基本需求与其收入水平无关。三是在既定的收入下,只有满足了基本需求才会将剩余的收入按照一定的边际消费倾向分配给非基本需求。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人而言,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基本需求是相同的。因此,本文将借用ELES模型测算人们的基本需求消费所需要的货币,并将此作为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线。ELES模型的函数形式表示为:


式(1)中,Ei表示第i种商品或服务的消费支出;Pi、Pj分别为第i、j种商品或服务的价格;Qi代表第i种商品或服务的需求量;Ri、Rj分别表示对第i、j种商品或服务的需求量;I表示农村居民的纯收入;βi表示第i类消费商品或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
对(1)式变形得:

将(3)式代入(2)式,得:

其中,ui为随机项。对于每一种具体的消费品,根据消费支出额(Ei)和农村居民纯收入(I)的数据,运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αi和βi,然后对(3)式等号两边进行求和,得到:

由于最低生活保障是面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生活救助制度,意在解决保障对象的基本生活问题,即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令维持人们基本生活所需的n中商品和服务的货币总支出:

由(5)式变形可得出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模型为:

(二)相关参数的计算
通过上面对ELES模型的理论分析可知,计算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涉及两个变量,分别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生活消费支出又细分为食品、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八项指标。农村居民按不同的收入水平分为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收入户和高收入户五个层次。本文将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农村居民分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数据,依据(4)式,运用SPSS16.0分别用八大类消费支出对不同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组数据求一元线性回归,相关参数估计值和回归方程的判定系数R2如表3所示。
系数R2可用来检验模型的拟合度,R2越接近1,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越好。从表3可以看出,R2的值均在0.950以上,表明该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多数常数项αi和回归系数βi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此,通过该模型计算出来的回归方程的可信度及有效度都较高。

表3 2011-2013年我国农村居民ELES模型的参数估计①
(三)农村低保标准线的测算
根据2014年《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相关内容,参照柳清瑞和翁钱威[5]的研究,本文将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生存型低保标准,包括食品、衣着和居住三项基本的生活消费支出。第二层是基本型低保标准,在第一层的基础上增加了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两项生活消费支出。第三层是发展型低保标准,在第二层的基础上增加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和其他用品及服务三项生活消费支出。根据公式(5)可以求出我国农村低保三个层次的具体标准(见表4)。

表4 三层次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理论值单位:元/年

表5 我国农村低保标准实际值及占理论值的比重单位:元/年,%
由表4和表5可以看出,利用ELES模型测算出2011-2013年的生存型低保标准分别是2258.63元/年、2539.24元/年、2833.98元/年;基本型低保标准分别是3005.93元/年、3420.11元/年、3817.99元/年;发展型低保标准分别是3978.21元/年、4505.90元/年、5216.68元/年。而现实中,2011年、2012年和2013年我国农村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1718.04元/年、2067.83元/年、2433.91元/年。以上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地区现行的低保标准普遍偏低,没有完全保障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更没有完全实现农村低保制度的效力。在2011-2013年,农村居民现行低保标准占比生存型低保标准的比重分别是76.07%、81.46%和85.88%,在数值上虽呈递增趋势,但始终低于ELES模型所计算出的生存型低保标准。从实际的救助效力来看,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在纳入低保人群接受政府救助以后,仅仅是能够维持最基本的吃穿住生存需求,其在医疗保健、教育娱乐等方面的需求很难得到满足,更谈不上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
四、农村低保救助水平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农村低保的救助水平,本文引入人均食品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总支出三个指标,对现行低保标准和ELES测算基本低保标准做对比分析。
(一)与人均食品消费支出比值的比较
由6可知,2011-2014年农村现行低保标准与人均食品消费支出的比值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但均未大于1。2014年这一比值高达98.67%,数值很接近1。这表明,我国政府正在加大对农村贫困人口的财政投入,在应保尽保的基础上提高保障水平。对比ELES测算的基本型低保标准与人均食品支出的比值,均大于1且在150%左右。由此可以说明目前我国执行的农村低保标准还不能达到满足农村居民的生理需求的最低费用,这和表5中的结果相一致,即我国农村现行的低保标准还未达到维持生存的标准。
(二)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的比较
197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了一个动态的贫困标准: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的中等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60%作为最低生活标准[6]。根据该标准的最低值50%计算的话,2011-2014年我国农村低保标准分别应该是3488.65元/年、3958.3元/年、4714.8元/年和5244.45元/年,远远高于我国农村现行的低保标准和ELES模型测算的基本型低保标准,但是ELES模型测算发展型低保标准达到这一保障水平。由此证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的动态标准线不适用于我国农村低保标准的确定。而郑功成[7]教授鉴于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处于发展中这一基本国情提出了将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50%作为我国城乡贫困线。然而,2011-2014年我国农村居民现行低保标准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分别为24.62%、26.12%、25.81%和26.47%,也未达到上述的比例范围的下限,这表明我国农村低保的救助水平偏低,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也存在一定的差距。
(三)与人均消费总支出比值的比较
2007年国务院发布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目标是稳定、持久、有效地解决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而农村低保标准占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总支出比值正是反映农村居民基本生活消费情况,这一比值的大小代表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好坏[3]。参考民政部对基本服务标准的规定,低保标准不能低于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35%。由表6可知,只有2012年达到了民政部规定的标准,其余年份均低于这一标准值。近年,这一比值呈动态变化且均稳定在32%~35%之间。对比ELES模型测算的基本型低保标准与人均消费支出的比值均高于35%且超过了50%。
通过以上分析,我国农村低保标准的确定均未达到保障基本生活的需求。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农村低保标准的确定不能只考虑贫困人口的生存需求,还应当考虑健康需求,防止“贫困陷阱”的发生。而通过ELES模型测算出来的基本型低保标准则是将农村居民的吃饭、穿衣,还包括日常的用水、用电以及医疗保健都考虑在内,所以说,它更适合作为我国农村低保标准。

表6 2011-2014农村低保线、测算线及相关数据单位:元/年,%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通过前文分析可知,我国农村地区的低保水平整体偏低,且未达到ELES模型测算的生存型低保标准,农村低保为贫困人群提供的保障水平无法满足他们的日常基本生活需求。而ELES模型测算出的基本型低保标准更适合作为我国农村低保标准。根据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定义可知,政府负责低保制度的制定、对低保申请者的资格认定、低保救助标准的设置、救助资金的筹措等各个环节,是农村低保制度的重要决策者。
(二)政策建议
1.转变救助理念,逐步提高低保水平。根据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相关政策可知,我国目前的农村低保救助理念是“保基本”,主要是保障贫困人口的生存需求,更准确地说是只能满足温饱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应当转变救助理念,充分考虑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和发展需求。同时,基于救助刚性和救助依赖的因素,在确定低保标准时,应当在科学测算的基础上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正如以需求层理理论为指导,ELES模型所测算的三层次低保标准,以生存型低保标准为基础,逐步过渡到基本型低保标准,最终提高到发展型低保标准。不断扩大农村低保的覆盖面,在应保尽保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低保水平。
2.明晰政府职能,增加财政投入力度。和其他社会保障项目不同,我国农村低保的救助资金一般来自政府税收。目前,我国农村低保资金的筹措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负担。如何分配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低保的财政支出和收入的权利关系到农村低保实际运行成效。在农村低保的实践中,中央政府的财政投入状况决定了低保制度的前进步伐。近几年,农村低保的发展离不开中央政府大量的资金支持。但从长远来看,这将会增加中央政府的负担,不利于农村低保制度的发展。因此,应当明晰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的职能,各地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的经济水平适当增加对农村低保的财政投入,中央政府需作宏观调控,为财政状况较差的省份提供补助,实现地区间的平衡,改善农村低保标准偏低这一现状。
3.重视民间组织,补充低保救助资源。农村低保制度的良好运行依靠强大的资金支持。但政府的资金投入是有限的,应当设法扩大低保物资的筹资渠道。民间组织的兴起,为我国农村低保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政府应当给予充分的重视。在具体方法上政府可以采取减税、奖励等政策鼓励我国的优良企业和知名人士积极投身于慈善事业,为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定期捐赠物资。各类民间组织在农村低保事业中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既可以弥补政府资金投入的不足,也能够满足农村低保人群的多层次需求。
4.加强低保立法,完善社会监督机制。任何一项制度能够有效实施必须有相关的法律作为基础。根据有关农村低保的相关政策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出现的“人情保”“关系保”等现象以及低保政策的违规操作者做出严厉的处置,使农村低保事业发展有法可依。同时,农村低保工作的顺利开展也离不开完善的社会监督体系。首先应当建立有关“低保”的投诉机构,如有对低保申请过程或结果不满的可以通过该渠道进行投诉;其次是发挥社会媒体的监督作用,使农村低保信息更加公开透明,农村低保制度能够更加公平公正。
[1]郭士征.社会保障学(第二版)[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257.
[2]弗雷德里克·C.特纳,亚历杭德罗.L.科尔巴乔,陈思.国家的新角色[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1,(1):111-122.
[3]毕红霞,薛兴利.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财政支持的适度性与政策优化[J].农业经济问题,2012,(1):29-36.
[4]江华,杨雪.农村低保线评估——基于需求层次与扩展线性支出法测算[J].人口与经济,2014,(1):116-123.
[5]柳清瑞,翁钱威.城镇低保线:实际给付与理论标准的差距与对策[J].人口与经济,2011,(4):78-79.
[6]许琳.社会保障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7]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理念、目标与行动方案[M].人民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管仲)
王倩(1989-),女,山东德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社会保障;毕红霞(1978-),女,山东文登人,管理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农村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