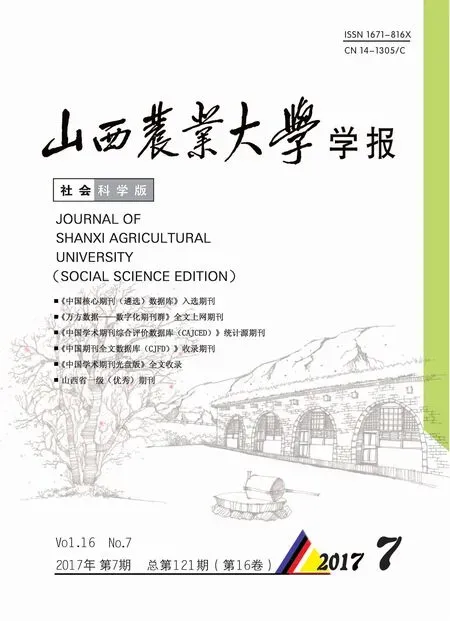论媒介化时代的社会风险与主体困境
冯月季(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论媒介化时代的社会风险与主体困境
冯月季
(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随着各种新媒介的兴起,人类已经进入了媒介化时代,大众媒介的发达给人类的社会生活带来了信息交流的便利,但是同样也带来了不确定性的社会风险。媒介泛滥和信息崇拜造成了主体困境,媒介化社会的主体被剥离了获得意义的文化根基,媒介化社会陷入了意义模糊的信息迷思与风险境地。
媒介;信息;主体;迷思;风险
一、媒介、信息与社会风险
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麦克卢汉提出了他著名的“媒介即讯息”的观点,麦克卢汉的意思是:“所谓媒介即是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物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1]。”
麦克卢汉在这里所用的“尺度”一词有些模糊不清,不过从他的表述来看,或许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文化或文明的“形态”或“范式”,麦克卢汉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媒介技术的变革对社会进步的影响,这也招致很多人把麦克卢汉当作技术决定论者。麦克卢汉并不排斥技术因素在人类文明变革中的作用,但实际上,麦克卢汉的本意则在于,他强调的是媒介形式对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并由此而产生的文化与社会变革。
也就是说,媒介的重要效果来自于它的形式,而非内容,一个人只有关注到媒介的形式能指所表征的信息所指时,才能成为一个冷静的媒介旁观者,而不是像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的内容就像破门而入的盗贼携带的一块多汁的肉,它的目的是分散看门狗的注意力[2]。”
但是,麦克卢汉在这里掺杂了他天马行空文学想象的成分,实际上,在大众媒介时代,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像麦克卢汉那样保持理性的观察力和抽象的思考力。在谈到关于媒介与人的认知平衡理论时,麦克卢汉自己也说:“数百年来,人类在这方面的失败具有典型的意义,这是完完全全的失败。对媒介影响潜意识的温顺的接受,使媒介成为囚禁其使用者的无墙的监狱[1]。”
或许是对大众的失望,麦克卢汉在他随后的一本书中即抛出了“媒介即按摩”(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的观点,顺便,又玩了一把文字游戏,把“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写成“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而把“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写成“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
我们看到,麦克卢汉关于媒介即“信息”、“按摩”、“混乱时代”、“大众时代”的这些隐喻并不完全是站在历史进步主义的立场上。麦克卢汉批评人们只看到了媒介技术延伸所带来的社会进步,却忽视了那些由此所带来的不在场的副作用,比如汽车在带给人们交通便利的同时,却往往忽视它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交通安全等潜在的风险。
于是,我们可以延伸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认为“信息即风险”。这样,在麦克卢汉与贝克之间就存在了某种交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的风险某种程度上指的是风险的媒介化。只不过,麦克卢汉的“信息即风险”指的是媒介形式,而贝克的“风险的媒介化”更多指向媒介的内容。但是两者并不冲突,媒介的形式与内容共同构成了大众媒介对社会发生影响的方式,同样,信息的形式风险与内容风险亦是互为表里。
在一个被大众媒介中介化的社会,无论何种形式的风险,都最终指向人们所掌握的知识对信息的认知。关于信息的定义,信息论奠基人香农认为信息是消除人们不确定性的东西。显然,信息指向人类的知识层面,但是香农的这个信息概念并不是没有问题。寻求确定性一直是人类的努力方向,这里的确定性指的是消除风险的确定知识,而知识来自于人类经验的累积。当人们试图通过获取信息来消除不确定性,并以此认为所获得的就是确定知识的时候,如杜威所指出的,人们恐怕把确定的知识和一个暂时确定的情境搞混了。杜威说:“经验不能为我们提供必然的真理,即完全通过理性来加以证明的真理。经验的结论是特殊的,而不是普遍的。由于他们不是‘精确的’,所以它们还不足以成为‘科学’[3]。”
因此信息作为知识,只能暂时消除人们所面对的不确定性,它仅仅是为人们营造了一个确定的情境而已,换言之,不确定性乃是人类社会文化的常态。这种不确定性和偶然性被现代社会的大众媒介以信息的形式告知受众,使得受众在享受科技和知识所带来的文明成果时,开始担忧其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风险。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主要特征在于风险的不确定性以及偶然性。并且社会风险来自于工业社会科技和知识的“副作用”(side effects),现代社会风险与前现代相比具有两个特征:不可控制性与全球化。前现代的社会风险是区域性的,并且是可以通过概率计算得出其结果,从而能够加以控制和处理;现代社会的风险本质上属于认知社会学家的范畴,是对未来社会后果的未知状态,因而无法预测和加以掌控。
继贝克之后,对“风险社会”理论阐述较为详尽的是德国社会学尼古拉斯·卢曼(Niklas Luhamann)以及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吉登斯作为继哈贝马斯之后最后一位现代论者,是从“知识技能”的角度来反思社会风险的。他将现代社会的风险看作是未来某个时刻与我们发生社会关系的事物被评价的危险程度,并将风险分为两种: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根据吉登斯的表述:“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我想把这种风险与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区分开来。所谓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于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4]。”
知识技能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如此往往会呈现出风险社会的“知识悖论”:一方面人们需要不断获得知识防范风险,另一方面风险也源自于知识。现代性维度下,举着理性旗帜的知识将传统和地方性知识冲击得七零八落,但是自身内部并未获得完整统一性,现代性知识以一种假说的形式得以存在,因为某种看似正确的主张或理论,在时间轴上不断被修正或阐释。
人们在使用知识技能的过程中,也会对其进行反思,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的知识属于社会制度的构成元素,它们掌握在各行各业的专家手中,因而形成了生产和制造各种知识的“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但是实际上由专家系统所得出的知识相当多的来自于实验室数据,它们无法囊括人类生活世界的全貌,并且在专家之间存在观点相左、意见不一的状况。如此就将现代性带进了一场史无前例地实验室运动中去,尽管充斥着刺鼻的福尔马林味道,但我们却无法用精确的参数固定未来,这使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暗含着这样或那样的社会风险。
德国社会学家卢曼也认为现代社会的风险具有不可预测性,对于风险的概念,他说:“风险这个概念常常被定义为‘预测’,并且仅仅是一个关于预测的问题,任何关于这个问题的小题大做都是不明确的。任何情况下关于风险的预测(预测错误也是一样),都不会像风险真正显现的那样如其所是[5]。”
卢曼是从社会系统的角度出发来考察现代社会风险的,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沟通会伴随着风险意识,卢曼称之为“风险沟通”。对于社会系统“风险沟通”的风险评估模式,卢曼主张抛弃过去的“风险/安全”模式,而代之以“风险/危险”模式。卢曼的风险社会理论与贝克有着明显的不同,贝克认为社会风险来自于后工业社会的科技知识所带来的副作用,卢曼则认为风险来自于个人决策行为。
对于卢曼来说,现代社会之所以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不是由于灾难或者危害本身的风险,是因为再也没有一个名之为命运或不幸的宽容外衣可以裹在危害的上面。对于决策者来说,可能面临不可预知的风险,对于不做决策而承受决策者的后果,则可能面临危险。
在贝克、吉登斯以及卢曼的风险社会理论中,尽管各自的出发点和关注视角不同,不过对于他们而言,提出风险社会的理论在于对当下现代性进行反思,贝克将以工业社会为代表的现代性称之为古典现代性,而自后工业社会以来的现代性则属于反思现代性。古典现代性是以传统作为变革的对象,而反思现代性则是以现代性本身作为变革的对象,正如贝克所言:这是现代性的自作自受。
发达现代性的社会风险所造成的伤害一般是不可见的,风险最初是作为与风险相关的知识而存在的,即知识操控着风险,并可以随意对之进行修剪。显然大众媒介作为当代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刊发的信息具有界定社会风险的权力,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从媒体的信息中对风险进行认知和评估,贝克指出:“知识在社会和经济上的重要性类似地增长着,随之而来的是控制媒体塑造知识(科学研究)和传播知识(大众媒体)的权力。在这种意义上,风险社会同时也是科学社会、媒体社会和信息社会[6]。”
二、媒介化社会的主体困境
自从人类进入大众媒介化社会后,就迎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信息大爆炸运动,有人做过统计:《纽约时报》平均一个工作日所包含的的信息量,比莎士比亚时代任何人一生所获得的信息量还要多。以互联网为主要媒介的信息技术正在加速重构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信息和知识的巨大增长让人类史无前例的享受这种增长所带来的便利,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人们在庆祝信息和知识增长的丰硕成果时,必然要承担这种增长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大众媒介时代的信息高度发达,将传统社会的沟通方式冲击得七零八落,组织崩溃、制度丧失其正当性,社会意义的基本来源被各种信息渠道切断,人们开始朝着高度个体化的方向发展,组织、社群与个体之间开始呈现疏离化的状态,自我呈现为碎片化和无中心性特征,再没有一个可靠的根基为自我提供认同这个世界的信息来源。在个体知识与社会知识之间呈现出越来越难以弥补的鸿沟,没有人能够跳出缠绕在我们周围的信息和知识网络,而且,这个网络越收越紧,个体逐渐成为不断向外张望的井底之蛙。
由于社会信息的急速增长,而个体的知识又难以跟上社会信息的增长速度,个体对社会的认知偏差不断加大,当信息沟通的模式变得日益繁琐和沉重,一种结构性精神分裂症在信息时代开始蔓延。不但出现自我认同的困境,而且将他人也视作认知社会的威胁:“在这个过程里,社会的片段化愈加扩展,认同变得更为特殊,日渐难以分享。信息化社会就其全球展现而论,也是奥姆真理教的世界,是美国民兵,伊斯兰/基督教神权政治的野心,以及胡图族/图西族相互灭种的世界[7]。”
信息的过度泛滥与人们接受信息的疲于奔命使得信息病成为传媒时代人们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信息社会带给人们无限的好处,但是各种各样的海量信息超出了人们的接收和消费能力,充斥人们思维的信息冗余构成了信息时代严重的精神污染。然而个体化的社会人们无路可逃,他们无法躲避由此带来的信息轰炸,不得不被动参与到各种信息的接收、解释与传播中去。
大众媒介改变了以往人们信息交流的方式,从口语时代进化到电子时代,信息交流不再局限于固定的时空之内,由此许多想象的社群应运而生,它们的构成不再是有血有肉的物质个体,而是虚拟世界中漂浮不定的个体思维。物质的、现实的个体思维被大众媒介上的信息带离了所在的地域,成为了漂浮在虚拟世界中的主体。“对他们而言,语言本是现实的直译,而如今它所例示的则是镜映成像的一场无穷游戏,一个深渊,主客体在其中彼此进行着不确定的交换。其中的符码、语言和交流的意义暧昧不清,而现实与虚构、外与内、真与伪则在这种暧昧意义的波光中摇摆不定。在这个世界上,主体没有停泊的锚,没有固定位置,没有透视点,没有明确的中心,没有清晰的边界。当福柯在《物的秩序》中写道‘人’已死去时,他表达的便是信息方式中主体的迷茫。在电子媒介交流中,主体如今是在漂浮着,悬置于客观性的种种不同位置之间。不同的构型使主体随着偶然情境的不确定而相应的一再被重新建构[8]。”
主体在大众媒介时代的迷失并不是空穴来风,马克·波斯特在他的另外一本叫做《第二媒介时代》的书中指出:相比于第一媒介时代信息的生产、销售、消费泾渭分明的关系,在第二媒介时代,这三者的关系已经模糊不清,一种全新的交往关系和传播模式很可能让三者成为一体,这是一种双向和去中心化的交流方式。或者借用吉登斯、拉什等人的说法:自反性主体。其言下之意是指:后现代主体在大众媒介海量信息的围绕下,一方面既是运用信息的主体,同时自身也参与到信息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中去,成为了被他人消费和欲望的对象。
这种信息传播方式将人的主体性分割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看似拓展了主体的交往范畴。然而实际上,由于主体的有限性和自足性,其认知范围和认知能力无法逾越大众媒介生产的光怪陆离的信息迷宫,更无法透视自我与世界的本质,虽其竭尽全力,仍旧在大众媒介构筑的信息场中打转。其做法恰恰造成了这样的后果:不仅无法认知外部符号世界,还造成了主体的分散和自我的离场。如果说在传统媒体时代,传媒以一种模式化实践的方式建构具有自律性和工具理性的主体,那么在以电子为主要媒介的大众媒介时代,“后现代性或信息方式所标明的交往实践则建构了不稳定的、多重的和分散的主体”[8]。
然而这些无中心化的和分散的主体,除了被绑架到密密麻麻的信息网络上终日劳心费神外,它们还有关于自身以及外部世界的知识吗?它们仅仅成为了大众媒介传播信息的存储器和过滤器,大众与传媒的主客体关系在后现代信息语境下开始发生了逆转。或许正是意识到了自身力量的孱弱,后现代主体开始在纷扰的大众媒介语境下寻求组建各种各样的文化社群,以此来对抗大众媒介对主体的剥离,确切地说,是为了寻求能够带来某种确定性的文化根基。然而,被信息殖民化的主体,失掉了其本真状态和中心性,能够在电子社群中寻找到它需要的意义吗?让-吕克·南希(Jean-Lue Nancy)说道:“我们那些多重的、分散的、极度碎片化的生存状态只有存在于共同范围内才会有意义可言,可是对于这些生存状态的意义,我们又如何才能领会呢?[8]”
三、媒介化社会的信息迷思与社会风险
媒介化社会的信息迷思的主要表征在于:面对大众媒介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泛滥,受众有限的信息接受和消费能力导致了主体的去中心化和分散性特征,缺乏固定的文化根基,主体在大众媒介时代的认知出现了不可预知的盲点,这同样是一种潜在的风险。
尽管受众被大众媒介时代的各种信息利器剥离了主体性,然而在媒介化时代,受众认知自我和世界的主要方式仍然不得不依靠大众媒介生产的信息,并且沉湎其中无法自拔,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患上了信息依赖症。曾试图有人以极端方式抵制电子媒介信息的诱惑,比如前几年在美国知识界兴起的“关机运动”,倡导者们试图通过远离电子媒介的方式告知人们,离开电子媒介一样可以生活。但是这项运动没有人能够坚持多久,简而言之,就是电子媒介已经把人们绑定为所生产和传播信息的一份子,受众在由电子信息构筑的迷思世界中无法单独存在,信息崇拜和信息依赖症成为媒介化社会的主要表征。
媒介化社会的信息迷思是一种文化的和符号的现象,它植根于传媒时代受众的内心深层结构,信息迷思所表征的是: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科技知识和信息知识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尽管不可避免地带来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的社会风险。然而,消除这些社会风险别无他物,必须依赖高度知识化的信息。
这是人类社会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是并不难理解,最近符号学的研究表明:当某种东西成为“禁忌”之后,反而呈现出更迷人的姿态。以科技知识和科技信息来说,不断有学者发出警示,提醒人们过度崇拜和迷恋科技知识和科技信息,将有可能葬送人类自己。但是这些善意的提醒并没有获得人们的赞同,在人们的思维中,人类文明的历史一直都是勇往直前、永远进步的历史。没有人会怀疑,建立在科技知识和科技信息基础上的社会形态与刀耕火种的社会相比,是一种彻底的历史进步。
但是风险确实伴随着信息知识的增长,当碎片化的社会个体感受到风险所带来的恐惧时,他们因为自身知识的贫乏,只能求助于掌握风险信息和知识的“专家系统”。也就是说,只有用产生风险的信息来对抗风险,社会个体所生存的世界才能获得暂时的安宁。这可以说是人类在“暴殄天物”之后所具有的一种补偿性心理结构,其主要用意恐怕在于:当尽情享受信息知识增长所带来的福利的同时,多少减轻由此带来的风险焦虑。
人类社会的信息迷思和信息崇拜构成了传媒世界有关信息的宏大叙事,在不少人看来,电子信息和媒介构成了对传统思维的肢解,无中心化和分散化的主体消解了传统的束缚,用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话来说,后现代的社会图景应当呈现出花里胡哨的场景。但是在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看来,以消解宏大叙事为指向的私人叙事反过来又构成了另外一个层面的宏大叙事,这种消解宏大叙事的力量即构成了另外一层宏大叙事的框架。在大众媒介时代,即是对媒介、信息或网络的过度迷恋,认为它们无所不能,能够引领社会个体走向多元化和个性化的信息乌托邦。
当社会个体开始这样的想象,即是踏入了信息的牢笼,他们无法把自己从对信息的过度依赖中抽离出来,人们所拥有的有限理性让位于对科学知识和信息的无限需求。“理论家谈论着人类‘受到限制的理性’以及在有限的或不完全的信息的条件下,做出决策的困难。不论是在政府政策、商业战略还是家庭购物诸层次,严重的信息短缺对工作、教育、研究、创新以及做出经济决策构成了威胁,我们大家都在迫切需要的一件东西,就是更多的信息[9]。”
人类对信息的无限需求塑造了信息的文化迷思,它成为大众媒介时代社会进步和化解风险的灵丹妙药。这是一种与信息霸权有关的意识形态,18世纪晚期,法国哲学家蒂斯特·德·特拉西创造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最初被用作一个哲学术语,用来表示观念科学。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总结了意识形态的三种主要含义:“特定阶级和群体所持有的信仰系统;幻想性的信仰系统——错误观念或者错误意识,这种信仰系统是与真理性的科学认识相对的;意义与观念生产的一般过程[10]。”
很显然,经由大众媒介生产和传播的信息,成为了社会个体某种观念和意义的能指,这种意义或观念是指:信息是保障社会进步和个体安全的源动力。社会个体由于无力承担信息增长和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对知识细分角色,他们把这项权利赋予生产和传播信息知识的大众媒介与专家系统,这样在认知诸如社会风险这类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的时候,社会个体不得不依靠那些信息和知识的掌权者,因为社会个体自身已经没有了独立的判断力和甄别力。
尽管每一个社会个体都有一定的社会身份,承担某一特定的社会角色,他们拥有认知自身的某些固定知识,但是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世界,特别是与社会风险有关的知识时,社会个体仍旧感觉到自身知识的贫乏,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专业化损害了社会个体的知识自足性,他们转而不得不向第三方寻求帮助,那些掌握风险信息和知识的大众媒介和专家系统成为了人们的救命稻草,只有牢牢地抓住它们,才能在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的世界中寻求一种暂时的安全感。在社会个体怀有的高度期望中,信息和知识不但操控了社会风险,而且操控了沉沦于信息迷思中的社会个体,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指出:“为什么科学家,那些沉醉于创造知识而且放弃了积极有效的行动的人,不仅能为行动者所容许,而且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还授予他们一定的社会地位,并且认为他们正在执行一种人们期望的社会功能?[11]”
[1]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 论人的延伸[M]. 何道宽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55, 49.
[2]沃纳·赛佛林, 小詹姆斯·坦卡德. 传播理论: 起源、方法与应用[M]. 郭镇之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0: 296.
[3]约翰·杜威. 确定性的寻求: 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M]. 傅统先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18-19.
[4]安东尼·吉登斯. 失控的世界[M]. 周红云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22.
[5]Niklas Luhamann. Risk: A Sociology Theory[M].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2: 7.
[6]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M]. 何博闻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52.
[7]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M]. 夏铸九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4.
[8]马克·波斯特. 信息方式: 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M]. 范静晔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19-20, 44, 46.
[9]约翰·布朗, 保罗·杜奎德. 信息的社会层面[M]. 王铁生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13.
[10]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55.
[11]兹纳涅茨基. 知识人的社会角色[M]. 郏斌祥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17.
(编辑:程俐萍)
On the social risks and the predicament in the media era
Feng Yueji
(SchoolofLiteratureandLaw,YanshanUniversity,Qinhuangdao066004,China)
With the rise of various new media, human has entered the era of media. Mass media not only provide human with great convenience of information exchange but also bring about social risks of uncertainty. Media flooding and information worship leads to human's predicament who has lost cultural foundation of acquiring meaning, falling into ambiguous information confusion and risk.
Media; Information; Human; Confusion; Risk
2017-02-01
冯月季(1977-),男(汉),河北保定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符号学、传播学方面的研究。
2016年河北省委讲师团系统科研课题(2016095)
G201
A
1671-816X(2017)07-006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