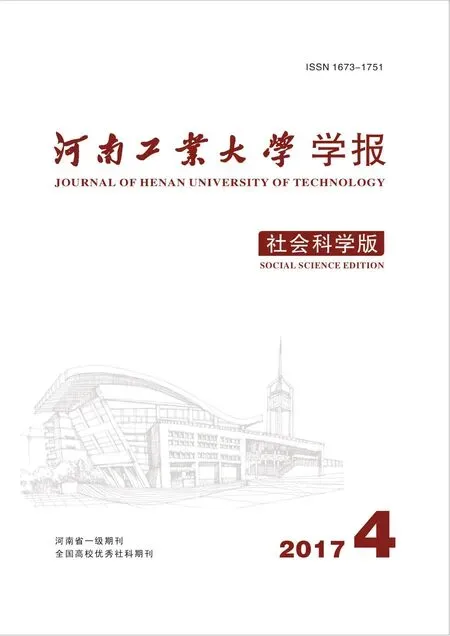佛教家僧渊源考述
左金众
(陕西师范大学 宗教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062)
佛教家僧渊源考述
左金众
(陕西师范大学 宗教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062)
家僧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起源于梁武帝统治时期,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梁代就已经形成完善的家僧制度。随着历史的演变,隋唐之际的家僧被称为内道场僧、门僧和门徒僧。梁代的家僧具有皇帝的顾问和秘书的性质,家僧和皇帝之间是一种上下级的隶属关系。家僧是由皇帝直接征召高僧形成的,并听命于皇帝的诏令和安排;此外,皇帝礼聘家僧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统治的考虑。随着佛教在唐代的兴盛,民间达官显贵的家中出现了私家化的门僧和门徒僧,家僧空前兴盛,并且广泛流行。
佛教;家僧历史渊源;演变
在佛教的中土化与世俗化进程中,家僧是一种比较独特的社会现象,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佛教的世俗性,以及中国人佛教信仰的功利性和实用性等特点。家僧对古代皇权、国家政治和传统思想文化都有着重大影响。然而,目前国内、外的学术界对此现象却未予以应有的重视。笔者对家僧的产生、发展和历史演变进行了梳理和考证。
家僧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梁武帝天监五年(506年),扶南国(今柬埔寨南部和泰国东南部一带)僧人僧伽婆罗(梵名Samghavarman)是中国历史上首位家僧,《续高僧传》记载:“天监五年,(僧伽婆罗)被勅征召于杨都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等五处传译……初翻经日,于寿光殿武帝躬临法座,笔受其文……华质有序,不坠译宗,天子礼接甚厚,引为家僧。”[1]统计显示,中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家僧共有13位,其中梁代8位,隋代3位,唐代2位。梁代的8位家僧为僧伽婆罗(460—524年)、法宠(451—524年)、乐氏僧迁(465—523年)、僧旻(467—52年)、法云(467—529年)、慧超(?—526年)、明彻(?—522年)、严氏僧迁(495—573年)等,他们均在天监年间(502—520年)被梁武帝礼聘为家僧。关于家僧的概念和性质,有的学者笼统地将家僧等同于门僧、门徒僧,并根据《汉语大辞典》对门僧的解释“(门僧)指约定为大户人家做礼忏,平时并有往来的僧道。”[2]认为家僧是被雇佣来做礼忏佛事的僧人。意大利学者Heirman认为:“家僧和皇帝之间体现的是一种雇佣中的等价交换关系,皇帝予以家僧在物质和社会地位上优厚的待遇,而僧人则辅助皇帝处理国家以及佛教事务。”[3]Heirman侧重于从政治雇佣和等价交换的角度来认知家僧。严格来讲,梁代的家僧是皇帝御用的顾问僧,“(梁代)德高望重的名僧……作为家僧成了皇帝顾问。”[4]家僧顾问的作用,一方面体现在佛学和佛教事务上,另一方面则表现在笼络僧人和加强对佛教僧团管理上,具有巩固皇权和稳定社会统治的政治目的,而且后者更为明显。家僧起源于梁代初年,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1 家僧起源的时代背景
宋、齐、梁之际,皇权得到加强、门阀盛行和佛教力量得以发展壮大;皇权、世家大族分别与佛教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是梁初家僧形成的重要社会背景。
1.1 皇权与门阀世家的矛盾
魏晋之际,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权利崩溃之后,拥有乡里势力的大族成为地方政治的主导力量,在原有政治体系无法正常运作的情况下,区域性的割据政权必须借助地方大族的合作方能巩固政权”[5]。南朝的开国之君通过与门阀豪族合作建立政权,在政策上倾向于世家大族,从而导致门阀豪族把持朝政,形成累世公卿的政局。世家大族“势力倾于邦君,储积富于公室”(《抱朴子·吴失篇》),拥有雄厚的政治、经济实力。门阀士族又通过九品中正制,“平流进去,坐致公卿”(《南书·禇渊传》),使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人为造成士庶天隔的畸形社会现象,加剧了寒门和世家大族的矛盾。梁代开国初年,“大政侵小,豪门陵贱,四民已穷,九重莫达”(《梁书·武帝纪》)。世家大族奢靡的生活,诚如颍川钟嵘所言:“服既缨组,尚为臧获之事;识唯黄散,犹躬骨徒之役,名实淆紊,兹焉莫甚。”(《梁书·钟嵘传》)这些“宽则优游物表,急则筹划私门;报国无心,救世乏术”[6]的门阀豪族侵蚀社会,显然不利于皇权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
南朝的开国之君并非出自世家大族,对门阀子弟在国家政治中的尸位素餐行为无能为力,只能给卑官小吏的寒门庶族授以实权来处理政务。梁武帝在用人上主张“无复膏粱,寒素之隔”。南朝自东晋开始就逐渐恢复皇权政治,门阀士族与皇权之间争斗不断。世家大族“戒备凭借武力树立的政权以及与这种政权相伴存的次等士族与寒人”[7],政治实权的下放引起了世家大族的不满,梁初皇权与门阀势力之间在社会政治上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加剧。
1.2 佛教力量的发展与壮大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译经时采用格义的方法推动佛教与玄学融合,一时涌现出大批的义学僧人,“南北朝共有义学僧58人,南朝56人,北朝2人”[8]。佛教的般若学在玄学的影响下形成六家七宗,使得佛教更适应南朝玄学的文化土壤。当时僧人道安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主动调和世俗皇权以及儒家之间的关系。以上诸因素,使得南朝的佛教势力迅猛膨胀。僧尼和寺院数量激增,“宋世有寺1913所,僧尼36 000人;齐世有寺2015所,僧尼32 500;梁世有寺2846所,僧尼82 700人。”[9]此外,南朝的僧人有着众多的信徒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如南齐永明十年(492年),僧旻在兴福寺讲成实论时,“其会如市……衣冠士子,四衢辐凑,坐皆重膝,不谓为迮……希风慕德者不远万里相造。”[1]南梁僧佑讲戒律学时,“凡白黑门徒一万一千余人”。随着佛教与玄学、儒学的不断融合,佛教在南朝得以迅猛传播,僧人和寺院数量飞速增长,高僧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到梁代初年,佛教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1.3 皇帝、世家大族与佛教的关系
南朝的皇帝和皇室大多信奉佛教,东晋元帝司马睿“善书画,尤善画佛像,或立于供养,或送臣下供养”(《隋书·经籍志》)。宋武帝刘裕借助僧人为其皇位的正统性辩护,僧人法珍借神人之口称道:“江东有刘将军,汉家苗裔,当受天命。”(《宋书·符瑞志》)齐竟陵王萧子良对佛教“敬信尤笃,数于邸园营斋戒……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南齐书·萧子良传》)。南朝帝王和皇室崇佛的传统,为梁武帝向佛教靠拢奠定了信仰基础。

南朝时期,佛教势力不断发展与壮大,皇室、世家大族与佛教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佛教作为一股独特的社会力量,它的倾向性对皇权和门阀士族的政治走向具有重要影响。梁初,如何笼络和控制佛教,以达到巩固皇权和稳定社会的政治目的,是梁武帝萧衍面临的最紧要的政治问题。
2 梁武帝与“家僧”的起源
2.1 梁武帝向佛教靠拢
佛教的五戒十善、善恶因果报应、极乐净土以及重道的教义思想,具有辅助政治,稳定社会的作用。“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厚矣……能行一善,则去一恶;一恶既去,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则百刑息于国……所谓坐致太平者也”[12]。梁武帝早年曾在竟陵王萧子良门下,“其佛教之信仰与其在鸡笼山西邸有重大关系”[11],他利用佛教来维护统治的治国思想可能在此时已经形成。“佛教与政治的联姻首先表现在作为封建政权代表的帝王对佛教的信奉。”[10]为巩固皇权和稳定社会,梁武帝频频主动地向佛教靠拢。天监三年(504年)梁武帝弃道崇佛,并颁布《舍事道法诏》,诏书中称自己“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业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法,弃迷知反,今舍旧医,归凭正觉;愿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识,同共成佛。宁在正法之中长沦恶道,不乐依老子教暂得升天”[13]。同年4月11日,他再次下诏,把佛教视作唯一的正道,“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于正道……朕舍邪外,以事正内诸佛如来……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广弘明集·归正篇》)。梁武帝以佛教为正法,以儒、道为邪法,把老子、庄周、孔子视为如来的弟子,表明了他独尊佛教,并企图将佛教定为国教。
魏晋以来,世家大族多崇奉儒家和道教,并在儒、道之中有着极高的权威和影响力。梁武帝抬高佛教,抑制儒、道,是从思想上抑制门阀势力,具有鲜明的政治意图。梁武帝还通过各种方式迫使人们信奉佛教,天监三年(504年),“(梁武帝)与道俗二万人……发菩提心”(《广弘明集·归正篇》),同时又责令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反伪就真,舍邪归正”。梁武帝努力将佛教上升为国家意志,并在全国强行推广佛教。其用意为:一方面树立他在佛教中的地位和扩大其在佛教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通过笼络佛教来抑制门阀势力,维护皇权和稳定社会。
2.2 对佛教教团的控制与设置家僧
梁武帝对佛教的控制政策具有极大的灵活性,《魏书·萧衍传》载:“衍崇信佛道,于建业起同泰寺,又于故宅立光宅寺,于中山立大敬爱寺,兼营长干寺,皆穷功极巧,殚尽财力。”[14]史称梁都建康城有“大寺七百余所”[15]。与建寺一体的是造佛像,天监六年(507年),梁武帝在“小庄严寺造无量寿像,长一丈八尺”;中大通二年(530年),在大敬爱寺“造一丈六尺旃檀像”;大同元年(535年),在同泰寺铸银佛像等。梁武的布施也是惊人的,“皇帝舍财,遍施钱、绢、银、锡杖等物二百一种,直一千九十六万”(《广弘明集·叙御讲波若义》)。为了加强与佛教之间的联系,天监十八年(519年),梁武帝 “发弘誓心……受菩萨戒”(《续高僧传·慧约传》)。据《梁书》和《南史》等记载,梁武帝在大通元年(527年)、中大通元年(529年)、中大同元年(546年)、太清元年(547年)有四次舍身同泰寺的经历,可谓是为了笼络佛教无所不用其极。此外,梁武帝还亲自注经、讲经、赞助译经和编写佛教书录、恪守佛教戒规。梁武帝采取建寺造像、布施受戒、舍身出家等一系列温和的政策深得朝廷内外美赞,《经律异相》序中称其为等觉、遍知;官员也在奏表、上书中,称他为“皇帝菩萨”。

虽然梁武帝在白衣僧正问题上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但他终究没有放弃控制佛教的梦想。因此,梁武帝转而笼络那些在佛教中德高望重、有巨大影响力的僧人,并礼聘他们为家僧。梁代三大师中的僧旻、法云均被他引为家僧。僧旻、法云这样有威望的佛教领袖对梁武帝的佛教政策没有异议,是梁武帝平息其他各种反对言论和控制佛教的最好方式。
3 家僧制度的形成
梁武帝统治时期,在家僧的选拔方式和选任标准以及家僧的职责和待遇等方面形成了完善的制度。
3.1 家僧的选拔方式和选拔标准
南朝时期,“虽然九品中正制度是占据着主导地位的选官制度,但是皇帝征召制度依然实行”[16]。梁代的皇帝征召制度也仍然在发挥作用,僧伽婆罗被萧衍礼接甚厚,引为家僧;法云也被梁武帝直接“下诏礼为家僧”。因此,家僧是由皇帝采取直接征召的方式在僧侣中选拔的。
梁代僧尼众多,并非都是家僧,此时对家僧的选拔有着严格的标准。首先,学识渊博,有较高的佛学造诣。如僧伽婆罗精通律、论、大乘方等经典和数国语言,“学年出家,偏业阿毘昙论……具足已后广习律藏……从跋陀研精方等,未盈炎燠博涉多通,乃解数国书语。”[1]僧伽婆罗在译经方面也有突出才能,“初翻经日,于寿光殿,武帝躬临法座,笔受其文……华质有序,不坠译宗。”法宠擅长成实学、毘昙学,“从道猛、昙济学《成实论》……通杂心及法胜《毘昙》”。慧超“广采经部及以数论,并尽其深义”。因此,渊博的知识和高超的佛学造诣,是成为家僧的重要条件。其次,德高望重,有广泛的影响力。僧旻德高望重,世人以其为师范,“自晋宋相承凡论议者,多高谈大语竞相夸罩,及旻为师范”。晋陵太守蔡撙盛赞僧旻为当世的素王,“昔仲尼素王于周,今旻公又素王于梁矣”。法云在上层社会中与“齐中书周颙、琅瑘王融、彭城刘绘、东莞徐孝嗣等一代名贵,并投莫逆之交”。德高望重,在社会中具有极大影响力,是成为家僧的另一重要标准。虽然家僧的选拔注重德才、个人的威望和社会中的影响力,但并非所有满足这些条件的僧人都是家僧,著名的僧人智藏和宝唱便不在家僧之列。智藏因白衣僧正事件和梁武帝有过激烈的辩论,使得梁武帝的佛教政策受挫。宝唱因治疗脚气,没有请示皇帝旨意,私自去异地治疗,受到梁武帝的惩罚,“以脚气连发,入东治疗,去后勅追,因此抵罪谪配越州。”这些事情表明家僧的选拔标准是在德才、威望、影响力三者兼具之后,还要僧人肯于服从皇帝的旨意。
3.2 家僧的职责和待遇
家僧由梁武帝征召而来,并服从他的诏令和安排。大部分家僧主要从事佛经的翻译、佛学义理、注疏、讲经等工作。如僧伽婆罗“被勅征召于杨都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等五处,传译讫十七年,都合一十一部,四十八卷”。僧旻“入华林园讲论道义……六年制注般若经,以通大训,朝贵皆思弘厥典……又勅于慧轮殿讲《胜鬘经》……选才学道俗释僧智、僧晃、临川王记室、东莞刘勰等三十人,同集上定林寺,抄一切经论。”家僧一方面充当皇帝的佛学顾问,另一方面,部分家僧又被梁武帝授予官职,处理国家政务。如:法云被“勅为光宅寺主,创立僧制,雅为后则”;慧超被任命为僧正“戒德内修威仪外洁,凡在缁侣咸禀成训……剖决众情,一时高望,在位二十余年。”最为典型的当属严氏僧迁,他起初是皇帝的佛学顾问,后来负责整顿佛教僧团,并最终由佛教走向政治。“帝制《胜鬘义疏》,班寿光殿,诸僧咸怀自恧,迁深穷理窟,特诏敷述……中兴荆邺,正位僧端,职任基月道风飙举,恂恂七众不齐而成……经诰盘结皆针盲起废,怡然从政。”可见,家僧既是梁武帝的佛学顾问,同时也是国家治理的政治顾问和参与者。僧人凭借佛学上的成就和在佛教中的地位以及影响力而被皇帝征召为家僧,皇帝以佛学笼络家僧,同时通过家僧把自己的意志渗透到佛教中,加强了对佛教的控制。
作为皇帝的家僧,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社会地位、荣誉等方面都能得到很好的待遇。法宠受到皇帝极高的尊崇,“上每义集以礼致之,略其年腊勅常居坐首,不呼其名号为上座法师。”同时皇帝对家僧在物质上也有丰厚的赏赐,“勅施车牛人力衣服饮食,四时不绝。”梁武帝更是对法云资给优厚“车牛吏力皆备足焉”。另外,家僧要受皇帝的制约,如梁武帝责令慧超前去受戒,“有诏令超受菩萨戒,恭惟顶礼如法勤修。”僧人明彻“天监末年勅入华林园,于宝云、僧省,专功抄撰,辞不获免。”皇帝对僧人的限制,说明是把家僧看作皇帝私人的僧人。
梁武帝时期的家僧制度是一种综合性的佛教政策,一方面拉拢高僧大德以优厚的待遇,积极推动家僧讲学、著述等,另一方面又授予家僧官职,让家僧帮助皇帝控制佛教僧团和处理国家事务。家僧作为梁武帝的顾问,受皇帝征召和礼聘,并负责皇帝安排的各项具体任务。在某种程度上,家僧与皇帝是一种上下级的隶属关系。
4 家僧制度的演变
梁代之后,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家僧又被称之为内道场僧、门僧和门徒僧。
4.1 隋代家僧向内道场僧的转变

4.2 唐代门僧在社会中的普遍化

5 结语
家僧的起源和家僧制度的完善均完成于梁武帝统治时期,梁武帝礼聘家僧具有控制佛教,巩固皇权,削弱门阀豪族势力等政治目的。在名称上,隋代是家僧向内道场僧过渡的关键时期。佛教在唐代繁荣到极致,内道场趋于兴盛,宫廷中有着众多的内道场僧人,在称谓上内道僧彻底取代家僧;在唐代,富豪权贵延请僧人为自己祈福、修功德,家僧逐渐被看作私家的僧人,也因此被称为门僧、门徒僧。然而,无论是梁武帝的家僧,还是隋唐的内道场僧,都隶属于皇帝;家僧和皇帝之间是既是顾问关系,同时又是上下级的隶属关系,家僧受皇帝制约,服从皇帝的旨意和命令,并为皇帝、皇室和国家服务,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在唐代,盛行于达官贵人家中的门僧、门徒僧,则具有私家仆人的性质。总而言之,家僧形成于梁代,兴盛于隋唐,并在唐代普及于民间;在形态上经历了家僧、内道场僧、门僧和门徒僧的历史演变过程,成为中国佛教文化中一种独特的现象。
[1] 释道宣.续高僧传[M]//大正藏(第5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2] 罗竹风.汉语大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3] RAUW T D, HEIRMAN A. Monks for hire liang wudi’s use of household monks (jiaseng)[J]. Medieval history journal, 2011(14):45-69.
[4] 镰田茂雄.简明中国佛教史[M]. 郑彭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5] 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利与家族网络[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6] 王伊国.五朝门第[M].北京:中华书局,2006.
[7]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8] 郭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M].济南:齐鲁书社,1986.
[9] 释法琳.辩证论[M]//大正藏(第5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10]高文强.东晋南朝文人接受佛教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1]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2]僧佑撰.弘明集[M]//大正藏(第5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13]释道宣.广弘明集[M]//大正藏(第5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14]魏收.魏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15]释法琳.破邪论[M]//大正藏(第5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16]张旭华.魏晋南北朝官制论[M].郑州: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
[17]赞宁.大宋僧史略[M]//大正藏(第5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18]张弓.唐代的内道场僧与内道场僧团[J].世界宗教研究,1993(3):63
[19]刘铭恕.隋唐时代的僧用和佛教的门僧制度[J].中原文物,1985(1):79-80
[20]释慧超.游方记抄[M]//大正藏(第5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AN ANALYSIS OF THE ORIGIN OF BUDDHIST HOME MONKS
ZUO Jinzhong
(School of Mechanical & Electrical Engineering, 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Monk is a unique social phenomenon of the Chinese culture originating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Wu of the Liang Dynasty, and it has its profound historical origin. Perfect system of Monk had already been formed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evolution of history, monk is also called field monk,door monk and Disciple monk in the Sui and the Tang Dynasties. The monks in the Liang Dynasty were more of the emperor' advisers and secretari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nk and the emperor was a subordinate relationship. The eminent monks recruited directly by the emperor became home monks and they followed the order and the arrangement of the emperor; in addition, the emperor cordially hired Home monk mainly out of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With the prosperity of Buddhism in the Tang Dynasty, there appeared private “door monk” and Disciple monk in the home of dignitaries. In the Tang Dynasty, home monks flourished and became quite popular in ancient China.
Buddhism; Home monk; historical origin; evolution
2016-12-20
左金众(1991-),男,河北广宗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佛教史方向研究。
1673-1751(2017)04-0105-06
B943.9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