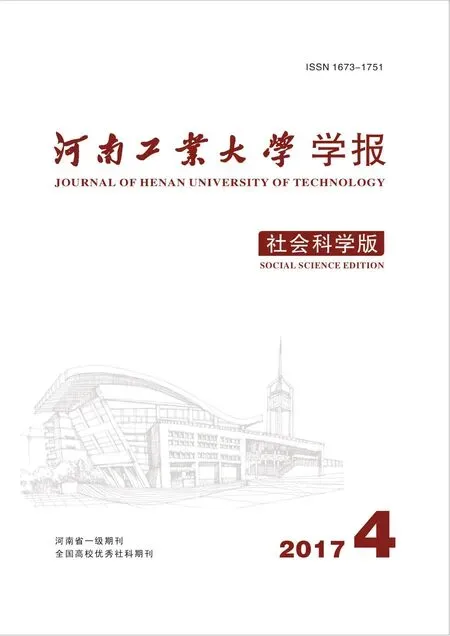“网约车”市场监管及其行政法追问
谭 波
(河南工业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网约车”市场监管及其行政法追问
谭 波
(河南工业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现代科技的发展与经济的转型会催生新生的市场,对新生市场的监管实际是旧有监管的升级改造,需要新的立法形势与法治要求与之相适应。对“网约车”监管的再定位可以集传统监管理论与现代立法于一体,按照新型的立法分类来分析,从准入监管与后续监管的大类入手,再于后者中细化为一般监管、协同监管、信用监管、风险监管,不断总结经验,完善监管标准,同时要辅之以对监管者的监管。
市场;监管;行政法
1 何谓“市场”?
要解决市场监管的问题,关键是对“市场”的界定。“市场”到底有多大,又何时形成,似乎不是能一言以蔽之的问题。伴随着经济的新常态步伐和网络经济发展的渐行渐深,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被置身于一种随时可能出现的“市场”之中,自己也随时可能成为市场的操盘手或力推者。2016年10月,由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广东省市场监管条例》开始实施,将“市场主体”界定为,“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按照上述条例的界定,“网约车”应该属于相应的交通服务市场。2016年7月,交通部、公安部、国家质检总局等七个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将出租汽车行业分为“巡游车”和“网约车”两类,从合法性上对“网约车市场”进行正名,我国也成为承认网约车合法性的国家:“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服务平台,接入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通过整合供需信息,提供非巡游的预约出租汽车服务的经营活动。”这种界定,肯定了“互联网+”背景下出租车市场所“遭遇”的新变化。实际上在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上,网约车是对传统出租车(巡游车)的一种补充。
由此可见,“市场”一方面是由社会需求催生,另一方面也需要官方的“招安”。关于前述两个文件的级别,前者是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后者则是由交通运输部主推并经征求意见和部务会议正式通过的规章,后经其他六部门同意而发布,这一程序就暂时从形式上为“网约车市场”赢得了发展先机。但是否其他领域的新生事物如无人驾驶,只要通过了类似程序,就不再需要其他的伦理挑战[1],就也可以形成相应的“市场”?答案显然为非,市场的形成首先要求不存在相应的合法性障碍与伦理障碍。
2 对“监管”的界定
监管(regulation)一词具有现代性,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曾出现的“官督”实际上是旧式行政管理的体现[2]。伴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和秩序的需要,监管已经融入生活中,诸如金融监管、环境监管等。其实,“监管权作为国家公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立法、行政、司法领域”[3]。我们通常所说的监管,是指“政府行政机构在市场机制的框架内,为矫正市场失灵,通过设定相关规范标准,对经济个体的活动进行的一种干预和控制”[4]。这是一种狭义的监管,也即政府监管。
从经济学的理论来讲,监管依据其监管主体介入的方式,可以分为直接监管和间接监管:间接监管指的是通过竞争法、民商法等法律而进行的监管;而直接监管又可分为经济性监管和社会性监管。社会性监管是以“保障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安全、健康、卫生、环境保护、防止灾害为目的,对物品的质量和服务的质量和伴随着他们而产生的各种活动制定一定标准,并禁止、限制特定行为的规制。”[5]如果说经济性监管主要依据行政方式,那么社会性监管就有倾向法律的特征,诸如金融监管、工商监管、质监监管、旅游监管等,都属于经济性监管,而社会性监管则囊括环境监管、卫生监管等方面,也是社会生活所必需的。随着科技的发展,经济性监管和社会性监管的涉及领域都多有扩展,以交通运输领域为例,网约车的出现与普及,带来的是交通领域的管理革新与监管升级,如果说“网约车”还可以归为较为传统的市场监管的话,那么像“网络游戏”这种涉及文化领域的新生事物,便明显地体现了经济性监管与社会性监管的交叉。其实在整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从经济性监管向社会性监管转变,应该是很多行政管理领域存在的一种普遍趋势。[6]
从立法层面来看,由于缺乏较为统一的立法和相应的法定表述,监管在我国当下的法定地位与其理论研究地位还存在一定差距。但是,从实际的立法需求来看,对监管的法律定位及其相应的解构只是时间问题。前述提到的《广东省市场监管条例》将监管界定为“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负有市场监管职责的部门(简称‘市场监管部门’)对市场主体及其生产经营行为实施的监督管理活动”。在这里监管又被分为准入监管和后续监管,后续监管又被分为一般监管、协同监管、信用监管和风险监管。对监管的此种界定与划分,是一种很必要的尝试,这也很可能成为立法过程中“地方包围中央”的一种再次尝试。
3 监管何去何从?
经由网络和现代科技而衍生的新生租车市场,也即“P2P”(peer to peer),或C2C(customer to customer),区别于传统的租车公司形成的B2C(business to customer)模式,有人称之为“共享经济”模式[7]。仔细分析,很多新生事物的某些特征往往只是传统事物在网络世界中的翻版,对于这些传统社会中已经存在的监管领域,需要做的是将传统的监管举措与针对网络经济和共享经济的监管举措结合起来。毕竟,“C2C模式的网约车车主,在管理者视野内是半隐形的,在角色上也没有共同特点。而其所从事的行业却恰恰是一个需要严格管理的行业。”[8]
3.1 准入监管
对网约车的监管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准入监管问题,由交通运输部、工信部、公安部、商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网信办等七部委共同出台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就对网约车平台公司、网约车车辆和网约车驾驶员分别做了各种规定。而在“网约车”尚未真正合法化的时间段内,也即在各地都在观望或酝酿相应政策的当口,“网约车”尚未实现真正的如期转正,此时管理上存在漏洞,司乘人员本人对这种过渡期的空白身份也是心生担忧,乘客为求方便,也只能与司乘人员共同“圆谎”,以期合法的招安日期尽早到来。这种情况,恐怕不单单是网约车市场才会碰到的,其他的“市场主体”在未来准入监管时可能遇到的类似情况应该尽可能得到统一解决。
于2016年11月1日起实施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最后一条提出各地应根据本地实际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根据统计,各地的网约车新政总体上有共性,但依然存在较大区别,这种区别表现在司机身份、号牌所在区域、汽车价格、汽车排量、汽车长度以及拼车限制等诸方面。具体分析见表1、表2、表3。
通过对上述表格的分析不难看出,一线城市特别是京津沪等对司乘人员户口和本市车牌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其他有些二线城市对本市车牌也有一定限制,对车辆轴距也有一定要求,有些甚至还对拼车次数做了限制,一些城市基本上通过这些限制条件实现了对网约车数量的限制,达到了各自城市管理的相应目的。但这种“硬条件”前提下导致的“重审批”也为一些学界及实务界人士所诟病,认为应该向“宽准入严监管”转型[10]。2017年2月,河南省郑州市的网络预约车新政出台,其中还对驾驶员的年龄与文化程度做了规定,在车辆要求方面对车辆的发动机功率以及新能源汽车、纯电动汽车以及混合动力汽车的轴距与行驶里程都做了相应限制。

表1 我国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与珠三角及华北地区网约车条件一览[9]
注:视为严格的条件:申请网约车需要户籍、北上广深需要本地牌照;视为一般的条件:申请网约车需要居住证、本地牌照;视为宽松的条件:申请网约车没有户籍、车牌的规定;△严格 ○一般 *宽松

表2 我国长三角地区城市网约车条件一览(上海除外)[9]

续表2
注:杭州最新管理细则规定,在本市取得浙江省临时居住证12个月以上就可以申请网约车牌照;△严格 ○一般 *宽松

表3 我国西部及东北地区网约车条件一览[9]
注:△严格 ○一般 *宽松
3.2 后续监管
在后续监管层面,网约车监管还需要面临很大的挑战,有很多漏洞规则制定者和监管部门还没有掌握。
3.2.1 一般监管
通常意义上的监管在网络环境下会变得机制多元,办法多样,当然也会面临问题丛生的局面。在准入监管时,各项技术条件的设置其实已经为下一步相应部门的监管奠定了基础,但即便如此,仍然不能保证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出现各式新型的网络诱因问题。上述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将“网约车”的市场监管权力下放至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含出租汽车管理机构),由其具体实施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管理。由此带来的问题在于,是否要全国2800多个县级相应机构分别制定各自的标准来保证“网约车”的顺利实施?关于此问题,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认为,网约车主要与城市有关,因此将全国2800多个县级相应机构精简至661个(含县级市)。但即便如此,这个数字也较为庞大。据我国行政法学学者周汉华的介绍,美国网约车监管具有很强的地方性,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制度,但最后一定会使最好的制度浮出水面,这也恰恰可能是制度生成的道路[11]。特别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在交通运输部的相应文件中,有些经监管部门认定的线上服务能力的结果,全国有效,而这应该成为未来“网约车”监管的一种共享机制。
2016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58号)中,要求“加强法制建设”,其中重点谈到“要加快完善出租汽车管理和经营服务的法规规章和标准规范”“形成较为完善的出租汽车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对于有地方立法权的设区的市及其以上级别的地方政府而言,立法不成问题,但对于其他县级市或者没有立法权的城市而言,只能通过出台文件或依托高级别政府立法的方式来完成这一任务,这样,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也就少了。
3.2.2 协同监管
通过“网约车”之“纲领性文件”的单位为7家,但在该文件的第五章“监督检查”中,却有着这样的规定,“发展改革、价格、通信、公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商务、人民银行、税务、工商、质检、网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网约车经营行为实施相关监督检查,并对违法行为依法处理”。
从部门职责交叉来看,主要是工信、公安、商务、工商、质检、网信等部门存在职责交叉现象,抛开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不说,这里的发展改革、价格、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人民银行、税务等部门虽然对“网约车”也有监督检查权,但根据未来的监管权整合与大部门制改革趋势,两个以上市场监管部门对同一市场违法行为都有监管职权的,应当依照法定程序调整为一个部门执法。 目前,针对职责交叉、多头执法等最为常见的解决形式可能是联合执法,联合执法的牵头部门为发起部门或者承担主要监管职责的部门,联合执法的牵头部门负责组织、协调工作,其他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在职责范围内参与联合执法。
前述《广东省市场监管条例》也提出,社会组织和公众应当同监管部门一道,共同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市场健康发展,而各级政府和监管部门则应当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与公众参与市场监督。协同监管应与客户监督同步而行。比如,游客在赴外地旅游过程中,因不能确定其赴机场等中转地的距离和所花时间,可能会委托旅店工作人员订车,旅店工作人员则可以利用此种机会采取“先约车再取消”的方式,从中抽头渔利赚取差价,这可能是网约车平台所未曾预料到的。在这个过程中,网约车司机和乘客,都成了旅店工作人员谋利的手段,而网约交易被取消,网约平台也无法采取应对措施。这种情况下,监管机关应该挺身而出,对这种变相的谋利行为进行规控。但是,这需要公众和社会组织的共同监督。
3.2.3 信用监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市场监管部门建立的信用监管制度包括很多方面,如市场主体信用承诺制、市场主体信用档案制、市场主体信用分类管理制等。要使信用监管起到应有的作用,应完善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的采集、记录和交换共享机制,强化信用信息的公开、公示和应用。乘客在享受网约车服务时其付费并不是现场完成而是通过网约车交易平台,因此,有些司机往往利用这一漏洞,甚至不惜铤而走险,采取故意扣费的方式,攫取某些并不太在意的乘客的多余打车费用[12]。这种情况就属于信用监管的范畴,需要监管部门完善各种信用评价与公开机制对网约车实现监管。
有些问题并不明显,需要监管部门强化识别,将其列入需要监管的行为现象。例如:面对一些冷门线路的业务网约车司机不愿接单,这时,乘客的需求要想得到满足,必须通过加价的方式来获取,平台协助出租车司机加价的行为实际上是对乘客的一种胁迫,也是新型经营方式下“拒载”的变种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乘客是一种弱势群体,而有些交易一旦发出又是不能取消的,对于乘客来说更存在着投鼠忌器的双重“压迫”,此类问题需要通过信用监管来解决。
当然,对市场而言,需要监管的不只是市场主体本身,服务的享受者也需要相应监督。比如,对网约车代理的行为监管就异常必要,网上一度流传的“30元任意跑”的“滴滴代叫”行为就属于这一类,这里的受害者是网约车司机,代叫者采取了“一锤子买卖”的方式,叫车的手机号只使用一次,而乘客作为参与者并不直接付账,这就苦了这些信任乘车者和代叫者的司机,虽然这种损失最后可能会通过网约平台得到部分补偿,但这种信任机制客观上也受到了极大的损害[13]。而有些乘客则因为其他特殊原因取消订单,却遭到了司乘人员的反复骚扰甚至人身攻击。如此看来,区分恶意取消、故意取消与一般取消,实属未来信用监管过程中必须重视的问题。
3.2.4 风险监管
风险监管的含义在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建立风险监管制度,对存在或者可能存在隐患的市场状况进行风险分析和评估,实施风险联动防控,防范区域性、行业性、系统性市场风险。如何防止网约车这种新生事物成为另一种非营运人士盈利的手段,也是监管机关需要面对的问题。比如,网约车虽然从某些层面杜绝了山寨出租车、黑车现象,拒载和议价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但某些方面的监管需求(如保险需求等)也同样迫切。这实际上属于风险监管层面下的衍生问题。因此,国内网约车投保的发展趋势也是较为明显[14]。其实,这种新生事物在国外的相应发展路径也是相似的,美国优步(Uber)在保险过程中会依循不同的状态采用不同的保险形式,然后再辅之以相应的保费增加来解决私家车在不同状态和时段下的保险问题。
4 “网约车”市场监管的行政法保障
“网约车”的出现表面上只是增加了一种交通出行方式与选择,但就实质而言,政府在新形势下需要改变行政心态、提高管理能力以及提供行政法治保障。
4.1 进一步推进各项清单制度
清单制度可以和相应的交通行政体制改革尤其是审批制度改革联系在一起,推行交通监管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收费清单制度。各项相应权力事项以清单形式向社会公开,分别厘清与行政权力相对应的责任要素,建立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制度,接受公众的监督。
4.2 强化相应立法及公众参与
交通领域要实现法治政府的子目标,首先必须强化立法,除了进一步完善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之外,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相应的地方立法都应该进一步发挥作用,特别是要将相应的法律、地方性法规能够解决的问题固定或调整在地方人大或其常委会,不轻易授权给国务院部门以及地方政府进行立法,不让监管者本身更多地主宰立法。2016年8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在审议环保税法草案时,就严格贯彻法律保留原则,相应的税制核心要素都没有授权给国务院或地方政府,而是将授权给了地方人大或其常委会。
在提高公众参与度方面,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广纳民意,注重意见来源的代表性;另一方面抓紧建立健全合理、有效的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
4.3 加强对政府规范性文件的监督和清理
如前所述,真正在交通领域起牵头作用的仍然还是交通运输部门,政府规范性文件应该包括前文提到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对“网约车”的市场监管,应尽可能通过地方政府规章调控,因为根据修订后的立法法的规定,“网约车”市场监管理应属于“城市管理”的范畴。对于规章,除了强化其通过程序外,应该加强清理,保持对文本的动态化管理。对于其他规范性文件,则应该加强合法性审查,严格遵循上位法的规定,不越权,保持及时公开,统一登记、编号、管理。
4.4 完善问责机制和纠纷解决程序
英国公共管理学者克里斯托弗·胡德的在《监管政府》一书中,提出了“政府内监管”的问题,也即监管监管者的问题[15]。目前来看,对于监管部门的监督,主要还是靠立法和监管系统内部的自我约束来完成。2016年7月,财政部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的通知》,出台了《法治财政建设实施方案》,其中包含了40条对应的举措,也涉及监管法治化的相应内容。对于交通领域的监管及对监管者的监管而言,同样可以采取《法治交通建设实施方案》中的相应举措加以推进。对于重要的行政决策,经过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后出现问题的,要落实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和相应的责任倒查机制,完善纠错问责的具体机制。要建立纠纷的语境机制,引导公众合理表达诉求;强化应急行政的处理能力,加强相应的行政复议程序,对复议过程中发现的普遍问题要进行跟踪反馈;对于相应的调解、仲裁和裁决工作,也必须依法而为;同时应完善信访环节。这些都是为了能更好地强化对监管者的监督,增强其自我抵御风险的能力。
[1] 南辰.无人驾驶技术势必引发伦理挑战[EB/OL].中国新能源网(2013-2-27)[2017-04-17]. 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44546.html.
[2] 刘刚,李冬君.中国近代的财与兵[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
[3] 潘波.银行业监管权研究——行政法语境下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4] 李嘉娜.市政公用事业监管的行政法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
[5] 许石慧.法律视野中的社会性监管[J].电业政策研究,2006(8):20-23.
[6] 王秀强.能源管理应从经济性监管向社会监管转变[EB/OL].和讯网(2013-3-12)[2017-4-17]. http://news.hexun.com/2013-03-12/151951261.html.
[7] 赵淑钰.该如何监管Uber式共享经济?[J].民主与法制周刊,2016(7):50-51.
[8] 李少威.网约车新政,谁的胜利?[J].南风窗,2017(2):26-27.
[9] 朱若淼,唐云路.网约车今天被管起来了,这会影响什么?[EB/OL].好奇心日报(2016-11-01)[2017-02-25].http://www.qdaily.com/articles/33957.html.
[10] 支树平.“重审批轻监管”转向“宽准入严监管”[EB/OL].中国网(2015-01-18)[2017-04-17].http://finance.china.com.cn/news/20150118/2912343.shtml.
[11] 李雅琦,张枭翔.网约车新政遇地方监管考验[EB/OL].澎湃新闻网(2016-08-05)[2017-04-17].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08629.
[12] 陈圣禹.打滴滴遭遇天价车费 5公里花了1700多元[N].北京晚报,2016-08-24(A08).
[13] 林家怡.30元任意跑 “滴滴代叫”真坑人[N].北京晚报,2016-08-02(6).
[14] 陈薇.11月起,网约车按营运车投保?[N].河南商报,2016-08-18(B03).
[15] (英)克里斯托弗·胡德.监管政府[M].陈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ON THE MARKET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VE LAWOF ONLINE CAR-HAILING SERVICE
TAN Bo
(School of Law, 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 technolog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y will lead to the birth of the new market, and the supervising of the new market is actually the upgrading of the old supervising, thus there is the need to deal with the new legislative situation and to meet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he rule of law. The repositioning of the regulation of “online car-hailing service” can be combined with the traditional supervision theory and modern legislation and analyz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ew legislative classification. The regulation first begins with the major categories of admittance supervision and follow-up supervision, and then goes further to the analysis of general regulation, collaborative supervision, credit regulation and risk management, constantly summarizing experience, improving the regulatory standards and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of regulators as well.
market; supervision; administrative law
2017-02-25
2016年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重大项目(2016-YYZD-06)
谭波(1979-),男,河南商丘人,博士后,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1673-1751(2017)04-0022-07
D912.1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