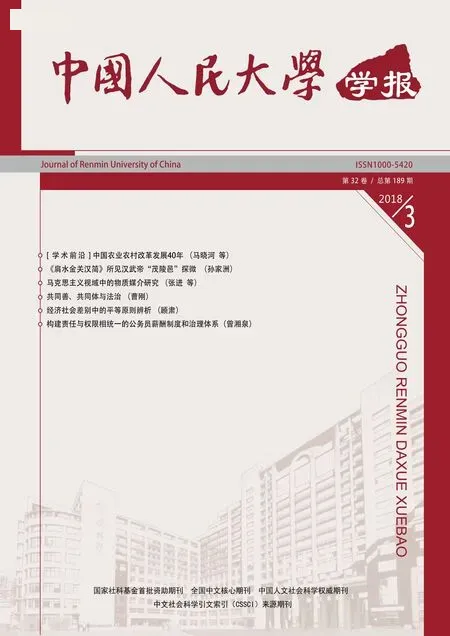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视角:“事实”何以推出“价值”
杨 松
事实判断何以能够推出价值判断?这是哲学家休谟留给后世学者苦苦思索的诸多难题之一。很多分析哲学家从语言分析的角度来探索事实判断推出价值判断的逻辑可能性,产生了不少真知灼见。但是,单靠语言分析难以解释语义与逻辑的来源,需要回归生活实践,回归到马克思主义那里去。笔者拟通过考察人们创造价值、确认价值和最终形成价值判断的具体历史过程,并在每一个环节厘清“事实”与“价值”的关系,从而说明在今天,人们何以能够合逻辑地直接从事实判断推出价值判断。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一次尝试。
一、生产活动中的“事实”与“价值”
在马克思看来,“价值”有两个含义:其一,作为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它表示凝聚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通过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的。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价值”。其二,哲学意义上的“价值”。20世纪80年代以来,李德顺、李连科、王玉樑等学者对马克思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做了深入的研究,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研究的重要基础。近几十年来,马克思在哲学意义上谈论的“价值”已经成为国内价值哲学界熟知的概念。那么马克思在哲学意义上讨论的“价值”是什么含义呢?
在马克思早期的著作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其对价值现象的描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我们都知道,“美”是一种价值,为什么在忧心忡忡的穷人那里,景色却没有“美”这种价值存在呢?这是因为“穷人”的需要不是“审美”,而是“生存”,因此他是以生存需要而不是审美需要来指向事物的,只有能够以合乎生存需要的方式与他发生关系的事物,才会成为他需要的对象,从而会被称为是有价值的。同样,“商人”的需要是“谋利”,矿物之所以对他而言是有价值的,也仅仅是因为矿物能够满足他的这一需要。可见,不管是穷人还是商人,其实都是以自己的“需要”去理解事物,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主动地指向事物,最终根据事物是否能够满足需要,因而以是否“满足需要的对象”来决定它究竟是否具有价值。
通过进一步的文本考察,国内学界比较广泛地注意到马克思关于“价值”一词历史起源的研究,这一段话尤其引起学者们的注意:“《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一书的作者、贝利和其他人指出,‘value,valeur’这两个词表示物的一种属性。的确,它们最初无非是表示物对于人的使用价值,表示物的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使用价值表示物和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而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2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根据原文编者的注释,“value”“valeur”两个词的意思都是“价值”。马克思认为,一方面,“价值”最初表示的就是物对人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使用价值”实际上就是表示物和人之间的关系,即物为人的存在。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就需要知道,这个“使用价值”表示的是物为人的什么方面的存在。很显然,当马克思回答说“使用价值”表示“物对人有用”时,他实际上就是在说“使用价值”表示物可以用于满足人的需要,因此这里的“物为人的存在”实际上就是说物为人的需要的存在。可见,马克思主义确实将“人的需要”与“价值”联系了起来。*但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使用价值”并不就等于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它仅仅是“价值”的一种具体形态。参见李德顺:《价值论》,22-2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正是在上述考察的基础上,学者们形成了关于马克思哲学意义上的“价值”的一种共识,即价值表示的是客体的存在、属性、变化等对于主体的内在尺度(即人的需要)的相符合、相一致的性质和程度。*李德顺:《价值论》,7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但是,“价值”是事物固有的属性吗?它是天然形成的吗?答案是否定的,“价值”主要形成于人类的社会实践特别是生产劳动中,而也正是在此过程中,“事实”与“价值”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关联。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第一个历史活动的论述表明,人类满足需要的活动乃是一切历史的开端。人们通过实践,特别是通过生产劳动来实际地创造、获取实物以满足需要。在生产实践中,人们力图获得的就是那些原本在他之外却经由生产劳动而变为能够满足需要的、因而是有价值的物,在此过程中,人们对外发生三重关系:
第一,他必须对作为自己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自然物有所认识,使得原来在他之外的自然物成为进入认识领域中的对象,进而把握自然物的性质、运动规律等,在此过程中人与对象发生的是“认识关系”。而在这一关系中,关于“事实”的认识不是纯粹中立的,它总是伴随着价值因素的缠绕,这是因为:生产劳动要能够进行,就必须在劳动的同时对自然界的各种事物有所认识,即形成关于“事实”的认知,否则劳动就无法顺利进行。可见,“事实认识”是为了满足“实践”的需要而在“实践”中进行的。这样,“事实认识”就内在地成为“实践”“劳动”的一部分,也是在“实践需要”的推动下而从事的人类活动的一种,从这个意义上说,“事实认识”以及“事实判断”的形成本身就已经是受到价值取向推动的活动。进一步说,“实践”是在人的需要的推动下,以满足需要为目的的活动,而“事实认识”又是为了这种活动而服务的,因此“事实认识”就不仅仅只是为了“实践”而存在,根本上是为满足人的需要服务的。这样,总结起来说就是:“事实认识”以满足实践需要为直接目的、以满足人的自身根本需要为最终目的,因而也是有价值特征的活动。
在“价值物”的形成过程中,并不是与人无涉的客观“事实”作为历史的前提,在先的是人的需要,即某种价值取向(或称“内在尺度”)。在需要的推动下产生了人的实践,而关于“事实”的认识和“实践”几乎是同时展开的——人们在认识“事实”的同时进行着“实践”,也在“实践”中认识“事实”从而形成事实判断。从历史现实来说,在创造价值物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并不是先有关于事物“是什么”的事实认识,然后从事实践活动并且判断事物是否具有“价值”,反而先有的是人们“需要什么”的价值诉求,并在致力于满足价值诉求的实践活动中,同时也进行着关于事物事实性质的认识。可见,就“事实认识”来看,“它属于主体对客体对象的本质联系的反映,这种反映也不能脱离明确的或潜在的价值目标的影响。因此,认识过程中的不同阶段都存在着与该阶段相适应的价值关系”*陶富源:《关于价值、人的价值的几个问题》,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6)。。
第二,在对自然物认识的同时,人也依据自己的需要将其从“自在之物”改造成“为我之物”,力图创造出有价值的产品,从而与自然物之间实际地发生改造关系,获得的是同时兼具“事实”和“价值”两种属性的产品。在改造关系中,人们则是要根据自己认识的结果和需要,开展生产劳动——利用自然界已有的劳动资料,通过自己的劳动力,将劳动对象按照自己的需要发生“为我”的改变,从而使之成为能够满足需要的产品。马克思通过“两个尺度”的思想来表达上述观点,他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马克思认为:一方面,人以自己的需要为实践的内在尺度,对自然物按照“为我”的方式来改造,这就要求生产劳动具有合目的性;另一方面,人们要依靠对自然物的变革进行生产,而自然物不会按照人的希望随意发生变化,因为自然物还有自己的性质、运动规律,这些都是事物自身具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必然性,也是人们实践的外在尺度。在比较初级的劳动中,人们只有不断尝试和重复,才会逐步明白自己的行为必须顺应自然物本身的规律,从而使得生产劳动具有合规律性。而在比较成熟的生产劳动中,人们会对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性质、规律等有清楚的认识,并以之指导实践,从而顺利达到实践目的。因此,结合上面的“两个尺度”来看,人对自然物的改造,最终是以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为基本特征的实践活动,是根据对事物的性质和规律的认识,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为目的,将自然物改造为满足需要的物的过程。正是因为生产劳动是人类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所以获得的是既包含“事实”,又包含“价值”的产品。
第三,人们在实践中不仅要与自然发生关系,而且还要尝试着以某种方式结合起来行动,从而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人们的历史活动不仅包括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生产,即进行生产物质资料的实践,而且还包括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产,即进行社会交往。而在社会活动中,人们的需要往往指的是安全、有序、高效、顺畅等等利益,而行为之有价值则在于对这些人们共同利益的维护或者实现。例如,为了实现财产的有序转移,要求人们必须以特定的方式来处理彼此之间的财产关系,而究竟是使用“口头约定”还是“书面契约”的形式,则根据人们在不同物品交换的场合下具体实践的结果来确定。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入,无论是“口头约定”还是“书面契约”,其具体形式、操作手段和应该注意的细节,都处处以“财产的有序转移”为目标,并在具体情况下改变自己的内容,也都在人们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获得了自己丰富的形态。
所以,当人们说一个社会行为是“有价值”的时候,一方面不是指行为本身天然地具有“价值”,另一方面也不是指人们首先要认识关于行为的事实特征,然后才能得出其是有价值的结论。只有当人们通过这种方式行动起来并达成特定的利益目标时,人们才会得出结论说这种方式的行为是有价值的。可见,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各类行为在根本上是为了实践的需要,从而也是为了人们自身“需要”而产生的,因此本身已经是具有价值维度的“属人”的行为。在实际活动中,如果通过这种方式的行为,人们获得了满足需要的从而是有价值的劳动产品或者达成了既定的社会目标,那么该行为就最终获得了所谓的“价值”。可见,行为的价值也是从人的需要开始,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的,而且并不是它们先具有某些事实特征而后才有“价值”,而是人们先带着“价值取向”(即内在尺度)以一定的方式去行动,而该行为在成为某种“事实”的同时,也成为“有价值的行为”。
二、消费活动中的“事实”与“价值”
人们通过劳动获得了产品,那么这些产品何以能够被称为是有价值的呢?事实上,人们是通过对这些劳动产品进行“消费”来确认其是否真的满足了自己的需要,从而得出这些产品是否具有价值的判断。如果没有人的“消费”,那么这些实践成果仅仅是出于人的“需要”推动而制造出来、具有某种潜在价值的东西,但是这时“价值”并没有实现,因为它尚未与人发生实际的满足与被满足的关系,因而也尚未成为与人的需要发生关系的对象。只有当它被用于消费、与人的需要发生关系时,才能够真正成为面向人的需要的对象。如果它在被消费的过程中确实满足了需要,那么人们就会说这些产品是满足需要的有价值的产品,这时产品的“价值”就真正实现了,并且人们也会得出“该产品有价值”的判断。反之,如果在消费的过程中,人们发现这些产品并不能满足需要,那么就会认为它们是没有价值的,从而得出“该产品没有价值”的判断。
如果说,在生产过程中总是表现出“事实”与“价值”的缠绕,那么从“事实”推出“价值”的做法实际上是在消费产品的过程中初步呈现的。当人们“消费”劳动产品的时候,首先会对劳动产品的感性特征有进一步的认识,并将之作为对劳动产品进行评价的基础。当然,人们实际从事生产劳动时,已经逐步地获得了关于产品各种特征的认识。例如,他们在采摘果实时已经对果实的颜色、形状等有了基本认知,但这并不能帮助他们全面了解该果实是否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只有通过实际地“消费”这些果实,获得关于这些果实特征的进一步认识,以此为基础才可能知道这些果实是否满足需要、是否有价值。例如,当人们在尝试吃果实的时候,就获得了关于果实的进一步认识——是甜的还是酸的,是否多汁、是否有果香、口感如何等,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说这个果实是否有价值。因此,马克思说:“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但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空中的。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可见,人们通过“消费”一开始就会对劳动产品的属性有进一步的认识,如果发现劳动产品的某些属性对人是有用的,即劳动产品因为具有某些属性而可以满足人的需要,那么人们就会说该产品是有价值的。
那么,劳动产品怎样就是有用的,即满足人的需要的呢?事实上,在对劳动产品的消费中,人们不仅获得了关于其属性的进一步认识,而且能够形成正向或者负向的感受,人们正是据此形成关于产品的价值认识。人在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在感受上是一种负面的、痛苦的状态。在生产劳动之后,在使用这些产品时,如果人们能够从负面的、痛苦的感受中解脱出来,获得正面的、愉悦的感受,那么也就意味着人们的需要得到了满足。例如,人们有“吃”的需要,感受到“饥饿”,这是一种痛苦的感受,在这种需要的刺激下,人们从事采集果实的劳动,获得各种果实。为了确认这些果实是不是真的能够满足需要因而是有价值的东西,人们就要实际地品尝这些果实。当人们吃到一些果实,发现它们能够充饥、香甜可口的同时,原来那种“饥饿”的负面、痛苦的感受也会消失,随之产生的是一种“饱足”“满意”等正面的、愉悦的感受。这样,人们就会据此说,因为该果实具有能够充饥、香甜可口等属性而使自己觉得满意,所以它是有价值的。相反,有的果实可能会酸涩甚至会有毒,当人们品尝它们的时候,会产生“恶心”“疼”等负面感受,因此人们就会根据这类感受认为,具有酸涩、毒性的果实是没有价值的东西。可见,在历史的早期,人们是在消费的过程中,通过自己的感觉器官尝试各种劳动产品,在自己的感受体验中,确认具有何种属性的产品是有价值的、具有何种属性的产品是没有价值的。
人们在对劳动产品进行尝试的时候,产生正面或者负面感受的同时,常常还会引起对事物的“情感”。“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人的需要的一种体验。”*李连科:《哲学价值论》,6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当人们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正面的、愉悦的感受常常还会导致人们产生对劳动产品积极、正面的情感,因而表现出对具有某些属性的产品的赞赏、喜爱。相反,若是产品没有满足需要,那么负面、痛苦的感受就会导致人们对具有某些属性的劳动产品产生消极的情感,因而表现出对具有该种属性的产品的批判、厌恶。因此,人们关于事物的感情与事物是否能够满足需要有关,“情绪因需要的满足与否而具有肯定或否定的性质,它成为人的需要是否获得满足的一个指标”*。可见,人们关于事物的情感不是任意产生的。“同需要毫无关系的事物,人对它是无所谓情感的;只有那种与需要有关的事物,才能引起人的情绪和情感。而且,依人的需要是否获得满足,情绪和情感具有肯定和否定的性质。凡是能满足需要的事物,会引起肯定性质的体验,如快乐、满意、爱等;凡不能满足人的渴求的事物,或与人的意向相违背的事物,则会引起否定性质的体验,如愤怒、哀怨、憎恨等。情绪和情感的独特性质正是由于这些需要、渴求或意向所决定的。”*曹日昌:《普通心理学》,342、341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所以,“价值”往往是与人们喜恶的情感相生相随的。
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根据消费情况对某些特定的事物、行为总是会有特定的情感,而随着这一过程的重复,人们逐渐在“价值”和“情感”“态度”等主观要素之间建立联系,即便脱离了实践,这种联系依然保留在观念中。特别是随着价值观的教育世代展开,不仅关于事物、行为是否有价值的观念固定下来成为一种价值知识,而且人们即便没有通过实践,也会建立“价值”与“情感”之间的稳固联系,甚至还学会用价值判断来表达这种情感或者引导人们去从事那些有助于获取价值物的行为。这样,人们就会逐渐忘记,价值物和关于价值物的情感诞生于实践活动,反而认为事物的价值是由人们的情感、意愿决定的。对此,马克思早有预见,他说:“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也就是说,人们(特别是脱离实践活动的思想家)会逐渐认为,自己不是出于需要并通过实践创造价值物,而是出于某种情感来决定事物的价值和行为规范,因此他们就会把主观要素而不是人的实践活动和客观需要视为价值的来源,这正道出了价值情感主义理论的来源。
此外,当人们通过消费发现,某些产品能给自己带来满意的感受,从而判断其是满足需要的产品时,往往还会考察、总结自己为了生产这种有价值的产品而从事的生产实践活动。如果人们发现,正是通过具有如此这般事实性特征的生产活动,他们才会获得这些有价值的产品,那么他们就会认为能够产生这种产品的生产实践活动本身也是有价值的。例如在北宋时期,人们需要大量的“铜”来造币,因为采用“胆铜法”(通过铁来置换含有铜离子的胆矾溶液)可以非常廉价、简易地制取“铜”这种有价值的产品,当时的人们认为,这种生产技术也是有价值的,所以在北宋年间,使用“胆铜法”制取“铜”的铜场大量存在。*胡维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纲:技术卷》,113-114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可见,如果按照某种生产方式从事的人对自然的改造活动,能够总是比较高效、安全、稳定地获取有价值的产品,那么它往往会成为人们普遍遵循的技术规范。*曹志平、徐梦秋:《论技术规范的形成》,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在社会实践中,“消费”体现为对社会目标实现后带来的利益的“享有”。人与人之间按照特定的方式结合起来从事生产实践活动,如果获得的成果也是可以通过人们实际地“享有”相应的社会利益而被确认是有价值的,那么人们往往也会确认,按照那些特定的方式结合起来从事的行为也是有价值的,也会由此逐步衍生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规范。例如,通过“书面契约”的形式能够有效地帮助人们实现对财产有序转移的利益的享有,那么该形式就具有社会意义上的价值。而“口头契约”虽然具有便利的特点,但是在维权问题上存在困难,难以帮助人们享有相应的利益,因此在实践中价值相对较小。
三、一般性的价值判断的形成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已经明确,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人类不是先有关于事物“是什么”的事实认识,然后根据这些事实认识来判断事物是否具有价值。相反的是,人们先有的是“需要”,即某种价值取向。人们在这种取向的推动下从事生产实践,在实践的过程中既获得关于产品的事实认识,又获得按照人的目的创造出来的、“为人”的产品,因此这个产品本身就是既具有事实属性又含有价值属性的物。而关于产品以及生产产品的行为是否具有价值的最终判断则是在消费产品的过程中确认的。
在人类认识能力和实践水平还不高的历史早期,或者是在对某类产品进行从无到有的创造过程中,人们是如何得出产品或者行为是否具有价值的结论的?现实的人具有意识能力,在长期、反复的实践过程中,其思维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因此逐步能够将实践中各种个别情况概括、归纳起来,形成一般性认识,并且能够使用语言将这些一般认识记录、表达出来,最终使得人们不必通过实践和消费而直接得出关于某些事物或者行为的价值判断。
在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水平还比较低的时期,生产劳动常常是尝试性的,获得的劳动产品也并不一定总是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这就要求人们在不断地尝试和摸索中,通过生产和消费获得各类产品是否具有价值的实例。马克思认为,随着人们反复地为了需要而生产劳动,并且通过消费来确认产品的价值,久而久之就会发现,特定方式的劳动获得的产品总是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由于这一过程的重复,这些物能使人们‘满足需要’这一属性,就铭记在他们的头脑中了,人和野兽也就学会‘从理论上’把能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同一切其他的外界物区别开来”*。在历史早期,人类也许只是反复生产一种产品,因此总是通过同一种劳动方式生产并且消费同一种产品,但是“在进一步发展的一定水平上,在人们的需要和人们借以获得满足的活动形式增加了,同时又进一步发展了以后,人们就对这些根据经验已经同其他外界物区别开来的外界物,按照类别给以各个名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这就是说,随着人的需要的类别越来越多,通过劳动获得的满足各类需要的劳动产品也越来越多,人们开始将这些劳动产品进行分类,通过使用语言命名的方式将不同种类的产品一一区别开来。此外,随着各类经验活动的重复,人们发现并非所有的东西都能够满足需要,有的总是可以满足需要,有的却不能,因此人们通过对一般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在不必实际地“消费”每一个产品的情况下,借助语言将满足需要的物和不满足需要的物区别开来,直接称某些物是“满足需要的物”或者是“有价值的物”,等等。因此,这就导致现在看起来似乎很多关于产品是否有价值的判断的形成,并不需要人们实际地“消费”产品。例如医生就会根据经验,在病人没有实际地使用药品之前,就直接告诉他这是好药、那是不好的药。“但是这种语言上的名称,只是作为概念反映出那种通过不断重复的活动变成经验的东西,也就是反映出,一定的外界物是为了满足已经生活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的人{这是从存在语言这一点必然得出的假设}的需要服务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马克思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反复地从事生产劳动以获取满足需要的产品的过程中,人们的认识能力和实践水平开始提高,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也极大地发展起来,从而在不断重复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某类事物是可以满足需要的、有价值的,并且通过使用语言下判断的方式将事物具有的“可满足”“有价值”的特征固定下来,因此人们就不必总是需要通过实际去“生产”和“消费”产品才能判断其是否真的具有价值。
但是,这只是人们在经验中通过不断重复的活动(生产、消费)总结出来的一般结论,并不表明这些产品先天地就具有“可满足需要”“价值”这些属性,“他们赋予物以有用的性质,好像这种有用性是物本身所固有的,虽然羊未必想得到,它的‘有用’性之一,是可作人的食物”*。如果没有人们长期的经验活动,没有对产品长期“消费”得到的结果作为依据,人们就既无法得出产品是否具有价值的一般结论,也无法在不从事生产、消费的情况下直接说某些事物是有价值的。因此,马克思总结说:“可见:人们实际上首先是占有外界物作为满足自己本身需要的资料,如此等等;然后人们也在语言上把它们叫做它们在实际经验中对人们来说已经是这样的东西,即满足自己需要的资料,使人们得到‘满足’的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不仅关于产品有无价值的一般结论是来自人们对长期经验活动的总结,而且关于行为价值的一般性结论也是如此。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从事生产劳动,就要以特定的方式结合起来行动,因此对个人的行为有特定的要求,以保证人们获得“通过生产消费品以满足需要”的利益。这样,“行为”也有能否满足“人们获得自身利益”这一需要的分别,因此它也可以被分为是有价值的行为或者是没有价值的行为。当人们通过反复的劳动、实践发现,只有用这种特定的方式来行动才能保护“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2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的时候,就“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2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这也就是说,当人们重复以某种方式进行生产并获得了相应的有价值的物的时候,就会产生将与这种生产有关的各类行为概括起来形成通则的需要,因此人们通过感性、理性的能力,从对各种个别行为的认识中总结出一般的行为准则,并使用语言将这些行为规定下来,这就直接导致习俗、礼仪、法律、道德等各类社会规范文本的产生。可见,在人类需要的推动下,“人类群体为维持生存延续在自己行为活动中所形成累积了一套规范、法则、秩序, 经由历史和教育积淀在个体心灵中, 并通由物质化的外壳即语言表现之”*李泽厚:《关于〈有关伦理学的答问〉的补充说明(2008)》,载《哲学动态》,2009(11)。。同样,这些规范规定的行为并非天然具有“价值”,而只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实际地从事某一行为并发现它总是可以帮助人们实现利益,从而确认这种方式的行为总是有价值的,此后才通过意识能力将这些反复出现的一般情况归纳总结,再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称它是有“价值的”“正当的”“应该的”行为。
就“价值”问题而言,人们首先是有了需要以及为了满足需要而从事生产实践,再通过“消费”来确认产品是否真的是有价值的。关于事物“是什么”的事实认知,并不先于人们的“需要”以及实践活动,而是在创造价值和确认价值的过程中同步进行的。只是通过这一现实过程的反复,人们才认识到具有某种事实特征的事物总是满足需要的,因而也是有价值的,然后将这种关系通过意识能力概括归纳起来,形成从事实判断到价值判断的过渡——因为事物具有事实特征A,所以具有价值特征B。这种概括一开始也许只是尝试性的,但是随着实践的进行,人们不断地通过创造产品、消费产品的活动来对这一概括进行检验,对之进行修正或者证实,逐渐地“因为事物具有事实特征A,所以具有价值特征B”就变成一种固定的观念而深入人心,并且通过教育代代相传,成为人们熟知的、习以为常的知识、标准乃至说话方式。这一过程最终导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可以很方便地从事实判断直接推出价值判断。
所以,从“事实”到“价值”推导的实现,我们固然可以从语言逻辑的角度进行分析,但是需要明确的是,语言逻辑其实只是人类生产实践的产物。来自生活世界的问题,还是应该到生活世界中去解决。在今天,人们在生活中从事实判断到价值判断的过渡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人已经是这么做的,并且鲜有人在实践中认为这一言说方式是不合理的,甚至也没有意识到其在逻辑上存在什么问题,这是因为“人的实践经过亿万次的重复,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式固定下来。这些式正是(而且只是)由于亿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列宁全集》,第55卷,1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可见,人们之所以可以从“事实”推出“价值”,从根本上说是源于通过劳动创造价值、通过消费确认价值,通过语言形成价值判断的历史实践过程,只有在长期的实践积累中,人们才最终能够实现从事实判断到价值判断的直接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