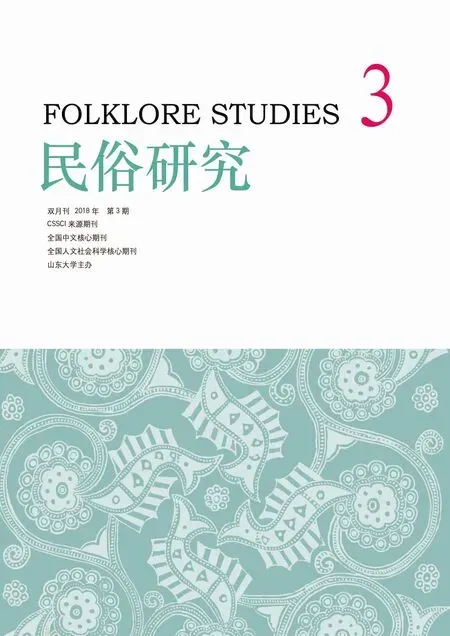“大闹”与“伏魔”:《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的禳灾结构
李永平
“张四姐大闹东京”故事意蕴深厚,流传久远,在长期的演述中,文本种类繁多,其中包括多种宝卷文本。《中国宝卷总目》著录该宝卷嘉庆、同治、光绪、民国版本总计35种,编号分别是1083和1566。《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又名《张四姐宝卷》)《摇钱树宝卷》《仙女宝卷》《月宫宝卷》、《天仙宝卷》(又名《天仙四姐宝卷》《斗法宝卷》《天仙女宝卷》《张四姐宝卷》《杨呼捉姐宝卷》),笔者统计在《中国宝卷总目》著录的存世宝卷版本数量上,位居前10位。
根据故事情节,我们把《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分为六个段落。
(1)仁宗朝,崔家家道中落,崔文瑞与母亲靠乞讨度日。
(2)玉帝第四女张四姐下凡,与秀才崔文瑞(原是天上金童)结为夫妻,张四姐利用仙术帮崔文瑞母子重归富有。
(3)员外王半城见崔家财宝和崔妻张四姐的美色后起异心,定计谋,设圈套栽赃陷害崔文瑞,企图霸占张四姐。
(4)为了解救被拘押的丈夫,张四姐与呼家将、杨家将几番大战,大闹东京,打败包公。
(5)包公用照妖镜去擒妖,前往地府阎王殿、西天、玉帝等处查访,最后在斗牛宫中查访得知是王母的四女儿下凡人间。
(6)玉帝大怒,派遣天兵天将、哪吒、孙悟空前往擒拿不得。崔文瑞原是老君殿上仙童,一家三人都被玉帝召回天宫。
六个段落中,第(3)(4)(5)部分才是故事的关键部分。本文拟从“表述的动力”角度,探讨该故事在表演过程中的“演述动力”,认为口头传统中,该故事的演述动力来源于文化文本的禳灾结构。
一、“大闹”与“伏魔”
为什么张四姐大闹东京故事,能够在民间以包括宝卷在内的各种文本长期流传,并形成复杂的演述版本?其演述的动力来源是什么?容世诚分析迎神赛社戏剧《关云长大破蚩尤》等傩戏时认为《破蚩尤》和安徽贵池《关公斩妖》没有多大区别,该剧的演出“实际上是在戏台上重演一次古代傩祭中方相氏驱鬼逐疫的仪式”,“围绕着叙事结构和演出象征吉祥/不幸、平安/艰难,以致更根本的生命/死亡等对立观念,构成一个意义网络,在整个驱邪的仪式场合里产生意义,最后通过戏剧仪式的演出,除煞主祭降服或者斩杀背负所有不详和凶咎的恶煞,象征性地消解以上对立。”*容世诚:《关公戏的驱邪意义》,《戏曲人类学初探:仪式、剧场与社群》,广西师范大学些出版社,2003年,第22-23页。笔者认为,“张四姐大闹东京”故事的多种文本的演述动力同样源于该故事包含的原型结构,其动力装置是“大闹”“伏魔”禳灾。远古以来,真实或想象的自然灾害、瘟疫、猛兽侵袭,导致集体性恐惧和存在意义上的焦虑,受迫害的想象和记忆由此转为采取集体行动的预防性书写或仪式性“干预”。这些最古老的经验形成“大闹”和“伏魔”的主题,转化为村落社会重要的民俗仪式或禁忌,做会宣卷只是仪式活动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宝卷故事只是民间信仰做会仪式中的演述部分。包含大闹-审判-伏魔原型结构的文学,只是“大闹-伏魔”原型的一部分,而包含该文化原型的仪式分布广泛。如果要追溯“大闹”-“伏魔”原型结构的来源,无疑要上溯到中国本土的禳灾祭祀民俗仪式源头“张天师降五毒”、“五鬼闹判”。*钟馗斩鬼最早的记载见于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奉敕为皇太子于灵应观写的《太上洞渊神咒经》,而该经最初的十卷成书时间约在陈隋之际。敦煌写本标号为伯2444的《太上洞渊神咒经·斩鬼第七》关于钟馗是这样写的:“今何鬼来病主人,主人今危厄,太上遣力士、赤卒,杀鬼之众万亿,孔子执刀,武王缚之,钟馗打杀(刹)得,便付之辟邪。”而另一篇标号为伯2569中写道:“驱傩之法,自昔轩辕,钟馗白泽,统领居(仙)先。怪禽异兽,九尾通天。总向我皇境内,呈祥并在新年。”钟馗不但负责打杀恶鬼,更具辟邪功能,钟馗的名字画像、打鬼都具辟邪“效果”。
神话观念支配意识行为和叙述表达的规则。人们认为,五毒是侵害人类的灾异,五月初五端午节被人们认为是“九毒”之首,民间便流传了许多驱邪、消毒和避疫的习俗。驱“五毒”成为端午节的民俗仪式的核心目的。《燕京岁时记》称:“每至端阳,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画天师钟馗之像,或绘画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售之。都人争相购买,粘之中门,以避祟恶。”*[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天师符》,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5页。至今,凤翔镇宅辟邪木板节令画中,还有《张天师降五毒》的题材。*凤翔县非遗中心编《凤翔木板年画》,陕内资图批字2014年第CB07号,第35页。在民间文学中,天师被视为法力高超,驱邪禳灾的职业术师,能够帮助人间芸芸众生渡厄禳灾。
“五毒妨人”,人想方设法镇压“五毒”以禳灾,这一观念逐渐演化为“五鬼”大闹人间,判官捉鬼、杀鬼、斩鬼伏魔的原型结构和文化传统,贯穿于剪纸“剪毒图”、年画“五毒图”、佩饰“五毒兜”、饮食“五毒饼”“炒五毒”等民俗事象和傩戏等文化文本之中。宋代以前有《五鬼闹判》,元代杂剧有《神奴儿大闹开封府》,明代有小说《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据目前所知,《五鼠闹东京》存世有两个版本:1.广州明文萃堂本《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四卷,今藏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2.柳存仁发现的英国博物院藏本,清代“书林”刻本《五鼠闹东京包公收妖传》二卷。参见潘建国《海内孤本明刊〈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小说考》《文学遗产》2008年第5期。从故事题材来看,《五鼠闹东京包公收妖传》故事经历过两次重大的改变,第一次是受到明代公案小说的影响,增入了包公判案情节。第二次是在清代中后期,受到侠义公案说唱及小说的影响,“五鼠”形象由精怪蜕变为侠客,而正是因为与不同时期流行小说的不断结合,“五鼠闹东京”故事才拥有如此绵长的生命力。《决戮五鼠闹东京》(《包龙图判百家公案》第58回),晚清有狭义公案小说《五鼠闹东京包公收妖传》。
明代的驱傩仪式中,也需要演述大闹-审判-伏魔故事。1986年,在山西潞城县南舍村发现了明万历二年(1574年)手抄本《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该抄本“毕月乌”项下录有供盏队戏《鞭打黄痨鬼》剧*《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中华戏曲》第3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鞭打黄痨鬼》是山西上党地区祭祀二十八宿时于神庙前演出的戏剧,它在赛社祭祀中只是祭祀仪式剧,表演时走上街头逐疫祛祟,成为热闹异常的大戏。
今天这种民俗仪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活态地保留在山西、山东等地。其中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赵康镇赵雄村的傩舞表演“花腔鼓”中有“五鬼闹判”仪式剧。王潞伟对此专门做过田野调查:五鬼闹判上街演出时,由五个被冤枉的小鬼和一个判官共六人组合而成。五个小鬼在戏弄判官时,步伐必须是蹦蹦跳跳。判官在行进中表演时没有规定的步伐,在五鬼闹判戏耍时,他一会儿手摇铃铛向五鬼示威,一会儿双手翻阅生死簿,寻找被冤枉屈死的名单。*王潞伟:《山西襄汾赵雄“花腔鼓”调查报告》,《中华戏曲》第40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戏剧由固定程式组成:“五鬼”大闹判官,判官与五鬼程式化的周旋之后,象征性的审判并斩杀“五鬼”,恢复人间的秩序。
明杂剧《庆丰年五鬼闹钟馗》,第四折钟馗有“一桩驱邪断怪的无价宝,助国家万年荣耀”,钟馗在五鬼头上放“三个神爆仗”,“爆仗声高”,“五鬼唬倒”,“将黎民灾祸消”,除了辟邪之外,钟馗也带来了新年的祝福。最后钟馗逐鬼、捉鬼,“刳其目,然后擘而啖之”*王季烈:《庆丰年五鬼闹钟馗》涵芬楼藏版,《孤本元明杂剧》30,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明末戏曲理论批评家徐复祚在《傩》一文中又云:“然亦有可取者,作群鬼狰狞跳梁,各据一隅,以呈其凶悍。而张真人世称天师出,登坛作法,步罡书符捏诀,冀以摄之,而群鬼愈肆,真人计穷,旋为所凭附,昏昏若酒梦欲死。须臾,钟馗出,群鬼一见辟易,抱头四窜,乞死不暇。馗一一收之,而真人始苏,是则可见真人之无术,不足重也。”*见翁斌孙抄本《花当阁笔谈》,引自徐复祚:《曲论》,《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240页。《兰宝太监西洋记》第九十回“灵曜府五鬼闹判”,出现国殇后,冥府中受苦的五鬼,哄闹判官。后世五鬼闹钟馗之“五鬼”又演变为包公故事《五鼠闹东京》中的“五鼠”。这与包公死后成为五殿阎王,往来三界降妖除魔的民间流行观念有关。
清代宫廷一直上演端午节应节戏——《斩五毒》(又名《混元盒》)。清廷每逢端午,必召“内廷供奉”进宫演出《斩五毒》。述五毒聚妖闹事,张天师降伏众妖,收于混元宝盒内。联系脉望馆抄校本《孤本元明杂剧》中《关云长大破蚩尤》《灌口二郎斩蛟》《太乙仙夜断桃符记》中的大闹-审判-伏魔的仪式性情节,其中的中间环节就是“审判”。《关云长大破蚩尤》最后一折关云长正末唱:“仗天兵驱神鬼下丹霄。今日个敕苍生除邪祟万民安乐。震天轰霹雳。卷地起风涛。金鼓铎获。剿除尽那虚耗。”剧中“将那造孽蚩尤拿住了”、“将孽畜紧拴缚了”,令“今日一郡黎民安乐,四时和雨顺风调”,证实该剧源于驱除邪祟仪式所遗留的痕迹。*《关云长大破蚩尤》,王季烈《孤本元明杂剧》第8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第9-10页。
“大闹”—“审判”—“伏魔”是村落社会长期形成的原型结构,同一结构,不同文本空间,不同形式相互吸收转化,彼此牵连,交错相通,各种版本的《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只是文化文本中的一类。正因为故事结构的“审判”禳灾功能,所以被编为各种剧本,例如通剧《张四姐闹东京》、洪山戏《张四姐大闹东京》、京剧《摇钱树》、桂剧《四仙姑下凡》、河北梆子《端花》、弋腔《摆花张四姐》、黄梅戏《张四姐下凡》、莆仙戏《张四姐下凡》、花鼓戏《四姐下凡》、皮影戏《张四姐》,在陕西“张四姐闹东京”故事则以陕南孝歌《张四姐下凡》的形式流传。
二、禳灾与洁净的跨文化文本
社会不是平面单调的,而是多声部的构成,在文学文本之外存在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多样逻辑,可以说“大闹”“伏魔”这个民俗事象源自于远古宗教仪式和过渡礼仪中祓禊污染时冗长而又热烈的仪式,在一代代仪式演述和集体记忆之中,散落为各种文化文本。在不同时代,伏魔禳灾的结构主体从方相氏到钟馗,再到关羽、包公,不断地发生位移。
道格拉斯研究表明,远古以来,人们通过建立分类体系,来确定污染的来源和危险所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民俗禁忌和律法。人们相信危险来源于道德伦理上的“过错”,通过分类“他们会区分有序和无序、内部和外部、洁净和不洁净”,边界的含混不清,反常的情形等都是不洁的、危险的、污秽的。*[英]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黄剑波,柳博赟,卢忱译,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3页。那些分类体系所无法穷尽的边缘、剩余、中间或过渡状态,往往是问题所在,甚至是“污染”和“危险”的渊薮,而“异类通常与危险和污染相联系”*[挪威]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董薇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10-311页。。“异类”或反常之物,由于触犯或逸出社会认知及文化分类的底线,多数被视为“暧昧”、“不纯”、“污秽”、“生涩”或“危险”的存在。*周星:《汉文化中人的“生涩”“夹生”与“成熟”》,《民俗研究》,2015年第3期。一个文化对人和民俗事项的分类往往内含着道德评价,人们往往会在内部寻找那些被“污染”了的存在或外部邪恶势力的代理人,试图驱逐或至少使它们边缘化,从而维系社区或体系内部的“净化”状态。*[美]杰里·D·穆尔:《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欧阳敏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00页。
处于“过渡期”(transition)或转换期(transformation)的人不仅是危险的,他还向周围环境释放污染。从人类学角度看,《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第三个板块王半城见崔家财宝和崔妻张四姐的美色,顿起异心,定计谋,设圈套栽赃陷害崔文瑞。崔文瑞衔冤对村落社会是危险的、不洁的。从仪式展演角度,正邪之间的对抗——“大闹”,正是这一阈限场域的仪式性书写,是“热闹”的内在结构。中国文化传统以“闹”(大闹、热闹)等活动渡过危险,闹因此也成为具有净化禳解功能的阈限阶段,只有“大闹”“热闹”才能渡过重重“关煞”,“焐热”重组生存环境。如前文所述,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赵康镇傩舞表演“花腔鼓”“五鬼闹判”这个节目一年一度在村落的搬演,主要突出一个“闹”字,“闹”是有冤要喊,有屈要申。*王潞伟:《山西襄汾赵雄“花腔鼓”调查报告》,《中华戏曲》第40辑,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人类学家范热内普认为,人的出生礼、成年礼、结婚礼、丧葬礼等“生命周期仪式”,其结构由前阈限阶段(分离期)、阈限阶段(转型期)以及后阈限阶段(重整期)组成。“转型”状态位于前后两个阶段之间的阈限期,个人处在悬而未决的状态,既不再属于从前所属的社会,也尚未重新整合融入该社会。阈限状态是一个不稳定的边缘区域,其模糊期的特征表现为低调、出世、考验、性别模糊以及共睦态。
中国文化传统解决阈限危险的方法是做会,通过“热闹”重组环境以祈福纳吉。江浙一带的“做会”仪式过程中要宣讲相应的宝卷,宣卷先生因此担任做会的执事。在“圣灵降临的叙述”中,焚香点烛请神佛,然后开始宣讲宝卷。结束时要焚烧神码(供奉的神像)等物送神佛。中间还要应斋主(做会的人家)之请,穿插拜寿、破血湖、顺(禳)星、拜斗、过关、结缘、散花、解结等禳灾祈福仪式。
婴儿的孕育是家族重要的阈限阶段,在江苏省常熟尚湖、福建莆田,为了预防不孕、流产或者是婴儿夭折,要举行“斋天狗”仪式。在江苏常熟要宣讲《目莲宝卷》及《狐仙宝卷》,在福建莆田则要举行红头法事“驱邪押煞”。法事仪式中,陈靖姑装扮法官,红布缠头,召集五方兵马降妖伏魔,与抢吃胎息的天河圣母和天狼天狗进行激烈地仪式性打斗,演出活动热闹异常。*[日]田仲一成:《中国戏剧在道教佛教仪式的基础上产生的途径》,《人文中国学报》第14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页。
民国11年(1922)《新无锡报》报导了前洲镇祠山庙会的盛况,“是日,殿上之老叟、妇女坐夜者约两千余人”,“时至薄暮,已经三殿满座,鼓声、锣声、唱曲声、宣卷声,喧闹震天,镇村万人空巷”*前洲镇志编纂委员会编:《前洲镇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33页。。无锡的佛头宣卷做佛事大都集中在每年正月和六、七月两季。正月里斋主请“做寿”,“请财神”,给孩子“开关”;六、七月里“大家佛”兴。
流传至今的伏魔仪式突出特点是以“大闹”“格斗”等为内涵的热闹氛围。世界范围内大都表现为大闹热闹等仪式场景。弗雷泽《金枝》第56章专门列举了流传广泛的公众驱赶妖魔的民俗仪式。新喀里多尼亚的土人相信一切邪恶都是一个力量强大的恶魔造成的,所以,为了不受他的干扰,他们时常挖一个大坑,全族人聚在坑的周围。他们在坑边咒骂了恶魔之后,就把坑用土填起来,一面踩坑顶,一面大喊,他们把这叫做埋妖精。*[英]J.G.弗雷泽《金枝》,汪培基,徐育新,张泽石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854页。在新年的头一天,即圣西尔维斯特节,波希米亚的男孩子都带着枪,围成一圈,向空中开火三次“射妖”,人们认为这会把女妖吓跑。圣诞节到主显节恢复之间的十二天或“第十二夜”,欧洲许多地方把这一天选作驱逐妖魔的恰当的日子。如在卢塞恩湖上的鲁伦村,男孩子们在“第十二夜”列队游行,打着火把,吹着号角,敲着铃铛、鞭子等等造成一片闹声,吓走两个树林的女妖斯特鲁黛里和斯特拉特里。人们认为如果他们闹得不够响,那年就不会有什么收成。又如法国南部的拉布鲁及埃地方,人们在“第十二日”的头一天晚上沿街跑,摇着铃,敲着壶,用各种方法造成一片喧闹声,然后借着火把和燃烧着的柴堆的光亮,他们大喊大叫,几乎把耳朵震破,希望用这种办法从镇上赶走一切游荡的鬼魂和妖邪。*[英]J.G.弗雷泽《金枝》,汪培基,徐育新,张泽石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869-871页。
在人生的主要转折点,在天时运行的重要节令,中国人都要热闹,闹元宵、闹社火、闹洞房。只有经过大闹才能渡过阈限阶段,拆除“爆炸物”的危险引线。闹对应的颜色是“红”,日子要过得红红火火,在婚庆期间,张灯结彩,挂满红灯笼,贴满红对联,穿上红衣裳,要闹洞房,各地民间至今流传着“越闹越喜”“越吵越好”“越闹越发,不闹不发”或“不闹不安宁(辟邪)”“不闹不热闹”等说辞。*谢国先:《走出伊甸园——性与民俗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3-55页。人生礼仪和节庆期间是大闹的最为灵验的时刻。
伏魔的仪式性民俗活动,积淀为热闹红火的社会审美心理,贯穿在各种文化文本之中。宋元话本有《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元代杂剧有《神奴儿大闹开封府》,明代有小说《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红楼梦》有《赵姨娘大闹怡红院》《王熙凤大闹宁国府》,晚清有狭义公案小说《五鼠闹东京》。《水浒传》中多处有“大闹”情节:“鲁智深大闹野猪林”“大闹桃花村”、“大闹五台山”“郓哥大闹授官厅”“武松大闹飞云浦”“花荣大闹清风寨”“镇三山大闹青州道”“病关索大闹翠屏山”“李逵元夜闹东京”等。联系《水浒传》第一回“洪太尉误走妖魔”中洪太尉大闹伏魔殿的情节就会发现,这些“大闹”是“天罡地煞(妖魔)闹东京”的神话观念的程式性演述。不同民族神话中都有降妖伏魔母题*王宪昭:《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395-1399页。。
文学原型只是文化原型的折射,“大闹”、“热闹”更多地表现为民俗仪式活动,过去每逢除夕、元宵等岁时节日,方相氏、僮子(由村民装扮)与无形的超验世界(鬼疫之属)冲突激烈,热闹非凡。由此,我们不难想象以“驱鬼逐疫”为宗旨的大型戏剧队伍在火炬的照耀下,在威猛的锣鼓和呐喊的人声中展演的浩大声势。
传统社会的灵验时间,要周而复始的演述古老的“大闹-审判-斩妖”仪式,以此达到净化的目的。安徽贵池的《钟馗捉小鬼》,钟馗戴青黑色面具,驼背鸡胸,手拿宝剑,身挂“彩钱”,小鬼则戴鬼面具。舞蹈以锣鼓为节,先是钟馗用宝剑指向小鬼,小鬼不断作揖求饶,钟馗恃威自傲,小鬼卑躬屈膝,二者形成鲜明对比。不久小鬼伺机夺过钟馗手中的剑,钟馗反而向小鬼求饶。最后,钟馗急中生智,夺回宝剑,将小鬼斩杀。尽管表演注入了世情因素,但表演的基本情节还是降妖伏魔与“斩鬼”。
元代以后,大闹-审判的主角主要集中在包公身上,原因是包公吸附了从方相氏到钟馗、阎王等角色功能。*李永平:《祭祀仪式与包公形象的演变》,《中华戏曲》第48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农村祭奠孤魂野鬼的习俗兼有“普度”与“判刑”两面,其中审判戏就是“鬼魂上诉”、包公受理控告、“审问鬼魂”(鬼魂诉冤)、“超度鬼魂”等阶段,展示了当时流传的审判孤魂野鬼的习俗。*[日]田仲一成:《中国祭祀戏剧研究》,布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9页。
三、《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的演述动力
把版本众多的《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还原到文化文本的结构网络中,方能窥见其中“大闹”的互文结构和禳灾内涵。村落传统中民间叙事的活力来自于远古以来的禳灾的精神传统。从表层上看,《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大闹”型故事与“伏魔”型故事的捏合形态。在“蒙冤—反抗—伏魔—昭雪”禳灾民俗仪式的演述中,重复的是“祓禊—洗冤”结构模型,它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类型性原型结构。原型结构的形成与人类自远古以来形成的巨大心理能量有关:不仅汲取凝聚,薪尽火传,而且是受集体无意识左右的一个自主情节的形成过程。原型在心理内核上仅是一些倾向和形式,它要获得实现就必需赖以现存的相应社会现实和情景。
道格拉斯认为,“仪式通过运用反常的象征将恶与死亡整合到生与善中去,最终组成了一个单一、宏大而又统一的模式”。*[英]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黄剑波、柳博赟、卢忱译,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50页。反复出现在古典作品中的大闹—伏魔结构,和降龙、伏虎结构一样,早就超越了一般的模仿和偶然的巧合。远古以来,人为的污染(失祀、冤狱、罪孽)导致秩序混乱,人不得不洗冤,搜寻替罪羊,祭祀禳灾,祈求上苍宽宥,使天理昭昭,以销释或者转移污染,恢复洁净。
从孔子时代就已经流行的古傩礼俗,从不同语言的宗教文献,到近代还在展演的目连戏和香山宝卷的演述传统,本身就是这种宗教性净化仪式的一部分。回鹘文木刻本《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刻本第三栏是回鹘文(划分为三栏,第一栏是图像,第二栏是梵文和藏文),附汉文佛偈如下:
敬礼手按大地母,以足践踏作镇压,
现颦眉面作吽声,能破七险镇降伏。
敬礼安隐柔善母,涅槃寂灭最乐境,
莎诃命种以相应,善能消灭大灾祸。*[日]高楠顺次郎等:《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6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年,第478-479页。
宝卷《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卷首韵文:
四姐宝卷才展开,王母娘娘降临来。天龙八部生欢喜,保佑大众永无灾。
善男信女两边排,听在耳中记在怀。各位若依此卷行,多做好事少凶心。
做了好事人人爱,做了坏事火焚身。作了一本开颜卷,留于(与)世上众人听。*方步和:《河西宝卷真本校注》,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25页。
两者相比,我们似乎觉察到,宗教仪式的实施,民间宗教信仰文献的展演,一年一度的节庆仪式,其背后共同的信仰活力源于他们“能破七险镇降伏”、“保佑大众永无灾”的功能和促使功能发挥效用的教化。
民间信仰中,人们将远古以来镇压邪魔的集体诉求“箭垛式”地背负到历史人物包公身上,他既能“日断阳、夜断阴”,能下地狱、上天宫,四处查访。贪财贪色的王半城制造冤狱,崔文瑞无辜蒙冤入狱,狱吏屈打成招,制造冤狱,必然招致灾异。为了洗冤,张四姐和包公成了张力结构的核心,一位持天界法物“大闹”东京,一位用照妖镜、赴阴床降妖伏魔:
有包公,听此言,心中暗想;命王朝,和马汉,急急前行。
抬铜铡,竖刀枪,甚是分明;又带上,照妖镜,去捉妖精。
桃木枷,柳木棍,神鬼皆怕;刀斧手,铜铡手,紧紧随跟。
一时间,就到了,崔府门前;叫一声,快捉拿,四姐妖精。
吓得那,一家人,胆战心惊;张四姐,听此言,冷笑一声。
却说众士卒逃回,吓得仁宗皇帝无计可施,忙派包公到天波府再搬救兵。太君两眼流泪说:“我杨家为了宋氏江山,不知死了多少儿郎,待我前去捉拿妖精,为国除害。”包公心中大喜:“有杨家女将出阵捉妖,必定成功,我且回南城府中。”*徐永成:《金张掖民间宝卷》(一),甘肃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53-54页。
包公在童子戏等傩戏中担当沟通人神、逐疫、辟邪镇宅、镇魂等角色,因之具有“神人相通”的巫师的法力。无论是《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五回描写李瓶儿死后的吊丧说唱《五鬼闹判》《张天师着鬼迷》《钟馗戏小鬼》《六贼闹弥陀》《天王降地水火风》《洞宾飞剑斩黄龙》《赵太祖千里送荆娘》*(明)兰陵笑笑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齐鲁书社,1989年,第104页。,还是贵池傩戏演出《舞伞》《打赤鸟》《五星齐会》《拜年》《先生教学》等小戏,最后一场必演出《关公斩妖》,和《关公斩妖》结构一致的即是民间信仰中的大闹、伏魔与审判。
细读《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包公下地狱上天庭四处查访,找到了导致污染的因由。《包公错断颜查散》宝卷中,“尸首不倒”这一细节在多种《包公错断颜查散》版本中惊人的一致,它不仅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情节,而且清楚地表明,宝卷展演活动具有超度冤魂,恢复洁净的宗教社会功能。因为,“尸首不倒”必有过错,这一关键性细节可以说是民族的集体认知传统所预设的。诸如此类的民间故事要素属于整个口头说唱传统,它们既可以出现于一般的故事情节当中,也可以出现于那些功能性的傩戏或仪式剧之中,其传统地位并非取决于纯粹的叙事性和戏剧性价值。
与《关公斩妖》等仪式剧不同的是,《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中,包公在查访伏魔的过程中,对张四姐的身份的查访(审判),擒妖除祟,使四姐重返仙藉,并度脱了凡男崔文瑞。容世诚认为这是中国宗教仪式剧的重要环节,和目连戏中的《刘氏逃棚》《捉寒林》、“关公戏”、《关公斩妖》《关大王破蚩尤》一样,呈现了大体一致的除煞禳灾母题,隐藏了《周礼》《后汉书》所描绘的傩祭仪式的表演原型。*容世诚:《扮仙戏的除煞与祈福》,容世诚:《戏曲人类学初探:仪式、剧场与社群》,广西师范大学些出版社,2003年,第124页。
文学批评家经常论述中国故事、戏剧的大团圆结构。对于口头传统中的结构程式,田仲一成的戏剧发生理论或许能启发我们:活态故事和戏剧表演背后,是“蒙冤—反抗(大闹)—伏魔(审判)”的倒U原型结构。这一结构表面上是民间心理需要,深层是远古以来累积而成的审美心理结构,它在故事表演中表现为“祭中有戏,戏中有祭”的演述活力与动力。过去仅仅从文学文本中,寻找这一神话观念的根源,如今看来,这些都是文字书写小传统的产物,真正的神话观念都根植于伏魔、除祟与禳灾传统。
故事千锤百炼的演述套路和跌宕起伏的戏剧性,背后的动力源于这种结构背后的功能性和无限生成转化性的禳灾传统,这是一种“永恒存在”的结构模型。民间故事讲述、传统仪式剧表演、宗教祭祀文献中的颂赞性韵文,与此类传统(套路)整体上以交感巫术心理“相似律”和“接触律”相契合。神话、传说、仪式、展演、口传叙事、物的叙事、文字典籍等文化文本,对人类文化生成、发展动态过程的予以整体呈现。追踪连接仪式、展演、口传叙事等文化文本背后的历史心性,才能明白文学人类学人与物(事)的互动,事中循理,物中悟道,是凝固文化记忆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