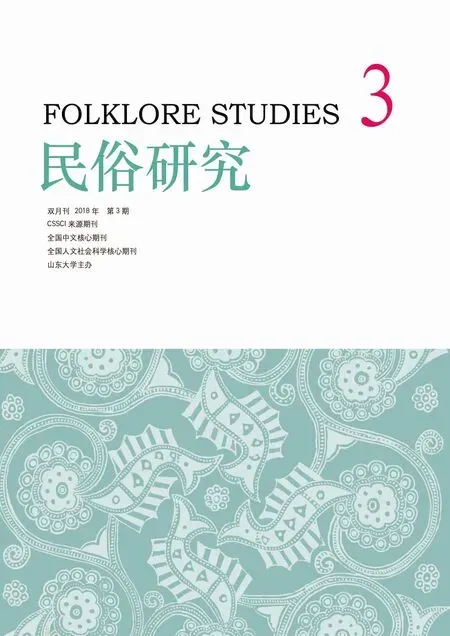仪式实践与榉村的社会整合
何 明 杨开院
一、绪 论
滇西地区作为中国社会族群结构最复杂的地区之一,其多元而独特的文化传统成为各族群和谐共生的最重要因素。在苛刻的地理环境下,各族群为获得更好的生存机会组成了共同的村落,并利用自然神灵信仰、仪式管理体系等方式维持着村落的认同。同时,各族群内部利用自身的文化体系,如祖先信仰维系着族群认同。在滇西社会的多元文化体系下,这两种认同始终和谐相存,贯穿于整部族群关系史,消解着族群冲突和矛盾,实现社会整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新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环境对传统的多族群村庄内部秩序带来了挑战。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文明之间如何实现平衡成为了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鉴于此,探讨多族群村落内部传统的整合机制及其功能的议题也就显得十分紧迫。同时,该议题探索了传统文化和社会整合的关系,对当代和谐社会建设具有一定的促进意义。
(一)“仪式与社会整合”研究回顾
仪式与社会整合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中的经典命题。学理上,仪式通常被界定为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是特定群体强化秩序以及社会整合的方式*参见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而社会整合则是“人与人、人与群体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联结关系,这种联结关系既可以建立在共有的情感体验、共有的道德情操和共同理想信念之上,也可以建立在因为生活所需求、功能依赖而形成的相互依存关系上”*刘少杰:《国外社会学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8页。。作为社会整合理论的集大成者,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详尽表述了宗教、仪式以及社会整合之间的密切联系。例如,他认为宗教是“表达集体实在的集体表现”*[法]爱弥儿·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1页。,是一种时间、空间、心灵构成的观念和感情的集合。而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之中产生的行为方式,它们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法]爱弥儿·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1页。。涂尔干认为,宗教和仪式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在包括宗教在内的集体意识产生的过程中,人们通过仪式加强了个体对于集体的归属关系。将个体的微弱力量与集体的强大力量相联系,从而达到凝聚和强化集体力量,达到团结社会的效果,这个过程就是集体实现社会整合的途径。基于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结构-功能论者更多地从仪式的“功能”“结构”视角出发,探讨仪式对于个体生命和社会结构稳定的“效用”。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仪式具有多种形式,各有不同的功能,如入世仪式的主要作用是“极其有效地延传部落的风俗信仰,以使传统不失,团体固结”*[英]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李安宅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3页。。这是原始部落利用仪式实现社会整合功能的手段。特纳从象征结构视角出发,认为“仪式的举行,不但可以解决社会文化内部原有的矛盾,更可以吸纳外来不同的力量,调节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冲突”*黄应贵:《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关照、理论与实践》,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58页。。同时,“仪式象征结构在不同社会文化脉络中实践,往往会结合其他社会文化要素而产生变化。”*黄应贵:《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关照、理论与实践》,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60页。范盖·內普认为过渡仪式存在分离—过渡—聚合三个阶段,这是过渡仪式的一般规则,这一规则对于克服危机,重建社会秩序起到很大的作用。柯林斯从“仪式互动”的视角出发,认为人们可以通过仪式互动而形成一个“链”,这个链是群体和社会共同体形成的纽带,仪式的“链”作用实现了社会整合。*参见[英]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林聚任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很明显,柯林斯的仪式链分析视角与涂尔干的社会整合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仪式之“链”正是集体意识之结,它们相同的功能在于使分散的个体适时而自发地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情感上或行动上的整体。国内的仪式与社会整合研究大多集中于对涂尔干社会整合理论的个案诠释和分析之上。丁宏通过对麦加城朝觐者的心理研究,认为仪式在增强民族凝聚力上具有重要作用。彭兆荣认为“仪式作为社会认同与社会动员的方式,既可以有整合、强固功能,又可能具有瓦解、分化作用”*彭兆荣:《人类学研究仪式评述》,《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张良从仪式空间视角对乡村社会整合进行了论述,认为仪式中的“各个程序、礼节都蕴含着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道德伦理,仪式的展示无论对于参与其中的人还是对于旁观者,都具有规训、警示作用”*张良:《乡村公共空间的衰败与重建——兼论乡村社会整合》,《学习与实践》2013年第10期。。当然,也有学者就仪式对社会整合的正向促进作用提出了质疑和挑战。陈彬、陈德强以湘东仙人庙为研究个案,对仪式促进社会整合理论进行了检验。两位学者认为社会整合属于抽象概念,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社会整合应该由情感整合和行为整合组成。普遍意义上的信仰认同并不等于情感整合,也不能直接导致行动的整合。该视角对我们重新思考社会整合理论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在不断变化的外部条件刺激下,仪式本身不再是一个稳定不变的文化载体,其中的整合模式自然会发生改变。本文试图运用仪式与社会整合的研究范式,分析榉村清明节和端午节期间不同祭祀仪式所产生的社会功能,进而探讨不同姓氏族群的“边界”以及文化认同机制。
(二)田野调查地介绍
榉村是滇西横断山脉上的自然村,隶属于云南省施甸县,距县城60公里。全村220人,共47户。按传统父系继嗣,榉村是汉人双姓村,有张杨两姓,其中张姓12户,杨姓35户。村民以农业为主,主要种植玉米、小麦、豆类和水稻。同时兼有猪、黄牛、水牛的饲养,为食物和畜力的主要来源。有可耕种土地494亩,其中旱地434亩,水田60亩。人均土地占有量为2.28亩。这个数字是加上1995年以后人们自由开荒土地所得,事实上,在1982年以前,即实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以前,榉村全部的承包土地仅有120多亩。作为典型的历史移民区,类似于榉村的复姓多宗族村落在滇西一带十分常见。把榉村选作田野研究点是因为该村张、杨两姓至今保存族谱、碑记或口头叙事资料,具有较为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据张姓保存的地契显示,榉村的张姓宗族最初于道光四(1824)年买下榉村北面的山坡,后便定居于此,形成一个大宗族。据杨姓家谱记载,榉村杨姓分两拨从60公里外的祖地迁入榉村,大致时间范围分别在张家买山后五十年至一百年间。两拨杨姓同属于一个大宗族,先迁入的一支与后迁入的一支因为血缘疏远,因此各成为两个家门(即“房支”)。迁居后,为共同抵抗周边的狼豹等野兽,张杨两个宗族基本上采取聚族而居的居住方式(现在,村庄还保留着破败繁杂的大型四合院)。因为自然条件恶劣,人口发展十分缓慢,据村庄80岁以上老人回忆,至20世纪30年代,榉村尚未超过15户。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榉村从最初的一姓一户、聚族而居变成了现在两姓杂居的中小型村落。尽管每个家门规模都在不断扩大,村落内部三家门格局仍然牢不可破,族群边界依旧清晰。
这一村落格局和族群边界是如何被保留并维持至今的呢?经过深入的调查,笔者发现存在于村民内心深处的“认同感”是主导因素,这里的认同不仅指自我宗族身份的认同,还指由村落的“地方感”共识而产生的地域认同。190年前,定居榉村的张杨两个宗族因为离祖籍地较远,无法回到各自的宗族祠堂祭祀祖先,自然也无法得到祖先的庇佑。在无力新建祠堂的困境下,人们开始把心灵寄托转向祖坟地和自然神灵。祖先和自然神成为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祭祀对象。无论是祖先祭祀还是自然神祭祀,烧猪(猪被宰杀后,用松枝等将其猪皮烧成黄色,用以祭祀神灵)都是最为重要的牺牲。祭祀完毕,所有参与祭祀的村民平均分食,与神灵共享盛宴。在近两百年的历史过程中,村民们不断演绎和重构着这两项仪式,村落的秩序被持续整合着。
二、榉村宗族秩序的整合仪式
宗族秩序的整合仪式指宗族祭祀仪式。“宗族秩序”指宗族内部以血缘世系为轴心的尊卑次序,这是一套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父系继嗣体系。在宗族内部,每一个人因为所属的世系不同而拥有不同的地位和亲属结构。在宗族祭祀仪式中,每个人(在世的人)的世系将会被重新强调。仪式轮值、族人聚会、均分祭品等活动强化了同宗共祖的认同意识,宗族内部的秩序得以整合。
宗族祭祀仪式在每年的清明节当天举行。这是当地同姓宗族的集体性活动,要求全族参与。宗族内部每户当头一年,负责准备香钱果品,组织祭祀仪式以及主持分肉仪式。参与祭祀的族人各户携带祭品,一起祭坟,不仅要祭飨自己家庭的近祖,还要祭飨全族的远祖。
杨姓的宗族祭祀仪式。杨姓的祭祖活动分为两支,一支为先迁入榉村的杨姓后代,他们在村后的杨家祖坟进行,我们且将这一支系称为“杨姓第一支系”;另一支至今与祖居地共享一片祖坟地,因此每年必须回到3公里外的罗村参加祭祖活动,且将其称为“杨姓第二支系”。迁到榉村后的100多年里,凡第二支系的老人过世,必须将棺木抬回罗村祖坟地安葬。所以从血缘上来看,榉村杨姓第二支系与罗村的关系更近,与村内第一支系的关系更远。事实上,严格以代际来计算,两个支系血缘相隔已经超过10代。
杨姓第一支系共25户,人手充足,组织仪式较为容易。25户人家每2户当头一年,每6户组成一个当班小组,协助当头户处理仪式事务,具体的轮值次序和名单记录在账本上。这一账本作为杨姓宗族内部事务管理文书,除记录清明祭祖仪式轮值次序、当班次序、轮值和当班名单外,还明确记录每年烧猪的重量、价格、每户分肉重量(份子)、每户应缴和实缴的香火钱、每年宗族财务的剩余以及跟下一年当头人家的交接情况。最值得注意的是,该账本还记录着当头人家的权利和义务。据账本记载,当头的两户人家在当年有使用和管理宗族山林的权利,但也要履行好管理祭祖仪式的义务,做好祭祖账目并保管好账本。清明祭祀仪式是宗族内部最隆重的仪式,文革期间曾经一度中止,80年代土地下户以后得到恢复,现在看到的账本就是仪式恢复后的产物。在清明节前5-10天,当头的两户人家需要召集族人召开祭祖仪式准备会议。族内每户派一人或两人参加宗族会议。榉村杨姓没有祠堂,宗族会议一般在当头人家的堂屋进行。这次会议主要商议祭祀仪式用品以及核定本年度的当班人员。上述事宜确定后,当头人家开始着手准备所有祭祀用品,包括用于祭祀的肥猪、香、纸钱、爆竹。最后,当头人家还要请族里的老人写作祭祖祝文。
清明节当天早上8点,当班的6户人家男性成员聚在当头人家,开始宰猪、烧猪、蒸制香火饭。一般来讲,烧猪需要将整头猪烤制成金黄色,香火饭包括三碗香油榨菜、一碗半熟米饭、一只熟鸡蛋、一杯茶和一杯白酒。准备齐全后,当头人和当班人在当头人家吃早饭。饭后,大家在烧猪头部系上红绸,当班的男人们将整头猪绑在竹竿上,抬到后山的祖坟地里,出发和到达目的地都需要鸣炮。当头人家负责将剩余的所有祭祀物品搬运到祖坟地。此时,族人们也携带者香火祭品到坟地集中,平日寂静的山路上顿时热闹起来。烧猪安放于始祖坟前的祭台上,所有祭品置于两侧,坟前的案台左右两边各燃着一支红烛。人们在空地上燃火焚香,在每一座祖先的坟前磕头跪拜、作揖插香。当头人家的男主人将香火饭端到山神(祖坟地的守护神,一般是一棵树或一块石头)前祭拜,一般的祭拜方式是:作揖—燃香、燃纸钱—磕头—献祭品(用手捡祭品的一小部分放在山神前)—燃爆竹。目的是请求山神护佑祖先的家园。凡是来到坟地的族人都必须向每一座坟墓磕头献香,必须向最近的祖先行重礼——三次叩拜。逝者的直系子女认真地清理着坟墓旁边的杂草杂树。如有新近去世的祖先,其亲人会将他的最后遗物或特意送给他的遗物(如鞋袜、衣服)在坟前焚烧。
祭祀完所有坟墓后,当头人招呼大家到先祖坟前听祝文。族里的长者面向始祖坟站立,郑重地拿出祝文,所有族人面向始祖坟整齐地站成一排,听长者的念辞下跪、磕头。整个过程中,坟地庄严肃穆,仅有长者的念唱声音在空旷的土地上回荡。念诵完毕,族人齐向先祖行三叩首礼。礼毕,人们开始分享祭品。当头和当班的人们将烧猪平均分成25份,每一份用事先准备好的竹篾条捆紧。
祭祖祝文模式
时也
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施甸县xx镇xx村为报祖宗恩德特备香烛果品三牲酒礼在杨氏家族宗祖坟墓前叩拜
三叩首
诗曰
清明时节家家忙,怀念宗祖上坟场,祖坟前面来叩拜,冢冢坟前桌满香,祖宗恩德年年报,祖宗保佑子孙世代昌。
十五代杨xx,杨xx,xx;十六代杨xxx;十七代杨xx(所有家族在世的家族成员姓名)。
礼毕,家族子孙叩首,叩首,三叩首。
起。
礼毕,人们领着“份子”肉回家,离开之前务必再到祖先的坟前磕头,诚挚邀请他们一起回家过节。离开坟地时每人拿一支点燃的香,据说这是引路香,祖先会随着香火的灰烬找到回家的路。回到家后,把尚未燃尽的香插在厨房的灶台旁。妇女用糯米粉制作糕点,这是清明节的主食;用豌豆淀粉制作豆粉,和烧熟的猪皮一起凉拌,作成凉拌菜。晚饭后,族人聚集到当头人家里“凑香火钱”,即每一户人家应当支付的祭品的价格。本届当头人和下一届的当头人一起负责记录支出和结余。完成后,账本交到下一届当头人手中,这一年的清明节祭祖仪式结束。
杨姓第二支系族人在清明节当天前往罗村,参加完罗村的祭祖仪式后,再拎着分到的烧猪肉回家。因为路程较远,榉村杨姓二支系不参与罗村的仪式轮值。
张姓的宗族祭祀仪式。张姓宗族的祖坟地位于距离村子20公里的山坡上,徒步来回差不多需要一天时间,所以张姓的祭祖活动被分成了两部分:清明节前一天家族成员到坟地进行上坟活动,带一些轻便的祭品进行祭祀;清明节当天进行在村里烧猪祭祀,家族成员聚餐。张家因为人数少,没有专门的宗族事务账本。
上述三个家门的祭祖仪式存在着相同的环节,即宗族成员团聚。杨姓两个家门的团聚时空合一,即清明节当天的祖坟地;张姓宗族因为自然条件的限制,没有将团聚的时间和空间合一,但其中的祭祖仪式表现形式却是一致的。祖先祭祀都以祖先的栖息地为仪式场所,祭祀都以献牲、敬礼、族人团聚、分食祭品为主要形式。这样的宗族仪式所体现的社会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在家族成员聚会过程中,村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家族团结、和谐和亲近的氛围。在祖先墓前集体跪拜、听祝文、诵姓名,村民从中感受到的是从祖宗到子孙后代绵延的历史感,自己在宗族中的位置也会得到重新确认。钱杭认为,汉族宗族内源性来自于宗族组织的实践体验,这种体验“不仅是宗教的、信仰的和非理性的满足,更重要的是世俗的、体现了历史感的、理性的满足”*钱杭:《论汉人宗族的内源性根据》,《史林》1995年第3期。。非理性和理性的满足背后却是族群边界的设定,族群边界是族群成员资格的标准(一种或数种)。巴斯认为族群特定的分类格局和价值取向一旦出现了自我实现的特征,在互动中展现自我族群的标志,那么,族群边界就会出现并且得到有效的维持。*[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主编:《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李丽琴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0-22页。个案中,三个家门不同的祖先祭祀地点就是自我族群的标志,祖坟地点表明三个家门属于不同的血缘群体,而血缘便是家门最显著的边界。边界内的人们以祖先祭祀仪式表达着自我的族群认同,然而,边界之外仍然存在着促进族群交流、融合的有效机制,那就是村落共同体。
三、村落共同体秩序的整合仪式
村落共同体秩序的整合仪式指的是祭祀村寨神灵的仪式。所谓“共同体”(关系)指的是“社会行动的指向——不论在个例、平均或纯粹类型中——建立在参与者主观感受到的互相隶属性上,不论情感性的或传统性的”*[德]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顾忠华译,马克斯·韦伯:《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康乐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6页。。“村落共同体秩序”指每一个人、每一户村民在村庄内部的位置。如果说村落是一张大网,那么作为次级共同体的三家门便是网络的三角支柱,个体的家户就是遍布其中的网络的节点。村民对村落共同体的认同通过寨神祭祀仪式体现出来。
历史上,榉村一年里需要举行三次村落祭祀,分别是农历二月初二的“祭龙王”,农历五月初五的“祭平安神”,农历六月二十三的“祭山神”。这些神灵之身被村民赋予在一些长寿健壮的树木上:村北有百年树龄的栎树是平安神的化身;旁边的大山楂树是山神的化身;村北两公里外的山泉眼是龙王的藏身之所。后来村民在山楂树下修建了山神庙,将山神、龙王爷、土地神三位神仙供奉于其中。村民们不论姓氏和宗族,每户人家当头一年,负责主持本年度的三次祭祀。二月初二烧猪祭龙,当头人家招呼每户一人(成年男性)在村口的平地上烧猪。此外,每户另安排一人参与村北面饮用水沟的清理工作以及村集体水井的清洗工作。烧黄的猪肉与米饭、茶、酒、香、纸一起在山神庙前供奉祭拜,请求龙王爷保佑村寨水渠永不干涸。完毕,男人们在山神庙前与神共进一餐,猪血炒嫩蚕豆、豌豆作为代表菜品,这顿饭主要食用猪的下水部分。饭后平均分割猪肉,形成均等的“份子”,各人拿份子回家与家人聚餐。五月初五那天杀羊祭祀平安神。榉村不养羊,端午节所需的羊要到外地购买。当头人家负责购买羊和其他祭祀物品,负责请仪式先生念平安经。制作祭品的地点就在平安树下。羊杀死后用火将表皮烧黄,然后以整只羊祭拜。同时在树下的大坪台上念平安经,烧平安纸,目的是保佑村寨平安。仪式完毕,村里的男人们在树下简单食一餐。羊肉平分,各人带回家。羊头不参与分配,交给下一年当头的人家。六月二十五祭山神。在山神庙前烧猪,以整猪和米饭、茶酒、纸钱、香火一起祭祀山神。对“三神”的祭祀表达了村民对赋予村庄生活资源的自然万物的感恩之情。凡举行祭祀的当天,村民忌工在家休养,男人参与杀猪杀羊,女人在家烹饪美味。
文革时祭祀活动被归入封建迷信,“三祭”停办。20世纪80年代传统文化恢复之风盛行,对于要不要恢复“三祭”的问题,村人展开了讨论。经过数次村民大会商讨,最后的决议是将“三祭”合为“一祭”,在每年端午节当天进行。实施方式为:在轮值方式上,延续以前的传统,每户当头一年;在祀品问题上,因为羊很难买到,决议以猪代替羊作为牺牲,祭祀平安神、山神和水神;祭祀后仍然按户数平分猪肉,同时,给下一年当头的人家多分半斤肉;在参与方式上,全村参与,每户一人(男性)参与烧猪。在村民看来,三祭合一的最大优势是节省时间和精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人们在私人时间支配方面有了更多的自由,人们可以按自己的生活水准在过年时多杀一头猪,多存一份肉。此外,市场的开放也为人们提供了额外的肉食获取路径。1991年,榉村举全村之力修通了进村公路,同时修建了钢管水道,翻新了老旧水井,解决了村里的饮水问题。2002年,村人再次召开会议,对端午节祭祀进行了规范:每户当头一年,除去当头人家,以“班”为单位,将村民按户数分为四班,每班8户人家,每班一年轮流烧猪。这样就解决了人手杂乱、偷懒耍滑的现象。2002年后不再到平安树下杀猪,而是到当头的人家去杀猪。猪烧黄后,把猪头、猪脚、猪尾巴、下水和米饭、茶酒、香纸一起端到平安树下和山神庙前祭拜。不再念平安经、烧平安纸。祭祀完毕,村民到当头人家“打份子”(分猪肉)。当班的村民中午在当头人家吃一顿饭,打完份子就回家去。同时,下一届当头的人家可以得到一斤额外的免费猪肉。当头人家负责保管村集体财务和账本、管理维护饮水管道,与下一届当头人家一起清洗村里的水井。
现在,榉村举行的村集体祭祀基本上按2002年决定的形式来进行。端午节前10-15天内,当头人家就要到村长家商议祭祀事宜。商议妥当后,村长打开广播器通知村民召开端午节祭祀会议。开会地点定于本年度当头人的家里。
案例1 2017年的端午节祭祀前村民会议
时间:2017年5月14日 农历4月19日
地点:村民杨SQ家 庭院
参与人员:每户村民派一个代表参加
会议主题:商议清明节杀猪祭祀的具体事宜。
具体内容:(1)决定猪的大小,250斤左右,由当头人杨SQ代表向村民杨ZS家购买;(2)YSQ负责购买香纸火;(3)杀猪时间不变,五月初五当天早上进行;(3)核定2班8户参与烧猪人员;(3)清洗水井。由杨SQ家和下一年当头的张QZ家负责。村长杨CJ认为本来需要淘洗坝头前池和村里的大水井,但最近气温上升,为保证水源,村里的大水井先不清洗,雨季到来再清洗。
案例2 杨SQ口述端午节祭祀情况
我家2015年当头,2班8户每户一人(男性)来参与烧猪。
我们买了四支大香,三个斋菜(花生、土豆、粉丝)、一捆小香。爆竹一份。两对大香平安树和山神树下各一对,斋菜主要放在平安树下。
我和其他人把烧猪猪头、猪脚、猪尾巴、饭气(半熟的米饭)、茶、酒一起端到山神庙、平安树下祭祀,然后放炮。打完份子后给下一家(下一届)多分一斤肉。然后他们来我家结账,将帐目清楚地写在账本上,参与烧猪的八户人家一起把柜子、碗筷、帐篷、乐器等集体财产搬到张QZ家(2016年当头的人家),算是交接清楚了。
从村落祭祀仪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提炼出两部分关键的内容:一是仪式的整合效力和社会对仪式的重构能力;二是族群的相互依赖性。
仪式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的认知,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仪式的表达有着直接的影响,这说明仪式本身是可以被整合的,仪式一方面整合着社会,另一方面也被社会整合着,这无疑是村民在艰难生存过程中探索出来的生活策略。190年前,张杨两姓就建立了和谐的生产互助关系。早期物资匮乏,在“三祭”仪式过程中,人们通过有规律的“同吃”“请吃”活动增加交流机会,增进村邻感情。正如萨林斯所说,“食物因此成为社会交往启动、维系或终结机制的工具。”*[美]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等译,三联书店,2009年,第250页。与此同时,仪式也被社会整合着。经过多次社会运动和经济的变迁,榉村的“三祭”最终浓缩为“一祭”。村民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大家有了更多的自由支配土地,也有了更多的生存选择空间,男性村民农闲季节性务工的现象也逐渐普遍起来,费时费力的“三祭”再也不适合村庄的现状了。改革后的“一祭”既保证了对村庄自然神灵的供奉,又不会打乱村民的生计安排。
榉村是一个多宗族的双姓村,当各宗族的祖先在此相遇时,他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最基本生存问题,还有多族群的社会关系问题。张杨两姓三家门在此共同生活了近两个世纪,每次遇到重大分裂性矛盾时,村庄秩序总能在波涛中重归有序。*具体案例可参见杨开院的《三条路的故事:道路修建与榉村村民个体化过程探析》(未刊稿)。深究原因,矛盾化解靠的就是族群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在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社会体系中,就族群的文化特征来说,联系几个族群的积极纽带取决于他们之间的互补性。这样的互补性可能会导致互相依赖或共生,建立起接合、融合区域。”*[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主编:《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李丽琴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0页。村落的先民们共同开荒拓土,互相传授生产技术;相邻而居,一起抵御野兽和自然灾害;“缔造”出共同的村寨神灵,遵从仪式规约,以受到等价的庇佑。而正是稳定仪式体系,平衡了不同族群之间的社会地位,避免了社会的分裂。
四、结 论
村民对宗族的认同来自于祖先至高无上的权威,具体而言,来自于中国汉人社会传统的宗法思想与孝道精神。清明节祭祖仪式通过对“接香火”的仪式实践,强化了村民的祖先认同,进而扩张到对宗族的认同。马克斯·韦伯将社会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分为三种纯粹类型:传统型权威、个人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廖晓东,陈晔:《中国社会转型期传统权威与现代行政权力的张力分析》,《行政论坛》2012年第4期。其中,传统型权威是指“建立在遗传下来的(历来就存在的)制度和统治权力的神圣的基础之上,并且也被相信是这样的(力量)”*[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在传统的宗法制中,“父权”“父子同一”是家庭的“安全阀”*参见许烺光:《祖荫下:中国乡村社会的亲属、人格和社会流动》,王芃、徐德隆译,南天书局发行,2001年。,这样的传统权威贯穿于宗族历史的始终,并通过规律性的仪式得以确认和维继。通过祖先祭祀仪式,人们得以重新认识宗族边界以及自我的宗族身份,从而建立宗族绵延不断的历史感和自豪感,增强对当下和未来生活的自信。
村寨神灵祭祀仪式的变迁过程既是仪式与社会相互整合的展演过程,也是多族群关系“进化”的历程。“稳定的族群间关系推论出这样一种互动体系:一套规则控制着互动的社会情景,并顾及一些活动领域的融合,从而使得部分文化避免了对抗和修改。”*[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主编:《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李丽琴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8页。更确切地说,共同的仪式信仰有利于族群边界的稳定。
榉村的宗族祭祀仪式和村落祭祀仪式是村民生存智慧的体现。这一村落整合机制也是滇西多族群社会普遍生存模式的缩影。在新型的经济形势和乡村政治管理体系下,这一传统整合模式虽然在形式上有所变化,但其整合效果却是值得肯定的。村民们传统的地域社会认同并没有因为行政地域空间界线的强化而改变,相反,村庄的整合仪式能够重新整合政治因素新出现的地域空间(如村庄合并),实现新的地域认同。如此看来,传统文化实践与现行的政治经济实践并不冲突,在一定程度上,二者能够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社会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