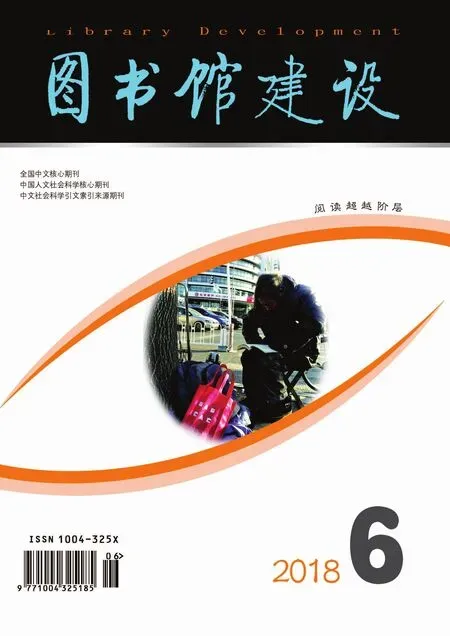文献价值区分与《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批评体系*
温庆新 (扬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2)
1 引 言
所谓文献价值区分,即对文献的知识信息进行价值区分与内涵建构,是指古典书目进行部类设置与作品归并之前,往往会对所收文献进行知识、价值、思想及谱系等方面的预判,以强调书目的部类内涵与所收具体文献皆能切合彼时政教①需求的意义指归与文献排列秩序,最终形成一套既可进行图书整理的技术体系,又隐含文教②所需的知识信念等严谨的分类体系。而文献价值区分的展开途径,主要包含文献书写内容的谱系归并及价值区分、文献生产主体的身份区别两方面。也就是说,古典书目一方面通过文献的现实地位与政教意义来区分文献的价值,另一方面则通过对文献生产主体进行区分以实现区分文献价值的目的。这两种方式,成为《四库全书总目》 (以下简称《总目》)进行文献价值区分的最主要手段。这也是我们以《总目》为中心去探讨古代书目与政治权力之关联性的主要方式。
纵观学界对《总目》学术批评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分类体系、辨伪方式、目录价值、辑佚标准、纂修思想,乃至对某类或某一作品的著录标准、思想内容与价值意义等方面。相关成果已较为充分。同时,学界往往从《总目》的政教意图切入,指出《总目》学术批评体系的建构方式与目的,皆是为实现“正人心而厚风俗”之类的“稽古右文、聿资治理”[1]1的政教意图。不过,即便是探讨《总目》的学术批评方法,亦仅限于纯粹的方法论层面,罕有学者从文献本身特有的知识结构与价值内涵的角度,探讨《总目》的文献观念与分类体系对其建构学术批评体系的影响。尤其是,基于古典书目的价值预设传统与文献价值区分等角度探讨《总目》的学术批评体系,学界几无涉及,而这些却是探讨《总目》的批评体系时无法回避的。
2 古典书目的价值预设与《总目》学术批评的文献原则
古典书目的分类并非简单的知识论存在,而是蕴涵着浓烈人伦彝常的价值论意义。因而,当古典书目通过分类来建构其文献秩序与展现文献的意义时,它并不是简单的形式逻辑区分,亦非纯粹的西方学科体系的科类设置。古典目录每置一种部类,往往有其特殊的文教价值与道德意义的考量。甚至,当不同时期的不同目录学家对同一部类的类名指称及具体书籍归并呈现出不一致的看法时,往往代表不同时期的政教意图及不同目录学家的个人经验,对相关书籍在当时所应当也必须承担的社会“功用”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确立了此类书籍在当时文治教化中的实际地位及其相应的文献价值[2]。故而,古典书目进行部类设置与书籍归并时,往往对所录书籍的价值意义进行了预设,并对所录书籍的实际功用与现实地位也做出了相应限定。
早在汉代,班固《汉书·艺文志》“总序”所言的“每一书已,(刘)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3]437就道出刘向作《七略》时,对其所校录书籍的“指意”与内容已作了提炼与限定;并通过“奏之”的方式,借统治者之口,进行符合彼时政教所需的强化推行。同时,《汉书·艺文志》所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3]1728,“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3]1732,建构了古典书目因不同文献类别而赋予该文献特殊的政教意义的批评方式。这种做法为《汉书·艺文志》及后来的书目所遵行。这就是古典书目“通过组织文献、考辨学术的现实层次,致力于追问文献体系与学术体系背后的政教人伦价值”等“申明大道”传统的具体实践[4]62-63。也就是说,古典书目分类时的价值内涵预设,就已决定书目通过对文献整理、归并及著录来展现文献学术价值的实践方式。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同一类别的书籍进行以时为序的编排,清晰还原该类别书籍在不同时期与不同人群中的接受情形,进而梳理其间的学术衍变脉络。由此而言,古典书目的价值预设,实际上是根据不同时期的文教需求,不断对所录文献的内涵进行规范化识别与诠释。这种预设之举,并非基于严密的科学准则,亦非着眼于诸如形式、逻辑、体态等外部形态。它使得古典书目更加注重文献的文本系统与知识系统背后的意义讨论。
这种对文献价值进行规范表述的方式就是《总目》学术批评的主要原则。所谓文献价值的规范表述,是指古典书目不仅会对部类的内涵与形式做出符合彼时政统③所需的限定与规范,而且强调所录具体文献应该切合当时的政统需求,甚至有意弱化、限定乃至批判具体文献中与彼时政统不合的内容与形式。乾隆曾指出编纂《总目》系为“钞录传观,用光文治”,“俾艺林多士,均得殚见洽闻,以副朕乐育人才、稽古右文之至意”[5]10。可见,清代统治者试图通过编纂《四库全书》,整合“天下”文献,统一思想,甚至借此消除历代典籍所含不利于政权统治的成分,从历史的高度诠释满族入主中原的正统性[6]。同时,清代统治者试图通过政治权力的干预,解构并重构传统经典,使其所重构的经典作品得以成为彼时的思想标杆,最终实现通过文化一统维护自身的统治利益。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总目》对文献价值的内涵与形式,均需做出规范化的表述,以排斥“异端之思”。
首先,对不同书籍所承担的教化作用进行区分。《总目》子部“总序”指出:“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于书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区而列之,名品乃定。……儒家之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录,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其别教则有释家,有道家,叙而次之,凡十四类。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之以兵家。兵,刑类也。唐虞无皋陶,则寇贼奸宄无所禁,必不能风动时雍,故次以法家。民,国之本也;谷,民之天也;故次以农家。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而生死系焉。神农黄帝以圣人为天子,尚亲治之,故次以医家。重民事者先授时,授时本测候,测候本积数,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百家方技,或有益,或无益,而其说久行,理难竟废,故次以术数。游艺亦学问之余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故次以艺术。以上二家,皆小道之可观者也。诗取多识,易称制器,博闻有取,利用攸资,故次以谱录。群言岐出,不名一类,总为荟粹,皆可采摭菁英,故次以杂家。隶事分类,亦杂言也,旧附于子部,今从其例,故次以类书。稗官所述,其事末矣,用广见闻,愈于博弈,故次以小说家。以上四家,皆旁资参考者也。二氏,外学也,故次以释家、道家终焉。”[1]769可见,《总目》对部类的价值区分,先是本于“治世者所有事”的不同作用而区分了儒、兵、法等六家;而后从“游艺亦学问之余事”的角度,区分了术数、艺术等四家。这就是通过文献价值的区分,来实现梳理学术派别与脉络衍变的典型。
其次,通过文献生产主体的区分实现文献价值的区分,从而对不同文献的价值内涵进行合理规范。《总目》从“外学”的角度区分了释家、道家两类文献,强调释道文献之于文治教化的作用有别于儒家、小说家等其他小类。这种做法其实是对文献生产主体进行区分的典型。从某种意义讲,《总目》对儒、兵、农等的区分,首先也是对此类文献的生产主体进行了社会角色的划分与归并,从而达到区分不同文献类别价值的目的。因而,当通过文献生产主体区分实现文献价值区分之后,《总目》既可以此梳理各家的学术源流,并据此进行内涵规范。意即上引的限定“名品”,如上引“小说家”时,强调小说家类的价值指向应与“广见闻”有关。这就通过明确的话语导向,最终达到规范文献价值的意图。
当然,《总目》进行文献价值预设时,必然会对文献的主体价值进行符合彼时政统所需的规范。这是对此前书目价值预设传统的另一承继,如子部“儒家类”小序所言:“古之儒者,立身行己,诵法先王,务以通经适用而已,无敢自命圣贤者。王通教授河汾,始摹拟尼山,递相标榜,此亦世变之渐矣。……自时厥后,天下惟朱陆是争,门户别而朋党起,恩雠报复,蔓延者垂数百年。明之末叶,其祸遂及于宗社。惟好名好胜之私心不能自克,故相激而至是也。圣门设教之意,其果若是乎?今所录者,大旨以濂、洛、关、闽为宗,而依附门墙、藉词卫道者,则仅存其目,金姚江之派,亦不废所长。惟显然以佛语解经者,则斥入杂家。凡以风示儒者,无植党,无近名,无大言而不惭,无空谈而鲜用,则庶几孔孟之正传矣。”[1]769所谓“今所录者,大旨以濂、洛、关、闽为宗”,即是区分文献的生产主体;“无植党,无近名,无大言而不惭,无空谈而鲜用”,即是对“儒家类”文献的价值进行主导性规范的典型。这方面的证据极多,不再一一列举。
综述之,虽然中国古代学术的存在与衍变直接体现为文献记录,然而,以目录、版本、校勘、辑佚为主体内容的文献学面向“天下”文献时,对“天下”文献的辨惑裁定、分类聚合、提要勾玄,表面上看是一种文献的整理,实际上隐含着围绕文献整理而展开学术批评、建构学术脉络的深层次意图[4]115-122。而其中的目录分类,则是文献学建构文献的学术价值与批评思想的主要话语体系,也是重要的表现形式。因而,古典书目的价值预设,就是古代书目进行学术批评的文献原则,而通过文献生产主体的区分实现文献价值区分,则是古典书目建构学术批评体系的最主要方式。
3 《总目》学术批评体系的运行
那么,文献价值区分如何推动《总目》学术批评体系的构建?对《总目》学术批评的话语使用、对象选择与体系运行,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3.1 文献生产主体的归并与《总目》学术批评对象的筛选
《总目》首先通过对文献生产主体进行归并来筛选学术批评对象,以奠定批评体系开展的前提。自刘向《七略》“条其篇目,撮其指意”起,古典书目就包含“目”与“叙”两部分。因此,古典书目不仅要对书籍进行部类归并,更是形成了“部类有小序,书名下有解题”[7]的重要编纂体例与批评方式。《总目》即属此类典型,其总序、部类小序及解题的“叙”说,即是进行文献生产主体区分的主要手段。不过,由于文献价值的展示方式不一、具体文献切合政统所需情形的不同,《总目》对文献生产主体的区分方法与学术批评对象的筛选方式又有多种。
一是,为确立“稽古右文、聿资治理”所需的道统,《总目》强调应充分发挥儒家思想与儒家著述的作用,而后才是兼顾诸子百家中有益于政教者。这从“儒家类”小序即见一斑。《总目》认为“无植党,无近名,无大言而不惭,无空谈而鲜用”,才是儒家的核心特征,也是彼时政统确立的理论指导。而“王通教授河汾,始摹拟尼山,递相标榜”等做法,已改变儒者“立身行己,诵法先王,务以通经适用而已”的本质;后世“以佛语解经者”,更是偏离儒家的原始教义。故而,此类著述或不足以提倡,或置入他类中,从而完成“儒家类”的对象筛选。可以说,子部小类的排列顺序,是《总目》区分不同类别的文献所承担的教化作用与现实地位的典型方式,意即在有利于文治教化、征信考订及启迪人心等方面的作用上,由儒家、兵家到小说家、释家、道家,次序是由重要到次要的递减,且不可变更。推而广之,《总目》经部、史部的小类类名与排序,亦可作此观。
二是,从清代政统的现实出发,《总目》对明人文献区别对待。乾隆曾指出:“明季诸人书集,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列。节经各督抚呈进,并饬馆臣详晰检阅。朕复于进到时亲加披览,觉有不可不为区别甄核者。如钱谦益在明已居大位,又复身事本朝,而金堡、屈大均则又遁迹缁流,均以不能死节,腼颜苟活,乃托名胜国,妄肆狂狺,其人实不足齿,其书岂可复存?自应逐细查明,概行弃,以励臣节而正人心。”[1]4从乾隆的言论看,所谓“词意抵触本朝者”云云,强调“明季诸人”作为文献知识与价值的创作主体,与彼时政统思想的背离。这就是甄别文献生产主体的作者身份以实现文献价值区分的典型。由于这种身份区分,导致《总目》对明人文献多呈鄙薄态势。
三是,从教化功用的角度,对文献进行道与器的区分。除从“治世者所有事”区分儒、兵等六家,从“游艺亦学问之余事”区分术数、艺术等四家之外,另有对西学文献的区分及著录。据考证,《总目》共收录西学著述凡二十七种,存目十三种[8]。这些著述集中于史部“地理类”与子部“天文算法类”“杂家类”中。正如《总目》“凡例”所言:“外国之作,前史罕载,然既归王化,即属外臣,不必分疆绝界。”[1]17所谓“既归王化,即属外臣”,是强调西学文献有助于从“器”的角度为“王化”提供参考。《寰有铨》提要所言“欧逻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1]1081就道出《总目》从“道艺并重”之“艺”的角度肯定西学科技知识,强化“以资参考”的“中体西用”思想。
综述之,《总目》不论是通过禁毁、抽毁、改易、存目、刊刻,抑或是“部序”论说、提要考辨等方式展开对象筛选,皆围绕文献生产主体的归并而展开。而《总目》进行文献生产主体的归并之举,紧紧围绕是否符合彼时政统所需的价值预设原则,加以展开。这就使得《总目》学术批评体系的运行,不可避免要受到其限定文献生产主体介入方式的影响。
3.2 限定文献生产主体的介入方式与《总目》学术批评体系的运行
乾隆三十八年(1773),刘统勋、于敏中等人论争如何编修《四库全书》后,达成协议,指出:“古人校定书籍,必缀以篇题,诠释大意”,“但现今书籍,较之古昔日更繁多,况经钦奉明诏,访求著录者,自必更加精博”,“俟各省所采书籍进行进呈时,请敕令廷臣详细校定,依经史子集四部名目,分类汇列,另编目录一书,具载部分卷数、撰人姓名,垂示永久,用诏策府大成”[5]54。这个意见得到乾隆肯定,认为可以“令承办各员将书中要旨隐括,总叙崖略”[5]55-56。据此,《总目》编纂之初就试图通过廷臣校定来“诠释大意”。而“要旨隐括,总叙崖略”的做法,即是四库馆臣依彼时政统所需重新对文献进行筛选、删改、限定的具体实践。《总目》“凡例”所谓“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四十三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1]18,即是予以贯之。这就使得被校定的书籍,其文献价值的展现并非是文献本身状态的自然流露,而是经过了有意筛选。这种筛选又使得通过应刊、应钞及存目等方式存留的文献的价值展现,实际上转化成了《总目》编纂意图的集中反应。因而,通过主动介入的方式,被著录的具体文献展现自身学术时,就被迫转成了体现《总目》所需的学术思想。
据此看来,四库馆臣在彼时政教意图的指导下,通过应刊、应钞、存目或提要考辨等方式,确立了符合彼时政教意图与学术批评体系的文字表达与文本内涵。并以此确立的文本,作为文献自身学术价值的主要呈现载体,从而通过禁毁、抽毁、删改、刊行或提要的方式,对已确立的文献载体进行强制传播。也就是说,《总目》确立了一种与彼时官方意志保持一致且系可控的文字系统,传递已经过筛选的文献及其意义,试图使此类文献能够快速、多元地传递开来。这种传播是以具有强制性的政治权力与具有主导性的思想体系为基础的。其所要实现的意图,是通过已进行价值规范的《四库全书》(即“官定”文本),把文献的作者意图、文本内涵与当时的政教思想相联系,从而有意引导文献对读者所产生的影响与当时的政教思想相合拍,建构符合彼时政统所需的文本语义系统。凡此种种,皆是《总目》所言“正人心而厚风俗”的文献价值所在。
换句话讲,《总目》通过强制介入方式,重新对文献的文本形式进行限定、对文献的文本内涵进行规范,以此引导读者阅读文本时的关注焦点,从而有意限定或蒙蔽文献本身的作者意图,甚至违背或改变作者的原意,弱化文献传播过程中的作者功用。藉此在文献的传播过程中,形成一种既能栖身于具体文本之中、又可独立于“作者”之外的官方权威式的文本语义系统,从而管束读者自由诠释文献的发挥空间。同时,从文献传播的载体形式看,《总目》的禁毁、抽毁或删改、刊行,是其试图通过控制文献传递的载体形式来表达官方意志的具体操作,从而限定或控制读者的接受范围,这也是清代官方学术批评体系的建构原则与实践依据。它使得被纳入彼时政统视域下考量的书籍的意义生成,并不为文献本身的文本语言符号系统或相应印刷形式的符号系统所决定,而是由彼时的政教思想、文化建设需要所决定。在此基础上,既然文献的价值已受限定,以此展开文献归并与文献阐述的过程,就是彼时统治阶层对文献的内容与意义重新进行体系建构的过程。
典例一,对明人文献的筛选与批评。由于《总目》对明代文献区别对待,故往往从清代政统需求出发,通过否定明代士风、学风的粗俗来批驳明人文献。例如,《易义古象通》提要言:“明自万历以后,经学弥荒,笃实者局于文句,无所发明;高明者鹜于虚无,流为态肆。”[1]31《通鉴纲目前编》提要亦言:“有明一代,八比盛而古学荒,诸经注疏,皆以不切于时文,庋置高阁,故杂采类书,以讹传讹,至于如此。”[1]434据此可知,《总目》多鄙薄明代士风的轻佻与学风的蹈空,致使明代学术的价值存有诸多缺憾,这也是《总目》对明代学术的整体看法。所谓“杂采类书,以讹传讹”,深深道出明人著书立说的疏落,以及由此导致的明人喜撰野乘、私史却又多不足于征信等诸多弊病。此类批评意见,紧紧围绕“以励臣节而正人心”而展开。这成为《总目》进行明人文献刊刻、删改、存目及评判的标准。可以说,正是因为乾隆曾指出“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故而,其所指示的方针“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易置之不办。”[5]239使得明人文献被大量销毁与删改。此类做法不仅弱化了明人文献的传播载体与传播渠道,而且从政统与道统④的需求出发,以清代的官方规范限定彼时有关明人文献的品评意见与批评方式。
典例二,对通俗小说的鄙薄与弃录。《总目》有关通俗小说的品评者,如《文海披沙》提要指出:“‘曹娥碑’一条,据《三国演义》为说,不知传奇非史也”[1]1103,《季汉五志》提要直接批判《三国演义》“乃坊肆不经之书,何烦置辨”[1]459,《梅花草堂笔谈》《二谈》提要亦认为:“《二谈》轻佻尤甚。如云《水浒传》何所不有,却无破老一事”[1]1100,《朱翼》提要认为该书“采及《水浒传》,尤庞杂不伦”[1]1173,等等。据此,《总目》认为《三国演义》等通俗小说所言往往不知为凭;尤其是,“坊肆不经之书”云云,认为通俗小说虽因书坊所刊而广为流传,但往往不能切合“经典”[9]。这就是批判通俗小说的生产、流通等环节,并不符合彼时的政统需求;以“庞杂不伦”为由展开对通俗小说生产主体与传播群体的审查,从而否定通俗小说的内容书写与政教价值。这就否定了通俗小说的文本语义系统与相应的印刷形式,以致批判通俗小说有碍“风俗人心”而予以罢黜。此类做法也是诸如钱曾《也是园藏书目》等清代私实藏书目著录通俗小说时,所贯用的批判举措[10]。
4 结 语
可以说,通过文献生产主体的区分实现文献价值区分,进行文献价值体系的归并与删改,限定文献本身的原始意义,剔除不合彼时政教所需的内容,建构一种带有彼时政统所需与官方色彩的文献收贮原则,这些成为《总目》学术批评展开的主要方式,也是《总目》学术批评体系有效运行的强力保障。这种官方学术批评体系视域下的文献品评视角,使得《总目》所颁行的书籍在政治权力的强化下,得以成为彼时各个阶层、尤其是士大夫阶层的主要进身之阶与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精神来源。这也是《总目》对相关文献的意义进行判定的主要依据,从而实现文化与思想领域的严控。
注 释:
①政教主要指政治与教化,它是古代政权统治的出发点与基础。②文教主要指文化与教育,它包含传统的“四部之学”,是传统学术体系建构的基础与价值意义所在。
③政统主要指古代政权统治思想的核心理念与实践措施。
④道统主要指向儒家传播学术与思想的脉络、谱系及理念,它以儒家的仁义道德为内核,是政统思想的来源与基础。
[1]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温庆新.民族文化本位视域下的古典目录学理论建构——傅荣贤《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读后[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8(2):110-113.
[3]班 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4]傅荣贤.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6]温庆新.试论政教视域下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说观念[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5(10):71-74,83.
[7]张舜徽.中国文献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00.
[8]霍有光.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看乾隆时期官方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态度[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7(5):56-57.
[9]温庆新.从目录学角度谈《四库全书总目》不收通俗小说的缘由[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7(11):77-82.
[10]温庆新“.戏曲小说”与《也是园藏书目》对“通俗小说”的设类及意义[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7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