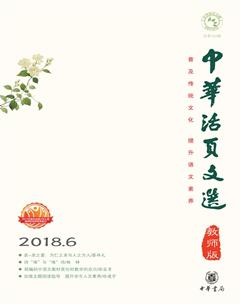亲—亲之爱:为仁之本与人之为人
蔡祥元
在《礼记》中,“慈”列在人伦之义的第一条,“何谓人义?父慈,子孝”(《礼记·礼运》)。但是,与孝、仁相比,它在儒家思想传统中并未获得足够的重视。孟子言必称尧舜,并将尧舜之道归结为孝悌。舜的父亲对舜很不好,但舜依然恪守孝道。此做法后来被视为孝道之典范。从中也可以看到,父母对子女是否慈爱,并不那么重要,父母没有因为不够慈爱而受到非议。但孝道不同,即使在父母未尽慈爱之道的情况下,也依然需要遵守。另外,由于慈爱在动物界也很普遍,孝爱则几乎没有,后者更能显示出人之为人的独特性。此外,从社会政治角度看,如果强调慈爱,并以此来苛求父母,会导致犯上作乱。古代儒者提出过这种担忧:“惟如此而后天下之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于见其有不是处耳。”在儒学思想传统中慈爱因而有意无意遭到忽视。但在我看来,这个疏忽极可能掩盖了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导致其在思想关键处有不通透之感。
一、从“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说起
《论语》中“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中的“为仁之本”有两种不同的断句:“为/仁之本”,即作为仁之根本;“为仁/之本”,即实行仁的根本。“为”的这两种用法在《论语》中都有,字面意思都通,关键在于其思想理路。前一种断句认为,这句话是从本体层面讲孝悌是仁之为(“作为”)仁的根本;后一种断句则认为,这句话是从经验层面、从方法层面讲孝悌是“为仁”(“行仁”)的根本。
程子、朱熹都注意到了两种读法的区别。根据他们的心性之学,仁更具普遍意义,它是“爱之理,心之德”,自然比孝悌更为根本,他们因而主张这里的“为仁之本”只能解作“行仁之本”。程子通过区分性与习,对此作了专门的解释:“故为仁,以孝悌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悌之本。”他以此明确否定第一种断句与理解:“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
但是,孔子是否持有一种普遍的、先天的人性观呢?大家都知道,孔子很少谈性,只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論语·阳货》),其弟子也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孔子不直接谈人的本性,并非偶然,因为孔子心目中有一种非普遍化的、性与习成的“生生之性”。在他看来,人并不天生就是人,还需有一个人之为仁从而成其为人的过程。所以,把仁作为普遍化人性来看待,并且套用习与性分的思想框架,很可能错失了孔子那里更为原本的人(仁)性论。
此外,叶德辉在《日本天文本论语校勘记》中指出,《论语》的许多日本古本此处均无“为”字,而写作“其仁之本与”。根据这些古本,孝悌在这里只能解读为“仁之本”,而不是“为仁/之本”。
二、孝爱与慈爱的同源互构关系
在考察孝悌与仁的关系之前,先探讨一下孝悌本身的根源。在与宰我讨论三年之丧是否太久的那段文字中,孔子点出了孝行的根本:“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孔子这里的回答很容易从报恩的角度去解读,里面隐含着某种功利的计算,就像欠债还钱一样。但是,孔子明确否认了这种理解。他认为仅仅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还远不是孝。孝的关键在于发动孝敬之心,而非单纯地养老。“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
这样一来,孝之根源的问题就变成对孝敬之心的追问。孟子认为孝敬之心是人的“良知”“良能”。他观察到,小孩天生就能爱其父母兄长,这是人的天然之爱(《孟子·尽心上》)。孟子的这一观察与断言,经过宋儒的阐释与发挥,使得孝被提升为天理:“良知、良能,皆无所由。乃出于天,不系于人。”把孝视作天理虽然避免了对孝的功利主义解读,但同时也屏蔽了对孝之根源的追问。
孟子的观察固然不错,但其断言却忽略了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孩子之所以天然地知道亲爱其父母,是因为他从出生之时就受着父母的呵护。如果孩子出生后,父母只是简单地喂养他,不真心地关爱他,甚至动辄打骂,这样的孩子能天然地觉得父母可亲吗?但是,这不又回到了报恩的解释吗?不正是因为父母的慈爱,所以我们长大后要孝敬父母吗?这里面确实有某种报恩,但不是功利主义的欠债还钱。父母之养育不单单只是提供物质上的抚养,而是直接关乎人之成人。人与动物不同,刚生下来时还不能称之为完整的人。他要成为人,还需要一个再生的过程。如果幼年不是由人来抚养,而是与动物生活在一起,这时他依然可以长大,如此长大之后只能是某种“狼孩”,而不是人。这个再生过程主要是在头三年完成的,并且主要是由父母(包括父母的父母)的参与来共同完成的。婴幼儿对世界以及自我的认知,是以父母为尺度展开的。如果把父母对儿女的养育之恩也称为一种债的话,那么,这不是那种可以偿还的“外债”,而是一种“原债”。“原债”是不可计算的,也是永远偿还不完的,它是我们生存结构上对父母的“亏欠”。
在《论语》中,慈爱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孟武伯问孝的时候,孔子没有直接回答什么是孝或如何行孝,而是直言“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这就表明,在孔子心目中,孝与慈处于一个互相关联的结构之中。孝之为孝,必须借助慈来理解。只有以此结构为视野,孝才具有直接的可理解性。慈早已经以匿名的方式隐含于孝悌之中。考虑到这一点,“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背后的完整意思应该是:亲-亲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里的“亲-亲”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亲亲”,即并非单向地亲爱其父母亲,同时还包括父母对子女的慈爱之亲。因此,孝爱与慈爱彼此共处于一种同源互构的关系之中。“‘亲爱主要表现为‘慈爱和‘孝爱。它们的源头和表现方式都来源于人的生存时间或‘出生时间。正因为‘亲与‘子的时相本性而非个体性,才使得亲子关系成了意义机制,而亲子之爱正是这种‘共构意义的原初发生的显现。”
可以说,孝慈互为其源,它们一同构筑了人性之本:“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
三、亲-亲之爱与人之为仁(人)
从字面看,仁说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亲爱之情:“仁,亲也,从人二。”(《说文解字》)将此亲-亲之情,推及他人,就是一般意义上的仁爱,“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只有经过亲-亲之情的熏陶与转化,一个人才可能对他人具有仁爱之心。忠恕之道是为仁之方,但是行忠恕之道者未必是仁者,因为它完全可能出自对一种游戏规则的遵循,从而成为一种冷冰冰的礼让。仁者之为仁者,更重要的倒是那份敦实厚重的人情味。孔子常讲刚毅木讷的人更近乎仁,而不是那巧言令色者。亲-亲之爱则是生命厚重感的一个重要来源。置身于亲-亲之爱中的人,生命中充满了牵挂。父母之于子女,乃是“唯其疾之忧”;子女之于父母,则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这种源自亲-亲之爱的牵挂,让一个人做事情的时候,会自然地多一份顾虑,因为每一个决定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家”。这样的人,如何敢任意妄为、犯上作乱呢?
当然,此种牵挂并非只是外在负担,它同时更是生命内在意义的源头。如果说男女之爱具有某种空间意谓的话——异性身体间的空间距离是引发男女之爱的重要原因,那么亲-亲之爱则更具时间性特征。生命本身乃是时间之流中的一种纯粹生成与创造。新生命的诞生及其抚育过程中绵延跌宕着一种原本的生存时间。在这里,过去与未来发生深沉的碰撞与交织,并因此激发出崭新的“现在”,它是我们人类能够感受到的最原发的生存“意义”。新生儿给父母双方乃至双方的家庭带来全新的“意义”,并以此赋予大家以新的“名分”。从怀孕开始,直至出生以及成长,父母双方乃至父母的父母与孩子一起共处于同一个时间化的“意义之晕”中,成为一个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大家相依为“命”,其中任何一个人的生命直接关乎他人的生命历程。
海德格尔区分了自己的死与他人的死。他认为,他人的死亡是可以经验的,但我们只能以旁观者的角度经历他人的死亡,因而只是一种对死亡的外部经验,而不是对死亡本身的经验。“我们并不在本然的意义上经历他人的死亡过程,我们最多也只不過是‘在侧。”只有面对自己的死亡,才能领会死亡的生存论含义。但是,如同海德格尔所指出的,自己的死亡总是悬而未决的,总是还未来临的,因为,当死亡到来时,“我”已经不存在了。因此,我们对自己死亡的“经验”只能是一种想象的经验,并且,由于它归属于一个未来的“我”,对它的经验也同样有某种异己性,也即表现为某种他人的死。也正因此,与旁观他人的死一样,我们也可以、甚至经常也会从容地设想自己的死。
海德格尔也提到了亲人的死。但他对亲人去世现象的描述是从外部进行的,因此,亲人之死同样被归诸他人之死。但是,我们经验亲人之死与经验他人之死是不一样的。他人之死可以被看作一件客观的自然事件对待。比如,某地发生车祸出人命了,很多人都愿意跑过去看一下。但是,如果你跑过去发现躺在地上的是你的亲人,你还能以一种猎奇的方式来观察乃至谈论死者吗?当然不可能。因为,在这里,你不可能再去旁观死亡,而是直接遭遇死亡带来的震撼之痛。再理性的人,面对至亲之人的离世,也会变得突然哽咽失语,他维持不住自己的日常理性。因为,在这里发生了一种原初-生命共同体的撕裂!他人的死亡往往被经历为一件客观的自然事件,而自己的死亡则是一种想象的主观事件,它们都说不上是对死亡的真实遭遇。但是,亲人的死亡则不同,在这里我们真实地遭遇着死亡的原初“意蕴”(Bedeutsamkeit)。可以说,正是通过亲人,我们才通达死亡本身。
我们不仅不能拥有自己的“死亡”,同样也不能拥有自己的“出生”,因为,在出生之时,“我”还不是我,也就说不上对“我”的出生的经历。人类的出生与动物不一样,后者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动物了。人类则不同,如果没有父母的养育,他长大后就可能只是一个狼孩、狗孩,而非人。但是,从我们记事起,我们就已经是“人”了,已经拥有一个完整的“我”,已经被抛入了一个“世界”。我是如何成为“我”的、如何成为“人”的,这在我们的意识中是缺失的。但是,通过养育子女,我们可以间接地“补充”上对自己成长的经历,从而使我们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养育子女不仅仅补全了我们的人生经历,它还使个人的生命获得了新生。有了子女,并不简单地意味着有后代或老有所养了,而是我们对“未来”有了新的想象与期待,重新有了“未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生命中伸向未来的能力也日趋减弱,会感觉生活索然乏味,沦为过去的简单重复。但是,养育子女会让我们获得新的生命体验。新生命的诞生与成长虽然会让我们付出很多,但它带给我们的会更多。每个父母在子女的话题上总是说不完道不尽,更愿意谈论自己的子女,而不是自己。因为在孩子身上发生的东西比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历的那些东西都更为“闪耀”!在抚育婴幼儿的过程中,我们见证着一个人成其为人的过程!婴幼儿在成长的早期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老子》第五十五章),极具感染力与冲击力地激活那逐渐被我们遗忘的对生命、对生活的原初感受力,从而帮助我们重新开启朝向“未来”的能力。只要想象一下,子女的夭折或早逝对一个人的打击就可以了。父母去世会让人很难过一段时间,但当事人可以相对容易地走出来。而失去子女的打击则往往是一辈子的,因为他的生存结构中缺失了朝向“未来”的维度!
张祥龙先生将这样一个生存-时间-意义的共同体称为“亲体”。“在儒家看来,人类的原本身体只能是亲子家庭,可以称作‘亲子体或‘亲体,它只出自阴阳(男女、夫妇、父母)和合,‘造端乎夫妇,兴于夫妇,而成就于亲子两代、三代甚至多代之间。……亲子在物理空间中是分离的(在家庭空间中是共生的),但通过生存时间而成为了一个意义的发生体。” 在“亲体”中,发生着空间(男女之爱)与时间(亲-亲之爱)的相互转化与交融;在“亲体”中,发生着过去与未来的相互交织与生成;在“亲体”中,我们才有“生”、有“死”。一句话,在亲体中,“我”才是“我”。
或许,这就是中国古人对人之为人的深切领会: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这种以亲-亲之爱为源的“仁爱”是儒家文明的根基,它与基督教文明中顺从上帝旨意的“博爱”有着微妙而关键的区别。
(选自《文史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