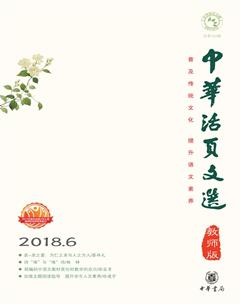“乐痛悲”心路历程背后的儒道争锋
黄志英
书圣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可谓“千古一文”,除了因为它在书法艺术上的登峰造极之外,更因为这是篇不可多得的美文。王羲之与他的《兰亭集序》早已成为中国文人的精神福祉。这篇文章也早被编入普通高中语文教材人教版第二册第三单元山水游记类散文。
此文是一篇“序”,是写在诗集前的文字。古人宴集时,常一同赋诗,诗成后公推一个人作序,《兰亭集序》即是脍炙人口的诗序名篇,其思想和辞藻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从中可以看出东晋一部分士大夫文人的生活情趣、思想修养、精神状态和文学造诣。
此文借序发挥,谈论生死哲学命题,不同一般。对待生命的短暂,人们何以自处?是走道家之路,一死生,齐彭殇,享受及时行乐的逍遥,还是行儒家之道,或独善其身,或兼济天下,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名声?这恐怕是历代文人名士都绕不开的生命追问。
东晋时代的王羲之也经历着一番内心的拷问,千古名篇《兰亭集序》也是出自对生命本体须臾的哀叹,从中透露出站在亘古时空高度的博大襟怀和强烈自信。王羲之想延长精神生命的长度,以求不朽,他俨然知道自己的书法、诗文将来会让后人有感,因此留下“后之来者,亦将有感于斯文”的《兰亭集序》。含蓄蕴藉的语言中可以让人深入体会的地方比比皆是。
王羲之在徜徉自然山水中感悟到了生命意义。他在文中叙述了由“乐”转“痛”及“悲”的情感變化,这段心路历程的背后,是一个真实而矛盾的王羲之在内心掀起的三场“儒道争锋”。
“乐”——起初,儒也相宜,道也相宜,信可乐也!
这种宴会之乐是怎样的呢?
开始是“儒也相宜”之乐。
乐在“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第一个“足以”之乐,来源于眼前人物、景物、活动。宾客以诗会友,斟酌字句,畅叙幽情。这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之乐。它体现出的是儒家之乐,在对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中展现自我价值,从而体味到的快乐。
接着是“道也相宜”之乐。
乐在“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第二个“足以”之乐,纵深到天、风、宇宙、自然,高阔渺远,物类繁盛,融入到天地宇宙中,这是一种忘怀物我之乐;让精神回归自然,从中获得生命的意趣。它体现的是道家之乐,即感官延伸到天地宇宙间,意念奔驰在心灵旷野上,人与自然同化,天人合一,万物齐一。这种快乐是放眼整个宇宙时空臻入无我之境时享受到的快乐。
“乐”之情,聚焦在两个“足以”,由人与人之间的恬适雅素之乐升华到人与自然宇宙之间忘怀物我之乐。儒也相宜,道也相宜,信可乐也!
“痛”——既而,欲道不甘,欲儒不得,岂不痛哉!
这种死生之痛又是怎样的呢?
作者首先将这种情感推己及人,确定了“痛”的范围——整个人类。
在第二段“信可乐也”之后,并没有顺势写“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因为这样接,“其”所指的对象范围就仅限于宴会之人,这断然不是王羲之大胸襟的手笔。他在“当其欣于所遇”之前,来了几句似断实连的文脉跳跃。“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
视野就立即跳出了此时此地此人,扩大到古往今来世上所有的人,不管人们的性格特点、生活态度和方式有什么不同,都有这种由乐及痛的体验啊。“其”所指的不仅仅是宴会之人,而是纵深到昔人、今人、后人。此痛就推己及人上升为人类的普遍情感,更为深重。
作者同时将这种情感上下勾连,确定了“痛”的缘由——生命短暂。
还是在第三段,“人之相与”之后,并没有马上接“或取诸怀抱”,而是又一次跳跃性地加入了一句“俯仰一世”,这一句“人生短暂”的感慨之情似乎来得太突然、太猝不及防?其实不然。作者用“俯仰”一词在上下文做了巧妙的勾连。
上文有第二段的勾连。“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宇宙浩渺无垠,自然万物繁盛、生生不息。然而,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对比之下人个体生命愈发显得渺小短暂。下文有第三段后半部分的勾连。“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短暂的,世事无常;“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更何况生命长短不由我决定,岂不痛哉!
这一切都水到渠成,本可以直接在“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后就浩叹一声“岂不痛哉”。然而,偏在这里再次跳跃,加上一句全文的警句:古人云:“死生亦大矣!”正是这一句,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整个人类更深重的“痛”。它承接上句“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表达出死和生也是重大的事,但是这样重大的事却不由我们自己决定的痛惜之情,也才因而生发出对美好生命痛爱之情。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生命爱得深沉。
然而,绝非仅仅如此。在这“痛”背后隐藏着更为矛盾而真实的情感——“欲道不甘,欲儒不得”的无奈。
要挖掘这种内在情感,我们且把目光放向东晋——看看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那里有一群怎样的文人,还有一个怎样的王羲之。
这是一个真正的乱世。宗白华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朝代政权更迭频仍,门族党派之间互相倾轧……
那时有一群寻找心灵归宿的文人。魏晋以迄南北朝,卷入政治风波招致杀身之祸的大名士就有:何晏、嵇康、张华、潘岳、陆机、陆云、郭璞、谢灵运、鲍照等。当时的知识分子逃避现实,远离政治,避实就虚,探究玄理,发现自我。残酷的政治清洗和身家毁灭,使他们无论是顺应环境、保全性命,或是寻求山水、安息精神,总藏存着无边的忧惧和深重的哀伤。当外在受残酷政治钳制禁锢,“文以载道”“诗言志”的传统儒家文人信条在这里行不通,只能转而内省,思考生命。
了解了时代背景后,我们更需要还原王羲之的生活经历。正如钱穆所言:“凡中国文学最高作品,即是其作者之一部生活史,亦可谓是一部作者之心灵史。此即作者之最高人生艺术。” 了解了作者的时代背景、生活经历,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作品精髓。
处于这种时代文化背景下的王羲之,曾经一度做官,他关怀国事,在政治上曾有积极用世的一面,在绍兴曾任会稽内史,官至右军将军。在他任职期间,薄功名利禄,为人耿直,关心百姓疾苦,是一个务实为民的清官。后辞官隐退,放浪形骸于山水之间。在这辞官与归隐中,包含着作者欲追求儒家立德立功而不能,唯有以老庄遣忧,退而求其次以立言的沉痛无奈的内心挣扎。
不仅如此,此序本为诗集而作,将《兰亭集序》与他自己的六首《兰亭诗》并观,就更能领会此时王羲之的内心隐痛。
在时代残酷压迫的背景下,文人们对生命常常有恐惧之感,常常用一些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他们崇尚老庄,大谈玄理,不务实际,思想虚无,寄情山水,笑傲山野。他们思想消极,行动无为,他们崇尚老庄,哪管人间苦乐与悲喜,只要自己觉得逍遥自在就可以了。王羲之也难免深受道家影响。
《兰亭诗》屡屡阐述老庄淡看生死的观点,如“未若任所遇,逍遥良辰会”的随遇而安,“取乐在一朝,寄之齐千龄”的及时行乐,“合散固其常,修短定无始”的生死无差。大多数诗句在直白地谈玄论道,如第二首到第五首,就出现了很多老庄的思想,如“大象”“逍遥”“群籁”“玄根”“过客”“虚室”等,前五首在思想观念上是比较统一的,但是到了第六首就有点矛盾了。
“合散固其常”出自《莊子·知北游》,原文是“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生和死是很正常的;“修短定无始”,人的寿命有长短,但是人本来就是“道”的一部分,死后复归于“道”,就无所谓长短始终了;“造新不暂停,一往不再起”,新陈代谢是不停的,宇宙自然的变化是时时刻刻的,过去了就不会回来,前面五首包括第六首前两句都是老庄那种“生死齐一”的达观。
但王羲之真的在这种道家思想中得到了完全的解脱吗?读到“一往不再起”这一句似乎就有悲慨了,接着写“于今为神奇,信宿同尘滓”,即使是很神奇的事物一宿之间都会变成尘土,然后直抒胸臆“谁能无此慨”,看似达观的王羲之也有生死倏忽变化之慨。那怎样来排遣这种悲慨呢?“散之在推理”,即通过玄理来开解自己。事实上前五首都是在谈玄理,但是还是生出了悲慨,可见其不能奏效。足见王羲之“欲道而不甘”啊。
“言立同不朽,河清非所俟”,于是他又回到了儒家“不朽”的观念上来,因为道家是无所谓“朽不朽”的,生死是齐一的,死不过是个体存在的另一种形式,由此可以看出王羲之还有事功之心。儒家追求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身处这个时代中的王羲之只能做“立言”之事,还来不及做成立德立功的事,因此感叹生命短暂,内心无比的沉痛无奈。如果能实现三不朽,也是虽死犹生,便不会有如此深切的感慨生命短暂的哀痛了。
“河清非所俟”,俟,是等待。《左传·襄公八年》:“《周诗》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人的寿命很短,等黄河变清是不可能的,比喻期望的事情不能实现。我想要“河清人寿”,我也想要“海晏河清”。不是我不想等,而是等不到,等不成,等不到长寿千年,也等不到国泰民安。诗人借这一句叹生命短暂,世道黑暗。这也是特定的时代中,特定的文人由乐而痛的必然的心路历程,饱含着深深的“欲儒不得”的无奈之情。
诗、序并观,便可见出诗人内心冲突之尖锐:既要以老庄散愁,又觉得老庄虚妄不实;虽明知其虚妄,仍不能不借重于彼。本质上中国的文人追求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要服务于时代,服务于社会。魏晋时代,文人整体不能有所作为,只得回归自我,走向自己内心,他们在儒家思想上,又追求道家的解脱,内心纠结。结合其人其诗,文中“痛”的心路历程,其实是一场“欲道不甘”,“欲儒不得”的儒道争锋,它构成了一个真实而矛盾的王羲之。
“悲”——至终,虽以儒斥道,又以道化儒,悲夫!
《兰亭集序》的矛盾主要体现在最后一段,这一段又主要体现在它语言表达的模糊隐晦上。
本段矛盾的关键在于“不能喻之于怀”,字面意思就是“在心里不明白”,不能明白什么呢?“喻之”的“之”到底指代什么呢?根据语境,这里的“之”可以指代“昔人兴感之由”和“临文嗟悼”。
如果说指的是“昔人兴感之由”的话,就是说王羲之不明白古人对生死发感慨的原因,古人发感慨的原因就是“生命短暂,必有一死”,那就是说王羲之不明白这些道理。但是如果这么看,那和第三段中的王羲之自己所写的“人之相与,俯仰一世”“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岂不是自相矛盾?他是知道这些道理的。
且看在“每览昔人兴感之由”后面紧接着的一句“若合一契”,昔人兴感的缘由,好像一块符契那样相吻合。“若”,好像的意思,既然大家思想情致都一样,那就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可是作者又说“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大概这情致也有“不一”的地方,那么到底又有什么不同呢?《兰亭集序》中倒是有一处“昔人之文”——“古人云:‘死生亦大矣!”
课文下对这句话的注释,仅有一句——“语出《庄子·德充符》”,再无它语。词句出自《庄子》,不免让人疑惑,难道王羲之是推崇道家思想的?那岂不是与后文斥责“一死生,齐彭殇”相悖谬。
这就需要我们探究到原文,“死生亦大”出处的两段原文如下:
①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庄子·德充符》
②仲尼闻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说,美人不得滥,盗人不得劫,伏戏、黄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无变乎己,况爵禄乎?”
——《庄子·田子方》
第①处大意:孔子说:死生是一件大事,却不会使王骀随之变化;即使天覆地坠,他也不会随着这些变化而丢掉准则。心里明白不依凭什么因而不随着外物的变化而改变,任凭外物的变化却坚守自己的观点。
补充:王骀,春秋时期教育家,鲁国人,约与孔子同时。学生比孔子的还多。
第②处大意:孔子听了以后说:古时候的真人孙叔敖,智者不能说服他,美色不能淫乱他,强盗不能胁迫他,伏羲、黄帝也不能笼络他。死生也是一件大事,也不使自己有所改变,何况是官爵俸禄的得失呢?
补充:孙叔敖,春秋时期楚国令尹。辅佐庄王独霸南方,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积劳成疾,病逝他乡,年仅38岁。
那么这句“死生亦大矣”究竟是哪位古人云的呢?
原来是庄子借孔子之口说的,既是庄子又是孔子的看法。既然是庄子两度借孔子之口强调死生亦大矣,可知对死生是一件大事的看法,儒道两家是一致的,那他们究竟又有什么不同?
道家庄子认为死生应顺乎天道,死生只是事物存在的不同方式,并没有什么不同,从而获得对这永恒情结的一种解脱。庄子两度借孔子之口强调死生亦大矣,是借以评价得“道”的王骀、孙叔敖,面临死亡的威胁而不随之改变自己“无所待”的状态。
在这同样的两句话中,儒家认为,虽然生命有限,但精神可以超越有限达到永垂不朽。赞赏的是作为春秋时期的教育家王骀、楚国令尹孙叔敖,能视仁义超过生死,不为死而动摇对仁义的追求。
所以“之”指代“兴感之由”中的看似“若合”,实则“不合”之处。儒道两家对死生看法也有不同,孰是孰非,到底应该倾向于谁呢?不能喻之于怀。
其实这里的矛盾正是王羲之真实的思想状态:在感性层面,王羲之和普通人一样,有七情六欲,有生死之慨,有立功以求不朽的追求,所以才会“以儒斥道”,写道“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斥责士大夫们把死生看作一样是不真实的,把长寿短命等同起来是妄造的。作者批判了时人人生虚无的道家思想,认为生就是生,死就是死,不可等同视之。暗含有生之年应当做些实事,不宜空谈玄理之意的儒家思想。
而在理性层面,由于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又觉得自己能夠“以道化儒”,以超越俗人的生死之慨,排遣无法作为的郁闷。正是在这种感性视角和理性视角不统一,“本我”的儒家思想与“超我”的道家思想的矛盾争锋下,才会出现“不能喻之于怀”。
按照上面的理解,后面的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
如:“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固”注释翻译成“本来”,似乎是和前文矛盾的,即“本来知道把生死等同,把长寿短命看作一样是荒诞妄造的”,既然本来知道这样,那么“临文嗟悼”就很正常,那何来“不能喻之于怀”呢?
我想,“固知”,是一种人之常情,是王羲之“本我”的儒家视角。只是因为平时过多的受流俗道家思想的影响,也会用“老庄思想”看生死。而此时却因为感慨昔人和兰亭集会,触动了“本我”的儒家真情,所以才出“固知”之语。
再如:“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今之视昔”似乎就是前面的“临文嗟悼”,那么“后之视今”也应该是“临文嗟悼”,那么“悲夫”也似乎来得理所当然。这个“悲”应该是指“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明明被触动了,但是却又在理性层面上加以掩饰,强作达观,王羲之是这样“视昔”的,后人也会这样“视今”。
古人,今人,后人,这种种死生之慨,无不是源于对短暂却又美好的生命的热爱,然而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这种热爱,实现生命的价值,却各有各的选择,问世间死生为何物,竟让人不能喻之于怀,谁又能把它想得清清楚楚,说得明明白白?古人是这样的,今人是这样的,我想后人也会是这样的,最终都陷于“虽以儒斥道,又以道化儒”,悲叹无奈以庄散忧,悲斥士族以虚谈废务。欲作为而不能,欲超脱而不得,千古同悲!
我们一步步地接近一千六百多年前的这次兰亭盛会,也慢慢地靠近王羲之,体味他作为这个时代大不幸的文人,内心发出的这些沉痛的感慨和对生命的无比热爱之情。
《兰亭集序》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复杂的王羲之,他既难舍道家的达观超然,以此散忧;又具有儒家常人的生死感慨,有立功追求。他既不像“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那么悲观;也不像两晋的那些玄学家那样看透生死那么达观。他时时处于儒道争锋的矛盾之中。
“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也许正是因为王羲之还没能忘却生死,忘情人世,他才能创作出饱含深情的《兰亭集序》,以及那么多饱含情感和个性的书法作品吧!
挖掘作者的内心冲突,他不同流俗偏向儒家,又倚重流俗的老庄之道。王羲之的矛盾正是一种本我和超我的矛盾,是一种感性和理性的矛盾,《兰亭集序》将这种矛盾充分地展现了出来,让我们接触到了一个真实的而非“神圣”的王羲之。
儒家偏向于哲学、伦理学;道家偏向于哲学,回归生命本真。儒道结合帮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活、理解生命。文学的非功利性滋养着我们的心灵,帮我们变得丰富、敏感、灵动,使我们的内心有了动人的柔软。《兰亭集序》的文化滋养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