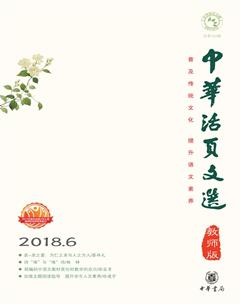喜耶,悲耶
李舜华
《西游记》充斥了佛光道影,然而,我们发现小说始终不过是一部对世俗人生的哲理思考之书。三教归心,实际是以“心”为核心,从主体出发,来探讨大人关系,探讨个体在宇宙间的存在及其意义。这一思考主要是由“心猿”孙悟空来完成的。人们已逐渐发现,孙悟空从大闹三界到取经证佛,从心猿的放纵到约束,实际反映了人类从童年到成年的心路历程。然而,人们在提及这一历程时,多是从形象内涵来笼统地加以概括。至于它怎样从最细微处支配了小说的结构,又折射了怎样的时代意蕴,却往往忽视,甚至单纯地视为一则浪漫主义的喜剧。究竟是喜是悲?这里,我们将所谓心路历程置于小说的整体结构来探讨,并在与同时代文本的比较中界定它真实的文化内涵。
一、心生种种魔生
孙悟空的心路历程与宋明心学密切相关。令人惊异的是,小说以此建构了一个十分精致的寓意结构,它几乎支配了小说的每一个细节与整体构成。
宋代心学大师陆象山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三教归心,即是以一心为本体,去探讨个体的宇宙存在;因此,小说一开始就将孙悟空的出生与宇宙的生成联系起来。
小说开卷,首先以神秘的术数构建了一个创世神话。以干支作大地纪年,从浑沌到天地分,再到阴阳交汇,“万物化生”“三才定位”(三才指天、地、人)。这里显然已摒弃了盘古开辟、女娲造人等早期神话,而有着鲜明的道教意味与理学色彩。接着,又由世界分成四大部洲,迤逦说到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山上的仙石。这一仙石以周天度数的三丈六尺五寸高与天相感,以二十四节气的二十四周长与地相通,最后以九宫八卦的九窍八孔——“此说心之始也”(李贽评)——与人相应。叙述者一支笔上下驰骋,穿越了时间与空间,千折百回,最终归结到仙石迎风化为一石猴。由此产生的石猴,显然寄托着人类对童年——原始生命的凝想。
1.无善无恶任天真
一开始,石猴混迹于群猴之间,逍遥散诞;接着,被尊为王,领导群猴序齿排班,分配了群臣佐使,“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位所拘束”,彼此“合契同情”“享乐天真”。以石猴为首的群猴世界,在浑沌中勾勒了老庄、孔孟所设想的人类童年的黄金时代。
王阳明心学认为“无善无恶为心之体”,禅宗《坛经》也道:“性中不染善恶。”无善无恶即浑沌。对整部小说来说,石猴一出世就意味着心猿的产生,潜伏着对天地秩序的威胁。它“眼运金光,射冲斗府”,一时竟惊动了天地秩序的执掌者玉皇大帝。但这一威胁尚是潜在的,很快金光潜息,初生的石猴首先呈现出一种无善无恶的浑沌状态,不知喜不知忧,所谓“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一回),只一味地精游玩乐、受享生命。
2.生死事大
一天,美猴王忽然在喜宴中烦恼堕泪:“今日虽不归人王法律,不惧禽兽威服,将来年老血衰,暗中有阎王老子管着,一旦身亡,可不枉生世界之中,不得久住天人之间。”(一回)“有善有恶谓之意之动”,对于石猴来说,真正的“心生”至于“魔生”正是在这一喜宴堕泪中萌芽的。
石猴突然悟到了歲月流逝、死生有年,心便由浑沌走向开明;而智识一开,善生恶死,便有无穷无尽的烦恼。“释氏以人生天地间,有生死,有轮回,有烦恼,以为甚苦而求所以免之……故其言曰生死事大。”(《象山全集》卷二)它的烦恼直接源于一种本能的生命意识,它意识到了自身的存在,意识到了生的喜悦;然而从岁月流逝中,它又意识到了死的悲哀,意识到了个体在宇宙间的渺小,所以它立志要“不生不灭,与天地山川齐寿”。孙悟空自号“齐天大圣”,其实也源于这一生命意识。
为了学长生不老,石猴远涉天涯,终于在西牛贺洲拜须菩提为师。对须菩提又谈禅又谈道标举三教合一,人们解释纷繁。实际以生命意识来看却十分自然,也即李贽《三教归儒说》所说:“儒、道、释之学,一也,以其初皆期于闻道也。”这一西行求道可以说是后来西天取经的预演,都象征着对一种人类精神境界的追求。悟得生死,只是心意初动;有善有恶,却可为善也可为恶。孙悟空一心在“长生不老”,最终得祖师传授内丹秘诀和七十二变化等等——此后得以大闹天宫、西天除妖的资本皆拜这一念所赐。
孙悟空学道后,是为善呢?还是为恶?
3.心生种种魔生
须菩提祖师逐悟空下山时,预言道:“你这去,定生不良。”果然,此一去,孙悟空闹了龙宫,打了冥界,最终闹上了天庭,扯旗立帜,与玉皇作对。不过,从开始到结束,孙悟空始终不是自觉的,而是自发的。
孙悟空回山后,与子孙团聚,其乐无穷。一日又虑(心又生,魔障又起):“我等在此,恐作耍成真,或惊动人王,或有禽王兽王,认此犯头,说我们操兵造反,兴师来相杀,汝等都是竹竿木刀,如何对敌。”(3 回)于是,赴龙宫借定海针,于冥界勾生死账,在孙悟空不过是任性而为,小小打扰怎么算闹呢?因此,玉帝一招抚,孙悟空便欢欢喜喜、勤勤恳恳地当了弼马温。一日“欢饮之间”,猴王忽然问起官阶——心念又起——闻知自己不过是一介马夫,恼玉帝渺视自己,这才怒下天庭。此后,也不是主动与天庭较论,而只是自扯旗号而已。玉帝征剿不得,又行招抚,封为“齐天大圣”,于是皆大欢喜。后来,孙悟空因蟠桃会未被邀请,不忿之下,混入会中,偷吃了仙桃仙酒,又偷了老君的金丹,一时畏罪逃下天庭。孙悟空原想关起门来,自在为王,但在玉帝天罗地网的逼迫下,终于喊出了“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达到了叛逆的顶峰。
可见在孙悟空,始终没有什么野心、妄心、不良心,有的只是自在心,由此产生的自尊心、好胜心、利名心,这一切都源于对个体存在的重视。孙悟空是天生成的一段真性情,喜欢无拘无束,却对等级尊严没有什么概念,对玉帝也不过是唱个诺而已。实际,他对自己的官阶并不如何重视,所以得个有名无禄的齐天大圣也心满意足,“但只注名便了”,使天地间知有我一人耳。但玉帝等人恰恰没有重视这一个体的存在;同时,孙悟空的自在心与自尊心种种,在他们看来,正构成了对天地秩序的一种威胁;于是,从一开始就试图收服。然而,玉帝的行为却推波助澜,正是在个体与社会、反秩序与秩序的不断冲突中,孙悟空越闹越大。
最后,还是佛法无边,将孙悟空压在了五行山下。于是,玉帝殿上众仙奉佛,喜庆“安天大会”。
二、心灭种种魔灭
“五行山下定心猿”,但这一定,不是真定,无论玉帝的兵力、如来的法力,都只是外在的强制力。心生种种魔生,那么,只有心灭才能种种魔灭。大闹天宫不过是一个引子,此后,小说用了整整八十二回来写西天取经,即“心猿归正”的艰难历程,书写生命如何在自我约束下走向生命的圆熟。
1.菩萨、妖精总是一念
在西天取经途中,孙悟空主要的职责与最大功绩是除妖。这些妖怪担负着什么寓意呢?
我们首先联想到孙悟空的命名,“鸿蒙初辟原无姓,打破顽空须悟空。”悟空是一个佛教意味很浓的名字,它意味着悟到一切欲望皆空。孙悟空刚皈依佛门,便一棍掃除六贼。这说明西天除魔,除的正是心中魔。西天取经在一开始就成了一则寓言。
此后的妖魔有着浓重的道教气息,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退居山林、自在为王;一是混迹朝廷、篡夺王权。中间又混杂着情爱故事、对长生不老的痴想等。个体欲望的膨胀,同样来自于对个体存在的重视,它构成了对现存秩序的直接威胁或潜在威胁。这令我们直接联想到孙悟空的大闹天宫。因此,在小说的叙述中,妖魔与孙悟空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是他当年的结义兄弟,如牛魔王;而关于黄风怪的曾经大闹天宫更几乎是孙悟空的一个翻版。可见,西天路上的大小妖魔大抵是人类内心欲望的放大,它们的故事与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同属于“放心”之喻。
而西天取经除妖便是“收放心”之喻,也即约束个体欲望的恣肆。李贽评道:“定要做齐天大圣,到底名根不断,所以还受人束缚,受人驱使。”(四回)西天取经,包括一路降妖除怪、争强好胜,在孙悟空还是好名,最终也被封为斗战胜佛。正如唐僧四十八回所说:“世间事,惟名利最重,似他为利的舍死忘生,我弟子奉旨全忠,也只是为名,与他能差几何。”这里,唐僧将自己与商人相比,由此看来,他们也是空而不空。偌大一个清净佛门,怎能允许欲望存在呢?仔细来看,以如来为首的西方世界并非是纯粹的宗教象征,它实际与玉帝携手,共同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存在。西天取经将个体生命纳入对某种特定信仰坚韧不拔的追求——这一追求是为维护社会整体秩序而设的,人也因此获得了自身的社会存在。人的个体存在与社会存在实为一身之两面。人是个体的人,更是社会的人,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自在不成人,成人不自在”。大闹天宫与西天取经实际代表着生命进程从童年到成年的两个阶段。西天取经也不是真的要灭一切心,悟一切空——那样的话,它就成了《心经》的机械图解——而是试图将个体欲望导引上正途,纳个体于社会之中。它灭的只是“恶心”“魔心”。
《西游记》中的个体存在与社会存在大致是以神(佛)性与魔性来隐喻的。取经路上的妖魔不仅与老孙有亲,而且大多与天庭或佛门有亲。于是,为欲所障,偶然下凡,又重返天界,几乎成为每一个妖魔故事的叙述结构。它们大抵象征着修行途中的昧心状态,而与得成正果的神佛相对。
也是在孙悟空第一次降妖,便借观音之口指出:“菩萨妖精,总是一念。”(十七回)菩萨妖魔不过是一身之两面,一念为恶则为妖魔,一念为善则为菩萨。
2.二心之争
孙悟空在五行山下,历尽五百年风霜后,幡然感悔,情愿修行。知善知恶可以是一霎那的事;然而,真正要做到为善去恶,却是一个漫长的心路历程。这一历程在小说中深化成历时十四年、行程十万八千里的西天取经。取经途中,魔性的诱惑或者说放纵欲望的诱惑处处可见。妖魔的世界,不仅是欲望的世界,而且是有情的世界、自在的世界。红孩儿被观音收做善财童子,是得了正果;但罗刹女想的是“我那儿虽不伤命,再怎生得到我的眼前”(五十九回),如意真仙想的是“我舍侄是自在为王的好,还是与人为奴的好?”(五十三 回)。他们或者以人间情感,或者以个体自在否定了佛门正果。甚至取经队伍也常动摇。唐僧因路途遥远、妖魔众多,每起思乡之念;猪八戒更动不动就喊回高老庄当女婿去。这中间倒是孙悟空坚决,八戒、沙僧的皈依都是观音的劝化,只有悟空是主动提出修行。即使如此,在西天取经中,心猿的收与放仍然经历了三次反复。
第一次,孙悟空刚从五行山下出来,心里还是有点想“重整仙山”,拾起旧日的自在,只是答允观音在前,得唐僧解救在后,这才皈依;所以,一与唐僧小小冲突,便一怒东回。在东海龙王那儿抱怨一通,得龙王一句“不可图自在,误了前程”劝语,又自行回到唐僧身边。
第二次,唐僧不识妖精,只恼孙悟空三次杀生,而一怒逐徒。孙悟空一回山,便作法杀人,“大圣按落云头,鼓掌大笑道:‘造化!造化!……我跟着他,打杀几个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来家,却结果了这许多猎户。”这一鼓掌大笑,可以想见当时孙悟空摆脱约束后,心中是十分舒畅。回名“花果山群妖聚义”就明确点明了孙悟空为求正果之余,不堪约束,渴望放纵的一面。
第三次,孙悟空因打杀草寇,再次被逐。这一次,他没有回山,而去到观音处等待唐僧回心。这里,孙悟空似乎奉佛之意更为虔诚,但接着却发生了“真假美猴王”的故事。六耳猕猴是作为一种潜意识出现的,它流露了孙悟空对师父的种种眷恋与怒怨之情。这一次,一直闹遍了天宫、冥界,整个乾坤大乱。
三次放逐显然过错并不在于孙悟空。孙悟空一意求经,对师父忠心耿耿;但恰恰是唐僧,总是听信谗言,动不动就念紧箍咒——紧箍咒成为一种强制性的约束力,成了孙悟空无法摆脱的烦恼。在不堪约束时,重返花果山、打倒唐僧,种种欲望便悄然起了。
孙悟空的三次反复,都隐喻着人心中“神性”与“魔性”之争。尤其是第三次,小说直接把它称为“二心相斗”,并把一心以外的异心明白说成是搅乱宇宙的妄心。尽管六耳猕猴已被孙悟空打死,但已泄露了人们徘徊于放纵与约束之间的困惑。直到取经成功,孙悟空还念念不忘紧箍咒,“脱下来打得粉碎,切莫叫那什么菩萨再去捉弄他人”。大概想起前情,还心有余悸。
关于西天取经,我们首先应该肯定,小说是把“收放心”作为生命最高境界的,这是前提;同时,由放心到收放心,生命的成长需要一系列的代价。
三、自在与成人
悲剧只是暂时的,孙悟空最终以喜剧的结局完成了心路的历程;另外,我们也可以说,尽管孙悟空以喜剧的结局完成了心路的历程,却掩饰不住其中的悲剧色彩。二心相争,究竟谁胜谁负。从小说本身来说,或者说从哲理化的人生角度来说,也许可以说灵山证佛的欢乐足以抹去所附着的各种对佛教的不恭、对金箍的诅咒,而所有的怀疑、烦恼至于苦痛都只是成长的代价。然而,如果复原小说创作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西游记》所构建的只是一个空中楼阁而已。
《西游记》一般认为创作于嘉靖末至万历初年。这一时期,或者追溯到更早的弘治、正德时期,应该承认,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变化。随着市民文化的日益扩张,以陽明心学为发端,掀起了一股具有近代意义的思想狂飙。所谓“阳明心学”很可能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指代着当时人们心里酝酿已久的思想倾向。简单来说,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新兴市民思想逐渐抬头,他们试图以自己的欲望与原则来重构历史秩序;这样,与维持原有秩序的以儒家为标签的传统思想之间,在交融的同时,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冲突。新兴思想中的自我意识与个体欲望具有不可阻挡的诱惑。然而,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人千年来所信奉的精神支柱,它所唤起的社会责任感仍然具有存在的价值;它并与市民阶层的发迹变泰的欲望相纠合。这样,二者的冲突在哲学领域中便衍化为人个体存在与社会存在的矛盾。
另一方面,这一冲突直接与政治相联。元末,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等俱起于布衣,角逐中原。最终朱元璋一统天下,建立了明王朝,却是与依赖德士、以儒家思想为号召相关的;此后,进一步假借儒学,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封建政治思想专制,同时又忌杀功臣。人们在欢呼汉人一统时,却无法忘记这一血淋淋的现实;人们在为明代集权兢兢业业地添砖加瓦时,却又追想了当年英雄逐鹿时个性生命力的恣肆。弘治,史称“弘治中兴”,在这前后,尤其是在这之后,社会危机不断显露:内阁倾轧、藩王作乱、农民起义、市民暴动、倭寇猖獗……王阳明正是在平定宁王之乱及各地农民起义之余,认为“平山中贼易,平心中贼难”,遂起而倡导心学,目的显然是在于治心以维持家国秩序。然而,阳明心学力图维持的已偏向一种精神上的家国秩序,至于现实中的明代封建政治却已是大厦将倾了。正是政治现实的失败,使自明朝建立以来人们即奉为圭臬的精神支柱——儒学产生了严重的危机,心学中潜藏的对个性的追慕便空前地高涨起来。嘉靖时,异端之尤者李贽大胆肯定人欲,鼓吹“童心说”;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李贽,却始终声称自己是一个孔子的追随者。他的狱中自杀,也许只是以最后的平静来结束一个因畸变而痛苦的心灵。李贽死于万历三十年(1602),此后,袁中道在《李温陵传》中高度评价了李贽的精神,却又列举了种种不可学之处。袁中道等人承受了因徘徊于传统与新兴之间而裂变的全部压力,在不堪负载后仓惶逃亡,他们对个性的发扬,不再有李贽矛盾中的抗争,而多少成了生活的一种润滑剂。
由此,再来看《西游》徘徊在个体与社会、放纵与约束之间的困惑,也许会获得更深一层的体会。我们很快想起另一部奇书《水浒传》。孙悟空从大闹天宫到皈依佛门,此后的西天取经,降除的恰恰是当年与自己称兄道弟的妖魔;水浒英雄从梁山聚义到朝廷招安,其后征讨的也是与自己当年同类性质的外邦(大辽)与义军(方腊)。二者是惊人的相似。早期研究中就有《西游》为《水浒》“翻版”一说,认为二书都反映了市民阶层反抗的不彻底,而最终得出“投降”说。《水浒》中的梁山泊以“义”为缔结,勾勒了一个“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自在生活,梁山作为放纵个体欲望的隐喻与花果山其实是一致的。但显然梁山聚义,并不利于实现众英雄搏一个前程的欲望——所谓前程,即边庭立功,它糅杂了封妻荫子与尽忠留名(个体与社会)的两种因素。可招安后的边庭立功,却掩饰不住离开水浒后备受约束甚至兄弟凋零的悲凉。《水浒》最终以功臣受戮强烈质疑了对纳入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存在的追求。这一追求在《西游》中却是以喜剧结局完成的。从小说人物来看,唐僧与孙悟空也仿佛是对宋江与李逵的摹拟,前者与后者的关系都是既矛盾又统一,表现了社会人对自然人的约束,成年对童年的抑制。只不过,李逵最终随宋江而死,而唐僧与孙悟空却两相扶持,终成正果。
《三国》是一部必需与《水浒》对读的奇书。汉末,群雄并起,逐鹿中原。刘备起于市井,他以汉室皇裔自居,以曾受献帝衣带诏、勤王锄奸为号,以称王是为部将所逼为辞,为自己涂上了一层儒家的“仁义”色彩。这一“伪饰”实际说明了市民阶层实现自身欲望的一种理性姿态。蜀国的建立,无疑说明了这一理性约束的成功。然而,小说在欲望实现的巅峰急转而下,刘、关、张的死亡无不源于个性的膨胀,以及对桃园结义(这一充满了市民色彩的团体)的承诺。事业的成功补偿不了兄弟凋零的痛苦;而蜀国最后的崩溃,又流露了对放纵自身个体欲望的畏惧。《三国》《水浒》在嘉靖时一刊行,便迅速传播;在它们的影响下,历史传奇纷纷出笼。这些小说无一例外地写成了两种悲剧,刘备式与宋江式。
由此来看,《西游记》喜剧中的悲剧因素便逐渐浮现出来。例如,第二次被逐,孙悟空一路凄凄惨惨地回到了花果山,见到一派颓山败景、子孙凋零,倍加凄惶。第三次被逐,悟空进又不是,退又不是,一边想着“当年弟子为人,曾受那个气来”,一边想着“我弟子舍身拼命,救解他的魔障”,“怎知那长老背义忘恩”。两相对比,越想越屈,于是跑到观音那“止不住泪如泉涌,放声大哭”(五十七回),这两段文字的悲剧气氛一点都不亚于《水浒》中宋江等人魂聚水浒,诉告徽宗一节。孙悟空一众灵山证佛,不过相当于水浒英雄征辽回来,一人未损又大建功勋一节。假如《西游记》让孙悟空衣锦还乡,花果山只怕是更加凄凉;那么,功成名就又能如何呢?孙悟空难免不会像宋江那涕泪滂沱。征方腊后,面对他人庆功,宋江却悲从中来,“当初小将等一百八人……怎知十停去七,今日宋江虽存,有何面目再见江东父老,故乡亲戚。”(八十九回)由此来看,《西游记》寓言的局限是非常大的,它回避了一个花果山的存在,孙悟空是孤身一个皈依佛门;牛魔王等也不是他的猴子猴孙;它所构建的只是远在西天的秩序,是一种纯精神上的,它丝毫未触及位于中心的玉皇秩序。此后《金瓶梅》便迅速堕入了一个空前的荒谬。西门庆积极依附原有政治秩序,在原有秩序内来扩张自己的经济与社会地位。东京朝圣,无疑说明了这一努力的成功;但极盛而衰,西门庆的死亡却在于对个体欲望的极端放纵。
新兴市民思潮在试图汇入传统儒家思想,以获得自身的一席之地时,却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征辽回来,宋江亲自上五台山向智真长者询问休咎,以为“前程事小,死生事大”,小说以一种独特的智慧,领悟到了“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的悲凉。成人与自在一语以及“问休咎”模式,反复出现在《三国》《水浒》与明嘉靖时期的小说中。《西游记》所谓的喜剧结局不过是暂时的逃避,小说在字里行间,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了喜剧中的非真实因素。
四、子系婴儿
尽管《西游记》有着种种的不真实,却仍是一则充满了浪漫色彩的喜剧性寓言。只是,该书真正的喜剧色彩,并不来自于安天大会或灵山证佛,它恰恰来自于孙悟空天真未凿、率性而为的个性魅力。
孙悟空是一个天地生成的石猴,它总是一派猴头猴脑、猴腔猴调,又促狭、又顽皮,就如孩子一般,充满了令人捧腹的喜剧色彩。正如李贽所评:“描画猴处,都是匪夷所思。”(七十五回)孙悟空成为李贽“童心说”的直接演绎。
第一回,须菩提为石猴取个姓氏:“子者儿男也,系者婴细也,正合婴儿之本论。教你姓孙罢。”李贽批道:“即是《庄子》‘为婴儿,《孟子》‘不失赤子之心之意。”在小说中,孙悟空始终是以“自然人”——也即天地生成的婴儿——面目出现的。这样,它对佛道的态度就跳脱得多,可以嘲佛骂祖,无所不为。这从表面上来看,似乎不是佛门弟子;但在李贽等人看来,率性而发,恰恰是真佛祖。李贽为“鲁智深大闹五台山”,道:“无所不为,无所不做,佛性反是完全的,所以到底成了正果。”小说对孙悟空也正是沿着这一思路来写的。
《心经》是理解全书的主线。在第十九回,唐僧虔诚地接受了《心经》,以后也不断念诵,却始终不能解得。悟空呢?在乌巢传经时,只一味冷笑,还捣了他的巢穴,不恭不敬之至;到后来倒是他解得“无言语文字”(九十三回),成了唐僧精神上的引导者。原因就在于悟空作为“婴儿”,有天地生成的悟性,“真如本性任为之”,故无处不是佛性,无往不是佛理。
“童心說”是晚明思潮中最光彩的一页。在这里,佛性不过是虚幻的灵光,其中凸现的始终是人的“个性意识”与“自我意识”。不失童心,才能去一切杂想,而生执著心,故能执著于完善生命的精神悟求。西天取经所构想的是:人由童年到成年,由自然人到社会人的历程,然则生命真正的圆满却在于进入成人社会后,“始终不失赤子之心”。
“子系婴儿”,赋予了孙悟空以无穷的魅力,《西游记》因此成为一则永远的童话。
(选自《明清小说研究》)
——以黄麻士绅纠葛为中心的讨论
——《李贽学谱(附焦竑学谱)》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