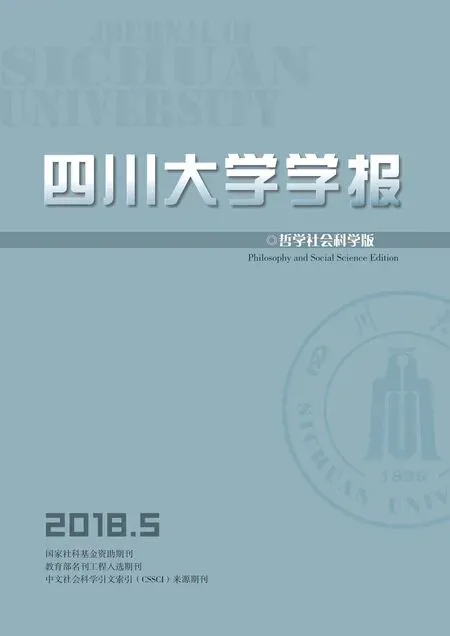西方国家“逆全球化”现象的一种解释
,
冷战结束后,美国极力倡导建立全球化的世界新秩序,在其对外战略中也以全球化作为立足点,而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曾反对全球化并将其称为“美国化”;然而,20多年后的今天,中美两国在对待全球化的态度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中国提倡推动全球化,而美国特朗普政府则采取了反对全球化的政策。*阎学通:《反建制主义与国际秩序》,《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2期,第0-Ⅵ页。其实,从全球范围内来看,作为全球化最早倡导者和推动者的西方发达国家近年来表现出了很强的“逆全球化”动向,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则表达了坚定支持全球化的立场。所谓“逆全球化”与“新全球化”究竟有何表现?特别是如何认识和解释所谓“逆全球化”思潮发生的原因?
一、“逆全球化”与“新全球化”现象及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国际体系中权力结构的变动和主要大国内政外交战略的调整,世界政治正经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国际形势跌宕起伏、变化迅速,“黑天鹅现象”层出不穷,国际政治的现状呈现出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全球化进程有所退潮。作为全球化最早倡导者和推动者的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表现出很强的“逆全球化”动向。全球化的发展前景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2016年以来,逆全球化日益成为一种运动式的浪潮,并且对西方国家维护自由秩序的主流政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西方主要国家在其重要理念、战略和政策层面均表现出了明显的逆全球化动向,*相关论述可参见Peter Trubowitz, “Trump's Victory Will Fuel the Growing Backlash against Globalization in the West,” LSE US Centre, November 28, 2016, http:∥blogs.lse.ac.uk/usappblog/2016/11/28/trumps-victory-will-fuel-the-growing-backlash-against-globalization-in-the-west/; 秦亚青:《世界秩序刍议》,《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6期,第8页。主要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对外来移民。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为标志,逆全球化现象开始在西方国家集中显现。在2017年法、德等欧洲大国的选举中,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也体现出了逆全球化思潮的重要影响。可以发现,曾经主导和引领全球化潮流的西方国家开始出现明显的逆全球化思潮,而这些思潮和理念又促使西方国家的战略和政策发生了很大改变。例如,特朗普上台执政不久就开始在国际贸易、移民等领域采取更强烈的保守主义政策。英国脱欧体现出的排外主义和国家主义,对欧盟其他国家的民众和国内政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法国、德国等欧洲大国的国内选举中,具有种族主义倾向、反移民、反一体化和反全球化的极右翼政党乘势崛起,势必对这些国家在一体化、移民等领域的传统政策带来极大的冲击。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逆全球化风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对全球化的坚定支持。2016年的一些调查报告显示,在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只有不到一半的民众认为全球化是“有益的”[注]Fred Hu and Michael Spence, “Why Globalization Stalled: And How to Restart It,” Foreign Affairs, No.4, July/August 2017, p.2.,而中国、印度两国民众对此表示认同的分别为60%和52%。[注]Richard Wike and Bruce Stokes, “Chinese Public Sees More Powerful Role in World, Names U.S. as Top Threat,” Pew Research Center, October 5, 2016,http:∥www.pewglobal.org/2016/10/05/chinese-public-sees-more-powerful-role-in-world-names-u-s-as-top-threat/.在国家政策层面,2017年1月中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郑重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强调“要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认为当前 “最迫切的任务是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并且希望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起到引领作用,“为解决当前世界和区域经济面临的问题寻找方案”。[注]《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全文)》,2017年1月18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7-01/18/c_1120331545.htm。
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特别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启动和实施,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论者据此认为,世界正在处于一种“新型全球化”乃至“中国式全球化”的新进程中,并对“新全球化”的涵义、原则、目标等要素进行了探讨。[注]相关论述可参见钟飞腾:《“一带一路”、新型全球化与大国关系》,《外交评论》2017年第3期,第1-26页;胡鞍钢、王蔚:《从“逆全球化”到“新全球化”:中国角色与世界作用》,《学术界》2017年第3期,第5-17页;Hu and Spence, “Why Globalization Stalled: And How to Restart It,” p.4.
关于全球化究竟源于何时,学术界有着不尽相同的说法,而且不同观点所界定的时间相差甚远。有人认为全球化源于1492年之后的地理大发现时代,有人则认为全球化始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还有人认为直至2000年,全球化才真正开始。[注]Alex MacGillivray, A Brief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 The Untold Story of Our Incredible Shrinking Planet, London: Robinson, 2006, pp.16-17.转引自蔡昉:《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及中国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1期,第7页。但是,即便是按照最晚近的说法,全球化所描述的仍是较长一段时期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现象。因此,仅就近年来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一些现象来界定何者为“新”全球化,恐怕为时尚早。不过,在前文的论述中,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这样一种反差:曾经作为全球化倡导者和推动者的西方发达国家近来表现出很强的“逆全球化”动向,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则成为了坚定支持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如何解释这种反差就成为了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本文将重点探讨为什么西方国家近些年来在政治上出现了“逆全球化”现象。
二、“逆全球化”原因探析:一种解释框架
要准确理解前文提出的“逆全球化”与支持全球化所形成的反差,必须对全球化对各国的影响有更深入的了解。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化进程不会给各国带来同样的利弊得失。冷战后加速发展的本轮全球化进程,是由发达国家极力倡导的,而这一进程也长期按照有利于发达国家、特别是有利于美国的方向演进。可以说,自20世纪90年代直至21世纪初,美国既是全球化的主导者也是最大受益者,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看来,全球化就是“美国化”。[注]邵育群:《美国与全球化关系的再定义——高度不确定的未来》,《国际展望》2017年第1期,第19页。因此,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20世纪90年代末制定其新世纪的对外战略时,着重指出要以全球化作为美国对外战略的立足点。[注]刘建飞:《全球化与美国21世纪外交战略》,《国际论坛》2000年第2期,第6页。然而,21世纪仅仅过去还不到20年时间,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态度就已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注]韩召颖、姜潭:《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对外战略的转向》,《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4期,第22页。当前,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国内政治势力认为,过去由美国大力提倡的全球化,已经使美国本身成为了利益不公平的受害者。[注]朱锋:《面对特朗普,是朝贡还是捍卫全球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7年2月20日,http:∥www.ccg.org.cn/Expert/View.aspx?Id=5927。那么,21世纪以来的近20年间,全球化发生了对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利的演变吗?
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弄清楚如何衡量全球化给各国带来的利弊,这就需要对全球化的含义及其影响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把握。简单地说,全球化是指世界范围内相互联系不断拓展、加速和深化的现象和过程。[注]Anthony McGrew,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Politics,” in John Baylis et al.,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6.但关于全球化的定义,学术界一直有着以下几种不同的看法: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不断强化的一种现象,即便是相距遥远的地方之间也有着密切的关联,某地发生的事情会受到千里之外发生的事件的影响;[注]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1.全球化即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注]Robert Gilp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364.全球化意味着去领土化或人们之间跨越国界关系的不断发展;[注]Jan Aart Scholte, Globaliza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Macmillan, 2000, p.46.全球化是一种“时空压缩”现象。[注]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安东尼·麦克格鲁(Anthony McGrew)在总结上述观点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个全球化的定义:全球化是一种历史进程,涉及在人类社会组织的空间范围内根本性的变化或转变,它将相距遥远的群体连接起来,并拓展了权力关系的影响范围,使其跨越了各个地区和大陆。[注]McGrew,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Politics,” p.20.总之,全球化最显著的表现形式就是打破各民族、各国家和各地区之间的相互隔绝状态,使世界范围内的交往成为可能,而随着这一进程的深入发展,全球化展现出了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众多领域的日益丰富的内容。[注]蔡拓:《全球化与政治的转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3页。
上述关于全球化的定义比较普遍、宽泛,需要注意的是,不管从理论还是现实层面谈论全球化,经济全球化都是其中最为基础和重要的内容。虽然学者们也强调政治与文化等领域的全球化,但其分析的基础仍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广泛而深刻的政治、文化影响。[注]蔡拓:《全球化与政治的转型》,第20页。因此,集中分析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就可以较好地把握全球化所产生的影响。从经济意义上说,全球化是指在现代化大生产的推动下,全球范围内形成的分工、交换(即贸易)、流动(包括资本和人员)的“时空压缩”现象。[注]胡鞍钢、王蔚:《从“逆全球化”到“新全球化”:中国角色与世界作用》,《学术界》2017年第3期,第6页。经济全球化的核心理念是主张商品贸易自由化、国际投资自由化以及人员国际流动的自由化(即移民自由)。[注]金碚:《论经济全球化3.0时代——兼论“一带一路”的互通观念》,《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1期,第6页。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商品、资本和人员(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全球的自由流动。因此,如果说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给参与其中的各国带来收益,又会使各国为此付出成本,那么这种收益或成本就可以通过商品、资本、人员(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给各国带来的不同影响来展现。
就21世纪以来全球化对西方发达国家带来的影响来说,可以尝试对商品、资本、人员(劳动力)等要素进行分析以解释目前逆全球化风潮(见图1)。

图1 “逆全球化”原因探析:一种分析框架
如图1所示,本文对全球化的分析以经济全球化为轴心和基础,而经济全球化最核心的要素是商品、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它们的流动所带来的结果对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产生了不同的深刻影响,各国因此做出支持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的不同政策选择。
三、全球化给西方国家带来的影响:基于三种要素的分析
探究逆全球化现象的动力机制,需要从商品、资本、人员等三种要素的全球流动给西方国家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由于逆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和对外来移民的限制,因此以下将以对商品和人员两种要素的分析为主,辅之以对资本要素流动的考察。
(一)商品的自由流动给西方发达国家带来的影响。商品全球流动对一国所带来影响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货物贸易进出口状况。为从整体上衡量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货物贸易水平,这里以七国集团(G7)整体的数据作为依据,因为七国集团囊括了美、英、德、法、日、意、加等主要西方国家。如表1所示,21世纪伊始,西方主要国家在国际贸易格局中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地位,2000年七国集团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47.64%,其中出口占全球总出口的45.57%。2000年以来,七国集团货物贸易总额在持续增长(2015年比世纪初增加了5.105万亿美元),但其在全球货物贸易所占的比重在不断下降。此外,七国集团的出口总额在世界货物贸易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也在不断下降。

表1 七国集团(G7)货物贸易总额及其占全球比重(单位:万亿美元)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数据库,http:∥unctadstat.unctad.org/wds/TableViewer/tableView.aspx?ReportId=101,2018年9月7日。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在同时期实现了迅速扩张。从表2可以看出,至2015年,新兴市场国家货物贸易总额比世纪初增加了10.446万亿美元,是这一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增加额的两倍还多。新兴市场国家在货物贸易总额和出口额上都已经领先于西方发达国家。

表2 新兴市场国家货物贸易总额及其占全球比重(单位:万亿美元)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数据库,http:∥unctadstat.unctad.org/wds/TableViewer/tableView.aspx?ReportId=101,2018年9月7日。
从以上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进入21世纪以来的近20年里,商品的全球流动即商品的全球化中,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贸易中获得的绝对收益虽然也在增加,但与新兴市场国家相比,美欧等发达国家的相对收益下降了。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货物贸易国际竞争力在下降,其在国际贸易格局中的地位也在下降。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说,全球化产生了对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不利的影响。而美欧等发达国家出于其国际战略或国内政治考虑,便提出了反国际贸易、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主张。
首先,从国际战略层面来说,21世纪以来,国际格局中出现了中国等新兴国家崛起、美欧等发达国家国际地位相对下降的“西降东升”的大趋势。而引起国际经济政治力量对比呈现出“西降东升”态势的前提条件便是新兴国家经济、贸易增速普遍高于西方国家。[注]林利民:《“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及其国际政治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5期,第13-14页。因此,如果美欧等西方国家在商品的全球流动中无法获得更多的相对收益,而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继续从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的相对收益,那么势必引起当前中美之间经济政治力量对比有利于中国的前提条件将持续存在,美国因而会对其全球主导地位感到担忧。因为中国国际贸易实力的不断增长会直接增进其经济实力,而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会逐渐转化为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例如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之后,从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后直至2014年秋季,中国就主要使用“战略军事”的手段来增进其在亚洲和西太平洋的权势影响甚或主导作用。[注]时殷弘:《“一带一路”:祈愿审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7期,第151页。此外,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中国越来越多地在世界舞台上发声,并提出一系列中国方案,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体现了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在全球治理中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美国看来,“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地缘战略,成为中国谋求欧亚霸权的重要举措。[注]钟飞腾:《“一带一路”、新型全球化与大国关系》,《外交评论》2017年第3期,第3页。因此,为扭转中美之间经济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动态势,从而长久维持其在全球的主导地位,美国不会无视中国等新兴国家国际贸易实力不断上升的状况,在本国国际贸易地位相对有所下降的情况下,美国便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修改乃至退出对其“不公”的多边贸易规则等逆全球化言行。
其次,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党和政治家把商品自由流动带来的贸易逆差当做其内部社会问题的“替罪羊”,将问题归咎于自由贸易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从而鼓动了民众的逆全球化诉求。以美国为例,21世纪以来的近20年间,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白人蓝领收入停滞,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成为“输家”,日益强烈地表达他们的不满。对此,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研究报告称,自2001年至2015年,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使美国损失了34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近3/4(74.3%)来自于制造业。[注]Robert E. Scott, “Growth in U.S.-China Trade Deficit between 2001 and 2015 Cost 3.4 million Jobs,”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January 31, 2017,http:∥www.epi.org/publication/growth-in-u-s-china-trade-deficit-between-2001-and-2015-cost-3-4-million-jobs-heres-how-to-rebalance-trade-and-rebuild-american-manufacturing/.这一结论在美国广为流传,政治家把它拿来当作理由,提出蛊惑性的承诺,以赢得民众的支持。例如,特朗普就曾以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报告作为其政策主张的依据宣称,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以来,美国损失了近1/3的制造业工作岗位,而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美国损失了5万家工厂,[注]周琪、付随鑫:《美国的反全球化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4期,第6页。进而宣扬其反国际贸易、反全球化的政策主张。早就有学者指出经济政策研究所的分析报告与实际情况不符,因为其分析方法存在着重大的缺陷,[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人民币汇率升值解决不了美国贸易逆差和失业问题》,《国际经济分析与展望(2011—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43-152页。更重要的是,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并非近年来美国制造业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造成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失业率上升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自动化等技术进步使得西方国家生产率得到了快速提高。[注]相关论述参见李未无:《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对美国制造业失业率影响的实证分析》,《财贸经济》2004年第3期,第41-46页;Hu and Spence, “Why Globalization Stalled: And How to Restart It,” pp.3-5.但是,技术进步毕竟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一种客观趋势,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处境艰难、日益不满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国内社会经济政策的滞后,这需要从制度上对国内利益格局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注]蔡昉:《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及中国策略》,第4页。然而,制度变革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也面临较高的政治风险,在西方现有的政治体制内,各政党及其领袖都只是追求以较低的政治成本换取相对有限任期内的政治权力。因此,迎合甚至鼓动民粹主义、将内部问题归咎于自由贸易和中国等新兴国家,更为容易,也是最符合西方国家政党和政治家利益的理性选择。[注]Alvaro Cuervo-Cazurrra, Ram Mudambi, and Torben Pedersen, “Globalization: Rising Skepticism,” Global Strategy Journal, Vol.7, No.2, 2017, pp.155-158; 蔡昉:《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及中国策略》,第6页。
(二)国际资本的全球流动。对于存在贸易赤字的西方发达国家来说,资本自由流动所带来的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它是这些国家抵消贸易赤字、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手段。

表3 G7与新兴市场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及其占全球比重(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数据库,http:∥unctadstat.unctad.org/wds/TableViewer/tableView.aspx?ReportId=96740,2018年9月7日。
但是,如表3所示,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呈下降趋势,虽然2015年这一数据有所回升,但与世纪之初相比,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及其占全球的比重出现了明显下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在此期间无论是在全球所占比重还是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上都比世纪初有了显著增长,2015年,新兴市场FDI流入量是世纪初的近3倍,增加额达到4481亿美元。
由于西方国家在商品的全球流动即国际货物贸易中的相对收益在减少,而国际资本流动呈现的状况无法很好地弥补其贸易赤字,因此,全球化在这两个方面的发展对美欧等发达国家来说是不利的。也就是说,资本的全球流动没能有效改善商品全球流动对西方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如前文所述,美欧等国出于其国际战略与国内政治考虑,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的言行。
(三)人员的全球流动。在全球化进程中,人员的流动会产生商品、资本等要素所不能带来的更为深刻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影响。历史上,大规模移民曾经使美欧等发达国家受益匪浅。一方面,移民为老龄化问题较为严重的西方国家带来了大量劳动力,促进了其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移民的到来为西方国家节省了巨大的教育和培训成本。更为重要的是,大量高学历移民进入西方国家,成为推动其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例如,据2013年的一份报告,美国29%的科学家和50%以上的科学和工程博士来自于移民。[注]Gene Sperling, “The Economic Case for Commonsense Immigration Reform,” The White House, March 13, 2013,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blog/2013/03/13/economic-case-commonsense-immigration-reform.然而,21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中人员的流动给西方带来的更多的是负面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恐怖主义肆虐、欧洲难民危机以及美国的身份认同危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东西方阵营对抗的终结,全球化得到了迅速发展。进入21世纪,随着科技的进步,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全球化发展进程进一步加速。然而,大致与此同时,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也日益进入了高发期。虽然不能说是全球化导致了新时期恐怖主义的肆虐,但是,全球化特别是人员的自由流动及其带来的便利被恐怖组织利用,使得恐怖主义的跨国联系及其行动能力得到加强。甚至有学者认为,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既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产生与蔓延提供了结构性条件,又为其提供了各种资源:一方面,全球化深入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剧变使许多民众产生了本土不安全感,而权力流散使得主权国家的权威不足,从而导致各国治理恐怖主义的能力有限;另一方面,全球化倡导的价值观念成为恐怖主义攻击的对象,而全球化带来的便于人们通讯的各种工具则为恐怖组织跨越国界招募其追随者和策划恐怖袭击提供了便利。[注]曾向红:《全球化、逆全球化与恐怖主义新浪潮》,《外交评论》2017年第3期,第156页。人员的自由流动使得恐怖组织不仅能够跨越国界开展活动,而且能在全球范围内招募人员。其结果就是,全球化进程所提供的各种便利被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利用,他们借此建立起相互之间的跨国联系,并在国际上不断扩大其影响,从而推动了暴力的全球化。[注]Andreas Behnke, “Terrorising the Political: 9/11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Globalization of Violence,”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3, No.2, 2004, pp.279-312.美国等西方国家则成为跨国恐怖主义打击的最主要对象,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2001年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使美国遭受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近3000人在这场袭击中遇难,美国遭受的直接经济损近1000亿美元。这是发生在美国本土的最为严重的恐怖袭击行为,大大削弱了美国民众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安全感。[注]金灿荣、董春岭:《“9·11”十年反思及对中国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9期,第16页。而近年来英法德等欧洲大国也深陷恐怖袭击的困扰。自2017年3月以来,英国遭受了议会大厦袭击、曼彻斯特球场袭击、伦敦桥袭击等接二连三的恐袭,2017年成为英国近20年来遭受恐怖袭击次数最多的一年。[注]《盘点英国近20年遭遇的恐袭:2017年“最受伤”》,2017年6月21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7/06-21/8256593.shtml。而法国则成为了近年来欧洲大国中恐怖主义袭击的头号目标,自2014年11月以来法国已经遭受了超过20起袭击,其中2015年11月在巴黎发生的严重恐怖袭击事件,造成了130多人死亡、近400人受伤,是近年来恐怖袭击死伤人数之最。[注]《法国巴黎发生严重恐怖袭击事件》,http:∥www.xinhuanet.com/world/blbz/index.htm。与此同时,针对德国的恐怖袭击数量也出现了大幅增长。[注]杨解朴:《恐怖袭击的“新灾区”:德国反恐形势分析》,2016年9月9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0909/c1002-28705280.html。面对日益严峻的反恐形势,为更好地保障自身安全,西方国家加强了对人员、资本等要素自由流动的监管和限制,这种做法无疑会迟滞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可以说,英国脱欧、特朗普对移民的限制、法德等欧洲大国出现的右翼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现象,都与恐怖主义的肆虐有着一定的关联。[注]曾向红:《全球化、逆全球化与恐怖主义新浪潮》,《外交评论》2017年第3期,第155页。
“9·11”事件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动了“反恐战争”,并加紧了对中东地区的干预。然而西方的战争和一系列行动,换来的却是“越反越恐”的结果。随后西方对中东地区特别是叙利亚问题的干预,不仅没有给当地带来民主和繁荣,反而造成了中东的乱局,致使众多国家的人民流离失所,沦为难民。2015年以来,从西亚和非洲部分国家涌入欧洲的难民数量激增,形成严重的难民危机,给欧洲国家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其实,21世纪以来,随着进入欧洲的外国移民数量的剧增,移民问题早已成为许多欧洲国家一个重要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在欧洲国家的选举中,各政治势力和党派关于移民问题的政治主张,是选民极为关注的重要议题。对外国移民持不同态度的选民甚至因此形成两大对立阵营。[注]宋全成:《欧洲难民危机政治影响的双重分析》,《欧洲研究》2016年第1期,第129页。在此次欧洲难民危机中,外国移民的大量涌入给欧洲各国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一是难民的大量涌入可能会激发本国民众的本土主义和种族歧视。大量难民涌入欧洲势必对欧洲国家的福利制度造成冲击,与此同时,难民可能会冲击国内劳动力市场,导致失业。在这种情况下,本国民众难免会产生不满和排斥情绪。二是外来移民特别是难民带来的犯罪活动和可能的安全威胁挑战了欧洲国家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例如,2016年新年前夜发生在德国科隆的性侵案中,由于案件嫌疑人有难民背景,科隆当地发生了极右翼势力抵制难民的游行示威活动;[注]《科隆性侵案背后,是撕裂的德国和欧洲》,2016年1月11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1/11/c_128614328.htm。而在2015年11月巴黎发生的严重恐怖袭击中,调查结论也显示袭击者利用了难民身份抵达欧洲并实施了恐怖袭击。[注]《巴黎恐怖袭击枪手疑以难民身份入欧》,2015年11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5-11/16/c_134820055.htm。这都给欧洲国家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带来了极大挑战。
随着难民危机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冲击,欧洲各国民众对外国移民持反对态度的人数也在急剧上升。以对难民最为欢迎的德国为例,科隆事件发生后一份最新民调显示,66%的德国人认为已经没有能力接待更多的难民,而在2015年年底前的同样民调中,仅有46%的德国人这样认为。[注]《德国多地对难民态度“急速冷却”》,2016年1月18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1/18/c_128639994.htm。难民危机带来的冲击以及民众态度的变化促使具有种族主义倾向、反移民、反一体化和反全球化的极右翼政党在欧洲主要国家大选中乘势崛起,法国、德国等欧洲大国的国内政治格局甚至因此发生了改变。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虽然“前进”运动候选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最终当选,但在竞选中,以“反欧盟、反全球化、反移民”和“法国优先”为口号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也赢得了相当多法国民众的支持,[注]《法国大选勒庞风头盛 欧盟命运引人担忧》,2017年2月8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7/02-08/8143641.shtml。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2017年9月25日的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获得了最多的选票,从而继续保持联邦议院第一大党的地位,为默克尔第四次出任德国总理奠定了基础。然而,在此次选举中,右翼的德国选择党获得了12.6%的选票,从而跃升为第三大党,成为德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首个跻身联邦议院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党虽然赢得了选举,但其得票率却大幅下降,德国的政治光谱发生了明显的右转。德国选择党成立于2013年初,该党在此次选举中的主要政策立场包括:德国应退出欧元区;对欧盟进行彻底的改革,各国应将合作重点放在保护欧洲外部边界上;应立即停止无序的大规模移民,主张德国关闭边界、修改相关法律防止避难权被滥用、严格遣返不合格的避难申请者等。[注]《德国大选“稳中有变” 新政府未来面临更多挑战》,2017年9月26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7/0926/c1002-29559297.html。德国选择党的崛起固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是近年来难民危机给德国带来的冲击以及德国民众态度的变化无疑是最为直接的原因之一。
欧洲难民危机及其带来的一系列困扰与美国主导的对中东地区的干预是分不开的,可以说难民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欧洲国家追随美国外交的苦果。美国自身尽管没有遭遇大量难民涌入的困扰,但是全球化进程中人员的流动也给美国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其中最大的影响就是外来移民所导致的社会过度多元化使得美国面临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
全球化进程中人员的流动,特别是外来移民的大量进入极大改变了美国的人口结构。据美国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年美国拉美裔人口为505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6%,与2000年相比增长了43%;与此同时,白人人口为1.968亿,虽然白人人口的绝对数量和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依然是最高的,但其人口增长率仅为1%,在美国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也由2000年的69%下降至64%。因此,如果照此趋势,到2042年,白人将成为美国的“少数民族”。[注]温宪、张旸:《美国或正走向“均为少数民族”未来》,《人民日报》2011年4月7日,第22版。而到了2050年,拉美裔人口将占美国总人口的30%,非洲裔将占15%,亚裔也将达到9.2%,其他少数族裔也将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注]潘荣海:《人口结构变化冲击美国现存秩序——“弗格森事件”的深度思考》,《光明日报》2014年12月18日,第8版。美国人口结构将会呈现出十分多元化的特征。因此,在可见的未来,如果外国移民更多地涌入美国,对美国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那么,作为美国国家特性的盎格鲁-新教文化以及“美国信念”必将会受到更大的冲击,[注]相关论述参见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前言”,第2页。美国人的身份认同会发生极大危机。因此,不愿看到这种情况的美国白人,就会对特朗普所宣扬的“边境俢墙、控制移民”等主张表示认同,美国社会中的反移民情绪因而高涨。
从以上论述可以发现,21世纪以来,商品和资本的全球流动给西方国家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出于其国际战略与国内政治考虑,美欧等发达国家便提出了反国际贸易、贸易保护主义等主张;人员的全球流动及其产生的政治、文化后果则直接造成了西方国家反对外来移民的风潮。这便是所谓“逆全球化”现象发生的因果机制。
四、余 论
全球化确实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各国带来繁荣的同时也会衍生出一些问题。当前,西方主要国家在理念、战略和政策层面的逆全球化动向,有些是因为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问题使其感到代价太大而对全球化产生了不满和抵制,有些则是其不愿或不能很好地解决其国内问题而“嫁祸”于全球化。总之,近几年出现的逆全球化风潮是西方国家对其在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所做出的回应。但是,逆全球化的政策绝对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美国等西方国家存在的商品贸易逆差问题,表面上是自由贸易的结果,其实更重要的是受西方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国内需求和经济结构的影响;[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人民币汇率升值解决不了美国贸易逆差和失业问题》,第145页。另外,将本国社会问题归咎于国际贸易和全球化则根本是缘木求鱼。国际资本的流入无法弥补贸易逆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施以很大的限制,这非但不是资本流动造成的,反而是因为投资受限造成的。恐怖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借助全球化人员流动的便利,对各国造成了伤害,外国移民(难民)借助人员流动便利进入欧美等国并带来了一系列难题,但是,恐怖主义和难民从根本上讲是全球治理失灵所产生的问题,移民带来的难题则反映了一国的国内问题,这些都暴露出西方原有的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机制存在很多弊端,不是限制外来移民、走向孤立所能够解决的。因此,改革国家治理机制,与新兴国家展开合作,共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才是西方国家解决问题的可取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