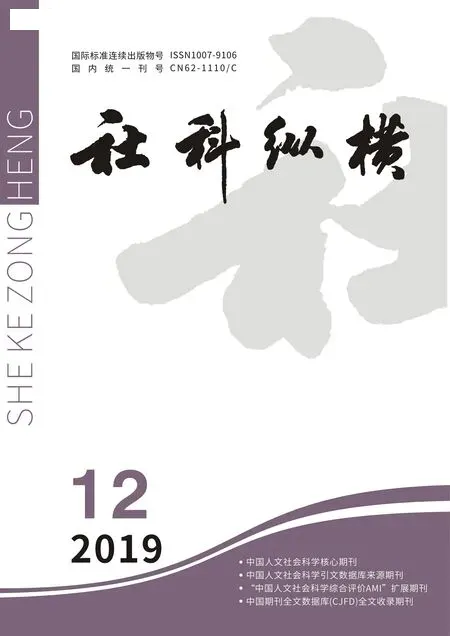丝绸之路视野下汉唐官服之革带探微
李 怡 高梦圆
(北京科技大学人文素质教育中心 北京 100083)
汉唐时期是建立在中原与西域、南方与北方等众多因素长期集聚发展之上的封建社会大一统格局的首个循环,其中官员服饰颇具时代特色。本文以丝绸之路视野下汉唐官服之革带发展变迁为中心进行探研,因为服饰是时代、历史、文化、政治、心理等多重因素交集碰撞中的折射反映,而且“如果社会处在稳定停滞的状态,那么服饰的变革也不会太大,唯有整个社会秩序急速变动时,穿着才会发生变化”[1](P367),遂具有突出的文化意蕴。
从大一统的秦汉王朝,中经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分裂,到重归一统的隋唐帝国,自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9世纪的1100多年构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而典型的朝代轮回,这不仅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且还使中国中古历史与欧洲中世纪历史发展途径迥乎不同,而陆上丝绸之路在东西之间起到了横向连通的重要作用。汉唐帝国通过丝绸之路既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开放、包容,又大规模引进并有选择地采撷各地优秀文化融汇于自身:从以佛教为代表的外来宗教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多维影响,到民众对胡食、胡乐、胡舞、胡妆等胡风胡俗的追求喜好,无不反映出汉唐文化东西融会的特点。作为汉唐官员礼服中实用性与礼仪性兼具的重要配饰——革带,虽然制出商周,但其具体构成的带钩、带身以及不断礼节化的过程,均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而逐渐变化。
革带,即汉唐时期官员礼服用皮革质腰带,古称鞶革,由于革带常用于系鞶囊①,因此又称鞶带。《周易·讼》:“上九,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白虎通义》卷下“衣裳”条:“以有鞶带者,示有事也。”革带通常以宽阔的皮条为之,端首缀以带钩,使用时系束在礼服之外,前服蔽膝,后系印绶,左右悬挂大佩或者杂佩。从形制上看,完整的革带由带身和带钩组成。带身,乃无装饰的皮革质腰带。王国维在《观堂集林·胡服考》中考证到:“古大带、革带皆无饰,有饰者,胡带也。后世以其饰名之,或谓之校饰革带(《吴志·诸葛恪传》),或谓之鞍饰革带(《御览》引《吴录》),或谓之金环参镂带(同引《邺中记》),或谓之金梁络带(《金楼子》),或谓之起梁带(新旧两《唐书·舆服志》),凡此皆汉名,胡名则谓之郭络带。”带钩,省称钩,是用于扣拢腰间皮带之钩,以玉、金、银、犀、铜、铁等材料制作。具体到带钩本身,往往由钩首、钩身和钩钮三部分组成,钩首和钩钮分别用于革带两端的连接,而造型变化则主要在钩身尾部:有铲形、棒形、耜形、鸟形、兽形、人形等区别,纹饰加工有雕刻、错金银、镂花等数种,华丽者还于其中鎏金镶玉、嵌绿松石宝石玛瑙等。
带钩最早为北方游牧民族使用,因此具有许多音译之名,如师比、鲜卑、胥纰、犀毗等。《战国策·赵策二》:“赐周绍胡服衣冠、具带、黄金师比,以傅王子也。”《楚辞·大招》:“小腰秀颈,若鲜卑只。”王逸注:“鲜卑,衮带头也。言好女之状,腰支细小,颈锐秀长,靖然而特异,若以鲜卑之带,约而束之也。”《史记·匈奴列传》:“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胥纰一。”司马贞索隐:“《战国策》云,‘赵武灵王赐周绍具带黄金师比。’延笃云,‘胡革带钩也。’则此带钩亦名‘师比’,则‘胥’、‘犀’与‘师’并相近,而说各异耳。”《汉书·匈奴传》:“黄金犀毗一。”颜师古注:“犀毗,胡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谓师北,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春秋时期带钩传入中原,先用于甲服,后来王公贵族普遍使用,战国至两汉极为盛行,三国以后被带扣取代,但直至清代前期,仍未完全绝迹,尤其是出于怀古心理,部分朝代大礼服仍喜用之。《孟子·告子下》:“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史记·齐太公世家》:“鲁闻无知死,亦发兵送公子纠,而使管仲别将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带钩。”
革带制出商周,与丝帛质大带配合使用,以起到固定服饰的实用功能。《礼记·玉藻》:“其颈五寸,肩革带,博二寸。”孔颖达疏:“凡佩系之革带者,以韠系于革带,恐佩系于大带,故云然。以大带用组约,其物细小,不堪悬韠、佩故也。”随着春秋时代带钩的中原化与西汉时期凿空之旅的开疆拓土,革带的实用性与融合性极为符合时代的需求,汉魏时期遂不断礼仪化、规范化。《说文·巾部》:“带绅也。男子鞶带,妇女带丝。”段玉裁注:“《内则》曰,‘男鞶革,女鞶丝。’《革部》‘鞶’下云,‘大带也。’按,古有大带,有革带。革带以系佩韨,而后加之大带,则革带统于大带,故许于绅、于鞶,皆曰大带。实则《内则》之鞶,专谓革带。此称《内则》者,谓鞶统于绅,佩系于鞶也。”在汉魏官员服饰制度正统初创之后,革带的礼服配饰地位更为巩固,史籍尤其是正史往往记述颇详。《晋书·舆服志》:“革带,古之鞶带也,谓之鞶革,文武众官牧守丞令下及驺寺皆服之。其有囊绶,则以缀于革带,其戎服则以皮络带代之。”《隋书·礼仪志七》:“(隋制)革带,案《礼》‘博二寸’。《礼图》曰,‘珰缀于革带。’阮谌以为有章印则于革带佩之。《东观记》,‘杨赐拜太常,诏赐自所著革带。’故知形制尊卑不别。今博三寸半,加金缕鞢,螳蜋钩,以相拘带。自大裘至于小朝服,皆用之。”
丝绸之路贯通之后,其东西胡汉长期交融交汇的成果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而革带之制也更加等级森严、冠冕威仪。唐代百官祭服、朝服、公服等大礼服的革带承袭隋制,诏令使用金质带钩,称金钩鞢②。《旧唐书·舆服志》:“(侍臣衮冕)带,钩鞢。”《新唐书·车服志》:“(群臣具服)革带金钩鞢,假带。”官员革带之制以带钩质料与带身色彩区别于天子革带,前者为黑皮带、金钩鞢,后者为白皮带、玉钩鞢。《新唐书·车服志》:“(天子)革带,以白皮为之,以属佩、绶、印章。鞶囊,亦曰鞶带,博三寸半,加金镂玉钩鞢。”唐代以后,因革鞓之带的使用,革带之制渐衰。两宋革带就较唐代有所不同。《宋史·舆服志四》:“祭服有革带,今不用皮革,而通裹以绯罗,又以铜为饰。”明代恢复革带古制,大礼服所用革带即恢复唐制,并沿用至清。《明史·舆服志二》:“嘉靖八年谕阁臣张璁,‘衮冕有革带,今何不用?’璁对曰,‘按陈祥道《礼书》,古革带、大带,皆谓之鞶。革带以系佩韨,然后加以大带,而笏搢于二带之间。夫革带前系韨,后系绶,左右系佩,自古冕弁恒用之。今惟不用革带,以至前后佩服皆无所系,遂附属裳要之间,失古制矣。’帝曰,‘……卿可并革带系蔽膝,佩、绶之式,详考绘图以进。’”
综上所述,汉唐官员革带虽制出商周,但其发展变迁、不断礼仪化的进程却与丝绸之路的连通交融息息相关。丝绸之路实现了汉唐历朝君主开疆拓土的政治军事目标,取得了与域外贸易交流的主动权,开启了与他者文明对话的通道,封闭已久的黄土文明得以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碰撞交汇,而正是这种相互影响力催生的复杂嬗变塑造了汉唐时期的文化特质及时代精神,这其中一个明显的表征就是汉唐时期胡汉服饰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借鉴,以革带为代表的服饰最终胡汉融合并不断正规化、礼仪化。
第一,汉唐时期革带之制既融合胡族元素于华夏服饰之中,又排斥拒绝胡服,与当时丝绸之路连通以来内外环境变化所影响的汉人夷夏观有着较大关系。两汉之时与匈奴的长期征战使其给汉人留下难以磨灭的残暴印象。《汉书·匈奴传上》:“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饮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字。”因此,两汉时期胡汉关系长期处于对立甚至敌对状态,人们对于胡服亦是较为排斥,夷夏之防是主流观念,故革带之制以汉为主以胡为辅。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持续连通,胡人政权常常启用汉人为官来维持其对广大汉人的统治,而不少汉族士人也怀揣“以夏变夷”的美好愿景入仕胡人政权,胡汉关系随之朝着缓和方向发展,传统的夷夏观也因此有所变化,革带之制也胡汉交融。隋唐皇室具有浓郁的胡族血统,更是摈弃胡人为蛮夷之观念,使夷夏和睦,出现了新的夷夏观——“守在四夷、恩威并用”,“怀柔远人,义在羁縻”成为时代的主流,对此变化的鲜明反映就是革带之制不仅胡汉兼容,而且进一步制度化、礼节化。总之,汉唐时期对革带胡族因素的态度总体上表现为由排斥到接受的转变过程,遂使胡汉交融的革带之制不断朝堂化、规范化。革带之制在汉唐之际不断发展的趋势是该时期胡汉民族融合和夷夏文化交流日益加强的突出显现。正如鲁迅在《坟·看镜有感》中所言:“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
第二,汉唐时期革带之制的发展变化是丝绸之路连通以来几百年一直进行着的民族大融合、文明大交汇的具体展现。南宋朱熹指出:“中国衣冠之乱,自晋五胡后来遂相承袭,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2](P896)此话虽有所偏颇,但却指出汉唐时期胡服盛行的状况。胡汉交融的革带形制功能变迁是汉唐时期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等多重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一方面,经济发展推动纺织技术的革升,皇权集聚则不断强化服饰等级规范,由此推动汉唐时期官员革带的不同风尚:汉代质朴稳重、魏晋南北朝洒脱浪漫、唐代华贵大气等时代特征都反映在革带的工艺、形制、寓意之中。另一方面,民族间的交流互动促进了革带胡汉风格的交融。“种族与文化”是汉唐时期突出的时代风格,胡汉之间的不断交融渗透已是突破单一、沿袭的过往格局,汉族胡化、诸胡汉化广泛存在。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指出:“总而言之,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是也。”[3](P71)因此,汉唐诸朝一方面希望通过官员革带制度的详细制订来彰显国威,更重要的是借此宣扬自我乃中华正统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又由于维护胡汉交融的现状且古礼繁杂难行的现实状况而促成了革带之制不断规范礼仪化。虽然森严的官员等级依旧,翔实的舆服脉络继续传承,但是汉唐官员服饰的革带制度已更多适应了时代变迁的要求,在崇尚古礼以示正统的维度之下,将胡族元素加以改进并提升为大礼服配饰以发挥其实际作用,遂使汉家制度胡族衣裳的胡汉复合制应运而生,服饰的文化意义十分突出!
注释:
①鞶囊,侧佩于腰的革囊。两汉为官员盛放印绶之袋,后逐渐演变为象征身份等级的饰品。
②鞢,承钩之具。《玉篇·角部》:“鞢,角也。”承钩之具应与钩相勾牵,使其不脱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