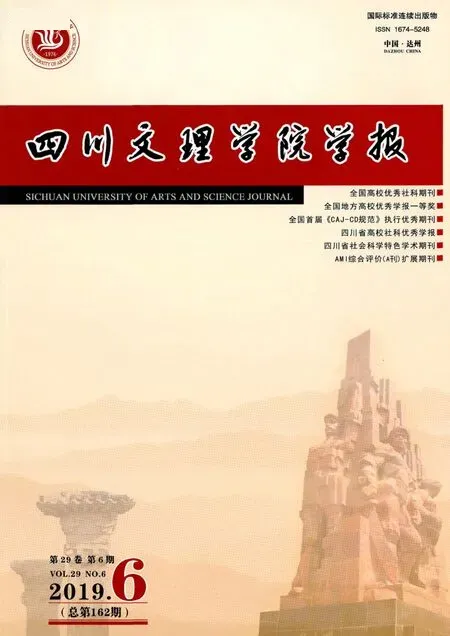浅谈文学话语与作文教学
钟 钦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 高教中心,四川 达州 635000)
我们的教育目标,是让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全面发展,既有健康健全的人格和完美充分的个性,又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而文学教育兼及德育、智育和美育数者,在传播知识的同时,还承担着通过审美教育,塑造新的、全面健康发展的人性及完善道德之功用。早在1912年,蔡元培先生就在《对教育方针之意见》中,率先把美育确立为教育方针之一。然而这些年来的语文课堂教学,虽说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却大体上搞成了似是而非的思品课、科学课、活动课、表演课,唯独看不到语文课,而语文课上的文学话语近乎完全消解。这样一来,语文教学的重要环节——作文教学,就走入了公式化、教条化、程序控制化的死胡同。一说到作文教学,许多人便“怎一个愁字了得”。教师教作文,想尽千方百计,使出浑身解数,结果收效甚微。学生写作文,不是啰啰嗦嗦,废话连篇;就是干瘪乏味,语言呆板。而且千篇一律,千文一面。枯涩单调,毫无生气。
学生作文为何成了这般让人痛心疾首的新八股文?究其实质,乃是作文教学时,未能强化甚至根本没能有意识地移植文学话语。
“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语言作为一种符号,标志着人类文化的至高成就,所以恩斯特·卡西尔把人称为“符号的动物”。“一个人的语言交际能力包括:1.阅读能力;2.口语表达能力;3.文字表达能力。而这三种能力的培养和提高,都需要学习文学话语。因为文学话语是“最具有准确、鲜明、生动的特点的语言”[1]3。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求,是写作的唯一载体,离开语言,离开文学赖以存在的实体,对文学就无法认识。所谓文学话语,是指大众口语的结晶,是文学家用来塑造艺术形象的话语,它具有高度的形象性和直观性。文学话语是“对自然话语的表现”,[2]“由于文学话语不直接陈述现象,其语境纯属虚构,因而它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自由性”,[3]在进入文学话语的世界时,非存在的、符号的、抽象的语境,使人们意识到面对的不是现实的客观世界,而是由虚幻的语境建造的时空,虽然是具体的、可感的,呈现于主体意念中的,但却和外在语境不再相联,是虚拟的现实,灵境的世界。
人的所有能力,无不以语言能力为其核心和前提。人对语言有着下意识的敏感,人对语言的感知与人对其它事物的感知有着本质的区别。“语感是在视听当下不假思索地从感知语音、字形而立刻理解语音、字形所表示的意义的能力。”[4]3-8语感的产生与形成虽然离不开人所特有的先天禀赋,但其语感“之所以变得灵敏、深刻、丰富、优美,多半是学校教育,主要是语文教学创造的结果。”[4]211叶圣陶指出:“语言的训练,我以为最要紧的是训练语感,就是对语文的敏锐的感觉。”[5]中小学的非语文学科重在“说什么”,所教学的是语言所表达的内容;语文学科重在“怎么说”和“为什么这么说”,教学应是如何进行表达,侧重于语言表达的形式和技巧。语文教学的重要环节的作文教学,就是学习、研究、掌握“怎么说”才能说得更好、更鲜明、准确、生动。这是作文教学的终极目标。大凡优秀作品,其语言都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要使学生感悟领会其独特的语言表达手法,进而掌握这种表达形式和技巧,是语文教学的重点,更是作文教学的重点。只可惜许多语文教师在进行作文教学时,一味强调“说什么”,不注重“怎么说”,或者至多强调一下要“言有序言有物”。对于怎么运用好语言这个载体,使之表达得更准确、更鲜明、更生动,也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却因未移植文学话语而无从谈起,一片茫然,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事倍功半。“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刘禹锡《视刀环歌》)。
就写作的实质来讲,写作就是作者将获取的信息,通过想象运用语言文字,再巧妙地重组起来传情达意、反映其心目中的世界的过程。法国博物学家、作家布封指出:“只有写得好的作品才是能够传世的。……如果他们写得无风致、无文才,毫不高雅,那么,它们就会淹没无闻……风格即是人本身。”[6]布封认为作品能否传世,关键在于“写”得怎么样,在于语言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个人特色的风格。文章靠语言生存于世。写文章首先得把语言写得美,并且得有个性特色。语言的好坏,不在于用了多少词语,不在于写得多么花哨顺溜,而在于准确充分地传达出此时空状态下此人的情绪。话有三说,巧说为妙。著名作家贾平凹谈到文学创作的语言时,有过十分精辟的论述:“一部好作品,使多少人笑之忘我,悲之落泪,究其竟,不过是一堆互不相连的方块字呢!然而,这些方块字,凑起来,有的是至情至美,有的却味如嚼蜡……我觉得,语言是作品的眉眼儿,作品有了美好的灵魂,再配上一副好眉眼儿,天下的读者就要一见钟情了!”[7]文章靠语言生存,语言靠词、句、标点活着。离开它们,一切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左丘明《左传·僖公十四年》)。任何词语、标点的增删、调换,句式的改变都会使文章发生嬗变。老舍先生说:“写文章,用一字,造一句,都要仔细推敲,写完一句;要看看全句站得住与否,每个字都用得恰当与否,是不是换上哪一个字,意思就更明显,声音就更响亮,应知一个字要起一个字的作用,就像下棋使棋子那样。一句,一段写完之后,要看看前后呼应吗?联贯吗?字与字之间,都必须前后呼应,互相关联。”[8]122这正所谓“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4]155
自然的和人类创造的所有的美的事物中,话语美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依存于对象美。赞美美的对象时,话语可能是美好的,也可能是丑陋的;鞭挞丑的对象时,话语可能面目可憎,也可能尽态极妍。话语美不同于世间万事万物的美,但又可以具有世间万事万物的美,它有独特的建筑美、音乐美、色彩美、形象美、情感美、意趣美等等。而汉语因其义、音、形、像、数、理六者互为一体的特质,就更有其别的语言难以望其项背的美。汉字内中包孕音韵、意象、物相、数理的基因,具有空间性、可视性、音韵性、意蕴性、数理性,表现出一种建筑美、绘画美、音韵美、意境美、数理美。
文学话语本身是具有审美价值的话语,它同自然话语的差别,不是性质上的而是程度上的。其对于审美效果的追求,成为其自身审美价值确立的依据。它力求描绘具体、生动的意义和形象,构成活动变化的人生图画、自然风景画、心理解剖图,竭力追求一种感性的、具象性的审美对象表现,即让人在想象中建立一个栩栩如生的对象世界。音韵、节奏、词汇、句法、修辞、语篇等,都力求在同话语意义上的联系中,表现出文学话语的审美价值。无论自然话语和文学话语,都包含着一定的信息量。熵是信息量大小的度量。话语的熵,“指的是在语言的随机试验中,随机试验不定度的大小。在接收到话语符号之前,熵的大小依赖于已出现的语言符号的数目和出现的概率,在接收到语言符号之后,不定度被消除,熵等于零。话语符号的熵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n为某语言中语言符号的数目;Pi为语言符号的出现概率;K是常数;H为熵,熵的单位是比特。”[9]实验测得英语27个字母(包括空白)的熵为4.03比特;俄语32个字母(包括空白)的熵为4.35比特;汉语的熵(包括在一个汉字中的熵)为9.65比特。而文学话语的熵值比自然话语的熵值就更大。作家王小波就主张文学话语必须包含极多极大极丰富的信息,并且极端精美。如杜拉斯(Dur as,M)《情人》的第一句:“我已经老了。……”无限沧桑尽在其中,言有尽,而意无穷。正如唐代史学家刘子玄在其所著的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史通·叙事篇》中所说:“言近而旨远,辞浅而意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
一般说来,影响和制约文学话语的熵及审美价值的主要因素有语音的配置、词语的运用、句子的结构与长短、修辞方式等几个方面。
第一,语音方面。南朝梁著名文学家、诗律学家沈约在《谢灵运传论》中云:“夫五色相宜,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语音系统的任何要素的选择、配置、组合,都会造成不同的风格效果。在汉语里,声、韵、调的排列,语音的平仄对仗、抑扬顿挫,音步的分列,音节的重叠,合辙押韵的韵脚、头韵、内韵和节奏,双声叠韵;谐声双关,语气语调的变化等,不单可以表达声音上的和谐悦耳,还有递进情感,开拓意义,提高审美价值的作用。“表现柔婉缠绵或悠扬凄清之情可以多用平声字,表现幽咽沉郁之情可多用入声字,上声字常用来表现矫健峭拔的风格,去声字常用采表现雄阔悲壮的情调。”[10]例如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全词97字,其中有57个舌齿音。这啮齿叮咛的声吻,将女词人悲郁惝恍、孤寂凄苦的心绪表露无遗,词中还运用了“黑”“得”等“险韵”。特别是创造性地运用了九组叠音字,不仅具有声韵回环美;更是辅之以双声舌齿音,使词句更富于情感色彩和音乐美,把叠宇艺术出奇制胜地推至登峰造极之境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词人寻觅无着、哀婉凄绝的精神状态。
第二,词汇方面。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词语有自己的生命,更有自己的个性。即使是同义词也往往并不完全同义,尤其是感情色彩上并不完全等值。同义词好比孪生子,在生活中,我们总是发现,即便完全是在同一环境中长大的孪生子,其性格脾气、外貌禀赋、言行举止等不完全相同,甚至完全不同。滕守尧在《审美心理描述》中分析“珠圆玉润”一词道:
在用“珠圆玉润”去比喻声音时,不仅是传达出一种真切的生理感受,也不仅仅是造成一种和谐感和舒适感,而且还有一种更加微妙的社会性联想;珠和玉都是人间稀有的宝物,一方面极为少见;另一方面又代表着某种华贵和高雅的性质。当用它们来比喻一种声音时,这种社会性的联想就为这种声音规定了某种更为朦胧微妙的高雅性和稀有性。
汉语是高度发达的语种,其同义词最为丰富。比如,表示“看”的词,仅单音节词就有70余个,而联绵词和合成词就更不知凡几。由于同义词在意义上的轻重、范围的大小、感情色彩、语体色彩、搭配对象和词性与句法功能上的差别,对于话语的熵及审美价值,作用巨大。例如:母亲、妈妈、母、妈、娘(另有:家母、慈亲、慈闱、寿堂、萱堂、堂萱、萱闱、媪、阿奶、阿婆、阿者、娘子、娘娘、内亲、姥、阿母、奶子、妈咪等)这组同义词,都是对母亲的称谓,有庄重的、有亲昵的、有口语、有俗称、有方言、有外来词等等,在不同的语境中,须使用不同的称谓,否则就不和谐不协调。其它类似的色彩词、古语词、外来词、口语词、方言词、行业词、流行词、成语、谚语、格言、惯用语、歇后语等,都可以使文学话语的熵和审美价值产生差异,形成不同的风格。
第三,句法方面。句法是话语结构的法则和规律。同一个意思,可以用不同结构的句子来表达,句子结构的不同,往往能够体现不同的精神个体性,传达不同的话语气韵和熵。如鲁迅《秋夜》开头“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它的意思至少可用下面几种不同的句子来表达。
1.从我的后园看出去,墙外有两株树,都是枣树。
2.两珠枣树都在墙外,在我的后园可看见。
3.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枣树。
4.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它们在墙外。
5.墙外的两株枣树,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
6.墙外的两株枣树,可以看见的地方,在我的后园。
7.墙外也有树,两株枣树,我的后园可以看见。
8.墙外也有两株枣树,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
9.树少,两株,都在墙外,是枣树,我后园可看见。
10.在我的后园,不是可以看见墙外的树吗?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呀。
略加咀嚼,滋味各异,感情色彩风格色彩便不相同。“采用不同的句式,可以表现出不同的风格。一般地说;常式句宜于表现平易典雅的风格;变式句则宜于表现新颖奇崛的风格;长句宜于表现委婉细腻、低沉深厚的风格情调,短句则宜于表现明快高昂、豪放雄壮的风格;而语素的重叠往往比单音节词表达的感情色彩更为鲜明。”[1]135例如:只见山。在左。在右。在前。在后。在脚下。在额顶(余光中《丹佛城》)。这既是短句,也是变式句,新颖奇崛怪异有趣,感情色彩相当明快。
第四,修辞方面。叶圣陶在《作文论》中说:“修辞的功夫所担负的就是一句话不只是写下来就算,还要成为表达这意思的最适合的一句话。”修辞方式,是指在特殊语境中,为了增强话语或文章的表达效果,而创造性地运用全民语言形成的具有特殊修辞效果的言语格式和所运用的一些修饰描摹的特殊方法。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共列举三十八种修辞方式:材料上的辞格九种,意境上的辞格十种,词语上的辞格十一种,章句上的辞格八种,常见的修辞方式主要有:比喻、比拟、借代、拈连、婉曲、双关、仿拟、降用、反语、排比、夸张、反复、对照、通感等。朱自清的《绿》仅千宇左右,光比喻、比拟、夸张、较物,就有五六十次,话语风格很是绮丽。鲁迅独特的语言风格的形成,和反语、借代、夸张、仿拟、谐音、双关、降用、升格、起跌、旁逸、例引、飞白、拆词、转类等修辞手法的运用分不开。为了适应复杂的话语环境,修辞方式常常需综合运用;多种辞格综合运用,能够“相映成越”“相得益彰”,使话语表达更加灵活多变,多姿多彩;产生出更为动人的光彩与魅力。
语音、词汇、句法和修辞在形成文学话语熵和审美价值上的功用,不是单一运用的单纯的话语手段,而是综合并用,同作品的思想形象、风格情调以及整个作品的体裁、语体,和谐统一,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作为本身具有审美价值并在世间所有话语集结的话语族中最为精美的文学话语,其本身便赋有下列特征:
一、形象性。文学话语形象性主要表现在它能够绘声绘色地状物摹形,人性物态生活图景,莫不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灼灼状桃花之艳,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这段刘勰赞美《诗经》的语言的话,就很形象很具体地指明了文学话语的形象性。
二、精确性。“义典则弘;文约为美”(刘勰《文心雕龙》)。片言百意。文学话语的精确性,是指用最经济的话语恰如其分地表现丰富的生活与思想。文学话语的精确,就是要凝炼蕴藉言简意赅,文学话语不精确,艺术形象就会失真。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原稿的“采腊梅花”到后来的“折腊梅花”,就是语言精确的表现。“一切诗文,总须字立纸上,不可字卧纸上。人活则立,人死则卧,用笔亦然”(袁枚《随园诗话》)。这种形象的能活立纸上的精确的字词,就是诗眼、文胆。比如:王安石的“绿”字,李清照的“瘦”字,黄山谷的“用”字,杜甫的“过”“湿”字。
三、情感性。文学是主情的,情是文学话语的灵魂。白居易《与元九书》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文章的感情正是通过蕴含情愫的词语,倾吐出来感染读者。语言强烈抒情的作品往往最感人。无论是情溢言表还是情蓄言中,无论是情隐言外还是情融意境,概莫如是。四、音乐性。话语自身音调的高低清浊、节奏的长短缓急有机组合,就会逼真传达现实生活的音响,使作品音调和谐、声韵抑扬顿挫、节奏鲜明、语流流畅、读着上口、听着悦耳,给人以音律美、句式美、文采美、风格美的美感享受。“一句话里有很高的思想,或很深的感情,而说得很笨,既无节奏,又无声音之美,它就不能算作精美的语言。”[8]55此外,文学话语还具有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个人性、全民性、世界性、模糊性等特征。
文学话语环肥燕瘦,千姿百态,各有其美,有的简洁洗炼,有的缜密细腻,有的隽永蕴藉,有的明快通俗,有的朴素清淡,有的瑰丽浓艳,有的庄重典雅,有的峥嵘峭拔,有的豪放飘逸,有的沉郁悲慨,有的调侃怪异等等。然则,“靡辞无忠诚”(孔融《临终诗》),“书恶淫辞之淈法度也”(扬雄《法言·吾子》),“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挚虞《文章流别论》)。文学话语要美,须得炼字、炼词、炼句、炼意。“炼辞得奇句,炼意得余味”(《邵雍.论诗吟》),言尽意无穷。此其一也。文学话语要美,须得话语形式与话语内容完美统一。此其二也。话语的形式美,须要体现对称均衡法则、节奏韵律法则、调和对比法则、音律美法则、文采美法则、句式美法则,最重要的是还要体现道法自然的自然美法则。“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李耳《道德经》)。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形式到了极至就无形式。话语的内容美,主要指话语内容的思想美、形象美、情感美、意趣美、哲理美、逻辑美等。此其三也。
文学话语移植进作文教学,有以下一些路径。一是语言具有情味韵味,用多种手法使其具有情感、画面感、动感,让作文语言鲜活精彩起来。例如学生作文“春风从窗户吹进来”,就可以升华为“和煦的春风一袭飘飘绿裙,轻轻柔柔地从窗户飞进来”。句子就有了意境美。鲁迅的《风波》写七斤嫂看见七斤的光头便忍不住生气:“怪他恨他怨他,忽然又绝望起来,装好一碗饭,搡在七斤的面前。”六个动词活灵活现地写出了七斤嫂的生气恼怒绝望。二是要恰当修辞,善用比喻,学生作文写不长写不好的困局就会迎刃而解。三是写人叙事的作文,要写好肖像、语言、行动、心理、环境的细节,化抽象、概述为具体,严监生临死时的两根指头,祥林嫂的肖像,孔乙己“多乎哉不多也”的语言,令狐冲与田伯光酒楼的坐斗,季羡林月下夹竹桃的美景等,这些细节,无不令人拍案叫绝。四是时少用或不用程度副词,而是使用形象性的语言,如“很黑”“挺白”“十分热”就不如“漆黑”“雪白”“火热”形象,“极高的峭壁上”远不及“入云的峭壁上”。五是少用甚至不用成语,要写就还原成语原本的意味,比如不用“万紫千红”,而是去把那些花开的色泽、情状、香味、种类具体地展现出来。或者是巧用、活用、化用成语,有学生作文写出了“一摞摞作业本与张老师举案齐眉”的妙句。六是一个意思,试试不同的表达方式,找到最好的。尽量使语言有陌生感、原创性、含蓄性、象征性、暗示性。“她脸红了”“她脸上腾起一片红霞”“她的脸红得像苹果”这类陈旧老套的语言应该由“她脸上噼里啪啦盛开出一片粉嫩桃花”所取代。七是每句话中,少用或不用“的”字,能删就尽量删掉。八是句式富于变化,长句、短句、整句、散句、常式句、变式句交替使用。“四周尽是山,起伏逶迤,连绵不绝”的表现力自然赶不上“只见山。在左。在右。在前。在后。在脚下。在额顶”。九是对话时,每个人说话不要超过十三个字。还要有说话者的语态描写。十是每一段和相邻的段落中,不要出现相同的词汇。十一要追求语言的音韵效果。汉语独有的声、韵、调体系,词根合成的词汇,众多的三字格词、四字格词,谚语、俗语等,本身就有内在的音乐性,这一切都使汉语音韵美妙。十二若有闲笔,自然生花。话有三说,巧说为妙,语言自然就会鲜明、准确、生动。
话语是实际的意识,当一个人的思想意识成熟之时,其话语——表达意识的常用格式也逐渐稳固下来。这些常用的稳固的词汇、句法等表达方式,便形成了一个人的话语指纹。话语最具民族个性,是故话语具有指纹性。汉语的话语指纹,乃是汉语特有的语音、句法、词汇及修辞系统。一般个人的话语指纹,是其习用词语和表义方式。什么样的人讲什么样的话,怎样的人就有怎样的讲话方式,即使两个人用同样的字句,说同一件事,也各有各的说法。因此,在学生思想意识成长之期的作文教学中,移植而且强化文学话语,丰富、提高、规范、美化学生的话语指纹,开拓、改变干瘪或罗嗦的话语图式,逐渐淡化进而彻底消解学生腔,让学生作文百花齐放争奇斗妍,使其“能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从而使全民族的大众话语更丰富、更纯洁、更鲜明准确生动、更富有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