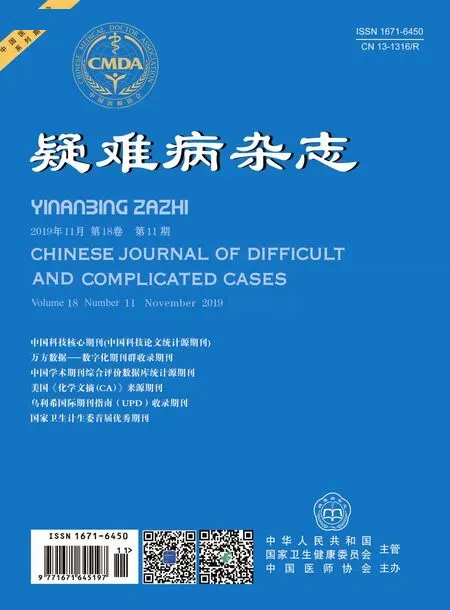管状胃代食管在食管下段癌根治术消化道重建中的临床价值
王会恩,薛文飞,赵庆涛,于雷,王志康,谷建琦,段国辰
目前食管癌在我国仍然是临床肿瘤中最常见疾病[1],而手术是早中期食管癌最佳治疗方式[2]。关于消化道重建,目前国内大量临床资料显示,管状胃以其较少的术后并发症,明显优于全胃组[3-5],且逐渐被大多临床医师采用。然而对于食管下段癌,因其肿瘤位于食管下段且近贲门,大部分弓下吻合即可,且占据胸腔位置较小,关于是否需行管状胃文献报道较少,且存在争议,本研究收集食管下段癌行管状胃代食管重建患者50例,观察管状胃代食管重建在治疗食管下段癌中的临床价值,为临床应用提供参考,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2011年7月—2015年10月河北省人民医院胸外科收治的术前经病理证实为食管下段癌且无合并心肺或肝肾功能不全患者100例,拟行食管癌根治术。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管状胃组和全胃组各50例。管状胃组男36例,女14例,年龄46~79(65.4±6.5)岁;病变长度0.6~7.0(3.4±1.9)cm;病理分期:Ⅰ期8例,ⅡA期20例,ⅡB期12例,ⅢA期10例;术后化疗38例。全胃组男38例,女12例,年龄48~80(64.1±6.9)岁;病变长度0.7~8.0(3.6±1.8)cm;病理分期:Ⅰ期6例,ⅡA期22例,ⅡB期13例,ⅢA期9例;术后化疗35例。2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或家属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手术方法 所有入组患者均由同一组术者完成手术。2组患者均全麻下插双腔管,均经左胸第7肋间开胸,行食管癌根治术。对照组以传统全胃代食管重建消化道,术中充分游离胃体,距贲门约2 cm切断,沿食管床将整个胃上提以圆形吻合器与食管吻合。观察组切断胃左动脉、胃网膜左动脉、胃短动脉和胃右动脉近端的2~3支,保留其余的胃右动脉分支、胃网膜右动静脉,在其外侧切断大网膜,以直线切割缝合器,从胃底部最高点小弯侧2 cm为起点,沿胃小弯与大弯平行,一并切除贲门,切开直至胃底制成顺行3~4 cm窄管状胃,并用3-0普通线间断缝合浆肌层,完全包埋胃小弯侧,最后同法以圆形吻合器行管状胃食管残端吻合。2组术后行化疗方案均为多西他赛+铂类。
1.3 观察指标与方法
1.3.1 围手术期指标: 包括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淋巴结清扫情况、术后住院时间、手术费用。手术时间即从切皮到缝皮结束;术中出血以实际情况统计出血量;淋巴结清扫情况以术后病理结果中报告淋巴结个数为准;术后住院时间以做完手术到顺利出院时间;手术费用指所用耗材相关费用(包括低值耗材)为基准。
1.3.2 呼吸功能检测:所有患者术前1周,术后1个月、3个月、6个月和12个月行肺功能检查,以实际值占预计值的百分比表示。肺功能监测指标包括肺活量占预计值的百分比(VC%)、最大通气量占预计值的百分比(MVV%)、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的百分比(FEV1%)。测定时均为进食2 h后,以排除在正常胃排空情况下进食对肺功能的影响。以△VC(术前检测指标-术后测定指标值)、△MVV(术前检测指标-术后测定指标值)、△FEV1(术前检测指标-术后测定指标值)反映手术对肺功能的影响情况。
1.3.3 生活质量评定:欧洲癌症研究组织(EORTC)的生命质量测定量表QLQ-C30于1987年制定,结合QLQ-OES24食管癌专用量表用于食管癌术后患者生活质量研究,经过临床证实能够较好地反映食管癌术后患者生活质量状况[6]。结合我国国内肿瘤患者生活质量的评定方案制定生活质量问卷调查表,如吞咽困难、反酸、烧心及胸胃综合征等[7],总分100 分,≥81 分为生活质量满意,对术后患者进行生活质量评价。
1.3.4 术后并发症: 包括吻合口瘘、胸胃综合征、肺部并发症、心血管并发症。吻合口瘘以胸腔引流为胃液或食管造影提示为金标准,胸胃综合征、肺部并发症通过胸片或CT证实,心血管并发症以术后心电监护情况证实。

2 结 果
2.1 2组围手术期指标比较 2组患者手术过程顺利,无死亡病例。管状胃组手术时间、手术费用多于全胃组(P<0.05),而2组术中出血量、淋巴结清扫数、住院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2组肺功能比较 2组食管下段癌患者术前VC%、MVV%、FEV1%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组患者术后1、3、6、12个月△VC、△MVV、△FEV1均呈逐月下降的趋势(P<0.01),而2组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3 2组生活质量比较 术后第1个月、3个月,2组生活质量评价基本相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术后第6个月、12个月管状胃组明显优于全胃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2.4 2组术后并发症比较 2组术后吻合口瘘、胸胃综合征、心血管并发症、肺部并发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见表5。

表2 2组患者术前肺功能比较
3 讨 论
食管癌切除术关键之处是消化道重建,消化道重建最常用的替代物是胃,缺点是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较高,生活质量较差[8-9]。吻合口狭窄的发病率为9%~16.1%[10],反流性食管炎的发病率为36%,胸胃综合征的发病率为0.92%~4.9%[11],术后吻合口瘘的发病率为2%~15%[12-13],而管状胃以其特有的优势逐渐被推广,具有以下优点: (1)管状胃体明显减少对心肺压迫,可明显减少术后心肺并发症。(2)管状胃切除部分胃组织可减少胃酸分泌,减轻术后胃食管反流。(3)管状胃以其与食管相似的管径,可减少胃内食物潴留[14]。多数认为食管术后吻合口瘘是最为严重的并发症,影响因素较多[15],然而大部分研究表明管状胃与全胃代食管吻合口瘘发生并未增加,本研究统计管状胃并未增加吻合口瘘几率,国内有部分研究表明管状胃可以降低吻合口瘘发生[16]。本研究发生吻合口瘘考虑与以下两点有关:(1)管状胃的胃小弯侧有较长的切缘导致血运稍差;(2)胃小弯侧使用切割缝合器闭合后,间断包埋不彻底。相关研究也表明管状胃管径越细,发生吻合口瘘的几率越小[17],因此管状胃直径也是影响因素之一。
大多数研究表明,管状胃容积较小可以降低胸胃综合征的发生率[18-19]。李晓明等[3]认为管状胃可以降低吻合口狭窄的发生率,而Heitmiller等[20]则认为吻合口狭窄的发生率管状胃组与全胃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提倡管状胃直径不宜过小,以4 cm为宜。刘兰波等[21]的一项Meta分析总结了4 137例患者,表明管状胃组与全胃组比较,吻合口瘘发生率、吻合口狭窄发生率2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反流性食管炎及胸胃综合征发生率管状胃组显著低于全胃组。本研究针对食管下段癌患者同样证实了管状胃代全胃在食管癌根治术中行消化道重建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

表1 2组患者围手术期指标比较

表3 2组患者术后肺功能变化比较

表4 2组患者术后生活质量评价比较分)

表5 2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例(%)]
食管癌术后患者早期肺功能降低的影响因素包括以下几点[22-25]:(1)术中膈肌切开,导致膈肌功能减弱,限制呼吸,手术切口创伤肋间肌导致呼吸肌功能障碍,以及胸壁创伤;(2)胸腔引流管刺激限制患者通气功能,导致肺膨胀障碍;(3)术中肺组织及肺门受到挤压和挫伤,使肺泡表面活性物质破坏,导致肺内炎性反应;(4)全麻时气管插管损伤呼吸道,导致分泌物增加,小气道痉挛,影响呼吸功能;(5)术中迷走神经切断、全麻对肠功能的影响导致肠胀气亦可影响肺通气[26]。以上因素的影响可随着术后的恢复而逐渐消失,但仍不会达到术前水平,主要是对胸腔胃的影响。因为传统全胃代食管组患者随着进食量的增加,胸腔胃开始明显膨胀,压迫肺组织,使肺容积减小,影响肺通气量;而管状胃组由于受到胃容积的限制,肺功能减损相对较少。因此管状胃代食管应用于食管癌手术可以减少对肺功能的不良影响[27-28],减少术后并发症。然而本研究全胃代食管后吻合口位置相对较低,占据胸腔内空间较小,大部分胃在腹腔,因此其管状胃的优势不能体现。
从外形上看,管状胃相对狭长,更接近食管形态,置于纵隔食管床空间,在保证食物顺利通过的同时还可以减少胃的容积,限制胃扩张,有利于胃排空。此外,管状胃重建食管较传统全胃代食管明显缩小了胃的体积,使得胃容积减少,胃酸分泌相对降低,能够有效地减少无张力性胃扩张,保持幽门松驰,降低术后胃扩张和胃潴留的发生。从而有效地预防胸胃综合征、反流性食管炎及胃排空延迟的发生,改善了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本研究表明虽然近3个月未能体现出管状胃优势,但在术后半年至1年体现出明显优势,患者生活质量明显改善。
综上所述,对于食管下段癌患者,管状胃代食管的近期疗效无明显优势,但术后半年的生活质量仍明显优于全胃代食管。
利益冲突:无
作者贡献声明
王会恩:设计研究方案,实施研究过程,论文撰写,实施研究过程,论文审核;薛文飞、赵庆涛:实施研究过程,资料搜集整理,论文修改;于雷、王志康、谷建琦、段国辰:进行统计学分析